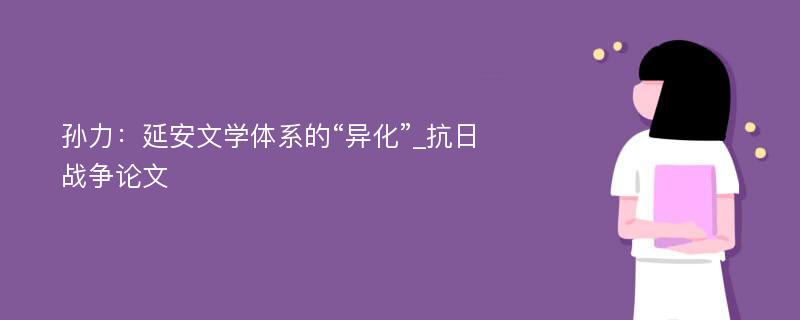
孙犁: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体制论文,孙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4)06-0058-11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作家的文学活动发生了重大转折。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导,解放区逐步确立了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制度,生活在解放区的作家的文学活动被逐步纳入了文学制度的规范之中,成为延安文学体制的自觉建构者。然而,孙犁并没有主动迎合延安文学体制对自己文学行为的规范,一直“像个散兵”[1]一样“游离于主流文化的话语中心”[2]。孙犁文学行为上的“另类”选择,固然有其精神方式和人格心理等个人因素。然而,当我们把孙犁的“另类”选择与延安文学体制的形成联系起来考察时,便会发现孙犁的“另类”选择其实是对延安文学体制的有意“疏离”。孙犁在文学行为上的特殊选择既与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矛盾性有关,也根源于其“伦理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正是在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过程中,孙犁既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另类”文学世界,也造成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孤独和苦闷。 一、暧昧的“公家人”身份 1938年春天,在同学和好友的鼓动下,孙犁放弃了自己正在从事的已有一年教龄的小学教师职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中地方抗日武装,成为解放区民主政权中的“公家人”。所谓“公家人”,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苏维埃政府为缓解战争状态下物资的匮乏而实行的供给制的享受者,他们主要是指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政党、政府、军队中的工作人员,是解放区地位和待遇特殊的“干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享受供给制的人员遍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整个解放区的党政军等各级部门,形成了特殊的“公家人”群体。随着延安成为充满着“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3]的“圣城”,大量的国统区知识分子作家来到解放区,纷纷加入了“公家人”的行列。[4]对于刚刚来到解放区的国统区知识分子作家来说,解放区的“供给制”生活显得相当“特殊”: 初到延安,什么都是新鲜的。……在招待所的第二天,领来一套灰布棉袄、裤,一双棉鞋。听工作人员说这些都不用给钱,是公家发的,而且每年发一套单的一套棉的。还有每月发五元钱边区纸币,可以自己买牙膏、肥皂用。从此,“公家”两个字印入我的脑海。我们过着供给制的生活,衣、食、住都不用自己筹划。没有工资,只有五元津贴费。大家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倒也很省心。[5] 这里吃饭穿衣全是供给制,吃得虽然不像成都那样两荤两素,但菜足饭饱,也大大超过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这里的衣服,里里外外全是军装,床上被褥、洗漱用具全是八路军战士的军用品,一人一份,一律平等。[6] 毫无疑问,国统区的物质生活资源要比解放区的供给制生活优裕得多。但是,解放区的供给制生活也有其独特性:它是由解放区的边区政府统一分配的,所有的人都按照同样的标准;它虽然只能满足基本的“菜足饭饱”,但是解决了知识分子作家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是“很省心”的;享受供给制的“公家人”生活“超过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它是解放区普通民众付出巨大的牺牲换来的,解放区普通民众是非常“羡慕”的。正是这种可以提供基本保障的供给制生活,为那些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创造了一种“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7]的特有环境,也形成了延安的“公家人”队伍中特有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体。 让解放区普通民众“羡慕”的不仅是这些知识分子作家个人拥有较为稳定的物质生活,而且他们往往是解放区各级党政军部门的负责人,其家庭成员也都可以享受“供给制”带来的好处。尤其对于那些生活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作家来说,他们还会时常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照顾。草明从上海来到延安后,一直为孩子不能进入中央托儿所而烦恼。然而,当毛泽东听说草明的困难后,事情马上就得到了解决:“毛泽东主席即找服务员请傅连暲大夫来。傅连暲大夫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他是杨家岭中央机关的保健大夫,他也曾给我们文抗的作家看病,所以我认得他。当下毛主席请他解决我的小儿子欧阳加入托的问题。因为他正管得着中央托儿所。我再次站起身来表示感谢他。毛泽东主席又吩咐他的秘书叶子龙同志,用他的名义给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写信,请他介绍我的两个女儿欧阳代娜、欧阳天娜到干部子弟学校入学。毛主席在信上签了名。”[8]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作家都像草明一样受到毛泽东的直接帮助。然而,这些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确实在延安的“公家人”队伍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在延安是“洋包子”,是解放区的“大作家”。[9]他们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批判精神和自由意识,脱离了宗法制规范下的传统家庭羁绊,成为名实相符的“公家人”。 然而,生活在冀中解放区的孙犁就远没有那些来自国统区而又生活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作家那么幸运。尽管孙犁也同样属于“公家人”,但是,孙犁的“公家人”身份在很大程度是有名无实的。他自己甚至是讨厌“公家人”的身份所带来的级别限制,以至于曾经因为有意“毁弃”根据地负责人签署的工作调动介绍信而长时间不能安排工作。[10]孙犁与来自国统区知识分子作家在“公家人”身份上的区别,其实是解放区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身份上的差异。一方面,抗战全面爆发后大量的国统区知识分子作家来到了解放区,他们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民众的欢迎,成为在解放区享受“供给制”的特殊知识分子“公家人”群体。由于他们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成长起来的,更多地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自觉地接受了“公家人”的社会身份带来的现代民主意识。[11]另一方面,生长在解放区而没有接受过“五四”以后现代大学教育的“乡村”知识分子也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成为解放区“土生土长”的“公家人”群体。他们大多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由于长期浸淫在传统的宗法制社会环境中,秉承着传统道德和乡村伦理精神,更倾向于在宗法制社会结构中形成的民间自由意识。他们的社会身份虽然变成了“公家人”,但却在精神结构和文化身份上没有转向“公家人”。因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的延安文学走向体制化的进程中,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作家因为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上的双重“公家人”意识很快就成为延安文学体制的自觉建构者,而以孙犁为代表的“土生土长”的乡村知识分子作家却因为社会身份和文化属性上的矛盾而没有形成统一的“公家人”意识,始终游离于延安文学体制之外。① 对于孙犁来说,从加入冀中地方抗日武装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似乎没有享受过“公家人”带来的任何优越性。当然,孙犁参加革命成为“公家人”是为了拯救沦陷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的家乡和祖国,而“不是为了追求衣食,也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12],更不是为了谋求“领导”的职位而光宗耀祖。正如孙犁后来反思的那样:“我没有能力去一步一步地当个领导啊,或者是下边有拨儿人呀,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在抗战期间也好,在战争期间也好,我都是穿得破破烂烂的,生活很艰苦,搞了那么多年,连匹马都没有骑上,连个自行车都没有。”[13]在冀中敌后开展的宣传工作中,孙犁甚至经常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有时连续几天只能靠酸枣和萝卜充饥,连一顿热饭都吃不上,更不要说那些让解放区普通民众异常“羡慕”的“菜足饭饱”的“公家人”的稳定生活了。[14]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冬天,顺道路过河间的叔父来看望正在下乡的孙犁,当时孙犁正“蹲在炕沿下烧秫秸取暖,弯腰弓背,活像一个叫花子”。[15]叔父看到后什么话也没有说,流着泪默默地走了。至于那种让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倍感“特殊”的“里里外外,全是军装”、“床上被褥,洗漱用具”、“一人一份,一律平等”[16]的延安供给制生活,在冀中解放区奔波的孙犁就从来没有奢望过。在更多的时候,孙犁甚至连日常的御寒蔽体的服装都没有。1939年秋天,孙犁等人从冀中平原调到了中共晋察冀机关所在地的阜平山地进行抗日宣传工作。阜平地区山高气凉,他们仍然身穿单衣,炕上连席子都没有。到了冬天,雁门关外天寒地冻,孙犁因领到的棉衣棉裤太小裹不住手腕脚腕而冻得手足生疮。1944年春天,孙犁在延安之行前领取单衣时因男装已经发完,只好领了带大襟的女装,幸亏有热心的女学生带着剪刀针线及时改成了“大翻领套头衬衫”,要不然孙犁又会没有单衣穿。孙犁就是穿着这样的“奇装异服”,不但在路过兴县时会见了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而且还穿着它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7] 作为身处残酷战争年代的而又经常出入于穷乡僻壤的“文化人”,即使孙犁自己是“公家人”,他在日常生活上的困顿也是司空见惯的。“那里最苦的是文化团体。有的人,在经常活动的地区,找个富裕的农家,认个干娘,生活上就会有些接济。如果再有一个干妹妹,精神上还会有些寄托。我是一个在生活上没有办法的人,一直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中。”[18]对于从小生长在农村的孙犁来说,生活上的这些艰辛其实都是可以忍受的。然而,最令孙犁难以承受的是自己作为独子却无法为处于沦陷区的家庭尽一份责任。孙犁一再说过,“我有很多旧观念”,中国传统的伦理教育和乡村文化环境使“我的旧观念很重”。[19]虽然孙犁在上中学期间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也阅读过一些新文学作品,但是他对农村传统的人伦习俗是认同的,16岁时他就依照父母之命与一位没有上过学的女子成婚。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成家就意味着必须挑起家庭的重担。然而,孙犁在民族战争的感召下参加了革命队伍,变成了“公家人”。因此,他不可能再留在家中,只能跟随革命队伍奔波于各个解放区。孙犁虽然是“公家人”,但是他不可能像生活在延安的那些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一样,将自己的亲人带在身边,使他们也成为“公家人”。孙犁必须离开家乡,远离亲人,让妻子在家中独自照料父母和孩子。战争阻断了交通,而孙犁又忙于宣传任务,很少有回家看望亲人的机会。1943年秋天,正在华北联合大学教书的孙犁接到了别人辗转带来的家中消息,让孙犁难以承受的是12岁的大儿子由于缺医少药已经在半年前夭折了。同样,孙犁在接到父亲生病的消息赶回老家后不多几天父亲就去世了,而他依照传统的孝道观念想为父亲立碑的愿望也因家乡开始的土改运动而未能如愿。这些事情都是作为“公家人”的孙犁终身引以为憾的。所以,有研究者说孙犁“是一名无悔的战士,一个有悔的人子、人夫、人父”[20],这大概是不错的。孙犁虽然可以毫不在意“公家人”身份带来的好处,但是“公家人”身份上的矛盾显然一直在强化着他的内心痛苦,并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自己对解放区文艺政策的态度。 如果孙犁一直生活在冀中解放区,那么他也许会认为从事抗战宣传的“公家人”都会和他所在的冀中解放区一样,不但生活历经艰辛而且精神充满苦闷。然而,1944年春天的“延安之行”使他对“公家人”的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在冒着生命危险经历了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孙犁终于踏上了陕西地界。与长期的民族战争导致的冀中解放区的破败不同,陕北不仅农村的“自然风光很好”,而且县城的房屋街道“完整安宁”。孙犁最初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做研究生,后因《荷花淀》《芦花荡》等小说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后名气大增而被提升为教员。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当教员期间,孙犁真正体验了只有“公家人”才有资格“享受”的延安“供给制”生活:每人一孔小窑洞,“内立四木桩,搭板为床,冬季木炭一大捆,很温暖”;窑洞里有“青釉瓷罐一,可打开水。大砂锅一,可热饭,也有用它洗脸的。水房、食堂,均在山下。”在延安“经常吃到牛羊肉,主食为糜子”,这在冀中解放区是根本没有“福气”和条件享受的。刚到延安时,“正值大整风以后,学院表面,似很沉寂。原有人员,多照料小孩,或在窑洞前晒太阳。黄昏,常在广场跳舞,鲁艺乐队甚佳。敌后来了很多人,艺术活动多了。排练《白毛女》,似根据邵子南的故事。”[21]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孙犁的身份从研究生转为教员后,他的生活待遇也发生了变化,由“吃大灶”改为“吃小灶”,并且可以带家眷。生活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员都带有家眷,而唯独孙犁只是单身一人,沙可夫提出让孙犁将家眷接来延安。然而,沙可夫哪里知道,“无论关山阻隔,小儿女拖累,父母年老,即家庭亦离她不开。”[22]在延安的一年多时间里,孙犁一直独自生活,直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冀中解放区才得以与家人团聚。 从冀中到延安,再从延安到冀中,虽然孙犁的“公家人”的社会身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地域环境的转移带来的却是文化空间的变更,由此带来了孙犁对“公家人”的文化身份的重新认识。从延安回到冀中解放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孙犁的情绪变得相当低落。在给田间的信中孙犁这样说:“从去年回来,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虑,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这是很不应该的,因此也就越痛苦。”[23]孙犁也试图“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文墨生涯”[24],但是一直没有从苦闷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探究其中的原因,似乎与孙犁对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矛盾心态不无关系。从社会身份上来说,孙犁当然是“公家人”。然而,从文化身份上来看,孙犁显然是游离于“公家人”之外的,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逐渐形成的以政党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即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孙犁并没有进入到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公家人”的主流意识形态规范之中,他的“公家人”身份与其个人意识一直是矛盾的。 二、游离于文艺政策的边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合法化,解放区的文学因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而逐渐走向了体制化,并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形成了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文艺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延安文学体制的基本形成,生活在解放区的作家大多数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建构者。然而,作为“公家人”的孙犁不但没有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建构保持同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游离于解放区的文艺政策之外的。 孙犁对解放区文艺政策的游离姿态并不是从他参加冀中地方抗日武装的那一天开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转化的过程。以1944年春天的“延安之行”为分界线,孙犁对解放区的文艺政策经过了从“跟随”到“疏离”的态度上的转折。在离开冀中解放区以前,孙犁紧紧“跟随”和“响应”抗日的民族号角和时代要求,全身心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服务。因为,在孙犁看来,“从一九三七年的抗日开始,我经历了我们国家不同寻常的时代,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有幸当一名不太出色的战士和作家。”[25]在全民抗战的“伟大的时代”里,孙犁为了“抗日”而参加了革命工作,“教书、编报、写文章”。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孙犁是“成不了一个什么作家”[26]的,“抗日”是孙犁参加革命工作的出发点,是他在冀中解放区进行文化宣传和从事文学活动的思想中心。正如孙犁自己所说,这个阶段文学运动的“基本路线”是“抗日的内容,和大众化的形式”。[27]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整个解放区并没有明确而具体的文艺政策。对于孙犁来说,能够参与到为“抗日”而尽责的文化宣传和文艺运动中也就意味着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学主张的积极“响应”。 既然是为“抗日”而工作,所以孙犁没有囿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而继承“父亲的那点财产”,而是毫无怨言地离开了需要自己全力支撑的家庭,加入了“为抗日而文学”的宣传队伍,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28]的道路,成为一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武装力量服务的“公家人”。1938年初春,在孙犁成为“公家人”伊始,他就按照冀中人民自卫军政治部的要求,在家中赶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作为随军宣传材料油印发行。编写《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主要是为了配合冀中解放区正在创建中的各种戏剧团体,为这些没有多少戏剧表演经验的剧团提供宣传和演出上的帮助。因此,这本小册子特别强调戏剧“用活人来表现”和“最大众化”的特点。因为是在战争状态下开展戏剧活动的,所以这类剧团“应该是轻便的、敏捷的、移动的”,应当用“最简单、最乡土化、最明确的对话”,演出“前方作战,或是打汉奸”的“抗日的题材”作品。[29]1938年秋天,孙犁来到了冀中解放区新成立的抗战学院,为学院招收的青年学生讲授“抗战文艺的理论与实际”、“文学概论和文艺思潮”等课程,并重点介绍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便推进文学与抗战的结合。在国家沦陷的灾难岁月里,孙犁急迫地实践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文学为抗战服务的主张,以至于因为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教学和文化宣传活动不能直接为前线的战士服务而感到遗憾:“不管我怎样想把文艺和抗战联系起来,这些文艺理论上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和操场上的实弹射击,冲锋陷阵,投手榴弹,很不相称。”[30]因此,数月后孙犁趁抗战学院解散之际,带领一个流动剧团下乡演出,为解放区的“抗日”活动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剧团的演出活动采取“现编现演,剧情就是身边的生活事变,常常才挂上幕布,因有敌情又拆下来到别村去演。演员着戏装化妆转移,是常有的事。”[31]这个剧团的流动演出活动一直持续到被编入吕正操领导的冀中区八路军直属队为至。 随着解放区革命武装力量的走向正规化,孙犁的工作对象逐渐转向了晋察冀地区的八路军部队。面对经常与日本侵略者厮杀的八路军战士,孙犁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像英勇的士兵一样出现在战斗的前线。然而,孙犁只“是一名文士,不是一名战士”[32],他只能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为前线的士兵服务。1939年春天,孙犁来到了河北最为贫困的阜平地区,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晋察冀通讯社。这里是中共晋察冀解放区的机关所在地,聚集了很多“公家人”,其中不少是“文化人”。晋察冀通讯社是应中共中央加强解放区新闻报道工作的要求成立的,各分区、县区都设有专门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干事。孙犁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各地的通讯员写信,为他们寄来的通讯稿件提出修改意见。由于从各县区和部队寄来的通讯稿件质量太差,孙犁和通讯社的其他人决定编写一本指导通讯写作的书籍,这就是由孙犁执笔“集体写作”的名为《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小册子。孙犁从通讯的定义入手,概略地介绍了通讯员的素质要求、新闻采访的主要方法和通讯写作的基本规范等问题,主张通讯员要“站在民族解放战斗的行列里”,成为“大军的尖兵”,“把抗战的每一个细微,向全国的人民报告,向全人类报告。”[33]这并不是一本简单地介绍通讯写作技巧的“小书”,而是包容着编写者浓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公家人”责任感的“大书”。也正是此时的记者和编辑生活经历,逐渐养成了孙犁的文学写作意识,“经常写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见闻,有所感触,立刻就发表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34]为“抗日”的要求而艰苦工作,为苦难的民族而尽着一个“公家人”的职责。这就是孙犁从事文化活动的基本心态,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要求而服务。但是,苦难的生活为孙犁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契机,创造了“良好的创作状态,在最自由、最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收获到他该收获的东西”。[35]一方面,作为“公家人”,孙犁为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尽心尽责。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人”,孙犁被生活中“小石块”所碰撞,结出了第一批创作的果实,这大概也是他自己所没有想到的。 在为解放区开展的“抗日”文艺运动奔忙过程中,最引孙犁重视的宣传任务之一是《冀中一日》的编辑。由于高尔基主编的《世界一日》和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的启示,冀中解放区党政负责人决定通过编辑《冀中一日》来“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36]《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开始于1941年4月,当年秋天孙犁返回冀中解放区后加入了《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虽然此时《冀中一日》的编辑已经进入定稿阶段,但是孙犁仍然以少有的热情加工润色了每一篇稿子。在读稿过程中,孙犁感受到了遍及冀中解放区的这场“集体写作”是“一次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运动与人民的实际斗争结合”[37],引起了普通民众对民族战争的关注,也点燃了普通民众对文艺的热情。对于孙犁来说,编辑《冀中一日》的“另一副产品”就是根据“看稿的心得”写作的一本被人们称为“文学入门之类的书”——《文艺学习》。针对普通民众文化水平非常低下的状况,孙犁写作《文艺学习》时“拟定了三个方针:一是通俗;二是边区现实;三是偏重‘怎样做’,不是文学概论,主要对象是在这次《冀中一日》发表了作品的人们。”[38]因此,《文艺学习》的写作注重“写作问题上的引导和启发”,而不是纯粹文学理论上的理性阐释。孙犁以《冀中一日》的入选作品为例证,介绍了文学写作的描写方法、语言运用、材料组织、题材选择、主题提炼等问题,强调了“民主和抗战”的现实作为“最有价值的作品的主题”的重要性。[39]在全面抗战的现实环境中,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作品应当通俗,但是,通俗问题的根本是作家要有“新的生活内容,新的生活认识”,“实际生活会解决了通俗问题。”[40]正是孙犁写作上的现实针对性,决定了《文艺学习》是一本能够为解放区的文艺政策服务的“实用教材”。《文艺学习》完成后,分别以《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怎样写作》等名称在八路军冀中三纵队的《连队文艺》、晋察冀边区文协的《边区文化》等刊物上连载,推动了冀中解放区的群众文艺运动的发展。 1943年春天,当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到晋察冀解放区时,孙犁也从冀中八路军部队来到了晋察冀文协。经过整风学习后,晋察冀解放区作家“与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小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主义倾向”和“‘艺术指导政治’与‘化大众’的理论”[41]得到了清除,以“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得到了确立。在文艺工作者的下乡潮流中,孙犁因要求下乡的请求没有批准而被调整到了《晋察冀日报》社,不久后又去华北联合大学任国文教员,一直任教到1944年春天去延安。 延安之行归来后,孙犁并没有返回华北联合大学,而是主动要求回到了冀中解放区。此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解放区文艺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形态所取代,“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利用各种方式逐渐推进,群众文艺运动成为解放区作家从事文学活动的核心。正当解放区的作家在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全面实施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孙犁却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虽然孙犁的身份是“公家人”,但总是为“公家人”所苦恼:“所苦恼者,咱在冀中也成了‘名流’,有生人来,要去陪着,开什么会,要去参加,有什么事,要签名。我是疏忽惯了的,常自觉闹出了欠妥之处,烦扰得很。”[42]也就是说,作为“公家人”,孙犁觉得各种社会活动太多,严重干扰了自己的创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孙犁虽然是在解放区文学体制内从事文学活动的,但是他把文学活动的重心放在了自己喜欢的小说创作上,并没有对解放区文艺政策规范下正在兴起的农村文艺运动表现出特别的热情。1946夏天,孙犁应邀参加了冀中文协等九个部门发起的“冀中抗战八年写作运动”委员会,并对类似于“冀中一日”的这场群众性集体写作运动信心十足。因为,“冀中八年写作运动,规模很大,人们的信心也坚”,“会比冀中一日再好些,可涌现大量新人材”。[43]然而,父亲的去世很快打消了孙犁已经聚焦起来的热情,而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则中断了这场集体写作运动。随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合并,新的文艺机构相继成立。然而,孙犁并不喜欢参与文艺社团的活动,对一些新成立的文艺机构的邀请没有多少主动性。因为,“文人宜散不宜聚,聚则易生派别,有派别必起纷争”。所以,孙犁“虽然一直在这个队伍中,但我的心情并不太爱好这个集体,身处其中,内心若即若离。”[44]但是,在解放区文学走向体制化的过程中,文艺社团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部门,放弃文艺社团的活动也就意味着远离了解放区文艺政策的要求。[45]1948年秋天,孙犁作为冀中文协的代表参加了新成立的华北文艺界协会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从延安撤离出来没有去东北的重要作家都参加了会议。然而,在孙犁看来,这次会议却是“参加者寥寥”。[46]自从回到冀中解放区以后,孙犁连续不断地遭遇了冀中文协的批评家对自己作品的批判。虽然引起批判的主要是“某些社会性原因”[47],但是也严重影响了孙犁参与群众文艺运动的积极性。在很多时候,孙犁对解放区文艺社团的态度表现得很消极,采取的是“在而不爱”的姿态。因此,在华北文艺会议上,“有人提出我的作品曾受批评,为之不平。我默然。有意识正确的同志说:冀中的批评,也可能有道理。我亦默然。”[48]当然,孙犁不会公开辩解,最多也只是在信中向关系要好的朋友发发牢骚而已。② 在孙犁的“公家人”生涯中,1948年秋天是要特别提及的。因为,这年的9月,中共冀中区委决定让孙犁担任中共深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包括乡艺运动”,孙犁自己也想借此“发动和检阅一下沉寂良久的乡村艺术”。[49]此时,解放区的群众文艺运动已经进入了如火如荼的阶段,一方面,是集体写作运动的全面开花。另一方面,是农村剧团的火热演出。其实,早在1945年底,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就做出了《关于阜平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的决定》,要求“各系统各级宣教部门及剧团等文艺组织,特别是领导机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组织群众文化生活。”[50]冀中行政公署和冀中文协按照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决定于1946年春天启动了冀中解放区的乡村文艺运动,将护持寺村剧团确定为“实践和发展《穷人乐》方向的范例”,要求全冀中的乡村剧团学习护持寺村剧团“创造自己所需要所喜欢的戏剧”、“由本村人来演”和“集体导演的创造方法”,“把文艺活动(从搜集材料到演出)和群众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文艺活动的过程,就是了解村中的问题,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51]孙犁一生比较喜欢戏剧,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从不会放弃去戏院欣赏戏剧。应该说,如果孙犁尽心尽力而为,他是能够将深县的以戏剧演出为中心的乡村文艺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而且,推动以农村剧团演出为中心的乡村文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重要内容,让农村剧团走向全面繁荣就是在文艺政策上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然而,孙犁任职后并没有将他所在的深县乡村文艺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在冀中行政公署管辖的六七个区县中,孙犁所在的深县成立的农村剧团的数量是最少的。因为,孙犁内心里觉得虽然“任宣传副部长,但在形式上仍系客串性质,因我吃穿,还是冀中文联供给。”[52]尽管客观上孙犁认为当宣传部副部长可以“学做一些文章以外的实际工作,藉以锻炼自己一些能力。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文墨生涯,对我日渐衰弱的身体,也有好处。”然而,在主观意识里,孙犁觉得自己“任‘副职’”是上级为了“照顾‘创作’”[53],因而他也就放弃了推动乡村文艺运动的主动性。事实上,在深县任职期间,深县政府的机关工作人员虽“多系工农干部,对我也还谅解。”孙犁自己也确实是“一不过问工作,二烟酒不分,三平日说说笑笑”。[54]没有像自己的好友王林、康濯那样积极参与到冀中解放区的乡村文艺运动中,“更没有起过先锋带头作用,建树较大功劳”。[55]他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小说创作,没有写过一篇关于乡村文艺运动的理论文章,倒是写出了《光荣》《浇园》《采蒲台》《种谷的人》等小说作品。[56]一旦有了空闲,孙犁要么“与深县中学诸老师游”,要么“经常回家”。[57]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孙犁没有尽到负责“乡村文艺运动”的宣传部副部长的职责。然而,孙犁似乎对这种远离解放区文艺政策规范的“自由”生活比较感兴趣,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天津解放中共冀中区党委要求进城才结束。孙犁担任的是主管乡村文艺运动的宣传部副部长,开展的却是具有强烈个人性的小说创作活动,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要求保持了相当远的距离,这样的文学行为不正是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吗? 三、现实主义的“伦理化” 如果说“公家人”的暧昧身份使孙犁“像个散兵”一样,在文学行为上不愿参与到解放区文艺社团的活动中,从而远离了解放区的文艺政策,让自己变成了解放区作家中的“另类”的话。那么,促使孙犁做出这种选择的更为内在的原因则是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确立。与解放区政党意识形态规范下的现实主义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同,孙犁的现实主义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把人的生活作为现实主义的中心,由此形成了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伦理化”内涵。正是在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过程中,孙犁看到了解放区文艺政策的缺陷,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创作没有成为单纯的政党意识形态的载体。 以1944年春天的延安之行为分界线,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经历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在离开冀中解放区以前,由于全民抗战的时代要求,孙犁以“公家人”的身份投入到文化“抗日”的洪流中,并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独立的文学观。在民族灾难面前,孙犁当然明白文学应当扮演的角色和需要承担的任务:“一个文艺工作者要走向敌占区游击区,深入体验领会,突击写作”,“文艺工作的责任是帮助我们的武装和人民的对敌人汉奸的种种以退为进,小与大夺,出奇制胜的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方法是能够及时地深刻地绘影绘形地反映这些斗争的各种特点、各种现象。”[58]可以说,全民族遭遇的战争让所有的解放区作家都成为民族救亡的宣传员,让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成为前线杀敌的宣传品。在刚刚加入冀中地方革命武装力量的一段时间里,孙犁对此并没有产生过怀疑。“我们都是爱好文学艺术,从而走进革命的队伍,这可以说是为革命而文学,也可以说是为文学而革命。”[59]他和冀中解放区的其他“文化人”一样,以笔为枪,驰骋在祖国的土地上,“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正如孙犁后来所回忆: 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地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60] 此时的孙犁,对自己从事的文学活动“不存任何顾虑”,完全是以“一个战士”而不是“一个文士”[61]的形象,酣畅淋漓地发挥着文学的宣传功能,尽着自己的“公家人”的责任。因为,“那时候,引导作家们写作的,就是这些鲜明而有号召力的政治目标”。[62]在“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时,孙犁的文学行为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持续不断的战争逐渐引发了孙犁对文学功能的重新思考。在抗战初期全民动员的时代浪潮中,文学毫无疑义地充当了民族救亡的急先锋,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宣传作用。但是,文学不能总是充当战争的宣传工具,作家不能总是扮演简单的“传声筒”,而应当通过发挥文学的特殊性来提升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精神力量。因此,孙犁认为: “传声筒”也不是一概可以抹杀的,如果真能把时代的声音播送给读者,起码是不能使时代的音响经过你的口腔,减弱或变更了声音的色调。而最能防止这个失败的,则莫过于把自己造成一个质地优良的传声筒。 同在春天,有燕子叫唤,也有乌鸦叫唤;同在夜晚,有夜莺也有枭鸟。在他们同是歌唱,是要人愉快赏识的,但我们听来感觉不同,基本上还是那个嗓子的质地的问题。[63] 在战争年代里,文学成为一种工具,作家成为一种“传声筒”,这是没有人会反对的,解放区的文学运动也是如此发展起来的。然而,如何使成为工具的文学能够展现出美的品格,使成为“传声筒”的作家能够在创作中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悲欢离合”,展现“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这大概是很少有人关注的。但是,孙犁却在认真地思考着。他从解放区作家所普遍认同的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入手,看到了“生活”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文学是反映现实生活并且推动现实生活前进的,作者如果没有生活,自然就谈不到创作了”,“有时我们常常抽象地谈艺术的政治性,或是文学的艺术性,反倒把生活性忘记了。没有丰富的切实生活经历,政治性和艺术性都不能产生。”[64]所以,孙犁提出,文学反映时代是很自然的,“作家应是主动的,自觉的,没有任何游离的”,有时“政治上的要求过于具体繁琐”反而会限制文学“反映时代的精神”。[65]虽然文学摆脱不了政治的限制,“政治永远不会忘怀文艺,文艺也不会忘怀政治”,政治与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固定,非常自然的关系”。[66]但是,从文学的“生活性”出发,“写作最好离政治远一点”。[67]因为,“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这样,文艺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里面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68]可以看出,孙犁对“生活性”的强调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这也是孙犁常常远离文艺社团的集体活动的内在原因之一。 延安之行使孙犁暂时远离了战争对自己创作的直接影响,他可以在更为平和的心态下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终建构起以“伦理化”为中心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并进而导致他对解放区文艺政策的疏离姿态。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孙犁先是作为研究生一边接受培训,一边继续创作,陆续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69]的《荷花淀》《芦花荡》等小说。不久后,孙犁被提升为文学系教员,专门讲授《红楼梦》。以《红楼梦》的讲授为契机,孙犁将在冀中解放区开始关注的现实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进一步做了系统化的思考。在孙犁看来,《红楼梦》“决非出世的书,而是入世的书,是为人生的书”[70],“它的主题思想,是热望解放人生,解放个性”[71],也就是“批判人性、解放人性,发扬人性之美。”[72]这一系列观念,都是在与文学系主任舒群的论争中产生的: 什么是《红楼梦》表现的主题思想呢?看惯了一些公式概念文章,脑筋里有一套陈腐的观念的人,反会在这一部作品面前,彷徨四顾,不知所答。而那些红学家们也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一问题。十年前,我们在延安窑洞里讨论这一问题,当时我粗浅地认为:曹雪芹的思想,主要是通过贾宝玉来表达。因这我想:在创作过程中,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只能通过他肯定的人物的言行表示他赞成的方面;通过他否定的人物的言行,表达他反对的方面。我认为贾宝玉是作者肯定的人物。[73] 表面来看,孙犁谈论的是《红楼梦》的“主题思想”问题,其实孙犁是想通过《红楼梦》反思现实主义的本质问题。只有从现实主义的本质要求出发,才能发现《红楼梦》的真正价值。[74]或者说,只有通过《红楼梦》这部经典,才能真正发现现实主义的本质。因为,《红楼梦》是曹雪芹思想成熟和确定时创作的,“成熟和确定的思想要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因为在艺术创作里,越是现实主义的方法,便越能表达明确的思想,只有高度的现实主义,才能保证高度思想性的体现。”[75]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是与作家的人生经验、社会风尚、家族制度、文化教育等联系在一起的,而绝不是简单地迎合时代的政治要求。或者说,一个时代的政治要求是隐藏在现实主义的艺术展现中,而不是表面上对政党意识形态的总体认同。所以,孙犁说:“现实主义的最大功能,是能在深刻广阔地反映社会现实之外,常常透露一种明智的政治预见。”[76]文学虽然摆脱不了政治的要求,但是文学活动的中心是文学本身,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才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出发点。 既然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根本,那么在具体创作中又将如何处理“生活”问题呢?所谓“生活”,就是“人生”。孙犁说:“在青年,甚至在幼年的时候,我就感到文艺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人生的,应该使生活美好、进步、幸福的。”虽然现实的生活,“所谓人生,很复杂,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是真善美和假恶丑并存的。但是,真善美是生活的本质,是人生的根本,文学就是要表现真善美的东西。因为,“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幼年时,我们认为文学是追求真善美的,宣扬真善美的。我们参加革命,不是也为的这些东西吗?”[77]真善美的东西往往是充满了理想的,文学追求真善美就是要“美化人生,充实人生,完善人生”。[78]然而,现实主义文学所张扬的真善美绝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应该是面对整个人生,对时代负责”[79],“真实地传达出现实生活,或者说是现代生活的情趣”。[80]其实,孙犁在这里强调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日常性”问题。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要关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因为,文学“既是写社会,写家庭,写人情,就离不开伦理的描写。”[81]由此,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最终落实到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问题上,他的小说也往往注重夫妻、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描写,表现中国传统伦理的价值取向。 当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走向“伦理化”以后,他很自然地就以基于“人的本性”的人道主义作为自己从事文学活动的基础,而不是将自己的文学行为囿于主流意识形态规范下的文艺政策。因为,在孙犁看来,“任何民族,因为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说是生活的总结,形成了本民族的道德观念,用这一道德观念,去评论是非,维系人心,保持民族的团结,保证民族的发展。这种道德观念,反映到政治上,当然也反映到文学上。”[82]在这里,孙犁将文学创作的“伦理化”功能明确置于政治规范之上,强调了作家的伦理追求的重要性。所以,孙犁提出: 文学艺术,除去给人美的感受外,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教育手段,即为了加强和发展人类的道德观念而存在。文学作品不只反映现实,而是要改善人类的道德观念,发扬一种理想,所以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83] 因为文学是以人为出发点的,利用文学当然可以促进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念的完善。现实主义又因与一个民族的现实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因而是更具人道主义精神的。孙犁说:“所谓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当然不是庸俗的普度众生,也不是惩恶劝善。它指的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了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比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希望有所扬弃。”正是由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广泛而深刻地关注和思考人类的现实生存状态,因而,“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84]然而,解放区的文学体制建构却受政党意识形态的规范,是远离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在精神的,解放区的作家也因此很难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所以,当孙犁离开延安返回冀中解放区后,面对正在全面推行的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解放区文艺政策时,他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和无奈。无论是以乡村剧团建设为中心开展的农村文艺运动,还是以真人真事写作为中心倡导的集体写作潮流,孙犁都表现出了“若即若离”的“在而不爱”[85]复杂心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犁终其一生都是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 注释: ①关于“公家人”的身份问题,赵树理的遭际与孙犁比较类似,他们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上矛盾性,在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乡村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性。 ②孙犁在1946年7月31日致康濯的信中说:“我觉得他(指批评者)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过于严重,老兄知道,咱就怕严重,例如什么‘读者不禁要问:这是真实的吗?’我不是读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离我家五里路的地方。”(《孙犁全集》(第8卷),第2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 孙犁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供给制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