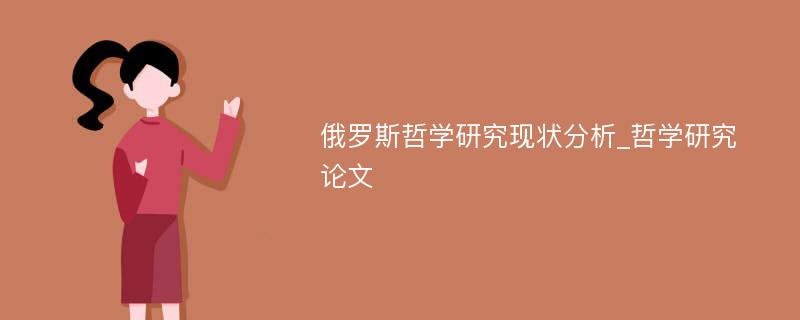
万花纷谢一时稀——俄罗斯哲学研究现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现状分析论文,哲学论文,万花纷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解体后的几年间,俄罗斯的哲学研究于混乱中呈现出一些特征,于纷杂中显示出一些线索。概括、分析这一特定领域的现象与走向,对于研究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总结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不无裨益。
一、哲学地位显著下降
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前苏联曾处于至高无上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这往往与国家政治、经济等重大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政权出台新的策略往往要求它作出理论上的论证,社会也表达了对它的迫切要求。在前苏联拥有众多的哲学系和哲学研究机构,哲学工作者队伍极为庞大,哲学类出版物数量繁多。从哲学史上看,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能在一个政权的维护下达到如此至尊的地位应当说是绝无仅有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声浪叠起,崇尚多元却陷入了茫无头绪的境地,百家争鸣但失却了大体均可认同的学科特征与应当遵循的学术规范。哲学的历史地位受到猛烈冲击,其存在的合法性与价值也受到普遍怀疑。先是官方政权不再给予支持,研究经费锐减,各级党校停办。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哲学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招生困难,教师流失严重,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人员减少到原有的1/3弱。接着,在国家最有影响的报纸上,竟多次发表权威人文科学院士有关解散哲学研究机构的呼吁。①哲学专业刊物只剩下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办的《哲学问题》,因经费不足,该刊已屡次在“致读者”中表达了难以为继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工作者队伍出现了三重分化;或者从哲学理论研究转向哲学史、哲学应用研究;或者由哲学研究转向历史、文学、社会学或其他实证科学研究;或者改变学者身份,抛弃学术研究,改行去从事其他实际工作。这直接导致了哲学研究水平的下降。同样是代表国家级水平的教科书,1993年由B·斯杰平主编的《哲学教学大纲》(供高校教师进修班用)较之1989年弗罗洛夫主编的《哲学导论》,不仅篇幅少得多,质量也不可相比。联想到哲学在苏联曾有过的辉煌地位,今天的情形用“一落千丈”来形容实不为过分。请听有关描述:“环顾四周,我们看到的是存在主义和哲学解释学的终结、实证主义的贫困和马克思主义的悲惨失败”。②这种论调与情绪充斥当今俄罗斯哲学论坛。
哲学研究在今日俄罗斯跃至这种地步,事出有因。首先从哲学本身的学科特点与社会功能看,它既不象苏联哲学界认定的那样威力巨大,也不似今天俄罗斯有的论者认为这样价值全无。二者都不是对哲学应有的公正态度,偏离了哲学的本性。事实上,从元哲学意义上讲,哲学不过是表达人们对世界的一种系统的看法,追求的是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它的功能渗透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并不能立竿见影、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其次,现今的俄罗斯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群众都普遍存在一种误解,即把过去苏联对哲学的曲解当成了哲学本身,把这种歪曲造成的不良后果算到哲学头上,因而就可以无视它甚至抛弃它。再者,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大环境看,整个社会已超出“坐而论道”的理论争论时期,实践理性已取代理论理性的重要位置,作为现实政治注角或宣传工具的哲学就显得不重要了。置身私有化、市场化大潮之中的广大民众,已经把全部兴趣投放到物质利益的获取上,投放到职业和地位的重新确立上了。在这种价值取向上,不能带来实利的哲学自然失却了感召力,失去了理论的轰动效应,被抛到了生活大潮背后,遭到被冷落甚而否定的命运。
二、与西方哲学接轨
苏联哲学界对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尽管曾存在某种程度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但批判性却是其重要特色。多数研究者不为西方学者的自我表白所迷惑,而是深入到学派与思潮内部,条分缕析,揭示出其固有的本质。他们的研究路子一般是:先考察研究对象的理论核心与认识论内容,然后确定其在该学派或思潮中的地位,也就是它与“过去的前辈和现在的战友”③的关系;最后从哲学上的党派斗争的表现来考察研究对象的哲学构思,把哲学体系引导到逻辑终点。正因为如此,苏联的西方哲学研究常常发人所未发,与西方表现出不同的看法并且对各种怪论给予应有的回击。这种理论个性赢得了世界声誉。在法国国际哲学协会主席、著名现象学家和解释学家保罗·科利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哲学主要趋向》时,奥伊则尔曼等哲学家应邀参加讨论与撰稿,他们执笔的内容有的就是西方哲学部分,这充分表明了对他们研究工作的重视和所取得的成果的承认。
现在俄罗斯哲学界抛弃了70年来的研究传统与优势,尽量与西方哲学接轨,重复西方哲学家的表述,有时连用语都一致,已提不出针锋相对的见地与批评。以B.斯杰平主持撰写的《哲学教学大纲》为例,这部被视为俄罗斯新哲学端倪(或萌芽)的教科书,共分5个部分:(1)哲学史;(2)社会哲学;(3)认识论与认识科学;(4)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5)逻辑与分析哲学。从这个目次上看该书呈现出如下特点:(1)原理性阐释、体系性建构被一般西方哲学的历史性介绍所代替,表明俄罗斯哲学界摧毁了旧的哲学世界后尚无力营造新的哲学大厦,只好拾人牙慧;(2)编写者倾向于个人主观嗜好,追随西方科学主义,把探讨个人体验,追索人生答案的人文主义的哲学排斥在体系之外,表现出极大的偏颇;(3)切断现行哲学与苏联70年传统的内在关联,因这一问题棘手而付之阙如,干脆予以避回。
曾以研究语言哲学著称的H·B奥孔斯基前后观点的改变,比较典型地反映出目前俄罗斯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态度。在七、八十年代,奥孔斯基曾出版过几部评述西方语言哲学的专著,比如《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研究》、《语言与语言哲学》等,书中对西方哲学走向语言分析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无论是日常语言学派还是人工语言学派,都是抬高语言学而贬低哲学,甚至企图用语言学代替哲学。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质上的差别:(1)在哲学对象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应把自然、社会、思想三大领域的一般规律纳入研究视域,而西方语言哲学则只研究语言问题;(2)哲学基本问题应是思维与存在能否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的问题,而西方语言哲学认为是语言分析与表达的问题;(3)哲学的任务应是以世界观与方法论去武装人的头脑,而语言哲学则认为是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4)哲学的目的应是改造客观世界从而也改造主观世界,而语言哲学则认为是创造理想的语言系统或明确日常语言的用法与含义。在作了上述对比之后,奥孔斯基认为,西方语言哲学从根本上“混淆了作为一般理论概括的哲学与作为具体部门科学的语言学的关系”,④其实质是把哲学变为书斋学者的抽象推导,而背离普通群众的生存境地与愿望。应当说,奥孔斯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依据对西方语言哲学的分析是中肯的、深刻的。但是,苏联解体后,奥孔斯基先是数年没有哲学著述发表,接着在今年初的一篇“访谈录”中抛出了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的论点:“西方哲学界鉴于科学发展成果迭现而哲学老在原来问题上踏步不前的事实,提出语言是哲学也是人类的家园,随着现代数理逻辑的跃进,语言分析得到了长足发展。不仅出现了语形学,还有语义学、语用学,在其他方面有基本逻辑和元逻辑,有现代逻辑(命题逻辑、量词逻辑)与非正统逻辑(模态、多值、非标准蕴涵体系、非标准的量词体系)。这些新成就使当代哲学的面貌有了根本改观,不失为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途径之一”。⑤奥孔斯基在这里把语言学与逻辑学的新成就误为哲学的新突破,以此认定西方哲学有望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直接否定了他从前的判断。
引渡当代哲学的舟筏在哪里?俄罗斯哲学界有人把它寄托在西方哲学提供的药方上。殊不知西方的各种流派与思潮都是各领风骚无几年,频繁更迭,难见得有广阔的前景。
三、宗教哲学研究兴起
宗教哲学在苏联曾被视为唯心主义的有神论而遭到被批判、被压制的命运,70年的苏联宗教哲学研究除了重复马恩关于宗教本质的论述外可说近乎一片空白。而在十月革命前,作为有着深厚宗教意识民众基础的俄国,宗教思想家曾有过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构成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排斥宗教哲学,无疑也就切断了俄罗斯渊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只讲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夫、别林斯基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不足以沟通传统与现实。哲学诚然是一种系统化的世界观理论体系,但它的根源在于普通民众所具有的朴素的世界观意识、俄罗斯普通民众的宗教意识不能根除,就潜伏着宗教哲学复兴的可能。
果不其然,苏联解体后,思想禁锢解除,宗教活动再度兴盛,各地被毁的宗教场所、建筑重新建立。普通民众接受了70年的无神论教育,到头来不过是一种外在理论的灌输,根本没有内化到其心灵深处,构成大众心理结构基础的仍是俄罗斯的传统文化意识的积淀与遗传。哲学家要走出困境,就不能不面对大众心理,使他们的意识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反映他们的内在要求,甚至迎合他们的趣味。于是就有了宗教研究会的纷纷成立,专业刊物也相继出现,各大学学报辟有“宗教研究”专栏,一批宗教哲学论著、宣传宗教教规教义的小册子行世。其中A.H.米特洛欣的《宗教哲学》影响很大,1993年1月问世至今一年多已几度再版,这与其他哲学专业书籍出版、发行的窘境形成极鲜明的对照。
除了俄罗斯国内的研究力量对宗教哲学倾注了大量精力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十月革命前后,有一批对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持异议的学者逃出苏联,在国外继续从事哲学或其他人文科学的创作与研究,其中从事宗教哲学研究的不在少数。他们掀起了一股俄罗斯“侨民哲学”研究的小浪潮。他们之中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夫、洛斯、弗兰克等人的著作在苏联解体前后纷纷在自己的国度出版,他们的宗教思想被认为是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污染”的正宗俄罗斯文化的精华,深深地扎根于俄罗斯文化的丰厚土壤中,因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现在,这些人的思路正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哲学界。有的论者指出:“它们代表了20世纪俄罗斯文化的最高水平,决定了俄罗斯文化的未来走向”。⑥
总之,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复兴迎合了哲学界内外的双重需要。在动荡的俄罗斯社会,无力把握自己前途与命运的普通民众只有靠内心的宗教信仰,依靠上帝来得到虚幻的满足,他们的宗教意识成了宗教复兴的土壤。而“侨民哲学家”们的思想对于曾以单一的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俄罗斯哲学界无疑吹起了一股清新之风。这种既有群众基础又有俄罗斯独特的理论创造的哲学对于已无多少活力可言的学术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容易的选择。但问题的要害在于,宗教理论能否真正解释清楚俄罗斯的各种社会现象,从而为摆脱困境指明出路?哲学除了安抚民众心理、迎合其趣味之外,其他功能哪里去了?比如引导作用、批判功能等。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
在前苏联哲学研究的各领域中,遭到“悲惨”命运的无过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了。按照著名哲学家、俄罗斯哲学学会主席弗罗洛夫1992年12月来北京大学访问讲学期间介绍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确体之后的一段时期曾受到压制,“所谓民主和多元论只是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流派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压制。当然没有官方的明文禁止,但已形成了一种社会气氛,使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停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而代之以非马克思主义流派;报刊杂志社和出版社不发表和不出版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和著作,或是有关部分予以删除后发表;许多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纷纷改变了立场,一些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⑦
那么,是否可以说积70年之功奠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已基本毁灭?近年来的材料表明,尽管上述状况未有根本改变,但少数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仍然顶着压力继续进行反思与探索。波波夫在一次“圆桌会议”上指出:有人企图完全否定历史唯物主义,过去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每一个字都正确,现在又说每一个字都不正确,这是理论上的倒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肃的学说,不能简单地否定,必须有超越他的新学说,马克思主义不能说没有毛病,但它是从整体上研究世界的,不象西方,只是从技术、宗教、文化等某个方面去研究,没有整体性。“我们的看法是要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要否定它”。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时没有的事实,现在有了,可以据此作出新的概括和总结。同时,波波夫指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国家的世界观,就不能发展了,因为它已经回答了全部问题,因此结论是“不能把任何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国家哲学”。⑧B.B伊连科夫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理论,一种科学,还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对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那时还没有这样的环境,只有在20世纪才开始注意文化的社会功能”。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欠缺不能构成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更不能抹煞它的科学性和永久价值。象伊连科夫这样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或理论来研究的学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150年的历史进行独立的反思和重新理解”,既不赞同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的作法,也对现今俄罗斯存在的一股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以为然。诚如弗罗洛夫指出的:“回到过去,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通过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积极努力,苏联哲学的成就将会重新被广泛接受,经过人们的科学研究和冷静思考,大部人还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命运,就寄托在这些持有理性观点不为时事风云变幻所动的哲学家们身上。
五、结束语
现在,正如有的论者所言:“俄罗斯哲学正处在不幸的时代,处在缺乏哲学与哲学创见的时代”。但是随着社会渐趋走上正轨,我们期盼,“这一时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12)有70年哲学传统与经验,有一支有较高素养与创造能力的哲学家队伍,俄罗斯哲学有望走出困境,重现生机。倒是我们自己不妨从哲学发展的这一特定历史现象出发,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首先,要恰如其分地估价哲学的社会功能与学科特点。盲目夸大其作用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既受特定生产方式的制约,也受到其他社会意识形式,比如政治、法律制度及思想、宗教、文化、科学等的制约;它的功能发挥的程度、范围与效果都是有限的。如果把不属于它自己应有的功能与属性强加到它头上,不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会走向反面,比如刺激人们不公正的判断与逆反心理。当然完全无视或抹煞哲学的功能也是不对的,作为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体系,哲学内在地规定人们的行为与选择,限制人的视野。企图否定哲学是短视的表现。其次,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个人都要培育一个理性的、健全的、成熟的心态,不能老是走极端,非此即彼。马克思主义150年、苏维埃社会主义70年都是抹不掉的客观存在,影响将是深远的。现在,前苏联、东欧之所以产生思想领域的极度混乱,原因之一就是有人企图否定历史成就,抱虚无主义的态度。第三,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与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之间的偏差,也要分析时代的发展暴露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哪些局限与不足。坚持与发展,确实是考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素养与能力的一个重要课题。
注释:
①托罗相:《哲学的价值》,俄《哲学问题》1993年第9期。
②B.B纳利莫夫:《哲学发展道路的沉思》,俄《哲学问题》1993年第9期第85页。
③《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79页。
④H.B.奥孔斯基:《语言与语言哲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324页。
⑤《西方哲学的走向——访著名学者H.B.奥孔斯基》,《莫斯科大学学报》1994第1期。
⑥A.梅斯里夫钦科:《宗教意识》,俄《哲学问题》1992年第5期。
⑦《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⑧参看《哲学问题》1994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