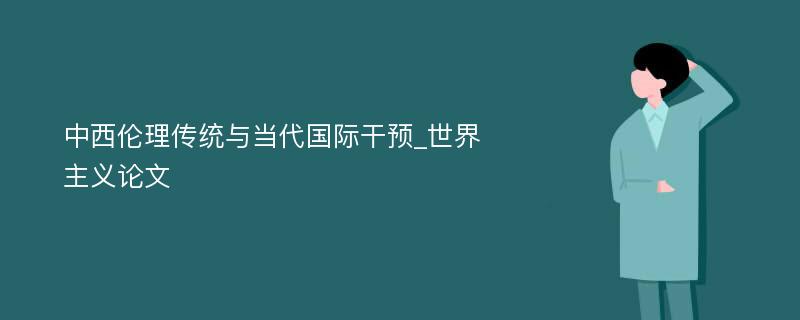
中西伦理传统与当代国际干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伦理论文,当代论文,传统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伦理传统构成一个民族或文明所蕴含的文化传统最具特征的内容,正如伦理规定本身构成关于社会安排和人类行为的最富意义的理念一样。它们不仅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共同存在于人的普遍本性(因而也是作为任何民族或文明成员的任何人的特殊本性)中的理想、激情、理性、甚至利益冲动,(注:Reinhold Niebuhr, "A Faith to Live By",Nation,V.164(Feb.22,1947),pp.207—208.)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决定他们生存环境和思想条件的客观要素。正因为如此,一方面可以认为至少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或文明都共有某些最根本的伦理信念,由例如中国传统的“天理”和西方悠久的自然法之类术语或概念来表述,(注:即使在伦理方面被当今不少西方人当作与之完全冲突的伊斯兰教及其原教旨主义,只要予以起码程度的认真考察,也能被证明一样共有这里所说的根本道德信念。参见Sohail H. Hashmi,"Interpreting the Islamic Ethics of War and Peace," in
Terry Nardin ed.,Ethics of War and Peace:Religious and
Secular Perspectiv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146 —166.)另一方面则必须肯定它们互相间在形形色色较具体的伦理准则、道德惯例和规范性判断方式上面有其重要差别,或者说体现了非常丰富的伦理多样性。不仅如此,在同一个民族或文明内,无论就同一时段还是就不同历史时期来说,一般都存在不同的伦理信念,它们只要是被许许多多的人所信奉并延续至一代人以上,就可以说构成一种“伦理传统”,或者说构成一个民族或文明的总的伦理传统中的分支传统。世界的伦理论辩,大体上就是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伦理传统和分支传统互相间的论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道德同一性和多样性。
因此,讨论中国和西方的伦理传统,至少意味着谈论中国和西方各自悠久的和现时代的伦理,加上历史上和当今它们内部种种不同的、但都被许许多多人信奉的道德理念。就国际事务领域而言,在中国方面可以看到传统的大一统伦理,所谓“华夏之教”、“礼教”、“王道”就是如此,它们同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大一统伦理、甚至同19和20世纪西方的自由国际主义伦理在根本精神上大概是一致的。但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还有从先秦法家发端的权势政治伦理,它们在根本信条、思想方法和情调风格方面同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乃至汉斯·摩根索和亨利·基辛格描述或主张的现实主义伦理是那么近似甚或一致。在当代中国,1949年往后约30年内有力地影响甚或支配中国对外行为的当然是毛泽东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伦理观,它既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源于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受尽屈辱因而满怀义愤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人们有一切理由将其归类于马丁·怀特所定义的“革命主义”传统,(注: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New York:Holmes & Meier,1992).又见时殷弘、叶风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欧洲》1996年第1期,第3节。)与加尔文主义、雅各宾主义和列宁主义一起体现激进的“上帝选民”、“自由公民”或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造反激情、道德两分(moral dichotomy)和世界主义解放理想。(注:当然,实际情况总是比理念模式复杂。在毛泽东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那里,现实主义伦理也起作用。实践检验、斗争策略和迈克尔·沃尔泽讨论过的对“宋襄公伦理”的无情否定(见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New York:Basic Books,1977,pp.225—228))等等,便是与之对应的哲学——政治观念及态度。)邓小平领导中国以来,伴随着国际政治观的变化,(注:时殷弘、吕磊:“美国对华态度与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概观”,《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3期第5节。)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伦理观也发生了即使局部、但仍非同小可的转换。国家间正义和国际分配正义取代阶级间正义(以及一定程度上民族间正义)成为其根本的国际伦理纲领,与近年来尤其突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非先前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一国际政治纲领相应。很大程序上可以说,中国约20年来新形成的国际伦理传统可称激进与保守性兼具的依附论伦理之中国形态,与当代西方主流的自由国际主义伦理截然对立,尽管作为分支传统的现实主义伦理起着比在毛泽东时代更为显著的作用。很明显,就西方而言,伦理传统一样有着在同一时段内的内在多样性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显著变化。
如同特里·纳尔丁教授在中美“伦理与国际事务”学术讨论会上将伦理传统考察限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注:时殷弘:“中美‘伦理与国际事务’学术讨论会述评”,《美国研究》1999年第3期,第 143 —144页。)一样, 这里的讨论显然只有着重于某个特定的问题才是实际可行的,而它要有尽可能大的现实意义,就应当选择对当今世界政治和伦理论辩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显然可以是国际干涉。美苏冷战结束以来的世界表明,现时期的国际干涉在伦理上大多涉及以下三个基本方面——强国与弱国关系的伦理、民族间关系的伦理、国际干涉本身的合法性或正义性标准。就中国和西方关于这些方面的伦理传统来说,值得讨论的主要应该有五项:(1)毛泽东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伦理;(2)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伦理;(3)西方经典现实主义伦理;(4)西方经典自由主义伦理;(5)当今西方自由国际主义伦理。(注:下面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依据时殷弘、宋德星:“科索沃冲突与国际政治伦理”,《美国研究》1999年第3期。)
二
在中国古代主流思想中,强国和弱国间关系的伦理主要在于仁慈,即强国对弱国的仁慈。(注:借用英国大哲学家边沁的话来定义,仁慈指用正面方式对待他国幸福的义务,即“试图增长”他国幸福的义务。见Jeremy Bentham,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chapter 17.sections 6,7.)在地理和文明双重意义上的“中央王国”应当用恩威并施的方式,感召、教化和保护被称为“蛮夷”的周边弱国,以此贯彻仁慈伦理。在这样的伦理中,没有修昔底德笔下雅典人对弥罗斯人的那种“强权即公理”逻辑,不承认“神性和人性的必然规律是在一切可能范围内行使统治”(注: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New York:Modern Library College editino,1951),p.334.), 但同时也没有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思想的创立者们当作头等准则来强调的国家不分强弱、一概平等的原则。(注:例如18世纪的国际法大师瓦特尔说:“强弱在这方面完全不造成区别。侏儒同巨人一样是人,一个小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完全不亚于最强大的王国”。引自J.L.Brierly,The Law of Nations,6[th]edition(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3),p.37.)毛泽东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强烈的现代正义信念和奋力争取民族解放的半生经历,不仅痛恨国际政治中的无论何种以强凌弱现象(即使发生在他们长期所属的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而且也不能容忍任何凌驾于上的强国以恩赐姿态给予的“仁慈”。毛泽东最钦佩的人物大概是戴高乐和铁托,而他最愿支持的无疑是敢于挑战强国霸权的欠发达弱小国家和民族。同绝大多数非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者一样,国家间平等和弱小民族自决是他从现代西方思想中选择出来的最重要原则,对这原则的坚信说到底来自一项在东方哲学中尤其根本的理念,那就是“物质力量同道德力量相比一钱不值”。(注:圣雄甘地语, 引自 Felix Gilbert,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1890 to the Present,2[na] edition(New York W.W Norton & Co.,1979),p.264.“苏联那些顽固分子……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铁,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283页。)毛泽东关于国家平等的现代正义观,他对强国霸权的强烈愤恨和对弱小民族国家的由衷同情,以及他那主要从道义信念出发的、关于中国将来真正强大后也永不谋求霸权的决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伦理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今中国的国际态度和立场。国家不分强弱一概平等,强国无权干涉弱国内政,国际争端的唯一合理解决办法在于平等协商、而非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强权政治——这就是当今中国政府所主张建立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根本规范,也是当今中国国际伦理的核心内容。
不过,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现今的国际伦理已不带有强烈的激进色彩。原则如初,气质已改。这气质涉及的是在具体实践中贯彻原则的力度和伸缩性,是追求实现道德理想的急切程度以及为理想搁置或牺牲利益的意愿大小。人们确实有时可以在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外交实践中看到与国际平等、国家自主伦理不大一致的情景:中国珍视大有国际不平等之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及其特权,不止一次地就自己和其他一两个国家谈论或宣告“大国责任”,认可甚或参与了某些虽由联合国主持但有赖于强国动议和支持的国际干预。除了以间或宣示的“中国国家利益”理由来表征的后果主义(现实主义)伦理外,人们从中国方面找不到关于这些政策行为的正式伦理原则,而只能象感觉气质那样揣摩它们背后的道义感。从中国国家发展程度的角度看,很少有人能否认它们是中国外交成熟化的表现,也是中国国际伦理成熟化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必然强调,国家间平等和反对国际干涉仍然为当今中国所信奉,而且不仅在中国国家利益权衡的意义上如此,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感意义上也是如此。
与后面要谈论的两个基本方面——民族间关系伦理和国际干涉本身的正义性标准——相比,国家不分强弱一概平等(以及与此相关强国不得干涉弱国)的原则似乎远为明确、远少争议地契合西方现代伦理传统。这原则可以说起源于非常悠久和有力的自然法观念,(注:参见前面注释中瓦特尔的断言。)构成始自西方并由其扩展到全世界的现代国际法和国际伦理的核心规范之一,并且体现在完全或主要由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和英国人)拟订的《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当中。然而也是在西方,从19世纪初的维也纳会议开始,强国以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特殊作用为由,依仗自己的优越权势,集体地规定某些强国特权,使之获得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在国际政治实践中,西方强国更是往往依据含糊宽泛的强国责任(例如从西奥罗·罗斯福自命的“国际警察”责任到作为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口头禅的“世界领导”责任),欺凌和干涉弱国。然而,无论是正式的强国特权,还是由自命的责任引伸来的强国权利,都不具有国际伦理意义上的合法性,也不符合西方本身的根本伦理传统,除非将雅典人对弥罗斯人宣告的“强权即公理”逻辑当作这样的传统,那是当今绝大多数西方人都不会同意的。
三
当今世界特别引人注目的国际干涉,包括关于波黑内战、科索沃冲突和库尔德人问题的干涉,多半同民族间关系密切相关。这加上就民族间关系实际进行的许多外交和政治干预,再加上世界不少地方发生重大民族冲突的可能,使有关的伦理论辩和伦理判断变得非常重要。民族间关系的伦理问题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民族权利平等问题,二是民族自决权同一个民族所属的那个(或那些)国家的主权之间的关系问题。(注:时殷弘:“论世界政治中的正义问题”,《欧洲》1996年第1期,第12—13页。)中国古代伦理传统所涉及的当然只是前一个部分,而且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文明程度甚至文明性质的差别决定华夏优越和蛮夷低劣,两者间无伦理上的平等可言。当然,华夏对待蛮夷须符合道德,那就是前面说过的居高临下的仁慈。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史例表明,只要蛮夷接受“教化”,以致接近甚或等同于华夏的文明程度并尊从中央权威,便能得到平等或较为平等的待遇,多少类似于19世纪50和90年代,奥斯曼土耳其和日本两国因被认为大致符合了西方“文明标准”而先后成为国际社会正式成员。(注:参见Gerrit W.Gong,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chapters 4,6.)中国共产党人在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执政者之前,其在民族间关系上的伦理立场也只涉及民族权利平等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对他们主要在于中华民族以及世界其他各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他们眼中的压迫民族几乎不外乎资本帝国主义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权利平等构成中国革命的一大主题,并且构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一最高事业的一大组成部分。同对国际强弱关系的态度一样,他们对这民族权利平等问题的态度有着最强烈、最深刻的道德动力。在取得中国政权之后,他们一方面继续强烈地持有这样的态度或信念,甚至发展到将压迫民族的范畴扩及“社会帝国主义”民族,由此证明了他们在道德上的不妥协性,但另一方面也着手处理先前基本上远非突出却更为复杂的国内民族问题。在政治和伦理传统远非现代的中国,通过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新中国民族政策,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实现并维持了那些当今举世公认、不容有任何质疑和保留的民族平等权利,即各民族在它们组成的主权共同体中保持本民族语言和文化传统、维系本民族成员之民族情感、被其他民族尊重以及充分参与多民族共同体政治生活的同等权利。由此,他们在中国形成了确实深入人心的民族平等伦理传统。
以1959年西藏爆发叛乱为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面对许许多多欠发达国家(较赢弱的、有欠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注:一项很好的讨论见K.J.Holsti,The State,War,and the State of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都存在的一个严峻问题:如何对待民族分离主义?在理论上,自从列宁和威尔逊同时分别倡导民族自决权,或更准确地说自从其非常简单、含糊地载入《联合国宪章》,便有了一种抽象地说已被普遍公认的民族权利,即每个民族都有权依自由意愿组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广大欠发达国家曾通过它们在其中占大多数席位的联合国大会,议决这项权利只适用于尚处于殖民统治下的民族,但显然这样的解释同民族自决权的抽象形态一样殊难一概贯彻。鉴于大多数国家包含两个以上民族,连同许多欠发达国家存在相当严重的“族性分裂”(ethnic splitting)问题和此类问题可能引发国内外大动乱,因而对以创立国家权利为一大(甚或主要)内容的民族自决权进行恰当评判可谓当代最重要、也最复杂的政治和伦理问题之一。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和江泽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十分明确、简洁和坚决的,那就是中国不容任何分裂,也不容任何外国就此进行任何干涉,世界别国的情况则应由其本国人民自主选择,不应以外来干涉决定或干扰之。不仅如此,尤其在出现超级大国支持分离主义势力的场合,中国的同情是在遭受这种势力挑战的主权国家政府一边。国家主权至上构成中国头号国际政治和伦理准则。
在西方的伦理传统中,直至非殖民化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达到高潮为止,可以说没有民族权利普遍平等观念,尽管极少数以普遍道德为绝对准则的西方思想家——最彻底的是康德——从民族群体间平等、和睦出发,反对大多数甚至一切形式的殖民半殖民入侵和征服。(注:康德就此表述的“世界律令”(the "eosmopolitan or world law"),见F.H.Hinsley,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67),pp.65—66,又见16世纪西班牙哲学家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关于美洲印第安人自然权利的著名观点: Frank M.Russell,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ew York:D.Appleton-Century Co.,1936),pp.137—141.)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运动及其激活的西方普遍道德思想,使民族间的平等伦理成为举世公认的。在民族自决权方面,就自由创立民族国家而言,同样不能说存在一种西方伦理传统:同“让民主安存于世界”(to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相反,民族自决在威尔逊那里是一条含糊的和显然大有保留的口号,他从没有意愿和道德冲动来追求、甚至即使是希望其普遍和彻底贯彻,而他以后几乎所有肯定民族自决原则的西方人同样如此。(注:参见 Alfred
Cobban,The 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Self- Determination, revised edition(New York:Thomas Y.Crowell co., 1969).)于是,我们面对这么一种伦理形势:大致只有中国(以及其他广大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分离主义者这两方面才有关于在当今时代自由创建民族国家的明确的道德取向,即前者接近绝对否定,后者则是绝对肯定。
显然,我们需要创立一套较为周全和实际的民族自决之伦理——政治判断准则。这套准则应当兼顾秩序和正义,做到对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都是公正的,并且尊重所有与这两者相连的有关各国各族人民的生命安全、经济福利和尊严。不仅如此,它还应当在一切有关场合都能贯彻,以它内在的应有复杂性来对应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两相冲突时必有的实际复杂性。在这方面,爱德蒙·伯克在18世纪末年所提正当的革命的三项先决条件,为我们提供了参照:必须存在“严重的、逼人的邪恶”;必须很可能、并且差不多肯定能导致大善;全无其他途径来“确立一个适于实现其理性目的的政府”。(注:Jennifer Welch,Edmund Burk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p.95.)据此,当一个民族要求从所属的多民族国家分离时,必须遵循三项标准来对此作出正当的道德评判和明智的政治选择,那就是:(1)是否存在非常严重的民族压迫;(2)是否全然没有局部调整现状的可能,以致除分离外绝无他途;(3 )分离给或很可能给有关各方人民造成的物质和精神苦难以及它导致(或很可能导致)的国际动荡是否过分巨大。唯有同时遵循所有这三项标准,才能在有分离要求的场合正当和明智地决定应优先考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是应优先考虑实现民族自决权。更进一步思考,我们还可借助于“正义战争”理论和更广泛的“道德审慎”原则,在这三条标准外添上(1 )分离成功的可能性问题,即没有适当的成功可能性的分离企图不能说合理正当;(2)宁愿失去采取正义行动的机会,而不冒做出重大不义行为和造成重大不义结果的风险。(注:Gordon Graham,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7),pp.118—122.“在关于拿起武器的场合按照道德审慎原则行事,就是凡对目的的价值和达到目的的成功机会没有把握时,一概宁不拿起武器……宁愿未匡正不义而不闯祸作恶:这有其充分的道义理由。”Ibid.p.,121)全面对照之下,不能说科索沃阿族武装之类分离运动是恰当的,更不能认为北约对南大规模动武之类国际干涉代表了国际正义。
四
对本文的主题来说,国际干涉本身的合法性或正义性标准问题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根据传统的现代国际法,国家作为国际社会唯一的主权行为者,享有得到国际广泛承认的自主和领土完整权利,因而任何破坏一国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外来行为,都是非法行为。如果使用武力来这么做,则是侵略行为,而侵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公认的罪行。因此,国际干涉、特别是武装干涉系传统的现代国际法所绝对禁止。联合国大会于1965年通过的《关于不允许干涉各国内政的宣言》就经典地表述了这一点,其中明确宣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为任何原因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外事务。”(注:引自Louis Henkin,International Law:Politics and Values
(Dordrecht,Netherland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p.132.)国际干涉不仅违背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而且由于这些原则富含的伦理意义而违背由来已久的国际道德。格老秀斯所说自然法(即普遍道德)的第一条就是“不侵扰他人所有”,(注:Grotius,"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in Michael Curtis ed.,The Great Political Theories,V.1(New Yord:Avon Books.1961),p.321.)瓦特尔用同样的自然法语言强调“倘若不尊重这使每个人确保其所有物的美德,人类社会……便将成为仅仅是一个你我抢夺的盗贼天地。”因而“所有各国培育和遵循正义的责任在于:每个国家都应当让其他国家据有属于它们自己的东西,尊重它们的权利,并让它们安享这些权利。”(注: Emmerich de Vattel,"Justice Between Nations," in Phil Williams et al .eds., 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cations ( Belmontcalif:wadscorth.Publishingco,1994),P.16.)
关于国际干涉的中国伦理不需进行多少讨论。在古代中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主权观念及其派生的各项国际准则,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干涉问题(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候国体系同现代国际体系有不少相似之处,中国古代典籍也记述了当时许许多多“干涉别国内政”的史事。但在这些典籍中受到道德、评判的一般并非干涉本身,而是干涉的方式和手段。参见 K. J. 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3[rd]edition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77),论秘密行动和干涉的一章。)。对毛泽东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国际干涉一般表现和助长了国家间、民族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因而是由衷愤懑和强烈抨击的对象,尽管在同苏联决裂以前,国际共处的某些跨国义务和意识形态信条限制了在反对国际干涉方面的彻底性和一贯性(注:如他们关于匈牙利学科和一些国家内部革命运动的政策行为所示。)。邓小平领导中国以来,对国际干涉、特别是强国干涉的差不多绝对的否定,构成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特征,这同前面关于当今中国对国际强弱关系和民族间关系的立场完全一致。它们结合起来,可以说最终形成了一种非常明确和连贯的当代中国国际伦理传统,其核心理念是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不过,最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变迁,国际法(也许某种程度上还有国际伦理)在其发展中出现了一种可谓自相矛盾的倾向:国家在法理上依旧拥有主宰本国内政外交的全权,但同时联合国、甚至某些区域性国际组织在法理上亦有权干预国家的某些种类的内部事务,并且不时充当原先仅由主权国家充当的国际法执法者。也就是说,国际干涉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是合理正当的。但需要大力强调,这样的国际干涉必须基于严格的、关乎国际正义的条件。西方经典现实主义者和经典自由主义者各自都提出过合理正当的国际干涉所需的严格条件,一般来说凡违背这些条件的国际干涉应被认为是不正义的。
西方经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和(或)人的本性使所有国家在其互相间关系中处于霍布斯所定义的那种战争状态,(注:见《利维坦》第13章。)一国不会(或不应)为遵守不干涉原则而听任自己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从根本上说,维持国家安全的真正途径是自助,而非效用往往值得怀疑的国际法或国际伦理,而这就意味着有时确实必须用对外干涉来确保国家安全。但这并不是说,在经典现实主义者那里只有权势政治。实际上,18和19世纪的著名经典现实主义者如瓦特尔、布罗汉姆勋爵和根茨等人都强调应当尽可能避免、排斥和限制干涉:唯有出现很可能倾覆国际形势、从而危及其他国家严格意义上的安全(实体安全)的局势,亦即一国实力急剧增长,并且明确地图谋对外侵略甚至称霸国际体系时,其他国家才可以进行干涉,以防止、制止或彻底挫败之。(注:Edward Gulick,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w.w.Norton and Co.1967),pp.62—65.)
与经典现实主义者相比,经典自由主义者关于国际干涉的辨析复杂得多,而其观点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绝对不干涉,其出发点实际上可以说是主权和政治人权的根本统一。例如康德强调,不干涉保证了一国的独立自主,使该国人民可以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地决定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注:Doyle,Ways of War and Peace,P.395.)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着力论说通过干涉向一国输出自由是极大的错误。一国人民只有在自己认识到自由的真正价值时,才会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自由并保持下去,而经由外国干涉赐予的自由不仅无法长时间保持下去,而且还可能出现下述情况:干涉造就一个象其前任那般压迫民意的新政府,或出自干涉的新政府由于本国人民对外国干涉者的反感而不得民心。在后一种情况下,很可能要么这个政府在一场内战中垮台,要么外国干涉者一直向其提供支持,但这又将使之成为一个不反映本国民意而只反映外国干涉者意愿的傀儡政府。(注:John Stuart mill" A Few Words on Nonintervention," in Essays on Polities and Culture,edited by Gertude Him-melfard(Gloucester, Paeter Smith,1973),pp.368—384.)
另一派经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负有保障基本人权这一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国如果不履行这一责任,甚至反过来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就丧失免于国际干涉的权利。因而,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保障本国人民的基本人权,也都有义务在绝对必需的情况下为维护别国人民的基本人权进行干涉。经典自由主义者、“当今美国主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注:mitchell Cohen and Nicole Fermon eds.,Princeton Readings in Political Thought (D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656.)迈克尔·沃尔泽认为,在三种情况下国际干涉是合理正当的:第一,如果一个帝国压制一个附属民族的独立要求,或者一个民族企图摧垮另一个民族,国际社会就可以进行干涉以帮助被压迫的民族获得解放,其时民族自决不能成为避不干涉的理由;第二,当一国发生内战时,如果一个外国以干涉来支持内战一方,那么另一个外国可以进行目的仅在于制衡这一干涉的反干涉;第三,如果一国国内发生大规模屠杀和种族清洗等广泛、严重的暴行,国际社会可以进行人道主义的干涉(注: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pp.106—108,339—342.)
象经典现实主义者一样,那些主张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国际干涉的经典自由主义者也非常强调干涉有其严格的先决条件:合理正当的干涉必须确实是为捍卫大量人口的基本人权所必需;干涉必须有节,即干涉造成的综合伤害不能大于若不干涉 就会发生的综合伤害;人道主义的国际干涉必须仅仅出于制止大规模屠杀和种族清洗等广泛、严重的暴行以及帮助实现有关人民的自决权之道德目的;干涉必须是所有可能的和平解决尝试都失败后的最终选择;被干涉国家大多数人民欢迎或至少不反对干涉。(注:见Doyle,Ways of War and Peace,PP.396—402)总之,国际社会或其任何成员都决不可滥用经严格限定的国际干涉权利。
五
在此临近结束之际,需要对本文作一概要的回顾。中西伦理传统,大致就是中国和西方各自悠久的和现时代的广泛伦理,加上历史上和当今它们各自内部种种不同的、但都有广大信奉者的道德理念。以对目前乃至未来世界政治和伦理论辩至关重要的国际干涉问题为焦点,可以相当具体并富有重大实际意义地讨论予以如此理解的中西伦理传统。当代国际干涉就伦理而言,涉及强国与弱国关系的伦理、民族间关系的伦理以及国际干涉本身的合法性或正义性标准这三个基本方面,而中国古代主流伦理只在前两方面有其相应的规范,那主要是与国家间、民族间权利平等的现当代观念格格不入的“仁慈”——华夏中央王国基于优越文明和权势而对周边蛮夷居高临下的仁慈。与之相反,毛泽东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从现代正义信念与其革命经历出发,坚持国家间、民族间一概平等,憎恨强国干涉和民族压迫,并且奠定了以国家主权为核心、民族平等为重要内容的中国国际及民族伦理新传统。邓小平掌舵以来,中国国际伦理虽然不再带有毛泽东时代异常强烈的激进精神,但国家主权至上这一政治——伦理原则和对国际干涉、特别是强国干涉近乎绝对的否定可谓更加突出,并且构成中国政府近年来时常重申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理想的主要特征。就西方现代伦理传统(注:如前所示,本文提及的现代以前西方伦理传统限于:(1 )与中国古代大一统伦理相似的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大一统伦理;(2)作为支流, 且并非西方独有的“强权即公理”逻辑。)而言,在强国和弱国间关系问题上,一方面有源于自然法即普遍道德的国家平等规范,另一方面却有与所谓“强国责任”相连的强国特权法则,而在民族间关系问题上,直至非殖化达到高潮为止,可以说没有民族普遍平等观念。关于国际干涉的合法性或正义性标准,当今西方自由国际主义者将人权的道德意义凌驾于主权的道德意义之上(甚至将后者抹煞),从而倾向于滥施国际干涉。相反,西方经典现实主义和经典自由主义者要么强调合理正当的国际干涉有其严格的先决条件,要么从主权与政治人权的根本统一出发,反对任何国际干涉。在与当代世界的正义和许许多多国家人民的安全及幸福密切相关的一大问题——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它实际上是民族间关系问题的一部分)上面,恰当的伦理传统之缺乏要求我们创立一套均衡、实际和较为精细的准则,它应以本文所提五项标准来指导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政治——伦理判断。
除此以外,关于当今和未来世界政治、特别是国际干涉所应有的一些基本政治——伦理准则,实际上可以从本文论说的中西伦理传统看到。其中,中国共产党人所强调和坚持的国家间、民族间普通平等最为起码和重要,而其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场原则上也大致是如此。另一方面,一部分西方经典自由主义者关于有限地容许很少种类国际干涉的主张,连同他们为此提出的严格的先决条件,至少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与历史上西方世界形成旨在限制暴力的“正义战争”理论相似,当今国际社会大概急需形成某种“正义干涉”理论,其宗旨须在于尽可能严格地限制国际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