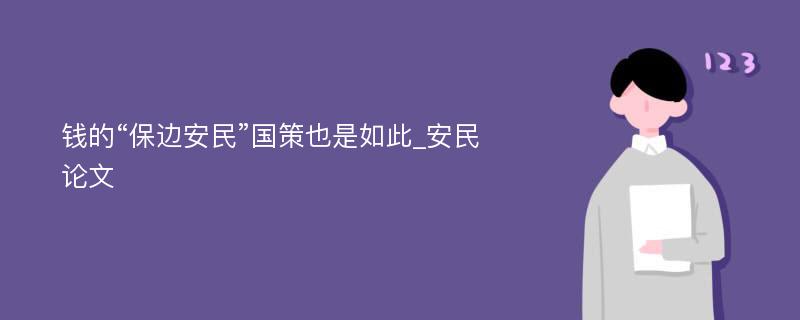
也谈钱镠“保境安民”国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策论文,也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人钱镠(公元852-932年)建立的吴越国,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从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钱镠被朱温封为吴越王开始,吴越国历三代五王,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弘倜“纳土”归宋,前后70余年,是十国当中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吴越国以杭州为国都,兼有“十三州一军”之地,境域范围相当今浙江省和苏南太湖流域,最盛时还包括福建的部分地区。对于浙江和苏南太湖流域地区唐末以来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历史学界,尤其是研究浙江地方史的学者,多认为吴越国之所以国运长久,能在恢复、发展唐末以来浙江及苏南太湖流域社会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钱镠及其继承者们贯彻执行了“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笔者以为此说尚值得商榷。
一、“保境安民”的提出
“保境安民”一词是后起之说。不过,“保境安民”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只是提法不同而已。
早在西周初期,周公在《毋逸》中即提出:“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①]南北朝时期,萧梁潼州刺史杨乾运兄子杨略也说过:“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国宁民,而兄弟寻戈,此自亡之道也。”[②]
五代时期,提出这一思想的统治者更多。例如,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保境息民,闽人安之。”[③]而唐李昪,当其臣下进谏出兵北伐后晋时,他却说:“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后来“汉主遣使如唐,谋共取楚,分其地”,李昪也没有同意,所以胡三省说:“史言唐主能保境息民。”[④]前蜀的王建,在其武成二年(公元910年)的劝农诏中也说:“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农桑之业。今国家渐宁,民用休息,其郡守县令务在惠绥,无侵无扰,使我赤子乐于南亩,而有《豳风》、《七月》之咏焉。”[⑤]
同样,钱镠在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的《镇东军墙隍神庙记》里也说过:“今则象轴焕新,龙纶远至,表勋名于万代,昭灵感于千秋。固当永葆皇灵,长垂幽赞。卫我藩室之地,遐请灾沴之源。保泰斯民,乂安吾土。烜矣赫矣,永作辉华。”当然,与王潮、李升、王建等人相比较,钱镠在这里主要是祈求神灵的保佑。不过钱镠另外也说过:“余于二十四得功,由石镜镇百总,枕甲提戈,一心杀贼,每战必克,大江以南十四州军,悉为保障,故由副使迁至国王。……余固心存唐室,惟以顺天而不敢违者,实恐生民涂炭,因负不臣之名。……十四州百姓,系吴越之根本。圣人有言: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云: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又云:省刑罚,薄税敛。”[⑥]言辞之间亦包含着不兴兵举,与民休养生息的意思。
由上述可见,避免兵举之事,保障地方安宁,与一方之民以休养生息的时机,以期达到“富庶自成于国霸”[⑦],乃是五代十国时期不少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们的共同思想。作为既得利益者,在一时无法进一步拓展领地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他们的愿望。
首先对钱镠的思想和政策进行四个字的总结的是明朝末年的史郑鄤。他在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写了一篇悼念钱镠的纪文,题为“保民享国”。文云:“时中原多故,蜀王氏、吴杨氏、汉娄氏、闽王氏,皆窃大号,以龙衣王册进王。王拒不纳,恪守臣节,保全境土。当五季战争之场,而江以南,独得免于磷青白骨之苦,其福庇斯民甚厚。唐庄宗长兴三年,三寝疾,抚文穆曰:将士推汝,宜善守之。又曰:善事中国,无失大礼。”[⑧]
明确提出“保境安民”四个字的则是民国时期钱镠三十二世孙钱文选。他在1925年撰写的《重建表忠观正殿纪略》中说:“王祖‘保境安民’,垂为世德。”同年,钱文选在另一篇题为《重修西湖王祖祠纪》中又说:“时,济阳卢督子嘉盛倡‘保境安民’之旨。”[⑨]这里所说的“济阳卢督子嘉”即卢永祥(字子嘉)。卢永祥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淞沪护军使,1919年任浙江督军。为了对抗直奉军阀的“武力统一”,卢永祥提出“联省自治”、“浙人治浙”(卢虽为山东济阳人,但自认原籍浙江宁波,并设法取得了进宁波卢姓族谱的资格),并在1920年7月1日指责苏军犯境并宣布派兵去南翔防堵的通电中,又提出了“保境安民”一词[⑩]。由于“保境安民”此说很适合当时一部分政客和军人保护一方地盘的需要,也适合普通群众期望社会安定、免受干戈之苦的心理要求,所以,一时之间,军政上下,都大谈“保境安民”。钱文选所说“时,济阳卢督子嘉盛倡‘保境安民’”,并追根溯源,提出钱镠“‘保境安民’,垂为世德”,正是当时形势之下人们思想的反映。
自此以后,史学界奉“保境安民”之说者渐众。近年来又有学者将“保境安民”奉为吴越国的基本国策,并以“善事中国”、“勿废臣礼”、“不兴兵举”为其基本内容,尽管没有下过明确的定义。
二、关于“善事中国”、“勿废臣礼”
“善事中国”、“勿废臣礼”,语出钱镠。《资治通鉴》记载,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钱镠在其弥留之际,嘱咐其子钱传瓘云:“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11)《钱氏家乘》也记载说钱镠“嘱曰:‘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勿废臣礼’”。意思是说,不管中原如何改朝换代,我吴越一概视为正朔,称臣纳贡,不要卷入其争战。
钱镠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后梁代唐,并遣使赴钱塘宣谕,其时文武大臣力谏钱镠举兵讨伐朱温,钱镠却说:“斯言罗隐早已言及,吾亦筹之熟矣。奈兴兵征讨,必动干戈;且兼淮氛未靖,湖州初平,吾若外讨,彼必乘虚滋扰,百姓必遭涂毒。古人有言,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吾以有土有民为主,故不忍兴兵杀戮耳。”(12)钱镠还说:“余固心存唐室,惟以顺天而不敢违者,实恐生民涂炭。因负不臣之名,而恭顺新朝。此余心之隐痛也。”(13)可见钱镠接受后梁进封,称臣纳贡,只是一种韬略。李昪(徐知诰)就曾说过:“钱氏父子,动以奉中国为辞。卒然犯之,其名不祥。”(14)钱镠同时也是为了远交而攻近敌,对付夙敌杨吴。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就在接受后梁进封的第二年,钱镠即“以淮寇终为臣患,欲速平之。命景仁奉表至阙,面陈水陆之计,请与禁旅”(15),策划共讨杨吴。同年九月,后梁以寇彦卿为东南面行营都指挥使,率师攻打杨吴以援吴越。虽然后梁此次兵败而归,但是它对吴越终究还是尽了职。12年后的贞明五年(公元919年)三月,后梁进攻吴国,“诏吴越王钱镠大举讨淮南。镠以节度副大使传瓘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大战狼山江(今江苏南通南狼山附近长江);接着又遣传瓘“将兵三万攻吴常州”。这是吴越国与吴国之间最激烈的战争之一。但是,同年九月后梁再诏钱镠发兵征讨南汉刘岩称帝时,“镠虽受命,竟不行”,“不肯自毙其力以伐与国”了(16)。
钱镠执行“善事中国”、“不废臣礼”也不是没有原则的。例如钱镠与后唐的关系一度曾相当紧张。那是天成四年(公元929年),后唐明宗李亶听信枢密使安重晦等人的挑拨,削夺了钱镠的爵位。钱镠毫不示弱,一方面上表申辩,一方面针锋相对,扣留了后唐使者。其时,后唐出使闽地的使者吏部郎中裴羽、右散骑常侍陆崇等遇海风飘流而至吴越国境,被钱镠“留于钱塘,经岁不得归”,以至陆崇病死于吴越(17)。钱镠与后唐的这一矛盾,最终还是以后唐诛杀安重晦,赐钱镠以“不名之礼”而告结束。
钱元瓘(传瓘)是接受钱镠嘱咐、继续执行“善事中国”、“勿废臣礼”的第一人。他一方面接受后唐的进封,并尊后唐年号为吴越国年号,后晋取代后唐以后,又及时接受后晋的进封和年号。但在另一方面,钱元瓘且又“遣使劝进(李)昪,谓人望以归”(18),鼓励李昪称帝。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李昪即大齐皇帝位,改元升元,钱元瓘即遣将军袁韬致贺(19)。天福四年(公元939年)李昪改大齐为大唐(史称“南唐”),钱元瓘又遣左卫上将军沈韬文“如唐贺南郊”(20)。钱元瓘如此作为,至少在名分上已将后晋降到了大齐(南唐)的地位。而其之所以如此,当然还是出于吴越国的利益。或者认为石敬瑭仰仗契丹所建立的政权终不可靠,同时也是为了借此改变与淮南对立的关系,所以投徐知诰之所好,劝进帝位。钱元瓘此举在改善吴越与南唐的关系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杭州丽春院大火延及内城,钱元瓘因受惊吓而发狂疾,南唐群臣争劝李昪乘机出兵吴越,但是李昪却说:“奈何利人之灾”(21),不但没有乘人之危,反而“特命行人厚遣之金粟缯绮,车盖相望于道焉”(22),救助吴越国。
钱元瓘的后继人钱弘佐对于“善事中国”、“勿废臣礼”的理解甚至超脱了“夷夏之辨”,将“中国”的概念扩展到了契丹。当辽朝耶律德光在会同十年(公元947年)正月攻灭后晋的时候,一度奉辽朝为正朔,改用“会同”年号。“钱塘大慈山甘露院牒称会同十年七月,有吴越国王押字及镇东军节度使印文。盖是时吴越与契丹信史不绝,故吴越奉其正朔在诸州镇之先。其改而从汉,则在八月受汉制之后也”。“吴越甘露院牒之称会同十年,在天福十二年七月。曷以不称开运与天福者,盖前此吴越与契丹通使不一而足,至是既布诏州镇矣。而汉使未至,宁有不奉其正朔者。间读《福州双石祠记》,有云会同十年从闽府承平,复封为安境侯。时福州新附吴越,故亦称会同也。所疑者,契丹以是年二月改元大同已,故《辽史》会同无十年,而吴越犹记十年者何?盖契丹降赦则称会同,而改元则曰大同,改元之后不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之号不行于南土,则吴越之称会同于丁未七月也,又奚疑焉!”(23)五代时期,吴越国是南方各国当中与契丹往来最密切的国家。这就是钱弘佐于“诸镇州之先”奉辽朝为正朔,继续推行其远交而近攻策略的原因。
吴越国在钱弘倜即位以后,先后奉后汉、后周及北宋为正朔,始终贡奉不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仍然是远交而近攻策略的继续。因为南唐自李璟即位以后,双方为争夺福州而又结仇隙。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善事中国”、“勿废臣礼”,不但可以北方中原“朝廷”的力量牵制南唐,甚至可以直接取得援助。如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钱弘倜曾派遣使者间道至于后周,请其出师进攻南唐。接踵而至的后周与南唐间连续几年的战争实始于此。所以南唐指责吴越“负约”(24)。又如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后周世宗亲征南唐,诏吴越国分路进攻常州、宣州。丞相吴程请命出击常州,另一位丞相元德昭反对,说:“唐,大国,未可轻举也。若我入唐,而周师不至,能无虑乎?”吴程又以“元丞相不欲出师”为辞,煽动将士殴打元德昭。钱弘倜一方面命吴程率兵攻取常州,另一方面又“匿德昭府中”,加以保护。后来吴程兵败而归,被“悉夺其官”(25)。从钱弘倜对吴程、元德昭的不同态度,也说明其本人的主旨也在于借后周之力以对付南唐。
总之,钱氏吴越“善事中国”、“勿废臣礼”,其真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吴国(南唐),是一种远交而近攻的策略。
三、关于“不兴兵举”
说钱镠“保境安民”国策者,大凡都以其“不兴兵举”为最重要措施。
其实,在军阀混战、藩镇割据局面下,“不兴兵举”,不但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也行不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说得好:“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只有在“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才能没有战争。战争是矛盾斗争双方的事情,不是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不是钱镠想“免动干戈”就可以免动干戈的。唐末五代的割据军阀,有的本来就是封建军阀,有的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他们的割据政权正是在互相争战中建立起来的,不是在战争中巩固、壮大自己,就是在战争中被削弱、消灭,“免动干戈”是暂时,战争是永存的,钱镠及其吴越国也不例外。
钱镠,用他自己的话说:“十七而习兵,二十一投军,……二十四得功,……垂五十余年,身经数百战”(26),从阻击、镇压黄巢起义军在浙江的活动起家,成为割据两浙的吴越国王。如果说刚刚投军时主要是为“生计所迫”的话,那么后来就不同了。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时,杭州已建以董昌为主的八都之兵,钱镠任都指挥使,唐朝诸道行营都统、淮南节度使高骈召董昌、钱镠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共议破黄巢之策,钱镠即说:“窃窥高公无讨贼之志,苟从其行,功效不立,是同坐罪。宜以捍卫乡里为辞……而归。”(27)反映了钱镠已萌有割据之心。到了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董昌称帝,其割据两浙的计划已经形成。董昌据越州(今浙江绍兴)称帝,给杭州钱镠和扬州杨行密是极大的震动。杨行密企图联络董昌以牵制钱镠;钱镠不愿芒刺在背,企图借此兼并浙东。所以杨行密竭力为董昌开脱罪责,钱镠则务求除之而后快。尽管朝廷一而再地表示赦免董昌,钱镠最终还是斩杀了董昌。消灭董昌以后,钱镠紧接着“令两浙吏民上表,请以镠兼领浙东。朝廷不得已,……以镠为镇海、威胜两军节度使”(28)。对于钱镠的这一行为,当时人们颇为反感。孙光宪《北梦琐言》即说:“钱尚父始杀董昌,奄有两浙,得行其志,士人耻之。”(29)
这里还不妨一提钱镠让贯休改诗的故事:
当钱镠被授为镇海、威胜(后改镇东)两军节度使以后,杭州灵隐寺僧贯休曾投诗祝贺:
贵逼身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莱子丝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
他时名上凌烟阁,岂羡当年万户侯。
钱镠赞赏之余,要求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贯休云:“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孤鹤,何不可飞!”(30)遂离杭而去。
“十四州”和“四十州”之差,最明显不过地反映了钱镠企图割据东南的思想。公元908年钱镠遣使诣后梁“面陈水陆之计,请合禁旅”以攻吴(31)。此后,919年钱镠配合后梁进攻吴国,940年钱元瓘谋取建州(未果),947年钱弘佐、钱弘倧谋取福州,952年钱弘倜遣使后周,谋求共攻南唐,956年积极配合后周进攻南唐,等等,都是钱镠割据东南思想的继续。吴国的疆域,在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后梁与吴越联合出兵进攻时,约有扬、楚、泗、滁、和、光、黄、舒、蕲、庐、寿、濠、海、润、常、升、宣、歙、池、饶、信、江、鄂、洪、抚、袁、吉、虔等30余州。如果能够一举消灭吴国(南唐),完全可圆钱镠“一剑霜寒四十州”之梦,这不能认为只是一种巧合。
综观整个吴越国历史,不但没有做到“不兴兵举”,而且是兵戈不息。据907年钱镠被封为吴越王起,至960年北宋建立止,54年当中,有战事的年分占22年,几乎每2.5年当中就有1年生战事,其中钱镠时代10年,钱元瓘时代3年,钱弘佐2年,钱弘倧时代1年,钱弘倜时代6年,贯穿吴越国历史始终。战争的性质,既有被迫反击、平定内“乱”的,也有主动出击、配合中原王朝出击和援救邻邦的。所谓吴越国“不兴兵举”,实与历史不符。
当然,如前所引,钱镠在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确实说过“不忍兴兵杀戮”的话。但是钱镠此说只是拒绝罗隐等人所谏出兵讨伐后梁朱温的遁词。即便如此,他也把“淮氛未靖”列为头等重要的原因。另外,钱镠还有一层难于启齿的原因,那就是他曾在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向唐昭宗“求封吴越王”,但是“唐帝不许”(32)。而后梁却主动进封钱镠为吴越王,这是正中下怀的事情,怎么可能还会出兵讨伐呢?
此外,欧阳修“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33)云云,亦常被人们引以为吴越国“不兴兵举”之证。其实欧阳修此说主要是指钱弘倜“纳土”归宋一事,而且不过是宋太宗褒奖钱弘倜“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为嘉也”(34)的翻版。再说钱弘倜“纳土”归宋,乃是大势所趋。钱弘倜自己离杭之前已有预感,所以行前一一诀别诸先王陵庙。到了宋都,则正如随从宰相崔仁冀所说:“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飞去耳”(35)。除了“纳土”归宋,别无选择。所以也不足以说明吴越国“不兴兵举”。
四、关于“安民”
“保境安民”,就“安民”而言,不但应该包含不兴兵举、使“民”免受战争之苦,同时还应该包含轻徭薄赋,予民休养生息。但是吴越国与其他诸国一样,也没有做到轻徭薄赋。
欧阳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云:吴越国“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堪其苦”。钱弘倜“纳土”归宋之初,权知两浙诸州军事范旻,也大谈“倜在国日,徭赋繁苛,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之太过,建议宋太宗“尽释不取,以蠲其弊”(36)。
吴越国首先是田税苛重。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云:“两浙田税亩三斗。钱氏国除,朝廷遣王方贽均两浙杂税,方贽悉令亩出一斗。”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亦有同样记载,只是将“王方贽”作“王贽”。未详孰是。《十国春秋》卷八七《江景防传》又云:“当五代之时,吴越以一隅捍四方,费用无艺,其田赋市租山林川泽之税,悉加额数倍。宋既平诸国,赋税恒仍旧籍以为断。忠懿王入朝,景防以侍从,当上图籍,叹曰:‘民苦苛敛久矣,使有司仍其籍,民困无已时,吾宁以身任之。’遂沉图籍于河。诣阙,自劾所以亡失状。宋太宗大怒,欲诛之,已而谪沁水尉。遂屏居田里以卒。”足见吴越国田税苛重。应该说吴越国从钱镠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致出现了“斗米十钱”(37),“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38),以及国有“十年蓄积”(39)的景象。虽不及南汉博白是(今广西博白)“斗米一、二钱”(40)及后蜀的“斗米三钱”(41),其成就也是相当显著的。但是吴越国人民的抗灾能力却很低。一遇灾荒,不是鬻子卖女,便是就食他乡。究其原因,主要就是赋税苛重,民无余资。
吴越国苛捐杂税繁多,“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凡薪粒、蔬果、箕帚,悉收算”。此外,吴越国还向民间征收一项称作“身丁钱”的人口税。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云:“吴越旧式,民间尽算丁壮钱,以增赋舆。贫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据陈师道《后山丛谈》记载:“吴越钱氏,人成丁,岁赋钱三百六十,谓之‘丁身钱’。民有至老死不冠者。”五代时期,南方吴、楚、闽、南汉等国都征收人口税,但据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一说,以吴越国为最重。《资治通鉴》卷二八八记载,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钱弘倜的臣僚“或请纠民遗丁以增赋,仍自掌其事,弘倜仗之国门。国人皆悦”。说明吴越国自始至终都在征收“身丁钱”。
吴越国的徭役也累年不断,人们为之怨声载道。吴越天宝三年(公元910年),钱镠“广杭州城,大修公馆,筑子城”。人们不胜其苦,遂在城门贴出民谣云:“没了期,没了期,修城财了又开池。”钱镠见了,不但没有悔悟,反而将民谣改为“没了期,没了期,春衣财罢又冬衣”(42),认为这是理所当然,钳制了人口。吴越国时期,除了几次修建杭州城之外,还修建了余杭城、嘉兴城、睦州城、温州子城、富阳东安城、常州福山城、萧山西陵城、松江城、苏州城及福州东南夹城等。据皮光业《吴越国武肃王庙碑》说,仅钱镠时期所筑城垒就有50来处。可见徭役之繁重。
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带给了人民极大的灾难。所以《咸淳临安志》卷五九说:吴越国其民虽“免于兵举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安民”二字,实际上并无依据。
注释:
① 《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引。
② 《周书》卷四四《杨乾运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及胡三省注。
⑤ ⑦ 《十国春秋》卷三六。
⑥ 《钱氏家乘·武肃王遗训》。《钱氏家乘》另有一篇《武肃王八训》,也有“自固封疆,勤修贡奉。吾五十年理政钱唐,无一日眈于三惑,孜孜矻矻,皆为百姓”等语。
⑧ ⑨ (26) (37) 《钱氏家乘》。
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11) 《资治通鉴》卷二七七。
(12) (13) 《钱氏家乘》。
(14) 《十国春秋》卷一五《南唐烈祖本纪》引《钓矶立谈》。
(15) (31) 《十国春秋》卷二三《王景仁传》。
(16) 《资治通鉴》卷二七○及胡三省注。
(17) 《旧五代史》卷一二八《裴羽传》。
(18) 《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
(19) 《十国春秋》卷一五《南唐本纪》。
(20) 《十国春秋》卷七九《吴越世家》。
(21)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
(22) 钓矶闲客:《钓矶立谈》。
(23) 《十国春秋》卷八○吴任臣“按”及“论曰”。
(24) (25)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
(27) 《吴越备史》卷一。
(28) 《资治通鉴》卷二六○。
(29) 《北梦琐言》卷五。
(30) 《十国春秋》卷四七《贯休传》。
(32)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
(33)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有美堂记》。
(34) 《宋史》卷四八○《吴越钱氏世家》。
(35) 《十国春秋》卷八七《崔仁冀传》。
(36) 《宋史》卷二四九《范旻传》。
(38) 《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39) 《吴越备史》卷三。
(40) 《十国春秋》卷五九《南汉中宗本纪》。
(41) 《蜀梼杌》下。
(42) 《十国春秋》卷七八《吴越武肃王世家》下。
标签:安民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十国春秋论文; 吴越王论文; 唐朝论文; 五代十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