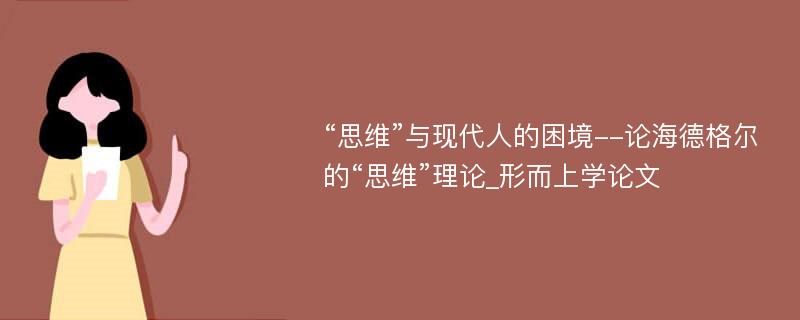
“思”与现代人的困境——海德格尔的“思”论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现代人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现代人困境的思考,海德格尔早期是从存在的意义之被遮蔽且此事一直为形而上学所遗忘这一角度出发的,着重生存论方式,从此在的存在机制来阐发存在的真理;此在对存在的意义的“领悟”是生存论得以展开的关键所在。后期的海德格尔则直接从存在论入手,强调要善于倾听存在的天籁之音,以“思”与“诗”来营建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家,把深受形而上学所害的“逻辑语言”还原为“思的语言”,以便为无家可归的人寻找一条可能的“林中道”;“思”在此担负着开路先锋之责。此“思”与早期的“领悟”一脉相承。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人能否走出“理性”所掘之“技术之渊”,对技术世界保持一种自由的关系?能否在传统形而上学丧失对技术进行本质思考的能力之后,把被技术架构于此因而身不由己的人重新唤回,从沉沦于存在者的境界中解放出来,看护存在的真理?这些都有待于“思”,有待于比形而上学思得更原始的“思”,有待于反逻辑的“思”、反价值的“思”。
有意思的是,海德格尔的“思”论不断遭到指控,认为它是随意性的牺牲品,不能被证实:“海德格尔如何能够说明这种思想不是随意的?如果它不是随意的,思想从哪里对它做出估量?什么样的法则支配它的行动?海德格尔凭借什么标准,衡量存在的真理,或者揭示存在向人展示的存在之真理的价值?”(注:《人道主义问题》,大卫·戈伊科奇等编,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译文略有改动。 )海德格尔的“思”论无疑在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值得认真研讨。本文仅就“思”与“技术人”、与理性、逻辑及实践的关系以及“反价值的思”的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技术人”
海德格尔对现代人状态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现代人现在已经完全被摆布到群众活动中去了,彻头彻尾是一种“技术人”。在《存在与时间》中,正如伽达默尔所言,海德格尔“强烈指责工业社会凭借其越来越牢固的一致性、凭借其社会交往的技巧和控制一切的公共关系,造成了一切个体生活形式的整齐划一。”(注:《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这种整齐划一的“技术人”维系自身于可靠的固定状态的方法,只是靠技术统摄下的计划、聚集与秩序而已。因此,技术人须加以约束,于是专事规诫的伦理学就愈益为人所需了,结果却是人愈发陷入彷徨无计状态而不能自拔。“当人把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以建设之际,人就把自己通向敞开者本来已经封闭的道路,蓄意地而且完完全全地堵塞了。”(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433页。)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使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因此,人本身及其事物都面临着一种危险:变成单纯的材料及对象化的功能。“技术的制造使世界井然有序,其实恰恰是这种井然有序把任何秩序(ordo)都拉平为制造的千篇一律,从而自始就把一个可能出现秩序和可能从存在而来的承认的领域破坏了。”(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 434-5页。)这个危险不是在偶然的危难中(如原子弹)、而是在人对存在本身的关系中威胁着人的本质。
现代人对这种危险的反应是逃到伦理学中去寻求庇护。人迫切需要有关责任感的指示,迫切需要说明人当如何合乎天命地生活以摆脱彷徨无计状态的规诫,人嗷嗷待哺,聊以济急的伦理学仿佛是挤进“技术人”口中的乳汁,暂且把人的本质保持在今天的状态中。而这在海德格尔看来恰恰是现代人的莫大悲哀。伦理学的迫切需求指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的存在出了问题。
海德格尔意不在废除伦理学,而是要从其中揭示出存在的被遗忘状态,唤醒人们去“思”存在的意义。他说:“当存在隐藏在长期的被遗忘的状态中并在当今世界历史时刻通过一切存在者的震动而透露出消息来之后,难道思还能使自己免除思存在的责任吗?”(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396页。 )这里海氏呼吁的“思”,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思维”或“思想”(后者已为“逻辑”、“文法”所坏),而是既听从存在而又属于存在,即按其本质来历而存在的东西。这种“思”是原始的“思”,比形而上学思得更原始。
但伦理学不是这种原始的“思”,因为它思而不听从存在,即不从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关联来思。以伦理学来应付当今灾难,尽管可收一时维系人的本质于当下之效,但却极易遮蔽存在被长期遗忘的状态,从而导致存在的湮湮无闻,人仍然无家可归,徨徨然如丧家之犬。伦理学不是人的家园,不堪当此大任。人欲向伦理学索取的太多,伦理学能够给予的则太少。人的索取用一句话讲,就是“有从生存到存在的体会的人应当如何合乎天命地老练地生活”(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395页。)? 而伦理学给予的只是维持现状。“思”付之阙如,拯救无从谈起。
二、“思”
海德格尔认定拯救须从人的本质攸关之处着手,从“思”着手:于是便追究存在的真理,由此来思人的本质问题。“思作为思须在思一切之前先思存在的真理”(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396页。), 存在的真理作为生存着的人的一个原始的基本成分,是“思”的本质根据。因此,“思”从生存对存在的从属关系来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生存”。
“思”的特点是“它说,它在,它满足”,即当它说它的事情时,它就在;而当它在时,它就使其本质满足。但“思”并非胡思和乱说。海氏认为,“思”的约束力在本质上比各种科学的效力更高,“因为此种约束力让存在去存在”(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400页。)。 “思”致力于建立有组合作用的“存在的家”,把人的本质处理到存在的真理中去。然而“思”从来不创造“存在的家”。思所做的是,把有历史性的生存带入存在的澄明中去,在此澄明中美妙事物与恶劣事物一并出现。海德格尔告诫道:“只有当人生存入存在的真理中去并从属于存在的时候,来自存在本身的那些指示之分发才会来到,而这些指示必须成为人所需的律令与规则。……只有这种指示的分发能够把人调配到存在中去。只有这样的配置才能够担带与约束。此外一切律令始终不过是人类理性的滥造之品。”(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402页。)
海德格尔在此对伦理学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伦理学律令不仅不能使人生存入存在的真理中去,而且更糟的是它会使人在所谓“理性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远离存在的意义,并且对此浑然不觉。因此,首要的事情不是订定规则,而是找到居留到存在的真理中去的处所。存在的真理使语言成为存在的家,把人守护到存在中去。
然而,能作存在之家的语言却并非是已被逻辑、语法戕害了的形而上学语言,而是那种由“思”的第一规律而来的语言。“把存在作为真理的天命来说,而且要说得适合天命,这是思的第一规律”(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405页。),此第一规律并非逻辑规则,而是逻辑诸规则由以变成规则的存在的规律。它要求:A.“每一次都要深思要说存在的什么以及要如何说存在”;B.“是否可以说此有待于思的东西,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在存在的历史的什么时刻可以说,在什么对话里可以说,从什么需要可以说。”(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405页。)可见,思的唯一事情就是时时把存在的持续到达形诸语言。
困难是,由于“现在存在(ist )的事物就处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早已先行在前的命运的阴影之中”(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578页。), 属于存在且听从存在的“思”于是不得不试着在此阴影中道说存在。在形而上学独霸天下的今天,当我们对任何一物一事作出某物是什么或某事怎么样的判断时,其实我们都已经是在形而上学中说话了。形而上学的终结者——尼采的情况就是这样。尽管他对形而上学作了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批判,但他所用之语言尤其是语言之结构如“什么是”等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即仍然是在ist的统摄下进行的。
逻辑对语言的霸占已经使人们很难用非形而上学方式讲话了。一说某物是什么,某事如何,就落入了本质与现实的区分之中,就把在场本身与在场者混为一谈了,即在场仅仅被看作在场者的最普遍的和至高的东西,从而被看作这样一个在场者。在场之本质,以及与之相随的在场与在场者的差异,始终被遗忘了。“思”沉沦了。“思之沉沦为科学和信仰,乃是存在的恶劣的命运。”(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565页。 )形而上学的逻辑遮蔽着存在隐含的本质丰富性,从而使存在遭受沦为最空洞的、最普遍的概念的不幸。概念语言只有基于对作为“相”的存在的解释才是可能的。从柏拉图以后,这种以种类和共性的逻辑说明方式来表象的概念语言就不可避免了。现在的人几乎已经丧失了以非概念方式说话的能力:言必有据,言必有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所谓有理即讲逻辑。理直气则壮。人们完全遗忘了,概念的霸权和把思想解释为一种概念性把握的做法,仅仅建基于未曾被经验的存在者与存在之差异的被遗忘状态之上。
三、“思”与理论及实践
“思”的行为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践的,更不是这两种活动方式的结合。倘若按科学认识的方式来设想这种“思”,或就实践的成就来衡量这种“思”,我们会发现这种“思”没有结果亦无作用。“思在其说中只把存在的没有说的话形诸语言。”(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403 页。)存在的“思”超过一切理论思考,因为它所注视的是光明,是存在的澄明,而理论唯有在此种光明、澄明中才能停留与活动。所以“思”是一种行为,但却是一种同时超过一切实践的行为。“思”突出于行动与制造之上,并非靠其成就之巨大,而是靠其思得比形而上学更原始。
“思”所以能思得比形而上学更原始,是因为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已经自行挤到此境,有一种觉悟开始苏醒过来,这种觉悟不仅思及人,而且思及人的自然本性,不仅思及自然本性,而且它还更原始地思及到:从存在本身方面来规定的人的本质才有在家之感。形而上学只关注人及人的自然本性,其对人的社会性的涉及也是在“理性人”这个大前提下,亦即是在人的自然本性的视域中展开的;而比形而上学更原始的“思”则有三度:人—自然本性—存在视域中的人的本质。此乃更原始之所在。
这种更原始的“思”永远不允许自己高居于理性的法官席上,作出高高在上的决断。理性根本不是公正的法官。它肆无忌惮地将所有那些与它不相符的东西都看作是臆造之物,并且还将它们排挤到由它自己划定的非理性主义的泥潭之中。理性以及对它的想象只是“思”的一种,它决不是通过自身而得到规定的。理性在对所有秩序进行理性化、规范化、平均化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向非理性主义遁逃的企图亦在此过程中产生。“思”却能够执着地置身于理性非理性的非此即彼的范围之外。
但逻辑不懂这些,逻辑把“思”了解为在概念的共通内容中进行意象的存在者的意象。而思存在的真理的“思”才抓住了逻各斯的原始本质。与“逻辑”相反对的思,就是要追思逻各斯的本质。在人们言必称逻辑的当代,否认理性的反理性主义正在悄悄地占着统治地位。原因在于,逻辑自信可以躲掉对“逻各斯”及基于其上的“理性”的本质所作的深思。其实逻辑正以自己发明的一种虚无主义来阻止对别的东西进行自由的眺望。这种虚无主义的特征在于,逻辑事先就把自己所认为的东西定为“肯定的东西”,并从这个肯定的东西来对可能反对该东西的领域实行绝对的否定。反逻辑或非逻辑就有原罪,就是死路一条。“逻辑霸权”酿制的虚无主义反而使反理性主义乘虚而入,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海德格尔指出,欧洲性的虚无主义现在日益显示出它的全球性趋势,正以各种形态不可抑止地遍及全球、吞噬万物,竟然成了人类的一个“正常状态”(尼采)。这一点已经日趋明显,其最好证明就是人们仅仅以反应的方式来反对虚无主义,不去深入分析虚无主义的本质,而只是对现今已有的东西进行修修补补。人们在遁逃中寻找拯救,回避人的形而上学的困境,不是对形而上学的本质进行质问,而是企图放弃所有形而上学,并用逻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来取而代之,以为这样就能获得解救。
其实,这就远远背离了“思”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当“思”思维着的时候,“思”就行动着,此一行动是最简单的行动,同时又是最高的行动,因为此一行动关乎存在对人的关系。“思”的历史任务正是完成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关系,把存在之可发乎外的情况形诸语言并保持在语言中。
但形而上学以“逻辑”和“文法”过早地霸占了语言的解释,语言之愈来愈厉害地被荒疏正是由于人的本质之被戕害,形而上学使语言几乎是无可遏止地脱出它的基本成分即存在的真理了。把语言从文法中、从因果之网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更原始的本质结构,即存在的真理之家,这就是思和创作的事情。这种事情不是通常所谓之“理论”,亦非通常所谓与理论相对的“实践”。视“思”为“理论”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将“思”作技术解释的结果。在他们那里,“思”是一种技术,为“做”与“作”服务。把“思”称为“理论”与把“认识”规定为“理论的”行为,都已经是在对“思”下了这种“技术的”定义的范围内发生的事情。
在海德格尔那里,“思”不是一门类似其它科学的任何一种科学,不是任何一种理论,而首先是一种行动,一种把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关系形诸语言的行动。但这种行动不是普泛所谓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因为它没有任何实践意义上的功利作用。向“思”要功利之用,无异于缘木求鱼。
“思”被贬为理论以便为行动服务,这种对“思”的技术解释损害了“思”的本性。毋宁说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待乃是“思”的丧失。只要“思”在,“思”就行动着,“思”永远是关乎存在的,而存在的历史则承担着并规定着人类的任何条件与情势。“思”的根本问题是要解决或更准确地说是要探讨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关系问题:存在在“思”中形诸语言表现出人的本质。而这种探讨是历史性的,不可能一思永逸。
四、反价值的“思”
因此,针对现代人为技术所迫无家可归的困境,“思”须反逻辑而行,反价值而思。如果把海氏反价值之“思”理解为主张人们认为是“价值”的一切东西——“文化”、“艺术”、“科学”、“人的尊严”、“世界”与“上帝”——都是无价值的,那就未免把海氏理解得太浅显了。诸“价值”自有其价值。但问题是价值化本身倒剥夺了被价值化的东西的尊严,因为价值化其实就是一种对象化,即把被价值化的东西设定为为评价人而设的对象。“但一种东西在其存在中所是的情形,并不罄于它是对象这回事中。”(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392页。)也就是说,“对象化”、 “价值化”并不能穷尽存在者的存在,而形而上学却认定存在者在其存在中所是的东西仅此而已。坚持对存在者“对象化”、“价值化”的结果是:存在被遮蔽。
海氏指出:“一切评价都不让存在者:存在,而是评价行为只让存在者作它的行为的对象。”(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392页。)与“思”不同, 一切评价都是一种主观化。把上帝宣告为“最高价值”是最大的亵渎神明之事。反对价值的“思”,并不是要鼓吹存在者的无价值与虚无,而是要反对把存在者主观化为单纯对象,是要把存在的真理的澄明带到“思”的面前。
问题在于,人不评价、人不作为、人不将存在者对象化,人不使世界价值化,何以为人?海德格尔的回答是:人是存在的看护者,而不是存在的主人,也不是存在者的实体或主体。因此,“人这样地生存着,看护存在的真理,以便存在者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在存在的光明中现象。至于存在者是否现象以及如何现象。上帝与诸神、历史与自然是否进入存在的澄明中以及如何进入存在的澄明中,是否在场与不在场以及如何在场与不在场,这些都不是人决定的了,存在者的到来是基于存在的天命。”(注:《海德格尔选集》,海德格尔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第374页。)
换言之,人不可仰仗理性为所欲为,蒙蔽存在的真理。人须做的是放弃形而上学的语言,开辟一条通向存在本质之探讨的道路,以此方式来沉思虚无主义的本质,沉思存在的真理,同时也就是沉思人的本质。在此道路上,人得以更原初地去经验存在者,去经验现代技术世界整体及自然和历史,而首先是去经验它们的存在。人的本质则在此道上历史性地展开为命运性的东西,被保存于存在中,并被存在释放出来,但决不与存在分离开来,而是看护并维持存在、使存在成形。这是一条循环的道路:在规定者与被规定者的相互关系中缠绕着一个循环,但此循环不能看作是非逻辑的思维的证明,而应被视为:在这里始终要思考整体的圆。对这种思而言,以无矛盾性为尺度的“逻辑学”永远不能成为标准。向这种思提出逻辑的要求,只能是重新把它诠释为概念的、形而上学的和技术的思想;而这正是海德格尔所竭力反对的。反逻辑的“思”、反价值的“思”的意义正在于此。现代人的拯救之道亦正在此“思”所开启的存在的真理之中。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伦理学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