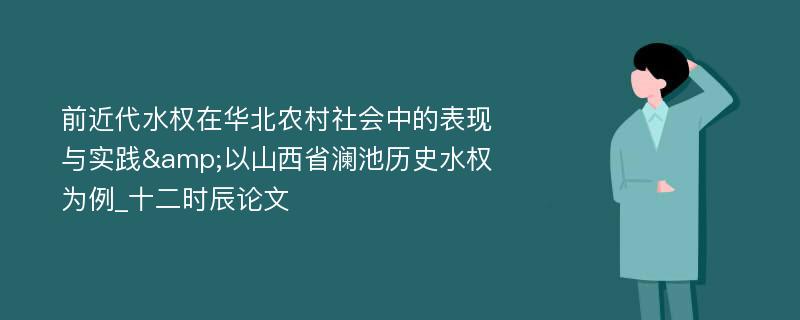
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的表达与实践——山西“滦池”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论文,山西论文,个案论文,近代论文,乡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年九旱,水资源匮乏乃是华北地区自前近代以来就已浮现且日益加剧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近年来的社会史研究中,对历史时期水利与环境、水利与社会问题的探讨几成热点,与此不无关系。研究者选择不同的角度,借助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展这一问题的研究,成就斐然,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涉及与水相关的组织、结构、制度、权力、文化象征等各个方面。①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运用“水利社会”这一概念,在回应和挑战美国汉学家魏特夫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东方治水专制主义”理论的同时,试图通过探讨“以水为中心延伸出来的一套社会关系体系”来解释前近代以来的华北乡村社会及其变迁,从而构建具有本土化色彩的理论解释体系。②本文正是顺应这一思路开展的一项实证研究。
本文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本文将围绕集体产权与私有产权二者的相互关系问题展开充分论述,通过历史个案研究揭示集体产权与私有产权各自的初始状态及发展变迁过程。尽管近年来学界围绕该问题的讨论已有不少,但多从现实社会制度变迁的角度切入,缺乏从历史维度进行的解释。其二,对一些具体观点的质疑和反思,如有论者将明清以来山西省汾河流域水利纠纷不断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水资源的公共物品特性及随之而来的产权界定困难问题,认为水资源所有权公有与使用权私有的矛盾是问题的根源所在。③这一解释虽然涉及产权问题,却未抓住问题的要害。问题的关键在于自前近代以来水资源作为一种稀缺性公共物品,其产权能否被合理界定,在实践中又是依据何种标准来界定的,究竟存在哪些制约因素,这绝非“产权界定困难”一般简单,也并非“公”与“私”的矛盾对立。
以上两个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产权问题。产权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最初的讨论大多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继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框架中进行的,引入产权分析也是中国学者在理解和提供改革方案时的一项重要工作。④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及人类学者加入其中,使有关产权问题的讨论已经跨出经济学范畴,进入了整个社会科学的视域。研究者们普遍注意到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权模糊”的乡镇集体企业在产权选择上的多样性,并不符合产权理论所谓“产权清晰”、“产权必须私有”这一基本要求。由于产权理论不能既解释“私有制”的成功,又解释“集体制”的不败,因而陷入逻辑困境。新近一些从组织社会学制度学派和“关系网络”学派以及人类学解释逻辑出发的研究为解释这一悖论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对此,折晓叶、陈婴婴已进行了及时的总结和评价,并进一步就“产权如何界定问题”做了深入讨论。以上研究中贯穿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产权存在被社会关系网络非正式界定的可能性。⑤产权不仅存在被非经济因素界定的可能,而且并不总是为效率原则所驱使,还受到政治过程、文化观念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使产权处于被反复界定的状态。⑥这些研究最终走向与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直接对话,“关系合同”和“关系产权”两个新概念的提出即可视作这一对话的初步成果。⑦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展,这样的对话将会持续进行下去。
本文对水权问题的讨论与上述研究思路比较贴近,不同之处在于:以往的研究多限于讨论当代中国社会的产权问题,对历史时期的产权问题也因缺乏典型的分析个案而较少关注。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文化积淀相当深厚的社会,当前很多社会现实问题与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并由此导致了中西方社会的诸多差异,具有“中国特色”。因此,对于产权理论,不仅要置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加以检验,也要求我们将视线拉长到前近代的中国乡村社会进行验证,以加深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形成客观的、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理论解释体系。
作为本文分析对象的“滦池”泉域,位于山西省境西南部的翼城县。翼城县地居中条、太岳两山之间,夏商时期为唐国,西周初为唐叔虞始封之地,春秋时期曾为晋国都城。西汉属绛县。北魏太和十二年置北绛县,隋开皇十八年改为翼城县,唐改称浍川县,宋复名翼城县。金升为翼州,元复为翼城县,沿用至今。“滦池”泉水发源于翼城县东南20里南梁村东,泉水流出后汇入浍河,由浍河再入汾河,属汾河水系,过去有东西二池,至宋熙宁年间,将两池砌为一池。1966年,在池南又新掘一池,名为利民池。现为南北二池。东依翔山,西临浍河,地处丘陵地带。
滦池一带村庄完整地保存有宋、金、元、明、清以来历代水利碑文,共计15通。其中,年代最早的是金大定十八年(1178),最晚的是清乾隆六十年(1795),这也是本文选取“前近代”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碑文按内容可分两类,一类以建庙祭祀为主,一类以水利争讼为主,内容连贯,可前后互证,学术价值极高,因而成为探讨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状况的一个理想个案。
一、权利分配:“初始水权”的形成及其特点
对泉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前近代山西社会的一大特色。该省尽管干旱少雨,却得益于特殊的地质构造,全境内尤其是汾河流域分布有众多断层出露的泉眼,翼城滦池泉即在此列。与山西其他泉水灌区相比,“滦池”灌区规模并不算大,历史时期受益村庄最多时仅12个,可灌溉土地4 800余亩。尽管如此,该泉域内村庄获取初始水权的方式却多有不同,错综复杂。
(一)初始水权村的形成
据碑刻文献和田野调查情况来看,滦池泉域12村的初始水权是分阶段获得的。当地人在描述传统时代各村用水状况时,习惯于使用“上三村”、“上五村”、“下六村”、“十二村”等地方性词汇。我们也从此惯习来展开分析。
1.上三村水权
碑刻中关于上三村的最早说法,是指位于滦池发源地的南梁、崔庄和下流(又名清流)三村。⑧后亦有南梁崔庄、涧峡、清流三村之说,⑨此说中南梁与崔庄是合二为一的。乾隆五十六年《滦池水利古规碑记》中又出现了第三种说法:“宋熙宁年间,南梁、涧峡始同下流运石修砌,合二池为一池。池庙废坠,又同下流修理,嗣后乃称为上三村也。”⑩即南梁、涧峡和下流三村。后两说中,唯有南梁与南梁崔庄称谓不同,且均出现在清代。由此可知,金代涧峡可能尚未独立成村,属南梁或崔庄二村之一。自金及清,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村庄设置及规模发生了变化,遂演变成后二说。
上三村初始水权的获得完全依赖天然地理优势。在滦池泉域,“用水之利者,实有二例:上村者以为己业,下村者盖出工力”。(11)此言高度概括了滦池泉域上下游村庄获取水权的不同途径。正因为上游村庄将滦池水视为己出,故有“其近水源头系南梁、崔庄、清流等村,各使水浇地,乃开辟以来自然之利,迄今无异”(12)的说法,得到周围村庄的普遍认同。不仅如此,上三村在用水时间和数量上也不受限制,“南梁、崔庄于东西二池取水,亦不计时候,麻白、地土、蒲汀、稻圃、花竹、果园任意自在浇溉、并无妨碍。外有下流村,接连南梁、崔庄同渠取水,自在浇溉”。因此,我们可将上三村视为滦池泉域享有特权的用水村。
2.上五村水权
上五村是指上三村之外,再加西梁(又称川西梁)和故城二村,合称上五村。有关上五村的说法,最早出现于大定十八年《平阳府绛州翼城武池等六村取水记》,该碑有“其泉水浇西梁、故城、南梁、崔庄,下流五村人户民田”的记载,这里所讲的乃是宋熙宁三年以前滦池受益村庄的情形。
此后,至元九年“重修乔泽神庙并水利碑记”中又出现了“上五村”这一称谓,并对各村水权状况做了更为明确的解释。关于西梁和故城二村的情形,据至元九年《重修乔泽神庙并水利碑记》载:“川西梁于东池内取水,往北行流,自在浇溉。然验各村地盘,一体浇溉。上村使余之水,退落天河。自熙宁三年,有武池村李惟翰、宁翌等纠集下六村人户,于故崔忠磨下,截河打堰,买地开渠,取上村残零余水。故城村常永政为不要买渠地价,六村人户许令自在浇溉村南夹河地土,此后通称为上五村也。”
通过比较可知,西梁村获取水权的方式与上三村类似,同样占据天然之利,只不过该村用水历来自成体系,与他村无关。与之不同,有“上三村”之称的南梁、崔庄和清流则因共用一渠之故,“捆绑”在了一起。熙宁三年下游六村在国家政策倡导下进一步开发滦池水利时,又因要“取上村残零余水”,与上三村在用水量和用水时辰的分配比例上存在关系,故“上三村”这一称谓只是相对于下游六村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故城村的取水权则源自于熙宁三年该村人常永政的义举。当年,下游六村从该村买地开渠,花费甚巨,如《大朝断定使水日时记》就有“熙宁三年武池村李惟翰、宁翌等备价铜钱千余贯于故城村常永政处,买地数十余段,萦迂盘折,开渠引水浇溉”的记录。因常永政不要这“千余贯铜钱”的“买渠地价”,换来了下游六村允诺的“自在使水”特权,令其子孙后代和村人受益。
综合言之,“上三村”与“上五村”两个称谓,均体现了“有关村庄在滦池水资源利用方面享有特权”这一深刻意涵,同时也表明:先天地理优势和水利草创时期先人的义举,乃是前近代时期华北乡村社会获取用水特权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
3.下六村水权
滦池泉域“下六村”这一称谓的出现则是拜熙宁三年王安石变法所赐,是“熙宁水法”在地方社会的集中体现。顺治六年《断明水利碑记》记载,下六村是指“首吴村,次北常村,再次武池村、马册村、南史村、东郑村”。熙宁三年以前,“上村使余之水,退落天河”(至元九年《重修乔泽神庙并水利碑记》),白白流走,不得利用。熙宁三年,由武池村大户李惟翰、宁翌牵头,纠集六村人户,谋曰:“可惜此水,始自创意擘划,买地开渠。”(大定十八年《平阳府绛州翼城县武池等六村取水记》)至元九年《重修乔泽神庙并水利碑记》对此事件记载最详:“自熙宁三年,有武池村李惟翰、宁翌等纠集下六村人户,于故崔忠磨下,截河打堰,买地开渠,取上村残零余水……下六村人户,各验愿出买渠价钱,分番使水,定作日期:吴村七时辰,北常三十时辰,武池九十一时辰,马册村一十九时辰,南史一十一时辰,东郑二十一时辰,通计一十五日轮番一次,计一百八十时辰,内余一时辰,令六村人户交番费用,周而复始。”可以说,下六村“取上村残零余水”开发水利的举动,一方面是得到北宋政府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水就下”的自然流动特性使然,非上游所能垄断。从以上记载中同样可见,下六村初始水权的获得,是在六村各自出钱、出力基础上换来的,同碑对六村的用水义务也做了规定,“六村人户于故崔忠磨上并东西二池以下渠路,并无淘掘之分”,因这段渠路属上三村所有,但要负责“故崔忠磨”以下渠路的淘掘之分,所谓“下村者盖出工力”即是此意。不过,至元九年碑对六村使水日期多寡不均的现象却未做任何解释。对此,顺治六年《断明水利碑记》做了清楚的补充说明:“其村大地多者出钱,费工各多寡不等,及至成功事竣,各照原出买渠价钱并开浚工力及地亩多寡,分定使水日期……每岁自清明日起从上至下,计十五日轮遍一番,周而复始,毫不容紊。至中秋后雨水滂沱,则不拘番次时刻,听其随便取用。”这就表明,六村初始水权的分配并非按照绝对的平均主义,也非以土地多寡,需水大小来配置资源,而是在特定时代场景下以参与水利开发的众村人户普遍接受的一个所谓的“公平”原则进行分配。水利创始之初的这一分配原则,为后世的水权争端埋下了无穷隐患。
4.十二村水权
十二村是在上五村和下六村之外,再加西张村,构成滦池泉域享有用水资格的十二个水权村。熙宁三年下六村在“故崔忠磨下”截河打堰,开渠引水后,西张村和下六村中的东郑村(两个位置偏下的村)合作,仿效下六村之举,截留六村石堰间透流之水,于马册村南桥下,“其西张村与东郑村各截河打堰轮番使水,以上流下接,西张村与东郑村并此水浇上下一十二村”(至元九年《重修乔泽神庙并水利碑记》)。这样就奠定了滦池泉域十二村共享水利的大势。
5.十二村以外的无水权村
从地理形势来看,滦池泉域并非只有上述十二村具备利用泉水灌溉的条件,梁壁、西郑、李村等邻接村社均具备引水条件,却从来没有获得过使水权,至元九年碑中就有“一十二村之外,其余邻接村社,并无使水之分”的记载,明确限定了权利边界。对此,大定十八年《平阳府绛州翼城武池等六村取水记》中有专文说明:原来,在熙宁三年武池等六村决定截河打堰挖渠之初,“有梁壁、西郑、李村人户薛守文等状告乞与上六村同共取水。及下手,薛守文等意恐不成,下状退免。六村人户李惟翰等截河田垒堰买渠取泉水,随地势萦迂盘屈经历将崖曲折,引水得行。未及浇溉,却有梁壁等村薛守文等状告乞侯例纳买渠钱,使水浇田,州县守夺未决,即重提举护秘丞归折,举其略曰:薛守文等洛见功效一成,便欲攘夺其利,情理切害。又有云:只令上六村使用财力人使水,薛守文等不得使水。文案已于当时刻之于碑后”。可见,梁壁等三村并非没有用水机会,只因三村领袖薛守文在开渠过程中的反复无常,不与六村戮力同心,致使他们丧失了本能享有的水权,并为此丢尽颜面,为时人所不齿。至今在滦池泉域尚流传有“梁壁村无别计,丢了水权缠簸箕”的俚语,足见该事件在当地社会中的影响。
(二)十二村初始水权的特点
结合上述事实与滦池历代水利碑文,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的外部特征。
首先,水权占有上是分等级的。从十二村总体来看,上三村使用和支配水的幅度、灵活性远较下六村为大,且占有明显优势。“南梁发源之地,为十二村之首。所以南梁任意自在浇灌,不计时候,非别村可比”,(13)即是对这一特点的有力佐证。如果用金字塔来形容的话,南梁等上三村和上五村居于塔尖,武池等六村处于塔中,西张村处于塔底,其余邻接村社则只有站在塔外观看的份儿。
退一步而言,即使在上三村内部,也有高下之分,南梁、崔庄就明显高清流村一筹,且占尽心理优势。清流村为了争取到与南梁村同等的使水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抗争,“至大观四年,下流村任重,告本县李老爷讳察案下,要与南梁分定日期,轮流使水。南梁崔九思等不允。李邑令因水利事大,以神之响应,并下流争水之事,闻于外台,奏宋徽宗皇帝,六月六日旨下,敕封栾将军为乔泽神,令李侍郎讳若水分定水例,断定每年清明起番,八月仲秋落番。南梁使水六日七夜七十八时,下流村使水二日六时。南梁村未收下流过水渠价。谕:下流闸水之日期,与南梁留三分饮牛之水。南梁村挑渠,亦在下流村日期内,以报南梁未受渠价之恩”(乾隆五十六年《滦池水利古规碑记》)。经过这次努力,清流村虽然得以如愿与南梁分水,却又不得不承受两项附加条件,仍然处在低人一等的地位。
此后,下流村仍在为获得对等地位而抗争,“至明洪武七年,下流王思敬等,欲翻前案。南梁渠长解周易等告至李老爷讳谅案下,审出真情。将王思敬等重责八十,仍照李侍郎断案”(乾隆五十六年《滦池水利古规碑记》)。这次努力再告失败,更注定了清流村在上三村中的弱势地位。
无独有偶。大定七年西张村与武池等下六村之间的争水纠纷,同样也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村庄试图获得与其他水权村对等地位的一种努力。武池等下六村的水源是上三村用毕之残零余水,本就比上三村低一格。西张村的水源则是取自下六村的残零余水,比下六村更低一格。大定七年,西张村人将下六村“堰斩豁”,要与下六村三七分水,遭到下六村的严辞拒绝,一时间诉讼纷纭,双方大动干戈。西张村人终因违背旧例,提供伪证而获罪(大定十八年《平阳府绛州翼城武池等六村取水记》),未能改变其低人一等的用水权限,足见滦池泉域村庄水权占有上划分等级的严重程度。
其次,水权分配上不公平不合理。在滦池泉域,一些表面上看似公平的规则,其实却隐含着最大的不公。位于滦池发源地的乔泽庙(即滦池水神庙),向来归南梁崔庄、涧下、清流三村打理,修缮庙宇之资,三村平摊。康熙五十二年,因建庙三村各分摊银57两余。乾隆六十年,又因修庙,三村各分摊银45两余。这看似很公平,但事实上,涧下用水户共57甲,南梁崔庄64甲,而清流村仅32甲。(14)这就是说,但凡有摊派,清流村每次按甲承当的负担分别是南梁崔庄和涧下的2倍或接近2倍。从前文分析中我们知道,清流村在上三村中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村小人少地少,却还要承担同样份额的摊派,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下六村水程分配上也存在不合理的方面。下六村水程期限总计180个时辰,其中,武池村就占有91个时辰,北常等五村加起来才有88个时辰。武池1村有地才11顷,北常村等五村则有地25顷(顺治六年《断明水利碑记》)。尽管这样的水程安排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但单从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来说,明显是不合理的。在用水紧张时期,经常出现武池村水多用不了,北常等五村水少不够用的情形。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导致水的利用效率大大降低,极易滋生买卖水权、以水渔利的现象。
再次,在村庄内部水权分配上也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至元九年碑记载了该年北常村王庆纠集下六村380余人,在滦池东池创开新渠的事件。在该事件中,拥有下六村一半水程的武池村,竟也有以张五为首的一拨人同北常村人一起“闹事”。在官府审理此案的过程中,又有武池村宁七官人名彦当堂指证,批评王庆、张五等人的不法行为。这就从侧面说明在武池村内部可能存在私人或大户独占水权,或水权为部分人垄断的现象。换言之,在该村,占有水权的是一拨人,参与争水的是另一拨人;既有守成派,又有造反派。
(三)村庄水权本身是很明晰的
尽管在水权分配上存在上述两大问题,但就村庄水权本身而言,还是相当明晰的,并不存在论者所谓水资源产权归属和界定困难的问题,也非水所有权公有与使用权私有的矛盾,而是水权界定本身依据特定标准导致其无法被合理界定的问题,在此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1.十二村均有固定用水期限,只要有水源保证,在固定水程内还是能够享有水利的。历代水利碑刻对各村的水程时刻记载最为详细也最为重视,水程期限和用水量受水利规章和社会舆论的双重保护,具有合法性,不容侵犯。2.水权到村,未见到户、到人的现象值得重视。我们可将以村庄为单位分配的水权,视为集体水权。以村庄集体名义将水权分配下来,再按照一定规则在村庄内按甲头、夫头二次分配水权的方式在洪洞、介休等县的渠册夫簿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我们在翼城滦池虽然没有见到类似的渠册夫簿,却不能证伪这一方式的存在。滦池水利碑中频频出现的各村“水甲头”题名和类似于南梁崔庄57甲的记载,足见滦池各水权村同样是按照类似的组织规则分配水权的。
二、权利表达:维护村庄水权的多种方式
“滦池”十二村在完成对初始水权的“瓜分”后,紧随而来的就是考虑采用何种方式,维护既有权益不受侵犯,保证长远发展;一些水权村还想方设法,试图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更多的水权份额;一些无水权村也试图加入用水者行列,争取能分到一杯羹。在此情况下,处在不同地位的村庄中,就出现了多种表达其用水合法性的方式。
(一)“水”、“神”、“权”合一的方式
乔泽神是滦池泉域民众唯一尊奉的水利神。此庙在当地共有两处:一处位于滦池发源地的南梁村;一处位于中游用水大村武池村。两处均称作乔泽庙,但调查中却没有人能够解释两处神庙的关系,二者也非正庙与行宫的关系,非常奇特。
更为奇特的是,每年三月初八日以南梁村为首的12个水权村,要以“殡葬”形式同祭乔泽神,成为历来延续的传统,如康熙五十二年《重建庙碑记》称:“祠宇创自三村,首南梁崔庄,又次涧峡,又次为清流,每年春三月,纠九村□奉祀事,敦请县□□□主,十二村鳞次焚香,灌鬯罔敢不恪。”
在此,我们先对以“殡葬”形式祭祀乔泽神的行为做一解释。应当说,它与滦池的来历有关。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春秋时期翼城曾为晋国都。公元前745年(周平王二六年),晋国新任国君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史称曲沃桓叔,由靖侯之庶孙、桓叔的叔祖栾宾辅佐,而栾宾的出生地即在滦池附近,滦池水利碑中“翼邑东南翔山之下,古有东西两池,晋栾将军讳宾,生其傍,故以为姓”的记载,即是言此。后晋国长期限于内乱。至晋哀侯时,曲沃桓叔之孙曲沃武公伐晋,双方战于汾水河畔,哀侯被擒死难,晋大夫栾共叔成(即栾成)亦殉难。因栾成之父栾宾曾是武公祖父桓叔的师傅,所以曲沃武公有心劝降栾成,但被栾成拒绝,苦战力竭而亡。晋小子侯继位后,为表彰栾成的忠勇,“遂以栾为祭田,令南梁、崔庄、涧峡立庙祀焉”(乾隆五十六年《滦池水利古规碑记》)。可见,滦池庙最初乃是祭祀晋将军栾成的祠宇。至宋大观四年,“县宰王君迩曾会合邑人愿,集神前后回应之实以闻朝廷。至五年,赐号曰乔泽庙”(金大定十八年《重定翔皋泉水记》)。由是栾将军祠始改称乔泽庙,并长期沿用下来。因三月初八为栾成忌日,故每年滦池十二村要在此时以殡葬形式祭祀他。(15)
以南梁村为首的上三村正是凭借这一历史渊源,在一次次隆重祭祀乔泽神的庄严仪式中,将其用水特权与冥冥神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巩固和强化了其在滦池泉域的特殊用水地位。由于乔泽神是滦池泉域最尊贵的神祗,其他水权村也不敢丝毫怠慢,纷纷加入到这一近乎狂热的祭祀行列中,似乎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使其合法的用水地位得到确认和表达。
地方人士对这一祀神活动中极尽奢华的场面多有描述,据记载:“每年三月初八日为行幡赛会祭祀之日,每到此日以殡葬形式祭乔泽神。定为南梁村、涧峡村、故城村、清流四村为行幡,其余各村都是挂幡,十二村轮赛。每年一小祭,十二年一大祭,轮赛之时,大幡一杆,高八丈,上系彩幡数层,驾五只大牛拉着,百余人从四面八方以绳扶行。小幡十二杆,各高二丈,一牛拉一杆。不独打幡,还有僧道两门身披袈裟,吹奏乐器引着:油筵、彩筵、整猪、全羊、大食、榴食七百三十个(需白面二千二百余斤)等各种祭品。还有狮子、老虎、高跷、抬阁、花鼓等故事,排列成行,鱼贯而行,异常热闹,洵称巨观。相演成习,已成古规,不可缺少。”(16)足见滦池泉域水神权三者合一的程度!
如果说十二村皆参加的祭滦神盛典,具有划分有无水权功能的话,那么南梁村和武池村对各自地盘上建立的乔泽庙资源的实际控制,又进一步强化了各自在十二村和下六村中无可动摇的霸权地位。南梁村水利碑中一段关于乔泽神庙地权的描述就颇具说服力:“殿前香亭,涧峡建焉。东殿子孙祠、西殿阎罗府、并山门、戏楼,俱系南梁所建。两傍虽有下村廊房,而前后左右地基,则无尺土不属南梁焉。”(乾隆五十六年《滦池水利古规碑记》)既然连整个泉域共同遵奉的神祗栖身之所也基本上由南梁一村提供,无怪乎该村会获得金字塔顶这一至高无上的地位。
与南梁村相比,武池村乔泽庙的修建年代则要晚许多,该村碑中有“建庙貌于宋元”的字样(万历三十六年《武池村敕封乔泽庙并建献殿碑记》)。就武池村在本村建庙的动机来看,也只能理解为藉以巩固其在下六村的水权优势。自熙宁三年该村大户李惟翰、宁翌领导六村开创水利以来,武池村人就一直凭借其祖辈的开创之功和村大人多的实力,在水权分配中占尽便宜。将最具感召力的乔泽神庙迎建于本村,岁时操办祭祀,不但可以巩固其已有水权,确保在下六村的首村地位,且可凭此与南梁等上游村分庭抗礼,尽可能摆脱南梁的控制。在此意义上,南梁与武池都有意将乔泽神这一公共资源占为己有。
(二)“竖碑立传”的方式
将祖先制定的用水规程或官府断案结果以碑刻形式保存下来,可谓滦池泉域水权村表达其用水地位最直接也最常见的方式,反映了泉域民众一种朴素的水权维护意识。如大定十八年,在制止了下游西张村及梁壁等三个无水权村的违例之举后,在武池村享有威望的李惟翰之亲曾孙李忠就提议:“往年西张争水,上用并提举文案碑定断了当。因叹曰:我等俱老矣。切虑将来,岁久年深,假令有争水使用如前日者,则晚生后进诸事未谙,仓卒之际无所依据,恐致错失,当如何哉,安得不思?虽而预防之,我今欲将大中议孟总判断定案,验□之于垂示子孙,以为照据。询于众曰可乎不可乎?众人乐后皆曰可。”(金大定十八年《重定翔皋泉水记》)由是刊立《平阳府绛州翼城武池等六村取水记》。与之类似,《大朝断定使水日时记》中也有“府断水例可录而刊石,传不朽,庶使将来更无讼也”的记载,表明“竖碑立传”已是滦池泉域一种很寻常的行动惯例。正因为有这一惯例的存在,使自宋金以来形成的用水习惯和规则世代延续下来。当面临不满现行规则的势力挑战时,历代水利碑就会跨越时空阻隔,成为村庄水权的有力见证,在处理水权争议的过程中,发挥实际作用。
与水权相对应的水利工程摊派、修庙费用等在水利碑中大量体现,也可视为村庄表达水权合法性的有效方式。武池村现存嘉靖二十四年《立死卖地基边刻》,就记述的是武池等下六村集体摊款购买崔庄地开渠过水的事件。这次摊银共十五两,其中吴村出银五钱八分八厘,北常村二两五钱二分,武池村□两六钱四分四厘,马册村□两五钱九分六厘,南史村一两七钱六分四厘,东郑村九钱二分四厘。显然,各村摊款应与各自的用水日期相对应,多者多摊,少者少摊。有意思的是,笔者在抄录该碑时,发现武池村和马册村摊款额的头一位数字像是被人有意凿掉,而非自然磨损。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在武池村一定有人抱有“只享水利而不愿过多出钱”的投机心理。
武池村碑林和南梁村滦池碑亭,都可视为泉域内不同村庄表达用水地位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编纂故事”的方式
这一方式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有关北常村四大好汉的故事。该故事的原型是明弘治年间和清顺治六年北常村参与的两起争水事件。
对于弘治年间发生的争水事件,《滦池变迁》叙述得非常形象:“按照旧规,下六村水程是清明起番,仲秋落番,十五天一轮,武池村占一半水程。即便如此,武池村仍贪心不足,妄想霸占六村的仲秋起落番水,便向知府恃富纳贿,知府受贿后,歪曲事实,偏袒断案。北常村王玘、程贤、郭迪三人气愤难平,当堂把知府的眼珠抠掉。三人被押解进京,朝官倚权当势、不问知府贪赃枉法、偏断水讼之罪,却以‘刁民狂徒’将三人问成死罪,并支起油锅威胁说:‘跳进油锅,把水判给你们。’三人明知难逃此酷刑,毅然跳入油锅。朝官见三人如此坚决赴死,知其必有冤屈,不敢食言,遂将仲秋起落番水断给北常村。”虽然乾隆五十六年《滦池水利古规碑记》中对弘治年间的争水事件有所记录,却不似如此详细,且最后审断结果也非地方文献所述,只是简单记载:“明弘治年间,武池村富豪王厚等欲乱成规,北常村王玘赴京上疏,命下批部、院、道、府问确、罚厚半石。”可见,地方文献叙述中可能存在夸张的成分。
同碑还记载,顺治六年,北常村又出现一位争水好汉杨景耀。三月清明起番,八月中秋落番,本是滦池十二村皆遵循的“千百年之成规”,“不意武池村伪官乔光启、乔毓秀、王豪、李萃荣等恃富欲乱旧规。北常村杨景耀具告县何老爷案下,蒙审解忿息争,批有执照,后不为例。耀思水利大事,复告本县徐太老爷案下,启仍恃官势,弄权变法,捏斗殴,拟耀不应打人,不论主仆拿来打死杨景耀等抵罪”。就这样,杨景耀被武池村强梁之徒勾结官府捏造罪名含冤处死。连同弘治年间王玘等三人,被誉为北常村的“四大好汉”。
据北常村王永贵老汉回忆:“村里原来有座四大好汉庙,在我小的时候已变成学堂,塑像用纸糊了起来,儿时我曾用手指把纸捅破,看到‘四大好汉’,手中端着一个盒子,老辈人讲是因为县官断案不公,他们就抠了县官的眼睛放在盒子里。后来‘四大好汉’跳油锅争得了阴历八月十五至清明之间的用水权,清明以后才能各村轮水。”(17)与前述碑文对照,王永贵所述显然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不过,北常村“四大好汉”的故事却成为彰显该村水权的一种最佳方式,在民众记忆中模糊留存,成为该村人努力捍卫村庄水权的精神动力。
(四)“口头传唱”的方式
在滦池泉域,还流传有“梁壁村无别计,丢了水权缠簸箕”、南史村“水打门前过,鸡鸭不能喝”等口头俚语,同样是乡村社会表达水权的一种常见形式。
关于梁壁村水权的丧失,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解释,兹不赘言。对南史村“水打门前过,鸡鸭不能喝”的问题,当地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来自于《滦池变迁》的记载:乾隆年间南史村民董仁,对地方官庇护势豪霸水的行为非常气愤,径直赴县衙,在公堂之上揭露县令贪赃枉法的行径,触恼了贪官,遂将董仁酷刑处死,并长期严惩南史村民,定出“水打门前过,鸡鸭不能喝”的禁约,立碑示众。另据东郑村人郑日新说:“因南史村居东郑村上游,不断堵截东郑水浇地,东郑村便依此碑为据,阻止南史村随意堵水。解放前,我任闾长时,怕此碑丢了,便将碑立在自家房内保存,不少村民见过此碑。‘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人做建房基石用了。”一种来自于实地调查。据武池村小学教师韩家森先生讲:南史村与下游的东郑村争水,由于南史村无人敢跳油锅,官府就将水权判给下游,这样水从南史村流过,即使家禽也不得随意喝水。(18)两种解释均表明在激烈的争水斗争中,南史村最终丧失了水权,且在后一种解释中又增添了类似梁壁村那样因争水权而丢失脸面的内容,同时也展现了水权分配中强者的嚣张与弱者的辛酸。
综上所述,水资源紧缺可谓滦池泉域及其周围村庄自前近代以来就面临的最大难题。正因为水资源的稀缺性,才会使水权意识在滦池这样一个社会里显得异常突出,并围绕它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制度、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心理。这一切恰恰是产权功能的体现,新制度经济学对此解释说:“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是一个资源十分稀缺的环境,每个人的自利行为都要受到资源的约束。如果不对人们获取资源的竞争条件和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亦即设定产权安排,就会发生争夺稀缺资源的利益冲突,以产权界定为前提的交易活动也就无法进行。因此,产权制度对资源使用决策的动机有重要影响,并因此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19)接下来的事例,就会证明这一点。
三、权利实践:水资源紧缺状态下的水权争端
滦池泉域水资源紧张主要是两方面因素使然:一为自然因素。自明弘治十八年(1505)起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止,滦池泉共五次停涌,陷于完全干涸境地,其中四次因大旱引起。泉水干涸时间最短者一年,最长达十年,“池水涌涸不常”引起的水量减少导致人心惶惶,舆论骚然;二是社会因素。据顺治六年碑所载:“因昔时水地有数,水源充足,人亦不争。自宋至金而明,生齿日繁,各村有旱地开为水地者,几倍于昔时。一遇亢旸便成竭泽,于是奸民豪势搀越次序,争水偷水,无所不至。其间具词上疏,案积如山。”
在水的供应日益减少的情况下,用水需求量却日益扩张,势必加剧水紧张的形势。顺治四年至六年武池村与北常村争水案、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南梁村与清流村争水案,就是在这种场景下发生的。在此,我们将以这两起水案为中心,具体剖析水资源紧张状态下的水权实践过程,并藉以探明水利纠纷不断的根源。
顺治四年,武池村人乔光启在清明轮番起水日未到之前,不遵旧例,擅自启渠使水,遭致北常村人不满。该村杨景耀乘机生事,以地多水少为由,“要将中秋后水,利五村浇地,不与武池村分使”,这反过来引起武池村人不满,双方争斗。事件发生后,有人提议说“计时使水在昔地少可均,今各村新垦地多,必计亩再为均融,难执往例胶柱之见”,意在更改旧日水例,重新分配水权。但主审官员却提出一个相当保守的处理意见:“水源有限,当日分村定时,正虑后世奸豪私治旱地使水,致他村不得沾溉故也。若此端一开,则百世之后,势必至上流之旱地尽成水地,仍纳旱地之粮,下流之水地转为旱地。及包水地之深,其流弊宁有底止?今惟仍照原定时数,如一村之内,虽地有私开而水不增刻,则私垦者本村必不相容,而伎俩自□,争端自息。又说者谓武池,一村计地一十一顷,却使水九十一时辰,北常等五村计地二十五顷共使水八十八时辰,从中秋后之水独许五村灌溉,以补前者地多水少之数。夫武池使水独多,当初立例,必有缘故,抑系创渠之始,该村李惟翰等为首,必其渠价工程独倍五村耳。清明之水,一刻千金,武池尚然。多分犹不足用,以致搀越,而况中秋以后之水,涓滴不与,势必构讼争斗,岁无宁日矣。”该方案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切“率由旧章”,不得以任何理由变更初始水权之分配格局,让矛盾在村社内部自行解决,这固然可以降低官府的监督和管理成本,却未免过于僵化,低成本低风险只能换来低收益,不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该思想指引下,对矛盾的焦点——中秋后水权分配问题,又做出一个近乎荒唐的判决:“中秋以后之水,仍照清明所定日期,挨次照刻轮使。八月十五日吴村起,酌定时日,不用者听其空悬日数,要用者必待原定时候。若云不限日期,不轮番次,是以又起争端,终非画一之法也。”(20)如此分水,尽管从表面上看不失公允,却依然是在旧日水权分配原则基础上施行的,无法有效改变“地多水少”村用水紧张的状况。
乾隆五十三年南梁村与清流村争水案中,也有类似现象。鉴于滦池的涌涸不常,南梁将该村一个名曰“金带”的洪水旧渠修复,“备池水不足之接补”。同样处于缺水状态的清流村觊觎人利,要求借使洪水,被南梁拒绝。于是清流村人“冒充渠长,扰乱清水起落规则”,希图多得水程,双方争讼。与前不同的是,翼城官员最初满足了清流村人的请求,将原来的“清明起番中秋落番”规则一律改为每年元旦起终止。南梁村人因该判决不合古规,未具遵结。后清流村又率众强行闸水,被南梁村将其闸板拆毁,双方剑拔弩张,复讼于庭。最终,平阳府主审官在验过“执照碑志、水例、古簿与北常村碑文”后,听从了南梁村的诉讼请求,“每年清明起仲秋止,仲秋以后并不轮流,仍照旧规”。(21)至此,清流村试图改变水权分配格局的努力彻底宣告失败。
从上述两起案例中我们看到,自宋熙宁三年以来,滦池泉域村庄围绕水权分配所形成的产权安排,对于消除争端本是有积极贡献的。但是,由于前近代社会对人们获取资源的竞争条件和方式作出的具体规定存在不合理、低效率和等级性的特点,因此当水资源稀缺程度加剧时,原有的产权安排就逐渐变得不适应了。由于维护原有产权的种种规章、制度、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的重重阻碍,实现制度变迁就会显得异常艰难。
结语:集体水权与私有水权的共存及其绩效
通过“滦池”这一极富典型性的经验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三点主要结论:
首先,由于水资源的严重匮乏,在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不但普遍存在而且相当突出;不但在广大民众心目中产生了一种浓厚的水权意识,而且以水权为中心,还形成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地方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心理,对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水权的形成主要受区域社会先天的地理位置差异、先人功德和一些具体经济指标如土地多寡、负担经费和劳动力多寡等多方面要素的影响。尽管就其外部特征而言,在水权占有和分配中具有分等级、不公平、不合理的方面,却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得到地方社会的普遍认同,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运行秩序。不仅如此,这种既定水权分配格局往往通过神灵信仰与祭祀、“竖碑立传”、编纂及夸大“好汉”故事以及民众口耳相传等特定方式表达出来,由此形成的民间社会舆论、道德观念和日常生活习惯,共同维系着现行水权分配格局,并赋予其“合法性”地位,使村庄水权得到“非正式”界定和保障,类似于研究者所提出的“社会性合约”这一概念,具有非正式制度的特点。当外部因素变化,出现重新界定水权的要求时,传统水权的这些非正式表达方式,又能够与正式制度如官府审断、法律制度等一起发挥作用,维系着初始水权分配格局,客观上阻碍了制度变迁的进程,影响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率。笔者认为不可武断地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而应将其视作前近代社会一种特定的“文化安排”,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的这一特点,具有社会适应性。它与传统时期政府的统治职能低下、人财物力资源贫乏、赋税征收方式等密切相关。前近代水资源配置尽管不尽合理,在资源相对充足的条件下,却能够维持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秩序,以极低的成本和费用规范和保障了村庄的用水权,国家也能够得到预期的赋税收益,区域社会秩序的稳定正是得益于非正式的民间运作逻辑,这一点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二,集体水权与私有水权共存于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这一特定“文化安排”之下,二者并不互相排斥发生冲突。从滦池的个案研究中我们看到,水权本身既包括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水权,也包括以家户为单位的私有水权。但初始水权通常是以村庄为单位而非家户为单位进行分配的。家户用水权只有在保障各自所对应村庄集体水权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家户水权是附着在村庄集体水权之上的。没有村庄集体水权,也就无所谓家户个体的私有水权。以家户个体名义进行的水权申诉和争斗行为通常被视为不合法行为而被严加制止和惩罚,并受到区域社会舆论和道德准则的批评和诟病。私人争取水权的行为即便在短期内可以得手,最终也会被彻底否定,重新返回到泉域民众认同的运行轨道,这一点在滦池的经验研究中已屡屡得到证明。由此引申而言,产权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历史问题,并非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下才涌现出来的一个新问题。这一问题在历史时期通过特定的“文化安排”,曾经得到妥善的解决,具有低成本高收益的外部特征。近代以来,随着资源稀缺程度的不断加剧,其边际收益才逐渐降低,重新合理界定产权的呼声才越来越高。但这时所强调的只是产权如何合理界定的问题,并非集体水权与私人水权之间的矛盾。
第三,水权是水资源稀缺条件下的产物,主要是指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在前近代华北乡村,对水资源所有权的争夺体现得并不十分明显,对水使用权或者说控制权则强调得较为突出。不断发生的水权争端,所争夺的并非水资源归谁所有的问题,因为在这一问题上,地域社会内村庄和民众已经有大致相同的认定,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水归国家所有,并非某村某人的私有财产;二是水源所在地拥有对水的特殊权利,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水的占有。但这是由地理因素所决定的,非人力所能改变。谁拥有对水资源的使用权或控制权才是矛盾的焦点。因此,前近代以来华北乡村社会发生的水权争端,主要是对水使用权的争夺,将水利纠纷不断的原因归结为水资源所有权公有和使用权私有的矛盾是无法立足的。再就水权争端本身而言,有两个问题需要重视:首先是资源短缺问题。导致水权争端发生最直接的原因是水资源稀缺程度的日益加剧和水资源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一正一反两条曲线导致水资源供不应求,发生争水斗讼事件在所难免。其次是水权制度本身的问题。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的水权呈现出等级性、不公平不合理性等突出特点,甚至存在地方豪势垄断、独霸水权的现象,造成水资源无法实现有效配置,影响了资源利用效率,加剧了水紧张局势。解决问题的关键应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开源节流,提高水利技术;二是合理界定水权,统筹配水,实现对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这就要求政府投入高额的资金、技术和监督成本,然而,不论前近代的国家还是乡村社会,这一点都根本无法做到。因而随着水资源的日益匮乏,水利纠纷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可见,将水利纠纷不断发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水资源的产权归属与界定困难也是有失妥当的。
最后,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产权是否且必须界定为私人产权才会产生高效率?目前已经有很多反面例子证明,私人产权即使被界定得很清楚,也仍然会纠纷不断。相反,产权主体模糊时,倒显得异常平静、和谐。如何解释这一悖论现象,当是下一步研究中需要重点分析的问题。
致谢:本文是笔者2006年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访学期间,多次向张小军教授请教、讨论的基础上完成的,蒙张教授悉心指导,获益良多,在此深表谢意;同时也衷心感谢业师行龙教授多年来的指导和帮助。
注释:
①参见萧正洪:《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王建革:《河北平原水利与乡村社会分析》,《中国农史》2000年第2期;行龙:《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年第6期;行龙:《多村庄祭典中的国家与社会——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4期;森田明:《清代的水利与地域社会》,福冈:中国书店,2002年;韩茂莉:《近代山陕地区地理环境与水权保障系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钱杭:《“均包湖米”:湘湖水利共同体的制度基础》,《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钱杭:《“烈士”形象的建构过程:明清萧山湘湖水利史上的“何御史父子事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②参见王铭铭:《“水利社会”的类型》,《读书》2004年第11期;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2005年第8期。
③参见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④参见折晓叶、陈婴婴:《产权怎样界定——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⑤参见Nee,Victor & Sijin Su.Institutions,Social Tiers,and Commitment in China's Corporalist Transformation.In John McMillan(ed),Reforming Asian Socialism:The Growth of Market Instituti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 Lin,Nan and Chih-Jou Chen,Local Elites as Officials and Owners:Shareholding and Property Right in Daqiuzhuang,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45—170; Yushen,Peng.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tional Econom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4,Vol.109,No.5.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⑥参见张静:《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张小军:《象征地区与文化经济——福建阳村的历史地权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申静、王汉生:《集体产权在中国乡村生活中的实践逻辑——社会学视角下的产权建构过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⑦参见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周雪光:《“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⑧参见金大定十八年《重定翔皋泉水记》,现存翼城县武池村乔泽庙。后文出现同碑时,不再注明存碑地点,以下类同。
⑨参见此说见于康熙五十二年《重建庙碑记》和乾隆六十年《重修庙碑记》之碑阴三村捐款题名,碑存翼城县武池村乔泽庙。
⑩该碑现存翼城县南梁村滦池碑亭。
(11)至元九年《重修乔泽神庙并水利碑记》,现存翼城县南梁村滦池碑亭。
(12)顺治六年《断明水利碑记》,现存翼城县武池村乔泽庙。
(13)乾隆五十六年《滦池水利古规碑记》,现存翼城县南梁村滦池碑亭。
(14)康熙五十二年《重建庙碑记》和乾隆六十年《重修庙碑记》两碑之碑阴三村捐款题名。
(15)民国《翼城县志》亦有解释说:“曰栾者,疑当时以死难,赐栾共子,因人名地,去晋为栾,故曰栾池。因栾宾及其子栾成生其旁,故以为姓。又栾共叔死哀侯之难,小子侯嘉其忠,赐以为祭田,故易为栾,后人渐讹写为滦耳。”此外民间也有传说称三月初八栾成下葬之日,挖坟出水,形成滦池泉,故而以殡葬形式来祭祀他,此说在滦池泉域流传甚广。
(16)李百明、段玉璞编:《滦池变迁》,翼城:翼城县档案局内部出版,1986年。
(17)2003年11月18日,笔者在翼城北常村对王永贵的调查口述,老人当年80岁。
(18)2003年11月17日,笔者在翼城武池村乔泽庙对韩家森的调查口述,老人当年72岁。
(19)卢现祥、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3页。
(20)以上引文均见顺治六年《断明水利碑记》。
(21)乾隆五十六年《本府裘大老爷断明起落番次水例碑记》,现存翼城县南梁村滦池碑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