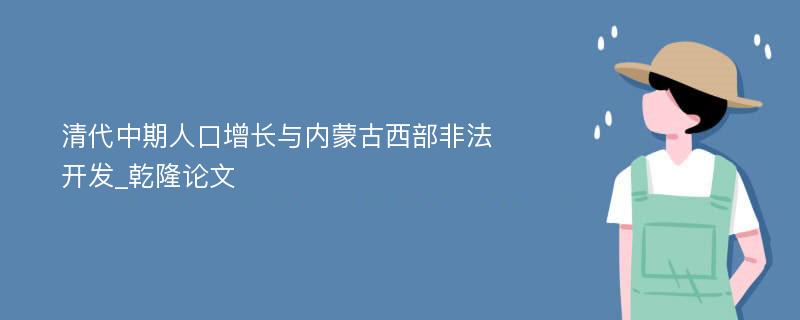
清中叶的人口增长与内蒙古西部的违禁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蒙古论文,人口增长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6)03-0005-05
一
清以前,中国人口大约在6千万上下,最多时达到7千万左右[1]。到了清代,我国的人口迅速发展。康熙朝以后,中原地区的人口迅猛增长。乾隆六年(1741年),清廷在内地省份各州县依据保甲门牌统计户口,这一年年底统计的人口总数为1.4341亿余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人口突破2亿,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突破3亿。在半个世纪里人口总数翻了一番,这在中国人口史上是空前的。
中国幅员辽阔,但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难以利用的土地面积很大,如沙漠、戈壁、冰川及永久积雪、石山、裸地等,土地资源相对量少。人口的急剧增长,形成了内地人多地少的突出矛盾。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清人洪亮吉曾作过估算,认为:“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矣。”[2]347-348就是说,一个人大约有4亩田地即可维持自己一年的生计。但是,由于人口剧增,从乾隆朝中期人口突破2亿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已达不到这个标准。有学者估算,乾隆十八年(1753年),人均耕地面积为4亩,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人均耕地面积减为2.6亩,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平均每人只有耕地2.3亩[3]。
可见,由于人口的剧增,已超出当时社会生产力所能承受的水平。广大农民终岁辛劳,不少人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处于饥寒交迫状况下的破产农民,一遇灾荒或社会变乱,往往会发生“民变”。对此,康熙帝晚年时就已觉察。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说:“今人民蕃庶,食众田寡,山巅尽行耕种,朕常以为忧也。”[4]2094雍正帝即位不久也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5]卷6乾隆执政期间使其“甚忧之”的突出问题也是如何养活日益繁衍的人口。在这种情形下,为生活所迫的贫苦农民为了生计纷纷向人口相对稀少的边疆地区迁徙,涌向内蒙古地区的流民呈现上升的趋势。
促使大批自耕农、半自耕农丧失土地而成为流民的原因还在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和自然灾害频仍[6]。以灾荒为例,自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山东、直隶、河南等北方省份,水灾、旱灾连年不断,触目皆是:“东兖二属,上年二麦失收,小民未免困苦。直隶、河南邻境之民有携家觅食者。……又前岁河南黄水溃决,泛溢于直隶地方。比年以来,两省近水居民耕种无资,衣食匮乏”[5]卷3。“以河南武陟等处七县,夏被旱灾,入秋又值黄水为害”[5]卷4。“以山东泗水等十一县,连年旱灾”[5]卷4。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原本脆弱,不可能具有有效的防灾抗灾能力,面对灾荒,尤其是大的灾荒,农民只能束手待毙或四处逃荒。为了解决灾荒及流民问题,雍正帝采取了缓征额赋、遣官赈济、施发米粥等救治措施,并颁布谕令:“朕临御以来,宵旰忧勤。凡有益于民生者,无不广为筹度。”“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5]卷6
对于流入内蒙古地区的灾民,采取“乐于就移”者,“免其田赋”,允许其开垦土地,对蒙旗王公“欢迎入殖者”,“特许其吃租”①。这既解决了流民的生存问题,又给蒙旗带来一定收益,被蒙古地区称为“一地养二民”。此项政令一开,又有不少内地灾民闻风而至。以后每遇荒年,清政府为解决灾民问题,往往都采取同样的措施。例如乾隆八年(1743年),天津、河间等处发生旱灾,衣食无着的灾民“闻知口外雨水调匀,均各前往就食,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者颇多”。清廷密谕各关口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放出”[7]卷195。次年,清廷又谕令山海关一带各口,对出山海关的山东、河南等地灾民,稽查“不必过严,稍为变通”[7]卷208,允许其赴口外开垦蒙地谋生。
清廷对蒙古地区采取的上述措施,不过是在荒歉之年的一项权宜之策,但由于大量的内地民人流入蒙古地区,当地的王公贵族和土地所有者受利益的驱动把土地更多地租佃给汉人开垦,公有牧地被大片占用。
以下我们以几组数字说明口外土地被开垦的情况。
雍正二年(1724年),在察哈尔右翼四旗被开垦的土地为29709顷25亩[8]。《口北三厅志》载:在张家口、独石口地区雍正时期新垦土地达3710.43顷,加上旧有的垦地,共有垦地6003.99顷。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也批准开放8处垦地,共4万顷。在鄂尔多斯地区,雍正朝以后,内地的移民越来越多,他们投亲靠友,互相援引,“一年成聚,二年成邑”。鄂尔多斯“东部与南部毗连晋陕处,则有河曲、神木、府谷等县,农民沿套边开垦,渐成村落”②。在内蒙古东部,也出现了土地大量被开垦的情况。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在卓索图盟的土默特贝子旗有汉民佃种地1643顷30亩,喀喇沁贝子旗有400顷80亩,喀喇沁札萨克塔布囊旗有431顷80亩[9]卷979。当时口外土地开垦规模,由此可见一斑。它的直接后果,则是使游牧草场逐渐缩小,致使一些中小台吉及牧民失去土地,开始影响当地蒙古人的生计。
另外,大量的内地农民涌入蒙古地区,也使当地原本单一的游牧经济向多种经济形式转化,这些新的经济因素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鄂尔多斯与宁夏等交界处出现了“内地民人,越界耕地,而蒙古等私索租价,每至生事互争”的情况[5]卷110。
对于这些出边的农民,内地官吏以其户口编籍于口里,往往要他们交纳草料,以充军粮。清廷又规定,内地民人耕种蒙民土地,应向蒙古交纳租银租粟,“各旗设立收头,按期赴伙盘地收取”[10],收毕将租银租粟交于蒙民。蒙古地方官也往往在汉民越界耕种之地私自索要租价,这就必然引起争端。
以上出现的这些情况自雍正朝开始引起清廷的注意。如雍正八年(1730年)的一篇上谕说:“察哈尔地方原系蒙古游牧处所,若招民开种,则游牧地方必致狭隘,且民人蒙古杂居一处,亦属无益。著行文察哈尔总管等,查有此等擅行招民开种之处,作速据实呈报,将前罪悉行宽免。倘仍复隐匿,一经发觉,加倍治罪。”[5]卷98在这里,雍正帝讲了造成游牧地区“狭隘”的原因,认为民人蒙古杂居,“亦属无益”,并对“擅行招民开种”明令禁止。
乾隆时期这种农牧争地的矛盾继续发展。乾隆八年(1743年),鄂尔多斯“各旗贝子等以民人种地越出界外,游牧窄狭等情呈报”。乾隆帝命理藩院尚书班第与川陕总督庆复前往榆林地区,会同陕北各县及鄂尔多斯各旗议定边墙之北禁留地问题,并订立了永久章程。规定:“有于旧界外稍出二、三十里,仍照旧耕种,其并未出界者,仍照前办理。有出界五十里之外,将种地民人收回,五十里之内,给予空闲地亩耕种。”[11]
针对内蒙古地区出现的蒙汉纠纷,乾隆帝说:“沿边省份,与蒙古地界相连者,夷民杂处,互相贸易耕种,闻地方官凡遇夷民交斗事件,心存袒护,并不秉公剖断,兼以口外之事,无足轻重,不肯加意办理,实为向来积弊。”他要求:“各该督府将军,应严饬地方文武官弁,以后约束兵民,不许欺凌蒙古,办理夷民事件,务令彼此公平,以免生端构衅。”[7]卷123清廷颁布禁止内地民人开垦蒙地禁令的前提是为了巩固、维护国家的封建统治,从这点出发,“宁辑边疆”是清朝历代帝王处理边疆问题的基本原则。而自雍正晚期以来的内蒙古地区持续不断的蒙汉纠纷已构成边疆的不安定因素,必须加以解决。乾隆十三年(1748年)在清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开始从民人手中逐渐收回租佃的土地,规定:“民人所典蒙古地亩,应计所典年分,以次还给原主。”[9]卷979翌年,乾隆帝颁布封禁令,对蒙古地区全面封禁。乾隆帝说:“蒙古旧俗,择水草地游牧,以孳牲畜,非若内地民人,倚赖种地也。康熙年间,喀喇沁扎萨克等,地方宽广,每招募民人,春令出口种地,冬则遣回,于是蒙古贪得租之利,容留外来民人,迄今多至数万,渐将地亩贱价出典,因而游牧地窄,至失本业……著晓谕该扎萨克等,严饬所属,嗣后将容留民人居住、增垦地亩者严行禁止。至翁牛特、巴林、克什克腾、阿鲁科尔沁、敖汉等处,亦应严禁出典开垦,并晓示察哈尔八旗一体遵照。”[7]卷348明确说明了“渐将地亩贱价出典,因而游牧地窄,至失本业”是封禁蒙地的主要原因。
二
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廷颁布对蒙古地区全面封禁令后,清廷加大了对封禁的管理力度,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由理藩院间年选派司员二名,会同地方官对蒙古地区进行巡查,督促地方官员清查私垦私典,并对违禁者绳之以法。蒙古官民等若“再图利,容留民人开垦地亩及将地亩典与民人者”,该扎萨克“照隐匿逃人例,罚俸一年”;管旗章京、副章京“罚三九”;佐领、骁骑校“皆革职,罚三九”;领催什长等“鞭一百”,“其容留居住开垦地亩典地之人,亦鞭一百,罚三九;……其开垦地亩及典地之民人,交该地方官从重治罪,递回原籍;该管同知、通判,交该部察议”[9]卷979。同时谕令直隶、山东、山西各省督抚转饬各关隘,严禁内地民人出口。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廷又要求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守边旗员,沿边州县,对出边民人“严行禁阻”[9]卷158。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再次强调:“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例治罪。”[9]卷979
嘉庆、道光两朝,清政府继续奉行乾隆年间的蒙地禁垦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依据具体情况作了相应的调整与补充。
(一)对已开垦地亩定界封堆,严禁私招流民开垦土地
嘉庆四年(1799年),吉林将军秀林奉命查办郭尔罗斯前旗招民私垦荒地一案,鉴于招留民人不便驱逐等情况,“奉请将该处留寓民人所开地亩立定节制,周围砌以土堆,嗣后不准再行开垦一垄,亦不许栖居一人”③。此建议被清廷采纳,以后处理同类事件均仿照本案办理。如道光三年(1823年),查明卓哩克图王旗招留民人255户,共垦地3184垧,冰图王旗招留民人103户,耕种熟地1546垧,“该二旗招垦熟地均经挖立地界封堆。严谕各民户,毋得复行展占,并传知蒙古不准再为招垦”[12]卷58。
(二)加强对各边门关口的管理,对私自招垦颁布更严厉的处罚条例
清廷又多次强调,内地民人禁止进入蒙古地区。对私自出边的内地民人,命令各边门一律严行禁阻:“嗣后各边门守卡官弁务遵例严行查禁,遇有出口民人,均询明来历呈报,不得任听成群结伙,相率流移。若仍前疏纵,定按例惩处不贷。”[13]卷164“若有官吏互相容隐,私行纵放,一经查出,即据实参处”[13]卷249。
为遏止私垦的进一步扩大,对违禁之事处罚更为严厉。对私自耕种、租佃蒙地的民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议定:“如有将禁止不准耕种及应撂荒地亩,私行耕种、租佃、增垦至二百余顷者,系民人杖七十,徒一年半;百余顷者,杖六十,徒一年。俱先行枷号二月,满日递解原籍,定地充徒。数顷至四十余顷者,杖一百,枷号二月,递解原籍,严加管束。”[9]卷979对私招民人开垦地亩的蒙古王公及有失察之责的盟长,分别依其所招民人之多寡,给予罚俸处罚;对无俸之协理台吉、闲散台吉、塔布囊等,依其招聚人的多寡,罚牲畜不等。如获罪后仍不知悔改,依旧违犯,则发往江南五省,交驿站充当苦差[9]卷978。
尽管清政府采取了以上各种严禁措施,但流入蒙古地区的流民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或减少,实际情况是“年年有驱逐之名,而迄无驱逐之实”④。嘉庆皇帝甚至指斥:“流民出口,节经降旨查禁,各该管官总未实力奉行。以致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再届查办复然。是查办流民一节竟成具文。”[13]卷236
是什么原因使得流民驱而不散,禁垦令屡颁却禁而不止呢?这一问题引起了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探讨。《清代边疆开发》一书作者总结分析了四条理由:
第一,蒙古地区的经济需要农业。草原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游牧经济,较为原始而又非常脆弱,经不起任何自然灾害的袭击,也不能满足牧民生活多样化的需要,因此,需要农业来补充。
第二,人口不断地迁移、流通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大趋势。清朝的统一,客观上打破了民族封闭的壁垒,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为人口更大范围的流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就清朝的禁垦政策而言,并不是绝对的禁垦。
第四,雍正、乾隆朝在一些已开垦的蒙古地区设置州县制度,等于承认农业开垦的合法性,农业区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后,禁垦令亦随之而停止[14]290-291。
上述分析是从不同侧面剖析了乾隆至道光朝蒙地禁垦屡禁不止的原因,有些论述还涉及较深的层次。这里我们转换一个角度,对此作一些补充。
嘉庆十一年(1806年),嘉庆帝谕曰:“郭尔罗斯地方……原议章程,除已垦熟地及现居民户外,不准多垦一亩增居一户。今数年以来,流民续往垦荒,又增至七千余口之众。若此时概行驱逐,伊等均系无业贫民,一旦遽失生计,情亦可悯。著仍前准令在该处居住。”[13]卷164道光二年(1822年)七月,道光帝说:“科尔沁达尔汉王、宾图王二旗界内,向有蒙古招留流民耕种地亩,并开设铺店生理。”“现在民人已有二百余户,垦成熟地已有二千余垧。若按名拘解审办,未免多滋纷扰。既一概驱逐,亦恐流离失所。著照该将军所请,准其将查出建垦房地,遴派妥干大员会同该王等按段履勘,挖立地界封堆,毋任再有侵越;并造具花名细册,就近责成昌图通判编立甲社,随时稽查管理,务使民户与蒙古人等相安,不致藉端生事。”[12]卷38以后,道光帝还有如下批示,在蒙古地方开垦,“第一无碍蒙古生计,方可办理”[12]卷408,“无碍牧场,应准开放”[12]卷447。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社会问题所致。蒙古地区既然是大一统的清王朝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历史发展不可能不与全国息息相关,完全隔离,是根本不可能的。内地频年荒歉,人民衣食无着,迫使清廷不得不准许灾民进入蒙古,以缓解尖锐的阶级矛盾。还在乾隆八年(1743年),天津等地发生旱灾,大批灾民纷纷涌向蒙古地方谋生,乾隆帝就说过:“本年天津、河间等处较旱,闻得两府所属失业流民,闻知口外雨水调匀,均各前往就食,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者颇多。各口官弁等,若仍照例拦阻,不准出口,伊等既在原籍失业离家,边口又不准放出,恐贫苦小民愈致狼狈。著行文密谕边口官弁等,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行放出。”[7]卷195
这段话清楚地道出了清廷禁止内地民人流入蒙古却又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的原因。为了稳定蒙古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清王朝制定了禁止内地民人流入蒙地的政策,为了防止内地民人因生活痛苦不堪而可能引起的社会动乱,清王朝又不得不允许内地汉民前往蒙古地区求得生存。这矛盾的两个方面,清王朝是根本无法统一起来的。它说明的问题是,清代的流民潮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绝不是封禁政策这道人为的“墙”所能堵得住的。它既不能抑制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又不能增强广大农民防灾抗灾的能力,更不能控制内地人口的急剧膨胀,解决人多地少的社会矛盾,这是清廷对内地流民屡颁禁令却“禁而不绝”的根本原因。
由于内地农民不断流入边外开垦种植,这一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农业得以迅速的发展。
《归绥道志·丰镇厅田赋考》对乾隆朝以来开垦的土地作如下记述:“二道沟等处旗租地,乾隆年招垦共九百五十六顷二十二亩”;“太仆寺改折牧地,乾隆年开垦升科,共地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一顷七十四亩一分”;“太仆寺折色牧地,乾隆年开垦升科,共地五千二百七顷五十八亩”;“五字图庙旗租地,乾隆年认领,共地三百三十六顷二十六亩”;“礼亲王牧地,乾隆年招佃升科,共地一千三百三十二顷三十九亩”;“承安牧地,乾隆年招民认垦,共地二千五百六十四顷二十一亩八分”;“距墙口外旧马厂地亩,于道光年间升科,共地七百四顷三十七亩八分”;“白塔沟牧地,道光年招垦升科,共地五十二顷五十六亩七分”;“顺承郡王牧地,道光年开垦升科,共地九百二十顷五十亩”。《归绥道志·宁远厅田赋考》载:“乾隆三十七年开垦宗室纳木谨旧厂地六百六十九顷四十五亩一分……军宏晌旧厂地一百七十五顷九十七亩四分”;“开垦克勒郡王旧厂地四百二十三顷三十三亩八分……公恒禄旧厂地一百七十二顷一十亩……公松椿旧厂地九十一顷三十四亩五分”;“乾隆五十年开垦宗室德齐奉恩将军恒林旧厂地四百九十一顷九十五亩七分”。《土默特志》载: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乾隆二年至光绪十三年(1737-1887年),垦地约有57606.95顷。
另外,清廷还因政治形势的需要而随时改变封禁政策。例如:在清廷对准噶尔用兵之际,因为急需粮草和驼马,清廷对山西、陕西等民人涌入蒙古西部地区垦种者,也往往采取默认的态度。特别是乾隆年间流经河套地区的黄河南徙改道后,原来的河道及沿岸的土地多为肥田,则更多的土地被开垦了出来。前引《绥远通志稿》称:鄂尔多斯东部与南部毗连晋陕处,“农民沿套边开垦,渐成村落”。
与伊盟相连的阿拉善地区,在嘉庆年间开始放垦。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定远营一带,已垦熟地1190顷67亩[9]卷978。
以上我们大致考察了自乾隆朝至道光朝百余年间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土地开垦情况。总的说来,尽管这一阶段清廷的禁垦令不断,但由于清朝无法克服和解决的社会矛盾,涌入蒙古地区的流民潮与蒙地开垦种植这两大社会问题始终无法解除,它的直接后果则是促使当地的农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起来。从内蒙古西部地区来看,流入的农民比东部区相对较少,而且相对分散。因而,这里的农业尚属初步发展阶段,又由于被开垦的土地多是适宜种植庄稼的肥田沃壤,所以这一时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虽然较前有所改变,但对生态的平衡影响不大。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该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呈持续上升趋势,并且在乾隆后期的近百年内达到高峰,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上述的结论。关于18世纪中叶以后,蒙古地区的畜牧业经济状况,国内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论述,故不再赘言。
[收稿日期]2005-11-05
注释:
①参见辽宁省图书馆藏油印本《凌源县志》卷头三《纪略》,张丹墀修,宫葆廉纂,王瑞歧续修。
②参见内蒙古图书馆藏:《绥远通志稿》卷1。
③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硃批奏折·民族事务卷》,嘉庆五年五月十一日直隶总督胡季堂折。
④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硃批奏折》,直隶总督杨廷璋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