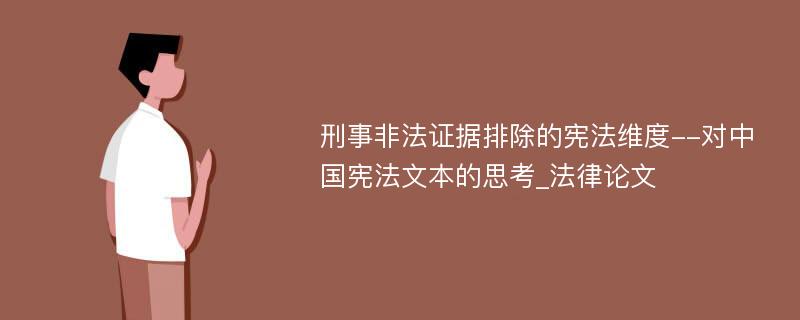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宪政之维——以中国宪法文本为基点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政论文,基点论文,中国论文,宪法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成为当前刑事证据法改革的基本趋势之一。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模式、程序以及证明标准等问题已形成一定的共识,并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立法建议。①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对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与我国公民宪法权利之间的关联缺乏深入的阐释。而观诸西方法治国家,刑事非法证据排除与公民宪法权利保障之间往往存在着特殊而密切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于宪法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讨,②但是,对于如何在公民宪法权利的框架之下建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乏应有的研究,而相关的讨论也往往以西方的规则为蓝本,未能以我国宪法条款作为参照系,从而使我们自己的根本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这样一个关系到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重大问题丧失其应有的指导作用。诚然,这一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宪法权利条款在司法活动中尚不具备直接适用性,但并不能阻碍我们对它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之间的内在关联作出理论上的阐释,以顺应世界刑事诉讼法发展的基本趋势,探索我国相关制度展期改革的可能路径。因此,本文从中国宪法文本出发,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作一粗浅探讨,其核心是寻求一种能够在公民宪法权利与刑事侦查取证权之间设定边界的法律机制。
一、设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以保障公民宪法权利为先
广义而言,刑事非法证据包括收集主体不合法的证据、取证程序不合法的证据、表现形式不合法的证据、未经合法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等。但是,对这些证据是应当一体排除,还是应当有所甄别?理论界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大致有3种观点:一律排除说、真实不排除说和区别对待说。③其中,一律排除说采取了一刀切的方法,过于绝对化,不利于在刑事诉讼中实现惩罚犯罪的基本目的,因而为大多数学者所不取。真实不排除说坚持了传统刑事证据制度中的实事求是原则,侧重于惩罚犯罪,漠视了人权的保护,因而也为许多学者所摒弃。而区别对待说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据非法证据的表现形态赋予其不同的排除效力,试图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两大价值目标之间取得均衡。这种观点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务界人士所禀持。然而,证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区别的角度也可以有所不同,问题是应当怎样对非法证据做科学、合理的区别对待呢?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立法技术的完善与证据规则体系的协调统一,同时它或许也能反映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立法的优先次序。
从证据类型或取得方法的角度对非法证据加以区别对待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9月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强调“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第61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8年12月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在强调“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的同时,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得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第265条第1款)显然,两高所设定的上述排除规则立足于非法证据类型和取得方法的区分之上。首先,区分了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只有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方有可能被排除;其次,区分了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和其他的非法言词证据,对前者应加以排除,对后者则不必排除。总的来看,排除范围相当狭窄,其初衷乃是不给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留下余地。④
然而,这样的区别对待显然是具有局限性的。首先,将非法证据种类划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划分,若以此作为取舍的依据,在学理上不能自圆其说,在实践中则会导致采取同等强度的非法取证手段,侵害同等重要的公民权利所获得的非法证据仅因其形式上的不同而不能被同等对待。⑤其次,仅从取证方法的角度区分不同的非法证据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有时取证手段虽然较为轻微,但其侵犯的法益却可能十分重大,致使一些应当排除的证据却未被排除。⑥
为此,我们应当引入其他的角度来区别不同的非法证据。譬如,美国著名学者达马斯卡根据排除证据的不同目的或原因将非法证据分为两类。鉴于司法证明以发现案件真实为其基本目的,第一类非法证据是指那些如果采纳则会阻碍发现真实的证据,排除的原因来源于认识论上的考虑;司法证明亦应保障发现真实以外的社会价值。第二类非法证据是指那些与外部价值相冲突的证据,排除的原因基于价值论的考虑。⑦我国有学者将需要排除的非法证据区分为三种:一是违反宪法的证据;二是一般的非法证据;三是技术性的违法证据。⑧结合两位教授的观点,笔者依据非法证据所侵害的客体或法益作如下分类:(1)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非法证据,如以刑讯行为逼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等;(2)违反重大社会政策的非法证据,⑨如侵害旨在增进家庭关系稳固的配偶拒证言权而取得的证人证言等;(3)阻碍发现案件真实的证据,如某些传闻证据、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被告人先前的刑事记录等;(4)违反刑事程序技术完备性的瑕疵证据,如有关单位出具的未加盖单位公章的证明文书等。上述4种非法证据侵害了不同的客体或法益,在其重要性程度上应有所差异,因而应当加以区别对待:
首先,对于技术性的瑕疵证据,由于并非是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取得,亦未涉及重大的法益,为了体现诉讼效率,促进发现真实,应当允许补救和修复。
其次,在阻碍案件真实发现的非法证据方面,我国传统的证据制度及其实践中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可以形成有关的证据规则,同时,由于此类证据与证据本身的证明力和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得甚为紧密,因此,在某些情形下亦可授权法官作自由排除。
再次,对涉及重大社会政策的非法证据,由于社会政策与国情、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因而此类证据规则不可匆促引进,而应结合我国社会实情多加论证。而且,证据制度的改革应有优先次序,比如不解决证人出庭问题,证人拒证权可能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最后,关于违反公民宪法权利的非法证据,笔者认为这应当是建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优先发展目标。简述之,原因有二:其一,公民宪法权利往往来源于自然人的基本人权,关系到人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尊严和价值。在现代法治社会,宪法权利可以超越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的不同而具有较大程度的普适性。传统中,我国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明显不足,此类证据排除规则留白太多,这种状况急需改变。其二,在现代刑事司法中,证据裁判主义乃是各国通例,而且案件事实已经消逝,相关的证据颇为稀缺,因此,证据的排除当慎之又慎,只有在遭遇重大的法益冲突时方可为之。笔者据此认为,在当前我国设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以保障公民宪法权利为先。
二、事实与权利之间的权衡
刑事案件的公正裁判须以案件事实的认定为基础,证据裁判主义要求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应当是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由于证据对于查明事实真相的重要意义,对待证据的态度成为一个主要问题。边沁认为:“证据是正义的基础,排除了证据,就排除了正义。”在他所谓的“自然程序体系”中,不应当排除任何证据,除非采纳这项证据纯属多余或者会导致困扰、开支或者拖延。⑩即使是在包含各种各样证据排除规则的英美证据法体系中,人们仍然将发现真实作为司法证明活动的首要价值。美国证据法学家威格莫指出:“大多数理论家都接受一个前提,即准确认定事实应当是证据法的核心目标。”(1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任首席大法官任奎斯特(Rehnquist,C.J)主张,刑事审判对于排除具有相关性的有罪证据所涉及的被告人宪法权利应作严格解释。(12)而我国传统的“实事求是”证据制度更是将追求客观真实作为一项排他性的证明目标,侦查机关被要求客观地收集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各种证据,审判机关也并不会因为认识过程之外的价值或权利来排除有证明力的证据。
然而,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人们逐渐认为,司法证明不仅仅是一种旨在“求真”的认识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旨在“求善”的道德实践,而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公民宪法权利恰恰是这种“善”或价值的核心所在。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事实与权利的相互关系问题,即它们在何种情形下互不相干,何种情形下相互促进,何种情形下相互冲突,在相互冲突的时候则需要作出一种痛苦的抉择。根据权利对于发现案件真实的不同作用,可以把诉讼权利分为3大类:真实促进型权利 (Truth-Furthering Rights)、真实中立型权利(Truth-Neutral Rights)和真实损害型权利(Truth-Impairing Rights)。(13)
真实促进型权利是指能够增进关于罪与非罪的合理判断,以达到所要求程度的确定性的那些权利,这些权利能够有助于法庭对事实作出准确的认定,与惩罚犯罪和保障无辜的社会目标是一致的。真实损害型权利呈现出相反的作用方向,它们可能会阻碍在刑事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揭示关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材料,这种权利的设定意图是在刑事司法证明活动中以牺牲部分客观真实为代价,实现更加重要的社会价值。还有一类诉讼权利既不能促进也不能损害案件真实的发现,从而与确定罪与非罪的刑事审判活动没有直接关联,可以称之为真实中立型权利。公民宪法权利根据其性质的不同,可以分别归属上述3种权利的一种。就美国宪法权利而言,第6修正案规定的被告人享有针对不利证人的对质权属于真实促进型权利;而第4修正案中规定的不受不合理搜查或扣押的权利,第5修正案中规定的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则属于真实损害型权利。有一些宪法权利会兼备真实促进和真实损害两种功能,比如第 6修正案中规定的辩护权,从律师能够帮助被告人调取、整理有关证据的角度,被告人的辩护权属于真实促进型权利;从被告人通过律师获得的法律知识、诉讼经验、心理承受能力上“平等武装”的角度,其辩护权又可以归属于真实损害型权利。真实中立型权利在刑事审判中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相关证据,如按照种族中立原则选择大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即属此例。
在以发现真实为其首要目标的理性主义司法证明体系中,存在真实促进型权利不难理解,但为什么会出现真实损害型权利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诠释:
其一,它体现了刑事司法活动在社会生活和法律制度中的实际地位。刑事司法是国家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其基本任务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惩罚犯罪,这一任务的完成状况是衡量刑事司法功能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但是,如果我们将刑事司法活动置于整个社会生活和法律制度的宏大视野之中,就会发现,刑事司法只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却不是全部内容。刑事司法的目标和价值也并非社会价值和社会目标的最高形态。除了充分发挥刑事司法系统的功能,有效惩罚犯罪,维护社会安全之外,社会和法律之中尚有更为重要的目标和价值,如促进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关系稳定等,因此,不应将证实犯罪、惩罚犯罪作为排他性的目标来看待,如果涉及更加重要的价值和目标,刑事司法中的发现真实也是可以退居其次的。
其二,在社会安全价值与个人权利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犯罪则是对现有秩序的最强烈的破坏。处于维护或恢复特定的社会秩序的考虑,国家需要对犯罪进行惩罚,这是国家追究犯罪的初衷。但是,社会安全价值只是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一个方面,不能因为追求这一价值而侵犯其他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价值,公民个人权利保护就是这样一种价值。刑事案件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之中,也往往会与犯罪分子以外的人产生联系,因此难免会有一些普通公民卷入其中,成为一名“犯罪嫌疑人”。司法机关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这就使得追究刑事犯罪的侦查活动与每个普通公民个人联系起来,涉及到普通公民的个人权利。在实践中,凶残狡诈的罪犯与有口难辩的无辜者之间确实没有一目了然的分界线,从严从快打击犯罪的愿望与保障无辜者权益的要求之间的冲突也会带来行动选择上的困难,但是无论如何,在惩罚犯罪与保护无辜这两个价值目标之间仍然可以找到相互协调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理性、正当的证明程序,违反这个理性程序所收集的证据就不能被采纳。
其三,制约侦查权的天然扩张性。相比于其他诉讼,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的运用具有主动性、普遍性和深刻性,这一点以刑事侦查权最为典型。在侦查活动中,为了及时获取犯罪证据和查获犯罪嫌疑人,常常要求侦查机关主动干预社会生活,单方面限制个人基本权益和自由。法律也因此赋予了侦查机关灵活多样的调查手段和强制权力。侦查机关既可以采取公开侦查,也可以采取秘密侦查;既可以采取任意侦查,也可采取强制侦查。而对于一些调查手段和强制性措施,普通公民如果没有合理的防御手段,那么侦查活动极其容易对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造成侵犯。所以有学者说:“如果基本权体系不能贯彻到刑事诉讼领域,等于委弃了最重要的守地。”(14)那么,为了约制侦查权的这种天然扩张性,有必要对侦查机关侦查权的行使设置一定的界限。
三、回归根本法: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刑事非法证据梳理
时至今日,在中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讨论正在走向深入,这说明人们已经认可了刑事证据领域中真实损害型权利存在的必要性。不过,如果我们探究一下包含着真实损害型权利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来源,就会发现,它们更多地是来自国际人权标准、国际公约或者某外国宪法,它们与我国宪法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因而并未得到深入阐述。借鉴国际准则或西方,固然可以弥补本国宪法制度之不足,但是,这种“踢开宪法闹革命”的做法不能不说存在着致命的缺点:其一,容易使新的排除规则的建构成为无本之木,难以得到充分地生长;其二,使根本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成为“两张皮”,有违法制的一致性(coherence)原则。伯尔曼说:“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为一体的系统”。(15)按照德沃金的看法,缺乏一致性的规则不能称其为真正的法律。(16)因此,笔者主张,回归根本法,将宪法公民权利作为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逻辑起点,将国际人权标准尽可能地纳入既有的权利框架之内,我国的宪法公民权利应当具有这样的包容力。
(一)侵犯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的非法证据。在我国《宪法》上,生命权、健康权属于一项隐含权利,即没有明文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可以推导得出的权利。例如,第36条关于人身自由的保护、第38条关于人格尊严的保护、第43条关于休息的权利、第45条关于弱者的特殊保护等条文,都是以生命权、健康权为前提的,是生命权、健康权的延伸。(17)生命权和健康权涉及人体生命活动的维持和机体生理机能的正常发挥,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属于基本权利中的核心权利,应当予以充分的保障。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是典型的侵犯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的取证行为。
值得指出的是,此类非法证据的排除与侵犯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的严重程度有关,而与证据的种类无关。“两高”解释明确排除了通过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但事实上,通过非法方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对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的侵犯程度可能丝毫也不亚于前者(如以强制人身检查手段获取物证),因此也应当列入应予排除的范围之内。
(二)侵犯公民人格尊严的非法证据。《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是指公民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它是人的主体性地位、个性特征、独立性和社会地位的综合反映。侵害公民人格尊严的非法证据是指以贬损其人格和主体性地位的方式取得的证据。其包括:(1)违反自愿性原则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2)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收集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3)以侵犯公民隐私权方式取得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4)未经犯罪嫌疑人同意取得的测谎结论;(5)以不恰当诱惑侦查手段取得的证据。
(三)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所取得的非法证据。《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里的人身自由主要是指身体自由或行动自由,是指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以及人身不受他人约束、妨碍、强迫和控制的权利。在刑事侦查中,侦查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的权限和法定的程序来实施各种强制性措施,违反了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即构成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侵犯。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所取得的非法证据包括:(1)侦查机关在不具备法定的实体标准或程序要件的情况下实施逮捕或拘留并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2)普通公民以非法拘禁等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而获得的证据;(3)侦查机关通过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而取得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4)在超期羁押状态下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
(四)侵犯公民住宅安全的非法证据。《宪法》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住宅安全是指任何机关或个人,非经法律许可,不得随意强行进入、搜查或者查封公民的住宅。住宅安全是公民人身自由的延伸,也是公民生活中最起码的一项权利。此类非法证据包括:(1)侦查机关在既无搜查证又不属法定特殊情形的情况下强行进入公民住宅所取得的证据;(2)普通公民在未经宅主同意的情况下,进入(秘密潜入或强行闯入)公民住宅而获得的证据。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住宅”应当作广义理解,不仅包括公民居住的房屋,还包括具有居住性质的车辆、船只、飞机等。
(五)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的非法证据。《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通信自由是指公民享有的信件、电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进行通信的权利以及保障其通信秘密的权利。《宪法》第40条和《刑事诉讼法》第116条也规定,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为了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可以对通信进行检查,但是却没有明确侦查机关对公民通信进行检查的具体标准和程序,在实践中侦查因而获得了介入公民通信秘密空间极大的决定权和自由度。应当明确,追查犯罪的需要并不能构成干预公民通信自由、开示公民通信秘密的绝对理由,侦查权与通信自由之间需要一条合理的界限,侦查机关如果没有法律的授权,擅自跨越这一界限,所取得的证据即为非法证据。
(六)侵犯公民辩护权的非法证据。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就使得被告人享有辩护权成为一项宪法原则。从世界各国法律规定来看,辩护权贯穿在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不受诉讼阶段的限制。但是,这在我国却有所不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这一规定,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服务职能,这种法律服务职能是否属于辩护范畴,却成为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相应的,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侵犯犯罪嫌疑人辩护权而取得的证据是否应当被排除就无法获得一个具有理论一致性的结论。因此,应当明确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同样享有辩护权,侦查机关只有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情况下才能取得合法的、可被法庭采纳的证据。
(七)侵犯人权的非法证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为《宪法》增加了一条重要条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3条第3款)。这一宣示性的宪法人权条款,显然为刑事诉讼中公民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提供了新的法律基础。然而,“人权”毕竟是一个十分宽泛和模糊的术语。宪法的人权条款是否涵盖了刑事诉讼国际人权标准的所有内容仍然存在疑义。目前学界的基本观点是,人权条款可以解释为基本权利保障的概括性条款,为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更直接而广泛的价值基础。在出现了宪法和法律没有规定的新的权利要求时,可以依据人权条款作出判断。而人权条款本身不能成为发现和提炼新权利的依据,它提供的是一种解释原则。(18)不过笔者认为,尽管人权条款与具体的权利尚有距离,但它无疑已经开启了吸收国际人权标准的宪法之门,也必将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逐渐完善提供推动力。
四、公民宪法权利与刑事侦查取证权的边界
行文至此,李白的诗句跃入脑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的确,尽管前文务求其全地罗列了侵犯宪法权利的非法证据,但充其量只是一些宽泛、抽象的原则或指针。置身刑事诉讼的语境,如果将公民宪法权利比作绝顶险峰之上的“胜境”,将排除非法证据的实践比作藉以脚踏实地、拾级而上的“石栈”,我们尚需架设钩连二者的“天梯”。毕竟,厘清条文、概念上的对应关系是容易的,而我们需要的却是付诸实施的一种机制。
这种机制的功能在于为公民宪法权利与职权机关的侦查取证权力设定边界。一方面,侦查机关的强制取证为追诉犯罪所必需,而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亦可要求对国家机关的某些强制取证行为承担一定的忍受义务。另一方面,强制取证行为行使不当,必然会对公民的权益造成重大损害。一般来说,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侦查取证行为虽然也有可能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了某种限制,但是由于它具有了正当化的事由,且不违背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因此应当视为国家追诉权力的正常行使。然而,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何在?正当和不正当之间又如何划分?一方面是宪法权利条款的微言大义和宽泛表述,另一方面是司法实践中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的清晰界分,二者之间应当如何联结?正如林钰雄教授所说:“公法上的相关讨论,应用到刑事诉讼上之基本权干预时,需要更为细致的转换。”(19)要使对于公民宪法权的保护切实地贯彻到刑事诉讼领域,首先我们在理论上就要确定一点,即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不能是抽象的,而应是具体的;不能只是立法中隐含之义,而应当是司法中的直接考量。笔者认为,可以从下述两个层面上来加以判断。
(一)涉宪性判断。应判断特定侦查取证行为是否直接涉及公民宪法权利,这是考量由此而取得的证据是否因为侵害了公民宪法权利而应予排除的前提要件。
这又可以从两个层次上来加以判断。其一,确定侦查取证行为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是否属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公法联系。如侦查机关本身所实施的取证行为,当然涉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系,不成问题;侦查机关委派特殊专业人员甚至私人进行某种取证行为(如通过医师对犯罪嫌疑人实施身体检查),尽管该专业人员或私人并非公务人员,由于存在这种委托或指定关系,因此也可归之于公法联系。如果纯粹是由公民的个人行为取得证据,尽管这一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但是,除非这种行为的侵权性质极其严重,否则所取得的证据可不作排除。(20)其二,确定该取证行为直接侵犯的利益是否属于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保障范围。如果说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目的正是要通过侵入或限制公民宪法权利来实现,而且,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害正是该取证行为的直接(而不是间接的或附带的)结果,那么该取证行为应属涉宪性公法行为无疑。值得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保障范围也可能处在发展之中,相关的概念可能会产生争议,则应通过立法或宪法解释来加以明确。
(二)正当性判断,即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化事由?如何确立和判断正当化事由?这可以借鉴德国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来加以具体阐释。
首先是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国家公权力行为尤其是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的行为,或者对公民权利有重大影响的行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作出,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不得实施。该原则的实质在于要求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在代议机关的监控之下。它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制约,也体现了国家公权的民意基础。(21)依此观之,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行为也不能任意作出,只有在立法机关对该事项作出了规范的情况下,它们才能按照法律的规范作出相应的行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把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都列为法律保留的范围。我国法律对法律保留事项已有所规定。《立法法》第8条、第9条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制定法律,且不得授权国务院先制定行政法规,即属于绝对保留事项。不足之处在于,法律绝对保留事项过于狭窄,与刑事诉讼领域相关之处仅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不能涵盖其他的宪法权利或其他的侦查行为。
将法律保留应用于排除非法证据的司法实践,则应在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对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侦查行为进行全面的规范。因为法律规定不完备,也就无法可违,自然也就不会存在非法证据问题。可从四个层面来加以具体化:其一,以法律明文授权,即要求在法律层次上明确各项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侦查行为,法律没有规定的侦查行为不得作出,否则所取得的证据则可能作为非法证据来加以排除。这同时也是程序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其二,禁止“法外”授权,即不得用法律之外的规范性文件(如关于刑事诉讼法的法律解释)来扩张侦查机关的权力、设置侦查行为的新种类。立法机关固然可以授权主管机关对法律作出补充规定,但是如果涉及公民宪法权利事项,其授权则应具有相当的明确性。其三,禁止类推授权,即法律如果没有明文规定某种侦查行为,则不得以手段或强度上的相似性来创设法律未加许可的侦查行为。其四,避免概括授权,即除要求侦查行为具备法律明文的授权依据外,还要求法律为之设定明确的要件限制。如果要件的限制过于模糊、例外过于宽松和任意,法律控制的密度则会大为减弱,证据的合法性与非法性之间的界限则会缺乏明确性,难以指导排除非法证据的司法实践。
其次是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它要求国家机关实施任何行为都应当选择对公民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并且对公民权利造成的损害不得大于该手段所保护的法律利益。(22)换言之,侦查机关所使用的取证手段与其所欲达成的“目的”之间,必须合乎比例,亦即具备相当性的关系。其具体内涵包括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狭义比例原则。适合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为达某一特定公法目的所采行之手段,必须适合或有助于其目的之达成。必要性原则是指,国家机关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特定手段,只有是不能选择其他同样有效且对基本权利限制更少的方法时,采取该项手段才可被视为是必要的,因此又称为最小干预原则。狭义比例原则是指限制基本权的手段之强度,不应超过达成目的所需的范围,同时因其限制所造成之不利益,不得超过其所欲维护之利益。(23)
如何按照比例原则来确定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正当性或妥当性?这主要使用因素权衡的方法,即一边是该取证行为所涉及的公民宪法权利,另一边则是一些具体的考量因素,如所追诉犯罪的种类或严重性程度(是杀人犯罪还是盗窃之类的犯罪)、犯罪嫌疑人的嫌疑程度(只是初始怀疑还是重大嫌疑)、运用该取证行为对于查清案件事实的必要性(有无较轻微的替代性手段)等。比例原则要求,用来与犯罪作斗争的侦查行为应当与“罪行的严重性、犯罪嫌疑程度、查明案件事实的必要性”以及所涉及的宪法权利相称。例如在德国,法庭在评估侦查人员取证行为是否符合比例性原则时,使用的是所谓的“最小强度手段”分析标准,即如果强度小的手段已经足够,那么较大强度的手段就是不被许可的。1963年6月10日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判决的“抽取脊髓案”典型地诠释了比例性原则的运用。在该案中,法庭裁定,警方为了确定嫌疑犯精神上是否健全,从嫌疑犯身上提取脊髓的侦查行为违反了比例性原则。虽然刑事诉讼法在通常情况下赋予侦查人员这样的职权,但是,这种行为却显然与所指控的那项轻罪(背信罪)不相适应。
因此,比例原则所主张的方法,实质上是衡量侦查机关取证行为所欲达到的目的与公民的宪法权利之间是否成比例,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这种办法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如过于依赖于个案情况,即在某些案件中适当的方法对于其他案件来讲可能未必具有正当性,有学者据此担心比例原则的适用会导致了法律的确定性和统一性遭到破坏,尤其是在法官直接援用此一原则时会因为法官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导致法官滥用比例原则。我国台湾地区宪法学学者陈新民认为,尽管比例原则存在着这样的缺陷,但不能据此否认比例原则在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比例原则的上述不足则可通过法院日积月累的判决,对“公益”及“人权”价值的关系逐渐累积成一些“典型案件”,以提供较为清晰的指标,从而消减比例原则“不确定”的色彩。(24)
就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而言,首先需要将特定侦查行为或与之相关的具体个案予以类型化区分,并以立法或判例形式来加以具体规制。比如,在立法层面,可根据侦查行为对有关宪法权利的侵犯程度,或者特定宪法权利的重要程度来设定此类侦查行为的法定条件。以德国法为例。由于监听易于造成对公民隐私权的严重侵犯,因此,在德国法上,实施监听需要较高的法定条件,情报部门实施监听的要求是:怀疑有事实上的依据(G10,第1款);刑事侦查部门监听的要求是:怀疑应当建立在明确的事实基础之上(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a),明显高于获得一般性搜查令的标准。(25)同样,鉴于公民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德国宪法法院要求对出版机构的搜查应适用更高的条件,即搜查应当“保证能够成功地获得适当的证据”,明显高于一般的搜查标准。(26)
在司法层面上,可以从司法方法论的角度,对特定类型的案件进行概括与归纳,以形成可供刑事非法证据实践遵循或比照的先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73年1月31日判决的“私人谈话录音案”(27)可以提供一个极好的例证。在该案中,联邦宪法法院阐述和演示了以宪法权利为基础排除非法证据的所谓“三步分析法”:第一步,判断证据的使用是否会侵害宪法所确立的个人核心权利,这是个人的最私密空间,超越于所有的政府权力。因此,无论指控有多严重,侵犯这些权利的证据必须排除,如在夫妻卧室内装电子窃听装置而取得的证据。第二步,判断证据的使用是否会侵入个人核心权利之外的隐私领域。侵犯公民这一领域权益的证据可以在法庭上使用,前提条件上它所代表的公共利益能够超越私人利益。这里涉及利益的重要性程度权衡。隐私领域之所以得不到核心秘密空间那样绝对的保护,是因为作为现代社会一分子的公民有义务接受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如社会成员的生命权和自由民主的社会秩序)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第三步是分析案件所涉及的证据是否属于不会泄露公民隐私信息的证据,比如商业会议的录音等。采纳此类证据不会侵犯被告人的隐私权,因此通常不会被排除。最终,法庭认为所涉及的国家利益并不超过隐私领域内的个人利益,因而不足以引起采纳录音带的效果。不过,法庭也指出,如果所指控的罪行不是纳税欺诈而是暴力犯罪,结果则会相反。(28)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行为的种类和性质多种多样,非法取证的形态五花八门,个案的具体情形又难以一一预知,因此,在公民宪法权利与刑事侦查取证权之间并无划一的边界,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不可能成为可以简单套用的公式,它既需要立法上的周密设定,也需要基于个案情形的司法续造。但是,无论如何,公民宪法权利应当成为非法规则最高位阶的规范目的,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置目的并不是为了排除一切不符合诉讼程序规定的证据,其核心是通过这种特殊的程序性制裁机制,来纠正和杜绝侦查人员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从而为刑事侦查取证权的行使确立明确的法律边界。至于更为精致的实务操作标准,只有刑事非法证据规则真正落实到司法实践,在司法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才能有效提炼并逐步完善。
结语
就目前而言,直接以宪法权利来指导排除非法证据的司法实践,显然存在着体制上的障碍。我国没有宪法诉讼,公民在其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不能在专门的宪法法院提起独立的宪法诉愿,或者由普通法院直接援引宪法规范作出裁判。宪法条款不具有可诉性,宪法权利条款自然缺乏直接适用性;法官也没有宪法解释权,而真正拥有宪法解释权的全国人大迄今也从没有行使过宪法解释权。然而,随着宪政和法治建设的推进,这种状况相信会有所转变。但即便如此,宪法权利的精神仍然可以透过立法和司法行为以及法理的诠释传递到排除非法证据的司法实践。
明确以宪法权利来引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使立法者和裁判者充分领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背后的重大法益冲突,明了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和慎用性。既不可为排除而排除,亦不可应当排除而不知排除。其次,随着我国侦查取证技术水平及刑事诉讼文明程度的提高,宪法权利仍能为非法证据范围的适量扩张提供兼顾安定性与包容性的立足点。再次,虽然就目前而言,宪法的实际权威度不足,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权利宣言书必将进一步深入人心。借根本法之力,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其所涉法益冲突以及法治所须付出的理性代价,也将会获取更多的社会认可。在这一点上,宪法权利或许比那些具有外国血统的“大词大语”更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
有人曾将我国的公民宪法权利喻为“睡美人”。这位“睡美人”何时醒来,以她的华美典雅之光缓和权力运作的暴戾之气,直接普照芸芸众生的百姓生活,就目前而言,尚是一种期待。
注释:
①参见陈光中、张小玲:《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1期。
②代表性的作品有:童之伟:《从若干起冤案看人身自由的宪法保护》,《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林劲松:《刑事诉讼与基本人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2004年5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学术研讨会,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③除了一律排除说和真实不排除说,其他观点还可以表述为区别证据种类说、排除加例外说、线索转化说等,但后者只是区别对待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因而可以归入广义上的区别对待说。
④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2001年1月2日,高检发诉字 [2001]2号)。
⑤极端的例子是,一些使用强制性取证手段获取的物证对于公民宪法权利的侵害程度并不亚于刑讯逼供。如在罗钦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加利福尼亚州警察未持搜查证进入被告家中,并闯入被告卧室,被告见状立即将两个药丸吞入腹中。警察认为被告所吞食者是毒品,就迅速扑上卡住被告脖颈以阻止药丸进入腹中,但未能成功。警察于是强制被告到医院,不顾被告反对,要医生以胃管迫使被告将胃中药丸吐出,果然为毒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警察的取证行为不仅侵犯了被告的隐私权,其手段更是“震撼了良心”,因此排除了所取得的证据。参见Rochin v California,342 US 165,(1952).(值得注意的是,此案判决的年份是1952年,根据当时判例,证据排除规则尚不能适用于各州。)其他的例子又如强制抽取血样,或者开刀取出体内的子弹以供比对等。
⑥联邦德国宪法法院1964年2月21日判决的“日记案”可以提供一个例子。这是一起伪证案,争点是被告人的日记是否应当被采纳。被告曾在另外一起案件的审判中作证,并否认与自己有牵连。但是,她有一本藏于别处的日记记载了她事实上与前案有所牵连,后被人提供给警方。初审法院采纳了这本日记,并据此判决被告犯有伪证罪。宪法法院认为,该案的取证手段并不具有强制性质,但侵害了被告的隐私权,因此应当排除作为证据的日记。Judgment of Feb.21,1964,19 BGHSt 325(1964).
⑦Mirjan Damaska,Evidentiary Barriers to Conviction and Two Models of Criminal Procedure:A Comparative Stud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January,1973,p 513.
⑧陈瑞华:《刑诉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法学》2003年第6期。
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尚无此类排除规则,但是民事诉讼程序中已有突破,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⑩William Twining,theories of Evidence:Bentham and Wigmore,London,1985,p.28.
(11)IA John Henry Wingmore,Wigmore on Evidence,§37.1,at 1018(Peter Tillers rev.1983).
(12)在Arizona v.Fulminate一案中,他反对对供述的非自愿性概念作扩张性解释。Arizona v.Fuminate,111 s.Ct.1246 (1991).
(13)这一分类由美国学者科弗和阿莱尼考夫首倡,参见Robert M.Cover & T.Alexander Aleinikoff,Dialectical Federalism:Habeas Corpus and the Court,Yale Law Journal,Vol 86,1977,at 1092-1093.
(14)林钰雄:《从基本权体系论身体检查处分》,《台大法学论丛》第33卷第3期,第150页。
(15)[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16)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以下。
(17)参见谢鹏程:《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以下。
(18)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法学家》2004年第4期。
(19)同前注(14),林钰雄文,第168页。
(20)关于私人不法取得证据的效力问题,有德国模式与美国模式之区别。在德国,由普通公民转交给警方的证据如果侵犯了个人隐私权,同样会被排除。在这个方面,德国并不对警方行为和私人行为加以区分,主要的关注点是在法庭上使用该项证据的效果。而在美国,同样的取证行为,如果由侦查人员实施,则会被排除;如果系侦查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实施,则会被采纳。 See,Graig M.Bradley, The Exclusionary Rule in Germany,Harvard Law Review,March,1983,P1043.从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角度观之,德国模式似乎更优,但是,对于私人非法行为所获证据的排除与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所获证据的排除不应适用相同的标准。
(21)参见胡建森主编:《论公法原则》,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22)参见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23)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页。
(24)参见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册,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80~281页。
(25)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2条,获得一般性搜查令的标准是:推测进行搜查可能收集到证据材料。
(26)同前注(13),Robert M.Cover & T.Alexander Aleinikoff书,第1041页。
(27)该案的案情是:一对夫妇将一些财产出售给被告人。被告人为了规避纳税,要求这对夫妇在合同中低估所出售财产的实际价值,然后由被告人将实际差价(70,000DM)以现金的形式付给他们。在被告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对夫妇录下了涉及税务欺诈的谈话,随后,他们将录音带交给了警方,于是出现了这盘录音带能否作为证据使用的问题。
(28)See,Kuk Cho,"Procedural Weakness" of German Criminal Justice and Its Unique Exclusionary Rules Based on the Right of Personality,Templ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Spring,2001,pp.24-27.
标签:法律论文; 非法证据排除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刑事犯罪论文; 人权论文; 思考方法论文; 刑事诉讼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