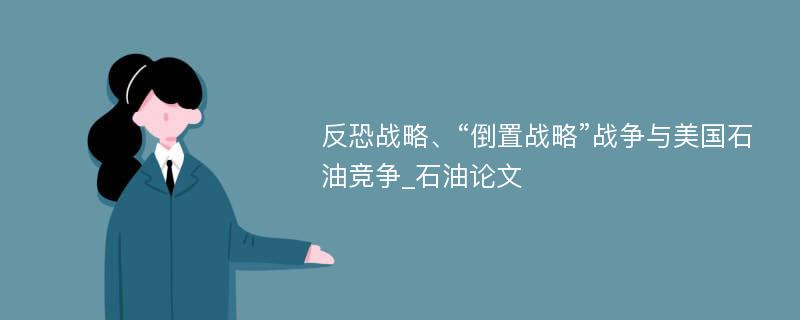
反恐战略、“倒萨”战争与美国的石油争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反恐论文,石油论文,战争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倒萨”逻辑中的石油因素
“9·11”事件以来,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改变了当今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将改变全球能源地缘环境。阿富汗反恐硝烟尚未散尽,美国又借反恐的“东风”,把矛头转向了伊拉克,寻找种种理由和借口,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和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地打响了力图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倒萨”战争。美国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这场战争将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值得人们的深思。
布什鹰派政府关于萨达姆·侯赛因政权“邪恶”的各种论调不一而足,但都找不到萨达姆支持或资助国际恐怖主义的有力证据。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化武器,对世界安全和地区稳定构成了威胁的理由,成为布什“倒萨”的主要借口。但是,这些理由或借口不免牵强,难以服人。人们不禁要问,即使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有地区霸权的野心,为什么他不使用呢?萨达姆清楚地知道,一旦他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攫取”了邻国的领土或油田,西方国家就有充分的理由起而攻之;一旦他攻击以色列,同样的命运将会等待着他。“与希特勒相比也许是可笑的——希特勒认为他能够赢,但萨达姆不能。即使他拥有核武器,他也不能赢得一场与美国的战争。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遏制萨达姆,而无需试图迫使萨达姆走向无理。”(注:Mo Mowlam,"The Real Goal Is the Seizure of Saudi Oil,"The Guardian,Thursday,Sep.5,2002.)“倒萨”还可能引发中东地区的动荡,导致反美的革命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的上台,危及中东的石油供应和影响到世界经济。既然如此,布什政府还一意孤行,这是为什么呢?仔细分析,美国“倒萨”的真实意图可能不止一个。其中,争夺和控制伊拉克的石油是重要原因之一,即美国的主要战略目的之一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以及“为了掌控沙特的石油资源”。(注:Mo Mowlan,The Guardian,Thursday,Sep.5,2002.)
第一,美国和英国政府及其跨国石油公司等能源利益集团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海湾战争以来,萨达姆的继续执政阻碍了其获得伊拉克石油的道路。除掉萨达姆·侯赛因,可以使西方的“投标者”获得伊拉克新的石油供应,减轻美国对沙特的石油依赖。实际上,除掉萨达姆,也就是“清除了整个海湾石油自由流动的最后威胁。”(注:Michael Theodoulou,"West sees Glittering Prizes ahead in Giant Oilfields,"The Times,July11,2002.)伊拉克的石油探明储量为1120亿桶,占世界总量的10.8%,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王国(以下简称沙特)而居世界第二位。据全球能源研究中心估计,伊拉克的实际石油储量高达2200亿桶。一旦萨达姆政权跨台,在未来5~6年时间内,伊的石油产量就可能从目前的200万桶/日迅增到600~1000万桶/日,国际石油安全环境将因伊拉克石油的大规模重返国际舞台而获得极大改善,美国的长期石油安全利益也会因为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政府而得到极大提高。(注:Faisal Islam,"Economies face Oil Slick,"The Observer,Sunday,August11,2002.)
作为能源利益集团的代表,美国副总统切尼曾表示,萨达姆“坐在10%的世界石油宝藏之上,因此他拥有巨大的财富”。正是这些财富引起了美国的战略关注。美国现任总统和副总统都曾经是石油商人,其内阁某些成员也出自能源利益集团,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大利益。《七姊妹》的作者桑普森表示,尽管没人怀疑美国人对萨达姆的仇恨,尽管“9·11”事件之后公众愤怒情绪的爆发和对恐怖主义的担心仍然是华盛顿对伊政策背后的主要潜在政治动因,但最近的事态表明,在美国深思熟虑的战略中,“石油已经赫然耸立于民主或人权之上了”。(注:Anthony Sampson,"West's Greed for Fuels Saddam Fever,"The Observer,Sunday,August11,2002.)美国的中东政策长期和深刻地受到了石油因素的影响,在伊拉克问题上也不例外。
第二,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沙特一直是美国最关注的国家之一。沙特石油的储量、产量和剩余生产能力对国际能源供求和油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长期以来,沙特与美国在能源政策和安全领域的“盟友”关系构成了西方石油安全的基石。然而,“9·11”事件以来,美沙关系处于极为微妙的境地。兰德公司指责沙特是“邪恶的中心”,沙特人“在恐怖链的各个层次上都参与了”,美沙关系的不睦已暴露无遗。首先,美国发现沙特政权是由一小撮“极不友好”的王室成员组成的。并且,沙特王室是布什总统反恐战争的主要目标——恐怖主义的主要捐资者。19名袭击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分子中就有15名是沙特人,兰德公司说“这绝不是巧合”。其次,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在对沙特石油依赖问题上,他们不得不有所改变了,即“是终结我们对沙特石油依赖的时候了”。(注:Irwin Stelzer,"Time to End Our Reliance on Saudi Oil,"The Sunday Times,August11,2002.)
然而,美国能够离开沙特的石油而生存下去吗?显然不是也不可能。恐怖主义对美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结果之一,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美国对获得长期稳定的沙特石油的战略意义的认识:
首先,尽管目前美国从沙特进口的石油每天只有170万桶,只占美国进口量的大约17%,但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AI)的预测,20年之后,随着拉美、西非等大西洋盆地国家——美国目前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石油供应能力的下降,美国对沙特等波斯湾国家的石油进口依赖将会更加严重。(注:EIA,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DOE/EIA0484,April 2000,p.175;EIA Monthly Energy Review,April 2001,pp.130-131.)其次,沙特的石油探明储量为2642亿桶,占世界总量的1/4,其最终可采储量可能高达1万亿桶。沙特巨大的石油储、产量在调节国际石油供求平衡、稳定油价方面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仍将是美国不得不倚重沙特的重要原因。重要的是,沙特的温和石油政策是符合美国的石油安全利益和外交战略利益的。“沙特外交政策的关键平衡作用是要把油价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既反对油价的过高以免损害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又竭力避免油价过低从而影响到产油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注:E.L.Morse and J.Richard,"The Battle for Energy Dominance,"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2,p.19.)沙特的这一温和政策特点不仅符合美国长期追求的战略利益,而且对海湾地区其他产油国,特别是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温和石油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对抑制伊朗等鹰派产油国关于高价、高产的主张也具有积极作用。最后,沙特剩余产油能力(目前为300万桶/日)的作用更加突出。沙特剩余产油能力是“等同于核武器的能源,一种对抗那些试图挑战沙特的领导地位和目标的国家的强有力的威慑力量。它也是美沙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把沙特的剩余产油能力看成是其石油安全政策的基石。”(注:Ibid.20.)剩余产能的存在不仅有助于沙特调节供求和油价,而且直接服务于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历史上,沙特多次证明了其剩余产油能力的作用。例如,伊朗革命和海湾战争期间沙特动用其剩余产油能力,增加产量,对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平抑油价起到了关键的平衡作用。
沙特石油既然如此重要,为什么还有人提出“是终结我们对沙特石油依赖的时候了”的主张呢?确实,一旦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以伊拉克的资源基础和生产能力,美国无疑可以减轻对沙特石油的依赖,但并不意味着沙特石油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降低了,伊拉克也不具备沙特拥有的独一无二的资源基础、生产和出口能力。美国担心的究竟是什么?可以说,美国主要担心的是沙特政权的稳定性,担心沙特出现一个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使命的反美反西方政权,进而影响到美国在沙特的石油利益。“9·11”事件以来,沙特王室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本·拉登之流攫取沙特政权的可能性,引起了美国的关注和担心。本·拉登之流“建立一个全球伊斯兰国家,把油价提高到每桶144美元”的风险是存在的。(注:Jeremy Rifkin,"Pumping up the Pressure,"The Guardian,Friday,April 26,2002.)历史上,石油与伊斯兰之间的联系就不可分,石油是伊斯兰国家仅次于对“真主”信仰之后的、最可依赖的资源、最大的“平衡器”、精神和地缘政治斗争武器。本·拉登之流即便不能攫取沙特政权,也将以恐怖主义方式袭击沙特的石油供应设施,在严重情况下,也可能影响到美国的石油供应安全。(注:David Buchan,"Reliance on Middle East Poses Problems,"Financial Times,Feb.1,2002.)本·拉登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最终目标,如果不是大规模报复西方,“就是推翻沙特家族”;“通过袭击石油供应国或中东国家政权,本·拉登先生的支持者将会给西方强有力的一击。”(注:Neela Banerjee,"Fears again of Oil Suppliers at Risk,"The New York Times,Oct.14,2001.)因此,美国的反恐战略表面上是为了防止恐怖主义颠覆亲西方的沙特王室政权,而深层动机仍然是沙特的石油资源。
第三,长期以来,控制沙特和伊拉克的石油,确保整个波斯湾安全和稳定的石油供应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目前石油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降低,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充足,国际能源安全环境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有了长足改善和进步。但是,美国时刻念念不忘的仍是中东石油。波斯湾是导致两次石油危机的发源地,是引发世界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率升高以及金融和债务危机的主要根源。两次石油危机使美国经济损失了4万亿美元,(注:D.L.Greene,"Economic Scarcity,"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Summer 1997,p.17.)其经验教训不谓不深刻。而波斯湾目前仍拥有世界探明石油储量的64%,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战略奖赏”。(注:Geoffrey Kemp,"The Persian Gulf remains the Strategic Prize,"Survival,Vol.40,No.4,Win.1998-1999,P.136.)石油安全史也已清楚地表明,波斯湾的政治稳定与石油供应安全之间一直存在着“瓶颈作用”,动荡多变的中东政治形势是美国能源安全的最大隐患,每次石油危机无不与波斯湾的政治形势发展有关,1973年和1979年石油危机是政治的副产品,1991年海湾战争也是为了石油。正因为如此,美国和西方将波斯湾继续限定为具有至关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就不足为奇了。(注:Shibley Tehhami,"The Persian Gulf:Understanding the American Oil Strategy,"The Brookings Review,Spring 2002,Vol.20,No.2,p.32.)
第四,确实,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拉克问题增加了中东政治多变的因素,也增加了中东石油安全的风险。然而,在目前中东局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美国的“倒萨”大旗一旦成功,一可以除掉伊拉克这个非稳定因素,获得对伊的石油控制;二可以进一步增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政治军事实力,控制沙特的石油;三可以对伊朗形成多层遏制,防止伊朗的重新崛起对波斯湾石油供应构成威胁。最终,获得对波斯湾石油的基本控制。总之,如英国前内阁成员莫兰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倒萨”的“整个事态与伊拉克威胁毫无关联,与反恐战争或道德也没有关系”。美国的战略实质只不过是,“在反恐战争的掩护下,以拯救西方的名义,攫取和控制这些至关重要的资产(石油)而已。”(注:Mo Mowlam,"The Real Goal is the Seizure of Saudi Oil,"The Guardian,Thursday,September 5,2002.)
从科索沃到阿富汗:通往中亚石油之路
在“9·11”事件爆发前夕,石油供应安全问题就再次提上了西方国家的议事日程,其标志是美国“国家能源政策”报告的出台和欧盟“21世纪战略能源的挑战”计划的问世。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没有在石油安全问题上沾沾自喜、掉以轻心,石油安全问题仍然是美国头等关切的重大经济和外交战略问题。美国和西方的全球战略在强调获得中东石油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其对中东石油日益依赖的危险性和脆弱性。“当传统的战略家展望2020年或2050年时,他们仍会看到作为国际能源安全政策的关键因素的中东石油。”(注:Dan Plesh,"Ending Oil Dependency,"The Observer,Sunday,Oct.7,2001.)美国总统布什也强调说:“多元化不仅对能源安全而且对国家安全都是重要的。过度依赖于任何一种能源来源,特别是国外的能源来源,使我们极易受到油价冲击、供应中断以及在最坏情况下被勒索的影响。”(注:John Pliger,"A Meeting of Blood and Oil:the Balkan Factor in Western Energy Security,"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Vol.4,No.1,May 2002,p.77.)波斯湾的石油因素束缚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手脚,作为一项战略解决方案,减轻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改善美国在中东的政策选择、赢得长期的反恐斗争的需要,就成为了美国的一项全球战略计划。
1991年苏联的解体打开了中亚独立国家油气资源的“潘多拉”盒子,里海丰富的油气资源立刻吸引了美国政府和跨国石油公司的注意。随着里海油气资源的纷纷发现,跨国石油公司蜂拥而至。但是,里海究竟有多少油气资源,各种机构的估计相当不一致。尽管如此,石油界在以下四个问题上越来越达成共识:(1)虽然里海不能成为“另一个中东”,但其资源基础预计至少与北海石油储量旗鼓相当。(2)由于国际石油资本进入里海的时间不长,里海的油气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勘探,这意味着里海已知的资源基础还可能增加。(3)出于战略考虑的需要,美国政府可能故意“低估”了里海的石油储量。(注:Gawdat Bahgat,"Oil Securit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Economic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xiv,No.6,Dec.1999.)(4)无论如何,“里海都可能成为今后10年世界石油市场极为重要的新角色”,对美国和西方石油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减轻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注:"U.S.Caspian Area Foreign Policy in Conflict with Resources Plans,"Oil and Gas Journal,Aug.11,1997,p'.19.)
然而,里海是内陆湖,远离西方的消费市场。里海油气再丰富,如果不能输送到消费市场,美国的战略计划和石油公司的投资将毫无价值。中亚大角逐的实质演变成了控制和争夺油气运输线路的斗争。在实施和拟建的中亚油气运输线路中,有所谓的“东向”、“西向”和“南向”等计划。“南向”线路要经过伊朗,把里海石油经过伊朗运输到波斯湾,线路短,成本低,占据了除政治以外的所有有利条件,但与美国孤立和遏制伊朗的政策相悖。“西向”线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得到了大力支持。“东向”线路除指到中国的线路外,还指从哈萨克斯坦等国到阿富汗再到阿拉伯出海口的线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之前,也初步考虑和论证过通过阿富汗中转中亚石油的可能性。如此,“西向”和“阿富汗线路”这两个问题与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美国的中亚石油争夺就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了。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和北约就担心其把里海石油通过“西向”线路运输到欧洲市场的计划会受到科索沃危机的影响。科索沃问题不仅影响到巴尔干地区的稳定,而且阻碍了美国的中亚石油战略计划。美国支持的“西向”线路之一是从保加利亚黑海的布尔加斯港,穿越马其顿到达阿尔巴尼亚亚得里亚海的法罗拉港。也就是说,“西向”线路不得不通过巴尔干地区,其中通过马其顿的输油管,离科索沃仅有20公里。由于“西方在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已经投下了极大的经济赌注”,(注:R.N.Taylor,"The new Great Game,"The Guardian,Monday,March 5,2001.)因此,巴尔干的冲突“对里海油气安全地输送到西方的需要构成了严重影响”。(注:John Pliger,"A Meeting of Blood and Oil:the Balkan Factor in Western Energy Security,"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Vol.4,No.1,May 2002,p.75.)显然,科索沃冲突影响到了美国的能源安全战略计划,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对美国的输油管道建设计划以及美国石油公司的投资造成严重威胁。这也是美国干预科索沃冲突的原因之一。确实,美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是多重的,把南联盟国家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肢解南斯拉夫和遏制塞尔维亚,是美国的主要战略意图。但是,美国宣称的“人道主义”干预也掩盖了其另一深层动机。美国的实际目标之一仍是着眼于“中亚的石油”,中亚石油因素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美国以战争形式干预科索沃的“人道主义”的“催化剂”。(注:Ibid.)
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对美国的中亚石油争夺的影响更加显见。确实,阿富汗是一个贫油国,不足以引起如此重要的战略关注。问题在于,它的北方邻国却蕴藏有对美国来说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油气资源。把里海石油输送到西方的“西向”线路,除要通过巴尔干地区外,还不得不通过俄罗斯,这有利于俄罗斯对中亚的政治和经济控制,这是美国花了10年时间竭力想要避免的事态。如果有一条通过阿富汗的输油管,就既可实现美国的“多元化能源供应安全”的目标,又可使美国“渗透”进入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市场——石油需求旺盛的南亚和东亚国家。把中亚石油通过阿富汗销往南亚和东亚,远比向西销售需求停滞和竞争激烈的欧洲市场有利可图。
1996年9月,塔利班控制阿富汗不久,石油业内人士就指出,获得经过阿富汗的输油管道的梦想是巴基斯坦一直支持塔利班,也是美国默认塔利班征服阿富汗的原因之一。1998年,在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参院外委会主席就表示,亚洲的能源饥渴以及对伊朗的制裁决定了阿富汗仍然是“里海石油惟一可行的其他输出通道”。“9·11”事件爆发前夕,EAI的报告还说,从石油安全的角度看,阿富汗的战略重要性在于其作为中亚到阿拉伯海出海口的“潜在中转站”的地缘价值。不难看出,阿富汗战争之前,石油因素已经成为美国对阿政策的主要考量因素之一。确实,“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危害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并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构成了严重挑战,这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主要和直接原因。然而,美国的反恐战争与其对中亚石油的争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却不是“巧合”。仅考虑反恐恐怕也不能解释这场战争的范围和目的。如同中东的埃及一样,阿富汗对于中亚的地区控制和石油争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亲西方的阿富汗政府更容易使美国获得通向里海石油的“阿富汗之路”;一旦美国成功地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以一个感激涕零的亲西方政府取而代之;一旦美国“凝固”了中亚和巴基斯担的经济,它就不仅打击了恐怖主义,而且也打击了中俄两国不断增长的中亚石油“野心”。(注:George Monbiot,"American's Pipe Dream,"The Guardian,Tuesday,October 23,2001.)
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以扫除恐怖主义残余和保护亲美的卡尔扎伊政权为由,宣布将“无限期地”驻扎在阿富汗。不仅如此,美国还借反恐的“东风”,将其政治、军事势力“楔入”了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美国和格鲁吉亚都说,格鲁吉亚处于“恐怖主义”威胁之下,因而需要美国的保护。实际上,保护输油管才是掩藏在美国训练格鲁吉亚军队反恐背后的“一个关键动机”。反恐不仅仅是美国和格鲁吉亚关系的惟一理由,“格鲁吉亚也是里海石油与土耳其之间最短的输油线路”。英国石油公司表示,“输油管自然会从美国的军事存在中受益”。(注:N.P.Walsh,"Oil Fuels US Army Role in Georgia,"The Observer,Sunday,May 12,2002.)从符合逻辑的角度看,美国长驻中亚的真实目的之一仍是中亚的石油,并具有兼顾牵制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意图。
反恐战略与美俄新型石油关系
美国的反恐战略不仅在中亚获得了巨大成功,有利于美国对中亚石油的争夺和控制,而且改善了与俄罗斯的关系。美俄新型石油关系的建立,可以说,也是美国反恐战略的具体成果之一。2002年5月,在“9·11”恐怖袭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致力于重新定义美俄新型伙伴关系的布什总统和普京总统,即在莫斯科首脑会晤期间签署了美俄“能源合作协议”。美俄之间的能源合作“将进一步减轻美国对中东的石油依赖,并予以布什总统在对伊问题上的更大灵活性”。俄罗斯以帮助美国反恐的方式使自己的石油进入了“诱人的美国市场”,而美国以反恐的名义赢得了“来自西伯利亚的礼物”。(注:Peter Baker,"Russia sees US as New Market for Oil Reserves,"Washington Post,Sunday,Sep.8,2002.)
美国为什么如此看重俄罗斯的油气资源呢?这既是美国反恐战略的需要,也是美国反恐战略与石油安全战略的有机结合。
第一,俄罗斯的油气资源基础、生产和出口能力是吸引美国战略注意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俄罗斯拥有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4.6%和天然气探明储量的32%,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能源工业的民营化进程不断加快,石油产量每天几乎增加了50万桶。2002年2月,俄罗斯石油产量超过沙特,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俄罗斯的前身——苏联的石油产量历史上一度高达1250万桶/日,占世界产量的1/5。近年来俄罗斯石油工业加速发展,其发展趋势表明,俄罗斯“正在成为通往下一个休斯敦——全球能源首都——的道路之上”。加拿大媒体更是把普京称之为“新的世界石油沙皇”。(注:Fiona Hill,"Russia:the 21[st] Century's Energy Superpower?"The Brookings Review,"Spring 2002,Vol.20,No.2,p.28.)
第二,俄罗斯能源工业的重新崛起以及作为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一支越来越重要的力量,刚好迎合了“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政治和战略需要。“9·11”事件以来的形势发展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对进口石油,特别是来自沙特石油脆弱性的担心。反恐的需要与对石油供应安全的担心使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必然进行能源合作。其逻辑基础是:美国将供给俄罗斯能源工业亟须的金融资本,作为回报,俄罗斯向美国提供稳定的石油供应。如此一来,“美国就能够更少暴露在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脆弱性面前,而俄罗斯的石油财主将拥有美国巨大的市场。”(注:Peter Baker,"Russia Sees US as New Marker for Oil Reserves,"Washington Post,Sunday,Sept.8,2002.)
第三,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地位和影响也是美国不得不倚重俄罗斯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要想获得中亚石油,必须处理好与俄的关系。俄罗斯里海部分的石油资源不如其他里海沿岸国家丰富,却不意味着其不看重或放弃里海的石油权益。事实上,俄罗斯与里海沿岸国家在里海的法律地位和资源分割上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有可能对中亚石油的开发利用构成潜在影响,进而影响到美国的中亚石油利益。“9·11”事件以前,美国的对俄政策一直遵循着两个自相矛盾的目标:一是鼓励俄罗斯更好地保护美国资本在俄能源业的投资,二是支持里海国家避免通过俄罗斯的输油管道输送石油。“9·11”事件之后,出于争取俄罗斯对美反恐斗争的支持以及获得中亚石油的需要,美国的政策不得不做出重大调整。这是美俄签署能源合作协议的原因之一。其目的是以深化与俄能源合作的形式,不仅获得俄的石油供应,而且确保美国对中亚石油的争夺和控制。(注:Michael Lelyveld,"Russia:Are Oil Exports to US a New Strategic Trade?"Radio Free Europe,July 9,2002,on line www.rferl.org.)
第四,美俄之间在伊拉克问题上也有重大分歧。伊拉克长期以来一直是俄的伙伴国家,即便在海湾战争之后受国际制裁的10年时间里,两国也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贸关系。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在伊拉克有数十亿美元的开发伊石油资源的合同,只等联合国的制裁解除之后即可实施。美国借反恐的“东风”试图推翻萨达姆政权,势必危及到俄在伊拉克的利益。美俄新型石油关系的建立,美国以能源合作的形式,使俄罗斯石油比较容易进入诱人的美国市场,借此可以缓和俄罗斯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其战略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注:Gawdat Bahgar,"The New Geopolitics of Oil:the US,Saudi Arabia and Russia,"MEES,Sept.9,2002.)
结论
美国反恐、“倒萨”与其全球石油战略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系。美国反恐主要涉及中亚和中东,而这两个地区是世界石油的“心脏”地带,其中的逻辑联系是显而易见的。逆向推理也应该是成立的,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推行全球反恐的最大赢家不是任何其他国家,而是美国本身。在反恐旗帜下,美国不仅强化了其对中亚石油的争夺和控制,获得了俄罗斯的石油支持,而且通过今天的“倒萨”战争,即将获得伊拉克的石油供应以及进一步加强了对沙特阿拉伯等波斯湾国家的石油控制。在此意义上可以判定,美国的“倒萨”战争并不全是布什政府宣称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之需要,而是具有更深层的动因。
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预见到美国反恐、“倒萨”对我国石油安全的长期影响。实际上,阿富汗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势力长驱直入中亚,已经使我国来自中亚的石油供应处于美国的严重影响之下;美俄签署的“能源合作协议”,又使我国来自俄罗斯的石油供应新增了强有力的竞争因素。可以预言,美国对伊战争之后,将使我国在中东面临的石油供应安全问题更加复杂化了。美国“倒萨”之后,将形成对中东石油的基本控制,一旦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完全可能利用其对中东石油的影响和控制来牵制我国。在最坏情况下,可能严重影响到我国对中东石油的获得。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担心美国会利用它在海湾地区占优势的政治军事存在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作为压服中国的一种工具”(注:Jonathan Rynhold,"China Catutious New Pragmatism in the Middle East",Survival,Vol.38,No.3,Aut.1996,p.111.),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我国目前在中东地区缺乏政治影响和军事能力,不能有效地保障自己在中东的石油安全利益。“中国目前缺乏军事能力,在该地区没有军事基地,也没有必需的海军能力和长距离空军能力在该地区起直接作用。”(注:Jonathan Rynhold,p.112.)显然,美国反恐和“倒萨”的主要战略目的之一是为了石油争夺,而我国的石油安全利益将长期处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影响之下,这将是我国在石油安全问题上的最大安全隐患。
标签:石油论文; 萨达姆论文; 沙特论文; 石油美元论文; 石油投资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恐怖主义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波斯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