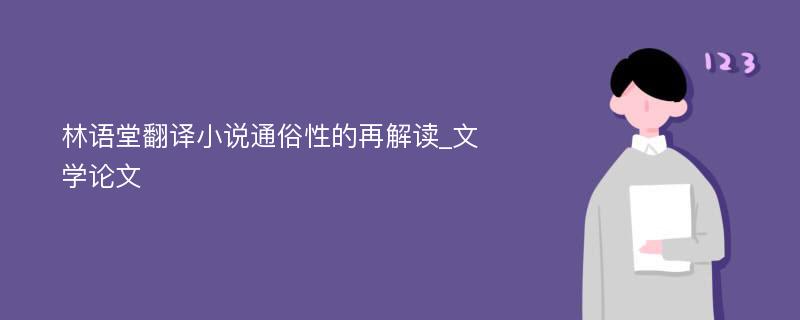
对林译小说风靡一时的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6-0131-05
林译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主体无疑产生了深刻影响。周氏兄弟、郭沫若、茅盾 、胡适、冰心、庐隐等作家都深受“林译小说”影响,周作人说过:“老实说,我们几 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 过他的译文。”[1]鲁迅尽管也从事小说翻译,但他对林译小说情有独钟。对此,周作 人曾经说过:“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 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版书面, 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2]郭沫若在谈及林译小说时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 很流行的,那也是我嗜好的一种读物。”[3]冰心十一岁就被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 事》所吸收,成为她“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 文学作品的开始。”[4]所有的这些表白,都表明了林译小说的确曾经风靡一时,并对 这些新文学的参与者的文化心理结构以深刻的影响。
我认为,林译小说之所以会风靡一时,是林纾的翻译契合了接受主体在特定的文化交 汇点上独特要求。一方面,林纾及其小说翻译,满足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接受主体的精 神需求;另一方面,接受主体的精神需求又反转过来促成了翻译主体的文学翻译活动的 继续和深化;特定的历史交汇点的独特要求注定了林译小说的中介性作用:它在风靡一 时之后,将会最终从文化中心而趋于边缘。尽管林纾和林译小说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历史 局限性,但其作为中介的历史作用是无法抹杀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林纾和林译小 说,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就缺少了一个连接这两个端点的中介性桥梁。
那么,在历史风云际会之时,为什么不懂外语、也没有留过洋的林纾的翻译反而切合 了读者的审美需求,并形成了一股颇有势头的文学现象,以至于我们对此用“林译小说 ”这样的专门术语来概括它呢?而那些懂外语留过洋、对西方文学自恃有着更为准确的 把握的翻译者,其翻译的文学作品并没有为读者所认同,甚至在早期也从事翻译活动的 周氏兄弟也反转过来,对林译小说爱不释手呢?质言之,林纾这一翻译主体的哪些独特 的精神特质满足了这样的一种审美需求的呢?
一
在对林译小说的解读中,时常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林纾不懂外语限制了他的翻译,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种言说模式,在充分肯定了林译小说的历史作用之后,总附带着指 出,林纾因不懂外语而使其翻译具有局限性。如寒光早在三十年代就认为,林纾“最大 的缺陷在于不会直接读原文”[5];当代知名学者郭延礼也基本上由此立论,认为林译 小说之所以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平,就在于其不懂西文[6]。即便林纾自己也曾经这样说 过:“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7],转而“惜余年已五十有 四,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请业于西师之门,凡诸译著均恃耳而屏目,则真吾生之大幸 矣。”[8]其实,林纾不懂外语,恰恰是他翻译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缘由。
实际上,林纾如果懂外文,他的翻译可能要比当下我们所见到的文本形式,在理论上 更完美,对西方文学的本体更切近,但是,作为历史发展中介的林纾就可能要退出我们 当今的文化视野。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林纾即便不能承担历史要求的体 载者,历史也会造就出这一历史要求的体载者。不管怎样,有一点是不会有大的偏差的 ,那就是其翻译在保持西方文学的基本韵味的同时,也契合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接受主体 的审美心理需求。在翻译过程中,拘泥于西方文本,用直译的方式直接登陆中国文化语 境,肯定无法找到其契合点;如果拘泥于中国接受主体的审美需求,完全改变西方文学 的本来面貌,肯定无法实现接受主体新的审美心理的培育,只有既遵循了西方文学的文 本世界,又把其纳入到中国文化语境,才能找寻到其契合点,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林纾 的翻译符合了这一现实的客观需求。林纾不懂外文,使他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己既有的 中国文化立场,他用中国文化立场来理解和整合西方文学,就实现了西方文学的东方化 过程。他人的口译使林纾的翻译只能在口译的基点上展开自己的东方化过程,他无法更 改其文学叙事所规范的既定事实,这就保证了林纾的翻译保留了西方文学的基本特质, 使其翻译确保自我独立的文学品格,不至于成为悖离西方文学的信马由缰式的杜撰,这 也是其翻译给接受主体以新的审美冲击力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接受主体对西方文学爱不 释手的重要缘由。这恰如钱钟书所说的那样:“我自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 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 ,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 界。”[7]钱钟书的这一表述起码明确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林译小说尽管是用中国 话语建构起来的独立文本世界,但这一独立文本世界是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的一个“新 天地”;另一方面,林纾的翻译,显然并不是直接照搬西方文本,而是经过自我文化心 理结构的整合,也就是说,林纾的翻译,已经在他的翻译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理解, 纳入到了自我所认同的中国文化中。这也是为什么林纾在翻译的过程中,总是用中国传 统文化的价值尺度来比照西方文学的重要缘由。这确保了林译小说尽管打开了不同于中 国传统小说的“新天地”,但绝不是一个和中国的文化绝缘了的审美“新天地”,在这 个“新天地”里,林纾还整合进了许多属于自我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这整合后的文本 世界,在西化程度较深的接受主体那里,则会感到它和西方文学的本体世界相去甚远。 这且不说在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那里对林译小说持何种否定态度,单就部分地 进入西方世界的、带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接受主体那里,就已经觉察到了林译小说存在着 无意误译和有意增删等问题。对此,钱钟书说过“后来,我的阅读能力增进了,我也听 到舆论指摘林译的误漏百出,就不再而也不屑再看它。”[9]尽管他们可以“不屑再看 它”,但林译小说的中介作用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些以后“不再而也不屑再 看它”的小说,却是当初为自己打开一片审美的“新天地”。其实,林译小说还是当初 的林译小说,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什么变异,出现变异的仅仅是接受主体的 文化心理结构,所以,通过这差异,我们可以看到,林译小说具有“非西非中”和“亦 西亦中”的文化品格。并且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使林译小说在特定历史坐标上获得了独 立的中介价值。
事实上,林纾在别人口述的基础上进行的小说翻译,经过了两次文化心理结构上的整 合。第一次是口述者本人对西方语言体系的汉语口语化,这经过了口述者既有的文化心 理结构的整合。我们知道,语言的转换,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从一种文化心理 结构到另一种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过程,所以,语言作为文化最直接的载体,本身就是 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操持外语的学人,多会具有西化倾向的重要原因。
林纾的翻译在口述者的基础上的再次加工,这就最大限度地促成了西方文学的再次东 方化过程。口译者本人之所以没有直接进行翻译,而是选择和林纾进行合作,就在于他 们可能感到,自己的口述如果没有林纾的再加工过程,其翻译就可能不符合时人的审美 需求。那么,林纾不同于翻译者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呢?无非就是经过林纾的笔译之后, 其文本更易为接受主体所接纳,这就是经过林纾的“因文见道”后,从口译者的口语转 化为林纾的古文的“林译小说”。
如果林纾有丰厚的西文功底,其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势必会出现裂变,其翻译就会出 现程度不同的西化倾向,这样的话,在接受主体那里,林纾翻译的小说就会和他们既有 的文化心理结构有较大的落差:一方面,认同西方文化的翻译主体,会对林纾这种非驴 非马式的翻译无法容忍,认为他甚至不是在进行翻译,而是自我言说;另一方面,对西 方文化一无所知、类似“白板”的接受主体,对其循规蹈矩的翻译感到无法接受,使其 无法在接受主体既有文化心理结构中寻找到位置,从而出现隔膜。显然,当接受主体完 全离开自己已有的理解所达到的限度时,其接受就无法进行下去。
二
林纾在翻译中使用的古文话语体系,使其翻译和时代的审美趣味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协 调,也就成为其翻译为社会所接纳的又一重要前提。对此,茅盾曾经说过:“林译小说 ”的“这种译法是不免两重的歪曲的;口译者把原文译为口语,光景不免有多少歪曲; 再由林氏将口语译成文言,那就是第二次歪曲了。”[10]当代学者郭延礼也认为:“用 文言译西洋小说或西方学术著作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西方近代文化的新内容与中国传 统语言形式之间确有难以协调的矛盾。”[11]其实,从绝对的价值尺度来衡量林译小说 的话,这样的立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任何真理只能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衡量 ,才会获得合理性的解释。林纾的古文话语体系,不仅没有限制其翻译,反而极大地促 进了其翻译,使其翻译的小说获得了当下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实际上,很多学者早就认同了这一点,如胡适曾就严复用高雅的古文来译西书时说过 :“严复用古文译书,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演说,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若用 白话,便没有人读了。”[12]这样的立论,对严复如此,对林纾的翻译又何尝不是如此 呢。
如果说胡适的立论还仅仅停留在一般理论的阐释上,缺少切实的精神体验的话,那么 ,郭沫若则向我们展示了其阅读的切身体会,他说林译小说的古文翻译:“我最初读的 Haggard的《迦茵小传》……这怕是我所读过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这在世界文学史上 并没有什么地位,但经林琴南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却增了不少的光彩……后来我 虽然也读过《Tempest》、《Hamlet》、《Romeo and Juliet》等莎氏的原作,但总觉 得没有小时候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译述来得亲切了。”[3]郭沫若这一话语,恰好印证 了林译小说的古文话语系统在传播西方小说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不仅如此,它 还说明了,林译小说对现代中国文学奠基者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至于形成 了一种文学积淀,即便是真正地进入了西方小说之后,依然在深层的审美情感上迷恋着 原初的审美体验,感到“林译小说”较之西方原作的文本更“来得亲切”。类似的体验 也许不仅为郭沫若所具有,也为后来钱钟书所具有:林译小说“只成为我生命里累积的 前尘旧蜕的一部分了。”[9]不管是亲切也好,还是“前尘旧蜕”也罢,都说明了这样 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林译小说是他们得以进入西方小说这一崭新审美天地的重要中介。
事实上,符合纯正的理论要求的翻译,在当时并非没有,但正确的理论并没有结出丰 硕的实践果实。像同期的周桂笙翻译的侦探小说《毒蛇图》,就是纯白话,其余的大多 是一些浅近的文言,其明白易懂较之严复、林纾的古文译文要容易理解得多,但却并没 有形成什么风靡一时。这除了其所翻译的文本本身和中国社会现实有脱节之外,也与其 使用白话有着关系。因为白话恰如林纾所说,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一哂”,认 为“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凡京津之稗贩 ,均可为教授矣。”[13]由此林纾信誓旦旦地指出:“知腊丁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 其不宜废者。吾时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14]这出现在五四 新文学发生过程中的文白之争,是林纾早期的文化立场的再次表白;而与林纾不同的是 ,同样在创作和翻译中也一度认同古文的鲁迅,开始了反戈一击:“四万万中国人嘴里 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15]显然,如果比照当年那 个也是长辫马褂、也是操着“之乎者也”话语、还是对林译小说情有独钟的青年鲁迅来 说,其显形层面上的转变无疑标示了其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全面转换。
在论及白话与文言之争时,蔡元培说过,“白话与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 占优胜的。——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从六岁起,到二十岁,读 的写的都是古人的话,所以学得很像。现在应学的科学很多了,要不是把学国文的时间 腾出来,怎么来得及呢?[16]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文化语境,把中国的知识者熏染得“很 像”古人,在这样的情景下,他们在无意识的潜层次上就必然形成了“嗜古如命”的文 化心理结构。所以,古文的外在形式也就契合了他们的这一结构的需要。
翻译由于社会文化、语言、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原因,绝非只是一种——对应的符码转 换,而是要在保持深层结构的语义基本对等,功能相似的前提下,重组原语信息的表层 形式。其中在重组的过程中,甚至一些基本信念被替换、被颠覆,文学发生了“范式的 变化”。西方语言区别于汉语的言文不一,它是言文一致的拉丁语系,这就使文学语言 和现实生活中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和谐一致的。但是,在汉语言中,汉语由于是一种象 形文字,其文字本身具有表达意义的作用,这就使书面语言得以离开口语而存活。而林 纾的翻译,则使西方现代小说的话语被整合为文言话语,并以此实现了对中国传统阅读 心理习惯的迎合,从而完成了登陆中国读者文化心理的艰难过程。这就使人们在一定程 度上接纳了西方小说,并且觉得西方小说和我们的文学与文法取着同一的价值取向,这 就使人们放弃了对于西方小说的排斥性文化心理,具有了一种可以“平等”对话的基础 。当然这里的“平等”是不可能真正的平等对话,但对话本身却表明了对话主体容许对 话对象的存在。
林纾利用自己的古文话语体系和传统文化心理,完成了对于西方文学精神和文化内核 的东方化历程。林纾如果没有这一种对外文的隔膜和正统的传统文化心理,代之以某种 程度上的西化的文化心理结构,那么,其翻译出来的文本要迎合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需 求,将会是非常艰难的。这里也说明为什么前期鲁迅的小说翻译没有获得成功,而林纾 的小说翻译却获得成功的内在缘由;同时还说明了为什么林纾在前期获得了成功,而后 期则被逐出中心而沦入边缘的内在缘由。
三
林纾的中国文化本位,使他的翻译最大限度地契合了接受主体的文化心理的实际状况 ,成为他们由此走出自我的另一重要中介。
很多学者指出,林纾因为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现实语境中,其对西方文化的解读也就 更多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烙印,以至于在解读的过程中,甚至有很多的误读。其实,恰恰 是这一点,确保了林纾在翻译中能够从其独特的文化立场出发,由个体文化情怀引发社 会文化情怀,进而促成了林译小说的最终确立。
林纾的时代,是一个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艰难的时世,已经使林纾这样的知识分 子失去了文化上的自豪感,而甲午之战的失利,更使林纾痛心疾首。江山社稷的摇摇欲 坠、社会矛盾的尖锐激化,文化意识上的重重危机,迫使知识分子把眼光从“从学习唐 宋古文”转向了社会现实,也开始认同“变”的观念。“夫古今之理势,固有大同者矣 ;其为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者,不可穷极也,执古今之同。而慨其异; 虽于词无所假者,其言亦已陈矣。”[17]这就很鲜明地认同时代变了,文不得不变的道 理。尽管这样的价值认同,还不可能一下子成为时代的主潮。甚至他们还认同“法度” ,强调文章之事,“夫有物则有用,有序则有法,有用尚矣,而法不背。”[18]但不管 怎样,这种“经世”倾向,已经使林纾的文化立场出现了转变,这也是支持着林纾企图 通过翻译来应对当下重重危机的一种策略性抉择。这诚如林纾自己所说,“纾年已老, 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19],“以振动爱国之志气”[20]。正是 强烈的“补天意识”,使林纾的翻译契合了探寻救亡图存的时人们的潜在心理需要。
林纾的“补天意识”和“经世意识”,使林纾在解读西方小说的过程中,能够超越自 己既有的文化限制,开始瞩目西方文学所显现出来的西方文化的深刻意蕴。从社会主体 的角度来看,林纾认为“英伦在此百年之前,庶政之窳,直无异于中国”,而英国之所 以超越中国,在于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的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指出“顾英之能 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并进而“恨无迭更司其人”[21]。 在叙及《黑奴吁天录》的翻译动机和心态时,林纾说:“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 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22]。由此可以看出, 林纾解读西方小说时,从补救中国弊端的实际出发,希冀对中国的现实有所推进;其次 ,从个体主体的角度来看,林纾认为“欧人志在维新,非新不学,即区区小说之微,亦 必从新世界中着想,斥去陈旧不言。若吾辈酸腐,嗜古如命,终身又安知有新理耶?”[ 23]林纾这里所显示出来的文化意识,表明了他和“嗜古如命”的个体主体截然不同的 文化立场,显示出“经世意识”参与现实变革的积极的一面。但是,在历史向林纾所开 的玩笑中,我们可以看到,林纾对“嗜古如命”者的决绝态度,似乎昭示其本人就是大 胆突进的改革者,岂不知,林纾的改革只是在自己所画定的“补天”这一范畴下进行。 但这样的解读,毕竟已经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文化意识,开 始认同“维新”的存在价值,并否定了“嗜古”的合理性。这样的理性认知,尽管在当 时还没有形成潮流,或者说连其提倡者也可能在文化实践过程中难以超越原有情感所认 同的理性,甚至这样的理性认知最终还要被认知者纳入到自我既有的文化价值范畴中, 但这样的话语,毕竟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解读主体提供了多种解读上的可能性,从而 为新文学新文化的发生提供了新的认知空间。
在审美理想上,林纾作为纯正的中国士大夫,在中国古典文化的长期寝染中,形成了 对于中国“文统”这一美学传统的认同。在林纾看来,六经、左、史、韩、欧、归、方 是“天下文章之归宿”,作文章讲究开阖、法度、波澜、声音等。对此,林纾表白说“ 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而其之所以认同《红楼梦》,则是从其“叙人间 富贵,感人情盛衰”出发,进而来印证“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 显然,林纾解读“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24]就具有了自己的独特思 维。这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审美标准,表现在林纾解读西方文学时,动辄以司马迁为代 表的“文统”为圭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史迁“笔法”不仅是林纾评判西方文学的价 值尺度,而且还是他认同西方文学的基石。这与其说林纾是对西方小说本体特质的发现 ,不如说是他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自然显现。例如,对《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林纾强调 “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作者司各德“可侪 吾国之史迁”[8]。当他译完哈葛德的《斐洲烟水愁城录》时竟叹曰:“西人文体,何 乃甚类我史迁也!”[23]然而,在过去的一些解读文章中,却对此没有做出较好的解释 ,而仅仅停留在林纾对类比方法的使用上,认为林纾是用中国文学来类比西方文学。而 没有看到,在这类比的背后,林纾以自己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为基础,并把其纳入到了 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获得了其个人化的意义赋予。因此,林纾在翻译过程中,经过 口述者的口译,完成了文学从西方话语到中国口语(也可以说是白话)的形式转变,而林 纾则又完成了从中国口语到文言语系的转换,并在这转换的过程中,对其所包蕴的文化 内涵进行了符合古典审美范式规范要求的重新置换。
林纾对于“文统”的认同,还表现在对于文主雅的审美自觉追求上。这与林纾特有的 文人气质有着较大的关联性。林纾是一个极其重情感的文人,而其生活中的种种不幸遭 际,又在某些方面强化了他的这种情感上的丰富性。众所周知,林纾本人“既遭闵凶, 遂病肺”。[25]而中年丧偶,更使林纾牢愁寡欢。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林纾开始了《 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这动机如果借用其合作者王子仁的话来说,就是“子可破岑 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蹙额对坐耶!”[5]而《茶花女》一书本身所叙述 的凄婉的爱情悲歌,更是和林纾的个人情怀相吻合,引发了林纾的悲情,这样,客体和 主体的情感就寻找了交汇的共鸣点。至于文本自身的悲情,更是和中国社会的普遍悲情 相契合,从而使林纾翻译的第一篇小说就一下子风行海内。这如果用严复的诗来概括的 话,则是“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而其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审美效果,一 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林纾渗透进了浓郁的个人悲情。类似的情感投入, 在林纾的翻译中是经常的。如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时,心情极度悲苦,并且不知 流下了多少眼泪。用他的诗来概括就是:“依微黄种前程事,岂独伤心在黑奴”(《醒 狮诗》)。其实,我们如果联系后期的林纾来考察的话,可以发现,林纾的个体精神还 是属于典型的悲情情感,如林纾“每年于载湉死日,亲赴其陵晋谒,对逊帝溥仪,则 执臣子礼甚恭。”[25]显然,这既是林纾对于西方文学进行整合时所具有的稳定的文化 心理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其外化后的译作之所以能够和接受主体的文化心理 结构获得对接的一个基础。
在调节自我的文化立场和审美理想的关系上,林纾则依恃着程朱理学所肯定的纲常伦 纪的恒定性,把西方小说中的人物纳入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中,进行重新整合和意义 赋予。例如,《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在林纾眼里看到的仅仅是“瞿、翁两孝子而已 ”[26],对于时人废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自由的议论则提出责难,指责他们“自 立异耳”。在《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中,不仅对人物定性为“孝子”,认为“忠孝之道 一也,知行孝而复母仇,则必知矢忠以报国耻。”而且指认“一烈一节,在吾国烈女传 中,犹诤诤然”[27]。如果在这里不急于对林纾的观念做出价值判断,而是从文化心理 结构审视,我们就会发现,林纾对西方小说的认同,是基于把对象所体载的理性,纳入 到中国文化的结构体系中,这无疑是误读和误判。但是,恰恰是这误读,却既迎合了主 流文化的规范需求,也契合了接受主体的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并成为林译小说得以风 靡一时的又一重要缘由。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针对林纾的翻译说过:林纾“每译一书,辄‘因文见 道’”;寒光也说过,林纾“太守着旧礼教,把礼字看得很重,不但他自己的言论和作 品,就是翻译中稍有越出范围的,他也动言‘礼防’,几于无书不然!”[28]志希则认 为,“林先生与人对译小说,往往上人家的当,所以错的地方非常之多。……现在林先 生译外国小说,常常替外国人改思想,而且加入‘某也不孝’,‘某也无良’,‘某也 契合中国先王之道’的评语,不但逻辑上说不过去,我还不解林先生何其如此之不惮烦 呢?”[29]新文化的主将说林纾“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掺进一 种愚谬的批评”。这些论断无疑是符合林译小说实际的,只不过在他们的文化视野里, 对之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而不是由此出发,进一步考察为什么恰恰是搀和了这样的“ 道”、“礼”和“愚谬”的翻译,倒是引起了风靡一时的文学大观,而那些符合其理论 尺度的翻译却是哑无声息、乃至落得个仅仅卖出几本的尴尬结局呢?显然,这里的答案 只有一个,就是林纾在搀和了这样的一些思想和情感之后,尽管其翻译的文本和西方原 文本有了落差,但恰恰是这落差,促成了中国的接受主体对西方文学的接受,而不是妨 碍了其接受。握有话语权的旧派人物能够接受,而居于边缘的新派人物也能够接受。一 方面,这除了“道”本来就早存活于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还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使 他们进一步亲和这样的“志同道合”者,尽管他们后来都背叛了这样的文化理念,但在 行动和潜意识的层面上,他们并没有断绝和这一文化传统的脐带,如鲁迅,面对来自母 亲包办的婚姻,也只能当作“礼物”来接受下来;另一方面,林译小说中尽管搀和了这 样的一些“道”,但还是无法完全遮蔽其文本原初所体载的西方文化的全貌,这就使新 派人物那正在成长着的文化心理结构获得了裂变的机缘,从而在一个新的基点上对西方 文学进行整合,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在接纳林纾和林译小说之后又最终走出林纾和林 译小说的重要缘由。
收稿日期:2004-07-04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小说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艺术论文; 林纾论文; 古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