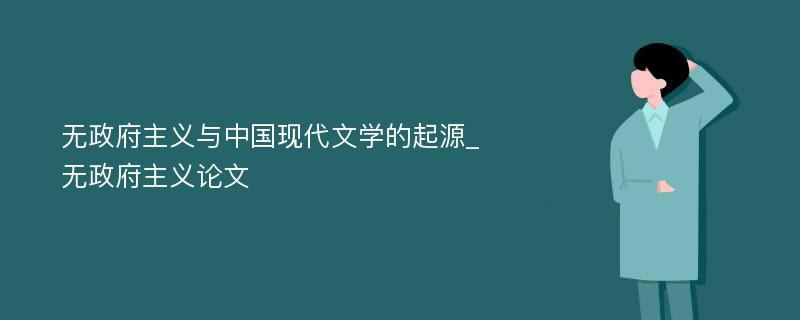
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政府主义论文,现代性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郁达夫曾经说过:“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注: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章·散文二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8 月版。)若以这种“个人”的发现作为现代文学具有了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这种“个人”的发现,并不始于“五四”而应将源头回溯至本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因为早在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已提出了“无父、无君、无法、无天”(注:“四无”见《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第21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的四无主义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原则。如果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视为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区别性特征,也同样要追溯到本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因为无政府主义以个人自由为旨归,既反封建主义,又反帝国主义,率先倡导平等、自由、男女均权、进步主义、世界主义等现代价值观念,可以说正是无政府主义提供了这些现代价值观念的原点。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出现的,单纯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学创作数量不多,也很少受到重视,但为理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对之加以考察是很有必要的。
一
本文打算先分析三篇在本世纪初出现的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小说,以见出无政府主义文学创作在本世纪初所独见的激进、前卫性质。第一篇是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虞初今语·人肉楼》,时间是1902年。这篇小说出现在梁启超主办的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新民丛报》上显得有些非同一般,因为它所持有的明显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民族革命社会革命的观念。小说的主人公叫“天冶子”,生长于“华胥国”,这个“华胥国”是“不知所谓君臣,不识所谓治乱”的“世界中自然一极乐国也”。天冶子带一童子偶入一国游玩,被这国中的人擒住,“亟欲肢解之。”他连忙辩说:“予人也,非禽也”。捉他的老翁说:“汝知此地否,此地名为须陀,吾祖自们焦来居于此,已数百年,专以食人为事,不意此地有数亿人,愈食愈多,食之不尽,顾未尝得一清洁白晰如汝者,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矣。”天冶子随后被带到一处酒楼,楼上悬额为“人肉楼”,其中一位老妪啖人肉最多,十余年间啖须陀人数百万,她旁边有数十人,“专执剖割之役以供奉老妪”。因天冶子人种特殊,所以有人建议先将他“养于一室,待其驯性,察其举动,乃可烹之”。天冶子被关进一室,其地广大无垠,蓄人无数,其中人皮、人眼、人耳、人心、人手足、人脑等各为一堆。“其中,最上品者,乃为人脑,故最为可啖。”而且烹人也分先后,瞎者、聋者、傻者等都排后面,“其目炯炯而其心昭昭者又最多言语者则先之,不特先之,而又多之,故今所余,炯炯、昭昭者无几也”。就在天冶子将要被烹的时候,他带的小童子逃脱,跑回华胥国报信,结果华胥帝举大兵飘忽飞来,声讨其罪曰:“吾种不同须陀种,非易烹也,岂有野蛮烹文明者乎!”遂肆意杀戮,结果使须陀人与扪焦人皆受戕贼。须陀人到这时方才醒悟,“知扪焦人专食我种,也并起而逐之”。结局是“闻老妪走于荒野为村夫所执杀云云”。这篇小说带有明显的政治影射性质,老妪即西太后,扪焦人即满族人,须陀人即汉族人,“华胥国”即梦中理想之国,在这里是以西方为背景想象的一乌托邦国家。“天冶子”有自然之子的寓意。这篇小说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不同于一般倡导革命的小说,着重于满汉之间的民族对立,而在这之上加上了文明与愚昧的对立,而这正是此后的五四人的启蒙主义文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华胥国“不知君臣、不识治乱”,是“世界中自然一极乐国”,显然寄寓着作者一种不同于传统专制社会的乌托邦的社会理想,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与“以人为食”的扪焦人的冲突,就成为一种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人与非人的冲突。而这种文明、愚昧之辨,人与非人之别正是“天赋自由、平等”的现代人意识觉醒的产物。其次,它不只是对满清专制者的吃人罪恶的揭露,而且是对数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抨击。小说中写到天冶子在囚室里看到“食人品分数千、又分新旧,一一标识,最古者为比干心,为鄂俟脯,其次为子胥目,为方孝孺……”由此可知,小说对吃人者的指控已不限于清朝统治者,而指向沿袭已久的专制主义文化。这种对“吃人”的主题的拓展,显然是鲁迅《狂人日记》所揭示的“礼教吃人”思想的先声。将传统社会里推崇的“忠臣贤相”统统视为吃人制度下无谓的牺牲者,这非已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人”的观念的转换者不能为之。而正是无政府主义者以绝对的“自由平等”为号召,成为二十世纪思想、文化领域反传统的急先锋。这是较早的一篇以“自然人”的理想批判中国传统专制社会的小说,作者显已具备了新文化启蒙者所倡导的“现代人”的观念,它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有明显相通之处。但它作为小说,还没有完成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转换,它沿袭了传统的笔记小说的文体,“虞”即是西周始置的掌管山泽的官员,《虞初志》为记载山泽之间的奇闻轶事、志怪志异之作,显然作者以《虞初今语》为题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策略,这增加了它的隐晦和婉转,但也阻碍了它的创作意图的传达,旧的文体束缚了作者新的思想。而《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篇之作的意义,应主要地在于其“格式的特别和忧愤的深广”,而不是象有些论者所强调的它是第一篇彻底反封建的小说。因为《狂人日记》不仅具有思想观念上的现代性,更在于它还具有了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对一种来自于西方的现代的文体形式的运用。同是写“吃人”,《人肉楼》,类似于一种站在局外人立场所做的“奇闻录”,而《狂人日记》则空前拉近了读者与主人公的心理距离,彻底打破了前者听故事时的超然心境,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强烈的审美感觉经验,这种现代文体的采用与作者的深广忧愤合而为一,所以《狂人日记》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文学的开山之作。
如果说本世纪文学中“人”的现代观念的出现在《人肉楼》中只是初萌,那么到了蔡元培的《新年梦》,这种现代人的理想已充分展开。《新年梦》写于1904年,也是一篇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自号“中国一民”,这是一位中国文学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世纪新人”形象。他是“中国人”,但又是“世界人”,他已具有“世界公民”的现代人类意识。他本是江南富家子弟,但自幼性情古怪,读书之外,喜学为“圣人之徒”所不齿的“工艺”,木工、铁工无所不学,一学就会。16岁离家,放弃遗产,自食其力,到通商口岸勤工俭学,学会英德法三国文字,后来游学欧美。因为他最爱和平自由,所以先到美国,后到法国。又因为专门学问德国最高,所以又到德国进高等工业学校,自己又出于兴趣研究哲学,毕业后又几乎遍游世界,然后回到中国。走遍世界的“中国一民”认为现代的世界之弊在于国与国、家与家之间的对抗,耗掉了许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导致“人类的力量还不能胜自然”,因此,世界大同还很遥远,所以最迫切的是“让那没有成国的好好造起一个国来才好,中国人有家没国,还天天说自己是中国人,真是厚脸皮吓”。“中国一民”认为造个新中国也不难,只要“各人把靡费在家里面的力量充了公就好了”。他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实现不了这个使中国人由“家人”到“国人”再到“世界人”的理想,就在梦中展开了他的20世纪新中国、新世界的设计。先是“立国”,再是“立人”,将文明的事业做到极顶。小说中颇有一些在当时人看来颇为惊世骇俗的设想,如在讲到未来文明社会的道德风俗上,他有这样的描绘:“那时候人没有什么姓名,都用号数编的,没有君臣的名目,办事倒很有条理,没有推诿的马胡的,没有父子的名目,小的倒统统有人教他,老的统统有人养他;病的统统有人医他;没有夫妇的名目,两个人合意了,光明正大的在公园里订定,应着时候到配偶室去,并没有男子狎娼、妇人偷汉这种暗味事情”。法律废除了,裁判所也取消了,“那时候造了一种新字,又不拼音,一学就会,又用着言文一致的文体”。最后这种达到顶峰的新文明又从中国,传到俄国、美国、印度、澳洲,直至全世界。大家商量开一个会,把国家都消灭了,把那个已无用了的万国公法裁判所、世界军也废掉了,立了一个“胜自然会”,人类再无互相争斗的事情,“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个世界大同之日到来的日子蔡元培先生把它定在下一个甲辰年,即公元1964年,其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的前夜,这是一个为时六十年(一个甲子)的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者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乌托邦的宏伟构想。
蔡先生的这篇小说发表在1904年,但其在社会上真正地产生广泛的影响或者说遇到广大的响应者则是在十年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非孝”的反家族主义、“新村运动”、“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等等,都可在蔡先生的这篇乌托邦小说中找到先兆。蔡先生的理想国设计的原则主要有两个,一个在于他对于“人”的信仰,或可称之为一种“现代人化宗教”(胡适语),一个在于他的科学主义,他的理想设计依据的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合理原则,如关于“数字人”“配偶室”等等的设想。这种现代合理主义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从神话的镣铐下解放出来,它最初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出现的,但它最终却可能变成一种新的神话:使一切自然的东西服从于专横独断的主体并最后服从于盲目的、客体的东西、自然的东西而达到顶峰。这种理性主义的设计极有可能转化成一种专断主义的恐惧,而这正表明世纪末的人们对这种现代性的整体主义决定论色彩予以反省的必要。
我们要分析的第三篇无政府主义小说是鲁哀鸣发表于1912年的一部白话长篇小说《极乐地》。这部小说写于辛亥革命之后,主要表达的是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的愤激失望情绪以及对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国极乐地的向往。该小说的主题可归结为一句话即中国必须在民族革命之后进行继续革命,通过不断革命来达至乌托邦的至境。小说中的主人公叫“白眼老叟”,他看到昔日的民族革命同志“革命成功,富贵得到手,入则娇妻美妾,出则高车驷马,食则山珍海味,居则深宫华室。国民、贫民非他所问,他所问的就是哪有公款,哪有好看姑娘,某处的名妓来了没有?”革命的结果只是旧官上面添新官,旧税上面添新税,因此认定政治肮脏,一入政界,人便跌进罪恶深渊。因此,他再举义旗,高呼“推倒不良政府,组织共产事业,废掉金银铜钱”的口号,率领二十多万人发动武装暴动,三次打败“中华民国政府”派来镇压的军队。但终因内讧失败,与妻子哀氏一起浮海飘流到了一个海外岛国。这个岛上的居民原是陈余的后代,他们的祖先见刘邦做了皇帝,“朝廷揽极大的权柄,要人生就生,要人死就死,民人没有一点权力,政府看人民如同奴隶、牛马一般”,便全家跑到这里。这个岛国700年前已废了金钱,于是“文明大进,物理昌明”,一片太平繁荣景象。岛上也取消了政府、军队、宗教、家庭和私人财产,并把金银铜钱堆积在罪恶岭当无用之物,最多用它来修桥和造厕所。总之这是一个无政府的乐园,老有所终,少有所养,人们互亲互爱,其乐融融,人们最为热心的事情已变成是科学和发明,以人为战胜自然。
这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政府主义圣徒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地、彻底地抨击。小说中的人物被分别命名为“江无政,孙无家,周无国,高无伦,张排圣,郑斥贤,曹无君,金无父,魏无妻,秦逆俗”等等,向一切传统纲常伦理宣战。作者认为“圣人是万世之贼,当初那些所谓圣人,立了些坏法子,叫什么三纲五常,什么三从四德,这皆是愚人圈套。”因此,主人公主张把那些四书五经并那些臭烂文章都烧尽,因为那里面都是“放狗屁”。他借白眼老叟的妻子哀氏之口说:“凡是世上的书,都是愚民术,尽量引着人做奴才,天赋人一个自由、自主的权,叫这些书束缚着不能申张,非但我们不可以看,还应当为那千古被它愚的人痛哭。”“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圣贤侠士,我没有一句话可以赞美他,唯送他一个谥号,叫做可怜虫”。“那史书上也没有古人的真面目”……。因此当白眼老叟在极乐岛上听说旧书都被烧毁、孔庙当了厕所,夫妻都拍手称快。另外小说还宣传了男女平等思想,并对妇女缠足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做母亲的伤残女儿的两足,刑罚终身,天下宁有这种妖怪慈母耶!这种母亲就是女儿的大冤家、大仇人,这缠足之苦,穿耳之辱,何时不报!”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切齿诅咒之声,不时激荡于整个二十世纪,其中缘由发人深省。《极乐地》反传统之激烈程度,五四时期也无出其右者,若将现代反传统的先驱只是上溯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显然有乖史实,因为《极乐地》不单曾在《国风报》上连载,而且后来还出了单行本,在当时就产生过一定影响。再如将鲁迅《阿Q 正传》等小说的意义仅仅估定在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反思上,也不足以说明鲁迅小说的深刻独到性之所在,象《极乐地》对辛亥革命的批判已经到了相当彻底的程度。
二
美国学者弗莱德里克·卡尔说过:“无论表指艺术还是政治,‘现代’都是一个革命的指令,是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激烈口号,它与各种矛盾、竞争的观念密不可分。”(注:弗莱维里克·卡尔(美)《现代与现代主义》第5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这种“现代”吁求在世纪初前现代的内忧外患的中国,又加上了“不现代”就要被开除球藉的恐惧,因此这种极度焦虑的情绪就引发了一种“宗教性”的现代性,所谓“宗教性的现代性”即是为现代化的变革鸣锣开道,进行社会动员,并赋予现代性以至善至美、超凡入圣的价值,将之视为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方式、灵丹妙药。追求“现代”成为一种面向无限的精神朝圣运动,它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一具体的文明阶段(从西方现代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中是找不到这种神圣性的),而导向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极境。这在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它表现为一种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先机,能动地创造历史的使命感。他们通过否定过去来捕捉现代,现代成为相对于“黑暗的过去”的“光明”,“过去”成为单一的被利用的负面的参照系统,为现代人现代化变革提供理由和依据。传统和现代之间发生了彻底的断裂,“现代”成为一种为未来生存,向未来敞开的时代,它以未来的标准要求现在,否定过去。这就决定了这种“宗教性”的现代性的激进主义色彩。1907年,吴稚晖、李石曾主办的《新世纪》杂志(巴黎),呼唤一种“新世纪”意识,“新世纪”的开端就是“新世界”的开端,他们将二十世纪的开始视为是一场大戏的开幕,将在反清革命中献身的徐锡麟、秋瑾、陈伯平烈士的遗照印在杂志上,称为“新世纪中国开幕之大人物”,“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女豪杰”,而将西太后画成半裸状骑在光绪帝脖子上,称为“帝贼后娼”。“偏激”对他们来说不具贬义,无政府主义的先驱刘师培就曾专门撰文写过“偏激颂”。这种“偏激”也是进行革命动员的策略,按吴稚晖说法,一旦“无政府主义满街走”,那么民族革命也就不在话下。
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影响二十世纪甚巨的几大观念中应首推他们的进步主义信仰,他们相信世界是在“时时更新、刻刻进化”的,人类进步的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因此“反动”、“保守”成为时代最大的敌人。这种进步主义具体地表现为一种创新崇拜,新旧不是时间判断,而是一种价值判断。他们标榜“无政府主义”作为“二十世纪之新主义”是对过去时代的一切主义的超越,《新世纪》首有专文将新世纪革命与旧世纪革命做比较,以见出其“革命”、“主义”之进化。新旧过渡时代的革命目标是“倾复旧政府,建立新政府,此胜于彼”,而“新世纪”则是“扫除一切政府,纯正自由”。前者的革命产生出“党魁、院绅”,“甘言运动”,后者的革命则“废官”“止禄”,“无有私利”。前者的革命者“牺牲利禄,饥渴名誉,铜像峨峨”,后者的革命者则“弃名、绝誉,专尚公理”。这样一种陈义甚高的主义自然较之过去的主义更有吸引力。再则无政府主义较之前此出现的现代性设计如“物质救国论”、“富国强兵论”、“民族国家主义”等都居理论上的优势,它承诺可能解决全部中国问题甚至世界人类问题。甚至与“三民主义”相比,它也具有它的理论优势,这表现在它可以以一个主义包容“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却难以包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要“毕其功于一役”,通过无限革命,直接建成无政府共产主义。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盛行是对政治糜烂的清末民初专制主义的心理反弹,进而排斥一切人为制度的压抑,带向一种空想的、唯意志主义的理想主义。直到一种进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扼制了它的传播势头。由于它自身缺乏真正的社会实践能力,所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政治运动在三十年代已难以为继,所以它转向了文化思想界的活动。三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华林已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文艺中心主义”,要以“感情消灭一切阶级”,这正表明了它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失败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
无政府影响现代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它的“个人本位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倡导反传统的“三纲革命”,“五常革命”,“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的“四无主义”,推动了中国文化由道德本位向个人本位的现代转型。“五四”时期的中学生施存统以一篇《非孝》而闻名全国,就是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启迪,而董凌霜则明确强调:“无政府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五四”反传统的个性解放运动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象郁达夫就非常推崇无政府个人主义的鼻祖斯蒂纳的“唯我主义”,强调:自我就是一切, 一切都是自我。 “Max.Stirner的哲学实是近代彻底唯我主义的源泉,便是尼采超人主义的师傅。”(注:郁达夫《自我狂者须的儿纳》,见《郁达夫文集》第5卷,第82页,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由此引发的“个人”的发现,就是否定个人之与君道、父、母的从属关系,将人从一切社会本质规定中解放出来,以个人主义的价值标准对传统进行价值重估,并成就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无政府个人主义在本世纪由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型中代表着一种离心的、分裂的力量,他们所张扬的个人解放,更多地带有一种感性意味,是一种情感的、欲望的解放。吴稚晖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无治人与被治者,谓之无政府”。(注:吴稚晖《吴稚晖先生文粹》第284页,全民书局1928年5月版。)褚民宜则强调,只有“人不役人而不役于人,人不倚人而不倚于人,人不害人而不害于人”(注:褚民宜《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184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 他们充分肯定人的自然本能欲望,指出:“男女交媾,本为生理之情欲,与饥食渴饮同一绝不足奇之条件”,因此与道德廉耻无关。“爱情之生,其惟男女相悦”,“欲人群进化,爱情普及,必自废婚姻始,必自男女杂交始”。父与子之间“有长幼之遗传,无尊卑之义理。”夫妻之间“就理论言之,若夫得杀妻,则妻亦得杀夫……若夫得嫖,则妻亦得嫖”。(注:《三纲革命》,见《新世纪》第11期,巴黎,1907年。)这种将自然人性论推至极点的个人主义,带有浓厚的反文明色彩。其实人类生存,既需要“进化”,也需要“秩序”,倘“秩序”无存,樊篱尽撤,“进化”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任何文明都建立在对人的感情欲望的程度不同的压抑之上。自然人性论者张扬人的“身体”的无辜和优先性原则,正代表着一种“身体主义”的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我们从张爱玲的《五四遗事》中,可以看到对这种“爱情至上,自由结合”的机智的反讽,它突出表现为一种被克尔凯格尔称之为“美学主义的生活方式”。
无政府主义可主要分为三个流派:斯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薄鲁东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后两者的影响后来明显超过前者,在于后两原都带有更易为国人所接受的民粹主义倾向。它们强调社会正义与社会平等,对资本主义持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倡导“人民主权论”,反对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刘师培在世纪之初就制定了一个由种族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经济革命的无限革命路线。他认为:“地球上邦国环立,然自有人类以来,无一事合于真公。……自民族主义明,然后受制于异族者,人人皆以为辱;自民均之论昌,然后受制于暴君者,人人均以为耻;自社会主义明,然后受制于富民者,人人均以为羞”。(注:刘师培《天义报·启》,见《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第1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因此这种思想上的次第觉悟就会引发行动上的不断革命。这种对“真公”的追求,使他形成了一种非历史主义的道德批判立场,这种批判立场与世纪之交的西方反资本主义的思想潮流一脉相承,身在东方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意大利“阿斯科那”村的无政府主义、世界改良运动遥相呼应,使得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现代性设计一开始就带有了反现代资本主义的色彩。民粹主义使得知识分子自觉得要努力成为社会的良心,民众的代言人,使得他们在投身实际的革命活动之前,已对自己的个人意识、精英倾向进行了先期的克服和自我批判,这种民粹主义对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文学影响之大是毋须多言的,单就文学史来说,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工农兵文学”的嬗变更替中就可以看到它的演进轨迹。
总之,本文之所以要谈论文学史很少论及的无政府主义的文学创作,一是想说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不是突然而至,有它更早的源头;二是想探明世纪初的现代性话语产生的语境和特质,在中国文化、文学即将走完它的百年历程之时,对之进行一次世纪末的回顾,以完成一种由“宗教性”的现代性向“反省性”的现代性的精神转换。
收稿日期:1998年2月28日
标签:无政府主义论文; 现代性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政府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个人主义论文; 新世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