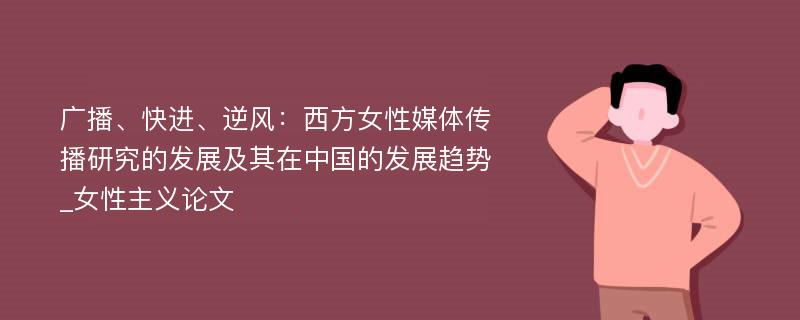
播放、快进与倒带——女性媒介传播研究在西方的发展及其中国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中国论文,快进论文,趋势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4)07-0196-05 “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要求政治承诺的社会运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可以形成学术的理论或者研究的领域”[1]140。因此,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时,可以看清并解释那些系统地存在于组织、行为和一系列规范价值中性别分化的途径。从1970年以来,也即是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进入学术视野期间,缘起于英语国家的西方女性研究就致力于行动主义(activism)、理论建设和方法论上的创新,由于其研究来自于社会中各种复杂与异常的问题[2],其理论棱镜难免复杂多变。一般来讲,女性主义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有三:“差异、发声和再现”[3]。在这个弥漫着的传播的现代社会里,这些理论框架与传播和媒介领域的研究有着不解的联系。因此荷兰著名的女性媒介研究学者凡·祖伦(Liesbet Van Zoonen)的看法“媒介一直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心”是不争的事实[4]14。 从时间发展来看,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第二次女性运动浪潮,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起步、中期快速并全面发展、之后是缓慢发展并不断回望反思,可以说是一个“播放,快进并倒带”的进程[5]4。但本文以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女性主义媒介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参照,把这个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起步、发展、全面发展与成熟并自我修正的阶段。 一、女性媒介与传播研究发展阶段:全球趋势 (一)起步阶段:对妇女刻板形象与社会性别分化的批评 早期阶段:60年代中晚期至80年代初,女性主义的第二浪潮也在这个时期发展并完成;电视开始出现并在北美和西欧等地快速普及,而杂志、报纸、小说以及收音机等传统媒介还是大众媒介内容的主要载体;这些媒介对妇女的刻板形象以及其对受众的影响成为早期女性主义的研究内容。 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妇女运动的复兴与贝蒂·付丽丹(Beetty Friedan)的一部书《女性的奥秘》不无关联,该书的作者本身是一位杂志的编辑,她控诉了妇女杂志这一纸质媒介以及参与共谋的专家给普通妇女带来的心理阴影,指出社会编织的妇女迷思就是让女人困守家庭主妇和母亲这一传统社会角色。1971年,另一名作者吉尔曼·格利尔(Germaine Greer)也在另一本女性主义经典著作《女太监》中强烈谴责了言情小说强化了女性受众对男权社会传统意识形态的迷恋。 1978年,塔奇曼等人编著了《壁炉与家庭:媒介中的妇女形象》,成为了“最早提出完整的理论框架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者之一”[4]22。她在这本著作的前言中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反映了支配性的社会价值观念,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迎合最大数量的受众,妇女注定要遭受“象征性歼灭”(symbolic annihilation)——被责难、被琐屑化、甚至不被媒介呈现。接下来的1980年,美国学者巴特勒和佩斯里(Buteler & Paisley)两人合著的《女性与大众媒介:研究与行动宝典》[6]为塔奇曼的作品提供了话语支持,该书指出:男性在大众媒介和新闻领域中的社会化支配地位,导致了他们生产的产品强调的是男性至上的价值观念。同时期内,麦格·盖勒荷(Maggie Gallagher)连续发表了几部有关女性与媒介研究的书籍,特别讨论了女性在媒介领域内工作机会的不平等现象,倡导妇女积极地参与并有所行动。这些研究论证、支持了该时期妇女运动的诉求[7]。 早期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祖伦发现:这一时期整个“传播研究并没有认识到社会性别议题的重要性”[4]20;在丹尼斯·麦奎尔的畅销书《大众传播学导论》1983年的第一版中,并没有提及“妇女”“社会性别”等女性主义关注的议题。直到1987年的修订版中,才有了一段关于女性主义的内容分析。经过早期女性传播学者的努力与倡导,以妇女刻板形象和性别的社会化以及批判意识形态等议题成为传播研究的最初议程。 (二)发展阶段:多元的议题、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出现 第二个阶段是全面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包括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1994年。这样划分是因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并未在全球普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依然是电视、收音机、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介。这个阶段的传播与性别研究的成果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多种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议题,方法和流派进入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研究视阈:比如,以权力和大众文化的视角来反思女性主义在大众传播学术研究中的贡献;涉及种族和文化、阶级的交叉研究;以及从性别的角度来看科技、信息与妇女的关系等等。 被认为是开启了性别与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内代表性成果的是1987年莱斯利·斯提夫(Leslie Steeves)《女性主义与媒介研究》[8]一文,斯提夫从类型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对基于激进、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框架进行了检视和批评,她把那些专注于色情研究女性主义者称为激进主义者;讨论刻板形象与社会性别社会化的称为自由主义者;而那些强调社会性别、阶级与意识形态互动的女性主义学者则称作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斯提夫认为:当时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占据了美国主流媒介研究的大半江山,然而,这些研究只专注于白人、异性恋以及中产阶级及以上的妇女,没能关注大多数女性的需求;而那些激进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者们又只关注文本而忽略重要的语境问题;相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因为关注女性的社会阶级和权力等问题,具有回答妇女在传播界为何被贬值这一问题的潜能。斯提夫还号召当时的传播学者跳出电影、艺术等人为的学科边界,从综合的眼光来研究女性与媒介的问题,这种打破学科障碍的观点在当时是颇具前瞻性和勇气的看法。 莱斯利·斯提夫的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了荷兰著名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学者凡·祖伦1991年《女性主义的媒介观点》中研究的基石,在1994年出版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祖伦对该观点进行了更详细的批评,该书则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一本女性主义研究体系化的专著”[9]。 祖伦认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的某些路径完全不同。而且斯提夫的这种分类所造成的问题太多,从政治策略和理论的角度进行区别反而模糊了各种理论之间和理论内部的差异。首先:各国的文化构成不同,女性主义也有多样化发展,自由主义在美国比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突出,其理论发展也不如社会主义与激进主义那样精密。同理,荷兰的激进主义与美国、英国的激进主义性质就不同。其次,经过不断发展和变迁,激进、社会主义女性的界限已经模糊,把两者进行区分并不能反映其论点多样化的特点。比如,当时的黑人女性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多元化和论点的繁杂,很难归入任何一种分类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类似的本质论与非本质类、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女性主义两分法也忽略了女性主义研究彼此交织和多元的一面[4]16-17。 (三)快速、全面发展阶段:《大众传播中的女性》三部曲 从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数字新媒体普及之前可以看做是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是女性与媒介、传播研究缓慢发展并不断成熟的阶段。这个阶段里最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要属《大众传播中的女性》继第一版(1989)、第二版(1993)之后的第三版(2007)[10]的面世。这三部同名论文集实际上代表了女性与传媒的研究的第二与第三这两个时间阶段的主要成果。 第一版《大众传播中的女性:挑战性别价值观》主要实现了编者帕米勒·柯瑞登(Pamela J.Creedon)所说的“性别转换”(gender switch)——该书目在于描述和讨论女性在大众传播就业领域的不平等,重新审视性别差异,挑战该领域的传统价值观[5]7。第一版首次把来自18位女性媒介学者的论文集合在一起,这些论文议题关于媒介法律、女性历史、有色女性、新闻教育、女性在新闻与传播业内的经济不平等以及妇女运动媒介提供的另类价值观,组成了一幅“看起来相当令人灰心”的画面[5]4。 1993年版的第二部《大众传播中的女性》收集了28位女性主义学者的论文,并增加了新的章节,这部书更新了女性在媒介各种职业地位状况的研究,也质疑了人们把性别问题继续窄化为“女人议题”的困境。但编者柯瑞登在研究后发现,“除了在大众传播领域女性主义研究领域中人数有所增加外,在实践操作上没有其他任何真正的变化”[5]5。男性依旧占据全职教授的位置,大众教育的模式依然如故。因此,柯瑞登认为第二版属于“转型变革”期。 2007年出版的第三部收集了来自24位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该书分为六个章节,中间第三、四两个章节不但更新了女性在大众传播职业领域内的现状研究、还增加了对健康传播的讨论、媒介学术中的量化研究、西欧国家以及海外女性与传播等专题;书中的第五个章节致力于为未来的研究建构一个理论基础,包含了跨文化传播的视角、语用学分析的方法以及媒介法律、女性职业领导权等早期的议题。该书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章节前后呼应,反思女性与媒介研究从过去20年以来的发展趋势。在第三版书中,编者科瑞登用“进一步、退两步”概括了20年后女性与传播媒介研究的进展;用“播放、倒带、快速前进”(play,Rewind,Fast Forward)[5]6总结了第一部——也就是早期阶段的研究,而“播放、快进、倒带”被用来总结第二部和第三部的研究。这样来看,女性主义与传播研究虽然得到了快速、全面的发展,但在女性主义研究者来看,女性在媒介和传播领域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依然充满挑战性。 二、新媒体技术时代背景下的发展与回望:十字路口 第四个阶段:在虚拟网络和各种新媒体相继问世的21世纪头十年末期至今。这段时期,女性与大众传播以及媒介等相关研究的不足和现状得到了更加深刻的批评和反思,在不断解构男权、社会性别技术歧视的同时更加注重学术建构的一面,比如:呼唤媒介改革、培养女性媒介素养和教育意识,鼓励女性生产自治媒介与文本内容,扩充公共话语空间,参与政策制定等公共议程,为女性赋权,寻找并发出更多少数群体的声音,因此第四个阶段是继续深化发展、不断自省并修正的阶段,解构的批评和建构的行动在此互相交织,女性媒介与传播发展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一)解构性批评:女人到底在哪里? 2011年,曾是《国际媒介与文化政治杂志》执行编辑的萨瑞卡科斯·凯瑟琳(Sarikaqis Katharine)教授在《妇女媒介研究》社论中反思了女性主义媒介学术现状,她认为当下的女性主义者研究的中心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即“女人到底在哪?”这个问题不仅指出了女性与媒介、传播相关的就业地位、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没有自己应有的位置之外,还指出了女性主义相关研究的困境——当代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以及行动主义经常处于“十字路口”。 萨瑞卡科斯认为,之所以这样,与女性主义本身的天性有关,因为女性主义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对世界进行“重新评估、解构和去神秘化”的过程;女性主义需要对自身所处的个人位置有大量的反思,以诚实的眼光来看待自身与周围社会、文化和政治世界的关系[11]115;也就是说,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需要高度关注女人生活中细微、深刻的变化以及保护女性权利的警觉性;然而,过多的注意媒介文本的多义性(比如大众流行文化中的偶像麦当娜、Lady Gaga等大众文化图标),过多地关注所谓的“积极受众”(女性对媒介文本的反霸权式的解读与意义生产)是不足的。这些内在性不足有三个方面:第一,人们容易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对文本或者角色的多元解读就足以创造出抵抗主流支配意识的空间以建构女性主义或者挑战结构不平等;第二,在大众主流文化中,使那些对主流大众文化表征的分析主流化,这与针对生产主流大众文化的大语境的批判性分析并不匹配。第三,存在一种把“新女性主义”归结到文本和角色分析当中去的趋势[10]116。 由此,萨瑞卡科斯指出:尽管在媒介和文化以及传播研究领域里发生了深刻久远的变革,但女性主义研究本身却缺乏团结有力的声音去批评、去要求变革。比如,在女性媒介研究中,类似批评英国媒体过于集中、反对未来数字的技术化、反对调查新闻的阻扰以及反对煽情新闻等议题,既不可见,也闻所未闻[10]117。在萨瑞卡科斯看来,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应该不只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媒介,而是要提供一种视角,除了继续开放探究的领域和建构知识的空间之外,还应该对行动主义的日常分析,对社会变革的政治诉求等提供学术证据[10]120。 2011年12月发表在《威斯敏斯特传播与文化杂志》上的编辑社论从历史的角度印证了凯瑟琳(Sarikakis Katharine)的观点。该文作者克里斯汀·斯库格(Kristin Skoog)[12]认为女性媒介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碎片化,分散的研究,缺乏整体观和连贯性;由于对大众媒介的研究实际上就源于历史学、社会学和媒介研究等学科的交叉地带。它与电影、媒介与传播、历史、媒介历史和女性历史等学科都有交集,这种学科的交叉性也意味着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方法对研究路径的影响。 斯库格认为,这种学科交叉性也意味着挑战性的一面,即女性媒介历史研究的“窄化”,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地域困境,在类似研究中,人们的研究大多来自北美和欧洲,缺乏来自其他非西方地区的国际视野;第二,在有关女性主义媒介历史的研究当中,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大众媒介而非传播上[12]1-2;斯库格发现,来自全球监测项目(GMMP,2010)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新媒体媒介内容生产,比如新闻报道以及新闻文本中,女性的声音仍然微弱,再现的机会低于男性。而来自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10周年纪念日上的报告也承认“全球数字鸿沟继续加大,媒介性别歧视呈爆炸式增长[12]1。 (二)建构性行动:好奇的女性主义 与此同时,对萨瑞卡科斯提出的女性主义者应该加强“行动主义的日常分析,对社会变革的政治诉求等提供学术证据”的号召,加拿大学者莱斯利·里根·谢厄德(Leslie Regan Shade)[13]做出了回应。她与后面提到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几位女性学者(Mary Celeste Keamey;Mary Beltran,Nhi Lieu,Madhavi Mallapragada)[14]更注重经验性的个案研究。其中,贝尔特兰(Beltrán)重点关注拉丁美洲女性在美国电影中的形象研究,而丽叶(Lieu)重点关注的是寄居美国的越南女性的媒介消费与媒介身份。马拉帕瑞咖妲(Mallapragada)则关注印度流散者在美国的数字与网络生活。当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类似关注不同国家的跨国女性主义研究成果非常多,瑞典、德国、新西兰……成果难以尽数。 谢厄德曾与萨瑞卡科斯·凯瑟琳(Sarikaqis Katharine)合作编撰过《国际传播中的女性主义干预——小心鸿沟》一书(2007),在书中她收集了有关“文化、再现、技术、劳工以及政策”等各种议题的文献,重点关注了妇女运动与媒介动员、媒介运动之间的裂变和缝隙,认为“倡导、教育和增强女性媒介意识对女性主义媒介运动在本地、国家和国际媒介文化政策中非常重要;而分解政策话语并使之渗透到社区中去也非常关键”[10]14。 2011年,谢厄德发表了名为《想要的、活蹦乱跳的:好奇的女性主义的数字政策极客们》的文章,在文中她特别推崇由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辛西娅·安罗(Cynthia H.Enloe)提出的“好奇女性主义”的说法,认为“女性主义者们应该对周围的世界抱有好奇心,除了善于发现日常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值得思考的问题之外,还应对主流媒体、甚至一些女性主义者本身容易忽视或者摈弃的问题保持敏感”[13]123。在这篇文章中,谢厄德主张:“要通过女性主义政治经济的框架来理解数字政策议题的重要性”,因为该框架不仅能发现源自于工业、国际政策制度的体制性、结构性的权力动力;能强调公民社会中由于ICTs的日常使用形塑出的性别化的社会排斥和文化赋权,还能发现文化劳工中的性别划分[13]127。 在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中,除了上面所说的从方法、认知论等理论层面的宏观分析和研究之外,对于女性媒介运动、女性对媒介的创造和使用等个案的、微观的经验研究的成果,谢厄德的个人努力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她一直研究北美青少年女性的政治经济地位,关注其在数字媒体政策参与中的结构性地位和影响,曾多次撰文讨论ICTs对女性媒介使用和生产的政治经济影响,并对媒介化与性别、女性创造网络空间等议题展开研究。 2013年,在美国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最出色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里,几位杰出的女性主义媒介学者与谢厄德一起联合审定了博士玛丽·凯勒(Jessalynn Marie Keller)的毕业论文——《仍然活着且活蹦跳的:后女性主义时代的女生博客写手及其女性主义政治》[15]。该论文延续了其导师玛丽·科尼(Mary Celeste Keamey)2006年对美国女孩生产媒介文本的研究,重构了青少年女性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行为,探讨了青少年女子博客书写对当代美国女性主义话语接入的政治意义,也丰富了指导委员会的几位女性学者的研究议题。作为好奇的女性主义,推动了女性媒介研究的新发展。 三、延续与变革:我国女性主义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发展 以上类似的经验研究,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社交网络的普及,在北美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其成果难以尽数;在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现代西方新闻与传播学术被引入中国之后,有关传播与性别的议题研究也开始快速发展并不断深入,但其发展过程与北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相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在初期阶段,首先是研究议题的广度和深度与北美、西欧等发达国家相比还不够,国内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各种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化表征;对妇女媒介内容、妇女专题的研究;以及女性在媒介领域的工作状况的描述和调查等方面;当然,还有对国外女性研究的引述,这些议题实际上关注的是媒介中性别化差异的“再现”问题。对于女性如何“发声”的途径和策略问题,也就是在社会各个领域为女性争取权利和权力方面,比如媒介监测、媒介内容生产,自治媒介,特别是媒介改革及其传播行动的系统研究还不够。 第二个阶段,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对女性主义的在线行动和媒介实践的研究在其他国家已经非常普遍,但在中国类似的研究成果还非常缺乏。在为数不多涉猎传播行动研究的几位学者中,厦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罗慧,中山大学的李艳红、暨南大学的李异平等人对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部分替代性媒体资料进行了引述、翻译和研究;其中罗慧的专著《传播公地的重建——西方另类媒体的传播民主化》(2012)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瞩目和好评:她分析了为少数群体代言的另类媒体的价值困顿以及媒介权力形态;尝试寻找另类媒体自治传播实践中传播公地如何重建的答案并倡导研究者要跳出制度崇拜的围墙;但除了指出民主传播的行动主体之外,她没能重点关注在我国已有发展的女性媒介的议题和研究。 把女性与媒介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并围绕替代性媒体的组建来主动挑战社会象征性权力,发起旨在促进社会变迁行动的,目前在国内学界能见度较高的有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卜卫研究员和她的团队[16]。卜卫借用了西方的传播行动主义与替代性媒介的理论,注意借助社会各界组织的力量,聚焦本土替代媒介及其组织的发展,为女性、儿童、劳工等弱势群体争取传播权和社会正义,也取得了令人钦佩的传播效果。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曹晋[17]、北京传媒大学的刘丽群[18]等学者关注的也是本土女性传播理论研究的建立及其传播实践的社会效果,特别是本土女性媒介或媒介组织如何提高女性的媒介素养。刘丽群等人进行的多是以政府组织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传统意义上的为女性赋权等妇女行动研究;综合研究女性媒介及其传播的理论研究已然出现,比如湖南师范大学的刘沁和李琦[19]对女性媒介生存空间的探索和研究。但严格来讲,为女性服务的女性媒介、妇女媒介组织等只能是为女性赋权的一种途径,这种研究还未能与其他NGO、或者其他草根类非女性媒介研究结成联盟,因此,其传播力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也因此,国内学界、业界特别需要有一批全面关注、专门且系统的女性媒体及其传播行动研究的成果面世,以便推动女性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公平,同时对中国当下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范式及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有所对照和创新。 四、结论与讨论 媒体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有关女性媒介的内容生产只是媒介改革活动的一部分,一般来讲,北美的媒介改革运动一般由四个相互包含的成分组成:一是“媒介批评、教育与媒介素养”;二是“创造、生产和分配独立的媒介”;三是“媒介政策行动主义”;四是“媒介正义”。围绕这四大议题,学术型的积极从业者们与媒介积极分子们一起建立了联合性的公民团体,动员并组建草根性的媒介组织。这就涉及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许多的具体问题[12]123:比如,“在这些不同的组织中,女性领导权的地位如何?哪些女性可以视作是主流媒体中媒介政策议题的发言人?这些组织的领导权有哪些种类?组织内是否有等级秩序,这些领导权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如何使媒介议题成为一个女性主义的议题?有何种有效的策略和信息?”。 以上问题,实际上都是女性为争取性别平等,为女性赋权过程中要自问自答的问题,作为一门内生型的媒介行动(media activism)研究,至少有“媒介改革”(media reform)、“媒介正义”(media justice)等三种称谓,但它们的目标和行动准则是一样的,即追求“社会变革”,认为相对于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另外的一种传播秩序”是可能的[20]11。 由于从事性别媒介研究一般都是媒介或者传播界、历史学界等学科出身的业内人士,而且大多数还是女性,因此,在追求性别平等,媒介正义或者媒介改革的过程中,如果能切实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融入,避免技术中心主义,或者“春游式”的方法;注意参与过程中的平等、动员和组织中的策略和目标,并借力于其他少数群体的声音和力量,女性主义媒介与传播研究才有更多可能找到新的方法论和认知论,以及新的研究领域。 在2010年《女性研究国际论坛》第三期中,来自美国田纳西的布鲁克·奥克利(Brooke Ackerly)和来自新西兰的亚基·特鲁(Jacqui Trure)指出:“维持行动者的根基和女性主义的实践,同时对时政保持联系;在展望将来时,女性主义研究者应该研究全球女性主义行动,研究那些看似割裂的文化和物质争斗中的全球性联系”[2]464;也就是说,女性主义研究的未来在于不断密切地跨学科研究与全球合作,确保做到“全球的语境,本土的联系”。因此,实现全盘的媒介公正和性别平等,改变女性的无名、污名化的社会面貌,虽然不易,但却是全球,特别是中国女性值得长期探索和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