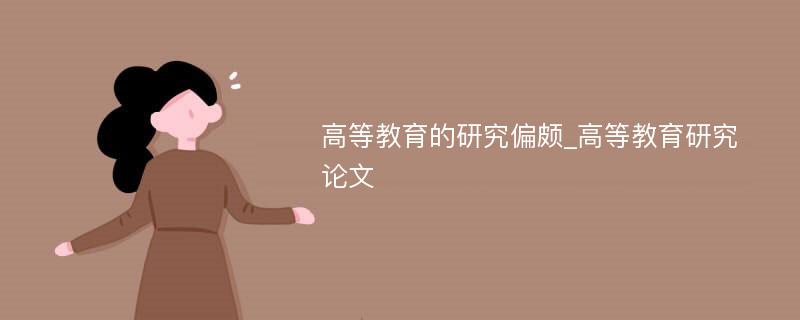
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偏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性偏向
尽管高等教育研究者们一直为建成本学科的规范体系而不懈努力,但与其他学科相比,高等教育更像一个规模宏大的研究领域,而不太刻意强调本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即通过一系列范畴运作向更深的理论层次扩展,其原因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高等教育活动,而非一种纯粹的社会意识;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范畴是高校、教师、学生、专门知识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概念,高等教育学一切原生的思想皆由此导出,并借鉴多学科的方法和概念形成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高等教育研究最初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历史上重大的教育危机,它迫使研究者们关注高等教育问题并试图提出解决的策略。而高等教育内部运行机理和外部社会联系的复杂性又使高等教育研究范围极具广泛性,几乎包含了高等教育领域内所有的现象、矛盾和问题,这又形成高等教育研究缺乏成熟学科最基本的系统性特征。直至二战后,时逢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才使高等教育研究具备了学科的雏形。但作为一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被镌刻上早期高等教育研究的印迹:偏重问题性研究。这根本上是由高等教育对象的性质所决定,只有紧扣时代突出的问题,才能展开思考和讨论,最终解决问题,形成科学理论。在这方面,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正是面对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进行概念重估,探讨所有重大问题的典范之作。
高等教育研究一旦脱离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就成了无本之木,前者依赖后者获得研究的原动力,后者限定前者的方法论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们才不去刻意构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也不亲睐华而不实的概念,形成了重实证研究,重问题考察的学科风范。
从高等教育研究群体来看,高等教育研究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是一个由多学科专家、学者组成的集合,高等教育的实践者、管理者本身就可以独立对高等教育现象、规律进行判断、归纳。这样一个队伍宏大的研究群体与以高等教育为专业的研究群体形成鲜明的参照。甚至有人惊呼最出色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通常不是由本专业的专业人员,而是由其它学科的大学教师通过把他们现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运用于高等教育研究而完成的。更多的多学科学者不断参与到高等教育研究的进程中来,使之获得了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视野,使之成为真正襄括大典、兼容百家的开放领域。
高等教育的“业余”研究者们感兴趣的是高等教育突出的现实问题,他们从来不对高等教育作系统性的评价,却擅长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形成讨论的“热点”,使高等教育研究呈现出以问题为中心的波浪进程。高等教育专业研究者们一方面要做好基础性研究,一方面又不得不对高等教育的热点讨论做出积极的回应。这两股合力造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性偏向。“问题研究始于足下”成了所有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共识。
二、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问题性偏向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它密切联系实际,能对高等教育实践的重大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它引人注目,担当起联合高等教育业余研究群体和专业研究群体的角色。这一偏向也深深影响了高等教育学研究。
尽管高等教育实践反对脱离实际的过于抽象的理论建构,但规模日益增大、运行日益复杂的高等教育系统需要结束高等教育广泛却缺乏系统性研究的局面,要求以学科的形式揭示高等教育领域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整体性规范。高等教育学研究正承担着这一特殊研究任务,它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基础理论部分和高等教育研究的高级形态。
然而,研究者们常将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研究混为一谈,并将问题性研究的偏好带进后者。问题性研究偏向使研究者们以当前紧迫问题为导向,甚至屈从于长官意志,难以进行基础性、整体性的理论探索。专业研究者将本来属于高等教育研究范围的所有问题、现象都纳入了自己视野,以至研究项目层次不高,研究成果水平不高,不能有效揭示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在进行问题研究时,又由于选题不合理,极易使某些高等教育学研究者以结论代规律,以特殊代一般,不是通过个案分析和问题研究得出普遍性规律,而是不顾时空限度稍作描述,即下结论。言谈空泛,理论于实践无补。无怪乎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成为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本来高等教育学研究并不是专业研究者的专职工作,业余研究者可进行一定程度的理论研究。然而业余研究群体易受当前热点问题的左右,热点一出现即趋之若鹜,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专业研究者正常思路,使他们也追踪热点、分散精力。
像其它学科一样,作为学科的高等教育学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虽然就学科性质而言,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但高等教育的特殊规律需要揭示,在当前教育基础学科不成熟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学还要进行一部分基础理论研究。高等教育学基础研究历时长,难度大,不以热点问题为转移,如果专业研究者们东施效颦,转移研究的兴趣和方向,势必使整个高等教育研究头重脚轻,就事论事,缺乏基础理论的支撑,永远处于经验描述水平。以热点问题研究营造的学术繁荣最终会被证明是一种“虚假繁荣”。
三、问题和理论的平衡
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迪尔凯认为一门科学进步的标志是它所研究的问题不再原封不动。问题是理论的源泉,问题的变动正是理论更新的动因。但问题不能代替理论。如果高等教育学研究仅停留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它的结论就会很快陈旧。
中国高等教育学产生伊始就采取了学科研究的形式,这是因为她生长在普通教育学的基础上,力图紧随70年代后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形势作出系统性研究,而不像西方早期高等教育研究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而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进程不断受到热点问题地推动,呈现繁荣态势。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成果成为高等教育学理论建设的直接材料来源。两者本质上并无矛盾。
举例而言,我国高等教育新问题的产生与当前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关联。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大了对教育改革的压力。人民受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强,而十年教育改革期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逐年下降。 教育资源短缺与教育需求扩张的矛盾成了当前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根本性矛盾。提高办学效益,引导教育消费,社会参与办学,重点投资211工程,高等教育成本补偿, 以产业经济方式开拓教育资源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皆源于这一根本性矛盾,从而使高等教育研究出现经济学的倾向。上述看似独立的问题都统一在教育基本矛盾之下。高等教育学研究者的任务是阐明高等教育的矛盾,探讨社会与教育的关系,为高等教育问题的思索和解决提供理论依据。
而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弊端,一是从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就匆忙推及全体(表现为太具体,忽视普适性);一是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大一统(表现为太抽象,忽视个体性)。高等教育学研究应从实验、案例、比较等方法论的角度对此予以匡正。然而,相较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热,高等教育学研究已明显冷落,高等教育史学,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哲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高等教育专业研究者的精力集中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历史和现实,高校和社会,价值和规范被割裂了,研究成果或失之迂阔或失之琐碎。公众从而有理由怀疑高等教育理论的实用可靠性。实际上原因正在于缺乏科学规范的高等教育理论。那些所谓的理论不过是从缺乏科学方法论指导的问题研究中得出的暂时性结论。
高等教育学研究必须冲破高等教育研究狭隘偏向的束缚,研究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供高等教育活动一般性的原理、原则的方法,指导高等教育活动的开展和高等教育的改革。纠正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偏向可从三方面契入。
第一,慎选研究课题,将能反映高等教育活动基本矛盾的问题归入研究范畴。高等教育科学理论不是来自于纯粹的逻辑推理,而是来自于高等教育的实践过程,实践中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开端。高等教育学的问题性研究应该注重所研究问题的相互关系。问题间的互动可能正蕴含着尚未被发觉的一般性规律和原理。
第二,形成研究群体的合理分工。高等教育专业与业余研究群体的划分只有相对意义,但进行研究时必须明确各自的职责。专业研究者不必将精力投放在具体细微的问题的实验、论证上,他们可借助于实践工作者和业余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从事科学意义上的理论体系的创建。
第三,重视高等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建设。学科群的形成是高等教育学成熟的标志。高等教育学没有自身独特的概念范畴和研究方法,它直接依赖于从分支学科中获得概念移用和方法论启示。分支学科不发展,高等教育学只会留下一个教科书的空架子。高等教育研究就不会摆脱理论水平低下的困境。专业研究者要掌握并精通其他学科,那是一笔可资利用的教育资源。
在长时期的问题研究热后,研究者也许会冷静下来进行理论反思,让问题搭台,理论唱戏,结束学科建设“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失调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