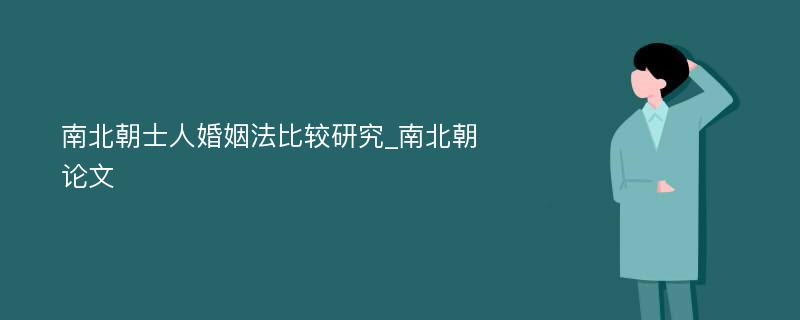
南北朝士族婚姻礼法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礼法论文,南北朝论文,婚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人所謂婚姻,原本是指結爲姻親的兩個家族。《爾雅·釋親》將全部親屬關係歸納爲宗族、母黨、妻黨三類,而宗族與母黨、妻黨的聯結則稱爲婚姻①,其實質是全部親屬關係的總和,而婚姻禮法(或習俗)則是規範親屬關係的倫理觀念和行爲準則。婚姻關係和婚姻禮法在現代學術中屬於家庭史研究的範疇,而家庭史主要是指親屬制度形成和變遷的歷史。整個中國古代文明史都與家庭制度及其倫理密切相關,歷代典籍記錄了大量有關親屬關係、婚姻禮法的事實和理論,研究這一問題是解讀中國歷史文化的關鍵,然而以往的歷史研究卻忽視了親屬制度和家庭倫理觀念的變遷。文化傳統的斷裂可能是造成現代中國歷史學者無法深入研究此類課題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尤其是文化人類學視角的缺乏,可能是又一個重要障礙②。李衡眉先生從昭穆制度入手,揭示了中國古代親屬制度的若干重要命題,是以文化人類學和歷史學相結合解讀中國古禮的傑出典範。他昭示我們,當我們從家庭史,即以婚姻爲紐帶的親屬制度和家庭倫理的角度,來重新審視史料時,我們會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豁然開朗的桃源仙境,原本看來毫無價值的記載都成了極其寶貴的家庭史史料,而所有史料都依照其自身的内部邏輯(即禮法的邏輯)焕發出奪目的光彩。研究視野的拓展和史料範圍的擴張是李先生給予史學界最大的啓示③。
進入正題之前,首先要説明關於禮的幾點基本認識:第一,禮產生於初民時代,是中國古代精神和物質文化的總名,是文字產生之前的重要文化載體。禮是上古時代習俗、禁忌、規範的遺存,是原生性極强的文化傳統,絶非階級社會的產物④。所謂“封建禮教”之説應該加以修正。第二,禮不是人們思想、行爲、知識和信仰的對立物。《史記·禮書》云:“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後人亦常云:“原夫禮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也。”⑤所以禮從來就是人性的表達,而依靠人們的觀念和行爲以傳承的。從這一意義上講,禮從不外在於人的觀念和行爲而存在,是匹夫匹婦日用而不知的傳統和規範。第三,禮是全體民衆的共同文化傳統,並非由少數社會精英所獨佔。禮產生之初就是由全體民衆共同創造、承繼和傳播的,在普通民衆之中,由於傳統的繼承性而尤顯濃厚。與之相比,社會精英往往處於多種文化的衝突和抉擇之中,處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下,他們往往是推動禮的破壞、變異或發展的主要力量。變禮的影響施加於民衆,形成新的文化傳統。可以這樣説,禮是大衆和精英共同擁有的文化傳統,而變禮纔是上層社會所獨有⑥。第四,禮不僅僅規範人們的行爲和觀念,而且也賦予關係網絡中的人們以對等的權利和義務,從不偏廢。衹是到了朱子理學成爲官方哲學之後,纔出現了將倫理義務絶對化的偏向。第五,禮往往規定了人們行爲的倫理底綫,所謂“突破禮教束縛”,很可能已經超越了倫理底綫,勢必就要遭受法律的制裁,這就是古人所説的“違禮入律”。超越倫理底綫的行爲是任何社會都不允許的,況且古代社會的倫理底綫也是源於普遍人性的,與今天並無不同。如果連基本的倫理底綫也視作對人性和自由的束縛,試問社會尚有何秩序可言?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誤解,只能是由於我們對禮的規則及其適用原則缺乏應用的瞭解。元明以後,隨著社會分化的日益發展,日常生活禮儀的融合性功能日益退化,代之而起調節社會關係的是包括國家法令和鄉規民約之類的成文法,它們雖然遵循禮的基本原則,但已不是禮的簡單再現。此時的原生性禮儀已經成爲行爲和文獻中的遺蜕,人們對其本來意義已不甚了了。其中,婚姻禮法較之國家祭祀、朝聘、盟會、册命、蒐閲等儀制,具有更明顯的原生性特徵,多爲遠古習俗的遺存,例如沿承三千餘年的昭穆制度就是古代兩合氏族婚姻制度的遺蜕⑦。這些習俗經過儒家的經典化而上昇爲禮,形成一套完整而獨特的文化體系,影響深遠。
研究古代婚姻禮法,我們需要明確婚姻禮法在家族禮法中的地位。《禮記·昏義》云:“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⑧古人重視夫婦之倫,因爲它是血緣世系與姻親關係的交點,血緣世系由此縱向展開,婚姻關係由此横向展開。“合二姓之好”,指夫婦的結合標誌著兩個家族的聯結,同時也確立丈夫對妻黨的責任和義務,妻子對夫族的責任和義務,這種婚姻關係以稱謂和服紀爲載體表達出來。“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指夫婦對於婚姻二族的祖先負有祭祀的責任,對後裔負有撫育的責任。《禮記·昏義》又云:“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按照人生歷程的順序,婚姻是家庭倫理關係的起點,甚至有時也被看做政治倫理關係,乃至一切倫理關係的起點,所以古人説婚禮是禮之始或禮之本,將婚姻禮法定位於全部禮法的核心地位⑨。古代婚姻關係重家族而輕個人⑩,故夫婦之倫的本義是以夫婦關係爲圓心的全部親屬關係(11),不是僅僅專指夫婦兩人之間的關係,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婚姻是宗族和母黨、妻黨關係的總和的定義了。由此看來,將婚姻關係及婚姻禮法作爲研究全部親屬制度和倫理觀念的關鍵所在,非常恰當。
關於南北朝時代的婚姻禮法,柳芳《氏族論》曾有精闢的論述:“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12)柳氏此語互文見意,先以江南的婚姻禮法評論山東士族,再以山東的婚姻禮法反觀江南士族,在比較中凸顯雙方婚姻關係和禮法觀念的特點及差異(13)。所謂山東士族尚婚婭,江南士族尚人物,簡單地説,是指山東士族姻親關係較密切,主要倚靠外族(包括母族、妻族)的支持,以獲取繼承權、士族身份、家族—社會地位,以及由此而來的一系列政治—經濟特權;與山東士族相比較而言,江南士族姻親關係相對疏遠,多基於個人才能贏得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14),並形成了兩種不同類型的親屬制度和家庭倫理。自魏晉以來,源於河南地區的新文化帶動了新倫理的興起和發展,永嘉以後隨晉室南遷,而河北不預此新潮流,仍舊保持漢代的文化傳統,於是南北文化出現差異(15)。南北士族具有階段性差別的婚姻禮法與其各自不同的婚姻形態、親屬制度交互作用,形成了彼此相異的特徵。柳芳不僅準確地描述了這一特徵,而且還昭示我們,婚姻關係是分析中古時代親屬制度和家庭倫理變遷史的肯綮所在。唐長孺先生曾就南北朝嫡庶身份差異問題作過精緻的研究,爲古代家庭史的研究開闢了新的路向,筆者全部構思都受益於唐先生富於原創性的傑構(16)。陳弱水關於唐代女性史和婚姻史的系列研究成果開闢了研究唐代親屬關係的新路(17)。王楠在考察唐代婚姻關係和禮法時,著重分析父權與夫權的衝突與合作中的女性地位,提出了許多新鮮的命題,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同時也構成家庭史研究的重要部分(8)。筆者試圖從南北朝親屬制度變遷和倫理觀念差異的角度對柳芳《氏族論》的觀點加以通解,探尋支配南北朝婚姻關係演變的禮法機制,以推進中古家庭史的研究。
一、宗族與母黨關係
1.南北嫡庶身份與權利的獲得與母黨的關係
關於南北嫡庶身份及所獲權利的差異,唐長孺先生論之甚詳。筆者由此深入對比分析南北母黨對於宗族後裔的嫡庶身份、家庭權利的支配之不同,特別是母親嫡庶身份對宗族男性後裔身份的權利的影響。北朝家庭中往往存在嫡妾不分的情形,而南朝家庭則嫡妾地位森嚴。母親嫡妾不分必然造成後裔嫡庶身份的天淵之別,母親嫡妾地位森嚴,其後裔嫡庶身份差異反而微乎其微。
北朝社會中常有兩妻並存的情況,如北魏陸定國有妻柳氏和盧氏(19),司馬金龍有妻源氏、沮渠氏(20),畢元賓元妻劉氏,入北之後又賜妻元氏(21),崔僧淵先娶房氏,又娶杜氏(22),李洪之元妻張氏,又娶劉氏(23),盧道虔先尚濟南長公主,後娶司馬氏,司馬氏出又娶元氏(24),北齊魏收兩妻崔氏、劉氏,比爲賈充左右夫人(25),薛琡先納於氏,再娶張氏(26),等等。這些家庭中都存在嫡妾不分、媵妾不平的問題。此外,北朝還普遍存在前妻去世而繼娶的情況,這也是造成嫡妾不分的原因之一。嫡妾不分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妻妾所生子女的嫡庶身份不確定,北朝家庭中,母黨在宗族後裔的繼承問題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兩妻都是士族的情形下,妻族的門第高低成了各自男性後代是否具有嗣子地位和士族身份的決定性因素。這以陸定國的事例最爲典型:
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争襲父爵。僕射李沖有寵於時,與度世子淵婚親相好。沖遂左右申助,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弈。安保沉廢貧賤,不免飢寒。(27)
就河東柳氏和范陽盧氏的門第而言,盧氏較高;而盧氏的姻族又是當權的隴西李沖(28),這爲盧氏的正嫡地位加上了極重的砝碼。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母黨門第對於宗族後裔身份、特權的影響力。同時,士族子弟是否或得繼承權,其家庭、社會地位具有極大的差別。如昕之承爵,從而得以尚主,職位顯赫,而其異母兄未能承龍祖爵,因而沉廢貧賤,不免飢寒,兩人的地位差別不啻天淵。當母黨爲皇族成員時,對於宗族繼承權的支配更有決定性。例如:
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悦。後娶沮渠氏,生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爲公,坐連穆泰罪失爵。延宗,父亡後數年卒。子裔,字承業。世宗時,悦等爲裔理嫡,還襲祖爵。(29)
這個事例中,沮渠氏爲公主所生,其外家爲皇室,故能依仗皇權支持徽亮爲嫡嗣(獲得繼承權),而源氏雖有太尉、隴西王的家族背景,但終究不如皇權强大,所以其所生之子只有降爲庶孽。若非徽亮坐罪失爵,恐怕源氏之後司馬裔終究難以承襲祖爵。就繼承順序而言,庶子的地位甚至還不如外孫,例如崔邪利有庶子法始,邪利亡後,其二女欺侮法始是庶子,常欲令劉文曄(崔邪利外孫)襲外祖之爵,後文華襲其父劉休賓爵,法始纔得襲父爵(30)。繼母入室也會帶來嫡庶關係的變化和重組。
北朝母黨成了辨認宗族後裔身份的標誌,有時甚至是唯一的標誌,這具有濃厚的原始遺俗的影響。當時人們談論某人時往往追究其母黨爲誰氏,謂之某某之出,如:“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王慧龍子〕寶興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31)僅就宗族内部而言,北朝士族並非如五代人所説,只須具備諸如崔、盧、李、鄭、王等高門姓氏就能自然獲得無差別的士族身份,這時母黨的門第高低、教養程度就是辨識同姓宗族後裔的標尺,母黨門第高者獲得收舉,有承嗣權利;母黨卑賤者不被收舉,行同奴僕,無承嗣權利。這裹姓氏所代表的父系宗族的權利受到了母黨權利的嚴格制約。母親代表的不僅是其個人,更重要的是作爲本家權利的延伸。
南朝社會看重人才——即個人才能,如爲庶出而有才能,亦可享有特權,姓氏是其家庭權利的直接來源(32)。江南士族所以重視個人才能,而不看母黨地位,其原因田餘慶先生從政治史的角度曾有精闢的分析:“東晉門閥政治,重門第兼重人物。當權門户如無適當人物爲代表以握權柄,其門户統治地位也就無法繼續,不得不由其他門户取而代之。王導死,琅邪王氏浸衰;庾翼死,穎川庾氏幾滅;桓温死,陳郡謝氏代興。凡此都是人物存亡影響士族門户地位昇降之例。所以當軸士族在擇定其門户的繼承人時,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專重嫡嗣,寧重長弟而不特重幼子。”(33)如果從家庭史的角度分析,筆者認爲,江南士族的身份和社會地位主要來自宗族權利的延伸,在承繼姓氏的同時也就獲得了士族身份,不必藉助母黨勢力的支持。江南士人人才凡劣則遭鄉族唾棄,而真有才能,即使母黨輕微也不妨礙獲得家族和社會的承認,如南齊的佐命大臣褚淵、王儉皆爲庶出,而學養婚宦也不遜他人。因此,輕忽母黨的事例常常見諸載籍,如:
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於諸舅禮敬多闕。重子絢,〔袁〕湛之甥也,嘗於公座陵湛,湛正色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之情。”絢有愧色(34)。
甥舅關係可以看做子與母黨關係的一個縮影,陳郡謝氏兩代輕陵舅氏,説明至少謝氏高門之中,推崇母黨的觀念是不存在的。更有甥舅反目成仇的事例,如僑姓高門謝邈慢待外甥長樂馮嗣之,馮便勾結强盜孫恩殺害謝邈;謝邈之侄謝方明手刃嗣之等人,爲之復仇(35)。
當所處地域變化時,河北分嫡庶、江南重人才的觀念衝突則更加鮮明,以下事例就體現這樣的特徵:北魏咸陽王有三子奔梁,“〔元〕翼與昌,申屠氏出。〔元〕曄,李妃所生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梁武帝蕭〕衍甚重之,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衍不許”(36),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元翼的觀念中,母黨門第是決定繼承權的重要因素,其嫡弟元曄爲隴西李輔之女所生,元曄之後纔有資格繼承其父的爵位。而梁武帝卻從江南重人才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認爲元翼的風儀氣質勝過其弟元曄,於是令元翼承襲咸陽王的封爵。
2.南北母黨對宗族社會地位的影響
北朝士族的社會地位主要依靠他們所掌握的禮法傳統,一旦失墜則難免淪爲庶族。特別是父親早逝後,母親在宗族後裔的學習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史書屢有記載(37)。早在東漢時期,就有士人母親教授經學的先例。北魏裴讓之母“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内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38)。皇甫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沈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39)。房景先“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40)。張宴之“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41)。來自母親的家庭教養是產生士庶之異的重要因素,如公孫邃和公孫叡是從兄弟,因母黨門第和母親教養不同,在家族吉凶聚會中便有士庶之別:
〔公孫〕邃、叡爲從父兄弟。叡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甥,崔氏之婿;邃母雁門李氏,地望懸隔。钜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42)
所以北朝士族得出結論,聯姻除了比量父祖之外,還要辨析母黨,舅氏(即母黨)輕微,將直接導致繼承權的喪失和士族身份的淪喪(43)。北朝家庭中嫡子能夠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從而躋身士族社會,而庶子往往失去受教育的機會,難免淪落。如邢劭嫡子大寶富於文情,其庶子大德、大道卻“略不識字”,即是顯例(44)。庶子因没有母黨的蔭庇,得不到家族成員地位的承認,所以不能出席宗族内的吉凶聚會,失去了親身參與禮儀實踐和社交的機會。如渤海高遵“賤出,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高〕允。允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吊集,朝貴咸識之。”(45)此後,高遵平步青雲,即得益於此。可見母黨的門第、教養是決定宗族後裔社會地位的要素。
北朝士族的社會—政治地位大致與三項因素密切相關,即姻援、門望、才藝(46)。我們應該注意到,雖然楊椿强調忠貞謹慎對於家族發展的作用,但實際上楊氏的姻援毫不遜於他人。雖然《誡子孫書》中還説道楊氏祖先遺訓不准後世子孫攀結勢家以獲取姻援,但實際上楊播父輩已不能遵奉(47)。這證明了姻援要素在山東士族仕途方面的重要性。太原郭逸、范陽盧玄、趙郡李順等與崔浩、隴西李沖與范陽盧淵的聯姻就是舊門與勢族結合的典型。這方面研究成果很多,茲不贅言。
江南母黨門第對宗族後裔社會地位的影響相對較小。就教養而言,王湛雖然爲妾所生,但就其人才而言,較之王氏其他成員絲毫也不遜色(48)。江南士族各有家禮、家儀、家訓、書儀,其子弟多從文本中學習禮義,從講談中磨練思維,與母黨、妻黨關係較弱,母黨門第低微仍不影響其所生子參與禮儀活動和社交活動。就仕途而言,其要素爲人才、門第和黨援三者。人才、門第與北朝無異,但黨援和姻援不同,姻緣是以婚姻關係相連結,關係穩定而單一;而黨援是因政治禮儀相影響,關係多變而複雜。北朝往往因聯姻而具有相同的政見和政治命運,南朝則純依政治利益而結合,婚姻的利益卻較少考慮。
3.南北異母兄弟的法律連帶責任
由於古代的法律是禮的延伸,古人所云違禮入律,就是以禮與律互爲表裹,用來規範人們的行爲和觀念;同時,法律的根本原則和基本標尺都來自於禮(49)。所以我們從律的角度分析南北異母兄弟的法律責任,目的是比較他們之間的禮法關係。
北魏崔鍾之異母弟崔朏從元愉叛逆,因非同母而不負法律責任,而崔朏同母兄弟崔敞則須負連帶責任(50)。雖然現在我們無法找到北魏律關於宗族從坐的規定,但從北魏的案例看來,至少從兄弟和再從兄弟(51),或者小功親以上的宗親都須從坐,總麻親的連帶責任極輕(52),這與漢代法律原則相一致。異母兄弟之間不負從坐責任,其實際親等已降爲總麻或袒免親了。應該説,從這方面看來,北朝異母兄弟之間的禮法關係是相當疏遠的。
南朝與此不同,連坐只問父系(宗族)親緣,不問母系親緣。所以宋時謝晦、謝皭爲異母兄弟(53),劉秉、劉遐亦爲異母兄弟(54),皆有法律上的連帶責任。尤其是劉秉、劉遐兄弟的一番對話,使我們對異母兄弟的法律責任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劉秉庶弟]遐人才甚凡,……秉當權,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時則云不可相關,從坐之日,爲得免不?”(55)
劉秉拒絶其異母弟的理由是擔心其弟才能不足以孚眾望,而不以異母介懷;劉遐的反問也證實了異母兄弟之間有必然的從坐責任。南朝律法以同祖兄弟爲從坐之限,只依父系親緣認定,而且只限定在同祖功親範圍之内。如朱齡石平定蜀地譙縱之亂,“所戮止縱一祖之後,〔侯〕德產事起,多所連結,乃窮加誅剪,死者甚衆”(56)。可見南朝法律一般情況下罪不及緦親,而只有特殊情形纔擴大株連的親等範圍。
二、宗族與妻黨的關係
1.南北宗族與妻黨關係的特點
北朝所謂“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正是稱譽盧度世、高允等人拯濟姻親、推先外族的行爲。史載:“無鹽房崇吉母傅氏,〔盧〕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恭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57)又曰:“〔北魏〕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之中,多〔高〕允婚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才任能,無宜屈抑。”(58)筆者認爲,形成這種社會風尚的原因是妻黨對於宗族保持勢族身份和權利具有重要作用,上至皇室,下至士庶,無一例外。如北魏孝文帝爲諸弟娉妃,其詔令曰:“至於諸王娉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逑。自茲以後,皆人乏窈窕,族非百兩,擬匹卑濫,舅氏輕微,違典滯俗,深用爲歎。”故皆娶郡姓和虜姓高門之女爲正室,先前所納,降爲媵妾,唯此纔能保持皇室家族的社會地位不致失墜。北魏孝文以後諸帝諳稔此中之道,所以當高陽王元妃盧氏去世之後,欲納博陵崔顯妹爲妃,宣武帝猶以爲“地寒望劣”,考慮很長時間纔同意這門婚事(59)。博陵崔氏尚且如此,其他門第低微的家族就更難以成爲皇室姻親了。如果所娶並非高門,則須假託高門、偽造譜系,以保證其婚姻的合禮與合法,同時也爲其婚生子嗣獲得家族承認提供了基礎(60)。如果身爲庶出,爲了保證自己小宗的地位就更需要和强宗大族聯姻,薛懷吉的行爲具有代表性(61):〔薛懷吉〕自以支庶,餌誘勝己,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
在仕進方面,妻黨的作用更是絶不可小覷的,連皇子也要依靠妻黨謀求進身之階:元英之子元熙,“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時于忠執政,熙,忠之女婿也,故歲中驟遷”(62)。這體現了文武才藝之外,姻援是不可或缺的仕進要素。因此,身居選官要職者總是營婚不暇,《北史》卷四七《袁聿修傳》載:
〔北齊〕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元〕聿脩常非笑之,語人曰:“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聯姻勢家以攀結姻緣,被視爲“榮利之事”。史稱王翊“鋭於榮利,結婚於〔權臣〕元叉”(63)。更有甚者巧宦鑽營,至於專以姊妹兒女謀取官位。如劉芳之子劉逖:
其姊爲任氏婦,没入宫,敕以賜魏收,收所提攜,〔劉逖〕後爲開府參軍。……盧士游,性深密,逖求以爲〔聘陳使〕副。又逖姊魏家者,收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遊,不許。逖恐事露,亦不逼焉。初,逖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逖乃爲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逖謀,逖乃告二人,故二人得之爲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64)
劉逖利用妻黨爲宗族牟利可謂出神入化、左右逢源了,從中我們也可以體會到妻黨對宗族仕途影響之巨。魏收更直接地指出,其姑父王椿能夠“名位始終”,主要是得力於王椿之妻鉅鹿魏氏(魏收之姑)(65)。而宗族之内,妻黨門第高下就成了兄弟競争權利的籌碼,故唐人稱之爲“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66)。山東士族有時爲了娶高門之女,竟然至於争鬥:
〔李〕神儁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儁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致紛競,二家鬩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儁惆悵不已,時人謂神儁鳳德之衰。(67)
北朝婚姻之家往往榮辱與共,北魏崔浩被殺,其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趙郡李氏、河東柳氏等皆遭株連。
與北朝風尚相反,南朝不藉妻黨維繫宗族的社會—政治地位。如:
齊高帝輔政,〔吴郡陸慧曉〕除爲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愈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賀邪?”(68)
陸氏解嘲之語淵源有自,東晉南朝以來,高門大族爲官皆曆清顯,不作尚書郎之類的濁官,祇有門孤援寡者纔膺此選(69)。且高門入仕極早,有些三十以前就已擔當方面大員了,如謝晦(70),而琅邪王融,自恃人才門第兼備,年未三十便望宰相(71)。雖然岳父身任吏部選官之職,但陸慧曉年愈三十方爲尚書郎,可見妻黨對於宗族的仕途並無助益。東晉以來,就有類似的傳統,掌握官僚仕途的吏部官員對於姻親尤其避嫌。如《晉書·華表傳附子廙傳》云:“庚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72)有時,婚姻關係惡化時,妻黨甚至成爲仕途的障礙。例如,何尚之與姻親劉湛交惡,“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爲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意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73)江南風氣,以入妻黨之門爲耻。如琅邪王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時爲荆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聚集耳,我不能爲桓氏贅婿。’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74)
江南姻親往往不因婚姻關係而具有相同的政治傾向,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更多是爲宗族利益考慮,而不考慮姻族權益,樂廣一句“不以五男易一女”,成了南朝士族處理此類問題的基本原則而屢加引用。例如宋時沈攸之攻叛將柳世隆把守的郢城,“夜遇風雨,米船沉没,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幼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急要,而卿不以在意,將由與城内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歡然意許。”(75)看來崔靈鳳並没有柳世隆之叛而受牽連,而且還參與了平叛戰役;柳世隆之叛也没有與姻親崔氏商議,這已經表明了婚姻雙方的態度。所以當沈攸之對崔靈鳳略有懷疑時,崔靈鳳衹消引用樂廣的一句話就自然地化解了危機。東晉末榮陽鄭鮮之不附外甥劉毅而盡心劉裕(76);王敬則之婿謝朓則告發岳父謀反,致使敬則被殺等等(77),都是此類事例。更有甚者,以犧牲姻族的利益爲宗族牟利。如褚秀之兄弟,爲了博得宋高祖劉裕的歡心,不惜殺害妹婿和外甥:
〔褚〕秀之妹,〔晉〕恭帝后也,雖晉室姻戚,而盡心於高祖。……秀之弟淡之,……淡之兄弟並盡忠事高祖,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後非一。……高祖將殺之(晉恭帝),不欲遣人入内,令淡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牆而入,進藥於恭帝。(78)
同時,南朝士大夫亦不因婚姻關係斷絶而交惡,如江湛娶褚秀之女,後被遣回本家,秀之子褚淵爲衛將軍,仍用湛孫江斆爲長史(79)。江南家庭結構較爲簡單,多爲功親同居,總麻以下親則相對疏遠,中表姻親更有互不相識者(80)。總之,江南婚姻關係淡漠是一種普遍的常態。
2.山東再娶之風的本質:娶母之黨
中國古代諸侯有所謂“一娶九女”,“諸侯不内娶”,“諸侯不再娶”等等禮法,然而僅限於諸侯階層,而士大夫則不適用這樣的婚姻禮法。其基本典據見於如下諸書。
《公羊傳·莊公十九年》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徐彥疏:必以侄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81)
《白虎通義》云:“適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於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於適。《經》不譏也。或曰,適死不復更立,明適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82)
《白虎通義》卷一○《嫁娶》“論同姓外屬不娶”條云:“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耻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於吴,爲同姓,謂之吴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以《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陳立原注:所引《春秋傳》,今三傳皆無此語,蓋《公羊家》嚴、顏二氏莊公二十三年‘公至自齊’説也。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云:‘内逆女,例月,莊二十三年公如齊逆女,成十四年僑如逆女,皆不月,容即以娶母黨失正,故略之與?律禁姑之子、舅之子爲昏姻,實《春秋》之義也。’)”(83)
禁忌也是風俗的反映,之所以有這樣的禁忌,是因爲有倫理問題存在。後起的禮法,非原生性禮法。中國古代歷史上,重視婚姻禮法是普遍現象,而魏晉北朝時代的山東河北地區的士族尤有甚者,再娶風俗盛行,就是一個特例。
再娶風俗是指士族男子如果未娶正室或喪妻則必須再娶,否則必爲社會輿論所譴責。例如李象“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84),又如夏侯“道遷不娉正室,唯有庶子數人”(85)。以致顏之推作《顏氏家訓》,專列“後娶”一篇,論述由再娶風俗引發的種種家庭問題。北朝歷代王朝都十分重視士大夫的婚姻倫常,北魏文明太后和孝文帝屢次發佈詔書,令嫁娶失時者以禮會之;南朝士人北來者,亦爲之賜婚,以正婚俗。孝文帝和宣武帝非常重視由家族禮法引伸出來的政治倫理,寓君臣之道於夫婦之禮。
再娶是爲了繼續保持與原來妻黨的婚姻關係,否則後嫡立前嫡廢,與前妻之黨的關係就斷絶了。崔浩與太原郭氏的婚姻能體現此類觀念對於婚姻選擇的意義:
〔崔〕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婿。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氏固執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86)
我們可以推斷出,一旦妻子去世,宗族與妻黨的關係也就疏遠、中斷了,婚姻之家也不再爲親。這遵循了禮法中“外親無二統”的原則。所謂再娶,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妻亡續娶,而是指娶母黨、妻黨之同姓,所以河北士族中常有所謂婚媾重疊的現象。例如太原郭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等,唐代盧氏墓誌仍以外族爲高門而自豪:“夫人范陽人也,其先有若北中郎將植,以經術重東漢,固安公度世,以才業翊元魏。自〔盧〕固安至夫人十一代,皆出於崔、李、鄭三族。”(87)對於以上倫理觀念有所認識之後,我們就可以通解許多北朝隋唐時代婚姻史、士族史上的疑難問題。例如唐代禁婚問題,以往僅從士族史的角度加以解釋,結果總是未達一間,如從家庭史的角度理解,則可以有所突破。北朝以來的士族只有娶高門之女纔能保持宗族的士族地位和後世的身份及權利。北周武帝統一北方之後,全面推行非門閥化政策,力圖解消山東士族的特權,壓制其社會地位,當務之急就是解消他們利用聯姻關係建立的網路。所以北周武帝即位伊始就頒佈了禁婚令,其實質内容就是禁止山東士族娶母之同姓,藉助母黨建立宗族的社會地位的行爲(88)。唐代多次發佈的禁婚令,就其實質而言,不過是武帝禁婚令的重申,其用意與武帝別無二致(89)。同時,我們也可以明瞭,正是北魏時代開始,婚媾重疊、娶母同姓成了士族共同風尚,於是唐代朝廷和民間都將禁婚嫁的源頭追溯到北魏時代的七姓十家七十子(90)。
正如前文所論,江南士族不依仗母黨、妻黨獲取家庭、社會地位,而且與北朝不同,母親、妻子去世之後,他們仍能與母黨、妻黨保持親屬關係,所以没有再娶的必要。顏之推云,江南士族妻死不再娶,而以媵妾持家,雖免不了所有齟齬,但限於妻妾身份的明晰界限,不會演出山東士族那樣的種種家庭悲劇。
楊樹達先生《漢代婚喪禮俗考》專闢《重親》一章,以研究重婚現象,重婚與再娶密不可分。與唯一的姻親家族保持婚姻關係是重點。
三、婚姻禮法的南北差異
一般説來,南北朝時代,南方妻妾地位分明,嫡子庶子差異小,結爲婚姻的兩家關係相對疏遠,即使妻子去世,夫與妻黨、子與母黨仍然保持婚姻關系,子女主要以父系血緣計,而不依生母的門第、身份定其高下,故嫡母與庶子、庶母與嫡子及異母兄弟之間關係相對融洽。北方家庭妻妾地位不穩定,嫡子和庶子有天淵之別,結爲婚姻的兩家關係十分密切,而一旦作爲婚姻紐帶的女性被出或去世,則婚姻關係也即告終結,故結爲婚姻的兩家爲保持婚姻關係常常採取多重聯姻的方式,於是形成了姻親不失其舊的風俗,子女在宗族中的地位主要依靠母黨、妻黨的門第來決定,母系血緣有時會成爲辨別子女身份高低的唯一標誌,所以異母兄弟之間的關係普遍緊張,在父親身後常常就宗族身份和繼承權問題發生訴訟,繼母壓制、虐待、迫害前妻之子的情形十分常見。南方家庭倫理具有新趨向,北方家庭倫理保存了原始社會的遺俗。以下從妻子嫡庶身份、嫡庶母子關係、異母兄弟關係等方面加以分疏,我們可以對以上結論進行驗證。
1.嫡庶關係的南北差異
一夫多妻制下,母親嫡庶地位的不確定性,是造成家庭内部紛争的重要原因。繼母入室造成親屬關係的重組:
〔畢〕元賓入國,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91)
這是國家法律直接干涉家庭親屬制度的例子,將畢元賓妻妾的地位完全顛倒過來,前妻劉氏所生之子祖朽兄弟變爲庶子,失去了繼承權;而祖暉兄弟卻昇爲嫡子,擁有繼承權。又如楊大眼之例:
〔楊〕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甑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深以爲恨。(92)
楊大眼元妻潘氏被殺之後,正妻的地位隨之喪失,其所生子甑生等人的身份立即降爲庶子,而繼妻元氏上昇爲嫡妻,其所生子也就是理所當然的嫡子了。這樣的變化極易引發妻妾之間、嫡母與庶子、庶母與嫡子之間,以及異母兄弟之間的矛盾和紛争。夫妻合葬也是區分嫡妻庶妻的重要方式,禮曰:“夫婦合葬皆爲妻”,能否争得與丈夫合葬,幾乎與能否成爲嫡妻同義(93)。因此而起的家庭糾紛爲數不少,如:
〔北魏傅〕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遂買左右地數頃,遣敕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馮先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氏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94)
某些人爲避免家庭糾紛而拒絶夫妻合葬,如北魏崔光韶臨終遺言曰:“吾運既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95)魏子健也有同樣的遺囑(96)。
南朝對於母親的嫡庶身份地位有十分清晰的區分,粱武帝曾有一篇論慈母含義的文章,足見江南風俗是以親屬稱謂來確定親屬關係,從而標識其身份地位的。其略云:“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97)對於慈母,江南禮法尚分爲三等,對於嫡庶大限,當然就有更加嚴密的區分。這樣就從禮法上杜絶了可能發生的所有嫡妾不分,子女嫡庶不明的情形,庶妻和庶子都安於自己的身份。由於江南士族不存在收舉與否及歧視庶孽的問題,庶子的身份並不影響他們的家庭、社會地位和未來的人生發展。於是類似北朝類型的家庭糾紛,江南絶少發生。正如顏之推所云:“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蝱,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鬬鬩之恥。”(98)
2.母子關係的南北差異
顏之推身經南北,對於當時家庭倫理的弊端有十分深刻的認識,對於河北後妻虐待前妻之子的現象,他不是僅從人性的角度分析,而是從婚姻關係的情理中加以探求,爲我們解決問題提供了明確的啓示: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妒之情,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争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爲防焉,故虐之。(99)
嫡妻對於庶妻和庶子的歧視是一致的,嫡妻防備庶妻超越自己的地位而變爲嫡妻,同時也嫉妒庶子的學業、婚宦超越己子,故壓制庶子和庶子的行爲其目的相同。《語林》云:
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賓客滿座,猶令秀母親下食與眾賓,賓見,並起拜之。(100)《晉書·裴秀傳》記此事稍詳:
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101)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裴秀嫡母既無禮於裴秀所生母,同時也嫉妒裴秀的聲名,故以令秀所生母爲賓客進食的方式來羞辱裴秀母子。實際上嫡母與嫡兄弟姊妹在對待庶母和庶兄弟姊妹上的態度也是一致的。《魏書·崔玄伯附道固傳》云:
道固賤出,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其父崔〕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興人門户,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略無兄弟之禮。時劉義隆子駿爲徐兗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爲從事。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駿以爲從事。道固美形容,善舉止,便弓馬,好武事,駿稍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駿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爲歎息。”青州刺史至州,辟爲主簿,轉治中,後爲義隆諸子參軍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弟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102)
這兩個事例雖然略有不同,但是足以證明,嫡庶之間關係的緊張,與家庭結構和婚姻禮法有關,凡是漢式(或曰北方)婚姻禮法支配的家庭,總會產生同樣的問題。以下事例則較爲極端:
〔李〕孝伯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遇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安民襲爵壽光侯。(103)
這是個後妻虐害前妻之子的事例。這裹需要解釋的是李孝伯爲什麼不以再娶的翟氏爲妻,而翟氏爲什麼因此忌恨李孝伯前妻之子李元顯?由於李孝伯前妻是崔賾之女,其子元顯因此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頗有才智。李孝伯欲以元顯爲嫡嗣,這樣就不能將再娶之翟氏當做正妻,只能作爲妾,否則本諸後嫡立前嫡的禮法原則,元顯必然失去其繼承權。也正是因此翟氏纔忌恨李元顯,他的存在不僅妨礙翟氏取得正室的地位,也妨礙了翟所生之子獲得宗族的承認(收舉)。元顯之死,無論是否翟氏所爲,總之翟氏和其子安民是最大的受益者,這一定程度上坐實了時人對於翟氏的猜疑,至少這種猜疑是合乎情理的。這與顏之推所説的“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104),亦若合符節。
江南嫡母和庶子的權利衝突較少,所以關係相對融洽,例如:
〔褚〕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吴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爲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
〔南齊劉靈哲之〕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焕,泰始中(465-471年)没虜,靈哲爲布衣,不聽樂。及〔父〕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虜中,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私贖嫡母及景焕,累不能得。世祖哀之,令北使告虜主,虜主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
以上吴郡公主以庶子褚淵承嫡(105),劉靈哲讓爵於嫡兄(106),王儉誓死保衛嫡母之墓(107),都是此類表現。又《南齊書》卷三六《劉祥傳》曰:“〔永明〕九年(491),〔劉祥〕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不相料理,楊死不殯葬,……爲有司所奏。”(108)説明異母兄弟有必須贍養庶母的義務,如果不履行義務,就觸犯了國家法律,有司就有權過問、糾彈了。
同時,庶子的權利也能得到父親和繼母的保障。首先是生存的權利,漢代繼母可以像殺死奴婢一樣殺死庶子,而不負任何法律責任。而東晉南朝以後,法律不再允許繼母隨意殺死庶子,《三十國春秋》曰:“晉安帝時(397-418),郭逸妻以大竹杖打逸前妻之子,子死,妻因棄市,如常刑。”(109)其次是婚宦權利,梁朝到溉、到洽兄弟生母魏氏寒微,然皆以才學知名,可見庶子也有受教育的權利。由於南朝庶子不被嫡母歧視,而且可以藉助嫡母黨的家世背景尋求發展,故其父到坦還求娶羊玄保之女,以泰山羊氏爲到溉、到洽的外家。到溉、到洽所生母魏氏也用本家貲產幫助他們結交當時名士任昉,使兄弟增長才學,爲他們博取聲譽(110),後到氏兄弟皆因此而步入清流(111)。這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發現,當繼母與庶子關係融洽時,父子關係同樣也是正向的,兩者一致。
3.兄弟關係的南北差異
柳芳曰:“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所謂後本宗,乃是尚婚姬之必然表現,主要是指異母兄弟之間的衝突,與賤庶孽關係也十分密切。本宗叔侄或兄弟因各自生母不同,父兄死後往往就嫡庶身份和繼承權問題互相争執,同姓相殘之事時有發生。如盧度世遭崔浩之難,其異母兄弟常欲陷之死地(112)。顏之推指出,北朝家庭異母兄弟爲了争奪繼承權,往往“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跡,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己直者,往往而有”(113)。此類事件,當時稱爲訟嫡或理嫡:
崔僧淵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虯。僧深得還之後,絶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驎、伯驥與母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祖龍剛躁,與兄伯驎訟嫡,並以刀劍自衛,若怨讎焉。(114)
又如:
〔薛〕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愛。興和(539-542)中,遂致訟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耻焉。(115)
北朝訟嫡之事還有司馬夏侯道遷之子夬與昚,可見異母兄弟的繼承衝突是普遍存在的,只有個別異母兄弟利益共用的家庭纔能和睦相處。如“〔李〕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鬩。及沖之貴,封禄恩賜皆以供之,内外輯睦”(116)。其實李沖爲了平息異母兄弟之間的紛争,付出了不小代價,史稱李沖“顯貴門族,務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爵官,一家歲禄,萬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117)。如此行爲,可謂矯枉過正。
異母兄弟相互友愛的故事以西晉王祥、王覽兄弟最爲著名,江南承繼西晉洛陽附近興起的新文化、新倫理,異母兄弟友於之事代不絶書。如謝皭生母郭氏“爲病畏驚,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皭至性,咸納屨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118)。一家尊卑應包括謝皭的異母兄弟,如謝晦、謝瞻等,如無友於之情,如何能“納屨而行,屏氣而語”十餘年呢?又如:“〔沈〕雍之與攸之異生,諸弟中最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儉吝,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取,輒取齋中服飾,分與親舊,以此爲常。”(119)
南朝異母兄弟友于之情甚篤,讓嫡之事亦非鮮見。正如顏之推所分析的那樣,北朝家庭中庶子不被收舉,則淪爲傭僕,毫無地位可言;而南朝家庭嫡庶身份確定,兩者關係反而比較融洽。
總結
南北地域家庭結構不同,而其中相同的角色就具有不同的地位和權利。南北地域文化在家庭禮法方面的差異可以總結成以下幾點:南方家庭規模小,結構簡單,妻、妾地位分明,嫡子、庶子地位差異小,結成婚姻的兩家關係相對疏遠,即使正妻去世,兩家仍然保持姻親關係。子女主要以父系血緣爲準,而不依生母的地位、門户定高下,故嫡母與庶子、庶母(妾)與嫡子、嫡庶(異母)兄弟之間關係相對平和,有法律上的連帶關係。北方與此不同,家庭規模較大,多爲大家族同居共財,甚至包括姻親外族(母族、妻族及其姻親),家庭構成複雜,妻、妾(或者前母、繼母)地位不穩定,嫡庶差異大,結成婚姻的兩家關係極爲緊密,而一旦作爲婚姻紐帶的女性去世或被出,則姻親關係就此斷絶,故結成婚姻的兩家爲保持婚姻關係,往往采取多重聯姻的形式(即婚媾重迭),形成了婚姻不失其舊的風俗(或曰再娶風俗),子嗣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主要依靠母族、妻族的門户來決定,甚至其母族成了身份的唯一標誌(在父系同爲士族的情況下),所以異母兄弟在父親身後常就身份和繼承權問題發生訴訟,而繼母虐待、迫害、壓制前妻之子的情形也十分普遍。在這種差別之下,南方士族多依靠“人才”(即個人才能)建功立業,而北方士族多以“姻援”(即强有力的婚姻關係)作爲仕途通達不可或缺的條件。
南北朝婚姻關係和倫理觀念的差異不僅是南北地域的差異,而且是時代的差異。中國古代社會前期,婚姻關係是家庭人倫關係中最重要的一倫,它是全部親屬制度和倫理關係的核心。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前期的家庭史,婚姻禮法正是肯綮所在。魏晉時期正值漢民族的親屬制度和家庭倫理變化成長的時期,而北方少數民族的南下,南北政治地域的分裂,促進了以婚姻關係爲核心的新型家庭倫理的演生和發展。江南的親屬制度和家庭倫理代表了新的發展趨向,而河北地區則保持相對陳舊的親屬制度和家庭倫理,新趨向較之舊形態而言,逐漸顯示出優越性。它適應中古社會生活的變遷,具有更强的調節能力和更多的寬容度,對於後世也有重要的影響。
注释:
①《爾雅注疏》卷四《釋親》曰:又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1592-1593頁)本文所用宗族、母黨、妻黨、婚姻四詞,皆以《爾雅·釋親》的意義爲準。
②近年來家庭史的研究有所進展,但如何運用文化人類學的視角來研究中國古代傳統的婚姻禮法,對於我們來説還是個重大的難題。
③李衡眉《昭穆制度研究》,齊魯書社,1994年。
④鄒昌林《中國古禮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
⑤《宋書》卷五五《傅隆傳》,中華書局,1974年,1551頁。
⑥以上觀點得益於郝師春文的教導。又參彼得·柏克著《歐洲近代早期的大衆文化》,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⑦李衡眉《昭穆制度研究》,67-88頁。
⑧《禮記正義》卷六一《昏義》,《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1680頁。
⑨正如我們所瞭解的,漢民族最初的產生、發展,是以氏族聯姻方式進行的,例如古老的周族是由姬姓和姜姓的聯姻而構成的兩合氏族。明乎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古人何以再三强調婚姻倫常在家族禮法中的核心地位了——這是我們民族對於自身歷史的集體記憶的遺存。
⑩吕思勉《中國制度史·婚姻》,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326頁。
(11)潘光旦《倫有二義》,原載天津《益世報·社會研究》1948年2月26日,此據潘乃谷、潘乃和選編《潘光旦選集》Ⅰ,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354-364頁。以上觀點鄧小南教授曾在“唐宋婦女史研究”課上有精闢的闡述,筆者受益匪淺,謹誌謝忱。
(12)《新唐書》卷一八九下《儒林·柳沖傳》,中華書局,1975年,5678-5679頁。
(13)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中華書局,1993年,34-37頁。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刊正氏族詔》也從不同側面説明了南北士族姻親關係及婚姻禮法觀念的基本特徵和差異,可以參見。
(14)以上觀點並不代表一種絶對化的傾向,即北方士族完全排除了個人才能,或南方士族完全排除了姻親關係之外的所有方式以取得社會地位和特權,相反地,需要强調的是,整個中古時代的士族普遍以婚、宦二途與庶族相區別,並進而獲得地位與特權,這是中古社會的主要特徵,也是我們理解這一時期士族禮法的基點。
(15)唐長孺《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55年,351-381頁。
(16)唐長孺《讀〈顏氏家訓·後娶篇〉論南北嫡庶身份的差異》,《歷史研究》1994年第1期,58-65頁。
(17)陳弱水《試探唐代婦女與本家的關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1分,1997年,167-248頁;《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與夫妻關係——從景雲二年〈楊府君夫人韋氏墓誌銘〉談起》,《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3期,173-202頁;以上成果結集爲《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18)王楠《唐代女性在家族中地位的變遷——對父權到夫權轉變的考察》,《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3卷,中華書局,2001年,135-167頁。
(19)《魏書》卷四○《陸俟附昕之傳》,中華書局,1974年,909頁。
(20)《魏書》卷三七《司馬楚之附金龍傳》,857頁。
(21)《魏書》卷六一《畢衆敬附元賓傳》,1361頁。
(22)《魏書》卷二四《崔玄伯附僧淵傳》,633頁;
(23)《魏書》卷八九《酷吏·李洪之傳》,1919頁。
(24)《魏書》卷四七《盧玄附道虔傳》,1051-1052頁。
(25)《北齊書》卷三七《魏收傳》,中華書局,1972年,490頁。
(26)《北齊書》卷二六《薛琡傳》,371頁。
(27)《魏書》卷四○《陸俟附昕之傳》,909頁。
(28)盧淵和李沖的婚姻關係見《魏書》卷四七《盧玄附淵傳》,1050頁。
(29)《魏書》卷三七《司馬金龍傳》,857頁。
(30)《魏書》卷二四《崔玄伯附邪利傳》,628頁;同書卷四三《劉休賓傳》,964-969頁。《南齊書》卷五五《孝義·崔懷慎傳》,中華書局,1972年,956頁。
(31)《魏書》卷三八《王慧龍附子寶興傳》,877頁。
(32)參唐長孺先生《讀〈顏氏家訓·後娶篇〉論南北嫡庶身份的差異》。
(33)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261頁。
(34)《宋書》卷五二《袁湛傳》,1498頁。又《晉書》卷四九《謝安附絢傳》,2088頁。江南舅甥之間往往因小事而發生齟齬,如《南齊書》卷四二《江祏傳》所載,劉暄和外甥蕭寶玄因生活瑣事而失和,以至於劉暄反對立外甥蕭寶玄爲帝(751頁)。
(35)《宋書》卷五三《謝方明傳》,1522頁。
(36)《魏書》卷二一《咸陽王禧傳》,540頁。
(37)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第十一章《寡母教孤》,中華書局,2002年,266-278頁。
(38)《北史》卷三八《裴佗附子讓之傳》,1384頁。
(39)《北史》卷三八《裴佗附皇甫和傳》,1394頁。
(40)《魏書》卷三九《房法壽附景先傳》,1423頁。
(41)《北史》卷四三《張彞附晏之傳》,1578頁。
(42)《北史》卷二七《公孫表傳》,976頁。公孫叡之母爲渤海封愷之從女,其妻黨爲清河崔浩。
(43)《魏書》卷二一《咸陽王傳》,534-535頁。這令我們對於公孫表爲子强娶封愷從女的性質有了深入的認識。
(44)《北史》卷四三《邢巒附邢劭傳》,1593頁。
(45)《魏書》卷八九《酷吏·高遵傳》,1920頁。
(46)北魏楊椿誡子孫書提及了這三項要素,見《魏書》卷五八《楊播傳附椿傳》,1290頁。
(47)楊播之母王氏是文明太后之姑,楊津之妻爲漢化甚深的虜姓源氏。見《北史》卷四一《楊津傳》,1500頁。
(48)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説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428-429頁。
(49)參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中華書局,1998年,48-64頁;又《唐代法制研究》,文津出版社,1999年,77-119頁。
(50)《魏書》卷二四《崔玄伯附鍾傳》,626頁。
(51)從兄弟的連坐責任見《魏書》卷四一《劉休賓附文曄傳》,966頁;再從兄弟的連坐責任見《魏書》卷二四《崔玄伯附邪利傳》,628頁。
(52)《魏書》卷五六《鄭羲傳》,1239頁。
(53)《宋書》卷四四《謝晦傳》,1350,1361頁。
(54)《宋書》卷五一《宗室傳》,1469-1470頁。
(55)同上。
(56)《宋書》卷四八《朱齡石傳》,1424頁。
(57)《魏書》卷四七《盧度世傳》,1062頁。
(58)《魏書》卷四八《高允傳》,1089頁。
(59)《北史》卷一九《獻文六王傳》,700頁。
(60)《魏書》卷二二《京兆王愉傳》,589-590頁。參拙稿《鮮卑婚俗與北朝漢族婚姻禮法的交互影響》,未刊。
(61)《魏書》卷六一《薛安都附懷吉傳》,1358頁。
(62)《北史》卷一八《景穆十二王傳》,670頁。
(63)《魏書》卷六三《王肅附翊傳》,1413頁。又崔光韶《戒子孫書》云:“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北史》卷四四《崔亮附光韶傳》,1638頁)
(64)《北史》卷四二《劉芳附逖傳》,1552-1553頁。
(65)《北史》卷九二《恩幸·王叡附椿傳》,3021頁。
(66)《資治通鑑》卷一九五《唐紀》“太宗貞觀十二年”,中華書局,1960年,6135頁。
(67)《魏書》卷三九《李寶附神儁傳》,897頁。
(68)《南齊書》卷四六《陸慧曉傳》,805頁。
(69)《宋書》卷五九《江智淵傳》曰:“〔濟陽江智淵〕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不爲台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悦,固辭不拜。”(1609頁)
(70)《宋書》卷四四《謝晦傳》,1361頁。
(71)《南齊書》卷四七《王融傳》,822頁。
(72)《晉書》卷四四《華表附傳》,1260頁。
(73)《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1734頁。
(74)《宋書》卷六六《王敬弘傳》,1729頁。
(75)《宋書》卷七四《沈攸之傳》,1941頁。
(76)《宋書》卷六四《鄭鮮之傳》,1695-1696頁。
(77)《南齊書》卷四七《謝朓傳》,826頁。
(78)《宋書》卷五二《褚叔度傳》,1502-1503頁。
(79)《南齊書》卷四三《江斆傳》,757頁。
(80)《宋書》卷五八《謝弘微傳》曰:“年十歲出繼,所繼父于弘微本緦麻親,親戚中表,素不相識。”1590頁。
(81)《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七,《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2235頁。
(82)班固著、陳立疏證《白虎通義疏證》卷一○《嫁娶》,中華書局,1994年,483頁。
(83)同上書,477-478頁。
(84)《北史》卷四五《李叔彪附象傳》,1676頁。
(85)《北史》卷四五《夏侯道遷傳》,1655頁。
(86)《北史》卷二一《崔宏附子浩傳》,789頁。又參《北史》卷四三《郭祚傳》,1569頁。
(87)《唐故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孫府軍故夫人范陽郡盧氏墓誌銘並序》,《北京圖書館藏歷代石刻拓本彙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29册,6頁。
(88)不娶母之同姓實即同姓不婚的本義,參吕思勉《中國制度史·婚姻》,360頁。
(89)參拙稿《北周、隋、唐初的士族政策與政治秩序》,《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3期,43-49頁。
(90)關於山東婚姻禮法與士族興衰之間的關係,請參拙稿《唐代婚姻禮法的特點與源流》(未刊)。
(91)《魏書》卷六一《畢衆敬附子元賓傳》,1361頁。
(92)《魏書》卷七三《楊大眼傳》曰:“〔大眼〕有三子,長甑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1636頁。
(93)類似事件西晉時代也曾出現過,參見《世説新語箋疏》(修訂本),684頁。
(94)《北史》卷四五《傅永傳》,1669-1670頁。
(95)《北史》卷四四《崔亮附光韶傳》,1638頁。
(96)《魏書》卷一○四《自序》,2323頁。
(97)《梁書》卷四八《儒林·司馬筠傳》,中華書局,1973年,676頁。
(98)《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34頁。
(99)同上書,37頁。
(100)《藝文類聚》卷三五《人部》“婢”,635頁。
(101)《晉書》卷三五《裴秀傳》,1037-1038頁。《晉書》卷三三《王覽傳》云:“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鴆之。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争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致覽斃,遂止。”(990頁)也是同類的事例。
(102)《魏書》卷二四《崔玄伯附道固傳》,629-630頁。
(103)《魏書》卷五三《李孝伯傳》,1173-1174頁。
(104)《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34頁。
(105)《宋書》卷五二《褚叔度附湛之傳》,1506頁;《南齊書》卷二三《褚澄傳》,432頁。
(106)《南齊書》卷二七《劉懷珍附靈哲傳》,504頁。
(107)《南齊書》卷二三《王儉傳》,433頁。
(108)此處言亡弟之母,意謂非劉祥之母,故知祥與亡弟爲異母兄弟。
(109)《太平御覽》卷五一一引《三十國春秋》,中華書局,1959年,2329頁。
(110)《南史》卷二五《到溉、到洽傳》,678-681頁,又參《梁書》卷四○《到溉傳》,568頁。
(111)《文選》卷五五劉孝標《廣絶交諭》李善注引劉孝綽云:“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悠然,不相存贍。”(中華書局,1977年,760頁。綽原誤標,據羅國威《劉孝標集校注》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12)《魏書》卷四七《盧玄附子度世傳》,1046頁。
(113)《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34頁。
(114)《北史》卷四四《崔亮附僧深傳》,1640頁。
(115)《魏書》卷六一《薛安都附真度傳》,1359頁。
(116)《魏書》卷五三《李沖傳》,1189頁。
(117)同上書,1187頁。
(118)《宋書》卷五六《謝皭傳》,1558-1559頁
(119)《宋書》卷七四《沈攸之傳》,1940-194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