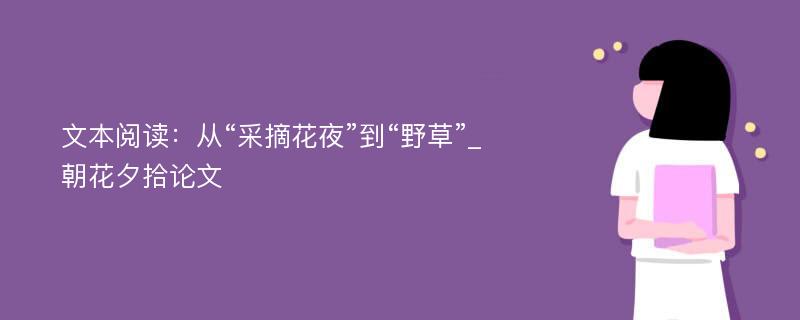
文本阅读:从《朝花夕拾》到《野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花夕拾论文,野草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1925年到1926、1927年这一段时间,鲁迅的作品主要有杂文集《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此外还有短篇小说集《彷徨 》的后期作品。这四个部分其实是个有机的整体。这些年学术界比较重视《朝花夕拾》 和《野草》的研究,而相对忽略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其实也会影响对《朝 花夕拾》、《野草》的把握。我想我们今天还是应该把这四部著作统一起来看,把它看 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或者可能比孤立的研究看出更多的一些东西。
一、
我们先看《朝花夕拾》。或者可以从《<朝花夕拾>小引》里这段话进入这部作品——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 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下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 没有。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 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 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 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缀,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 所的东壁;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 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注: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 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29-230页。)
这里所说的“纷扰”,包括“东壁……流离……挤出”,都与这一时期在女师大风潮 、三·一八惨案中和陈西滢们的论战有关。所有外在的“纷扰”——与“当局”、“文 人学者”……的生命搏斗,都会转化为内心的“纷扰”,并且会由此焕发出一种生命的 欲求:从内心深处的记忆中,寻找生命的“闲静”,以抵御这样的“纷扰”;从自我生 命的底蕴里,寻找光明的力量,以抵御由外到内的漫漫黑暗。我想这应该是鲁迅写《朝 花夕拾》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因。因此,我在读《朝花夕拾》的时候,有一句话,每读一 次,都会感到心灵的震撼。这就是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结尾的那一声呼唤“仁厚 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注:《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 第2卷,248页。)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鲁迅心灵深处的呼唤,是他在受到外部的种种 伤害以后所发出的生命的呼唤:他要回到这个“仁厚黑暗的地母”的怀里,永安他的灵 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朝花夕拾》是鲁迅的“安魂曲”。许多人在《朝花 夕拾》里所感受到的是在鲁迅其他作品中不容易见到的温馨、慈爱,或者像我曾经说过 的,是鲁迅心灵最柔和的一面的显示,恐怕都是缘于这样的心理动因。
《小引》中谈到文体的杂乱,也很值得注意。人们很容易就发现,鲁迅所特有的“杂 文笔法”对他的散文的渗透:在回忆中经常插入对现实中的“名人”、“名教授”、“ 绅士”、“指导青年”的“前辈”……也就是陈源们的讥讽(注:参看《<朝花夕拾>· 小引》、《狗.猫.兔》、《<二十四孝图>》、《无常》、《琐记》、《藤野先生》、《 <朝花夕拾>后记》,分别见《鲁迅全集》第2卷,第230页,第232页,第240页,第251 页,第252页,第253页,第268页,第269页,第270页,第273页,第292页,第306页, 第308页,第334页,第335页。)。这些文字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有着更多的 相通。表面看起来,这都是随手拈来,顺便“刺”它一下,很容易被看作是涉笔成趣的 闲笔。其实在鲁迅是一点也“闲”不起来的:“闲话”只属于陈源。这些“杂文笔法” 是在提醒我们读者:鲁迅整个的思考,《朝花夕拾》里的回忆,始终有一个“他者”的 存在:正是这些“绅士”、“名教授”构成了整部作品里的巨大阴影。鲁迅在《朝花夕 拾》里所要创造的“世界”是直接与这些“绅士”、“名教授”的世界相抗衡的:不仅 是两个外部客观世界的抗衡,更是主观精神、心理的抗衡。于是,我们注意到了在《< 二十四孝图>》里的这段话——
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然而究竟能有比阳间更好的处 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注:《<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2卷,第 252-253页。)
这里提出的“阴间”和“阳间”的对立是能够给读者以惊异感的:由“鬼”组成的“ 阴间世界”和由“人”——特别是由“正人君子”——组成的“阳间世界”,在鲁迅的 记忆里,竟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而鲁迅显然亲近于“鬼”的“阴间”,而疏离、甚 至憎恶于“人”的“阳间”,这都是非常特别的。把这点说得最透彻,描绘得最好的无 疑是《无常》这一篇。
他们——鄙同乡“下等人”——的许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积久的 经验,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只有一个会,而且这个会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 乎势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人是大抵自以为衔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 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注:《无常》 ,《鲁迅全集》第2卷,第269-270页。)
这里,又有一个“正人君子”与“下等人”、“愚民”的对立:前者不但掌握着“阳 间”即现实社会的“公理”,而且以“维持公理”为己任;后者则处于“活着,苦着, 被流言,被反噬”的地位。这样的对立图景在这一时期鲁迅著作中是频频出现的:例如 ,在《春末闲谈》(1925年)里“治者”、“阔人”、“君子”、“特殊知识阶级”与“ 被治者”、“小人”的对立(注:《春末闲谈》,《鲁迅全集》第1卷,第206页,第204 页,第207页。),《写在<坟>后面》(1926年)中“聪明人”与“愚人”的对立,等等。 这对于此后鲁迅思想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讲到“下 等人”的命运时,所说的“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恰恰是他自己在与现代评 论派的“正人君子”们论战时的生存境遇。这正意味着,当社会“公理”的垄断者与维 持者要将鲁迅逐出时,鲁迅感到了他与处于社会底层的“下等人”、“愚民”之间处境 与命运的相同;当他自觉地自我放逐于体制之外时,鲁迅也就顺理成章地回到了“下等 人”与“愚民”中间。
在这样的生存选择背景下,鲁迅幼时的民间记忆的浮现与强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处于鲁迅民间记忆中心的是民间戏曲中的“鬼魂”。鲁迅在生 命最后时刻,几乎是与他所说的“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 —“女吊”共同度过的(注:《女吊》,《鲁迅全集》第6卷,第614页。),这当然不是 偶然的。
而在1926年的“此刻”,鲁迅最神往的却是“无常”。他怀着深情这样说——
我至今还确凿记得,在故乡时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而 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
请注意他的身份:他是“鬼”而“人”——首先,他与人“最为稔熟,也最为亲近” ;同时,他又确实是鬼,但也因此可以超脱人间的种种麻烦与污浊,保持更完美的人性 ,所以鲁迅不禁发出感慨:“莫非入冥做了鬼,倒会增加人气的么?”你看,鲁迅一则 说他“理而情,可怖而可爱”,二则说他“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这都是鲁迅最 为欣赏的性格,甚至有点像是说他自己,所以鲁迅说:“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 当”,可以说无常所显示的是鲁迅所向往的“理想的人性”——这是鲁迅在20世纪初就 与同窗好友许寿裳仔细讨论过的。再看看无常的样子:
身上穿的是斩衰凶服,腰间束的是草绳,脚穿草鞋,项挂纸锭;手上是破芭蕉扇,铁 索,算盘;肩膀是耸起的,头发却披下来;眉眼的外梢都向下,像一个“八”字。头上 一顶长方帽,下大顶小,按比例一算,该有二尺来高罢。
……雪白的一条莽汉,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笑还是在哭。但他一出 台就须打一百零八个嚏,同时也放一百零八个屁……
这是一个“平民化”的鬼,甚至有些其貌不扬,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遇 到他这种模样,所以鲁迅说他“是和我们平辈的”,“他不摆教授先生的架子”。“无 常”是作为“勾摄生魂的使者”出现的。鲁迅说,“无常”是表示人“对于死的无可奈 何,而且随随便便的”,这是真正“理而情”的人生态度,是在充分认识与把握人和人 生的有限性以后,对于现实人生的一种豁达。鲁迅由此想起的是家乡的“下等人”也是 这样把“求婚,结婚,养孩子,死亡”看作是“明白”而寻常的人生之路的;鲁迅后来 说到自己时,也自称为死的“随便党”。或许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上的共鸣,使鲁迅对 “无常”有着特殊的亲切感吧。
当然,更让鲁迅向往的是,在“无常”面前,“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时都是‘一 双空手见阎王’”,“无常”手里拿着大算盘,死限到了就得死,“你摆尽臭架子也无 益”。不仅“无常”,阴间里的阎罗天子,牛首阿旁,都是“真正主持公理的脚色,虽 然他们并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什么大文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人们怎能不“发 生对于阴间的神往”(注:以上所引均见《无常》,《鲁迅全集》第2卷,第268-274页 。)!这里自然是有潜台词的:你们这些“正人君子”高喊什么“公理维持”,讲什么“ 正义”,讲什么“公允”,都不过是串戏的把戏;而“无论贵贱,无论贫富”的真正的 公平与公正,只能存在于民间的想象之中。这恐怕是《朝花夕拾》里提出的非常重要的 一个命题。这和鲁迅在本世纪初所提出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是一脉相承的。那时 ,他所针对的是维新派的“志士”,而在1920年代他在经过了对自命为“特殊知识阶级 ”的“现代伪士”的论战之后,他又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还可以作一点补充:我们前面说过了无常性格中的诙谐与豁达,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他 性格中的坚毅,这种以坚毅为内核的豁达、诙谐,其实是表现了鲁迅的故乡浙东人的民 性的。鲁迅在前引文字中说他和故乡的“下等人”一起欣赏“无常”“口头的硬语和谐 谈”,这正是这样的民性在绍兴方言中的表现。鲁迅的回归民间,自然也包括了从地方 文化传统中寻求精神的支撑。
当然,在鲁迅这里并不存在着对民间与地方文化的理想化。所以在我们一开始就引用 的《<朝花夕拾>小引》中,他在谈到“思乡的蛊惑”时,紧接着就说,“他们也许要哄 骗我一生”:这种回归中的质疑恰恰是最能表现鲁迅的特点的。
二、
现在,我们一起来读鲁迅的《野草》。
鲁迅在与萧军的通信中谈到《野草》时曾经说过:“那是我碰了很多钉子之后写出来 的”。这也就提示我们,《野草》和这个时期他的一系列论战,和“五·四”之后知识 分子的分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野草》的第一篇是写作在1924年9月。这时候女师 大风潮还没开始,但鲁迅已经在《未有天才之前》里跟胡适展开论战了。大概前后有13 篇(从《秋夜》到《狗的驳诘》),都是在鲁迅介入女师大风潮之前。鲁迅介入女师大风 潮之后,又有10篇(从《失掉的好地狱》到《一觉》)。最后一篇《题辞》写在1927年4 月26日。大概就在1924年到1927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之内,鲁迅先后经历了与胡适及现 代评论派的论战,一直到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以至“四·一二”事变。但 这些外在的论争、事变都是作为背景存在的。
来看《影的告别》。
在这一篇里,“影”所“告别”的“你”(“形”),人们可以作不同的解释。我自己 的理解是,“你”(形)和“我”(影)是一个共同体;“你”(“形”)是作为“群体”的 存在,是按照社会规范的常规、常态去生活的,而“影”却是一个“个体”的存在,而 且是社会规范的反叛者。“不知道时候的时候”——从表面看起来没有时间,也就没有 记忆;但就好像做梦一般,沉下去,沉下去,最后浮现出来的是生命最深处,原始的生 命本体的记忆与意念。于是,“影”(“我”)就向“形”(“你”)“告别”了——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 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意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乐意”,“我不愿意”,“我不想”,五个小节中,连续用了十一个“我不” 。这里表达的是非常强大的主体精神、意志,是一种无条件、无讨论余地的拒绝。首先 拒绝的是人们或者认为是天堂,或者视为是地狱的一切现实的存在。对于人们预设的未 来——那所谓无限美好的无限光明的“黄金世界”,“我”也同样拒绝。就连“你”— —这个生活在既定的原则、规范里的“群体”的存在,我也要拒绝。说到底,这是对于 “有”的拒绝,对已有的,将有的,既定的一切的拒绝。
“我不如彷徨于无地”——这里的“无”是与“有”对立的;这里的“彷徨”所表现 的生命的流动不居状态是与前面的“住”所表现的稳定的生命状态对立的。这正是“我 ”的选择:“我”拒绝“有”而选择“无”,“我”拒绝“住”而选择“彷徨”。我的 生命将永远流动于“无”之中。那么,“我”是谁?“我不过一个影”,一个从群体中 分离出来的,从肉体的形状中分离出来的“精神个体”的存在。那么,“我”将有怎样 的命运?“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因为我反抗现有陈规,反抗黑暗。“然而光明又会 使我消失”,因为“我”与黑暗是一个共生体,“我”的价值就体现在和黑暗捣乱中, “我”必将随黑暗的消失而消失。“吞并”与“消失”就是“我”必然的也是唯一的命 运。
“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影”的形象:尽管内心充满了痛苦、彷徨与犹豫,却要硬 作欢乐,然后独自远行。临行之前,“你还想要我的赠品”,于是又引出了“我能献你 什么呢?”也即“我还拥有什么”的问题。“无己,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我所 拥有的只是黑暗,只是空虚:“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 ,或者会消失于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这里连续几个“我愿意” ,正是对前面的“我不”,“我不愿意”的回应。——从拒绝现有与将有,到选择无的 黑暗与虚空,完成了一个历史过程。
“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 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注意这里有一个转换:当独自远行,一个人被 黑暗所吞没的时候,“我”达到了彻底的空与无;但也就在这独自承担与毁灭中,获得 了最大的有:“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注:《夜颂》,《鲁迅全集》第5卷 ,第193页,第193页。),“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正是在这生命的黑暗体验中,实 现了“无”向“有”的转化:从拒绝外在世界的“有”达到了自我生命中“无”中之“ 大有”,这一个过程或许是更为重要的。
这里提到了生命的黑暗体验,这是一种人生中难以达到的可遇不可求的生命体验,如 一位研究者所说,这是一种生命的大沉迷,是无法言说的生命的澄明状态:“如此的安 详而充盈,从容而大勇,自信而尊严”。你落入一个生命的黑洞之中,这黑洞将所有的 光明吸纳、隐藏其中,这里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光明:“充盈着黑暗的光明”( 注: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322页、 第336-340页,第325页。)。鲁迅自己也说:“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 ,自在暗中,看一切暗”,“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予的光明”(注:《夜颂》, 《鲁迅全集》第5卷,第193页,第193页。)。鲁迅正是这样的“爱夜的人”。不仅《影 的告别》,而且整本《野草》,都充溢着他以“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所听到、看 到的“一切暗”,以及他所领受到的“夜所给予的光明”。——这是我们在阅读《野草 》时,首先要注意和把握的。
《影的告别》实际上讲了两个方面:一是他拒绝了什么?一是他选择了、因而承担了什 么?这构成了《野草》的一个基本线索。
我们再来看其它几篇。
先看《求乞者》。读这一篇,首先感受到的是无所不在的“灰土”,几乎要渗透到你 的灵魂。这更是一种“灰土感”:生命的单调、沉重与窒息。这就像鲁迅所说的:“是 的,沙漠在这里。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 至于没有好奇心。沉重的沙……”(注:《为“俄国歌剧团”》,《鲁迅全集》第1卷, 第382页。)没有任何生机,没有任何生命的乐趣,“没有好奇心”也就没有任何欲望与 创造的冲动。“灰土”之外是“墙”,“墙”之外“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这也 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隔膜,这心灵的隔绝不仅是社会、历史的,更是人类本身的, 人于是永远“各自走路”。《求乞者》一开始传递给我们的,不仅是生命的窒息感和隔 膜感,更是一种近于绝望的孤独的生命体验:依然是郁积于心的黑暗与虚无。
于是就有了“求乞”与“布施”:开始是孩子向“我”求乞,我知道这是“儿戏”, 拒绝布施;后来却反诸于己:“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而且也同样“我将得不 到布施”。这里仍然贯穿着一个“拒绝”的主题:不仅“我不布施”,而且“但居布施 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显然,这里的“求乞”和“布施”是带有象征性的。首先我们可以把“布施”理解为 温暖、同情、怜悯、慈爱的象征,人们总是祈“求”着别人对自己的同情与慈爱,也给 别人以同情与慈爱。这似乎是人的一种本能,但鲁迅却投以质疑的眼光:他要看看这背 后隐藏着什么。在《过客》里也有类似的展开,有这样一个情节:“小女孩”出于对“ 过客”的同情,送给他一个小布片,这自然也是温暖、同情、爱的象征。“过客”开始 很高兴地接受了:作为孤独的精神界的战士,他显然渴求着爱、温暖和同情;但想了想 之后,却又断然拒绝,并且表示要“诅咒”这样的“布施者”。鲁迅后来对此作了一个 解释:因为一切爱与同情,一切加之于己的布施,都会成为感情上的重负,就容易受布 施者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所以鲁迅说:“反抗,每容易磋跌在‘爱’——感激 也在内——里,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注:《书 信:250411致赵其文》,《鲁迅全集》第11卷,第442页。)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孤独的 精神界战士,要保持思想和行动的绝对独立和自由,就必须割断一切感情上的牵连,包 括温情和爱,既不向人“求乞”,同时也拒绝一切“布施”。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种“ 求乞”、“布施”理解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高度概括:人总是对“他者”有所 “求”,同时又有所“施”。而有所求就难免对“他者”有所依赖,以至依附;反过来 ,布施也难免使对方对自己有所依赖与依附:鲁迅就这样从“求乞”与“布施”的背后 ,看到了依赖、依附与被依赖、被依附的关系。这确实是十分独特而锐利的观察。更何 况现实中的“求乞”常常是虚假的——鲁迅对于不幸中的人们不得不求乞,本是有一种 感同身受的理解与同情的,他自己就有过“从小康坠入困顿”的痛苦经历,饱尝过被迫 “求乞”的屈辱(注:如我们一再强调,鲁迅是始终站在不幸者即生活中的弱者这一边 的,他为他们的生存、发展的权利作了最有力的辩护;但他强调的是弱者的自强,而不 是等待他人的恩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布施”也表示了憎恶。);但问题在于 中国的“求乞者”或者自身并不真正需要求助,或者身处不幸却并无自觉因而“并不悲 哀”,但却“近于儿戏”地“追着哀呼”,以至“装”哑作“求乞的法子”。鲁迅在“ 求乞”的背后又发现了“虚伪”与“做戏”:既不知悲哀(不幸)又要表演悲哀(不幸)。 正是这双重的扭曲,激起了鲁迅巨大的情感波澜:他要给与“烦腻,疑心,憎恶”!于 是就又有了鲁迅式的“拒绝”:这回拒绝的是“温暖,同情,怜悯与慈爱”,他依然选 择了“无”:“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将可能导致内心的 软弱的心理欲求(如布施、同情、怜悯之类)、情感联系(如“布施心”)通通排除、割断
,铸造一颗冰冷的铁石之心,以加倍的恶(“烦腻,疑心,憎恶”)对恶,加倍的黑暗对 付黑暗,在拒绝一切(“无所为与沉默”)中,在与对手同归于尽中得到“复仇”的快意 。鲁迅的这种选择,是一把双刃剑:既对他的敌人有极强的杀伤力,而且毋庸讳言,也 伤害了他自己,构成了他内在心灵上的“毒气、鬼气”的另一方面。鲁迅因此说他自己 也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凡指向对手的也将反归自己, 这实在是十分残酷与可怕的。鲁迅这样的“自残”式的选择,不仅付出的代价太大,而 且是很难重复的,很可能是“学虎不成反成犬”。
《希望》一篇,仍然是从自己对生命存在的感受、体验说起——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 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 ,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这里讲的是生命的“平安”状态。在《野草》里,鲁迅好几处都提到“太平”。《失 掉的好地狱》一开始就写到地狱的“太平”:“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 。”(注:《失掉的好地狱》,《鲁迅全集》第2卷,第199页。)《这样的战士》里也提 到了“谁也不闻战叫:太平”(注:《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第2卷,第215页。) 。“太平”是一种宁静的有秩序的状态,引用《论睁了眼看》里的说法,就是“无问题 ,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注:《论睁了眼看》,《鲁迅全 集》第1卷,第238页。)。在鲁迅看来,这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虚假的 表面的“太平”掩盖了地底下真实的矛盾与痛苦,于是受压制的“鬼魂”的“叫唤”、 呻吟,也变得“低微”。鲁迅说他“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注:《<野草>题辞 》,《鲁迅全集》第2卷,第159页。),他更憎恶这地面的“太平”。在他看来,这样 的“不闻战叫”的“太平”,最可怕之处,是造成人的心灵的“平安”:“没有爱憎, 没有哀乐,没有颜色和声音”,这是对生命活力的另一种窒息与磨耗。于是,鲁迅感到 了生命的“老”化:这不仅是生理的(鲁迅这时才45岁),“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 ,头发也一定苍白了”。这“平安”中“魂灵的苍老”,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命题,是鲁 迅的发现,更是鲁迅所要拒绝的。
于是又开始了历史的追索:“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也曾充满希望。——“忽而这 些都空虚了”,只得用“自欺的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 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并因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但又暂存着对“身外 的青春”的希望,那“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 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尽管“悲凉飘渺”,却“究竟是青春”。现在却突 然发现四围的“寂寞”(也即“太平”),“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 多衰老了么”?——这真是步步逼退:这是一个“希望”逐渐被剥离,逐渐被掏空的过 程。
我放下了“希望之盾”,于是,听到了裴多菲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这其实也是鲁迅的发现:他发现了“希望”的欺骗性与虚妄性——这同样是由“有” 到“无”的过程。但还要推进一步:“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按一般的逻辑 ,“希望”既然是一种绝对的欺骗,那势必会转向“绝望”;但正像论者所指出的,“ 这种绝望内在参照仍然是‘望’”,“仍然是以否定的方式承认了‘希望’”(注:王 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322页、第336-3 40页,第325页。)。要彻底抛弃“希望”,就要同时抛弃“绝望”;把两者都虚妄化, 完全掏空,才能达到彻底的“无”。于是,又有了独自承担——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 身中的迟暮。
“肉薄”是一种躯体的搏斗,不带有任何精神上的“希望”或“绝望”,“和黑暗捣 乱”就是了,既不计“后果”,也不追求“意义”;而且是“由我”一人进行,与别人 无关。这非常接近前面《影的告别》里所说的“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 己”的境界,这也是彻底的“无”向“有”的转换。然而,文末又留下一句可怕的话— —但暗夜又在那里呢?……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准备独自承担反抗 ,却突然发现:反抗没有对手了!
这又引出了下一篇——《这样的战士》。
如前面所引,鲁迅曾说:“《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鲁 迅在和陈源论战时,多次提到他自己的“碰壁”:他把文人学士的攻击比喻为“墙”, 而且是“鬼打墙”:分明存在却又无形。在《这样的战士》中,又把这种感受提升为“ 无物之阵”——
但他举起了投枪。
……
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阵则是胜者。
人们首先注意的是“无物之阵”上的“旗帜”和“外套”,据说有“各样好名称:慈 善家,学者,文人,长者,青年,雅人,君子……”,还有‘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 ,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可以说,这里几乎囊括了一切美好的词 语,前者标志着一种身份,后者则标志一种价值,现在都被垄断了;这就是说,鲁迅这 样的精神界“战士”所面对的是一个被垄断的话语,其背后是一种社会身份与社会基本 价值尺度的垄断。而这样的被垄断的话语的最大特征就是字面与内在实质的分离,具有 极大的不真实性与欺骗性。这种身份词语与价值词语的垄断,正意味着一种具有欺骗性 的语言秩序、社会秩序的建立与垄断;另一方面,话语垄断者正是拿这些被垄断的话语 对异己者——精神界“战士”进行打压与排挤,软化与诱惑:要进入就必须臣服,要拒 绝就遭排斥。而鲁迅这样的精神界“战士”几乎是没有犹豫地就作出了他的选择——“ 他只有他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
了他们的心窝。”
这正是最彻底的拒绝与反抗:对一切既有的,被垄断的,欺骗性的身份话语与价值话 语(及其背后的语言秩序与社会秩序)的拒绝与反抗,这同样也是“无”的选择,而且依 然是孤身一人的独自承担。对于以话语作为自己基本存在方式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拒绝 与反抗,是具有根本性与特殊的严重性的。
接下来是《复仇》、《复仇(其二)》。
这里所要表达的,是“无物之阵”的另一面:精神界“战士”面对的是自己为之奋斗 与牺牲的群众。这是一群“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是欣赏残酷与表演的“看客”。 你看——
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
路人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而且拼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 们已经预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一切生命活力的自然释放,一切真实与真诚的生命搏斗与挣扎,在这些“路人”的眼 里,都只是表演;他们从四面奔来,只是为了“赏鉴”,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找一点刺激 ,用牺牲者的鲜血来慰藉自己麻木的心灵;而正是在这鉴赏过程中,“战士”悲壮的努 力与崇高的牺牲全被戏剧化,在“哈哈一笑”中,真实的(而非“文人学者”那样虚假 的)意义与价值被彻底消解:这也是化“有”为“无”,却是绝对消极的,只能产生“ 无聊感”——这也是无时不刻缠绕着鲁迅的生命体验。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 是以“无”对“无”,拒绝表演,拒绝动作:“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 抱或杀戮之意”,以“无所为”来对抗、消解路人的“赏鉴”,把他们置于“无聊”的 境地,并且倒过来“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将“看与 被看”的结构颠倒过来,并从中感到“复仇”的快意。
再看《死火》。
首先题目本身就充满着矛盾:是生命之“火”,但是“死”的。这典型地体现了鲁迅 思维的特点:不是单一的“死亡”或“生存”的视角,而是从“死亡”和“生存”的双 向视角,从生死关系中来想象“火”。于是,就有了“我”与“死火”的一次奇遇,而 且有了“我”与“火”之间关于生命的选择的哲学讨论。提出的问题是:“死火”如果 不跳出“冰谷”,就将“冻灭”;如果跳出后继续燃烧,也将面临“烧完”的命运—— 其实这正是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会面临的:无为,就必然“冻灭”;有为,也依然“烧完 ”。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死亡(“灭”、“完”)的宿命,人只能在这个大前提下作出极其 有限的选择。“死火”的选择是与其冻灭,“我就不如烧完”,鲁迅这样的“战士”的 选择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宁愿“烧完”:至少在“烧”(挣扎)的瞬间还会发光 ,即使是微弱的光辉。他们看重的不是最后的结果,更看重生命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 看,当“战士”作出这样的选择时,他是同时预计到自己悲剧性的结局的。因此,这也 可以看作鲁迅对自我选择的质疑,他从来没有将其赋予一种绝对的理想价值:这不过是 宿命之下的极其有限的选择而已,这里是包含了许多无奈的。而鲁迅对“无为”(“冻 灭”)的拒绝也是意义重大的——这种拒绝也是贯穿鲁迅一生的:20世纪初,他就在《 摩罗诗力说》中尖锐地批评了老子的“无为之治”;到离世前他还在坚持批评老子的“ ‘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注:《<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第521页 。)。而鲁迅自己是始终坚守“绝望的反抗”的——所谓“与其冻灭,不如烧完”,既 是绝望的选择,也是对绝望的反抗。
但这样的自异于常规社会的“战士”就必然是孤独的:“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 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这又是一个反归:对现有的一切经验、逻辑 和秩序的怀疑,拒绝,反叛,都指向对自身的怀疑,拒绝与反叛,即所谓“自啮其身” ,也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彻底掏空”,达到彻底的“空虚”与“无”。然后才能进入 对“本味”的追寻,即所谓“抉心自食,欲求本味”,也就是从人的存在的起点上追寻 那些尚未被现有经验、逻辑和秩序所侵蚀的本真状态。
看《颓败线的颤动》。
这也许是《野草》中最震憾人心的篇章。那位老女人的遭遇所象征、展示的是精神界 “战士”与他所生活的世界,现实人间的真实关系:带着极大的屈辱,竭诚奉献了一切 ,却被为之牺牲的年轻一代(甚至是天真的孩子),以至整个社会无情地抛弃和放逐。这 样的命运对于鲁迅是具有格外严重的意义的,本身即构成了对他“肩住黑暗的闸门”, 放年轻人“到光明地方去”的历史选择的质疑。
她冷静地,骨立的石像似的站起来了。她开开板门,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 一切的冷骂和毒笑。
这里有一个转换:原来是被社会遗弃,现在是自己将社会遗弃与拒绝。
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 ,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 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 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这里所反映的“战士”与现实世界的感情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作为被遗弃的异端,当 然要和这个社会“决绝”,并充满“复仇”、“歼除”与“咒诅”的欲念;但他又不能 割断一切情感联系,仍然摆脱不了“眷念”、“爱抚”、“养育”、“祝福”之情。在 这矛盾的纠缠的情感背后,是他更为矛盾、尴尬的处境:不仅社会遗弃了他,他自己也 拒绝了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他已经“不在”这个社会体系之中,他不能、也不愿用这 套体系中任何语言来表达自己;但事实上他又生活“在”这社会之中,无论在社会关系 上,还是在情感关系上都与这个社会纠缠在一起。如果他一开口,就有可能仍然落入社 会既有的经验、逻辑与言语中,这样就无法摆脱无以言说的困惑,从而陷入了“失语” 状态。“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这又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也是很带悲剧性的“无”的选择:不能(也拒绝)用现实人间 社会的言语表达自己,而只能用“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一个真正独立的批 判的知识分子,他的真正的声音是在沉默无言中呈现的。所谓“非人间的,所以无词的 言语”,指的是尚未受到人间经验、逻辑所侵蚀过的言语,只能在没有被异化的“非人 间”找到它的存在。因此,——
当她说出无词的言语时,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 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 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
这是极其精彩的一个段落,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的境界:拒绝了“人间”的一切,回到 了“非人间”,这“沉默尽绝”的“无边的荒野”,其实是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在某种 程度上,这正是鲁迅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更具真实,就像在《影的告别》中的“影” ,在无边的黑暗中,拥有了无限的丰富,无限的阔大,无限的自由。这一段文字,在我 个人看来,是最具有鲁迅特色的文字;而且坦白地说,在鲁迅所有的文字中,这是最让 我动心动容的。
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过客》。这一篇可以说是鲁迅对自己的生命哲学的一个归结。
我们是这样遭遇“过客”的——“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 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这是 典型的在旷野中匆匆而过的“过客”,往往使我们自然地想起鲁迅本人的形象。他一出 现时,就一直在往前走,他遇见老人,老人向他问了三个问题:“你是怎么称呼的?” “你从哪里来的呢?”“你到哪里去?”而他的回答都是“我不知道”。应该说,这三个 问题,是20世纪整个人类,西方哲人和东方哲人都同时面临的“世纪之问”,而鲁迅的 回答都是“我不知道”。——这回答本身就有很大的意义。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过客” 的选择。他其实有三条可供选择的路,一是“回去”,“过客”断然否定了,他说:“ 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 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这是“过客”的 一个“底线”:绝不能容忍任何奴役与压迫,绝不能容忍任何伪善。二是停下“休息” ,这是老人的劝告,但“过客”说“我不能”。最后只剩下往前“走”了。但也还有一 个问题:“前方是什么”。剧中的三个人物有不同的回答:小女孩说前方是个美丽的花 园,这可能是代表年轻人对未来的一种向往与信念;但“老人”说,前面是坟,既然是 坟,就不必往前走了;而“过客”的回答是,明知道前面是坟,但我还是要往前走。这 说明“过客”的选择,不是出于希望的召唤。是什么引导他不断往前走呢?他说,前面 有一个“声音”在呼唤。老人也听到过这声音,但他不听它召唤,它就不喊了。但过客 却无法拒绝这前面的声音:正像薛毅在他的《无词的言语》里所说,这是他内在生命的 “绝对命令”——往前走(注:薛毅:《无词的言语》,[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第12页。)。一切都可以怀疑,但有一点不能怀疑,就是往前走。走的结果怎样,怎么 走,这些都可以讨论,但有一点不容讨论,就是必须走。这是生命的“底线”,这一点 必须守住!这样就有了他最后写的《野草》的《题辞》。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的“充实 ”的世界存在于“沉默”也即“无(言)”之中。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 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鲁迅的 自我生命的价值是通过死亡来得以理解的,由死知生,向死而生,由死亡反过来体会、 证实生命的价值。因此,他对生命有“大欢喜”。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 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 笑,我将歌唱。”——鲁迅“自爱”野草,因为这是他的生命;同时也渴望“地火”的 “喷出”将野草“烧尽”,也即用自我生命的毁灭,来证明新的世界的真正到来。他将 为此“大笑”与“歌唱”。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鲁迅显然期待通过《野草》的写作,结束自我生 命的一个阶段。这同时也是一个新的生命过程的预示。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小结。从《野草》里可以看到,当鲁迅将他自我放 逐,或者整个学界、整个社会把他放逐时,他所达到的境界:拒绝、抛弃一切“已有” 、“将有”、“天堂”、“地狱”、“黄金世界”、“求乞”与“布施”、“希望”与 “绝望”、“学问,道德,民意,公义”等一切被垄断的话语、逻辑和经验……。也就 是说,对现有的语言秩序、思想秩序和社会秩序给以一个整体性的怀疑、否定和拒绝。 也就是把“有”彻底掏空;或者用佛教的说法,就是要对“有所执”进行拒斥。这样, 他所拥有的就只是“黑暗”、“空虚”、“无所为”、“肉薄”……,并在这样的拥有 中实现最大的自我承担与毁灭。这样说,鲁迅不是太黑暗了吗?但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他所进入的“黑暗”世界、“虚空”世界,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无所有,而实际上是 非常丰富的,应该是更大的一个“有”:对现有一切的拒绝达到无、空,由无、空达到 更大的有和实,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鲁迅最后说的是:“但我坦然,欣然。我 将大笑,我将歌唱”。如果你仅仅看见承担黑暗的鲁迅,而看不到这承担后面的“坦然 ”、“欣然”、“大笑”和“歌唱”,你就不能真正理解《野草》。鲁迅对黑暗承担本 身虽然是极为沉重的,但另一方面,却使他自身的生命达到更为丰富、博大、自由的境 界。我们读鲁迅的《野草》时,一定要把握这两个侧面,否则很可能产生误解。而最后 ,鲁迅又把他的生命哲学归结为不计后果、不抱希望地,永远不停地“向前走”这一绝 对命令,这更是使他的生命获得了不断开拓的活力。这是可以通向最后十年的鲁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