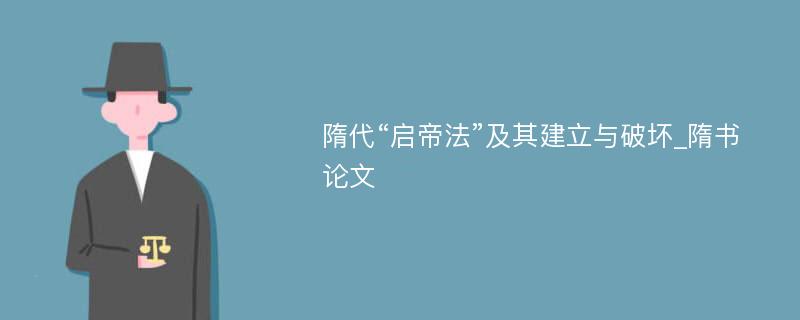
隋《开皇律》及其立与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隋代年祚不永,38年而亡,然却两修隋律。《隋书》卷33《经籍志·刑法篇》载,“《隋律》十二卷,隋《大业律》十一卷”,其十二卷之《隋律》修之于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史论有别于其子隋炀帝杨广大业初更修之隋律而称之为《开皇律》。
从开皇初(581)到大业初(605),隋律更修时间之隔不过二十余年。那么,隋炀帝于“祖法”更化何以如此之速呢?《旧唐书》卷50《刑法志》载:“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以定律,令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比及晚年,渐亦滋虐。”是隋炀帝大业初修律,意在去苛归平,而这一点则正是隋文帝修《开皇律》以代北周《刑经圣制》的基本精神;而隋文帝之《开皇律》何以又由平趋苛,复行前辙如此之快呢?此为本篇试论之一。次之,比较隋代两律,《大业律》只是在律例名目上作有增广,在处罚尺度上《降从轻典》①,其精神与框架则一仍《开皇律》不动,质言之,《大业律》的重修只是隋文帝开皇中以后刑法政治向大业初政治转化的产物,与律学本身无大关涉,故言隋代律学当以《开皇律》为主,此为本篇叙论之二。为叙论之便,首叙其二。
一
《隋书·刑法志》记,“高祖既受周禅,乃诏尚书左仆射、勃海公高颎,上柱国、沛公郑译,清河郡公杨素,大理前卿、平源县公常明,刑部侍郎、保城县公韩濬,比部侍郎李谔,兼考功侍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通典》卷164《刑法二》载开皇初修律人,仅云“高颎等”,下余不名。是修定律法乃一代典制大局,大臣领衔,几为惯例。因之,《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与《新唐书》卷58《艺文志》载十二卷《隋律》,皆只云“高颎等撰”。夷考其实,《隋书·刑法志》关于开皇初隋律撰修人多有阙载。择补如《隋书·李德林传》载,“开皇元年,勑令与太尉任国公于翼,高颎等同修律令。事迄奏闻,别赐九环金带一腰、骏马一匹,赏损益之多。”是于翼、李德林等周齐旧臣亦予隋初修律,且李德林由北齐而入周,予杨坚禅周建隋亦有力,人为山东文秀,其参修,而“多有损益”,对于《开皇律》修成之面貌自有影响。值得指出的是,《隋书·刑法志》未载《开皇律》的主修人。《隋书·裴政传》记,裴政“开皇元年,转率更令,加位上仪三司。诏与苏威等修定律令。政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同撰者十有余人,凡疑滞不通,皆取决于政。”故《通鉴》辑载开皇修律事,即云:“初,周法比于齐律,烦而不要,隋主命高颎、郑译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②,而后人亦视《开皇律》主修之功非裴政莫属。明清之际王夫之曰:“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③
裴政,由萧梁而入北周,隋禅周而为隋官。历官多在法曹、刑部,“用法宽平”,其人身历南北,多在臬司,广涉南北律学而有识断,对于《开皇律》的影响自不可小视。
就《开皇律》而言,前后有开皇元年初修与开皇三年复修两次,其中开皇二年高颎等人修纂的《开皇令》30卷、目1卷,多为行政法规及朝仪之制,不涉刑法与民法,可置而不论。隋开皇元年修律,其内容有如下几端:一,“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④定刑名为四等,一曰死、二曰流、三曰徒、四曰杖,此用法唯简,刑罚从轻的革新,弃除前代酷虐之肉刑,体现了隋律肇建之初的宽平精神;二,采自北齐“重罪十条”,创设“十恶之条”入正法,罪在不赦,“虽会赦,犹除名”⑤,此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核心之律,亦具有中华法系浓厚的宗法伦理政治色彩,强调以法的强制力来推行礼的规范,以求施法于“诛心”之上;三,援引南陈“官当”之法,明法规定各品官吏可依官品、官俸赎罪免刑,此为维护政治阶级利益的特权之律,亦为南朝门阀政治弩末之势入隋之后的一种反映。结此数端,《开皇律》大致承袭了中国封建法律的基本精神,故亦宜其为此后历代封建法典所沿袭。
开皇元年隋律修成,于十月奏上,凡1735条,“诏颁之”⑥从律学的角度看,《开皇律》较之古今杂糅、繁而不要的北周律确有了较大进步,“杂格严科,并宜除削”⑦法行宽平的原则适应了周隋禅代之后,世望宽平、人心思稳的政治需要。因之,隋律在开皇初的续修亦将本此精神而展开。
开皇三年,隋文帝“因览刑部奏,断狱数犹至万条。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勑令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⑧此次修律,主要内容有如下两端:一,减省刑名,“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唯五百条”⑨,此为对开皇元年修律行宽平精神之延续,反观可知,元年所修于刑名减省、拨苛归平方面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二,规范名例,革《北齐律》而定其篇名为,名例、卫禁、职志、户婚、厩车、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此为《开皇律》因革南北朝律学,乃至汉魏两晋律学之精华而做的一次封建律法范畴的总结,对此后,乃至东亚诸国的中古法典修定均有先河垂则之效。
《开皇律》的成就在于承前启后。史称,上“采魏、晋之典,下及齐、梁”,盖就其显流所承而言。则北齐之律对其影响最为直接,前引《隋志》及《旧唐书志》约略已明。陈寅恪先生则更明示之:“至宣武(《孝文帝次子,元恪》正始(504-507)定律,河西与江左二因子至关重要,于是元魏之律遂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取精用宏,宜其经由北齐、至于隋唐,成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则也。”⑩北魏修律虽在南北朝对峙时期,却成之于孝文迁洛之后;程树德《九朝律考·后魏律》云:江左之士在北者已不乏其人(11),故融汇南北律学条件以备。陈氏所云,“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历史地看,其精神乃是汉魏法学之绪,只是在晋永嘉乱后,而文化、及律学遂亦因士人之播迁、典籍之流荡而溃为河西一隅、南北之分而已,因之,其发源既一,宜其亦能有求汉化之北魏诸帝的汇“于一炉而冶之”的结果。
北魏律源既明,此后经北齐而入隋亦明:公元528年,契胡尔朱荣入洛,北魏名存而实亡。此后,先有关中西魏、关东东魏,后则有北周、北齐分禅二魏;北齐居邺修律以《北魏律》为蓝本,史称其“法令明审,科条简要”(12),续魏晋之律神韵;北周居长安创制远追姬周,所修《大律》则仿宗周之旧,故史有杂糅古今、烦简失当之讥。隋禅周立国,而北齐亡于周之臣遂亦多归隋室,其修律不依周而多取于齐。程树德《九朝律考》“隋唐二代之律,均以此(指《北齐律》)为蓝本“云云,与《隋志》所记均吻合,是《北齐律》乃隋律融取南北律学之主要因子。
隋初修律,经北齐而远绍北魏,承接了魏晋以来的汉法正源,融汇了南北朝律学发展之精华,因此能成就其传输汉法传统于唐律的关键所在;同时,这也是隋之所以站在统一全中国门槛之前,而能出色地体现综合大分裂时代各区域文化遗产的历史卓越性所在。
隋初《开皇律》修定,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于法系一源的系统性特征,故其上不仅能承中华法系之主流,而且下亦能开启此后历代法典之长流。《通鉴》记《开皇律》修成事曰:“自是法制遂定,后世多遂用之”(13)。其中,《开皇律》对唐律影响最著。史称,唐高祖李渊,“及受禅,诏纳言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寻又勑尚书左仆射裴寂”等人“撰定律令,大略以开皇为准”(14)。唐武德初修律,至武德七年而成,“被称为《新武德律》;它极像《开皇律》,也包含五百条款。因此这部初唐律令大致是经过隋代合理化处理三国南北朝时期法律的成果”(15)。至贞观朝,“唐太宗诏房玄龄等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而大旨多仍其旧”(16),而《新唐书》卷56《刑法志》亦肯定唐因隋律。清末民初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其《重刻〈唐律疏议〉序》中即曰:“隋律简要,而唐实因之。”
隋代的统治虽然极为短暂,然而由于历史进程之关系,它却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关节”意义。这个“关节”意义即蕴含着中华文化于分裂之后的再综合的意义。文化,我以为,非仅指政治之一统,也非仅指纯一民族之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在历史纵轴上得到普遍认同性的社会精神的积淀之物;因之,南北朝可有政治上之长期对峙,北朝亦可有多民族的历史冲突,然而在文化的作用下则一归融于中华传统之文化,隋初《开皇律》融南北律学而修订是一个具体的体现。因此,隋作为一个结束南北分裂,再作中华一统的王朝,其历史遗产传诸唐的意义,就不仅在于“政治作品”的丰硕之美,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预成于先的文化综合的历史的努力,《开皇律》是这种“努力”的成功之例,故其意义亦当揭橥于此!
二
法,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政治之政治。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里,它与宗法制下的伦理政治关系尤为紧密。汉以《春秋》义断狱,虽不见于隋律而精神不断,且伦理政治张纲常之表乃在于归旨忠君之本,而“君君,臣臣”,“子民天下”的忠君之政则不啻专制政治之代名词。因此,考察中国古代律法之立与毁,我以为当以一定的政治背景,及专制主义政治运行发展情况为依据,方可见其兴毁之间的历史本质。
《开皇律》修隋禅周伊始。隋禅周,从鲜卑宇文氏到弘农杨氏,江山易帜,换的只是皇帝的姓氏,完成的只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权力转移。然而,这一切又并非仅仅只是历史简单的平面循环,新朝旧朝之相代而相别,毕竟将“革故鼎新”以光大新朝姿态的剧目推到了新统治者的面前。汉高入关,“约法三章”而秦民牛酒以迎,对于隋文帝来说并非陌生;“厚德载物”以“仁”治天下,对于隋文帝及其集团成员亦非鲜知。因此,修律以简,论法从宽的历史示范,首先从经验的角度提示了隋文帝及其统治集团制订新律的操作原则;其次,北周末年,刑政弊坏的“当代之史”,更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规定了隋文帝及其统治集团亟修隋律的政治动因。史称,“隋高祖为相,又行宽大之典,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17)可见,开皇初《开皇律》的修纂,乃有杨坚未禅周之前的未雨绸缪之作;而其政治之效亦如《隋书·文帝本纪》所云:“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
周末宣帝宇文赟,生性多疑“摈斥近臣,多所猜忌”(18),用法严酷深重,甚至弃已定律法若弊屣,“诛杀无度”(19),以恐怖求集权。稽其所本《刑书要制》,创于西魏,原已“用法深重”(20);至其“又广《刑书要制》而更峻其法,谓之《刑经圣制》”(21),将重法严刑推于极致。史称,宿卫之官,“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没。上书字误者,科其罪。”(22)内外用刑,无所不及,“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挞,其间诛戮黜免者,不可胜言。每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官人内职亦如之。后宫嫔御,虽被宠嬖,亦多被杖背,于是内外恐惧”(23),“上下愁怨”而“内外离心”。综观周末刑政之酷,乃在于君主的任情施罚。杖刑,为封建刑法之常刑,隋制五等,极之亦不过百而已,宣帝逾制“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其后加至二百四十”(24),而名“天杖”,天杖意即“天子之杖”,是君权侵凌法权之典型表现。可见,北周末年的律法弊坏已亟待后起者起而“革”之。
北周末年法治弊坏的局面,构成了隋文帝欲行“革故鼎新”的政治目标,然促成其力行并规定隋初律法尚宽平精神者,却仍在周隋禅代之际的现实政治。史载,隋文帝“始迁周鼎,众心未附”,“诸子幼弱,内有六王之谋,外致三方之乱。握强兵、居重镇者,皆周之旧臣。”(25)杨坚禅周,内有周室宇文诸王的谋乱,外有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三方强镇的反兵,而北境突厥之摄图亦藉口:“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26)而“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27)是开皇初内外政治、军事形势均于禅代而立的隋文帝有极大之压力。因此现实政治之迫压,向有“至察”、“多疑”(28)之性的隋文帝亦一方面“推以赤心,各展其用”(29)示天下以坦诚以谋强化新朝的政治向心力;而另一方面则惟有尽快革除北周酷政,来争取那批在严刑重法下“各怀苟免”(30)的北周旧臣的反持,并藉以昭示新政权的“仁德”以谋求更为宽阔的政治合作基础,减少政权换马过程中的历史震荡。因之,开皇元年二月隋禅周,十月便有新律颁示天下;而隋文帝于开皇元年《开皇律》颁行之诏曰:“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31)其“取适于时”云云抑有其现实政治之所指。
《开皇律》从开皇元年初修,“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到开皇三年复修,律条从1735条减定为500条,前后修订皆本着一种简化、削减的修律原则,这些显然都是对周末“用法深重”、“更峻其法”刑政严深之弊的反拨。是《开皇律》之立立于法尚宽平之精神。而对于“自前代相承,有司拷讯,皆以法外”(32)的坏法之举,隋文帝颁律之后亦屡有诏令,反复“申勑四方,敦理辞讼”,“刊定科条,俾令易晓”(33),并“置律博士弟子员”(34)以彰朝廷明法之志;而臬司吏员“断决大狱,皆先谍明法”、“诸曹决事,皆令具写律文断之”(35),凡此亦都是对周末逾制用刑、“法外”施治的有力反拨。是《开皇律》之立立于成文法之后切实推行,故史论曰:“自是刑纲简要,疏而不失”(36)。
开皇初律法的制定及其推行情况,均说明隋在新建之初于封建法政建设上确有“刷新”之效。开皇六年,隋文帝“诏免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道逆人家口之配没者,悉官酬赎,使为编户。”(37)的宽大之举,亦说明《开皇律》在三年定讫之后的推行确实收到了它镇抚兼用的双刃剑之效。《开皇律》,“取适于时”以适应政权转移需要政治使命亦大致完成,而“诏修”、“钦定”的封建法所具有的专制本质,决定了它,最终将无法走出它所因革对象的那种由兴而毁的历史怪圈。
三
《开皇律》的运行,盖衍至开皇中,此后渐成空文。
《开皇律》的毁弃,首先表现在君权对司法权的侵凌,并由此导致任情予夺,“不复依准科律”(38),公然坏法的状况。开皇十七年三月,“听诸司于律外决杖属官诏”颁下:“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论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39)此为明之于载籍的“律外”决罚之诏。复稽史事,则隋文帝开中国封建朝廷“廷杖”之先河,亦其毁法之举。开皇中,文帝“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40);殿廷设杖,“一日之中,或至数四”;经高颎等强谏,方才使文帝“令殿内去杖”(41)。然不久文帝又缘怒欲杖人于殿,“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以鞭代杖,直取《开皇律》所废之酷刑,“自是殿内复置杖”而“殿廷杀人”(42)之事屡起。至此,以“诏”、“勑”驱严刑,《开皇律》初颁之诏中“先施法令,欲人无犯之心,国有常刑,诛而不怒”(43)的立法精神已被隋文帝的君主意志侵凌的荡然无存。
次之,《开皇律》的毁弃,还突出表现在对封建法律“治吏”功能的越法之用上。开皇十六年,合川仓少粟一案,经鞠,文帝仅“以为主典所窃”,即令有司“驰驿斩之”(44)。其治吏“用刑太急”(45),亦前史所鲜见。“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弛”(46),隋文帝越法治吏,势必引起开皇中以后隋律执行情况的恶化。开皇十七年,“听于诸司律外决杖属官诏”颁行之后,“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47)的法政意识在统治阶级中几成习尚,而臬司之“吏存苟免,罕闻宽惠”,缘上情而“乘时射利者”(48)一时纷起。《隋书·酷吏·厍狄士文传》记,“士文至州,发摘奸隐,长吏尺布升粟之赃,无所宽贷。得千余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岭南,亲戚相送,哭泣之声遍于州境。”隋文帝治吏,“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49)吏,居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之底层,汉以来,多指府、台及诸曹主文牍簿书之令史等杂差之员;衍至隋:“令史之任,文案烦屑,渐为卑冗,不参官品。”(50)然隋吏虽卑,作为封建政治运作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却依然不失其官民交接之关节的作用。是“治吏”之政乃是强化封建国家机器运转之效的举措,而令由喜怒,刑尚“惨急”(51),毁法而治吏的行径则不啻亦正是专制集权政治在吏治问题的典型表现。
复次,《开皇律》的毁弃,还在于将封建律法“治民”之刑推于极限,自毁“体国立法”之初衷而“天下懔懔焉”(52)。史称,开皇十七年以后,“是时帝每尚惨急,而奸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盗,人间强盗,亦往往而行。帝患之,问群臣断禁之法。杨素等未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诏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业,以赏纠人。时月之间,内外宁息。其后无赖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遗物于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大抵被陷者甚众。帝知之,乃命盗一钱已上皆弃市。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焉。”(53)至此,开皇三年,“以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而复修《开皇律》以“轻刑罚”(54)的开皇初刑政精神亦已荡然无存。
《开皇律》的毁弃,无论“廷杖”之酷,抑或“治吏”、“治民”之重,均体现为封建社会形态下君主之权对封建国家司法之权的侵凌。这种导源于“法自君出”的封建法本质的现象,其兴毁之间的关系亦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谈及中国古代专制政体与法制之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下,虽然愿意给自己戴上锁链,但却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凶暴。”(55)因之,我们可以看到,隋禅周后,新政权由于政治的需要,创立了与它结构需要相适应的律法和国家,《开皇律》有以服务于新建之隋;但是,由于它内在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倾向的本质规定,却使它不可避免地要走上与之结构稳定需要而悖逆的毁法之路,是《开皇律》的毁弃乃有其封建法通则的历史规定性。然而,任何一种有关“通则”的抽象认识,亦唯有置诸具体的历史之中才可能获得确切的历史性把握。《开皇律》的旋立旋毁有其具体的历史内容,揭示它有助于对“通则”的认识,试论于次。
首先,《开皇律》君定而君毁,当与隋文帝对中国传统法家关于刑法治国之思想的偏颇体认有密切之关系。如前述,《开皇律》衍至开皇十年前后开始逆转,而此一时期正值隋文帝平定三方、分裂突厥、灭陈统一南北,内靖诸王而制度粗定,政治与军事均取得极大成功之时期,抑其固有之专制集权之政治基因由隐在而转为现实之条件的成熟之期。是隋文帝在开皇中将更多的力量用于对内治理的政策运作之上。开皇九年二月,平陈战事甫定,四月,隋文帝即下诏曰:
丧乱以来,缅将十载,君无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溥,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朕为帝王,志存爱养,时有臻道,不敢宁息。内外职位,遐迩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轨不法,荡然俱尽。兵可助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刑。(56)
是年十二月,复下诏曰:
朕祗承天命,清荡万方。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浇浮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其时也。(57)
从开皇九年两道诏书所申之旨来看,隋文帝显然是准备进一步强化礼乐教化以助刑政来达到内治于国的政治目标。这里,“礼”非本文之范围,暂不论。仅就其礼刑并用的传统伦理政治思想来看,则隋文帝之思想显然又是建立在“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浇浮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的传统伦理纲常委地殆尽的认识之上的。此种认识大致贯穿隋文帝思想之前后,如仁寿二年闰十月“修定五礼诏”:
自区宇乱离,绵历年代,王道衰而变风作,微言绝百大义乖,与代推移,其敝日甚。
是年十二月“下诏数蜀王秀罪”亦曰:
自王道衰,人风薄,居上莫能公道以御物,为下必踵私法以希时。上下相蒙,君臣义失,义失则政乖,政乖则人困。
而仁寿四年七月临终“遗诏”则进一步明言:
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58)
隋文帝如上之认识,无非是一种是古非今的社会认识。换言之,这种在理论上认为世风不古、民心浇薄的社会认识,在中国“王霸道”杂用政治模式的规定下,则势必于治理的措施上为刑政治国一翼的力度的强化张开口子。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论及隋文帝开皇中隋律趋苛之政时曰:“隋文不知(笔者注:当训为“智”),而防之如仇,乃益以增民之陷溺”,复溯其认识之源曰:“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其说行而刑名威力之术进矣。”(59)概括王夫之之说,则隋文帝之社会认识,及由其导源而形成之刑政思想亦当接近于中国历史上,以“性恶”的认识为前提而主张严刑法治的商鞅、荀卿一派的法家思想。荀卿主张“性恶”,于《荀子·性恶》中曰:“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垂刑法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卿之前的商鞅于《商君书·开塞》更直陈其说,“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而内含法家思想之《管子·重令》,则径直将君主集权与重法严刑置为一谈,曰:“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于此不难看出,史论有“素不悦学”而“任智”,“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的隋文帝,在开皇中后自毁其法的行径,是与其是古非今的社会认识分不开的;而此认识于思想轨迹上又是非常切近中国古代历史上商荀一派的法家思想的,因之而有开皇中偏离“王霸道”杂用之范而耽于严刑一端的《开皇律》之废(60)是为其一。
次之,关于《开皇律》的毁弃,旧史多指论为隋文帝的性格作用,此论当亦不失微观考察的合理成分;然而,一旦将历史人物的性格作用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背景割裂开而作出此论时,则这种结论也就由“合理”走向了谬误,旧论之失亦即在此。
唐太宗李世民与群臣论及隋文帝时,曰:“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61),此论说明隋文帝有至察多疑之性格,并以此性格“意义”为中介而影响隋律之运行。
隋文帝的性格特征,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其政治品格的成因,则当存在于他禅周而立的历史行为之中。
隋文帝禅周虽不属一姓之传的“内禅”,然而,他的女儿即周宣帝的皇后;周宣帝死即为其子周静帝的母后,是隋文帝以当朝皇上“外公”的身份以行禅代,虽不属于“内禅”而有“内禅”之便,故李世民讥其为“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已含杨隋之立非英雄之业之讽。可见,隋文帝有“内禅”之便的立国之举,相较于马上得天下的英雄之业自然只是一种低姿态的“和平”方式;而与此方式相偕而来的便是一个新政权应有的政治、事功的缺失,以及朝廷上下大批存在的“二朝臣僚”,两者均从不同方面给隋文帝以压力,并缘此构成了隋文帝难以释怀的政治忧患情结。因此,禅代伊始,隋文帝一方面“推以赤心”,谋求政治向心力之强化;另一方面则通过律法修定,“刷新”旧政,建立新政权“仁德”形象,谋求更为宽阔的政治合作基础。然而,一经政权易手之动荡过去,而克定三方、北靖突厥、统一南北等事功的获得,专制集权政治基础形成之后;隋文帝治内之政应期而出,在“是古非今”认识的激荡之下而复炽了,以致“蓄疑御下”(62),严刑求治而废隋初律法宽平之精神。可见隋文帝至察多疑之性格至转化为“蓄疑御下”、严刑求治的政治品格,当与其特殊的政权建立背景有很大之关系。是为其二。
总之,“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63)。《开皇律》的毁弃,首义亦当求诸其封建法典与封建专制主义之冲突的内在本质,然亦不可忽略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关系,以上补充之论唯请方家正之。
注释:
①《隋书》卷25,《刑法志》。
②《资治通鉴》卷175,“宣帝太建十三年”。
③《读通鉴论》卷19,《隋文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⑤⑥⑦⑧⑨(12)《隋书》卷25,《刑法志》。
⑩(11)陈寅格:《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刑律》,中华书局1963年版。
(13)《资治通鉴》卷175,《宣帝太建十三年》。
(14)《旧唐书》卷50,《刑法志》。
(15)《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四库全书总目·〈唐律疏议〉提要》,转引自刘俊文《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
(17)(19)(20)(21)(22)(24)(30)(31)(32)(33)(34)(35)(36)(37)《隋书》卷25,《刑法志》。
(18)(23)《北史》卷10,《周本纪下》。
(25)(28)(29)《隋书》卷2,《高祖下》。
(26)(27)《隋书》卷51,《长孙览传》。
(38)参见《隋书》卷25,《刑法志》、《隋书·赵绰传》。
(39)(49)(54)《隋书》卷2,《高祖下》。
(40)(43)(44)(51)(52)(53)《隋书》卷25,《刑法志》。
(41)(42)《资治通鉴》卷177,“文帝开皇九年”。
(45)《隋书》卷2,《五行志上》。
(46)《潜夫论》。
(47)《资治通鉴》卷178,“文帝开皇十七年”。
(48)《隋书》卷73,《循吏传序》。
(50)《通典》卷21,《职官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
(55)《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56)(57)(58)《隋书》卷2,《高祖下》;另参见《全隋文》有关各条。
(59)《读通鉴论》卷20,《唐太宗》。
(60)另参见《隋书》卷73,《循吏传序》。
(61)《贞观政要·政事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62)《读通鉴论》卷19,《隋文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
(63)《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