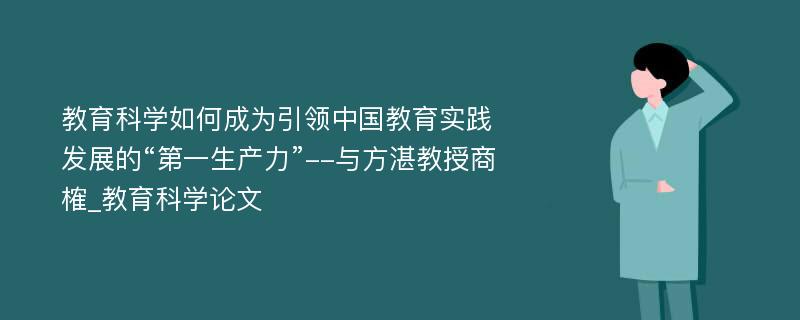
教育科学如何才能成为主导我国教育实践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兼与方展画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导论文,第一生产力论文,教授论文,我国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既把教育推上了社会的核心位置,又对教育科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科学技术已日益成为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教育实践界迫切希望教育科学也能够像自然科学对现代生产那样,给予及时、全面和有效的指导。然而目前在我国,教育科学能否从总体上承担起这一指导重任?教育科学如何才能成为主导我国教育实践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这是摆在教育界,尤其是教育理论界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我国关于应用性教育理论的诸种话语不同现象及其症结
其实,教育界早就对上述问题做过相关探索,突出表现在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关系的讨论上。针对有关教育理论脱离教育实践的指责,教育理论界主要从基础理论(或研究)、应用理论(或研究)分类的角度,来阐述不同性质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不同关系。强调基础理论(或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反对以“直接应用性”来作为衡量所有教育理论(尤其是教育基础理论)的惟一价值标准。方展画教授曾专门撰文论述了教育科学研究、教育基础研究、教育应用研究的含义以及与教育实践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与其他任何科学研究一样,教育科研是由教育的基础研究(或者说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和教育的应用研究所组成,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在性质上、功能上并不完全相同。……教育的基础研究,实际上是对教育本质、教育内在规律等的一种深刻的认识,是对教育现象或实践的一种理性的把握。它的性质是揭示教育的原理,在逻辑的层次上构建教育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的功能是增进人们对教育的完整理解,把握教育诸多要素之间的逻辑关联,解决对教育的认识问题。……教育应用研究是指应用教育基础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有关教育的基本原理或所形成的某种(些)基本理论来解决教育实践、教育改革、教育决策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这类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应用性,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教育的应用研究直接实现着为教育决策、教育改革服务的功能,这一功能能否得到有效发挥,首先取决于教育基础研究的进展与成果。但教育基础研究本身又与教育决策、教育改革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注:方展画:《重视基础研究,强化应用研究》,《教育研究》1999年第6期。)
以方教授为代表的以上论述无疑是较为明确、详细和系统的,然而来自教育实践界的指责至今仍“不绝于耳”。原因究竟何在?
如果我们对双方的观点加以仔细分析,则可发现:双方对应用性理论的解释存在分歧。理论界主要侧重从应用教育基础研究成果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实践界则强调理论对实践的直接现实作用,而不管该理论是教育基础理论还是教育应用理论,甚至是方教授上述定义中未能囊括的教育理论。比如,类似“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学”这样的教育科学群中的学科理论,恐怕人们不会对其自身所具的较强的应用性感到怀疑;然而按照方教授的定义,既无法把这样的学科研究归入教育基础研究(因为这样的学科研究所揭示的规律和方法可以直接为实践界所用),也无法将其归入教育应用研究(因为它们分别是采用非教育学科的理论框架来观照教育中的作为“个体”的人,探讨如何运用非教育学科的方法来分析教育活动)。
这种话语不同现象不仅在于理论界与实践界之间,而且存在于理论界自身。比如:叶澜教授认为应用理论(或研究)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使人们获得一套把理论(注:应指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行为的指示或工具”。(注:瞿葆奎主编:《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1978-1995),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P992。)而陈桂生教授则认为应用研究成果包括经验总结、调查报告(注:瞿葆奎主编:《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1978-1995),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P992。),似乎与叶澜教授的解释有实质性的不同。因为经验总结、调查报告这类具一定理性层次的成果可以主要从甚至完全从实践中得出。
由于理论相对于具体实践者的有用性既与理论的性质、深度等因素有关,也与实践主体自身的需要和理论素养等有关,因而教育基础研究中某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只要与实践主体情况相适应,也许就不需要应用研究这一中介,何况作为教育科学群中一分子的“教育心理学”本身又属心理学的应用学科。“教育统计学”亦可类推。
因此,以上有关应用性教育理论的多重话语不同的问题之症结,主要在于目前教育实践中客观存在着两种应用研究层次的理论指导模式:1.直接来源于教育基础研究成果运用的指导模式(即后于并依赖于教育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模式,方教授所定义的教育应用研究与此一致)。2.直接来源于教育实践新探索的总结提升并为时空范围更广的实践提供指导,同时也为教育基础研究提供新的源泉、新的课题和新的发展的指导模式(即先于相应的教育基础研究出现,并来源于单纯经验性探索的教育应用研究模式)。然而,教育理论界却试图只用基础研究成果的运用模式来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偏好恐怕与对以下两个问题的看法有关。
二、如何看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象
现代科学技术已日益成为现代生产发展的先导和基础,日益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并对现代生产力发展起着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受现代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现代生产中第一生产力的鼓舞和启发,一些教育理论工作者也相应将教育科学研究(理论)的结构划分为基础研究(理论)和应用研究(理论)这两大门类。但他们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门类结构观照分析教育科学的结构时,十分关注“技术已日益依赖于科学理论的指导,技术本身越来越带有实验科学的性质”(注:李继宗主编:《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P34、P17。)的这个现代科学技术的特征,而忽视了“技术日趋科学化”(注:李继宗主编:《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P34、P17。)的两个特殊条件:“科学的深入发展和技术的高、精、尖化”(注:李继宗主编:《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P34、P17。)。因而他们在分析教育基础研究(理论)、教育应用研究(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现存关系时,往往倾向于只强调基础研究(理论)对应用研究(理论)的根源性和基础性。
其实,即使在“科学发现往往超前于技术发明,技术发明又往往超前于实际的生产,……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已共同成为制导和控制生产发展趋向和速度的关键”(注:洪晓楠等编著:《自然科学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P25。)之今天,在相对浅表的科学发展层次,技术并非高、精、尖化的传统产业,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关系也可能存在这样多重复杂的因果关系:从生产经验中总结出新的技术知识,技术一方面指导更广泛的生产实践,另一方面或者仅作为已有科学结论的新例证,或者上升为科学,科学又提升技术,从而更有效地指导生产实践。如果用科学、技术、生产的实际运动方向来说明,则三者关系可描述为:“以科学→技术→生产为主,以生产→技术→科学为辅”(注:洪晓楠等编著:《自然科学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P25。)。因此,即使在现代,也不能否认导源于生产实践的技术在一定条件下之存在。
当我们立足于现代社会这个存在,对科学、技术、生产关系作静态分析时,绝不能忽视对其他历史的动态考察,尤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领先、主导和基础地位并非有史以来始终如此。
科学技术并非有史以来就是社会生产中的第一生产力,这不仅可从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在古代并不存在的事实、从自然科学结构及其分类的演变过程得到旁证,也可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演变中觅得踪迹。科学与技术在相互关系上存在发展的阶段性。“19世纪下半叶以前,由于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比较落后,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上升为科学的过程比较缓慢。因此,科学与技术在发展中几乎是相互脱节的。有时,技术上出现了重大革新,但这种革新却不能及时地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比如,蒸汽机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达到实用阶段,而作为其理论根据的热力学理论却直到19世纪中叶才建立起来。相反,有时科学上作出了重大发现,但技术上却没有条件加以运用,甚至不能被人们所理解与接受。比如,麦克斯韦早就预言电磁波的存在,随后又被赫兹的实验所证实,而电磁波被用来传送电讯却经历了20年之久。进入20世纪之后,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依赖才日趋明显。于是,两者相互依存,彼此促进,关系越来越密切,呈现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注:李继宗主编:《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P34、P17。)。
三、如何判断教育科学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
如果我们循着前述那些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类比”和“移植”思路,用上述标志、标准来分别观照、衡量教育科学,则不难发现,目前我国的教育科学远未达到相当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就总体而言尚不具备主导我国教育实践的能力。
虽然从方教授为代表的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文字描述上看,我国的教育基础理论(或研究)与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教育应用理论(或研究)与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科学及应用科学在认识或改造世界的意义上没有本质的差异,但我国的教育基础理论(或研究)、教育应用理论(或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实“盛名难副”。由于教育科学的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的独特复杂性,目前,在我国教育领域,“科学”[相当于实然的教育基础理论(或研究)]转化为“技术”[相当于实然的教育应用理论(或研究)],以及“技术”上升为“科学”的过程比较缓慢,因而“科学”与“技术”在发展中存在比较严重的相互脱节现象。有时,教育基础研究提出了领先于教育实践的导向性理论,但总体上却缺乏技术实现的条件。比如,针对我国教育过分强调适应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学者提示人们注意“教育的超越本质”;针对把教学过程仅仅视作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的传统看法,有学者提出:“教学过程也是学生生命活动的过程”,要让“课堂教学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但由于相应的应用研究跟不上,这些充满睿智的思想目前就总体而言只能停留在一般呼吁上,教育实践界基本上仍然“我行我素”。相反,有时来自实践的教育应用研究出现重大革新,但这种“技术”上的革新却不能及时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比如,发端于教育实践界的素质教育思潮,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种最初诞生于教育教学一线的新教育改革思想,已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在政府的倡导下,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富有新意的素质教育实践模式(“技术”)。但毋庸讳言,这种来自经验探索的新“技术”,其“理论根基尚十分薄弱”(注:康宁:《试论素质教育的政策导向》,《教育研究》1999年第4期。)。
当我们把视角进一步投向新“技术”的来源时,又可发现:新“技术”并非主要导源于系统、综合的教育基础研究,“科学”与“实践探索”对新“技术”的贡献率几乎不分上下(注:这里的新“技术”既包含先于“科学”出现并来源于单纯经验性探索的“技术”,也包含后于“科学”出现的“技术”)。江苏泰兴洋思中学“面向全体学生,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全面提高课程实施水平”的经验,主要是蔡校长率全校师生通过艰苦探索而得。虽然具备较高的实践价值,然而,在教育基础理论上却算不上是创新,因为这类“技术”本可以通过已有教育基础理论成果的运用去独立推导出来。这种状况也可用方展画教授关于教育科研应用过程的描述框架来作如下刻画:本可在构想、实施和结果三个环节全程运用教育基础研究成果,但实际上却直到结果物化这一环节才将教育基础研究成果加以运用。可以这样认为,这类“技术”虽然在相应的“科学”之后出现,但却主要不是在该“科学”的运用中,而是在与该“科学”相对脱离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这种本应导源于已有“科学”的新“技术”,却实际主要导源于实践探索的事例,在目前教育领域几乎“俯拾即是”(这恐怕与教育中“科学”发展不够深入,“技术”尚未高、精、尖化有关),但在已深入发展的当代自然科学那里(尤其是高、精、尖领域)几乎不可能发生。
由此看来,目前我国教育科学只能被认作处在相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前现代”的发展阶段。方展画教授所描述的教育基础研究、教育应用研究的定义及其与教育决策、教育改革实践的关系,与其说是现状的真实写照,倒不如说更象未来的憧憬图。相对于现代科学技术而言,教育基础研究、教育应用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尊称”,我国的教育科学对教育实践,目前尚不能发挥人们所期盼的类似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那种作用。这一点可从世界范围教育科学的发展状况得到佐证:尽管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已有300余年历史,但世界上一些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著名分类中“均忽略了教育科学”(注:瞿葆奎、唐莹:《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载《教育社会学》(吴康宁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版。)。
如果我们此时运用上述认识去反思、去重新审视教育理论界关于不同性质理论与不同实践具不同关系的观点,则可发现该解释之所以不能令实践界满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解释者没有注意全面客观地认识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象,疏忽了该现象得以存在的相关条件,且都只从静止而非发展的角度看待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并将其不恰当地类比、移植到尚处“前现代”阶段的教育科学上。因而不仅混淆了自然科学的“现在时”和“过去时”,也混淆了教育科学的“现在时”和“将来时”。“不同性质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具有不同的关系”这句话形式上并无不妥,问题出在对“不同性质的教育理论”及其与实践关系的理解、认定和相应解释上。如果相对现代科学技术而言,目前我国的教育基础研究、教育应用研究尚有“尊称”之嫌的话,则其与实践的前述关系就难以“名副其实”了。因此,任何不关注适用条件和范围就用自然科学的结构和功能来类比解释教育科学的结构和功能的做法,其有效性是很值得怀疑的。任何试图用教育科学的将来情形解释教育现状的论述难免不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四、教育科学怎样才能成为教育实践的“第一生产力”
如上所述,教育领域中“科学”与“技术”在发展上相互脱节,是处于“前现代”阶段(相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教育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因而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亦是该阶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问题在于怎样使教育科学由“前现代”向“现代”发展,尽快从“现在时”转变为“将来时”。这涉及教育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重视教育的基础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强化教育的应用研究”(注:方展画:《重视基础研究,强化应用研究》,《教育研究》1999年第6期。)。这句话固然不错,然而未免失之于“一般化”,未反映出教育科学研究的特殊需要。笔者认为,教育科学要能成为主导我国教育实践的“第一生产力”,就必须提高“第一生产力”所必须具备的“科学性”。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具有长期的思辩传统,而最缺的是提升学科科学性所必需之“实证研究”。因此,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应在不放弃价值、理想的前提下,把“实证研究”放到突出显要的位置。这是教育科学能发展为主导我国教育实践的“第一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这也是自然科学发展史所昭示的成功之路。“全部自然科学……的内容,都是由科学实验得出来而不是由脑子臆造出来的。……科学实验是理论的源泉,是自然科学的根本”(注:张文裕:《燕京·剑桥·普林斯顿》,载《神奇的发现》(人与科学卷)(一),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1月版,P313。)。没有系统的观察、可验证的科学实验以及严密的逻辑思维,科学认识只能停留在现象的描述、经验的总结和猜测性的思辩阶段,其认识形式只能主要是直觉的、零散的、个体的,从而自然科学的大厦也就建立不起来。正是通过科学实验,才积累了有关自然界的许多事实和规律;再经过科学家的思维整合,才建立起了经过反复验证,反映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体系;进而人们才得以运用这些规律去改造自然,发挥自然科学的“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自然科学格“物”、教育科学格“人”,就完全拒绝自然科学的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昭示。我们也不能因为实验教育学派的自然科学化偏向,就将“小孩同洗澡水一起倒掉”。
加强实证研究是夯实教育科学大厦基础的必然要求。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撑,教育科学研究就难以从研究主体个人的小天地中走出来;其研究成果就难以从个人的“构念”转化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行动指南。如果我们在建设教育科学大厦时,“宏大叙事”方式难以有重大突破,为何不能改用实证研究方式,一砖一瓦地累积,积小胜为大胜呢?
总之,只要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坚持“求真”与“求善”的沟通与统一,强化实证研究材料点滴而广泛的积累,并在适当时候对丰富的实证材料进行抽象整合,则总有一天,我国的教育基础研究、教育应用研究相对于现代科学技术能“名副其实”,教育科学能够成为推动我国教育实践发展的主导力量。我们盼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