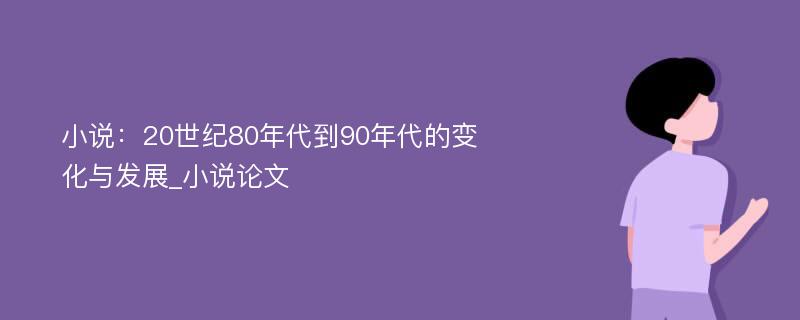
长篇小说:80年代到90年代的变化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长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篇小说的篇幅和容量,决定了它往往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创作与成就之代表的特殊地位。譬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这些标志性的作品,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前十七年的一个具综合参考价值的归纳和总结。而新时期的开始,由于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待收拾旧山河从头越的特色,因而失去了连贯性的文学短期内很难产生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故此,体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创作的特征,代表那一阶段文学成就的只能是对生活的感悟、捕捉和表现更为灵敏迅捷的中短篇小说。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花园街五号》、《新星》、《古船》、《活动变人形》、《金牧场》、《浮躁》、《平凡的世界》、《洗澡》、《玫瑰门》等大批作品的涌现,长篇小说的影响渐渐超越已经成熟定型的中篇小说,以及开始转向追求灵巧精致的短篇小说。有了这样的基础,加上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大件”的指示给了众多创作者和组织者特殊的动力,80年代出现长篇小说“大生产”式的创作热潮,也就成为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与80年代的长篇小说,固然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也就不乏某些相似、相近甚至相同的特点,如在《桥》、《绿色的太阳》这些90年代的“改革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到《花园街五号》、《男人的风格》的影子;而《活动变人形》一改长篇小说表现大矛盾、描写大冲突以概括和反映某个时代社会缩影的“规则”,将平凡人生、家庭琐事、小矛盾、小冲突引进长篇小说的表现视域,对90年代长篇小说的影响,更是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但正如“江山代有才人出”、以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或雅或俗的名句所言,“变”是恒数,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变”的制约,都是在“变”之中得以进步(进化)和发展,受到主、客观世界双重影响的长篇小说,更是不能例外。跟80年代的长篇小说相比,90年代的长篇小说,由于创作者以及社会生活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因而,从内容到形式,从描述视点到表现层面,从题材选择到叙述方式……都有了极为明显的变化。其中,最具普遍性的,似乎是以下的几个方面:
从“泛政治化”到世俗化、故事化
当代中国由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一直是整个社会的中心话题,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路线是纲,纲举目张”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再到“革命、组织、斗争、思想、觉悟、原则……”一系列政治话语在社会生活中普遍运用,无不反映出社会生活与文化都极为明显的突现泛政治化的强烈色彩。这样,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表现习惯乃至遣词造句,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深刻而又全面的影响。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曾被喻作“阶级斗争风雨表”的文学,自然也就跳不出“泛政治化”的“围城”。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是革命斗争故事,如《红岩》、《红日》、《红旗谱》、《小城春秋》、《野火春风斗古城》……二是社会政治运动的再现,如《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艳阳天》等,就十分明显地反映出文学自觉服从服务于政治的追求。
新时期开始的文学,作为政治反思的先行者,以揭露“红色恐怖”的罪恶,控诉政治高压,激发民众痛恨极左思潮为己任,因而,“政治”的色彩比“文革”及“文革”前的文学,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从《班主任》、《伤痕》等作品中感受到的政治热情无疑要远远强于艺术的品味和欣赏。
80年代的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基础起步,“文革”前的样本及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政治热情,还有时代面临的迫切任务都决定了不可能超越“泛政治化”的创作定势。故此,从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芙蓉镇》、《将军吟》、《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到第二届获奖作品《沉重的翅膀》、《黄河东流去》,再到第三届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都市风流》、《第二个太阳》,以及虽然由于多种原因没有获取茅盾文学奖,但反映出那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特色、创作追求和创作成就的《新星》、《古船》、《洗澡》、《金牧场》等,都不难看出80年代的长篇小说,由“政治”的视角切入,表现意识形态层面思考的创作追求。
如果说《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基本还是沿袭再现某一场社会政治运动的创作,《沉重的翅膀》表现了改革的艰难,与革命斗争故事异曲同工;那么到了《新星》、《古船》、《洗澡》、《金牧场》……则有了更大的发展。《新星》关于领导干部素质的描述,《古船》对某一段历史及由历史体现的“革命”和“革命”方式、手段、目的的反思,《洗澡》对政治运动正、负面效果的表现等,就“泛政治化”的创作而言,应该说都具有很大的拓展意义。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创作已经达到比较高的层面,就“政治”而言,已难以再深入揭示更尖锐更敏感的话题,也就不可能在同样层面的创作中有更大的超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90年代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审美趋向都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对于文学的理解,认识和要求自然而然发生嬗变。这一切必然会影响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中,“泛政治化”的创作固然还在继续,但比较多的创作已经表现出向世俗化、故事化转变的明确追求。从90年代初的《米》(苏童)、《呼喊与细雨》(余华)、《废都》(贾平凹),到90年代中后期的《长恨歌》(王安忆)、《尘埃落定》(阿来)、《第二十幕》(周大新)、《红瓦》(曹文轩)……无不表现出这一点。
世俗化创作跟泛政治化创作的明显不同,就在于后者比较多地关注“政治”对人的制约与影响,描写的重心也比较多地放在或是揭示人在政治风浪中的起伏,或是反映政治运动的过程,也就是比较多的表现“政治人生”,《洗澡》、《古船》、《新星》都是如此;而前者则更多的描写跟“官场政治”有一定距离的世俗人生,像《米》叙述一个流浪难民由米店老板的女婿到黑社会头目,再到黑社会追杀对象的经历,《长恨歌》表现了一个平凡的女性从40年代末以来长达数十年的情感追求的多重坎坷与挫折。
由于世俗化的创作多以平凡人生为表现对象,不着重历史的“再现”,因而,虚拟性、故事化的色彩要远远强于“泛政治化”的创作。而正是由于世俗化的创作不着重“再现”历史,故此,历史在世俗化的创作中往往只是一种背景,重要的是故事本身而不是历史应该是一种什么模样。此外,由于世俗化的创作更多地关注世俗人生,所以人的好坏善恶,也就更多地从伦理的角度去评价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评价。
这一切,都表现出追求世俗化、故事化的创作者有意识地隐藏和消解“作家即思想者、导师、人生审判者、是非善恶划分人”之类的身分、角色,更多地承担讲故事的任务。他们一般只将故事提供给读者,往往不作相应的限定,有意识地让读者自己去阅读、欣赏和品味。故此,世俗化、故事化的创作跟“泛政治化”的创作相比,一般说来要平和一些,也松驰一些,还有就是民间色彩要强于官方代言人的色彩,民间话语也多于政治话语。像《第二十幕》在一定的层面上可以说表现了中国这一百年来的发展形态,包容的社会历史内容无疑是十分丰富的,而作品只是通过描述尚家几代人为发展“霸王绸”的奋斗历程,表现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艰难。历史以及关于历史的评价蕴含于故事之中,作者并没有站出来进行意识形态的解释。
从短焦距到长焦距
借用“焦距”这一光学概念或许不够准确,但从作家与作品之距离的角度出发,去分辨80年代与90年代长篇小说的不同,还是比较明显的。
简单地说,80年代长篇小说的作者与自己的表现对象距离比较近,而90年代长篇小说的作者与自己的表现对象距离则稍远一些。这一方面反映于80年代的长篇小说,不论取材历史还是现实,由于创作者社会政治热情比较高涨,在努力发现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十分积极地提出医治社会弊病的处方,不满足于社会人生观察者、叙述者的角色定位,为此不仅往往压制不住表述自己对历史、对社会、对现实和人生的理解、认识之欲望,而且往往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地提出应该怎么样而不应该怎么样。因而,作家在作品中的存在普遍都比较明显。由“新星”李向南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固然不难看到作者的政治理念,其中也包括“人生应该追求什么”的显示;而通过李向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则表达了作者“要想解决当下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极需要李向南式的领导干部”的呼喊。《古船》对历史的反思,的确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作品中多次出现《共产党宣言》,更是表现了作者关于革命与革命目的的理解,以及迫切将认识与理解比较直接、比较明确地告诉读者的欲望。另一方面则表现了80年代的长篇小说的确是比较多地从“政治”的视角出发去确立主题和选择表现对象。为此,80年代的长篇小说往往是以迫近的观点,比较集中地由呼喊改革,到反映社会改革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
到了90年代,我们从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中,就很难再看到《新星》和《古船》那样的表述,也很难再看到作者于作品中的强力突现。题材选择视点的不同,自然是原因之一。80年代的长篇小说,普遍将描写视点对准当下现实的热点问题,如《新星》就是当时众多新干部纷纷走上领导岗位,而新老干部交替又难以避免地出现一些矛盾的直接反映;《古船》所表现的也是社会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后面临的“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及资本所有者”、“均富还是均贫”、“斗争是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唯一方式”……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关于文学的一些论争,如“文学首先是文学”、“小说即‘小’说”,还有“将历史心灵化”等,不可避免会给长篇小说的创作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明显地于题材的选择和切入视点中体现,也就是对“现实感”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而正是由于认识到文学作品的“现实价值”并非只是社会当下“问题”的反映,“矛盾”也不仅仅是一些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因而,在进入描写时自然而然会拉开一定的距离。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一般不再像80年代那样比较普遍地采用“报告文学化”、焦点新闻式的题材选择,不再是社会上出现个体经营者就写个体经营者,“官倒现象”严重就写“官倒”,对社会改革有争论就写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在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确立上,思考与熔铸内涵的兴趣要远远强于搜寻“现象”的所谓“敏感”显示。
具体表现为,一是将视点更多地对准“历史”。其中,像《白鹿原》(陈忠实)那样的创作,固然是努力由描述历史的过程表现出历史的真实形态,而像《米》以及《清水幻象》(革非)那样的创作,“历史”是虚拟的,作者并不想告诉读者“历史”的本来形态,只是借用那么一个背景讲述一段人生的故事。既然是讲述他人的故事,作者与故事及故事中的人生自然存在一定的距离,也就用不着作者对是非、善恶、好坏、美丑进行更具体更直接的评判,也就用不着十分迫近地描写生活表现人生。这样的创作追求,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如吉成的《血印》、潘军的《风》、范小青的《老岸》、田中禾的《城廓》等,虽然描述角度并不相同,背景选择也各有各的思路,但虚拟性、故事化、距离感……都是相同的。
为此,90年代的不少长篇小说,不像80年代的基本都是自以为神圣的一脸严肃,在认真思考社会历史人生的同时,由调侃、自嘲、讽喻等似乎不那么严肃的表述,适当地融入“游戏”的成分与色彩。
其二则是由80年代那种由具体“问题”切入转为思考带一定抽象意蕴的矛盾。关于生存以及由生存衍化的多种矛盾,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有多种角度的切入和描述。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对于生命与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无疑是比较深入的。而阿来的《尘埃落定》,就根本来说,也是对生存、生存选择和生存竞争的描述。《第二十幕》描述出中国民族工业生存与发展都十分艰难的同时,最为感动读者的还是尚达志追求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坚韧、顽强。《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曲折命运固然是受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可在相当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生的无奈才是人类无法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此外,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阮海彪的《欲是不灭的》、余华的《呼喊与细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创作,都表现出探寻抽象意蕴的努力。
长篇小说的创作由“近距离”到“远距离”有其社会原因,当社会矛盾从简单变为复杂,从相对单一变为多样及多样纠缠时,力求比较全面,比较深入地描述、表现社会、历史与人生的长篇小说,要想追求纵深感和更开阔的展示空间,拉开一点距离观察、思考、认识和描写表现对象,似乎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从相对单一到相对丰富
以《洗澡》、《古船》、《活动变人形》、《金牧场》等为代表,80年代的长篇小说的确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整体去看,形式的相对单一,基本都是由“问题”入手的描述视点,应该说是80年代长篇小说的一个明显的不足。
跳出“泛政治化”创作的“围城”,摆脱用故事演绎“问题”的创作定势,90年代的长篇小说显得相对自由,不再那么拘谨。描述层面大大拓展,几乎没有题材的“禁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作者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自由王国”。
80年代的长篇小说,除了极个别的创作,如张承志的《金牧场》,铁凝的《玫瑰门》,贾平凹的《商州》等之外,几乎都是围绕某一矛盾组织人物和故事进行单线叙述,而作者又比较多地采用全知全能视角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长篇小说的叙述角度、叙述方式与手段则要丰富得多。如吉成的《血印》,由郭一民、毛牛、英子三个人物表现“犹豫和矛盾”、“莽撞和行动”以及“跟着感觉走”这三种意象;李锐的《万里无云》以多重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老城的《魔界》通过“记者”、“向导”、“屠家三少”的三个视角描述屠家三少的经历以及战争是如何改变人性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将“词典”的形式引进长篇小说的创作,而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在先写死亡最后才写出生的叙述中,表现出了对结构的精心考虑与安排。此外,阿来的《尘埃落定》,以一个“白痴”的视角去描述带相当封闭性的部落人生,在较好表现生活原始形态的同时,也由视角的独特而强化艺术的感染力。
这一切,显示出90年代的长篇小说作者,在重视开拓表现视域的同时,结构意识和形式感也得到了很大的强化。而正是有了这两点,使得90年代的长篇小说变得颇为复杂和丰富。80年代的长篇小说虽有描述角度和视点的变化,但基本上可以用“社会小说”、“社会问题小说”加以概括,也还可以用“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之类的概念去划分。而90年代的长篇小说已很难再套用这些概念。由“外”向“内”选择题材,造成了题材的模糊性,使之不易用某一题材概念去界定作品,像《日光流年》描述“三姓村”几代人为活过40岁奋斗不息,就不好明确地说那是一个什么题材,阿来的《尘埃落定》,大部分表现对象的社会身分是少数民族,但它跟传统意义的“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又明显见出区别和不同,《白鹿原》的主要描写对象是农民,但又难以将它圈定为“农业题材”。此外,胡小胡的《太阳雪》、肖克凡的《原址》、刘立中的《二十一个半》写到了国营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乔良的《末日之门》、黄国荣的《兵谣》主角是军人,但这些作品都不同于80年代,更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工业题材”、“军事题材”的创作。
正是如此,90年代长篇小说这个大家族,在保留了“历史小说”、“社会问题小说”等基本成员的同时,又增多了《白鹿原》、《缱绻与决绝》(赵德发)那样的“家族小说”,《私人生活》(陈染)、《一个人的战争》(林白)那样的“女性小说”,《九月寓言》(张炜)、《故乡面和花朵》那样的“文化小说”,《皇城旧事》(袁一强)、《左邻右舍》(姜贻斌)那样的“市民小说”,还有《弑父》(曾维浩)、《日光流年》、《返祖》(童天一)那样的“探索小说”。此外,像王小波、王朔那种带有明显个人独特性的小说,无疑也是90年代的长篇小说显得比较丰富的一个重要因素。
简单地说,90年代的长篇小说跟80年代相比,文化探寻的兴趣要强于图解政治概念的热情,从《白鹿原》、《九月寓言》、《第二十幕》、《长恨歌》、《尘埃落定》,到《女巫》(竹林)、《清水幻象》、《日光流年》,再到《高老庄》(贾平凹)、《故乡面和花朵》,还有《羊的门》(李佩甫)等,文化的内蕴都是比较丰实的。此外,形式拓展、创新的自觉,尤其是以个人的视角代替集团、集体的视角,不仅使90年代的长篇小说大大拓展表现视域,增进了艺术个性的自觉追求,而且,众多创作者对长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的驾驭,也更为熟练和自如。进步、提高,变化、发展,都相当显著,但在如何更好地处理个人艺术追求与社会生活内容相融合,历史和现实相沟通,探索、实践跟大众欣赏相一致等问题上,都还有许多需要创作者进一步加以努力解决的地方。否则,虽然已具备一定的基础,但要想在新世纪之初就实现长篇小说真正意义的繁荣,并适应市场化所形成的压力,似乎还不大可能。
标签:小说论文; 第二十幕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活动变人形论文; 故乡面和花朵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尘埃落定论文; 洗澡论文; 日光流年论文; 长恨歌论文; 金牧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