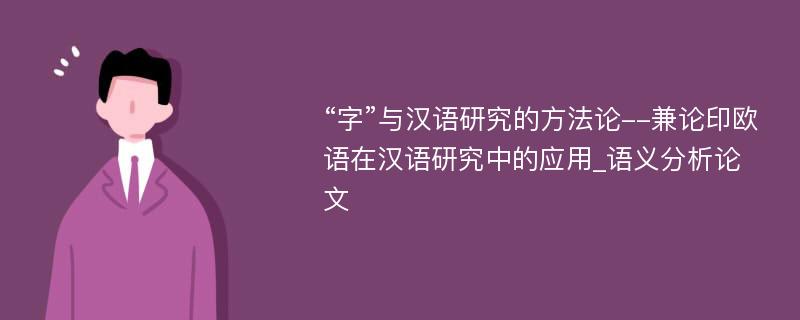
“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兼评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方法论论文,印欧论文,眼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义型语言和语法型语言在结构原则上的差异,我们曾进行过一些具体的讨论(徐通锵,1991),但要真正弄清楚每一种类型的语言结构,还需要弄清楚语言结构单位的性质,因为它凝聚着语言结构的基本特点。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印欧系语言是语法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不同语言之间虽然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普遍特征,但基本结构单位不能“张冠李戴”。近百年来的汉语研究,特别是其中的语法研究,把“字”逐出语言而代之以词和语素,这在方法论上无异于“张冠李戴”,使汉语的研究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印欧语的眼光”。要摆脱这种“眼光”的束缚,还得从“字”开始,研究它与语言结构的关系,就汉语论汉语,从中总结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以便为汉语的研究探索一条新的途径。
一、“字”和汉语结构的基础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一种语言如何将现实编成“码”,使之成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这与该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有关。印欧语社团的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它的基本精神是抽象和推导,采用下定义的方法把一个个概念说清楚。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大体的情况是:词对应于概念,句子对应于判断;概念要接受判断规则的支配,与之相应,词的结构要受特定句法规则的制约,具有能机械地适应句法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机制,即有特定的形式标志去表示结构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推理由于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出新判断(结论)的过程,语言编码的规则可能与它的关系远一点,而篇章结构的特点则与它的关系较为密切。
把印欧语的结构基础与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联系起来考察,人们可能不以为然,但只要看一看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论断的根据。现在流行的语法理论首先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建立起来的,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语法理论对后世语法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为什么是哲学家首先对语言研究感兴趣?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与特定的编码视角、编码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希腊语有丰富的形态变化,亚里斯多德根据这种语言的结构特点把现实分为十大范畴:实体(substance)、性质、数量、关系、地点、状态、情景、动作、被动、时间,其中“实体”是本质,其他九个范畴是偶有的属性(accidents),是用来表述实体的。在逻辑判断的结构中,实体最主要的特征是主体(subject),从逻辑上说就是主词(subject),别的偶有性范畴都是表述这个主词的,因而是它的宾词(predicate)。句子的结构规则和逻辑判断相对应,主词在语法中的反映就是主语(subject),能充当主语的词是体词(subsantive word)或名词;宾词在语法中的反映就是谓语(predicate),能充当谓语的词是动词(包括后来分出来的形容词);主语和谓语之间由一致关系相联系。这一逻辑理论体系以希腊语的结构为根据,而它又反过来成为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的基础。有人说,亚里斯多德如果说的是另一种不同于希腊语结构的语言,他就会创立另一套逻辑理论体系,这很有道理。Lyons(1979,270-274,334-344)曾对上述问题进行过具体的分析,读者可以参看。总之,这一理论体系抓住了印欧系语言编码机制的核心,因而它的基本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一致关系相联系的“主语—谓语”结构是这一语法理论体系的“纲”,构成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词的结构和功能都只是这个“纲”上的“目”,一切特点都受这个“纲”的控制。比方说,词的句法活动范围与句法结构位置存在着规律性的联系,因而功能单纯,可以据此进行词类的划分(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是名词,谓语位置上的是动词,定语位置上的是形容词,等等);由于一致关系的要求,词的结构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一套能随句法结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形态体系和词根加前、后缀构词的派生法构词体系(徐通锵,1991,56-59)。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句子是一种封闭性的结构,只要是一致关系所联系的主谓结构就是一个句子;句法结构单位的语法特征突出,无论是构词、变词还是造句,都可以用一定的语法规则加以控制。
汉语的编码机制与印欧系语言不同,因为汉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印欧语社团那种以概念、判断、推理为基本形式的三段论,而是一种“比类取象”的过程。“象”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哲学概念,指现实现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传·系辞上》)。每一种“象”都同某一类实体相联系,既表征实体本身的特征,也表征实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并通过关系来确定实体的性质。解释“象”的方法多取定义式的说明,如“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卑而大,扈”(《尔雅·释山》),而解释“象”与“象”之间的关系大多不用判断性的定义,不用推导,而用比喻,一种“象”通过与另一种差别很大的“象”的比较,找出共性,把握实质,即在不说出“象”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的情况下去把握“象”的本质,古人所说的“援物比类”就包含这种意思(王前,刘庚祥,1993)。如果以印欧语社团的思维形式为参照点,那么汉语的“象”大体上相当于概念,而“援物比类”的“比类”则相当于推理;这里没有与判断相当的思维单位,这可能是汉语的句子结构根本不同于印欧语句子的结构的一个深层原因。下面为了便于理解和行文,“象”仍以概念名之。以这种思维形式为编码的基础,汉语的结构基础自然会产生一系列不同于印欧语结构的特点。和“象”相对应的语言形式是“字”,和“比类”的思维形式相对应的是“因字而成句”(《文心雕龙》)的句。由于汉语中没有相当于印欧语的“判断”那一级的思维形式,因而在“因字而成句”时没有固定的结构模式的限制,可以自由地、开放性地表述所要表达的意思,使句子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特点,不象印欧系语言的句子必须限制在一致关系的框架之内。
“字”是汉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构单位,它与印欧系语言的“词”不同,具有自己一系列特有的特点。这可以概括为:结构简明,语法功能模糊,表义性突出。“字”的结构简单而明确,是一个以“1”为基础的“1×1=1”的层级体系,或者简单地说,它是表达一个概念(意义单位)的一个音节,形成“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的结构格局(徐通锵,1991)。这是汉语的结构基础,各个结构层面(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的结构特征都交汇于此,因而每一个层面的研究都得以“字”为基础。正由于此,“字”的含义广泛,所指模糊而不定,既可以指它的书写形体(如“说文解字”),也可以指一个音节(“吐字清楚”“字正腔圆”),还可以指音义结合的语言结构单位(如《文心雕龙》的“因字而成句,积句而成章”等),甚至还可以兼指以上各项内容。总之,“字”在它的简单的结构中隐含着复杂的内容,过去把它仅仅看成为一种文字单位是没有根据的。其次,作为语言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它缺乏印欧语的“词”那样的语法特征,既没有和句法结构位置的固定性联系,也没有表示语法功能的形态性标记,因而其语法功能模糊而隐蔽,无法根据特定的句法模式进行功能性的分类。例如“图”字,根据《汉语大字典》提供的线索,它有12个义项,其中有些义项的功能相当于印欧语的名词(地图、版图),有些相当于动词(绘画、描绘;思虑、谋划等),有的相当于形容词(图片、图像)。应该把“图”归入哪一个词类?很难说。汉语的词类问题所以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第三,和“语法功能模糊”这一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字”有顽强的表义性,这恐怕是“字”的一种本质特点,是语义型语言的一种内在结构基础。这一点人们颇多疑虑,需要在这里进行一些重点的分析。
“字”的表义性特征以往多注意形声字之类的结构,缺乏语言的分析,这或许是把“字”归结为文字问题而产生的一种不良结果。形声字代替假借字而成为汉语最重要的一种书写形式,固然可以从一个侧而反映“字”的表义性的语言特点,不过它究竟是一个文字问题,不宜作为根据来证明“字”的表义性。汉语中借字(借词)的命运与印欧语系语言的借词很不一样,可以从侧面说明“字”的表义性特点。
借词是音、义都借自外语的词,是两种语言相互接触的产物。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大量新事物和新概念,表达这些事物和概念的外语词也渗入汉语,这样就发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的碰撞和矛盾。汉语一直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对待外来词的“入侵”,尽可能采用意译法,只借用其概念而扬弃它的语音构造和语素组合成词的那种语法构词规则,坚持“字”的表义性;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意译化方法,就暂时采取音译,而后再换之以意译,象telephone由“德律风”而改为“电话”,microphone由“麦克风”而到“扩音器”,band由“版克”到“银行”,cement由“门汀、士敏土”而“水泥”,piano由“披亚诺”而“钢琴”等等,都是先音译后意译的具体例子。《辞源》出版于1915年,吸收西方语言的外语词计2431条;《辞海》出版于1937年,吸收外语词计12879条。根据耿军(1990)的统计,大体情况如下:
《辞源》
借词 305 12.56%
专词1187 48.82%
意译词
939 38.62%
《辞海》
借词521840.51%
意译词 766159.48%
“专词”指人名、地名等,必须音译。意译词的比重,《辞海》明显高于《辞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汉语社会对外来词的改造方向。有些难以意译的外来词就尽可能设法进行汉语化的表义性改造。印欧语的词是多音节的,汉语往往就只取其第一个音节,再配以一个加上意符的汉字,使之汉语化,这里尤以化学名词最为突出,例如,Magnesium(镁),Natrium(钠)等等。这种汉语化的改造办法由来已久。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我国,由于翻译佛经的需要,汉语从梵语和中亚的一些“中介语”(如吐火罗语等)借入大量词语,由于语词结构上的矛盾,汉语就对它们进行了汉语化的改造。如“佛”借自梵语,原文为buddha,音译为佛陀、佛驮、浮图…,bud-仅为其中的一个音节,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由于“佛陀”之类的音译词不合汉语“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意义”的强制性对应习惯,不利于复音词的构成,汉语社会就把buddha这个词的意思归入bud-这个音节,译为“佛”,使之汉语化,尔后再以此为基础造出“佛土”“佛法”“佛像”“佛身”“佛经”“立地成佛”之类的字组,使之消除外来的痕迹。这是汉语改造外来词,使之意译化的一种重要方法。上述这些方法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坚持“字”的表义性,反对把它降格为一个纯粹音化的符号。这是汉语为使外语的结构适应自己的结构特点而进行的一种调整。印欧系各语言之间的借词由于语言结构类型的一致,因而借用很自由,基本上只需要进行字母的对应转写就可以把另一种语言的词借进来,不需要进行原则的调整。这与汉语的意译化方法相比较具有天壤之别。汉语的特点就是在这种不同类型语言的结构撞击中显现出来的,这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义”在汉语结构中的地位。汉字的发展始终坚持它的表义的趋向(王宁,1991,73),这正是它适应汉语的结构特点的反映。汉字忠实地记录了汉语的结构。所以,“字”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的表义性,这是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基础,也是语义型语言的一种最基本的结构单位。汉语的研究应该以“字”为基础去探索它的结构。
前面的比较与分析说明,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词”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原则的差异,其集中的表现是:“词”的突出特点是它的语法性,受一致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结构规则的支配,而“字”的突出特点是一个音节和一个概念(意义单位)的一一对应的强制性和它的顽强的表义性。基本结构单位是语言结构的最活跃的细胞,它们之间的差异正是不同类型的语言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集中体现,我们应该循此去研究语言的结构,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汉语中的“字”和“词”
“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那还有没有词?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词”是印欧系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问汉语有没有“词”,实际上是在用印欧语“词”的标准来衡量汉语的结构单位。由于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不同的语言只是采用不同的方式对相同的现实进行编码,因而相互之间可以进行代码的转换。以“词”为视角考察汉语的结构,自然可以找出相当于“词”的语言现象;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即使在汉语中找出类似印欧语word那样的“词”,它也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只是一种辅助性的结构单位,而且它与印欧系语言的词的性质和特点也不完全相同。人们可能会说:这是奇谈怪论,而我们认为这正是汉语的实际情况。
作为语言的结构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只有“字”,没有“词”;“词”这个字只是指“意内而言外也”(《说文》),既与“字”的意思无关,也与现代语言学的word之类的单位无涉。词是《马氏文通》所开创的汉语语法研究从印欧语中移植进来的一种舶来品,在汉语中没有根基。在这方面论述得最清楚、最科学的是赵元任(1975,233-234),认为印欧系语言的word(词)这一级单位“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字”与汉语的句法结构》一文中讨论过,这里不再重复。汉语中没有“词”,但又有象“词”那样的语言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词”与“字”的关系。赵元任说“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这“词概念”指的是“音节词”(字)、“结构词”(语法结构单位)之类的东西,不过我们这里想根据概念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来了解“词概念”,并借用赵的论断来讨论“字”与“词”的关系。“词概念”是无形的,它需要借用一定的物质形式才能表现自己的存在。那么这无形的“词概念”寄托在哪里?就寄托在“字”的义项和“字”的结合之中,象前述的“图”字的各个义项就隐含着类似印欧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功能的词。现在很多语言学家都已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多义项动词应看作不同的词”(马庆株,1989,168),“一个字可以代表不相干的若干词“(孙景涛,1986,32)。但“字”的意义范围是模糊的,连续的,而义项是对模糊的、连续的义域进行离散化分析的结果,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的字典对同一义域的不同处理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词”不能代表“字”而成为汉语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
“字”通过结合而构成的字组(特别是其中的固定字组),其作用大体相当于一个“字”。这是汉语在演变中为减少“字”的数量而又要保持和丰富语言的表达能力而进行的一次重大的自我调整,以使保留下来的“字”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编码功能。象表示“黑色”意思的“字”在上古时期有98个之多(张永言,1984),现在常用的只留下“黑”等少数几个字,通过与有关字的结合构成字组去表达各种与“黑色”有关的意思。这种增加“字”的长度以减少“字”的个数的自我调整的客观效果是为词概念找到了一种较为客观的表现形式,这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复音词”。如果说,一个“字”中可以隐含着几个不同的“词”,那么“字组”就可以以“字”的某一个义项或语义特征为基础把语言中与此有关的“字”拉过来,彼此相互注释,相互限制,构成一个语义明确、功能相对单纯的“复音词”,使原来隐含在义项中的词概念明确化和离散化。如果仍以前述的“图”字为例,那么,“地图、版图、海图、挂图”等是“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周礼·夏官·职方氏》)中的“图”的意义的复音化和语词化;“图案、图像、图形、草图、按图索骥”中的“图”是描绘出或印出的形象”(《玉篇》:“图”,画形也”)这一意义的散离化和复音化;“图存、图谋、徐图、雄图”等则是“图”的思虑、谋划”意义(《说文》“画计难也”)的具体化和语词化;“贪图、妄图、希图、试图、企图”等是“图”的“设法对付、谋取”义的明确化,等等。这样,字组中的“字”通过相互注释、相互限制就使“字”的广泛而模糊的含义比较明确和离散,隐含在义项中的“词”也由潜在而变为现实,以往把复音词的大量产生归因于语音的简化,认为是为了避免同音的干扰而创造复音词。这两者之间可能有联系,但不一定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近代北方话的发展可以为这一论断作出明确而有力的注释。吕叔湘(1963,21)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明确提出:“北方话的语音面貌在最近几百年里并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双音词的增加以近百年为最甚,而且大部分是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关的所谓‘新名词’。可见同音字在现代主要是起消极限制作用,就是说,要创造新的单音词是极其困难的了。”复音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恐怕需要从减少字数而增强保留下来的字的编码能力的关系中去理解,它是我们探索汉语语义发展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同音字的大量产生是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果”,不是“因”。
“词”不管是寄托在“字”的义项之中也好,还是通过“字”的结合而形成的复音词也好,都得以“字”为基础;没有“字”,就不会有“词”,这或许可以成为对赵元任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这一论断的一种注释。不过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通过这些办法找出来的“词”和印欧系语言的词不是一个东西,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原则的区别。
第一,印欧系语言的word受句法一致关系的支配,因而其语法功能是有定的,可以据此进行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划分,而汉语的词以语义规律为基础,与语法规律为基础,与语法规则无关,因而它的句法功能,妙用“主语一谓语”框架的结构标准来徇,是无定的,无法据此进行词类的划分。汉语的“词”的语法功能还得以语义为基础去分析,不能和印欧系语言的Word混为一谈。
第二,从结构上说,Word在印欧系语言中是一种离散的、现成的结构单位,与语素、词组的界限大体上是清楚的:语素没有重音,词只能有一个重音,而词组则有几个重音,而汉语中散离的、现成的结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吕叔湘,1964,45),“字”与“词”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字”中隐含着几个词固然难以确定,就是依据“字”的组合而构成的“字组”(词),它与“字”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呈连续的分布状态。汉语的结构基础,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对一的对应,我们如以此为视角,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字”和“词”之间的连续统(continum)。请比较:
书甭①鸟儿② 刀子③友好④ 图存
看书
字1 12 2 2 2 2
音节 1 11 1.5 1(?),2(?) 2 2
概念 1 11 1 1 1 2
这里只分析到二字组。三字组(“红通通”)、四字组(“稀里哗啦”)由于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这里从略。“看书”作为一种非词的二字组放在这里,以便比较。着眼于“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对应的结构格局,就可以发现“词”的语音形式的一种连续统式的分布,如果把方言中的所谓Z变韵,D变韵,嵌1词之类的现象都收集起来进行分析、排比,在这个连续统中还可以插入其他的类型。根据这种连续统式的分布状态,“字”与“词”的关系或许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规律:字组(这里含单字,把它看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字组)越短,它的语义越广泛、模糊,其中可能隐含的义项就越多,因而它的语义功能也就越复杂,可能代表的词也就越多;反之,如果表达一个概念的字组越长,则它的语义越明确,其中可能隐含的义项就越少,语义功能、句法功能也就越单纯,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长字组只能有一个意义、一种功能。这种字组的长度与语义功能、句法功能的明确性的反比关系顺着连续统而渐次发生变化,这也是汉语的“词”难以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两方面的区别足以说明,汉语的“词”和印欧系语言的word实际上不是一种性质的结构单位:word受句法一致关系及其相关规则的支配,而汉语的词则受语义规律的制约;把由“字”的结合而构成的“词”叫做“字组”或“固定字组”,恐拍比叫做“词”更确切、更合适。不过“词”这个概念现在已颇为流行,可以因循旧贯,因为重要的是“确定介乎音节词(指“字”——笔者)和句子之间的那级单位是什么类型的,至于把这些类型的单位叫做什么,应该是其次考虑的问题”(赵元任,1975,240)。
汉语的“词”以表义性的“字”为基础,没有“字”也就不会有“词”,不管是认字的还是不认字的,都知道“字”是什么东西,而“词”则是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之后才能掌握的结构单位。赵元任说“字”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心主题”,而“词”则是在许多不同意义上的辅助性的副题,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什么是“中心主题”?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语言的结构本位。汉语是一种以“字”为结构本位的语言,语言研究如果能紧紧扣住这种结构本位,并以此为基础吸收国外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能使汉语的研究水平向前发展一大步,其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五·四”前后开始的汉语音韵研究和方言研究。高本汉在研究汉语音韵时没有偏离“字”这一结构本位,而是用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这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来改进这种结构本位的研究,因而为汉语音韵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徐通锵、叶蜚声,1980,1981)。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兴起于结构语言学的兴盛时代,而其奠基人就是结构语言学派的权威学者赵元任,但是他没有照搬结构语言学的语言调查的理论和方法,而一切以“字”为基础,并于二十年代编成《汉语方言调查表》;有了这个字表,我们就能照字记音,进行方言结构规律的研究。直至今天,这本字表仍旧是我们进行汉语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的一本必不可少的手册。方言连读变调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也是以“字”为单位进行研究的,讲“二字组”“三字组”的连读变调,从来不说“语素与语素”的连读变调。这种以“字”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使汉语方言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突破性的进展。这些领域虽有很多争论的问题,但从来没有发生过要不要以“字”为基础的争论,这说明它们的研究方向没有偏离汉语的结构本位,因而其研究成果都比较成熟。语法研究的情况截然相反,它抛弃了“字”,而以印欧语类型的词为基础,这就偏离了汉语的结构本位,因而引起了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三、以词、语素为结构单位的汉语语法研究和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
汉语的语法研究为什么会偏离“字”这种结构本位?这与学术研究的传统和语言研究对象的变化都有密切的关系。传统的汉语研究以“字”为本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不研究语句的结构;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而不管在魏晋时期就已开始发展起来的、与文言文不一致的口语。这两点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距离越来越大。鸦片战争以后,社会要求言文一致,要求研究一直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文,“所望吾国好学深思之士,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孙中山,1918)。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我们自己又没有相应的研究传统,就只能到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去找理论、找方法,因而从《马氏文通》开始的中国语法学就用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来观察汉语,使汉语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印欧语的眼光”。
什么是“印欧语的眼光”?朱德熙(1985)认为它就是“把印欧语所有而为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但是,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这里没有一种客观的鉴别标准,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所谓“眼光”,实质上就是观察语言结构的一种宏观的观察点,与编码的特定视角有关,因此确定“眼光”的客观标准应该是语言的结构常数或结构关联的基点。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常数“1”在句法层面,由“1个句子=1个主语×1个谓语”的“1”控制着整个语言的结构(徐通锵,1991,56-59),因此“印欧语的眼光”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的“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和与此相联系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划分。汉语研究舍“字”而取“词”,实质上就是要以这一套理论体系为观察点来改造汉语的结构,使之适合于印欧系语言的结构框架。《马氏文通》开始形成了这种“眼光”,但由于它与语言事实有矛盾,因而其后不久人们又想摆脱这种“眼光”束缚陈承泽,1922,14)。汉语的语法研究就是在这种束缚和反束缚的矛盾和竞争中发展的,而矛盾和竞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处理词和与此相关的问题。《马氏文通》是字、词并用,“字”指结构单位,而用“词”指结构单位的功能,说明它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汉语研究的影响。完全抛弃“字”而改用“词”,始自黎锦熙(1924,2-3)的《新著国语文法》,认为“文法中分别词类,是把词作单位;不问他是一个字或是几个字,只要是表示一个观念的,便叫做词”,“词就是说话的时候表示思想中一个观念的‘语词’。”从此以后,“字”就被逐出语言的研究,清除了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一个障碍。为什么“《新著国语文法》的英文法面貌颇浓厚、颇狰狞”(黎锦熙在解放后为该书写的序言)?这与“词”观念的确立是相互呼应的。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偏重于模仿,不大注意汉语本身的特点,难以满足汉语研究的需要,因而在三十年代引发出一场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强调汉语特点的研究。这次讨论很有价值,是试图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的一次尝试,虽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摆脱”的意识也还比较薄弱,没有找到解决词类问题和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的办法,但为四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四十年代以王力、吕叔湘和高名凯为代表的汉语语法研究比较强调汉语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已经突破了“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而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这主要是:句法结构的研究已突破印欧语的动词中心说,分出名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三种类型;在动词谓语中提炼出连动句和兼语句,突破了印欧语的句子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定式动词的结构格局;词类问题的处理也已根据汉语的特点出现了一些松动的办法;比较强调句法语义的研究,等等。当然,每本著作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但这些想摆脱印欧语语法理论束缚的趋向是有积极意义的。五十年代的语法研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宾语问题的讨论,一件是词类问题的讨论。这两次讨论都主张根据汉语的特点用新兴的结构分析法来研究汉语,反对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特别表现在词类问题的讨论上),反对语言分析中的语义标准。这些对促进汉语的研究很有意义,避免简单地用汉语的事实给西方的语法理论作注释,不过在反对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结构这一点上却有一些讽刺意味,因为它批判了这一种“印欧语的眼光”(例如汉语实词因没有形态变化而不能分类),却为另一种“印欧语的眼光”的流行和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或者说,在批判表层的“印欧语的眼光”的过程中却又深化了深层的“印欧语的眼光”。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谓语中心,这是对印欧系语言动词中心说的一种改进,“连动”和“兼语”统一为“连谓”,使句子的结构更符合“主语—谓语”结构框架中的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的标准。第二,用语素代替词号作为汉语语法结构的基本单位,把汉语完全纳入结构语法的框架中去研究。这恐怕是“印欧语的眼光”的一种更深沉、更本质的反映。如果说“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那么汉语中不仅没有语素这种单位,而且连这种概念也没有。可能有人会说,“字”就是语素。否!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第一,语素基本上是一种线性结构,不含非线性的因素:不能有重音,不是语言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单位,即使是词根,没有相应词缀的配合,也无法实现编码的功能;ablaut之类的元音变换(如bring-brang-brung中的i-a-u)是非线性的,但很难把这种“变换”看成为语素,IA模式分析这类问题的失败经验(Hockett,1945,99-105)已为此作出了充分的反面说明。和语素相反,“字”是一种非线性结构:“字·音节·意义(概念)”之间存在着强制性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声调的使用使得同样复杂程度的单位占比较短的时间”(赵元任,1973,93),“字”是汉语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单位。第二,语素的功能单纯,只是词的结构要素或表示词的某种特定的句法功能,而“字”是汉语结构的枢纽,是语音、语汇、语义、语法的交汇点,因而是各个层面的基本结构单位。第三,一个“字”中可以包含若干个不同的词,而语素绝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构。“字”与语素实际上是不能进行类比的两个不同类型的范畴。把语素作为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实际上就是把汉语中不存在的东西作为结构单位,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语法体系可能很精致,但不实用,与汉语的实际状况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这里对五十年代以来的“印欧语的眼光”问题之所以讲得比较多,就是因为这涉及那些反对“印欧语的眼光”的学者的“印欧语的眼光”。我们从学习语言学的第一天起就在接受印欧系语言理论和方法的熏陶,对“印欧语的眼光”已经习以为常,不是主观上想摆脱就能摆脱得了的。我们非常反对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但在评述“五·四”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时却是用这种“眼光”来分析有关的问题的(徐通锵,叶蜚声,1979),因而分寸的掌握不大准确。朱德熙是反对“印欧语的眼光”最有力的一位学者,但他对汉语的语法结构的看法却打有很深的“印欧语的眼光”的烙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批评某些传统观念,很可能我们自己也正在不知不觉中受这些传统观念的摆布。这当然只能等将来由别人来纠正了,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朱德熙,1985)。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自然也同样适用于本文的分析。
前面简要的历史回顾说明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由于它的影响和干扰,我们就难以根据汉语的特点而进行独立的研究,只能是“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吕叔湘,1986)。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用来分析印欧语,固然可以得心应手,而用来研究汉语就会捉襟见肘,矛盾重重,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主语—谓语”结构框架下的词类划分以及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结合”中的最大难题,《马氏文通》以来的语法论争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条轴线展开的。为什么?因为汉语以“字”为本位的结构与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之间的矛盾犹如南辕北辙,难以调和。语言学家虽然想了很多办法,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其中包括汉语语法的结构本位,但都难以调和两类语言在结构上的矛盾而实现“结合、的目标。《马氏文通》用“字”研究词法,用“词”研究句法,由于这里的“字”对等于印欧系语言的word,所以是一种以词为本位的语法研究(邵敬敏,1990,51)。《文通》凭语语义分词类,由于“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以何如耳”,因而无法解决词类以及它和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此路不通,黎锦熙(1924,6,29)主张以句为本位来解决这个难题,提出“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位置、职务,才能认定这一个词是属于何种词类:这是国语文法和西文法一个大不相同之点。所以本书以句法为本位,词类多从句的成分上分别出来”,并把这些论述概括为“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著名论断。这里虽然已经发现汉语与印欧语语法理论之间的矛盾,但还是依照这种理论来研究汉语,给词分类。句本位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是成立的,只要抓住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语—谓语”这种封闭性的结构就可以进行词类和它与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但在汉语中这种理论是不成立的,因为汉语的句子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一个句子能否成立,不决定于有无“主语”或“谓语”,也不决定于是一个“主语”和“谓语”还是几个“主语”和“谓语”,而决定于一个事件的话题的相对完整的叙述(徐通锵,1991,1994),因而无法把它纳入“主语—谓语”的封闭性结构框架中去研究。语言学家发现这种理论—不能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二不能解决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能放弃,另探新路。五十年代以后汉语语法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德熙,他用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他没有在结构本位问题上发表过明确的意见,但从他的研究实践来看,前期偏重于语素,认为它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词、词组、句子等都只是语素的不同层次的序列;后期在理论上偏重于词组,认为“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以词组的结构规则为“纲”来研究汉语的语法(朱德熙,1982,1985),后来人们把这一思想明确地概括为词组本位,陆俭明(1992,127)还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解释。语素有没有成为一种“本位”,作者没有说,学术界也无评论,我们也不必给它安上一顶“本位”的帽子,但语素在朱德熙的理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词组本位”的理论,它的是非曲直应该放到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历史中去考察。它是在词本位、句本位无法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以及它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之后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理论假设。朱德熙想用这一理论来解决词本位、句本位无法解决的矛盾:既要保持“主语一谓语”的结构框架,又要排除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为此,他提出汉语语法的两大特点:第一,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不像印欧语那样一一对应(名词和主宾语对应,动词和谓语对应,形容词和定语对应,副词和状语对应),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对应(如动词和形容词不仅可做谓语,而且可以做主宾语……);第二,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和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一致,这种一致性“还特别表现在主谓结构上。汉语的主谓结构独立的时候相当于英语的句子,不独立的时候相当于英语的子句”,“汉语的主谓结构实际上也是一种词组,跟其他类型的词组地位完全平等”(朱德熙1985,8)。这两个特点,以“二”为体(本位),以“一”为用,这样汉语句法结构的分析就可以限制在词组的层次上,只要分析“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这些词组的结构就行,词类的划分也是以此为基础考察它的分布,不必考虑它与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这是朱德熙的语法理论的一个发展,1982年的《语法讲义》还把能否“作谓语”“作定语”作为划分形容词的一个标准,而到1985年的《语法答问》由于考虑到汉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系是一对多的错综“对应”,不能不放弃这种句法功能的标准,不然,“由于百分之八九十的动词和形容词可以做主宾语,能够做定语的名词百分比更高”,就会陷入“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词无定类的泥潭。朱德熙的词组本位理论在理论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不能反映汉语句法结构的本质,因而能够运用的范围很窄。汉语句法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开放性,与印欧系语言以一致关系为标志的封闭性的主谓结构形成鲜明的对照。词组本位不仅不能反映汉语句法结构的开放性,而且还进一步把封闭性的句子结构缩小到词组的结构,这就使语法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难以分析汉语以开放性为特点的句法结构。其次,朱德熙所说的汉语语法的两大特点实际上都是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而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印欧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对应,以此为准,汉语的“对应”就是一对多。一对一的对应是语言结构规律的反映,而一对多的所谓“对应”,这里只能说不存在规律,不成规律的东西自然也就不能成为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大弊病就是要在这种不存在规律的地方找规律。总之,词组本位象词本位、句本位那样,仍旧不能把握汉语语法结构的脉络,难以有效地解决语法研究中的问题。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的语法研究一方面抛弃汉语特有的结构本位——“字”,而另一方面却又在“印欧语的眼光”的支配下寻找它的本位,从语素、词、词组到句子,差不多各级“本位”都试过了,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说明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适用于印欧系语言的研究,拿来研究汉语,由于语言的普遍特征,在某些狭窄的领域内可能适用,但无法解决汉语研究的基本问题。一种语言的结构本位只能有一个,语音、语义、语汇和语法的研究都得以它为基础,不可能是一个领域一个“本位”。汉语的研究还得继承我们自己的传统,以字为“本位”,研究句法的结构规则。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不需要实现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汉语实际的结合,而是说在“吸收”和“结合”的时候必须以汉语的结构本位——“字”为基础,因我之需,为我所用,不要因“印欧语的眼光”的干扰而把汉语“结合”到印欧系语言理论中去研究。研究汉语的方法论原则还得立足汉语,参照科学思潮的发展,在汉语的研究中提炼相应的理论和原则,“张冠李戴”式的研究恐怕很难解决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难题。
四、“字”本位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前面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字”与汉语结构的关系,但要真正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还得弄清楚“字”与语言研究方法论的关系。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语言的规则归根结蒂都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不同语言的差异主要是因编码视角的不同而形成的接受投射方式的差异。汉语以“字”为结构本位,其突出的特点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的强制性和顽强的表义性;它以“比类取象”为编码的特定视角,直接接受现实规则的投射,不需经过特殊的形式规则的调整,因而语言范畴与概念范畴一致,与印欧系语言的两类范畴既有联系又有矛盾的情况很不一样。这些特点决定了汉语研究的独特的方法论,这就是可以在语言规则和现实规则之间建立起对应的联系,用临摹性(iconisity)原则来描写。
临摹性作为一种明确的方法论原则为时还不长,始自本世纪三十年代Peirce的论述,但它的基本精神早就已经在深刻地影响着语言学家的研究实践,希腊—罗马传统的规定说和约定说之争,我国先秦时期的名实之争都与这种原则的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临摹性原则的基本精神据Perice的描述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临摹图像(iconic image),它必须与它所指的事物相似,如相片、塑像、语言中的拟声词;一种叫临摹图像(iconic diagram),它是符号的系统排列,其中没有一个符号和它所指的东西相似,但是符号之间的关系必须表现它们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技术图案、无线电线路等。“语言中成素(element)的次序平行于实际的经验或认识的顺序”就是Peirce用来说明语序规则的临摹性的一句名言,经常为语言学家所引用(据Haiman 1980;jakobson).Peirce的这两类临摹性后来Haiman(1985)简化为“成分临摹”和“关系临摹”,以此探索语言研究的方法论。
语言规则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临摹性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象汉语这种直接接受现实规则的投射的语言,临摹性原则应该占据支配地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尽管缺乏理论性的探讨,但在实践中却始终恪守着临摹性原则,训诂学中“以形求义”和“因声求义”就是这种原则的两种重要的表现方式。“以形求义”可能因其“形”而归入文字问题,但不要忘记这里的“形”只是求“义”的一种方式。汉字为什么一直顽强地坚持它的表义性?就是由于它与汉语临摹性的编码原则相适应,是“字”中有“言”,可以通过“形”去研究”“言”(义),是观察“言”的一个窗口,世界上别的任何发展成熟的文字体系都没有这种功能。如果说,“以形求义”的“形”终究与文字有关,那么“因声求义”的“声”就完全是语言的问题了。为什么可以通过“声”而能求取“义”?这不是与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约定性矛盾吗?不错,有点矛盾。我们过去对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的理解有点绝对化,固然,狐立的一个字人们看不出它的音义结合的理据,但如着眼于字族的结构,那就不难发现同族字中“字”与“字”之间的制约关系,找出理据,使人们有可能去“因声求义”。段玉裁、王念孙等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通过“一声之转”的“转”去探求“字”的语义,从而使汉语的语义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性进展。这一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这种“因声求义”的原则的重要性和生命力。它是汉语临摹性原则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这方面的问题太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这里只是借此说明:“字”中形、音、义三位一体,是汉语临摹性编码的基本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已经基本上把“字”与临摹性原则的关系说清楚了,现在应该在此基础上研究汉语语句结构规则的临摹性问题,建立语义句法,继承和发展汉语的研究传统。
以临摹性原则为基础的汉语句法研究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但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其基本精神就是弄清楚句法规则的语义基础,或者说在语言规则中找出现实规则的投射理据。现在这方面有点深度的研究在我看到的材料中主要有戴浩一(1985)的时间顺序原则(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和石毓智(1992)关于语义的“±定量”和句法的“±肯定”的关系的论述。时间顺序原则的具体含义是:“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戴列举了大量事例对此进行了很有启示性的分析。确实,这是汉语的一条重要的临摹性原则,有很强的解释力。以往的语言学家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例如洪堡特早就说过汉语的句子跟思想的简单明确的顺序一致是汉语特殊的优点(据Robins,1973,36);Haiman(1980,516)也曾依据语序的特点提出“有理据的临摹性”(the iconisity of MOTIVATION:"语法规则像拟声词一样直接表现它的意义。这种临摹性的最清楚的例子就是语序。如果其他的方面都一样,叙述句描写的陈述次序和它们所描写的事件的次序是对应的。”应该说,汉语是最一贯地遵守这种临摹性原则的语言。戴浩一的时间顺序原则是对这些论述的改进和补充。这种原则在汉语的研究中很重要,但使用的时候也有一个“度”,即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戴浩一对这个“度”的解释是:“把动词作为中心参照点,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跟动词有语义联系的成分”,这恐怕不确切,至少是不全面的。先请看下面的两例。
1.槽内的水左冲右突,翻着花,滚着个,激扬飞溅,像暴炒着一串玉珠,风翻着一槽白雪,隆隆声震荡着山谷。(郑伯伦:《黑龙潭印象》)
2.演员们的出色表演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例1除最后一句“隆隆声震荡着山谷”外,中间的各个“动词”性词语的顺序只代表观察者的思维顺序,而不代表现实现象的时间顺序,更动其间的次序,句子照样成立,而且意思不变。为什么?因为这里的“主语”是无生的“槽内的水”,时间顺序原则的一个重要条件与“主语”的有生性有关,戴浩一列举的全部例子的“主语”都是有生性词语,离开了这个条件,“谓语”中即使有若干动词,它们的排列顺序也不一定与现实现象本身的先后时间顺序一致。例2的“出色表演”和“成功地塑造”虽与时间顺序有关,但在“出色”和“表演”之间,“成功”和“塑造”之间就与时间顺序不一致,因为只有在“表演”之后才能知其是否“出色”,“塑造”之后才能定其是否“成功”。这种矛盾与说话的时点有关,只有在演出之后才能依照例2的次序排列,说明汉语的句法分析不能局限于“主语—谓语”的框架,而应引入语境、说—听双方的交际意图之类的内容,进行实际的语义分析。所以时间顺序原则在接受现实规则投射的时候有一定的语义条件的限制,不能随便扩大它的使用范围。
石毓智关于“±定量”和“±肯定”关系的分析是临摹性原则的一次成功的运用。“量”是一种重要的语义特征,可以自由地用数量字或程度字修饰的都是不定量的(前者表离散,后者表连续),反之即为定量的;不定量的“字”或字组可以加“没”或“不”否定,即既可以用于肯定的结构,也可以用于否定的结构,而定量的“字”用于“±肯定”就有很大的限制。他根据现实的规则“量大的事物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存在,量小的容易消失”的投射理论研究汉语的“±肯定”的语义规则:语义程度极小的定量“字”只能用于否定结构,语义程度极大的定量“字”只能用于肯定结构,语义程度居中的不定量“字”才能自由地用于肯定和否定两种结构中。假定有一组同义系列的“字”或“字组”,按其语义程度的大小从左到右排成一个系列(左边的为小量,右边的为大量),例如:
挂齿
提起
说起
谈论 叙说 诉说
倾诉
这些字组的句法表现可以整理出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连续系列:“挂齿”的语义量小,只用于否定结构,前面都有表否定的“不”或“没”;“倾诉”的语义程度高,只能用于肯定结构,其前不能加“不”或“没”否定;语义程度居中的“谈论”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或否定的结构;靠近左端的“提起”“说起”经常用于否定结构,表现在前面加上“不”或“没”说起来更顺口,而靠近右端的“叙说”“诉说”经常用于肯定结构,如前面加上“不”或“没”否定,说起来比较别扭。我们以往不知道语义和句法之间有什么联系,石毓智的研究为这种联系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另外,这也为同义系列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课题,要求以语义量的大小排成一个系列,从中比较和研究它们与句法结构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开发前景的新领域。
以临摹性原则为基础的句法研究现在还是初步的、零散的,研究的成果也比较粗疏,而且还没有摆脱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的干扰和影响,但是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方法论原则在汉语的句法研究中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的。我们这样推崇临摹性的研究,这不是我们的主观偏爱,而是根据以“字”为结构本位的汉语编码方式的特点而得出来的结论。“字”的临摹性必然会引向句法结构规则的临摹性。这是观察汉语句法结构的一个关键,也是能否摆脱“印欧语的眼光”束缚的一条重要途径。自然,要用临摹性原则建立汉语语义句法的一个完整体系还有一系列原则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结构和“字”的语义分类之间的关系。结构与分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印欧系语言的“主语—谓语”结构和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词类划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这种依存关系的一个有力例证。传统的汉语研究只有文字、音韵、训诂,没有语句的结构,自然也就不必对“字”进行分类。汉语研究的客观需要要求我们去解决这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有了眉目,其他如结构规则、句型、语序、层次、虚字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有定”“±肯定”之类的问题的解决才有可靠的理论根据。结构框架的问题我们建议采用“话题—说明”(徐通锵,1991,1994),而其他的问题有待于来日的研究。
注释:
①这里指合音字,北京话比较少见。历史上曾有相当数量的合音字。方言中的变音(包括变声、变韵、变调)很多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合音的范围。
②代表单音节化的儿化。
③“子”代表轻声,马蒂索夫把这类现象看成为“一个半音节”,很有道理(据戴庆厦,1990,3)。
④这里代表变调。变调的实质是使两个单字调合而为一,形成一个跟单音节声调相类似的声调(五台,1986,4)。所以这种类型的例子,从声调看,它相当于一个音节;从声、韵母的组合来看,它是两个音节。这一类例子把它看成一个音节或两个音节,都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