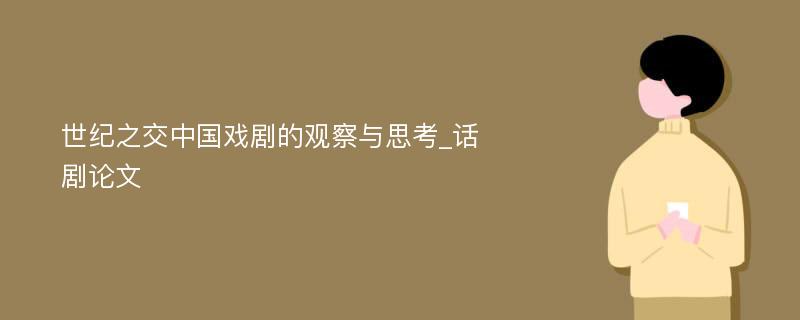
世纪之交中国话剧的观察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话剧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艺术来说,没有哪一个时代像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那样令人酸楚交加,比起近代社会的文明演化造就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变迁来,现在的艺术困境更为难以置信,许多传统的衰退宛如吊在高楼的双手,眼见着渐渐滑脱却只能揪心而无可奈何。曾经风骚一时的一些艺术被无情的市场和绝情的时代磨去光彩,甚而退缩一隅,甚而无声无息……大众文化的气息笼罩陈俗,传媒的光芒遮蔽艺术,网络勾连着时尚培养起来的新一代,眼睁睁地看着艺术如同老澡堂的残喘或老茶馆的变异而变色换颜。
在世纪交替的关口,戏剧的景象的确微妙而尴尬,艺术面临的种种难以言述的现象都可以在戏剧中得到体现。冷眼看待中国戏剧的世纪末体现,也许可以窥见艺术的蜕变轨迹,为21世纪的戏剧发展寻求可行之路。
2000年中国话剧的情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情调的变化
我们曾经习惯于传统积淀的中国戏剧风味,由《雷雨》、《北京人》等所构筑的旧式家庭纷争如此令人津津乐道,由《风雪夜归人》、《上海屋檐下》等造就的人间命运纠葛如此牵肠挂肚,由《屈原》等表现的荡气回肠的历史风云人物如此栩栩如生,由《茶馆》等造就的艺术生活世界如此厚重深沉……这一切戏剧艺术的精华都还能呼应现代人情世故的需要吗?在历史走到21世纪跟前的时候,无形的变化早已彰显。中国话剧积淀下来的艺术感染力主要是产生它的历史所附加的厚重感,根源于时代纠葛的传统戏剧风貌,在培育它的几代人的心目中具有神圣感,却遇到了传媒时代的风习冲击,往事云烟的留存不是没有牵连观众的旧情昔梦,但改变了的情调却成为现代戏剧的明显现象。于是,在某种程度上,轻渺的现代情感取代了容纳时代家庭的厚实社会情感,人性本能的复归带来莫衷一是的纷乱情感展现。这种感受不仅仅是孤立的现象,甚至在本质上中国戏剧的风貌都受到影响。不妨拿中国话剧的大本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重头戏《风月无边》来看看现代情感的介入怎样改变了艺术的情调。
在这部交杂着辛酸和放纵无羁色彩的剧目中,戏剧雅士李渔的坎坷人生自然展露得令人动容,时代的羁绊和世俗的偏见都使他的生活具有了封建年代文人才士某种苦难浓缩的意味,也因而具有社会的批评力。但20世纪末期出现的《风月无边》却实在是沾染了当下时代的风习,风流才子的倜傥无羁,固然使舞台人物显得潇洒飘逸,却难免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才情与男女情的绵长,情不自禁的对落难公子的苦楚欣赏,超过了过去年代戏剧的严肃揭露倾向,在人性情感的张扬上,剧作与表演都不遗余力。显而易见,话剧的感性力量得到扩张,外在的吸引力被不由自主地扩大宣扬,《雷雨》式的内敛咀嚼意味悄悄消淡。尽管《风月无边》的艺术感染力依然深厚,结尾暗恋十郎的女伶雪儿戏中“跳江”而真的深情跳江殉情,达到叩动心扉的悲剧高潮,但打动观众的情份力量的确也只限于此,我们这个时代所弥散的情调完全流贯在《风月无边》中,在创作者成功的欢呼和观众欢呼成功的背景下,21世纪的话剧情调变化可能就无可逆转了。这里的变化是不由自主的,艺术的渴求和商业的讨好同样真实,典型的期待和人性的偏向也两不放弃,批判力的削弱是无可奈何的潮流驱使,我们只有微叹而已。
同样的情调也表现在空政话剧团的《霸王别姬》中。作为中国文化典型人物之一的楚霸王与虞姬的生死恋情,曾是艺术无比美妙的生发乐章,无论在司马迁的笔下,还是在梅兰芳的身段唱词中,荡气回肠的艺术魅力不是体现在性格悲剧的无可挽回的叹息里,就是在生生死死的眷念缅怀中,神圣的人生际遇的悲剧感撞击人心。但时代造就的小剧场话剧《霸王别姬》,真就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感情颠覆的现实。演出的生动热闹是毫无疑问的,但中国文化积淀下来的深刻印象却在重新诠释中分崩离析。悲剧感的新式索解落脚在我们没有想到的商业化人性观中,不免令人生疑。剧中奇异之处是生造的吕雉突兀地出现在垓下之围中,横亘于项羽与虞姬之间,吕雉对项羽的真情诱惑和遭拒后心理的委屈与愤恨尽管相当新鲜,导致这种“两个女人对两个男人的爱情追逐和人性判断交织出一幕幕复杂多变又可歌可泣的戏剧冲突”(引语均为话剧说明书原文),但历史的尘封感却顿然消失。显然,创作的现代根据是人性情感的复杂化,“对久远的历史人物作出了今人的重新塑造”的意图显而易见,然而,无非是当今人们困惑于感情纠葛并试图从中解脱尴尬情怀的远古寄托,“将在重新挥就的历史画卷中读解出至今仍在困惑我们的诸多人性悖论和命运抉择”的确是创作者的终结目的,只不过艺术的沉淀被多少有些轻浮的现代情调弄得不三不四,而现代人的复杂情感并没有借古事产生心灵的震颤。
情调的变化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本源于改变传统戏剧严肃政治面孔的意图,却难以摆脱时代潮流的支配,话剧在革故鼎新的路途中还能葆有多少艺术情感真实?的确值得思考。
二、主流的式微
导源于时代变化的话剧带来了多元形态的表现形式,在世纪末还略有兴盛气象的演出舞台上,过去曾明显一统天下的现实主义略显式微,杂乱的多元形态的时代气息造就了中国话剧多样化的嘈杂。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表现等西方曾经相当时尚的现代潮流都在中国剧场或民间中得到实践,即便是趋近于现实主义的话剧,也多结合了多种表现手法和现代形式,单一化的现实主义已经改变。话剧现实主义的变革当然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需要思考的问题也就在这里。回顾中国话剧艺术历史,就艺术的厚重感而言,毫无疑问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还是那些人们喜爱的现实主义话剧,为中国话剧留下耐久话题的是《上海屋檐下》、《风雪夜归人》、《雷雨》,以及《茶馆》、《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等优秀之作,加上世纪末期《古玩》和《生死场》等剧作,聚合为颇有生命感的话剧艺术风景长廊。就整体而言,这些剧作给人以动人的生活气息、厚重的文化底蕴、浓郁色彩的市井或乡野风俗画,无论观赏还是阅读,都楚楚动人。在中国社会风云起伏的背景下,它们对生活的真实再现和对生活认识的艺术表达,的确叩动人心。时代造就了大气深刻的中国话剧经典,观众习染着话剧的天然色彩,现实主义如同在其他姊妹艺术中一样成为话剧当家本色。
然而时代变了,在社会批判淡化和集体意志削弱的年代,话剧创作的观念和方法都不由得产生巨大的转变。有关变化的理论上的反映可以从2000年出版的《先锋戏剧档案》一书中看出一些眉目,在这部代表90年代话剧思潮多样变化的作品集中,嘈杂的心态和顽强的变革实践热气卓然显现。从罗列的各式作品展览中固然可以看到话剧实验的基本痕迹,更可以窥见话剧艺术理论倡导的积极和杂乱交织的眉目。比如其中孟京辉得意的一篇《现实主义批判》的文章,把现实主义视为一种“恶习”,“恶劣不堪的限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生长”等,显示了现实主义式微的社会背景和观念形态状态。也许是时代变化使然,开放的社会背景下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是艺术观念支使的结果。曾经起主宰作用的反映生活的艺术观念,对社会和人的关系极为重视,却难免忽略人本身的七情六欲,更漠视人隐秘的意念和本能的反应,艺术的创造性却时常和人的精神本能直接相关。当开放时代赋予人更大的精神自由的可能空间时,关注自身的意愿便空前强烈,于是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的氛围逐渐削弱。在孟京辉所认识的理论中,现实主义是颇多疑惑的:“现实主义戏剧经常置真正的社会现实于不顾,把模糊的视点落在不值一提的戏剧冲突和不愠不火的戏剧事件上,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关注生活的拘泥小事而茫然于惨淡淋漓的人生。”这里的阐述未必使人舒服,过于决断的言辞也不免偏激,但可以看出,他所代表观念的表述根源于对个性与时代气息的反拨。由于时代已经变化,多元文化的宽容度自然会造就人们对过去定论的疑惑和反思,而现实世界的活生生现状,更促使人们对艺术表现的真实度重新审视。无论承认与否,世纪末话剧艺术的走向是多元取代了单一,主义的式微其实是摆脱束缚后的艺术的一种试图重新选择和摸索。
我们的疑问只是在于:任何艺术远离开生活的疾苦和百姓的生命悲欢,还是否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作为艺术的形式,可以有多样的自由表现形态,但作为艺术的精神实质,疏淡了人生和现实悲欢就肯定没有意义。当今另一位著名话剧导演林兆华对90年代话剧与80年代话剧有一个比较评价,即认定前者不如后者。他认为就艺术生命力和激情而言,90年代的话剧艺术是退步的。姑且不论这一评价是否完全合理,但就整体而言确有其理,原因何在值得人们深思。可以断言,在缺少时代感的艺术中要找到具有持续性的艺术生命力,恐怕是难之又难的。因为,艺术形式可以变迁,主导风格可以转换,但艺术的生活反映和对现实生命感的表现却不可丢失。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娱乐文化的时代,休闲文化和疏离苦难成为艺术必须面对的现实,创作的切近潮流不可避免,但在时代必然改变的主流变化中,如果艺术没有和人间大社会痛痒相连、休戚与共的责任感,听任庸俗和时尚摆布左右,那么,艺术将混同流俗的命运也就可以预期了。
三、先锋的活跃
世纪末是实验戏剧愈来愈自由地展现自己创造力的适宜时代。伴随着世纪转换,思想形态束缚显见减弱,曾经执着于个人感性创作的一些戏剧工作者渐成气候,颇有了一些品牌效应,创作的熟练和节奏都大大增强,个性意识愈来愈成为他们创作的动力;社会认可度也自然呈现。而话剧市场化的步伐被迫加快,投入产出的机制造就了话剧出品人的个体化,统一意志的生产难以规模实现,执著个体的创造性愈发明显,这也是实验和先锋在话剧中更为时兴的一个因素。而市场的需要从被动到接受经历了很快的转换,随着话剧小众化的不可避免,热心观众的年轻化和新奇感增强,对话剧“传统”的建立就是从标新立异的剧作开始认识已是尴尬的现实,不断地接受先锋成为刺激观赏的一个重要因素,投合这股世纪末潮流的创作不断加码,话剧变革成为常态,对话剧形式变化的见怪不怪成为各种艺术形式中最具宽容度的现象。
这里所谓的先锋其实并非装置主义或行为美术之类的前卫性,而是指世纪末出现的有别于传统、注重形式感或形态比较各色的多样化戏剧。早在80年代探索戏剧中,新异感的形式已经冲击了中国话剧,而90年代以小剧场戏剧演出所显示的艺术前卫的姿态和个性色彩更加明显地从观念形态上呈现。话剧舞台明显形成为传统和革新两大派别,而传统的式微和创新的不绝如缕也习见不怪。在90年代形成的许多戏剧同道者的探索团体,如牟森的“戏剧工作车间”、林兆华的“戏剧工作室”、郑铮的“火狐狸剧社”、孟京辉的“穿帮剧社”等的存在和变革,标识着艺术跨上探索的台阶的潮流。
尽管人们很难再以郭沫若、曹禺、老舍这样的传统大师来衡定现在话剧的艺术创造,没有可以比肩的话剧艺术大师是我们不免悲哀的内心隐痛,但清醒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是嘈杂和逐潮追浪交织而无法潜心深远艺术的时代,为争取观众和自己生存已经是颇为繁难的事,于是,产生适应时代转换的非传统艺术也是可以理解的。“先锋”的概括就是指和沉稳的传统、主流习惯的既存形式相对的新鲜变化。
但是,世纪末的“先锋”并非80年代对于西方戏剧借鉴的令人惊异的创新,而是更多根源于商业支配和生存需要的艺术变化,显然更为自由大胆和顺畅,也不免摸索坎坷和奇特,由之引发的不仅仅是艺术的褒贬,而是更为广泛的文化议论。但实际上,比起80年代初期的话剧变革,世纪末的话剧无论如何变化都不会再引发当时的震动和惊惧。毕竟时代造就了宽容,艺术的兴趣指数也在下降。以小剧场戏剧艺术为典型的先锋戏剧更明显地面向现实和面对观众,改变了戏剧高高在上的演出常规,愈发积极直接地和真诚的观众情感进行交流,讲求与现场的呼应,显示了艺术摆脱孤芳自赏的自觉状况。话剧艺术革新折射着艺术和生活现实的密切关系,它典型表现了探索的价值取向和意义所在。在世纪末话剧中,诸如《爱你不容易》(空政)、《非常麻将》(李六乙)、《思凡》(孟京辉)、《恋爱的犀牛》(孟京辉)、《原野》(李六乙)、《女仆》(林荫宇)、《咖啡伴侣》(姬洁),以及《切·格瓦拉》和《永不失眠》等作品都从各个不同角度展现了这种变化的痕迹,在不同方面体现着创新的努力。可以说它们的重要价值,是打破传统、拓展话剧表现时空、外在上改变了话剧形态和表现形式,但内在的却是开通了艺术创造观念,继续着话剧革新的新路。
创新是大势所趋,从一定意义上看,创新之路才刚刚开始。“先锋”的价值是寻找到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化的中国话剧新世纪艺术之路。然而,被世俗所缠绕的悦众追求和孤芳自赏式的形式探求改变着艺术的方向。艺术一旦流连在纯实验先锋的狭小天地中,津津乐道于“花活”的耍弄,还会有艺术冲击力吗?狭隘的个性探求充其量只是把玩的观赏品而已,哪里还会有《雷雨》、《茶馆》、《屈原》式的洪钟大吕的艺术经典,更遑论产生曹禺、老舍、郭沫若式的艺术大家了。先锋的道路也许会造就出不拘一格的人才,但培育艺术生命的土壤还需要有艺术传统和渴求艺术观众的扶助,高耸的艺术之碑永远是站立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巨人造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