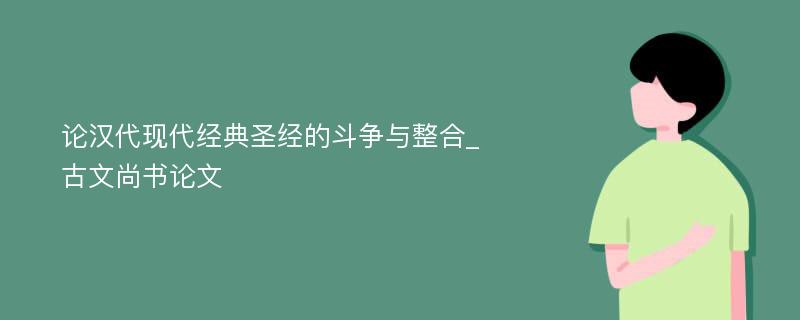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汉代论文,古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2-0106-06
一、关于两汉今古文之争的性质
学者一般认为,两汉的今古文之争先后发生过四次,第一次发生在西汉后期,另三次则都发生在东汉。至于争论的性质,或以为是两个不同的学术宗派之争[1],或以为是围绕增立博士之争[2],或以为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之争(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章第九节之一,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编第八章第一节,翦伯赞《秦汉史》第二编第十一章第二节之一等,皆同此说。),等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够准确,而其通弊则在于将两汉的今古文之争笼统言之,不加区别。其实两汉今古文之争的性质绝不相同,兹略论之如下。
西汉后期的争论发生在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是由刘歆提出为《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四种古文经立博士引起的。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这件事,结果“诸博士或不肯置对”[3](《刘歆传》。按以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皆出此《传》),即以沉默表示反对。因此刘歆写下了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对博士们加以指责,说他们“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忌,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以《尚书》为备(案指二十九篇之《今文尚书》),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等等。因其言辞过切,不仅招致诸博士的怨恨,也引起了一些执政大臣的愤怒,如大司空师丹即“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这场争论,以刘歆所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的失败而告终,刘歆也被下放到地方做官去了。但这次争论除博士们所谓“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之说,略带学术性质,并没有涉及到任何具体的学术问题。且当时的博士都甚浅陋,大多没有见过古文经,更谈不上有所研究,故“不肯置对”,宜其然也。至于博士们一致反对立古文经的根本原因,则是为了垄断利禄之途,不愿古文经学派出来跟他们争饭碗。因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读经可以做官,著名的经师还可以做大官,今文经学得以迅速发展,到宣、成时期,即已由此而形成了“士族”这一特殊势力。金春峰在其《汉代思想史》(修订增补版)中对此有很好的分析,其中有两段话说:
由于尊儒政策的确定,在社会上,在民间,经学取得了迅速发展,经过六十多年的积累,终于形成了“士族”这一强宗豪族力量。……宣成时期今文经学确立全面统治地位,本质上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
汉代经学重师法、家法,又形成“累世经学”的特殊现象。每一经师,门徒众多,代代相传,党同伐异,壁垒森严,在社会上形成为一种特殊的势力和朋党。……经学的经师或“家”的代表,往往是政府中的大官,相互援引荐举,门生故吏亦纷纷占据要津。于是上下左右,朝内朝外,盘根错节,势力更加牢不可拔。这也是经学在宣成时期能够确立统治地位的原因。[4]
这样一种由今文经学势力垄断政治和仕途的局面,仅凭刘歆的建议,就想让古文经学插足进来,将固有的格局打破,当然是不可能的。
东汉时期的三次争论,第一次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据《后汉书·儒林传·序》,建武初年,刘秀即已恢复了西汉的十四博士之学(注:《后汉书·儒林传·序》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后汉书·百官二》“太常”条所列十四博士同。)。尚书令韩歆又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5](《范升传》。按以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皆出此《传》)。于是“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对韩歆的建议展开讨论。刘秀亲自主持了这次讨论,并指名要今文《梁丘易》博士范升发言。于是范升竭力反对为此二种古文经立博士,“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下来以后,范升又以书面形式上奏朝廷,表达反对意见。范升提出的反对理由,除认为“《左氏》不祖孔子”,传授不明,非先帝所立等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段话:
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令《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乘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己。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范升所竭力反对的是增立博士,而并不问所增立的是古文、今文。《左》、《费》是古文,不消说了,然而《京氏易》属今文,他也反对,只是前此未能阻止得了,至今心中怏怏,还要说它不当立。又其所举可能会竞相争立的经学派别,亦不限于古文,如《高氏易》就属今文。《汉书·儒林传》说高氏名相,其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而丁将军之《易》则受自田何,是《高氏》属今文《易》学无疑。又《春秋》的《驺》、《夹》二家,《汉志》“驺”作“邹”,只说“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是其为今文、古文,尚难断定。当时未立博士的经学派别,远不止上述诸家,故范升又提到“《五经》奇异,并复求立”。所谓“《五经》奇异”,无非是经说互异的各种学派,其中盖今、古文兼包之。而范升之所以反对增立博士,则是为了捍卫经学的道统,故曰“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并引孔子的话,以示“异端”之害而当攻之,而要求“反本”。其所谓“疑先帝之所疑”一语,亦暗示《京氏易》虽立而当废,因为《京氏》主要讲阴阳灾异,与《施》、《孟》、《梁丘》明显不同(注:《汉书·儒林传》曰:“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故西汉先帝于“《京氏》虽立,辄复见废”。因此他主张除现有的博士外,不论今古,一概不再增立,以绝《五经》奇异竞立之望。他把攻击的焦点,集中在“《左氏》不祖孔子”上,又“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而《左氏》学专家陈元对范升的反驳,也集中在说明《左氏》所传乃“孔子之正道”[5](《陈元传》。按以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皆出此《传》),于是相互辩难,书“凡十余上”。这次争论的结果,倒是古文经学取得了部分的暂时的胜利:刘秀虽没有同意立《费氏易》,然“卒立《左氏》学”。当时太常为刘秀提出了四位《左氏》专家的名单,作为《左氏》博士的人选,供刘秀圈定,陈元排在第一位。刘秀却“以(陈)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但李封当时已年迈,不久即病死了,于是“《左氏》复废”。
由上可见,这次今古文之争的性质,已由西汉末年利禄之途的争夺转变为学术道统之争了。这种转变的原因何在呢?这就与古文经学在东汉初年所处的地位有关了。古文经学在西汉一直处于受压制、受排挤的地位(王莽当政时曾立古文经博士,这里姑且不论),但到了东汉,这种局面已经大大改变了。刘秀本人就是古文经学的支持者,这由他“卒立《左氏》”可见。且刘秀自建国之初,就十分重视古文经学及其学者,已经把今、古文经学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大量任用古文经师为官,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如杜林、郑兴、陈元、桓谭、卫宏等,皆在朝廷任职(皆详《后汉书》本传),有的甚至充任朝廷要职如杜林官至大司空,就是明证。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由于通古文经也可以做官,甚至被朝廷所重用,人们自然争趋而研习之。这里还有一条材料,很值得注意,即在这次围绕韩歆提出为《左氏春秋》立博士的争论中,竭力反对立《左氏》博士的,还有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桓谭和卫宏!据《东观汉纪》记载:“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毁訾,故中道而废。”[6]这两位古文经学家具体出于什么理由而加入反对立古文博士的大合唱,因史料缺乏,已不可考。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即以刘秀为首的东汉政权对今古文经学者一视同仁地重视和任用,利禄之途既开,因此是否立学官,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这应该是桓谭和卫宏反对立《左氏》博士的基本前提。
总之,自东汉初年开始,今古文之争,已成为道统之争(谁更能传孔子之道)、学术之争,与西汉末年的今古文之争,性质已迥然不同。我们从发生于东汉的以后两次争论,更可以看出这一点。
东汉的第二次今古文之争,实际是由章帝发起的,是章帝支持古文经学大师贾逵对今文经学展开的一次全面挑战。贾逵之父贾徽就是两汉之际的一位古文经学家,而贾逵则“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而“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5](《贾逵传》。按以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皆出此《传》)。章帝即位,“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诏逵入讲,而“善逵说”,于是命贾逵“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这是章帝在《春秋》学领域命贾逵对今文经学发起的挑战。于是贾逵“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认为“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书上奏章帝后,受到章帝的嘉奖,赐给他布五百匹,衣一袭,并令他“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可见太学此时虽未立《左氏》博士,实已开设《左氏》课程,且选《公羊》学之高才生以教授之,由此开了东汉太学教授古文经学的先例。这是古文经学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贾逵又“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于是章帝又“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这是章帝支持贾逵在《尚书》学领域对今文经学发起的挑战。于是贾逵又“集为三卷”,上奏章帝,“帝善之”。紧接着又命他“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诂》”,这是在《诗》学和《礼》学领域支持贾逵对今文经学发起的挑战。这一系列对今文经学的挑战,由于有章帝的支持,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接着,章帝又命“诸儒(即太学博士)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这就进一步打破了自西汉以来太学只讲授今文博士之学的旧制。章帝不仅让贾逵在太学教授古学,且“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李注曰:千乘王伉,章帝子也。)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后汉书·儒林传·序》也说,当时古文经“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这又开了古文经弟子拜官的先例,实际是自刘秀以来任用古文经师政策的沿续和发展。我们由“学者皆欣欣羡慕”可以看出,此例之开,在当时对学者影响之大。
这次贾逵在章帝支持下对今文经学发起的挑战,基本上是唱的独角戏,即有挑战而无反击,所以严格地说,谈不上争论。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只有一个《春秋公羊》学者,名叫李育,“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义”。在他拜博士前,曾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但并非针对贾逵的挑战,而是有感于“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谶纬,不据理体”而发。李育拜博士后,曾参加章帝于建初四年(79年)召开的讲论《五经》异同的白虎观会议,在这次会上李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如果说对于贾逵的挑战今文经学家有所反击的话,仅此而已。
东汉的第三次争论发生在桓、灵之际。当时著名的《春秋公羊》学者何休正遭党祸“废锢”在家。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他“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这可以说是《公羊》学对《左氏》、《谷梁》二学发起的挑战。然与他同时的郑玄则针锋相对,撰写了《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三书,对其一一加以批驳。于是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5](《郑玄传》)
所谓今古文之争,自西汉后期至东汉后期,近二百年间,见诸史籍而能寻绎其脉络者,仅此而已。由上可见,对于汉代的今古文之争,既不可夸大,以为壁垒森严,水火不容,且贯穿于汉代经学之始终,而对争论的性质,亦不可一概而论,当区别西汉与东汉:西汉是围绕立博士之争,实为利禄之争,东汉则主要是学术道统之争。且就学术道统之争而言,其争点也主要在《左氏》。故皮锡瑞说:“汉之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唯《左氏》、《公羊》为甚。四家之《易》与《费氏易》,三家之《尚书》与《古文尚书》,三家之《诗》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丘明不传《春秋》抵之;韩歆请立《左氏》,则范升以《左氏》不祖孔子抵之。……各经皆有今古文,未有相攻若此之甚者。”(注:见皮锡瑞《经学通论》之《春秋通论》“论《公羊》《左氏》相攻最甚何郑二家分左右袒皆未尽得二《传》之旨”条。)这种说法倒是比较客观的。因此,除《左氏》外,其他诸经之今古文,皆不闻相攻之例,各自传其学,相安无事。就经学的争论而言,今古文之争,还远不如今学内部的争论之甚,且贯穿两汉经学之始终,其例甚多,而西汉宣帝甘露三年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会议,即其显例。
二、关于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今古文经学虽为两个不同的学派,它们对经书的解说不同,治经的方法与学风不同,但它们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经学,在维护汉代封建统治、为封建政治服务方面,都是一致的,两者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是汉代的今古文两派虽有斗争却能够长期并存、并走向融合的政治基础。
今古文经学的融合,发生在东汉,而主要是由古文经学大师完成的。古文经学大师,多兼通今古学,号称“通人”。如“扬雄则称‘无所不见’,杜林则称‘博洽多闻’,桓谭则称‘博学多通’,贾逵则‘问事不休’,马融则‘才高博洽’,……自余班固、崔骃、张衡、蔡邕之伦,并以弘览博达,高文赡学”[7](《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第八》)。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的《伪经传授表下》中还特设“通学”一栏,列举汉代古文经学家而堪称“通学”者达五十余人之多。这种博学兼通,比之大多只专守一经、罕能兼通的今文“章句”陋儒,是一种巨大的学术优势,这正是古文经学大师能促使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学术基础。
今古文经学的融合,还与今文经学自身的腐败以及今古文之间的争议有关。今文经学的腐败,主要在它的烦琐化。这种烦琐化,一是表现在师法、家法的增多。今文经学立博士的就有十四家,而未立博士的今文学派,更是多不胜数,我们只要略翻两《汉书》之《儒林传》便可看出这一点,故而班固有“大师众至千余人”之讥[3](《儒林传·赞》)。二是章句解说的增多,如《小夏侯尚书》学者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3](《艺文志》“六艺”类小序颜注引桓谭《新论》)。故班固批评说:“后世经传既已乘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3](《艺文志》“六艺”类小序)这种烦琐化的趋势,到东汉则更甚,尽管东汉统治者曾多次下令删减经说,终不能扼止这种趋势。这样烦琐化的结果,使今文经学终成无用之学。皮锡瑞说:“凡学有用则盛,无用则衰。存大体,玩经文,则有用;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无用。有用则为人崇尚而学盛,无用则为人所诟病而学衰。”[8](《经学极盛时代》)经学本是为政治服务的。对统治者来说,能为政治服务即为有用,不能为政治服务,丧失其思想统治的功能,即为无用。如果一种学术,烦琐到皓首也难穷经,支离到令人莫知所从,这种学术也就走到尽头了。东汉的今文经学之所以衰落而为古文经学所战胜,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说到今文经学的腐败,人们还往往指出它的谶纬迷信化、神学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当时的时代思想氛围来说,还没有把摒除谶纬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东汉时期,不仅今文经学日益谶纬迷信化,就连古文经学,也跟着谶纬化了,不过在程度上没有今文经学那么严重罢了。
从为政治服务的角度来说,今文经学的烦琐化,固已愈益难餍统治者所需,而今古文经学之间对经书解说的歧异和争议,亦使经学日益背离“尊儒”的初衷。因此,改造传统经学的任务,自然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种改造,在经学范畴内,就只能走融合的道路。
今文经学虽烦琐,但并非一无是处。所谓融合,就是兼采今古文经学之长,革除今文经学的烦琐之弊,重新对经书作简明扼要的阐释,而造成一种新的经说。这一任务,在当时,只能由兼通今古的古文经学家来完成。
首先在融合方面作出努力的,当数许慎。许慎是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却博通群经及今古文经学,故“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5](《许慎传》)。许慎的著作有多种,然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要数《说文解字》,其次则为《五经异义》。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对字义的解释,虽多采古文经说,然亦兼采今文。《说文叙》曰:“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左氏》、《论语》、《孝经》皆古学也。”就其所列举之经书而言,即有《易》孟氏为今学。又《礼》,即《仪礼》,段注说,当时“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许不言谁氏者,许《礼》学无所主也。古谓之《礼》,唐以后谓之《仪礼》,不言《记》者,言《礼》以该《记》也”(注:按段注以为《仪礼》之名始于唐,不确。据文献考之,最迟在东晋初年即已有《仪礼》之名了,参见拙作《仪礼译注》之前言《仪礼简述》一:《关于〈仪礼〉书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是其所据《礼》亦为今文经学。又见于《说文》中明引今文说者,还有《公羊传》五处,分见于“噧”、“辵”、“嘂”、“覢”、“媦”诸字之注;董仲舒说二处,分见于“王”、“蝝”二字之注;《易》京房说一处,见于“贞”字注;《鲁诗》说一处,见于“鼐”字注;《尚书》欧阳氏说一处,见于“离”字注;《五行传》(段注说即伏生《洪范五行传》)二处,分见于“疴”、“沴”二字注,等等。这种兼采,正体现了融合的精神。
更能体现融合精神的,则是他的《五经异义》。惜其书宋时已佚,清人有多种辑本,我们这里用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本。该本辑《异义》凡百条。由该本可见,许慎于有争议之每一事,皆先列举今、古文说,然后以“谨案”的形式,表明自己的看法。其中大部分肯定古文家说,反映了许慎作为古文经学家的基本立场,但也有一些是肯定今文家说的。如关于服役的年龄问题,即肯定今文《易》孟氏说和《韩诗》说,而否定《古周礼》说;论虞主所藏,则肯定今文《戴礼》及《公羊》说,而否定古文《左氏》说;论天子驾数,引今文《易》孟、京及《春秋公羊》说,又引古文《毛诗》说,而肯定今文家说,等等。可见,作为古文经学家的许慎,却并不固执其古文家说,而是以一种较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待今、古文经说,是则肯定之,非则否定之,且由此亦可见许慎对传统的今古文经学皆已不满,而企图对之加以改造,故陈寿祺在其《五经异议疏证》之《自叙》中说:“叔重此书,盖亦因时而作,忧大业之陵迟,救末师之薄陋也。”
今古文经学的改造、融合,最终是由东汉末年的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郑玄在《戒子书》(附见于郑玄本传)中述其平生之志曰:“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所谓百家,即指今古文及其间所包含的林立的派系。将此林立之派系,纷纭之经说,加以改造而整齐之,一统于他所理解的“先圣之元意”,此即郑玄平生之志。郑玄之所以终身不仕,就是为实现他的这一志向。因此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5](《郑玄传》),而遍注群经,对各经皆以经过他改造而融合今古文经说之长并参以己意之说,重新解说之。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非郑玄这样博学宏通之大儒不能胜任。经过他的这一番改造,今古文的界限不见了,家法、师法的藩篱不见了,而使经学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学者称之为“郑学”。长者出而短者黜,新学出而旧学衰。当汉末经学派系林立、官方经学烦琐可憎、学者无所适从之时,博采众家之长而又简明扼要的郑学的出现,自然使人们感到新鲜可喜,“自是学者略知所归”[5](《郑玄传》),皆争趋而学之。于是郑学出,而两汉传统的今古文经学皆衰微了。皮锡瑞说:
所谓郑学兴而汉学衰者,……学者苦其时家法烦琐,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故经学至郑君而一变。[8](《经学中衰时代》)
可见郑学盛行,而两汉经学之家法皆因罕有人传习而渐趋衰亡。皮锡瑞又说:“郑君党徒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8]非虚美之辞也。清代的今文经学家,每以汉代经学家法的灭亡归罪于郑玄,这是不公平的。殊不知优胜劣汰,新生战胜腐朽,是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郑玄何罪之有?两汉传统经学的灭亡,咎在其自身,而不在郑玄也。
收稿日期:2000-05-09
标签:古文尚书论文; 汉朝论文; 春秋论文; 历史论文; 古文论文; 仪礼论文; 今文经学论文; 东周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甲骨文论文; 金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