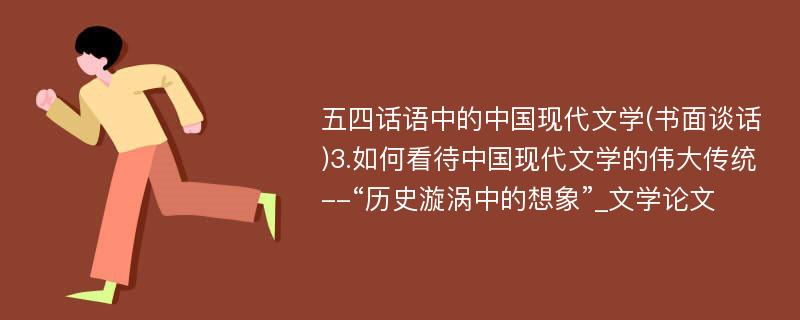
五四话语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笔谈)——3.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传统——在历史的旋涡中展开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笔谈论文,旋涡论文,如何看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社会分化,要求文学和作家积极介入公共领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很多人甚至认为,文学在当代影响力的下降,是因为作家放弃了公共职责。当年曾经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纯文学”等概念也因此受到了相当强度的质疑。该如何考虑文学和作家的当代选择?文学该如何参与公共问题?又能参与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简单的道德义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对“文学”知识本身的历史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文学充分介入历史空间,文学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社会历史职责,这种观念意识既传统也现代。说它传统,从“文学”角度来说,是因为“诗史”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屈原到杜甫、白居易,无数的中国古典诗人用他们的笔记下了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的景象,期望以此促进社会现实的改良。而从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分子”的产生历程来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知识分子”虽然与儒家的“士”有很大的区别,但也继承了“士”的强烈的“济世”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主流作家多数是怀抱着济世救民、传播新文化、改造中国现实的理想而走上创作道路的。文学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在中国文学中有悠久的传统,我们在看到这一点的同时,更应该意识到,中国文学的这个特色更是一个现代事件。因为独立的“文学”知识门类本身就是现代的产物,现代以前并没有独立的“文学”观念。“五四”前后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知识分类和现代大学学制,“文学”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才产生了归入“文学”门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当我们说“文学知识分子”该如何如何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谈论现代问题。
文学和文学从业群体必须充分介入现实作为一个现代事件,最集中地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过程中。在古代中国,并不是每一种“知识”都被看做能够承担“济世”功能的。这一点对虚构性的文字写作知识来说极为明显。古典的“诗史”传统主要是针对诗和文,词曲小说是士大夫羞于启齿的文类,更不用说去讨论它们如何载道济世了。与此相应的是,“士”在古代有时也称为文人,因为他们从事着文字研究与写作工作。但是文字研究和写作工作必须“经世致用”,才是“士”的工作。专门从事文学想象工作包括诗文写作,在古代并没有什么地位。纯粹的文学想象工作比如虚构小说获得比较崇高的地位,更是现代的产物。其中最主要的核心因素是启蒙文化。梁启超提倡以“小说新民”,小说成为了载新文化之道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小说逐渐由不入流的文体一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类家族中的大宗,小说家也由人们羞于启齿的身份一度转变为大众的精神导师。
文学及其从业人员应该努力去承担重大历史职责,这种身份意识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事件。谈论这些问题,无非是想说明一个基本观点:并不存在一个关于“文学”和“文学知识分子”群体的标准定义,人们关于各种知识包括各种知识群体的种种想象或定位无疑都是存在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明确这一点,无疑对于人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知识分子问题,会打开更为宽阔的视野,而不至于从某个先验的界定出发,去裁判不同的知识群体,从而掉入自己设计的种种逻辑陷阱。
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话题一直是长盛不衰的题目。80年代的人们通常用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独立审美意识的失落与复苏来概括从“五四”到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分子的历程。这种历史叙述表达了追求独立创作权的愿望,但是“从失落到复苏”这个措辞显然预设了一个关于文学知识分子的标准定义。这种愿望表达方式使当年的人们陷入了一种很明显的逻辑悖论状态:一方面高调指责“文以载道”,另一方面却不假思索地强调新启蒙、改造国民性。力图从某个本质化的定义出发思考问题,更为突出的表现是逻辑专断,蒙蔽了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比如,80年代还形成了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中国文学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萌芽于“五四”,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中国文学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独立地位,甚至被取消。联系到小说家地位提升的过程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学知识分子执行的职能,我们应该看到,革命意识形态其实没有消灭文学知识分子,而是希望用另一种“道”——革命意识形态取代五四启蒙之“道”。
当然,革命意识形态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当这个“道”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后,文学知识人所载的这个“道”,事实上与“国家政权”失去了距离。在国家意志强烈的一体化要求下,人们失去了在国家政权之外展开想象、批判甚至是生活的空间,这不仅仅严重违背了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想象中有着重要地位的“个人主义”追求,而且也使知识人的多样化选择成为不可能。也就是说,革命意识形态取消的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多样化的知识追求,尤其是“五四”个人主义。但是从“文以载道”的角度来说,用文学的方式讲述民族的新文化,承担中国现代化的大叙事,启蒙意识形态、革命意识形态和80年代的新启蒙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基本特色:在充满政治色彩的文化旋涡中层开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也正是在其中形成了“精英”意识,所以,今天的人们希望文学知识分子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承担公共职责无疑是这种传统一脉相承的结果。
立足于今天的历史环境,如何看待这个传统,是一个很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简单地说继承或放弃这个传统并无济于事。指责作家犬儒,沉迷于形式技巧,缺乏公共意识还只是一种宽泛的道德要求,而且容易陷入种种本质主义的思考藩篱。在一种历史化的思考中,讨论特定知识以及特定知识分子群体的公共职责问题,还必须联系到特定知识在目前的知识场域中所处的位置。
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是有其专业身份,知识合理化和现代大学学科设置使知识分子以特定专业属性出现在人们面前。因此,谈论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问题,回避不了如何实现专业知识与公共价值的结合。在文学领域,很长一段时间,文学界经常哀叹中国文学知识分子缺乏专业意识,反反复复检讨自己过于入世,不能专注于纯粹的审美追求。虽然极力强调纯粹的审美追求,但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比如在80年代,人们的这种专业性追求并不影响其公共价值。因为相对于国家意志一体化的历史环境,“纯文学”包括其他学科的独立性追求,表达了从国家意志一体化中解放出来的普遍愿望,这是为什么很专业的“纯文学”问题会成为重大历史问题的原因。而近20年来,随着国家意志逐渐调整对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控制方式,加上市场机制和西方学院知识评估体制的进入,知识人所面对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比如在当年,一种非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会被视为挑衅国家意志的权威,而今天一位作家谈论一种新的叙事形式,很大程度上只具有专业性的价值。尤其是在市场机制下,夸张的修辞、特立独行的人物形象很多时候只有广告策划意义。
随着各学科独立性追求的政治性淡化,专业性突出,不同学科从业人员在公共场域中的地位也相应发生改变。文学从业人员在这一结构领域中的地位变迁表现得很突出。中国现代作家经常扮演着时代思潮引领者的角色,而90年代以来,作家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文学抛弃了社会,最终自己被社会抛弃。其实,单纯从文学是否关心现实出发,很难说明文学和文学从业人员影响力下降的原因。无论是目前的网络写作,还是在一些成名作家的作品里,我们仍可以看到大量深刻介入现实的作品,只不过没有产生当年的社会影响。
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前面提到的专业分工,早在80年代,王蒙《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就曾提到:“要求惩治坏人的人去找律师检察院,要求打发时间的人干脆去看《卞卡》,他们都没有必要一定去找作家找文学作品。”另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是媒介形式的多样化,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用文学的方式反映现实,所产生的冲击力已经无法和电子媒介相提并论。不要说用文学的方式反映现实,即使虚构故事,目前小说也很难应对影视剧的挑战。因此,在这个媒介形式迅猛发展、经济问题占据着人们生活中心的时代,当我们期望作家承担历史责任的时候,人们首先要问的问题是:文学还能做什么?
谈论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不仅仅文学从业人员必须检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公共问题的结合点,在一个专业分工精细、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的时代,其他学科的从业人员同样如此。公共问题总是与各种专业知识联系在一起,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公共知识等待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去探求去发问。这时,人们必须思考,一位专家该如何谈论自己不熟悉的公共问题?不同的谈论方式对于问题的解决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无疑都是必须仔细辨析的问题。人们或许会指出,专业体制划分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本身是一种需要批判的对象。今天,知识分子的批判指向无疑应包括现代学院专业体制。但是,立足于批判是一回事,如何批判又是一回事。前者是个立场选择问题,并不仅仅关涉到知识分子,因为一个非知识分子也同样可以做出相同的选择。而后者则无疑需要进入一个相对专业化的领域。比如,谈论“纯文学”如何遮蔽了文学形式与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隐蔽联系,又如何影响文学知识人积极介入当代的历史空间等问题,都是在文学知识的边缘探求“纯文学”和各种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跨学科的努力表现出对现代学科分类体制的反动,但无论何种努力都隐含着特定的学科逻辑。也就是说,目前的跨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目前的学科分类为前提的。
必须指出的是,谈论知识分化后知识人的种种局限,并不是否认知识分子介入时代公共空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新文化,上下求索,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多数知识人以社会不公正的批判者作为自我定位,作为一种伟大的传统,我们无法用专业追求简单打发。面对激烈分化的时代,经济传统促使着知识分子参与现实问题,这是知识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之所以称做“传统”,是要说明它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过程,深刻切入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但又不是先验本质的东西,从而保持着对未来或对异类的开放性。因此,当今天的知识人背负着这种传统向时代发问的时候,无疑必须首先检讨:在当前的知识结构场域中,不同的知识还具有什么样的历史能量?这些能量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达到最大化。比如“纯文学”问题,做一名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在目前的中国语境是否可以成为一种选择?如果可行的话,那么专业性很强的“纯文学”理想则从一个“意识形态”转而成为一种充满现实批判性的资本时代的梦。此外,知识的传承与积累需要相对独立的空间。儒家士大夫一般不会问:树叶为什么是绿色?月亮为什么是圆的?鱼为什么只能生活在水里面?这些似乎无用、无精神高度、甚至无道德关怀的种种知识探讨,我认为是有着悠久而深厚经济思想的中国知识人所必须重视的内容,到今天仍然有强调它的意义。
标签:文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