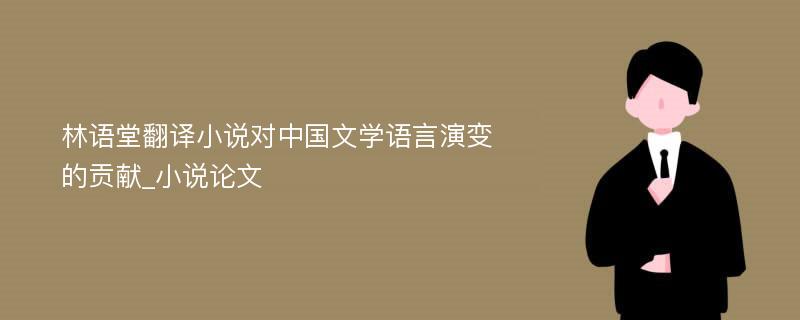
“林译小说”对中国文学语言演变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贡献论文,语言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学语言由“雅”到“俗”的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曲折发展的过程。自古至今语言的革新从未停止,由难懂的方言、典雅的书面语言逐渐向规范化、通俗化方向发展。林纾深知这一点。“五四”时期,他被视为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其实是误会。
早在1913年2月24日, 林纾就在新创刊的《平报》“社说”栏发表了《论中国丝茶之业》,提倡创办白话报,以宣传养蚕知识。(注: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第3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他还是白话诗的最早写作者,他的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1897)比胡适的《尝试集》要早二十年。他盛赞“《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还说:“非读破万卷书,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注:林纾《致蔡鹤卿书》,见《林琴南书话》第20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这表明他对白话小说《水浒传》、《红楼梦》是肯定的。他反对白话文运动,与他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一样,认为社会和文学的发展须循序渐进,不可走“极端”,犹如王元化先生不主张所谓“激进主义”(注:王元化《我不赞成激进主义》,《英才》2000年第九期。),并不反对白话文,而是反对取消文言文。因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呼吁彻底废除文言,才激怒了林纾。如果有人以林纾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为例,证明他在文学语言的“顽固”,那就错了。相反,“林译小说”在文学语言演变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指出:
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的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狄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注:《胡适文存二集》第121—122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胡适虽肯定林译小说对古文的继承与突破,但他未能指出林译小说与古文的“质”的区别,更没有看出“林译小说”在语言通俗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林纾是古文家,推崇“左氏传、马之史、班之书、昌黎之文”,认为这四家是“天下文章之族庭也。”(注:陈希彭《十字军英雄记》,见《春觉斋著述记》卷三第30页。) 但他翻译外国小说所用的语言与其古文作品有很大区别。他也从不把自己的译文与古文混同。其《春觉斋论文》说:“适译《洪罕女郎传》,遂以《楞严》之旨掇拾为序言,颇自悔其杂,幸为游戏之作,不留稿也。”(注:《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第111页。) 他连译书序跋尚且不承认属于纯正的古文,更不必说译文了。
众所周知,古文家特别重视语言的“纯正”、“雅洁”。至桐城派对古文语言的要求更严格,诸如不许使用时文评语、传奇小说、市井白话、尺牍口气以及艳词丽句。林纾的古文创作和古文理论较之桐城派规则更为严格,绝不许古文中“窜猎艳词”、“鄙俗语”和近代出现的“东人新名词”。他曾从袁宏道文集中摘出“徘徊色动”、“魂消心死”等词,指斥道:“‘破律坏度’,此四字足以定其罪矣。”(注:《春觉斋论文·论文十六忌·忌轻儇》,见香港商务印书馆1963年《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第101—102页。) 但当他翻译外国小说时,便感到这些规定和禁忌已不适用。林译小说其实便使用了大量俗词白话。书名如《恨绮愁罗记》、《恨缕情丝》、《金台春梦录》等等,使用了纤艳丽句。其他词汇,如“小宝贝”、“爸爸”、“阿姨”、“儿子”、“姑娘”、“接吻”、“伙伴”、“母鸡”、“老伴”等都是俗语。此外,还使用了许多“新名词”,如“股票”、“专制”、“自由”、“民主”、“社会”、“地球”、“个人”、“团体”、“神经”、“俱乐部”等等,以及许多外来的音译词,如“马克”、“法郎”、“布丁”、“安琪儿”、“咖啡”、“密斯脱”、“密斯”等等。这不但带有“洋味”,也令读者一看就知是翻译作品。《迦茵小传》写道:
迦茵入室,易湿衣,衣湿直透肌肤之上。乃易取礼拜日礼服,焕然照眼,衣作灰色,而领缘袖口,均白罗折叠,通明作云态,尽梳整其发作懒妆,垂巨结于后。迦茵初不觉,而绝世风姿,益以妆点,其一时无两之秀媚,殆出天然。妆毕,至客座,啜茗而已,不能进膳。自念吾命胡为人凌践至此?觉此时荣卫之内,均如火灼。顾今亦不管许事,且进省格雷芙矣。阿姨十二句钟可归,今日殆终局之日,见格雷芙一倾吐其款曲,明日或为阿姨所逐,正在意中。于是秉烛入面亨利。甫至门,迦茵足停,适见亭立一巨镜,再以烛奴一照,遂得备细自照其姿容,此第一次已与已相见而惊其美也。自觉具此绝世风格,在希腊古史中,正宜演出无穷事业,乃一身竟孤飘至是。瞥见己之双波,如剪秋水;睫毛秀润,适当双蛾之下;樱口微绽,如乳婴浓睡弄笑状;匏犀微露,灿白如象牙;……一堆金黄发,蓬蓬若结云气。此时衣色深灰,愈显其倾国之貌。迦茵徘徊审视久之,曰:“镜中人良不吾欺也。”以此之故,希望遂生。(注:《迦茵小传》第十四章第89—90页,见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这段场景描写,其实不能登“大雅”之堂,与古文“雅洁”的要求极不相符。出现这种情况不可能是林纾的一时疏忽。钱钟书说:“林纾译书所用的文体是他心目中以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着若干‘古文’的成分,但却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大。”(注:钱钟书《七缀集》第94—95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 的确,林译小说中有不少白话口语。钱钟书曾举《滑稽外史》第二十九章用了“便宜”二字:“惟此三十磅亦非巨,乃令彼人占其便宜,至于极地。”类似的例子在林译小说中比比皆是,如《块肉余生述》:
而余之恨壁各德至于次骨,即斥之曰:“畜生!”(第2章)
迦茵勿多言,讵吾之性质汝弗知耶!(第4章)
即六辨士之微,亦不之受。(第5章)
股肱皆紧附如香肠。(第7章)
汝为我世界上知心之良友。(第8章)
彼又思及老伴矣。(第10章)
专为吾肆招延贸易。(第11章)
此人空前绝后之大学问家也。(第17章)
且未交一言,已涌身投于情海。(第26章)
尤利亚曰:“伙伴言之。”(42章)
出表,待此五分钟。(第52章)
这些译文中的“畜生”、“性质”、“辨士”、“香肠”、“世界”、“老伴”、“贸易”、“大学问家”、“情海”、“伙伴”、“五分钟”等,无法用文言恰切地表达。另外,有些口语必须使用白话,是刻画人物所必要的。《迦茵小传》描写:“格林华德氏大笑,以手指迦茵曰:‘妮子,果诚悫哉?以汝发披其肩,容颜如玉,大似天仙化人,宜其不打诳语。以吾决之,汝必不忍于密室中亲吻,人果欲亲汝者,想汝必回身避之矣。’”(注:《迦茵小传》第十四章第11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便使用了“妮子”这样的口语。可见, 林译小说的语言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文。
林译小说中还使用了大量的外来语。如前文所举“布丁”、“辨士”、“星球”等。再如,《黑奴吁天录》第15章:“彼夫妇在蜜月期间,两情忻合无间。”《离恨天》第10章:“人生地球之上,地之沐阳光者亦仅有其半。”《块肉余生述》第4章:“余译其意,即专制之别名。”第19章:“且在此小社会中实冠其曹偶。 ”等等。此外,林译小说中还有大量外来名词的音译,如“佛郎”、“马克”、“卢布”和所有人名、地名等。林纾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使自己的译作带些“洋味”,另外有些音译是“信”所必须要求的。对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读音,他就直接采用音译,如“密斯”、“密斯脱”、“密昔司”、“咖啡”、“布丁”、“安琪儿”等,而对中国读者较陌生的外文读音则加汉文注释或将外文单词照录在译文中。如:“列底(尊闺门之称也),安可以闺秀之名保此人,此人听老夫保之。”(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第5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此外,林译小说中还出现了不少欧化句法,与古文的区别更为明显,以至“林译小说的语言不是古文的语言,这应该是无须怀疑的了。”(注:张俊才《林纾评传》第149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林译小说对文学语言的改革显然适应了新时代的要求。
三
在晚清众多的翻译小说中,林译小说大受读者青睐,甚至在1981年商务印书馆重版《林译小说十种》竟迅速销售一空。这是意味深长的现象。“五四”时期,林纾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中,从语言演变规律的角度反复申诉:“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说明他并不反对白话,而是认为白话文须有古文基础。但他仅凭自己的感悟,不会从传统与现实不可分割的理论上解释这种关系。然而在文学实践中,林译小说既保持了传统古文的韵味,又进行了通俗化的改革,发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必要环节,对中国文学语言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注释:
①韩愈《进学篇》,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精读》(下册)238页,张大新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