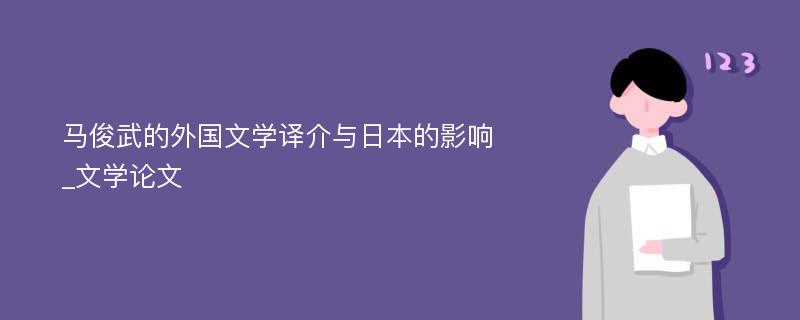
马君武的外国文学译介与日本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外国文学论文,马君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182(2007)03-0102-06
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字厚山,后更名同,留学日本后又更名和,字贵公,号君武,后以君武行。曾用笔名有贵公、马贵公、马悔等。马君武出生于广西一个小幕僚家庭,父亲早年去世,由母亲做工抚养并随表舅读书,1899年考入桂林体用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后因撰文评论朝政得失而被开除。之后马君武远赴新加坡,见到流亡中的康有为及其弟子徐勤等,开始了他与保皇派的一段交往。1900年到1901年间曾在广州、上海读书,1901年冬赴日,1903年9月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制造化工专业,成为京都大学第一个外国留学生。1905年参加同盟会,后回国,曾执教于中国公学并参加国学保存会,1906年末,因官方缉捕远走德国。辛亥革命后归国并积极参加南京共和政府筹组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赴德国留学,于1915年获柏林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留德学生中第一个获得工学博士学位者。归国后曾积极参与政事,任交通署长、广西省长等职,后致力于教育,1940年病逝于广西大学校长任上。
在南社作家群中,马君武是桂冠最多的一个。他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杰出的教育家和学者,卓越的翻译家和爱国诗人。
由于时代的关系和个人的际遇,马君武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翻译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马君武早年外国文学翻译活动中来自日本的影响做一些带个人色彩的、但尽可能客观可信的梳理。
一、马君武的雨果、拜伦观与日本的关系
以现有资料看,马君武最早提到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文字,是他发表于1903年《新民丛报》第27号的《茶余随笔》。该文由“爱国之女儿”、“菲律宾之爱国者”、“中国人无公共心”三节短文组成,雨果(文中译为雨苟)的名字出现在第二节“菲律宾之爱国者”中,这段文字主要是介绍菲律宾爱国作家黎沙儿① 和他的绝命诗《临终之感想》(今译《我最后的告别》)的。马文可能是受到当时梁启超文风的影响,在切入正题前大肆铺排,列举了一系列爱国者。有能言之爱国者,如甘必大;能行之爱国者,如克伦威尔;成功之爱国者,如华盛顿;失败之爱国者,如玛志尼、巴枯宁。雨果被列为能以文爱国者,“所谓能文之爱国者,发挥共和,鼓吹自由,排除王政,九死不悔,若拉马尔登(今译拉马丁,法国诗人)、雨苟之徒,即其人也。”[1] 109作者对雨果的看法,显然不是从其文学成就出发,而是注重其政治作为的,他是把雨果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热爱“自由”、坚持“共和”的民主斗士来看的。
半个月之后,马君武在《新民丛报》第28期上又发表了《欧学之片影》,其中的《十九世纪二大文豪》一节,说的就是雨果和拜伦。为什么在诸多欧洲文豪中他对雨果、拜伦特别注意,另眼相看呢?马君武在文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十九世纪之大文豪亦多矣。其能使人恋爱,使人崇拜者,非苟特(歌德),非许累尔(席勒),非田尼逊(丁尼生),非卡黎尔(卡莱尔)。何以故?因彼数子之位格之价值,止于为文豪故。至于雨苟及摆伦则不然。
雨苟者(一作嚣俄),法兰西之大文豪也,而实爱自由之名士也、国事犯也、共和党也。摆伦者,英伦之大文豪也,而实大军人也、大侠士也、哲学家也、慷慨家也。若二子者,使人恋爱,使人崇拜,使人追慕,使人太息。[1] 126
原来作者所在意的并非他们的文学创作,而是他们“之位格之价值”超越“为文豪”之处,是他们作为“爱自由之名士”、“共和党”、“大军人”、“大侠士”的所作所为。因此,他的文章重点也就不是介绍他们的文学成就,而是歌颂他们反对专制、帮助弱国反抗异族统治的功绩。因此,在行文中作者对雨果、拜伦的作品介绍得极为简单,只是列举了一些书名,而对他们文学之外的活动却大加渲染。
雨苟幼时喜讴歌拿破仑第一之功德,投身王党,及后入议院为议绅,则翻然与拿破仑第三之帝政相反对,以是被放。及拿破仑第三败,雨苟复归,大为国人所崇敬。及千八百八十五年雨苟死也,举国哀悼,以国礼葬之,诚文人旷世之荣典也。[1] 127
摆伦曰:大丈夫常立赫赫之功名于世间,故居常当练习戎器,操柔筋骨,使吾身能当风尘波涛之各种险恶,而不为所困。后居意大利,闻希腊独立军起,慨然仗剑从之,谋所以助希腊者无所不至,竭力为希腊募巨债以充军实。大功未就,罹病遽死。英伦失其第一文豪,希腊失其第一良友。希腊通国之人莫不震悼,为服丧二十五日,下旗,鸣炮三十七响以志哀,因摆伦得年三十七也。[1] 128
可见,马君武对雨果、拜伦的推崇是他们反抗专制、帮助弱国的非文学活动和他们的政治态度。那么,为什么马君武对雨果和拜伦会抱有这样一种评价和看法呢?我们知道,马君武在赴日之前,的确已经有相当好的英文与法文基础,对于雨果和拜伦的作品他应当可以读懂原文,他在《十九世纪二大文豪》中,介绍雨果和拜伦作品篇名时,用的都是法文、英文原文,这也很能说明问题。但是,无论我们怎样设想,20出头的马君武在到日本不足半年的时间里读过了雨果、拜伦的大部分原作(考虑当时国内的情况,他在国内大量阅读雨果、拜伦的作品更不可能),并且因此产生了对他们的看法与评价,依然是不现实的。那么,马君武侧重从文学之外的贡献,或者说侧重从政治的角度来评价这两个欧洲作家,这样一种观点是来自何处呢?我们先来考察一下马君武当时所处的文化环境。
(一)马君武的留日经历和他与改良派的关系
马君武是南社成员中与改良派有过密切关系的少数人之一。他是1901年冬经香港赴日本横滨的,经他的同乡、大同学校教师汤觉顿介绍,住在大同学校并与梁启超结识。而在此之前的1900年,19岁的马君武就在新加坡谒见过康有为并执弟子礼,当年他还奉康有为之命回国策应唐才常自立军的起义,虽然起义失败,马君武也未能完成师命,但因此一事,他也算是康门弟子了,到横滨之后他和梁启超关系密切也就在情理之中。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8日创刊,马君武就开始在上面发表文章,虽然马君武后来说这一段的文字生涯是因生活窘迫,卖文为生的。不管是因“颇穷困”“以谋自给”,还是当时与梁启超思想相投,总之,这一时期的马君武勤于笔耕,文章频频见报。而且其“欲改革中国,则必自改革中国之道德始”,[1] 128 [2] 不但主张与梁启超的“新民”说气味相投,连句法都与梁的极为相似,可见他当时不仅与梁启超声气相通、交谊甚笃,而且受梁氏影响极深。在马君武发表前述两文之前的1902年秋,梁启超在横滨还创办《新小说》,目的是“专欲鼓吹革命。”因“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鄙人感情之激昂,以彼时为最矣。”[3] 298梁氏在他反满情绪最为激昂之时创办了《新小说》,并且第2期(1902年11月15日)上就刊发了雨果和拜伦的画像,像的背面附有简单的文字介绍,这个介绍比马君武《欧学之片影》中的介绍早四个多月,是中国关于雨果、拜伦最早的文字介绍。② 我们把它与前文中马君武《欧学之片影》中的《十九世纪二大文豪》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
嚣俄(雨果)生于千八百二年,卒于千八百八十五年,十九世纪最著名之小说家也、戏曲家也。少有神童之目,十六岁时应法国学士会院(按学士会院者法国文学之渊薮也)之悬赏投诗一首,惊倒一世。其后著作愈富,各国无不争翻译之。嚣俄不特文家而已,又大政治家也,晚年为国民议会议员,大有建白。其没也,法人荣以国葬之礼,年八十三。
摆伦生于千七百八十八年,卒于千八百二十四年,英国近世第一诗家也。其所长专在写情,所作曲本极多,至今曲界最盛行者尤为摆伦派云。每读其著作如亲接其热情感化之力最矣。摆伦又不特文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当希腊独立军起,慨然投身以助之,卒于军,年仅三十七。[注:《新小说》第2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902年12月14日)。标点为笔者所加]
对比上文,我们会发现马君武的《十九世纪二大文豪》一文,对雨果、拜伦的介绍要详细,资料也更多,不但列举了他们的重要作品,还谈了二人的婚姻生活(笔者未引),但是强调他们文学之外的建树和死后的哀荣这一点并无太大变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同属于改良派系统的两大刊物上,连续出现把雨果拜伦相提并论、并且同是看重他们反抗专制压迫特点的文字,这一点本身就耐人寻味。联系马君武从1901年底就开始的与梁启超的密切关系,就不能排除这两个刊物上关于雨果、拜伦的文字间潜在的联系。《新小说》上关于拜伦的介绍,除生卒年等最基本的信息之外,作者特意强调拜伦为“一大豪侠者”和他帮助希腊独立斗争的义举,而对他创作的介绍却不够准确,说“其所长专在写情,作曲本极多,至今曲界最盛行者尤为摆伦派云。”很可能是作者在写此短文时,还不太了解拜伦和他的创作,而是以当时执笔者在日本能见到的资料为依据的,③ 但是取舍和评价时却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与视角的,因为据现有资料看,日本的拜伦接受并不特别强调他帮助异族争取民族独立的“侠”举。但是拜伦帮助希腊人这件事对于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却是格外的有吸引力、有宣传价值。因为他们正处于“双重奴隶”的惨境:被满族统治压迫了二百多年,又面临列强侵略、瓜分祖国的危险。这时候,发现拜伦这样的“大豪侠”,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鼓舞和激励。而恰好这一时期在舆论界影响极大的梁启超,又对义和团运动后满清政府的反动极为义愤,加上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他对勤王起义已不再抱希望,转而致力于启蒙宣传,思想上也开始倾向反满革命。雨果反抗专制和拜伦帮助希腊人争取民族独立,恰恰是一种可以借鉴的资源,用来宣传、表达他此时的主张,而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思想主张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在这样一种语境中,雨果和拜伦就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不仅代表争取自由、平等、民主的战斗精神,也代表西方国家中帮助被压迫民族摆脱外族统治压迫的正义力量。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马君武写《欧学之片影》时,通过西文或者是日文,接触了较为详细具体的关于雨果、拜伦的资料,但由于处于同样的语境和一致的思想,在选择侧重点和进行评价时,自觉地秉承了《新小说》上短文的观点。这种推测也可以从对拜伦的《哀希腊》的翻译上找到旁证,梁启超在他1902年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翻译了拜伦《哀希腊》中的两节,马君武1905年翻译了《哀希腊》全部16节,虽然此时的马君武已成为孙中山革命派中的骨干,政治上已与梁启超分道扬镳,但他选择翻译此诗的想法和目的与梁启超却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还是对梁氏的补充与完善。与梁启超一样,马君武不但是借拜伦的“我为希腊一痛哭”,来哭“可怜国种遂为奴”的中国,即所谓“拜伦哀希腊,今吾方自哀之不暇尔”;而且还要借拜伦的诗告诉中国人“自由非可他人托”,“国民自是国权主”的道理,可以说,马君武最初的雨果、拜伦接受直接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当然也就间接地受到日本文坛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特别的接受方式,马君武拜伦接受的着眼点从一开始就明显不同于日本文坛,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二)日本文坛的拜伦介绍对马君武的影响
马君武《十九世纪二大文豪》关于拜伦的评价与木村鹰太郎的《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有一定的联系。首先从时间上看,木村的《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1902年7月出版,马君武的文章是1903年3月27日发表,中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以当时中国留日学界对日本文坛的关注程度看,马君武极有可能在写这篇短文时已经见到过木村氏的著作。从文章的内容看,马君武文中有“喜讴歌拿破仑”,木村书中有“拜伦既爱为自由而战斗之华盛顿,亦爱蹂躏世界之拿破仑之大意志。”④ 马君武有“故居常当练习戎器,操揉筋骨”,木村有“仍不废乘马出游之事,亦常入近所林中练习短枪”。④ 马君武说“大功未就,罹病遽死。英伦失其第一文豪,希腊失其第一良友。希腊通国之人莫不震悼,为服丧二十五日,下旗,鸣炮三十七响以志哀,因摆伦得年三十七也。”木村曰:“马维罗科达托公(希腊独立军领袖)知拜伦之死为希腊至痛之事,感其国家并其自身失去无二良友之双重悲哀,(中略)由大炮台放三十七发大炮,此乃高贵死者之年龄也。(中略)国民丧期二十一日。……”④ 以上对比可以看出,除服丧期有21天和25天的差别外,马君武文中的基本材料与木村的并无太大不同。虽然如此,但与梁启超和苏曼殊一样,马君武对于拜伦援助希腊独立战争的着眼点与木村鹰太郎有很大的区别。木村氏的着眼点是拜伦的自由主义和反抗精神,是从他的性格出发。“拜伦乃以自由主义之人,不能漠然坐视”,“彼自尊心强,决不立于人后之秉性,常颂叛乱、自由之精神。尝曰:‘人若不必为本国自由而战时,可为他国而战。’”⑤ 马君武则着眼于他帮助被压迫民族的无私、慷慨,“谋所以助希腊无所不至,竭力为希腊募巨债以充军实。”当然,从马君武的语言能力考虑,他对拜伦的了解很可能还有其他渠道,比如,木村鹰太郎在《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的“凡例”中列出的英文参考书Thomas Moore的The Life of Lord Byron with His Letters and Journals,就不能排除马君武也有读过它的可能性。
二、马君武的其他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日本留学经历
据现有资料记载,马君武对外国作家作品的介绍翻译除上面谈到的雨果与拜伦外,还有歌德的《米丽容歌》,即著名的“迷娘曲”,选自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阿明临海岸哭女诗》,选自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的剧本《威廉·退尔》;英国诗人胡德的《缝衣歌》;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心狱》(今译《复活》)、《绿城歌客》(今译《卢塞恩》或《琉森》)等。
(一)马君武的德国文学翻译与日本留学经历
马君武曾两度留学德国,他精通德语,熟悉德国文学,推崇德国文化,但他的德国文学翻译却早在他留德前的留日期间就开始了,如《米丽容歌》(由于印刷错误或作者笔误,该诗出版时印成《米丽客》)大约译于1903—1905年间,但是他的这一译诗的蓝本是否德文却令人怀疑。据1914年6月由上海文明书局印行的《马君武诗稿》,《米丽容歌》中译文后所附的确实是德文,但是据史料看,马君武留日之前在桂林的体用学堂学过英文,在广州和上海的教会学校学过法文,却并无学习德文的记载,而他滞日期间也无学习德文的记录。马君武在日期间尚不通德文还有一个旁证:1903年旧历元旦(实为正月初二即1903年1月30日)马君武在留学生会上演讲公开倡导排满,惹恼了留学生总监汪大燮,汪一开始想遣送他回国,后又试图化解矛盾,动员马君武去欧美留学。之后汪大燮致函汪康年说:“马君武其人通英法文,笔下亦颇好,故前劝其赴欧美留学,居然劝动。”⑥ 信中只说马君武通英、法文,并没有说马君武通德语,以汪大燮留学生总督的身份和马君武在留日学界的名气,如果他真通德语并且已达到能翻译诗歌的水平,汪应该不会不知道。那么,1914年版的《马君武诗稿》中《米丽容歌》译文后所附的德文,能否用来证明他翻译此诗的蓝本是德文就值得推敲。而至今也未发现《米丽容歌》在此前发表过的线索,因此其原始状态究竟如何就成为一个悬案。如果《米丽容歌》真是马君武在日期间所译,那么他当时译此诗所据蓝本很可能是英文或日文而非德文。假如我们找不到新论据否定马君武此诗是在日期间的译作,那么,不管翻译的蓝本是何种语言,他选择翻译这首诗应当是和日本文坛歌德接受的情况有关联的。
当时,整个中国留日学界都把日本作为了解西方的窗口,很关心日本在各方面对西方的接受,马君武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也应当注意日本文坛当时的动向。那么日本文坛的歌德接受又是什么情况呢?虽然从明治四年(1871)开始歌德的名字就随着一些西方著作的翻译、介绍传到日本,但他真正作为一个文学家被介绍翻译却是明治20年代的事。除不太知名的《独逸奇书·狐的裁判》(歌德根据民间故事写的《列那狐的故事》之日译本)外,最早被介绍翻译的作品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有明治22年中井喜太郎根据1802年的英译本的翻译,明治24年高山樗牛根据德文本翻译的、题为《淮亭郎的悲哀》的译本。中井喜太郎的译本由于所依据的英文原本误译不少,再加上他的翻译不完全,受到了精通德文的森欧外的批评。有趣的是,由于森欧外当时在日本文坛的声誉和影响,他对中井喜太郎的批评引起了人们对歌德这部作品的关注,从而使之流行,由于流行热度极高,甚至产生了“维特主义”这样一个表示感伤主义意思的新名词。这部作品影响到了明治中期的大部分作家,在明治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形成了风靡日本文坛的“维特热”,当时人们认为,身为作家没读过“维特”就是耻辱,连尾崎红叶这样的旧派作家也被它打动。[4] (第四卷,58—63、75)
歌德的诗歌创作的影响,在日本著名作家岛崎藤村的诗歌创作中尤为明显。[4] (第四卷,66—72)当然,介绍翻译歌德最力的还要数森欧外。森欧外作为明治大正年间为日本文坛引进外国文学的第一功臣,在介绍歌德方面的作为也得到文坛的广泛认同。森欧外11岁开始学德语,青年时代又留学德国四年,德语非常好,留学期间就买了德文版的45卷《歌德全集》拼命阅读。他非常仰慕歌德,对歌德及其文学创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回国一年后的1889年,就与“新声社”同人翻译了一批外国诗歌,作为《国民之友》第58号的夏季附录出版,即明治年间著名的译诗集《於母影》。其中歌德的《迷娘之歌》在当时就被认为是“第一名译”,受到广大文学青年的喜爱,在日本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该译诗集的每首诗都没有标出译者的名字,但是日本学者认为,从翻译的水平之高这点来看,《迷娘之歌》的翻译非森欧外莫属。《迷娘之歌》是歌德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一个人物——被拐骗少女迷娘所唱(它并不是什么爱情诗,而是病重的迷娘所唱的思乡之曲。)不仅在德国文学史上非常著名,而且由于贝多芬、舒伯特等著名音乐家为它谱曲,在欧洲也流传甚广。森欧外在德国时就曾精读过德文版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并在原作《迷娘之歌》的左侧用铅笔写下“千古绝调”几个字。[4] (第四卷,16—19)可以推测:由于森欧外的精彩译笔使这首诗震撼了日本文坛,也迷醉了年轻的马君武,使他暂时超越了反满革命的现实文化需求而翻译了这首著名的诗歌。之所以说马君武是受到日本文坛的影响而译《迷娘曲》,除前述森欧外译作的极大影响会波及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马君武这一可能性存在外,还有歌德名字的翻译发音也有日语的特点,马君武译此诗时把作者歌德为“贵推”,而当时日本文坛把歌德译为“ゲ—テ”,极似中文发音的“贵推”,而马君武发表于1903年3月12日的《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中歌德译为“苟特”,1903年3月27日的《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方法》一文中,也还是“苟特尔”。差不多同一时期对一个外国作家名字译音发生较大的变化,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的结果呢?另外,每节诗的结尾马译为“愿与君……”,日译为“君と共にゆかまし”,两者非常接近。综上种种,即便马君武翻译《米丽容歌》(迷娘曲)的蓝本不是日文本,但也很有可能参考了森欧外的日译本。
马君武所译《阿明临海岸哭女诗》,摘译自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学界一般认为是马君武第一次留学德国时的译作⑦,但均未明确译诗所依据的是何种文字版本。莫世祥编的《马君武集》中,该译诗前的译者小序中提到《少年维特之烦恼》时,引的是德文原文的书名,但译文后所附的却是英文,据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说,1914年上海文明书局版的《马君武诗稿》中,该诗后附的就是英文。[5] 18由此推断,马君武译此诗所据的本子倒更有可能是英文版的,但是按常理推论,此诗如果译于他留德期间,理所当然应当以德文原版为蓝本,为什么会用英文版为蓝本呢?据卫茂平的“考辨”,该诗在《马君武诗稿》出版前也未在其他地方发表[5] 66,因此它的原始状况便无从追寻,故笔者只能提出一个假设:也许这一作品是他留日时受到日本歌德接受时“维特热”的影响,根据英文版翻译的旧译,后来才发表的。当然,笔者关于《米丽容歌》和《阿明临海岸哭女诗》的翻译蓝本仅仅是推测,如果新的资料出现,这种假设极有可能会被推翻。
还有一个小小的证据似乎也能证明马君武留学德国之前就受歌德影响不小,1914年6月,陈布雷读了不久前刚在上海出版的《马君武诗稿》后,给柳亚子写了封信,其中专门谈到马君武的译诗:“译作更有灏瀚流转之妙,与曼殊以宛丽胜,真堪各树一帜。曩在沪见此君服御,喜效德文家贵堆装束,知其心仪已夙。”[6] [7] 367—368陈布雷信中说的“曩”,应该是1902年到1906年间。马君武是1900年起走出广西的,他先去南洋拜见康有为,后受命回国策应唐才常的起义,无果而终。1901年他曾在上海读书,但显然那时他还未接受歌德的影响,也谈不上“效”“贵堆”的装束。而在1902—1906年间,留学日本的马君武因母亲居沪,有时由日本回上海省母,基本具备了已受到歌德影响又会在上海出现的条件。试想,留学东洋的青年,崇尚西方文化,又是文学爱好者,模仿自己崇拜的外国文豪的打扮不是也很正常吗?而马君武以这样的装束出现在上海的某一社交场合或徜徉于上海街头,被陈布雷撞见,印象不深才怪,所以到大约十年之后的1914年,陈布雷还记忆犹新。1906年底马君武便赴德国留学,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911年11月才回国,这一段时间当然要排除。而从1911年底到他第二次赴德的1913年底之间,虽然马君武有可能出现在上海,但绝不可能仿效歌德的装束。一则此时的马君武已年过30,早过了“追星扮酷”的年龄(笔者以为任何时代的人青年时代都有偶像崇拜的冲动,马君武也不例外),再则从归国起,马君武就忙于新政府的筹建和革命后的各种事情,绝无闲工夫去学歌德的装束的,况且,这时距陈布雷写信的时间最多也就两三年,说“曩”也不太恰当。
席勒的《威廉·退尔》是马君武第二次留德时的译作,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有趣的是,马君武1903年3月在《欧学之片影》中对席勒的评价和十多年后他翻译《威廉退尔》时的看法却相去甚远。在《欧学之片影》中他认为:歌德、席勒等作家不“能使人恋爱,使人崇拜”,“因彼数子之位格之价值,止于为文豪故。”但是他发表于1915年的《〈威廉·退尔〉译言》却说:
吾欲译欧洲戏曲久矣,每未得闲。今来居瑞士之宁芒湖边,感于其地方之文明,人民之自由,到处瞻仰威廉退尔之遗像,为译此曲。此虽戏曲乎?实可作瑞士开国史读也。予译此书,不知坠过几多次眼泪,予固非善哭者,不审吾国人读此书,具何种感觉耳。[8] 50
显然,他欣赏席勒的这部作品不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去看的,当然席勒也就不“止于为文豪”了。其实,十多年之后的马君武评价作家与作品的标准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是他对席勒及其作品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而他1903年对席勒的评价显然是受到了视野的局限,也就是说当时他很可能没有见到过席勒的《威廉·退尔》,而他的这种局限可能与当时的改良派的视野和日本文坛情况相关。翻看《新小说》等改良派刊物,我们发现最早的关于席勒的介绍在1905年3月,已是在马君武写《欧学之片影》之后两年了。而日本文坛又是如何介绍席勒和他的《威廉·退尔》的呢?
《威廉·退尔》最初被介绍到日本正是明治10年到20年自由民权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当时文坛风行讴歌自由的政治小说,《威廉·退尔》的内容正符合这种潮流,所以明治13年、15年和23年各出现过一个《威廉·退尔》的译本,分别是《瑞西独立自由之弓弦》、《退尔自由谭》和《威廉的儿(退尔)自由之一箭》。但是这三个译本都不是全译,《退尔自由谭》甚至就是“断简零墨”;而且流传也不广,《瑞西独立自由之弓弦》被日本比较文学专家柳田泉称作“初期翻译文学中稀本中的稀本”,《威廉的儿自由之一箭》刊于《少年文武》杂志上,不久后就“被埋置于故纸堆中”。虽然明治38年(1905)4月有一个由佐藤芝峰译的《威廉·退尔》出版,但译者将故事的舞台改为江户时代的日本,而且对剧中大量出现的“自由”、“权力”、“义务”、“同盟”等词语有所忌讳,翻译中大多删除了,真正是“苹果树上结出了柿子”,已经完全变味了。[4] (第四卷86—108页)而当时一心一意追求革命救中国的马君武虽然正在日本,但他很可能没有见到这个译本,或者见到了也不会在意。可以想见,当德文已经相当精熟的马君武在1914年二次留学德国时,读到德文原版的《威廉·退尔》时是何等激动,“予译此书,不知坠过几多次眼泪,”绝不是虚话。可以说,马君武1903年对席勒的评价不高,除了他在外来文化接受上还没有摆脱改良派影响外,还和日本文坛当时没有好的《威廉·退尔》译本有一定的关系。
(二)马君武对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与日本留学经历
马君武译托尔斯泰的作品,是1913年到1916年的事。《心狱》191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三部中的一部,译者“基本上忠实于原著。就当时的翻译水平来讲,《心狱》是值得肯定的一部译作”。⑧《绿城歌客》发表于1916年上海出版的《小说名画大观》上。[9] 120以上两作品均为德文转译。马君武选择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出于什么样考虑,除了他百字左右的《〈绿城歌客〉译言》[8] 51之外,没有留下其他可资参考的文字,但是马君武在日本和梁启超关系最密切的1902年,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第一期上,曾刊登过托尔斯泰的像,⑨ 因此也不能排除马君武当时就注意到托尔斯泰的可能性。这期《新小说》刊登托翁的相片,很可能与日本的托尔斯泰介绍相关,而日本的托尔斯泰输入从明治2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的《复活》日译本译者是内田鲁庵,译作连载于明治38年4月5日—12月22日的《日本》上。[4] (第三卷,185—186)
注释:
①今译黎萨尔(1861—1896),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驱,诗人、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小说《不许犯我》、《起义者》,诗歌《献给菲律宾青年》、《我最后的告别》等。因致力于民族独立斗争,于1896年12月30日被西班牙殖民统治者枪决。
②郭长海先生在《雨果作品的中译补谈》一文中说:马君武《十九世纪二大文豪》是中国介绍雨果最早的文字。郭文见《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5日。
③日本明治年间介绍拜伦最详细、最有影响的木村鹰太郎的《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虽然在1902年7月出版,但从内容上看,《新小说》上介绍拜伦这段文字的作者恐怕还没读到这本书。
④转引自北冈正子著《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24页、28页、35—36页。
⑤同上页“④”,第28页。
⑥详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177页,三联书店1995年4月出版。其实马君武当时并未去欧洲,而是于1903年秋入京都大学读化学专业去了。
⑦参见莫世祥编《马君武集》446页;又见曾德啰《马君武诗文著译系年录 一》,《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124页。
⑧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219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北京出版社1992年7月版戈宝权的《中外文学因缘》120页说:“1913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马君武译的托尔斯泰的著名长篇小说《心狱》即《复活》,封面上印了托尔斯泰的画像和一段简介的文字”;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中记录:马君武译《心狱》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9月初版。
⑨戈宝权先生《中外文学因缘》115页说1907年1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民报》11期上刊载的托尔斯泰相片是“我国报刊上最初”的托翁相片,不确。
标签:文学论文; 马君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少年维特之烦恼论文; 梁启超论文; 明治时代论文; 歌德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雨果论文; 哀希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