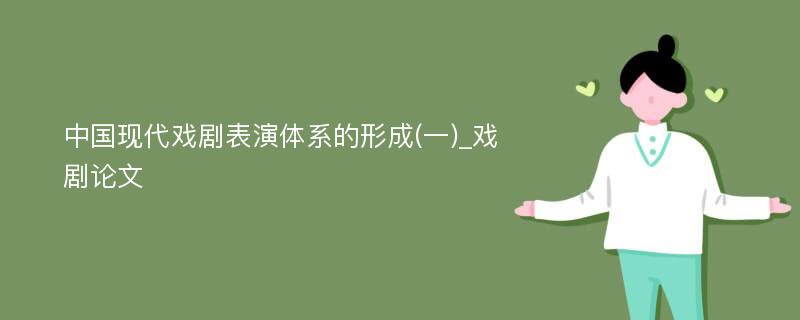
中国现代戏剧表演体系的形成(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戏剧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话剧从西方传入中国,我国的戏剧开始从古典戏剧时代,发展到“废除歌唱而全用对话”的现代戏剧时代。在近百年中,中国现代戏剧经历了初创、发展和成熟的不同历史时期,并造就了一代伟大而杰出的现代戏剧家,郭沫若、曹禺、老舍、田汉、夏衍、阳翰笙、洪深、欧阳予倩、陈白尘、李健吾,等等。他们的戏剧活动与剧作,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然而,戏剧的发展仅有伟大作家和作品是不完整的。戏剧离不开舞台表演,离开舞台表演,戏剧便失去了艺术生命。
中国现代戏剧的表演形式和表演体系,是中国现代戏剧艺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戏剧表演形式和表演体系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戏剧完成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标志之一。因而,总结和研究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表演形式和表演体系的基本精神和方法,及其形成过程,是20世纪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
我国古典戏剧极重视表演艺术的创造。它的丰富内容和完美形式,把我国古典戏剧艺术推向了极致,形成独特而精美的戏剧表演艺术体系,在世界戏剧艺术史上占有很高地位。
我国古典戏剧表演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动作和表演兼于一身,“歌者与演者之为一人。”[1]我国古典戏剧历经千百年的创造、发展、提炼,形成一套系统而完整的戏剧艺术(包括人物、动作、歌唱)程式。就舞台表演而言,程式化的动作表演方法与技巧非常丰富,可以表现现实的、抽象的、心灵的复杂而多样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我国独特的戏剧表演形式,来自生活又渗透到生活之中。
我国古典戏剧的程式化表演艺术,是生活美的高度集中和概括。它是我们民族审美追求、审美观念、审美习惯与情趣的表现。正是这种程式化的美,才使我国传统戏剧艺术,深深扎根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我国现代戏剧的表演形式,在本世纪初,完全是采用西方话剧艺术的程式化表演技巧。西方的话剧艺术的表演形式,有其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悠久的戏剧艺术传统。但是,西方的戏剧艺术形式,与我国广大戏剧观众的审美需求、审美习惯相去甚远,因而很难在我国广大戏剧观众的欣赏中得到认同。所以,中国现代戏剧的舞台表演艺术,必须具有我们民族的特色。解决中国现代戏剧表演形式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是把我国现代戏剧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推向前进的关键一步。
要建立起中国现代戏剧的表演形式和表演体系,首先要克服长期存在在舞台表演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简单化、公式化和随意化的倾向,还得解决戏剧文学的叙述形式问题,语言的科学化、规范化问题,等等。中国现代戏剧的表演形式和表演体系,必须是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有着我国现代生活氛围、现代生活美和具有广大观众欣赏指向的、独特的表演艺术。
为使我国现代戏剧在表演形式上得到发展,并形成一套完美的表演体系,走过的道路是长期的、曲折的、艰难的。
在话剧(新剧、文明戏)从欧洲传入中国的早期,其形式的新颖特别使中国人耳目一新。辛亥革命前后,文明戏、新戏剧团体,一度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得到人们普遍欢迎,产生过不小影响。然而,文明戏的寿命是短暂的。文明戏衰落的原因很多。然而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致命原因,是表演上的混乱、粗制滥造、随心所欲。洪深对当时文明戏的创作和舞台表演状况的描述,是令人惊异的。他说,文明戏“在表演上,因欲博得观众的拍掌或发笑,往往任意动作,任意发言,什么身份剧情性格,甚至情理,一切不管,所演的戏竟至全无意识。”[2]他接着指出:
所谓文明戏,是怎样一个东西。(一)从来没有一部编写完全的剧本的,只将一张很简单的幕表,贴在后台上场处。(二)有时连这张幕表,也不肯郑重遵守。(三)绝对不排练,不试演,不充分预备的。(四)有时演员上场,甚至连全剧的情节,还不大清楚。……
由此可见,文明戏是一种非艺术的、非组织的戏剧和团体。欧阳予倩说,文明戏的无理滑稽异常之多,几乎每个戏剧都有一个滑稽仆人,插科打诨,无聊戏谑,脱离了戏剧艺术的常轨。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文明戏,类似欧洲的即兴式的戏剧。在16、17世纪的意大利曾广泛流行过即兴剧。即兴剧(亦称兴喜剧)是一种随编随演的,情节夸张、无聊戏谑、插科打诨的闹剧。然而,在意大利是将严肃的戏剧及表演,与即兴剧严格区别开来的。
20世纪初,是我国新旧戏转换的时代,戏剧界也有一批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话剧创作和表演的戏剧家。他们认定目标,打破陈旧的观念,扩大戏剧研究范围。他们要把对戏剧的认识,“纳入正轨的艺术论和戏剧论。理论是事实之母,我们应当综合世界共同信仰的各种戏剧论来作我们研究的标准,将中国从来对于戏剧的种种误解一齐推翻。……目下我以为应当拿戏剧的尺,把中国的戏剧从新量一量,估一估价,中国的戏剧,有特殊的形式,用哪种形式所能表现人生的能够到什么程度,我们应当拿一种实验来证明一下。”[3]他们在表演艺术上,做着不懈的追求,探索着话剧表演艺术的基本规律和方法。
到了30年代,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建设、戏剧创作和戏剧团体的组织,都有长足发展,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时期。中国现代戏剧的表演艺术,也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尤其是对现代戏剧表演艺术的理论探索与建树,为我国现代戏剧表演体系的发展与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把30年代我国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建设推向鼎盛时期,作出突出贡献的作家、理论家有:曹禺、洪深、欧阳予倩、田汉、夏衍、陈鲤庭、郑君里、李健吾、袁牧之,等等。从3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全面开始与深入,以郭沫若为首的戏剧界,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们的戏剧活动的组织之严整、工作之认真、表演方面的创新,都是现代戏剧史上空前的。他们的工作,使我国现代戏剧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使现代戏剧表演形式和表演体系的发展与形成的进程,大大加快了。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曹禺和他的剧作。在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是曹禺的剧作,把戏剧这种文学形式,与其它叙述文学形式严格地区别开来,使中国现代戏剧有了自己民族的特质。曹禺在戏剧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娴熟而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摄取生活深层内涵和人物内在感觉的刻苦而认真的态度,追求戏剧的独特性质和诗意本质方面的执著精神,尤其是在使戏剧作品具有强烈的舞台感觉和舞台表演内涵方面,都为我国现代戏剧表演形式和表演体系的形成,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与有利条件。
曹禺剧作的出现,在戏剧界产生的作用不同凡响。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夏衍说,他1937年春天写的第四个剧本《上海屋檐下》,“也可以说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因为,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的手段。引起我这种写作方法和写作态度之转变的,是因为读了曹禺同志的《雷雨》和《原野》。”[4]说曹禺戏剧的出现,是我国现代戏剧发展一个新起点无疑是正确的。
在30年代,戏剧理论家开始探讨戏剧表演的理论问题。1937年,由著名戏剧理论家、导演郑君里等人,陆续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翻译介绍到我国。这是我国戏剧理论界、表演艺术界的重大事件。40年代初,焦菊隐又开始翻译介绍丹钦柯的《回忆录》。此后,一直到60年代中期的几十年中,中国现代戏理论界、著名导演、表演艺术家,不断深入探索和实践斯坦尼的表演思想和表演体系。
把斯坦尼体系创造性地运用到我国现代戏剧表演艺术中,并把它与我国传统表演艺术结合在一起作出杰出贡献的理论家、表演艺术家,有欧阳予倩、焦菊隐、辛泯、欧阳山尊、金山、夏淳、梅阡、蔡骧,等等。他们通过郭沫若的《屈原》《虎符》《蔡文姬》《武则天》,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家》,田汉的《文成公主》《关汉卿》,老舍的《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等剧作的成功演出,创造并丰富了完整而系统的中国现代戏剧表演理论和表演体系。
中国现代戏剧表演理论和表演体系的形成,是我国现代戏剧从创作到舞台表演达到成熟的标志。中国现代戏剧表演体系的形成,使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我国传统表演艺术,焕发出新的光采。
二
为了论述中国现代戏剧表演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物质,必须先了解中国戏剧界对斯坦尼体系的认识和实践。
斯坦尼体系,形成于本世纪初,是19世纪意大利“体验派”戏剧表演形式和表演方法的创造性发展与完善。这种表演方法重视人物、角色和生活的关系,强调角色对人物思想、感情、情绪、心态、欲念、希望的体验。体验的目的,在于创造角色,进而付诸动作和表演,再现人物的真实性、整体性和戏剧性。
这种表演方法,是一种“再体现的艺术创造方法”,称之为“体验艺术学派”,简称“体验派”。
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精神和方法,全面运用于我国现代戏剧表演艺术实践中,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
从50年代起,我国现代戏剧创作、舞台表演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的时期。许多戏剧精品的出现,一大批有才华的造诣很深的著名导演、表演艺术家的全身心的艺术创造活动,理论界艺术界对斯坦尼体系的深入探讨、研究和艺术实践,对我国传统表演形式和方法的继承和创新,都为中国现代戏剧表演形式和表演体系的形成和走向辉煌,提供了优越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50年代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成为中国现代戏剧表演艺术的圣殿。在那里聚集了一大批现代戏剧艺术界的精英,随着许多经典性的戏剧作品的演出,中国现代戏剧表演体系得以形成。
对戏剧理论尤其是戏剧表演艺术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是肩负北京人艺领导工作的著名戏剧艺术教育家、表演艺术理论家和导演焦菊隐先生。焦菊隐一生从事戏剧艺术教育工作。从40年代起,他努力探讨和研究斯坦尼表演体系的思想和方法。50年代,他又不断探索和尝试如何将传统的戏剧表演形式和方法,与现代戏剧表演艺术相结合,为创造我国现代戏剧艺术表演体系,殚思极虑。就总体而论,他认为,表演体系是戏剧艺术的舞台表演规律和格律。中国现代戏剧表演体系的精神和方法是:借鉴和运用斯坦尼表演体系的基本思想与原则,重视对生活的研究和认识,从心理体验入手,再创造出真实的艺术形象,表现生活的丰富而真实的内涵;竭力创造舞台的诗的意境,形成鲜明的意象,用抒情的方法造成强烈的内在的戏剧感觉与节奏感,以产生戏剧的震撼力;同时,继承我国传统的、古典的表演艺术的形式和技法,增强现代戏剧艺术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使之具有我们民族传统戏剧艺术的风格、韵味和魅力。
斯坦尼表演体系,在中国现代戏剧表演艺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它成为中国现代戏剧舞台表演艺术的现实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为此焦菊隐对斯坦尼体系的理论研究,把斯坦尼体系的精神和方法在表演艺术实践中的运用,取得了极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首先,焦菊隐指出,斯坦尼体系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面旗帜,其“美学原则和创造方法的基本点,是从生活出发,从实际出发”。[5]因而,斯坦尼体系反对一切形式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表演方法。斯坦尼的现实主义表演方法,强调演员自觉意志的重要性与创造性,强调“内心活动和形体活动的一元性”。斯坦尼体系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发现了生活和人的发展规律,生活和人在发展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则,根据这些法则探索出一系列有名的“心理技术”。“通过这些技术,演员就可以封闭某些不合于角色的内心因素,培植发展某些角色所需要的内心因素,首先使自己内心思想情感变化,然后以角色的灵魂,投胎于角色的形象,而再体现为舞台上的人物。这就是他的再体现的艺术创造方法的基本意义。”[6]
我国的表演艺术家们,在创造角色的过程中经过反复认识和实践角色的内心思想情感,排除自己的主观想象,创造了许多真实动人的艺术形象。于是之在扮演《龙须沟》的程疯子时,起初只停留在认识、理解他所扮演的人物上,不懂得“创造角色的过程,是一个体验的过程”。他说:“我也和以往有些演员一样,想要先一下子把我的角色理解清楚,再去体验生活。但是焦先生和事实都告诉我,那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倘若习惯于过急地把角色作了分析,勉强得到了貌似系统的解释,然后再就教于生活,那结果就叫做从概念出发,体验生活就会形成剽窃一招一势,成了形式主义,甚至,不但完全没有用处,反而觉得体验生活不能帮助我们什么了!”[7]我国许多优秀的现代戏剧作家,都具有深厚扎实的生活基础,渊博的知识和广博高深的文化素养。他们创造的戏剧人物,为表演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创造天地。在谈到老舍的戏剧人物时,英若诚说:“这些人物从生活中提炼出来,没有现成的舞台程式可循,这就逼得演员们不得不抛弃那些表演上的‘套子’,到生活中去寻找养料。多少舞台上令人难忘的形象,例如程疯子、丁四嫂、庞太监、虎妞,都是从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吸取来,创造成功的。”[8]现实主义的表演精神和表演方法,要求艺术家“到生活中寻找养料”,用身心的体验、实践,使自己的艺术创造达到角色的精神的深层世界。
其次,戏剧家郭沫若、曹禺、老舍、田汉等,都是最大的抒情派。他们的戏剧作品,把生活中最富有诗意的成分组织起来,充溢着浓郁的抒情因素和抒情本质。这类充满诗意的作品,需要相应的表演形式和表演方法,将戏剧作品具有的强烈的抒情情调与抒情力量充分表现出来。
戏剧作品的抒情因素和成分,来自生活现实的抒情本质,因而带有抒情格调的表演,必须向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发掘,即使面对的是平淡的日常生活现象和人物的平凡行动,也必须如此。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发掘,就是通过表演,剖白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的“内在的感情”,通过表演艺术家“内在特质的创造”,表现出人物心理的与精神的奥秘,从而使观众感悟到人物内心世界各种情感、欲念、欲望的萌动、产生和变化,感受到表演所产生的巨大震撼力。
许多杰出表演艺术家对《屈原》《虎符》《蔡文姬》《武则天》《北京人》《家》《关汉卿》的舞台创造,让观众深切感受了独特的、浓郁的诗的意境,鲜明的生活节奏。焦菊隐对《蔡文姬》演出的富有诗意的艺术处理,使整个舞台表演,是“在诗的意境上的会心”。《蔡文姬》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作品。主要人物曹操、蔡文姬的开阔胸怀,潇洒风度,在国事家事上的明辨是非的政治风貌,以国事为重、心存天下的厚重感情,在文学上的开拓精神,在诗作上表现出的辉煌思想,都焕发出了光采。剧作中正集中地概括了蔡文姬、曹操生活中最崇高、最富有诗意的成分。作家标明《蔡文姬》是一部“五幕历史喜剧”,然而焦菊隐执导时在艺术处理上,“却大胆地提出这出戏要从‘悲剧’入手。虽然作者的用意是要强调文姬终于摆脱了个人的悲哀,思想感情终于飞跃到新的明朗开阔的境界。但是从舞台艺术的规律上看,没有前三幕《胡笳十八拍》的哀怨悲愤,也就没有《重睹芳华》的幸福之感。甚至可以说,前三幕的哀怨悲愤愈深,后两幕的幸福之感就愈容易被观众感受到。所以焦菊隐同志十分着力地抓住抛儿别女的悲剧情调,予以形象的渲染处理。这个很大胆、很有魄力的构思,来自导演和作者在《蔡文姬》诗的意境上的会心。”[9]
第三,继承和弘扬传统的戏剧表演形式、表演方法和技巧,把传统的表演精神与方法融于现代戏剧表演艺术中,是确立和形成我国现代戏剧表演体系的不可或缺的方面。传统的戏剧艺术形式、方法和规律,是我国古典戏剧美学思想的体现,是我国戏剧观众审美追求、审美观念的体现。所以,我国现代戏剧艺术吸取、运用传统表演艺术的优秀成分,借鉴和学习传统表演艺术中创造性、规律性的东西,才使中国现代戏剧表演体系植根于我国古典艺术哲学的深厚基础之中。
尽管我国现代戏剧与古典戏剧表现的生活内容、表现形式和表演方法,有根本区别,然而古今戏剧表演艺术在摹仿行为动作和语言动作等方面有共同之处。我国戏剧的传统表演艺术,与西方戏剧表演艺术在原理、规格、规律上,也往往相似,不谋而合。在舞台表演方面,我国传统戏剧有极丰富的经验,有极具特色的表演形式。不同表演艺术之间的学习和吸收,是表演艺术发展所必需的。焦菊隐在谈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年对“形体行动方法”的探索追求时指出:“我国戏曲在这方面的经验,不但很丰富,很成熟,而且已经达到了灿烂的程度。这是我国戏剧在世界范围内独特的成就。作为话剧工作者,不只应该刻苦钻研学习斯氏体系,并且更重要的是,是从戏剧表演体系里吸收更多的经验,来丰富发展我们的话剧。”[10]。总之,向传统的戏剧表演形式学习,根本目的在于极大地丰富我国现代戏剧表演艺术,使中国现代戏剧表演艺术具有鲜明而浓厚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未完待续)
注释: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2]洪深:《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见《洪深研究专集》。
[3]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转引自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
[4]夏衍:《上海屋檐下·后记》。
[5]焦菊隐:《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习》,见《焦菊隐戏剧论文集》。
[6]焦菊隐:《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习》,见《焦菊隐戏剧论文集》。
[7]于是之:《我怎样演“程疯子”》,见《人民戏剧》1951年3卷1期。
[8]英若诚:《老舍先生与北京人艺》,见《剧本》1979年2期。
[9]苏民、刁光覃、蓝天野:《忆焦菊隐同志导演〈蔡文姬〉》,见《光明日报》1978年9月24日、10月1日、10月8日。
[10]焦菊隐:《略论话剧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见《焦菊隐戏剧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