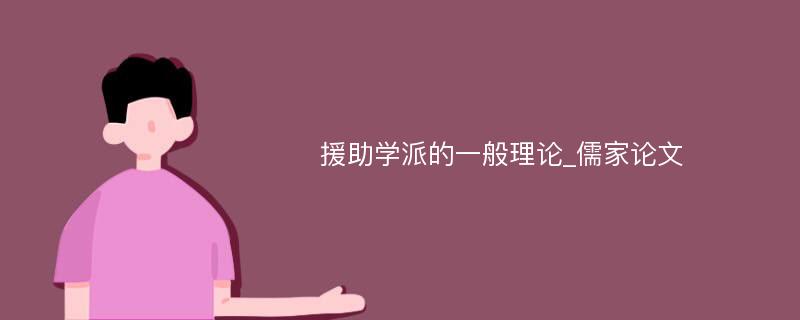
啖助学派通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中叶,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春秋》学派。这个学派以啖助、赵匡为先驱,陆淳(质)集大成,对当时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宋人陈振孙说:“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①]清末学者皮锡瑞也说:“《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又说:“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学者,皆此一派。”[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认为,清代以前两千年经学凡六变,其中唐代的“孔(颖达)、贾(公彦)、啖(助)、陆(淳)”为上承章句之学,下启宋明理学的第二变。这些评价表明了啖赵陆学派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有关啖助、赵匡、陆淳三人的生平事迹及相互关系,史籍记载矛盾而简略。《旧唐书》卷一八九下《陆淳传》说陆师赵,赵师啖;《新唐书》卷二○○说赵、陆二人皆为啖助弟子。陈振孙则说匡师助,陆师匡、助。今考吕温代陆淳写的《进集注春秋表》,其中说“臣(按:指陆淳)……以故润州丹阳县主簿臣啖助为严师,以故洋州刺史臣赵匡为益友”,明白道出了陆淳与啖、赵二人之间的关系[③]。至于赵匡,也找不出他师事啖助的证据。
啖助著有《春秋集传集注》及《春秋统例》,赵匡著有《春秋阐微纂类义统》,均已佚。陆淳的著作今存三种:《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春秋集传微旨》三卷。这三种书是陆淳在啖赵二人的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实际上集中了啖赵陆三人的《春秋》学思想。他在《春秋集传辨疑》凡例中说:
《集传》取舍三传之义,可入条例者于《纂例》诸篇言之备矣。其有随文解释,非例可举者,恐有疑难,故纂啖、赵之说,著《辨疑》。
这就明白地指出《纂例》、《疑辨》二书综合了啖、赵二人的研究成果,而集其大成。二书中多处明标“陆淳曰”,提出自己观点。至于《春秋集传微旨》,则先列三传异同,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在该书自序中,陆淳说“其有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迹虽近义而意实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介乎疑似之间者,并委曲发明,故曰《微旨》。可知该书大体上为陆淳自撰,代表了他本人的观点。但每条必称“淳闻于师曰”,以示不忘所本。
一、对《春秋》经的理解
在《春秋集传纂例》一书的开头,陆淳以八篇文字比较详尽地阐述了啖助、赵匡及他本人对《春秋》及三传的理解,这是他们学术思想的纲领和治学的出发点。
首先,孔子修《春秋》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这是每个治《春秋》的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过去《左传》学者认为孔子修《春秋》是为了“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公羊》学者认为是为了“将以黜周于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谷梁》学者则认为是为了“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比较而言,《左传》着重于制度典礼,从历史的角度去探求孔子修《春秋》之旨:《公羊》、《谷梁》二家则着重于善恶褒贬,从道德的角度去探求孔子作《春秋》之旨。啖助却认为,三家之说都“未达乎《春秋》之大宗”,因此不可能真正理解夫子作《春秋》的深刻用意。他认为,《春秋》之作,是为了“救世之弊,革礼之薄”。他具体论证说:
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縡,救縡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④]。
夏文化以“忠”为特色,殷文化以“敬”为特色,周文化以“文”为特色。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明以周礼为主要内容的周文化已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是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所以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啖助从变革的角度解释孔子修《春秋》的用意,把孔子看成是一个文化改良主义者,而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因此他不同意所谓孔子修《春秋》是为了复兴“周礼”的说法,主张《春秋》之作在于用夏政以救周失。他提出:
《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也矣[⑤]。 啖助认为在这一点上,杜预的认识全错了;而何休所说“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然话是说对了,但语焉不详,没有把握关键所在,因而只对了一半。
那么,杜预、何休为什么错了?啖助认为他们“用非其所”,即不从“性情”上去说,却从“名位”上去说,从外在的虚文去看《春秋》之旨。表面上孔子修《春秋》,于“改革爵列,损益礼乐”三致意焉,但实际上真正目的在于“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所谓“立忠为教”,是说孔子作《春秋》,在于树立“忠道”进行教化;所谓“原情为本”,是说孔子所提倡的“忠道”来源于人类固有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思想动机,将目的与手段分开,强调“权”“宜”,重视人物或事件的价值意义,至于如何实现其价值目的,则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啖助等人用这种方法去对《春秋》经文进行重新诠释,在对《春秋》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时,比纯粹用事实、用效果、用礼法去衡量要灵活得多,主观随意性也更大。解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评判标准及价值观任意发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用旧瓶装新酒。这种“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补啖助等人广泛地用于《春秋》学的研究之中。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传》引用孔子的话批评晋文公“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陆淳则说:“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义,则晋侯请王以狩,忠亦至矣”。他通过发掘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宣传“尊王”的“忠道”。所以陆淳总结为什么要“为贤者讳”说:“凡事不合常礼,而心可嘉者,皆以讳为善。”[⑥]
赵匡论《春秋》宗旨时也有与啖助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方法大略有二:兴常典,著权制。所谓“兴常典”相当于啖助的“立忠为教”,如凡是郊庙、丧纪、朝聘、搜狩、婚娶违礼则讥之。至于“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这就是所谓“著权制”,相当于啖助的“原情为本”。但赵匡比啖助更强调《春秋》的褒贬大义。他认为《春秋》之作,目的在于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也就是通过“例”“体”而寓褒贬。所以他说:“故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知其体,观其大意,然后可以议之耳”[⑦]。
二、对《春秋》传注的批评
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后,对“三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应该注意的是,他们在批评“三传”时虽然使用了比较尖刻的言词,但并非对“三传”一概否定,在批评的同时还是有所肯定的。
关于“三传”,他们认为古人对《春秋》的解说,本来就口口相传,自汉以后才有章句,著于竹帛,于是“三传”才得以广为流传。《左传》博采载籍,叙事尤为详备,能使百代之下详知春秋历史本末,人们可以通过它的叙事去探求《春秋》经文的意旨。何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故“比余二传,其功最高”。在这里啖助等人并没有抹杀《左传》叙事详赡的优点,甚至认为它比公、谷二传对《春秋》的贡献更大。但是,在他们看来,《左传》“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对《春秋》经义的阐述远远不够,而且是非混杂,让人难以把握。
关于公、谷二传,啖助等人认为,最初也是口口相传,后人根据先儒口授的大义,将它散配入经文之下。由于传授之间难免滋生歧义,以讹传讹,因此与《春秋》经的本旨乖谬颇多,没有抓住圣人的真正用心。不过,他们还是承认,尽管二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由于其大义是由子夏传下来的,故从传经这一方面来看,比《左传》要严密得多。啖助等人对公羊、谷梁二传的批评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说“《谷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钩深”,即对圣人的微言大义有所发明;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批评二传“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舂驳不伦,或至矛盾”,太拘泥于文句,往往穿凿附会,强作解人,故奇谈怪论,随处可见,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圣人夷旷之体”。啖助特别批评二传处处以“一字褒贬”之说释经。他虽然不反对《春秋》寓褒贬之说,但认为“褒贬”说对于解释《春秋》大义并非普遍适用。事实上也有许多“文异而意不异”的经文,无法用“褒贬”去兼赅。因此他批评二传“繁碎甚于左氏”[⑧]。
在解经时,啖助等人大胆地对三传的经说提出质疑。如《春秋集传纂例》卷二释“望”字,陆淳记赵匡之说:
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谷梁无其名。说左氏者云“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说谷梁者云“泰山、淮、海”。据礼篇云,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鲁之封内,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内则不祭,而云祀河、海,则三家之义皆可疑也。
啖助等人不仅对《春秋》三传不尽信,而且对汉魏以来注疏家之说也不盲从,甚至大胆地加以怀疑,经过考证,得出自己的结论。在当时学术界中,《公羊传》何休注、《左传》杜预注、《谷梁传》范宁注被作为官方法定的《春秋》注本,其地位几乎与经书本文相等,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啖助等人以巨大的勇气,反对旧《春秋》学,在批评三传的同时,也向何、杜、范三家注发难。他们认为三家注没有真正找到通往圣人之道的正确途径,去理解圣人的深意,在注解过程中没有以王道作为指归,对经书中的人物或事件作出合符儒家价值观的论断,并发挥圣人的微言大义。他们提出注疏之学虽然不是直接地用著作的形式去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在为圣人之书作注时应该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在里面。因此,注疏之学,虽因旧史,但要“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遗憾的是,“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啖助等人进而指出,“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他们对汉唐以来传注家批评之严厉,于此可见一斑。
“三传”没有把握圣人作《春秋》的宗旨,注疏家又没有发挥出“三传”的大意,致使《春秋》大义湮没不彰,这是啖助等人总结汉唐以来《春秋》学而得出的结论: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纂例》卷一《春秋宗指议第一》)因此,他们要舍弃前人的传注,直接探求圣经大义。他们批评传注家故弄玄虚,事实上《春秋》经文并不像有的传注者理解的那样“文义隐密”,而是非常简易明白的。啖助说:
《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止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⑨]。
传注者把本来“简易著明”的一部《春秋》经弄得晦涩难懂。不仅如此,《春秋》一经而分三传,每传自两汉以来又有许多家注,注中又有疏,强调“疏不破注”,不离师说,家法、师法门户之见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讦,搞乱了人们的视听。平心而论,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自两汉以来,经学作为官方扶植的学术,发展到唐代出现了种种弊端。虽然孔颖达《五经正义》颁行以后,经学表面上归于一统,但并没有克服繁琐晦涩的毛病,而仅仅对文句的解释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谈经者“不复知有《春秋》微旨”,特别是学者不再去探求儒家经典中蕴含的深刻义理。啖助等人评击前人传注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解经传统,创造一种新的治经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但以通经为意”,不讲家法,不根师说,兼取三传,合而为一。啖助说:
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其未详者,则据旧说而已[⑩]。所谓“理”,实际上是他们这一学派开创的一种主观的解经方法。借助于他们标举的“理”,以此作为标准去衡量前人传注的是非,“考核三传,以短取长”,直接为《春秋》经文作注。因此,他们主张凡是与《春秋》经文无关的传注,应予删削。在回答有关“无经之传,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谠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的责难时,啖助说:
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言,理自不得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入《春秋》乎![11]这样,经学更加简易明白,较少繁杂芜秽之弊。啖助等人在自己的经学研究实践中,力求简明,点到为止。现存陆氏三书,解经要而不烦,确实让人耳目一新。这也是啖、赵、陆《春秋》学能够在中唐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
三、啖助学派与中晚唐变革思潮
啖、赵、陆新《春秋》学的出现,与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两汉以来,儒家经学一直以章句训诂为主要形式。儒家义理被淹没在训诂义疏的海洋中,学者把明章句、通训诂作为治学的目标,甚至皓首穷经,花费毕生的精力于一字一句、一名一物,使儒学失去原来那种切近社会、重视经世致用的特征,积极向上的精神大为减弱,经学成了一些俗儒致显宦、求利禄的工具。学者成了书虫,对社会、对民生缺乏应有的关心。另外,从东汉以来,经学成为少数门阀世族的传家之学,世代专守一经或数经,炫耀门第、垄断文化,使儒家文化丧失了它的大众性一面。部分学者死守先儒之说,不知变通。因此经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到隋末唐初,这种章句之学已开始受到批判。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说》,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己任,对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作出自己的理解,提出“通变之谓道”、“道能利生民”,主张通变,重视生民,使儒学能切合现实,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到了中唐,逐渐形成一股怀疑思潮。面对唐王朝建立以后逐渐出现的社会矛盾。部分学者对旧的经学和传统观念表示怀疑,提倡富于批判精神的独断之学。刘知几《史通》就是这一思潮的卓越代表。这股怀疑思潮,是唐代中后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正是这一思潮的继续发展。他们的经学研究具有“通经致用”的时代特点。啖助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12]他认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都以行道济民为目标,后世口诵夫子之言的学者更应该效法孔子的救世精神,而不应该把治学与行道判为两途。赵匡在《举选义》一文中批评那些远离实用的章句之徒说:
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13]。他看不起那些“口问义、诵疏文”的读书人,认为这是白费精神去学习那些既无益于自己又无益于社会的学问。陆淳也有相似的看法。他曾对吕温说:
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天子咸临泰阶,请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14]在陆淳看来。国家政治的根本在于“生人为重,社稷次之”。因此,陆淳等人在章句训诂盛行于世的时代,独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精神。他们的主张代表了对两汉以来经学的反动以及向儒学原旨复归的历史潮流。柳宗元曾概括陆淳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15]。他们继承了孔孟儒学的“仁政”理想,并将其贯穿在《春秋》学研究的始终。在《春秋集传微旨》卷上解释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一条经文时,陆淳不采用三传旧说,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贤非德之人不应该居于统治地位。如果“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这是三代以下“家天下”的恶果,而非儒家提倡的理想制度。在这里,他实际上是利用儒家理想之道对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又如在《春秋集传纂例》卷六《军旅例第十九》中,陆淳记啖助之语说:
观民以定赋,量赋以制用,于是经之文之,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经纶,武足以御寇。故静而自保,则为礼乐之邦,动而救乱,则为仁义之师。……今政弛民困,而增虚名以奉私欲,危亡之道也。同书同卷《赋税例第二十一》陆淳记赵匡的话说:
赋税者国之所以治乱也,故志之。民,国之本也,取之甚则流亡,国必危矣,故君子慎之。这类解释是对儒家原始精神中“民本主义”思想的发挥。
啖助等人解释《春秋》,不仅比较注意发挥儒学中蕴含的“仁政”、“民本”思想,还对春秋霸业进行否定。在先秦儒家孔子、孟子看来,齐桓、晋文等春秋霸主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图谋称霸诸侯,其心可诛,但客观上也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有所匡正。那么啖助等人为什么要对春秋霸业进行否定呢?这要从中唐的社会政治形势中去找原因。
自安史之乱后,唐代形成了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对中央闹独立。唐德宗建中年间,以朱滔为首的河朔四镇自比春秋诸侯,模仿春秋盟会的形式叛唐称王[16]。啖助等人否定霸业,正是针对困扰唐代政治的藩镇割据。在《春秋集传纂例》卷四《盟会例第十六》中,赵匡抨击诸侯盟会说:
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贤君立则信著而义达,盟可息焉。观春秋之盟,有以见王政不行,而天下无贤侯也。他们强调“王纲”“贤君”的重要性,而对盟会基本上加以否定。否定了霸业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当前藩镇割据的合理性。
唐代建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积累也越来越多。到了中唐,朝廷中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势力,“永贞革新”就是这股变革势力的一次大亮相。变革思想在意识形态中有所反映。啖助等人的《春秋》学主张就充满了通权达变的思想。他们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主张“反经合道”、“变而得中”(《微旨》卷中),肯定变革是事物发展的常规,从而得出在政治上应积极变法的结论。在《春秋集传纂例》卷六《改革例第二十三》中,陆淳记赵匡之语说:
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况淫君邪臣从而坏之哉!故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弊端必须通过变革来加以消除,使天下重归于治。变革与否,是治乱所系的重大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兴亡的征兆。如果说柳宗元等人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么啖助等人则站在学术变革的前沿,他们的变革思想为改革派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四、啖助学派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啖助等人的《春秋》学研究,是从汉学向宋学过渡时期的产物。他们在当时被看成“异儒”,受到不少学者的推崇。不仅柳宗元曾师事陆淳,大和年间著名学者刘贲的《春秋》对策中许多观点也与他们的精神一致。陈商、陆龟蒙等人都相信陆淳的学说。因此,啖助等人《春秋》学的出现,带动了整个经学的蜕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这次蜕变,经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面向现实的特征。从文化意义上说,啖助等人的《春秋》学研究,是韩愈、柳宗元等8人掀起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并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啖助等人开始直到清朝乾嘉年间,《春秋》学显示出与前后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是与啖助等人的影响分不开的。他们对《春秋》学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转变上:
第一,从章句训诂向义理阐发转变。啖助以前的《春秋》学研究大多拘泥于对字句的阐释,较少对义理的发挥。事实上,《春秋》作为儒家五经之一,它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对它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字义诠释的水平上,研究者还应该对其中隐含的义理加以必要的发挥。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承担着为社会政治提供理论依据的功能。而现实社会政治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也要不断加以调整,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难以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经学义理化,有助于建立起一个不断适应社会政治形势变化的意识形态体系。因为从总体上来说,谈义理比讲训诂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使经学更具有实用价值。
第二,从《春秋》三传分立走向三传统一,变专门学为通学。自汉代以来,《春秋》分为三传,左氏偏重于补充史实,公羊氏则着重于对义理的阐发,谷梁氏介于二者之间,三传互不相容,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形同水火。即使一传之下,也往往数家。如一个《公羊传》,就有胡毋氏、董氏、严氏、颜氏等不同的派别。门户不同,使《春秋》学成为聚讼之学,读书人莫知谁是而无所适从。啖助等人把《春秋》学从三传纠纷中解放出来,不再死守传注,而是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依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经文,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舍传求经”。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完全弃传注于不顾。在他们的研究中,对于三传的优点加以吸收。如史实取左氏最多,义理则不论左氏、公羊、谷梁,合则留,不合则自出胸臆,另作解说,以期融为一家之学。啖助、赵匡、陆淳这种“会通三传”的《春秋》学出现以后,三传分立的时代就基本上结束了。
自啖助、赵匡、陆淳开创新《春秋》学派之后,继起者大有其人。卢仝著《春秋摘微》,韩愈曾赠诗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始终。”可知其舍传求经更为彻底。此外,冯伉有《三传异同》,刘轲有《三传指要》,韦表微有《春秋三传总例》,陈岳有《春秋折衷论》。这类书大体上都调和三传,目的在于“幸是非殆乎息矣”[17]。由此可见,会通三传或舍弃三传,是中唐以来《春秋》经学的总趋势。
宋代学者继承了啖助、赵匡、陆淳的治学传统,在《春秋》经学研究中往往弃传就经或重经轻传,注重以经求经,直寻《春秋》大义。如孙复、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翁等,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啖助等人的学风受到宋代学者的推崇。邵雍说:“《春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以兼治。”将他们的《春秋》学提到与三传并称的地位。程颐从维护儒家学说的权威地位出发,赞扬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朱子对他们的治学方法十分赞赏,称“赵、啖、陆皆说得好”。元朝名儒吴澄高度评价了啖、赵、陆的创新之功:“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啖、赵、陆《春秋》学方法的影响还波及到其它诸经的研究。北宋初,李之才教邵雍学《易》,就先让他读陆淳等人的著作[18]。不过,正如皮锡瑞所说,“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知啖、赵、陆之平允。”[19]的确,自从啖助等人开风气于先,宋人继流风于后,说《春秋》者大有其人。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大力发挥“尊王大义”。以后效法者众多,《春秋》成为宋代第一大经,《春秋》经文被随意引申,主体意识被过分张扬。南宋胡安国作《春秋传》,以议论解经,标举《春秋》的核心为“尊君父,讨乱贼”,连朱熹也批评它牵强之处很多,不尽合经旨。但由于该书的政治实用性很强,宋以后一直受到尊崇。元朝确定《四书》、《五经》为取士标准,《春秋》就采用胡传。胡传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被称为“《春秋》四传”。
以主观臆见解经,难免横生议论,曲解经义。因此啖、赵、陆的《春秋》学尽管得到勇于创新的学者的喝采,但也受到了一些严谨学者的批评。如欧阳修说:
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拙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也[20]。这番严厉的批评,从某些方面击中了啖助等人《春秋》学的要害。他们虽然克服了过去经学中繁琐拘泥的弊病,却往往又难免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解经时的主观随意性。这种主观随意性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有所反映。因此,我们在肯定啖、赵、陆《春秋》学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消极影响。
注释:
① 《直斋书录解题》卷二。
② (19) 《经学通论》之四《春秋》。
③ 《全唐文》卷六二六。
④ ⑤ (12)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春秋宗指议第一》。
⑥ 《春秋集传微旨》卷中。
⑦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
⑧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第二》。
⑨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议第三》。
⑩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注义例第四》。
(11)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子取舍三传义例第六》。
(13) 《全唐文》卷三五五。
(14) 《全唐文》卷六三一《祭陆给事文》。
(15) 《陆文通先生墓表》,见《柳宗元集》卷九。
(16)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
(17) 刘轲:《三传指要序》,见《全唐文》卷七四一。
(18) 《宋史》卷四三一《李之才传》。
(20) 《新唐书》卷二○○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