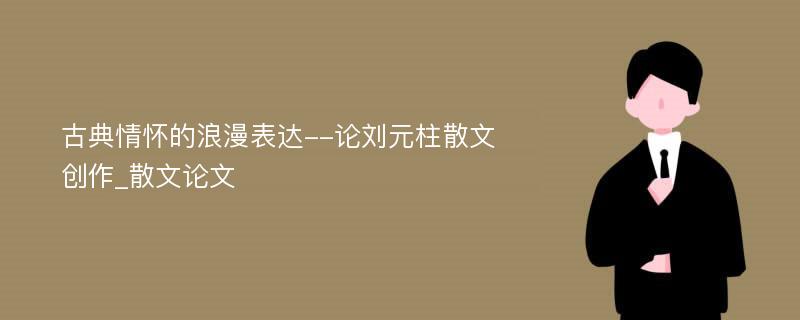
古典情怀的浪漫抒写——论刘元举的散文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怀论文,散文论文,古典论文,浪漫论文,论刘元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春风吹拂的日子里,我忙里偷闲地拜读了刘元举已经出版的大多数散文作品,它们是散文集《黄河悲歌》、《西部生命》、《上帝广场》、《表述空间》,以及可以称之为广义散文或大散文的长篇纪实文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以下简称《爸爸的心就这么高》)等等。应当承认,这些作品对我的吸引和打动是持久的、多方面的,它们常常让我产生联翩的浮想和久久的回味。而在所有这些吸引和打动中,最让我感到激赏不已的,则是作家贯穿于大部分作品字里行间的那种很是个性化的古典情怀与浪漫笔致,以及由此二者相互映照补充而成的一种沉郁而不失高蹈,宁静且兼有灵动的审美风度。它们把元举的散文和当下许多散文家的创作区别了开来,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和认识元举的散文世界,提供了必要而又可靠的标识。
元举出生于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五个年头。在他已经踏过的生命旅程中,既有学生时代遭遇“文革”梦魇的不幸经历,又有青春韶华对劳动艰辛和生存不易的深切体尝,更有80年代以来,立足于文学战线,积极参与全社会思想解放、经济变革、体制转型的丰富实践……所有这些并非轻松的历史邂逅和命运前定,都使得元举在写散文时,既无法像上一辈作家那样,在强大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支撑下,简单而执著地沿着政治向度做激流勇进式的抒发;也不会像当下活跃的文学新人类那样,热衷于抓住主观感觉和情绪,更多沉溺于才智的炫示或语言的狂欢;而是情愿放出空前睿智的目光和日趋强健的灵魂,透过异态纷呈的历史与现实景观,去探照民族乃至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含义和生命真谛。于是,我们在元举的散文世界里,看到了一种迥异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意绪。一种熠耀着强烈的人文色彩与人本光芒的古典情怀,一种以关心人的价值、张扬人的潜能为主要内涵的,被作家自己称之为“神性”的审美特质——
不是吗?元举写散文,喜欢抓住一个又一个的大题目,做系列的搜集和表达。迄今为止,他已经初步推出了有关钢琴音乐、建筑艺术、中国西部、欧洲建筑与文化等几个大题目和大系列。而这每一个题目的选择和每一个系列的建构,对于作家来说,都不仅仅是某种兴趣的满足,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生存质量的贴近与审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肯定与张扬。例如《表述空间》一书,其笔墨虽然涉及到了中外建筑领域林林总总的人物、事件、背景、作品和知识等等,但作为基本线索和中心意脉的,却是人与建筑的深入对话,是作家穿行于光怪陆离的建筑之林时的人性抚摸与人格感悟。正因为如此,我们透过该书所看到的,既有人对建筑的尊重和建筑对人的体现,又有人对建筑的轻慢和建筑对人的漠视,它们把人与建筑的相互关系,在一个较深的层面上,清晰而生动地揭示了出来。一部《上帝广场》是作家漫游欧洲的收获,该书开阔的视野和舒展的叙述,无形中聚拢了那么多亮丽的风景,奇异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同时也承载了作家自己绵绵不断的异域观感和家国沉思。它们踸踔恣肆,异彩缤纷,但最终又可归于一个大抵统一的主题,这就是:面对种种艰困与挫折、诱惑和异化,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应当怎样保持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与尊贵,应当怎样让自身的生存更具魅力也更接近诗意。纪实文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讲述了一位天才般的钢琴少年,在父亲的引导、培养和呵护下,创造艺术奇迹的故事。内中小主人公和他爸爸的形象固然真切感人,但作家投注于他们身上的有关两代人生命质量、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思考,又何尝不触动读者的灵魂。至于采撷于中国西部大地的《黄河悲歌》、《西部生命》二书,更是在展示人与自然的强力冲撞和整体较量中,真诚呼唤着傲岸、壮美与崇高,深情讴歌着劳动、进取与创造,充分肯定着理想、信念与意志,从而交织成慷慨悲歌,气势磅礴的人生大写。毫无疑问,如此这般的追求,都把散文乃至一切文学作品所必须具备的“人学”品格,表现得昭然而又沛然,平生出令人神往的魅力。
统观元举的散文世界,其浓郁的古典情怀和强烈的人文精神,不仅单单体现在许多作品整体意向的把握与传达上,而且还常常渗透于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勾勒与评价中。熟悉元举散文创作者大都知道,多年来出现于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主要有两类,其中一类是历史与现实生活里的强大者、成功者、超凡者,同时也包括悲剧式的英雄;另一类则是处于不同历史条件或社会环境下的普通人,以及生活中的弱势者和逆境里的奋斗者。在同历史的成功者和生活的强大者相遇时,元举每每拥有足够的热忱和智慧,并很善于运用这种热忱和智慧,去激活不同对象身上蛰伏的卓而不群的精神亮点和生命神髓。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视线里常常闯进一些高度个性化的人物:二战时西欧战场上的巴顿将军,凭着对战争规律的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不断地出奇制胜,创造辉煌,最终竟使残酷的军事对抗产生了神奇的艺术意味,他自己也因此而赢得了“军事艺术家”的称誉(《上帝广场·艺术家巴顿》);美国佬赖特既非豪门出身,又无正规学历,他原本只是一个土里土气的移民后代,然而却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划时代的建筑大师。其中成就他的主要是威斯康星的峡谷、草原和牧场——是这一切给了他开阔的胸怀,浪漫的气质,聪颖的悟性,以及对美国文化独特的感受能力,当然也包括大胆执著的实践精神(《表述空间·走近赖特》);中华男儿郎保洛、雷建生,选择了用江河的激流来砥砺意志,谱写人生,他们并非不知道面临的危险,但却毅然用生命向危险挑战,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决定了他们即使被黄河击碎,也依然不愧为时代的英雄)《黄河悲歌》)……诸如此类的人生视景尽管在“行当”上相去甚远,但却都包含了一种堪称“美丽”的东西,它们使读者真正体验到了面对生命的心驰神往。
然而,在走近生活中的普通人和弱势者时,元举便多了几分抑郁,也添了几分柔情,其笔下的文学亦仿佛深沉和舒缓了起来。它们尽可能直观地讲述着:19世纪饱尝社会戏弄和命运揉搓的巴黎茶花女;在国内外历经坎坷、倍遭磨难的女画家杨光素;善良而又孤傲、大度但却不幸的图书管理员李小路(《上帝广场》);当然还有那许许多多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的柴达木石油工人(《西部生命》)。而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悲天悯人,同情弱者,而是作家从自己曾有的底层生活经验出发,与人世间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弱势者,所进行的一种真诚的、平等的情感沟通和心灵对话。显而易见,以上两种人物的描写与评价,是投注了或者说体现着元举现实的人生态度和主张的,即:推崇积极入世积极进取,礼赞生命创造生命潇洒,但是却又绝不简单的以成败论英雄、定褒贬,而是在此同时,关注人生的苦难与不幸,呼吁社会的良知和公平。应当承认,这样一种倡扬强大而又不遗弃弱小的人生态度和主张,在今天既需要竞争,又需要道义的社会环境中,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它不仅把文学作品同样应当拥有的传统的人道主义和时代精神嫁接了起来,而且还为因处于变革大潮而很容易观念倾斜、顾此失彼的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可资参照的立场。这庶几是元举古典情怀特有的价值所在。
显然是基于自觉的、坚定的人本主义立场,元举对一切压抑、扭曲和背离人性的东西,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的。而这种批判在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便首先很自然地指向了日趋喧嚣也日趋膨胀的都市文明和科技文明。请读读《表述空间》中的《环境咏叹》和《原谅城市》二文吧!它们从作家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出发,倾诉着当代都市人普遍面临的生存空间的局促、绿地草坪的匮乏、空调的弊端、噪音的危害、建筑的单调与无序,以及交通堵塞、垃圾乱放、空气污浊等等。所有这些都使读者清醒意识到: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既包含了尊严和方便,又伴随着伤害与挤压。无疑是为了反抗这种伤害与挤压,同时也为了抵御由于这种伤害和挤压而很容易导致的现代人的精神焦虑与灵魂干涸,元举毅然告别都市,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朝着荒凉,也朝着古朴的西行,其足迹先后到达了黄河源、柴达木和西藏。在西行的旅途中,作家饱览了黄河的粗犷、戈壁的浩瀚、雪域的壮美,感知了两亿年前山与海之间那惊心动魄的冲撞与搏杀,当然也目睹了这片土地上人的坚韧与顽强。这时,他禁不住激越和亢奋起来,开始笔酣墨饱地讴歌生命的伟力和自然的造化,讴歌大西北的雄浑与苍茫,同时从全新的生命体验出发,继续表达着对都市文明的厌倦和批判……应当指出的是,元举虽然一再批判乃至诅咒着都市文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将都市的一切和一切的都市,从根本上统统加以否定,事实上,他也有赞美都市甚至忘情于都市的时候。关于这点,我们读他的《上帝广场》即可不言而喻。只是所有这些面对都市的赞美和忘情,都是因为作家眼中的欧洲都市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与人的默契,是一种人的意志的投射和情感的外化,它们同国内许多匆促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暴发户”式的城市姿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元举对都市文明褒也好、贬也罢,都最终是以人为本体、为尺度的,都是他特有的古典情怀的充分流露。
在揭示现代都市文明和科技文明所造成的人性扭曲与压抑的同时,元举的散文创作还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鲁迅先生早就为之忧虑的国民素质与根性。在作家笔下,相当一部分国人的处世态度是不健康的。当面对自然美景时,他们过于狭隘,也过于霸道,过于急功近利,也过于一厢情愿。于是,一系列粗糙、生硬的人工装饰,使喜欢变成了占有(《敏感的河流在我的心中颤栗》);在城市居住中,他们常常暴露出自私、慵懒和狂躁,凡此种种很容易恶化公共生存空间,而恶化了的公共生存空间,又总是反过来破坏着人们平衡健朗的生活态度(《城市语境·环境咏叹》),导致恶性循环。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决策者的各级政府官员们,其眼光和水准也分明不容乐观。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总也走不出“官本位”的心理定势,总习惯用长官意志裁决一切,以致不时地在种种好大喜功、颐指气使和随心所欲中,制造着生活的错误,也展览着自己的无知。其中江西南昌新建滕王阁的失度憨大、四川成都中心广场环境被一批高层建筑所破坏等等(《表述空间》),均堪称这方面的典型。即使是代表着社会理性与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又何尝不暴露出某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弱点,如过分的拘谨、软弱、清高和迂腐……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文学,都从事实的反面呼唤着健康的人格与美好的人性。它们把作家始终不弃的匡世济时的责任感以及愤世嫉俗的正义感,挥洒得郁郁勃勃,淋漓尽致,从而使读者又一次感受到了来自创作主体的如潮水般涌动的古典情怀。
应当看到,在元举的散文创作中,其以人为本、大写人生的古典情怀,至少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文艺复兴,这无疑是古已有之的。只是这种古已有之的对人的尊重、理解和张扬。在历经数百年风云激荡,人类社会已跨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并不曾失却自身的积极意义,相反因为科技的裹挟和物质的壅塞而倍显光芒。它所具有的丰腴而强劲的内涵,就像一种实效甚好的心灵保健品,把充足的营养成份和活性元素送给了现代人,从而使其有可能从种种污染、挤压和包装中突围,继续保持人生鲜活的自性和旺盛的创造力与进击力。由这样的视角看问题,元举的古典情怀实际上又是一种现代话语。
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作家的元举,一向有着开朗的性情,飘逸的气质和阔大的胸襟,以及热爱艺术和耽于畅想等特点。这样一些主体因素自然而然地渗透于其作品之中,随即幻化为一种浓郁的、几乎无处不在的浪漫气韵。它们最终又与同样是源于作家生命深处的古典情怀和理想精神相融汇、相整合,这时,元举的整个散文世界便不仅具备了充实饱满的内质,而且在叙述表达等最直观的形式层面,呈现出个性盎然的审美风度。
读元举的散文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作家驱笔为文,无论写人物抑或描景物,讲知识抑或谈感受,都有一种主体情感涌动其间,而这种情感绝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式的故做多情,而是真正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自然流露,是创作主体与审美客体对接与撞击之后所迸发出的强劲的生命之流。譬如,在从黄河源到柴达木的西行系列散文中,元举的生命激情总是被目光里的恢宏、坚忍或崇高所唤醒、所牵动:面对光光亮亮、漾漾荡荡的河西大走廊,他感到生命的大门无比兴奋地敞开了,“我渴望着回到古战场,渴望着前面出现那山崩般激扬的马队,马蹄下飞扬起遮天蔽日的黄尘,马背上翻飞起寒光闪闪的大刀片,那里边肯定会有我,我会比别人更骁勇善战。(《河西大走廊》)而一旦遭遇黄漂勇士的壮烈牺牲和由这牺牲引出的种种轻漠,作家则禁不住动情地发问:“悲哀的黄河呀,你流淌了世世代代,你带走了许多污秽和耻辱,也带走过欢乐和英魂,你载得动无边的平庸和渺小吗?”(《难忘黄漂》)咀嚼着这样被至性与至情浸泡过的文学,我们足以增添体内所需的钙质与活力。同样,在《上帝广场》一书中,元举真挚激越的情感蕴藏,也不断由客观景物所引发、所点燃,进而幻化为一个个真情流溢的生命磁场: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掀动着爱与美的潮汐(《贝多芬的魅力》);巴黎的凯旋门催生出“深沉的忧郁以及无法诉说的哀怨(《世纪对话》);那一条条大小不等的中外河流,更是搅拌了复杂多变的忧喜悲欢(《敏感的河流在我心中颤栗》)……所有这些,都贻人以深深的打动和强烈的震撼。即使在《表述空间》这样一部专谈建筑的作品里,作家的激情也依然汹涌澎湃。它不仅让那些很容易陷入枯燥的专业知识,变得生动和柔润起来,而且为作家构建的整个艺术空间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平添了一种阳刚和雄健之美。
在元举的散文世界里,生命激情并非单单是一种艺术血脉和审美元素。同时还是一种精神酵母和灵感促生剂。它很自然地开启了作家面对大千世界各种物象的联想和想象能力。并推动这种能力进入了“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的理想空间。这时,作家笔下的许多形象和景物都因为想象和感觉的参与而发生着错位和变形,直到实现审美效果上的“离形得似”或“无理而妙”。不是吗?浩瀚戈壁上的黄沙,原本是无知无觉、无性无灵的。但它成了《悟沙》的抒写对象后,便幻化为西部的象征和语言。它不仅拥有刚柔相济的容貌和动作,而且还表现出性格上的热情与沉默,暴虐与缠绵,以及渴望让人听懂的永不消歇的倾诉。作为中国古建筑的斗拱现已是建筑行业的标志性符号。之所以如此,其原初的意义或许仅仅因为它在建筑中“作用最大、责任最大、压力也最大”,然而,作家却硬是在这一符号中读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痛苦和人格扭曲。于是,斗拱变成了苦难的写意与投影(《寻找建筑文脉》)。还有,在山脉与河流疏远的并存中,作家发现了平庸与圣洁的差异,以及世俗与英雄的难以沟通(《我与〈黄河悲歌〉》)。而那一条著名的塞纳河,更是让作家沿着“水”的意象和线路,串联起了繁纷摇曳的社会与人生(《敏感的河流在我的心中颤栗》)。应当承认,所有这些都是感性的、具象的,但又绝不仅仅是感官的狂欢和感觉的复现,而是感性之中渗透了理性,具象之内包含了抽象,即作家那一系列的联想和想象中,很自然地积淀了自己的生活体验、观念认知、学养储备、情感评价等等。这令我们不禁想起刘勰在谈论“神思”时的名言:“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文心雕龙·神思》)元举展开想象时的特点,恰恰可作如是观。显而易见,这样一种植根于社会和生活的艺术想象,不仅有效地强化了作品形象思维的特征,而且还在这种形象特征的强化中,清晰地浮现出作家特有的浪漫气质与人格,最终为读者从作家的角度观照和理解作品,提供了便捷。其审美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应该谈谈元举散文的叙事艺术了。在这方面,作家每每表现出一种极为突出的特点,这就是:行文洒墨既不过多的考虑是否符合散文的规范和体式,也不刻意追求什么变革或新潮,而是坚持从艺术创造的目的和需要出发,一任自己的性情、胸臆和匠心,做自由充分、无拘无束的传达,由此使通体叙述变得既酣畅淋漓,又多姿多彩。如《解读茶花女》一文,它状写的是作家在巴黎参观茶花女墓地的情景,但却不曾让笔触局囿于既定的时空和过程,而是以此为中心展开了多向度的辐射:既引入了小仲马名著《茶花女》中描写女主人公的精彩段落;又介绍了巴黎社会流传的有关茶花女原型阿尔芒西娜·普莱西的种种材料;还讲述了作家年轻时与小说《茶花女》相关的一段经历。上述内容浑然于一体,便大大丰富了一篇原本简单的游记作品的思想、情感和审美含量。《爸爸的心就这么高》因为以郎氏钢琴为表现对象,所以书中一再写到了音乐,特别是写到了具体的音乐演奏场面。而这些音乐描写同样是奔放不羁,尽脱窠臼的。它们似乎不再满足于一般化地渲染现场氛围,模拟音响效果和勾勒音乐家的风度,而是在此基础上,发挥作家富有音乐修养的强项,让其大胆地进入主人公的内心和音乐作品的内里,于生命层面展开由内而外的象喻性的语言创造。毫无疑问,这样写成的散文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音乐的营养,同时也接近了音乐本身,因此常常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撼动力。至于一部《表述空间》,更是在长短不一的篇幅中,把小说式的人物刻画、报告文学式的主体宣叙、杂文式的剖析议论、以及随笔式的知识传播、学术普及聚拢在一起,从而调动种种手段,发挥种种优长,托举起建筑这“凝固的音乐”。元举曾说:“我崇尚有个性的人,因此,我就是一个有个性的文人。”(《西部生命》)可以这样断言:元举的散文叙述是实证着这一点的。而此种个性化和性格化的散文叙述,或许同当下散文的常见形态拉开了距离,但是却从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我就是我”的散文精神。因此,它还是值得我们从整体上加以肯定的。
总之,如果把元举的散文创作比作一曲宏大的生命交响,那么古典情怀的浪漫抒写遂构成了此种交响的主旋律。这种主旋律对于整个乐章来说,不仅意味着人文高度和精神重量,而且发散为独特的艺术气势和审美风度,它最终使作家成为当代散文领域令人关注的“这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