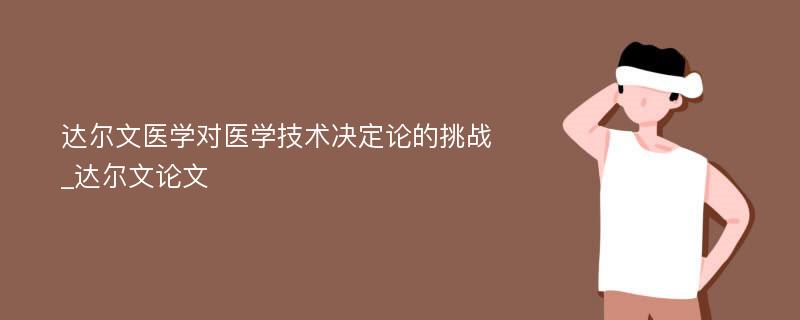
达尔文医学对医学技术决定论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尔文论文,医学论文,决定论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物医学模式与医学技术决定论
生物医学模式是伴随近代医学的发展逐渐形成的,其显著的特征是趋向于用理化、生物的语言,用实验仪器获取的数据精确地解释生命现象和病理现象,并借助医疗技术手段干预疾病。历史地看,它是近代自然科学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贯穿生物学与医学领域的必然结果。
近代自然科学蹒跚起步时,笛卡尔便在心物分割的基础上为它提供了一套分析性的推理方法,奉献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在他看来,心与物全然两样,互不归属。物质世界仅仅是一部机器,没有目的、生命和精神,它依照力学法则而运动,而且可以根据其组成部分的排列和运动加以解释。此后,牛顿为这一机械自然观补充了数学公式,将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等人的工作综合起来,建立了经典力学体系。它描绘了一幅因果决定论的宇宙图象,其中的每一个事件都由初始条件决定,因而原则上均可以被精确地预言和控制。由于近代医学与生物学携手并进,而生物学又坚实地站在物理学和化学的背脊上,因此,机械自然观和还原论的分析方法向医学领域的渗透在所难免。
在生物医学模式300多年的旅程中, 它始终受这样的信念所支配:人是一架机器,其机体可以被还原为一些最基本的构件,通过对各构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就可以认识整个机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器官、组织、细胞和分子曾被当作生命机体的基本构件与疾病的“病灶”。生物医学家们相信,人类的疾病都是可以解开的生物学之谜,每一种疾病总有一个关键性的机制统领着其余过程,抓住它便可以想出某种方法来控制紊乱。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下半叶巴斯德与科赫建立的特异病因说,为生物医学提供了一个“经典”疾病概念:疾病是由特异病因造成的具有特异病理改变和特异症候群的临床诊断单元。换言之,在病原体与疾病之间存在线性因果关系,而症状与体征是识别疾病的标签。
生物医学对疾病的精确定义与定位,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手段。它对疾病的技术干预同样遵循笛卡尔“人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部件失灵”的教条,以效定人体特定部位的特殊生物机制为目的。以药物治疗为例:19世纪巴斯德细菌理论的建立以及对各种病原微生物的识别,促成了一系列抗感染疫苗的发现,它们被用来对付伤寒、破伤风、白喉及其他传染病。20世纪,医学问题被简约为在分子水平上寻找发病机制,机制被认识,就再寻找一种药物去对抗。无论是采用抗生素、安定药、心血管药或是多肽药,药物学家们都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药物释放系统,尽可能按需要控制释放和使药物特异地进入患部。
在医疗技术的推动下,生物医学创造了无数的人间奇迹,从传染病的控制到开心术、试管婴儿、基因治疗直至克隆生命,这一切都曾是人们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事。它的节节胜利编织了一个现代“神话”,那就是凭借医疗技术手段,人类可以征服一切疾病,即便对现今的癌症、艾滋病等顽症,人们也坚信医疗技术对它们的征服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换一个角度看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医疗社会建制,也不难发现它是按急性病治疗方针构建的,形形色色的医院和医疗中心是它的“硬核”。医生与护士们都认为,只有不断采用最新的医疗技术,才能提供最佳的服务。加之市场经济的牵引与催化,医院对配备高新的医疗技术仪器十分的热衷。医学的高技术化趋势,也使医院的人员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百多年前,医院中医生与辅助人员的比例是2∶1,现在却变成了1∶15。各种诊断与治疗仪器的应用,加速了医院的专业化倾向。 虽然病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进入医院,但他们却象工厂传送带上的物件一样,在各科室间轮转。社会公众一边抱怨医疗费用的增长,一边抱怨技术化的医学日愈丧失了对病人的人文关怀。
二、达尔文医学:第三只眼睛看疾病
20世纪下半叶,生物医学模式在医学实践中面临的一系列困境,促使人们对其理论基础进行全面反思。1977年,美国精神病教授恩格尔率先提出了取而代之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并很快获得了全球范围的认同。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生理医学模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对人性本质的忽视以及对生命整体性的支离分割。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影响健康与疾病的心理、社会因素留下应有的空间。
生物医学模式支配的医疗实践活动,虽然在处理急性病方面出类拔萃,但它对治疗过程中的特异现象,尤其是对现今许多与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却束手无策。更为严重的是,对技术干预的盲目崇拜,不仅导致了大量医源性与药源性疾病,而且使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医疗费用高速增长的财政危机,使医学误入了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胡同。正如恩格尔所言:“生物医学模式引起的彻底征服疾病的誓言,只不过是迎合了人类追求人间天堂的根深蒂固的愿望,我们已经为没有和不可能实现的诺言付出了代价。”①
毫无疑问,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对生物医学模式的超越,对此。已有许多文章和著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恕不赘述。然而,从整体上比较新旧两种医学模式,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对疾病进行的是共时性研究与近因解释。更为具体的地说,两者在既定的时空横截面上,把疾病视为患病时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环境(自然、社会环境)的历时性变迁对疾病的影响,却成了一个盲点。
众所周知,从古到今,生命科学研究一直并存着博物学与生理医学两个悠久的传统。据此,著名生物学史家E ·迈尔把生物学划分为近因生物学与终因生物学两个方面。前者主要研究生物的结构与功能,包括遗传学、发育学、生理学等;后者则研究生物的演化和历史,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为典范。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生物学家们就致力将两者结合起来,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但由于各种原因,进化论向医学领域的扩展却姗姗来迟。
1991年,美国进化论生物学家乔治·威廉斯与精神病医生伦道夫·尼斯共同创立了医学科学的一门新学科——达尔文医学 ( DarwinianMedicine),并将其定义为“探索疾病敏感性的进化论解释”。尼斯解释说,达尔文医学的核心是把每一种疾病都作一种进化,并作出贴切的解释。例如:感染不是遭遇致病微生物的结果,而是寄生与寄生物之间的权力竞争;创伤不是一种组织损伤问题,而是保护机制和修复过程的相互作用,符合自然选择学说;引起疾病的基因不是有害突变的产物,而是适应环境需要的选择,这种选择还有待我们去发现;等等。概言之,达尔文医学是从物种的观点考虑疾病而不是从个体的人考虑疾病。②
毫无疑问,达尔文医学不可能绕过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这一核心的概念与法则。但它对此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诠释,那就是强调自然选择的不完美性以及进化过程中适应性变化所导致的利弊双重效应。威廉斯与尼斯认为,支持达尔文医学的是进化过程中适应性变化可能会导致有明显的消极与积极后果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适应性变化都应被视为一种妥协。例如:背痛是常见的一种症状,它是站立姿势的一种代价;有效组织修复的代价是癌;强大的免疫系统的代价是免疫紊乱;焦虑的代价是惊恐疾病。③
达尔文医学关于自然选择不完美性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生物对单一环境的适应会使这种适应逐渐变得脆弱,无法适应环境的适度变化,从而发生疾病。例如:狩猎、农耕时代,在灾荒与饥饿的压迫下,耐饥饿型基因的个体生命力最强,从而使这种基因得以保留和扩散。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食物相对充足,一部人的过度进食取代食物匮乏,营养过剩代替营养不良,体内基因无法处理这些新因素,于是便有了糖尿病。其二,生物经自然选择获得的适应结果是整体状态的,而不是单个器官与单一功能。人类虽然以万物之灵自居,但在许多方面,比如说感官方面,我们对自然的适应能力比一些动物要差得多,这就用不着再多举例。因此,达尔文医学认为疾病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永恒苦难,是人类为其获得的某种益处所付出的一种代价。目前,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们正致力于研究,为什么自然选择仍然使人的身体保持有易致病性;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与各种疾病有什么关系;基因的功能与疾病有什么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詹姆布尔说:“进化论医学主要是一种关于我们如何想象以往岁月中,进化对我们的作用以及它为我们设计了什么样的猜测游戏。”④
三、挑战与启示
虽然达尔文医学现在还处在浪漫的起步阶段,理论基础十分脆弱甚至带有一定的思辩色彩,但它观察疾病的全新视角,对我们反思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事实上,它已对医学技术决定论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首先,达尔文医学把时间之矢引入疾病研究中,从而深化了人们对疾病动态性与过程性的认识。传统医学模式对疾病的近因解释固然重要,但这种“近视”只揭示了时空座标上的某一点。形象地说,它寻找的是人类患病之“流”,而不是人类患病之“源”。因此,近因解释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它对隐藏在“偶然”发生的各种疾病背后的历史“必然”缺乏充分说明
其次,达尔文医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强调了人对环境的文化适应性与各种疾病之间的关系。虽然达尔文医学从自然选择的不完美性方面,揭示了人体结构的缺陷及其易致病性,但从农耕时代之后,人类主要是通过其文化来适应外部环境的(此后人类基因变革极微弱,大约在0.005%左右),因此,人类的许多疾病尤其是精神疾病与文化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人类自身的繁殖长期采用自然的方式,但工业文明与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对自然繁殖的技术控制成为可能。它无疑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一种进步,但无形中也使现今妇女患子宫内膜癌、卵巢癌和乳腺癌的危险性比远古时代高。比之生物医学模式仅把人视为一种生物的存在,达尔文医学更为重视人的整体性,在这一点上,它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有异工同曲之处。
再次,达尔文医学从进化的角度揭示了健康和疾病的互补性,强调了疾病对人类进化的有益作用。事实上,健康与疾病不过是生命活动的两种基本状态,彼此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全然没有人与疾病的竞争,生命活动就会终止。
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达尔文医学否定生物医学模式“对症施治,症去病除”的技术干预原则。生物医学认为疾病及其症状是能够被排除而且必须被排除的人体的孤立缺陷,并相信凭借技术的手段可以解决一切医学问题。达尔文医学认为它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机体的防御功能与疾病,例如:发势是对感染的一种防御;疼痛是对机体组织损伤的一种防御;而呕吐、腹泻则具有加速排除有害物质,使机体免受毒素侵害的功能。但生物医学却片面地采用技术手段消除类似的症状,无形中降底了机体的防御功能,引起了对机体的进一步伤害,这也是各种医源和药源性疾病产生的根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