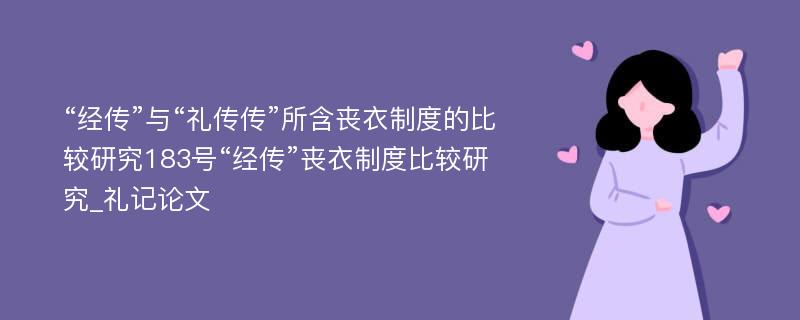
《礼记》与《仪礼#183;丧服》经、传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丧服论文,礼记论文,所载论文,制度论文,仪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0)05-0048-10
关于先秦丧服制度的规制,除了在《仪礼·丧服》经、传中有系统、全面的记述外,在其他先秦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和阐述。今传本小戴《礼记》之论礼诸篇是《仪礼·丧服》经、传以外的先秦文献中记述和阐释丧服制度最多的典籍。《礼记》论礼诸篇所记述的丧服制度虽然大多与《仪礼·丧服》经、传结合,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丧服传》解经时也有与经文不一致之处,而在这种情况下,《丧服传》的内容往往与《礼记》论礼诸篇的有关内容相合。笔者拟在本文中对《礼记》论礼诸篇与《仪礼·丧服》经、传所载丧服制度的同、异情况进行具体考察和分析,并对形成这些同、异现象的原因进行推测和论述。
一、《礼记》论礼诸篇关于丧服制度的记述与《仪礼·丧服》经、传基本上是一致的
通过考察、对比《礼记》论礼诸篇与《仪礼·丧服》经、传三者所记述的有关丧服制度的内容,便不难发现三者有关丧服制度的主体内容是大同不异的,亦即除了少量相违异者外,绝大部分内容是相同的或相辅相成的。如《丧服经》未为嫂、叔制服,对此,《丧服传》于大功章解释说:
夫之昆弟何以无服也?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妻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礼记·大传》也有云:
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
上引《丧服传》与《礼记·大传》对《丧服经》中“嫂叔无服”的解释文字,几乎完全相同,有可能是同源于孔子当年对《丧服经》的传授和解释(理由详见下文)。此外,对于嫂叔无服的原因,《礼记·檀弓上》则更进一步概括指出:“嫂叔之无服也,盖推而远之。”显然,这段《檀弓》之文是对前引《丧服传》与《大传》之文所体现的主旨精神的归纳概括。
又如关于斩衰服的居处饮食之制,《丧服传》于斩衰章章首曰:
居倚庐,寝苫枕块,哭昼夜无时。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寝不说絰带。既虞,赞楄柱楣,寝有席,食疏食,水饮,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练,舍外寝,始食菜果,反素食,哭无时。(注:按此段传文中“赞楄”,今本作“翦屏”;“反”,今本作“饭”。兹从武威汉简本《服传》校改。)而《礼记·间传》则曰:
斩衰三日不食,……故父母之丧,既殡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此哀之发于饮食者也。
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
父母之丧,居倚庐,寝苫枕块,不说絰带。
父母之丧,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纳。显然,上引《丧服传》与《礼记·间传》中关于斩衰服居处饮食的规定虽然字句有差异、次序也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基本内容却是一致的。
上述种种相同、相似或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内容在《仪礼·丧服》经、传与《礼记》论礼诸篇中比比皆是,兹不备举。此外,在《仪礼·丧服》经、传与《礼记》论礼诸篇中还有一些看似矛盾而实际上是相通的内容。如关于丧服用杖的问题,《丧服传》解释说: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齐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无爵而杖者何?担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辅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妇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而《礼记·丧服小记》则曰: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礼记·丧服四制》亦有云:
杖者何也?爵也。……或曰担主,或曰辅病,妇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显然,在关于用杖的制度上,《丧服传》与《礼记》的解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依据《丧服传》的说法,似乎丧杖本为有爵者而设,后来才扩大使用范围,及于无爵男女之为丧主者与无爵男女需“辅病”者。可是,《礼记·杂记下》有云:
古者贵贱皆杖。叔孙武叔朝,见轮人以其杖关毂而輠轮者,于是有爵而后杖也。明言古代本来“贵贱皆杖”,直到叔孙武叔见轮人(贱者)亵渎丧杖后,才改为只让有爵者用杖。应该如何理解《丧服传》与《礼记》的不同说法呢?清儒郑珍解释说:
细思二文,子夏就贵贱皆杖时明皆杖之原委;作《[杂](小)记》者就其时贱者废杖,明贵者独杖之原委。文虽异而实同也。(注:郑珍《〈仪礼〉私笺》卷四,《续四库全书》本。按郑著将所引《礼记》“贵贱皆杖”之文误标为《小记》,应校改为《杂记》。)
应该说,郑珍的解释是很有道理的。由此可知,《丧服传》与《礼记·杂记下》的不同说法是由立论的不同角度所致,而并非对于用杖之制有着根本对立的意见。
《礼记》还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一些服丧事实,这些服丧事实中许多是与《仪礼·丧服》经、传的规定不相符合的,因而它们是被《礼记》作者作为“非礼”的行为而被记述下来的。通过这些记述也可以发现《礼记》与《仪礼·丧服》经、传在服制观念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如《仪礼·丧服·记》云:“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为其妻,縓冠,葛絰,带,麻衣縓缘。皆既葬除之。”《传》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据上引《丧服》经传,可知诸侯之妾子(公子)于父在时为母、妻只服不在五服之中的、象征性的丧服。据《传》文“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可知国君为妾无服。又《仪礼·丧服》缌麻章曰:“贵臣,贵妾。”《传》曰:“何以缌也?以其贵也。”郑注曰:“此谓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贵贱而为之服。贵臣,室老士也;贵妾,禫娣也。天子诸侯降其臣妾,无服。士卑无臣,则士妾又贱,不足殊,有子则为之缌,无子则已。”据郑注,则天子诸侯为臣妾无服,而只有公卿大夫之君才为贵臣、贵妾服缌麻之服。
而《礼记·檀弓下》则有这样一段记载:“悼公之母死,哀公为之齐衰,有若曰:‘为妾齐衰,礼与?’公曰:‘吾得已乎哉?鲁人以妻我。’”按,悼公之母,郑注以为即“哀公之妾”。由于鲁哀公违犯了国君为妾无服的礼仪规定,故有若讥而问之,鲁哀公便以“鲁人以妻我”来文过饰非。由此可见,《檀弓》作者亦以哀公之举为非礼,故书而讥之。从而可以推论《檀弓》作者对于《仪礼·丧服》经传关于国君为臣无服的主张是认可的。
在此需指出的是,郑玄于《仪礼·丧服》注中明言“天子诸侯降其臣妾,无服”,而于上述《礼记·檀弓下》所记哀公为悼公母齐衰下注云:“讥而问之。妾之贵者,为之缌耳。”谓有若“讥而问之”是正确的,但认为国君为贵妾服缌,则既与《丧服》之郑注自相矛盾,又与《丧服》经传之义相违异,不足为训。
二、对《礼记》与《仪礼·丧服》经、传不同服制内容的考察与分析
(一)《礼记》不同于《仪礼·丧服》经、传的服制内容
《礼记》论礼诸篇中关于服制的记述虽然与《仪礼·丧服》经、传的基本精神一致,但也有一些不一致或相违异的内容。如《丧服经》规定,致仕或因故被罢官、被放逐之臣为“旧君”服齐衰三月之服。《丧服传》曰:“为旧君者,孰谓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齐衰三月也?言与民同也。”又曰:“大夫为旧君,何以齐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扫其宗庙,故服齐衰三月也。言与民同也。何大夫之谓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犹未绝也。”
可见《丧服》经、传均主张为“旧君”有服。可是《礼记》中却有多条为旧君不反服的论述。如《礼记·杂记上》云:“违诸侯,之大夫,不反服;违大夫,之诸侯,不反服。”这是说无论是离开诸侯到大夫处任职之臣,还是离开大夫至诸侯处任职之臣均不为其“旧君”有服。再如《礼记·檀弓下》云:“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馈焉,曰献。使焉,曰‘寡君’。违而君薨,弗为服也。”这是说曾任公职而未确定俸禄者离职后,为旧君无服。《礼记·檀弓下》又载:“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据子思所论,则“为旧君反服”是古礼,而在其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之际)似已无人为旧君反服了。
据此可以推论,《仪礼·丧服》经、传的主张可能是宗周时期旧有的礼俗遗制,而《礼记》所载则是春秋战国之际人们为旧君服丧的实际情况。后来齐宣王向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询问:“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孟子便对为旧君有服与无服的问题作出了如下的解释:“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孟子认为君须待臣“三有礼”,然后臣才为旧君有服;反之,则臣为旧君无服。不难看出,孟子对为旧君有服与无服的解释是对《礼记》所载子思观点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由此可见后世将子思、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称为思孟学派,良有以也。
再如《仪礼·丧服》齐衰三年章:“慈母如母。”《传》曰:“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若是,则生养之,终其身,如母。死则丧之三年,如母。贵父之命也。”而《礼记·曾子问》则云:“子游问曰:‘丧慈母如母,礼与?’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似乎孔子不主张丧慈母如母,与《仪礼·丧服》的规定有所不同。
对于这种矛盾现象,郑玄于《仪礼·丧服》注曰:“此主谓大夫士之妾,妾子之无母,父命为母子者也。其使养之,不命为母子,则亦服庶母慈己者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为母大功,则士之妾子,为母期矣。父卒则皆得伸也。”而于《曾子问》则注曰:“此指谓国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可见郑注认为《仪礼·丧服》所谓之“慈母”是对大夫士之子而言:而《曾子问》中孔子与子游所讨论之“慈母”则是对国君之子而言,亦即孔子批评“丧慈母如母”为“非礼”是对国君之子而言。其说虽然似乎能够自圆其说,但难免曲意弥缝之嫌,难以令人信服。于是,后来梁武帝萧衍曾试图对此作出新的解释,他说:
《礼》言慈母凡有三条: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扶隆至,虽均乎慈爱,但嫡妻之子,妾无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正是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而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名。师保既无其服,则此慈母亦无服矣。……子游所问,自是师保之慈母,非三年小功之慈母也。故夫子得有此对,岂非师保之慈母无服之证乎?郑玄不辨三慈,混为训释,引彼无服,以注慈己,后人致谬,实此之由。(《南史》卷七十一《儒林·司马筠传》)
萧衍虽然对郑注提出批评,但其思路实际上与郑注是一致的,都是以《仪礼·丧服》与《曾子问》所谓的慈母并非同一概念来说明二者在为慈母是否有服上的矛盾和歧异。应该说他们的解释都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均难以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当时对于为慈母是否有服确实有着不同的意见,《仪礼·丧服》经、传的编作者主张有服,而《礼记·曾子问》的作者却不同意有服,故托名孔子批评“丧慈母如母”为“非礼”。当然,由于文献不足征,还难以论定《曾子问》中所载孔子对“丧慈母如母”的批评是否为假托,但是,我们说当时对于为慈母是否有服这一问题存在不同意见,还是有文献学根据的。根据之一是,《礼记·曾子问》又云:“昔者,鲁昭公少丧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丧之。有司以闻曰:‘古之礼,慈母无服。今也,君为之服,是逆古之礼。而礼,国法也,若终行之,则有司将书之以遗后世,无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练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练冠以丧慈母。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按鲁昭公与孔子为同时代人。如果这段记载可靠的话,那么便可推定孔子之前的时代,丧慈母原是无服的,最起码可以推定其时对于为慈母是否有服是有不同主张的。根据之二是,战国时著名儒家学者荀子虽主张为母服丧三年,但又主张:“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荀子·礼论》)即晚于子游、子夏等人的荀子既不同意丧慈母如母的主张,也不同意为慈母无服,而是主张为慈母服大功九月之服。由此可见,直到战国晚期,对于慈母之服,即使在儒家内部仍有不同意见。
明乎此,便知前述郑玄、萧衍的解释虽似有一定道理,但难免刻意弥缝之嫌。实际上《曾子问》与《仪礼·丧服》经、传的不同内容有可能是由其作者的不同主张所致,不必为二者的歧异强为弥缝。
实际上,《仪礼·丧服》与《礼记》论礼诸篇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相违异的内容,只是为历代经学家的调和、弥缝所掩饰,因而往往使人习焉不察。如关于五服用布之升数,《仪礼·丧服》经、传与《礼记·间传》的记述也有所歧异。《丧服经》之“记”(注:按今本《仪礼·丧服》分经文与记文两部分,学界过去一般认为“记”文的撰作晚于“经”文,甚至晚于“传”文。1958年出土的汉简本《仪礼》与《服传》为我们认识“经”、“记”的关系提供了实物佐证。在简本中,经文与记文之间无任何区别标识,而且传文释“记”与释“经”之体例也并无不同。因此,沈文倬先生认为:“经和附经之记不应看作前后撰作的两种书,而应作为同时同人撰作一书的两个部分来看待。”(沈著《汉简〈服传〉考》(下),《文史》第二十五辑)沈氏之说甚是。为此,笔者采用其说,将《仪礼·丧服》之记文与经文同等看待。)文曰:
[斩]衰三升,三升有半。……齐衰四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丧服传》曰:
[斩]衰三升。(斩衰章)……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大功章)……缌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缕,无事其布。而《礼记·间传》则云:
斩衰三升。齐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缌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缕,无事其布。
关于五服用布之升数,《仪礼·丧服》之“记”文载有斩衰二等、齐衰一等、大功与小功各二等;《丧服传》则于五服仅各载有一种升数(唯齐衰缺载);而《礼记·间传》则于齐衰、大功、小功三种服制均列有三等。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呢?《仪礼·丧服》之郑注、贾疏均认为,斩衰有二等服,三升半为义服;自齐衰以下至小功各皆有降服、正服、义服三等之服,故齐衰有四升、五升、六升之分,大功有七升、八升、九升之分,小功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之分。依照郑注贾疏之说,上引《仪礼·丧服》之“记”、“传”与《礼记·间传》所载五服用布升数之不同,似乎只是详略不同,亦即只是《仪礼·丧服》之“记”、“传”有所缺载省文而已。实际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仪礼·丧服》“记”文所载丧服升数之所以比较简略,可能是因为其所追记的周代早期丧服制度对丧服用布的规定本来就比较简单,也不很精确,也许只是大致规定出各服的用布升数范围而已,如“大功八升,若九升”,可能是说大功之服可以用八升布,也可以用九升布;《丧服传》只是对丧服用布随文略作讲解而已,因而便有欠系统和全面;而《礼记·间传》中关于五服升数的记载之所以较《仪礼·丧服》经、传更加全面和系统,可能是出于其作者的发挥和补充,或者是由于《间传》撰写时代的丧服制度已有了新的发展和演变。如果以郑注、贾疏正、降、义之说来解释《仪礼·丧服》“记”中所载的五服用布升数,则难以解释何以齐衰只列降服,大功只列正、降二服,而小功则只列降、正二服。如此缺乏条理的记载,殊难令人理解。
为什么《仪礼·丧服·记》中的各种服制会有几种不同的升数呢?孔达生先生解说:
考之先秦典籍,皆无‘义服’之说,《丧服篇》中,更无一字提及‘义服’者,止有正服、降服二种。所谓‘义服’,当是汉以后才有的说法。后儒所以有义服之说,可能是因《丧服·记》所说衰裳升数,斩衰有三升与三升半,大功有八升与九升,小功有十升与十一升等不同,因而创造出‘义服’之说。其实《丧服·记》所记一种服制而有二种升数之布者,可能是表示可以任用其一之意,而非作一成不变的硬性规定。先秦之世,当无义服之说可知。(注:转引自章景明《先秦丧服制度考》,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98页。)
孔氏之说很有道理,可以信从。
(二)《礼记》所补充的《仪礼·丧服》经、传所无的服制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服制规定在《仪礼·丧服》经、传中均未提到,而《礼记》论礼诸篇却作出了补充性的规定和说明。如对于同母异父昆弟之丧服,《仪礼·丧服》经无明文,《丧服传》也未作说明,而《礼记·檀弓上》则云:“公叔木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仪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闻也,鲁人则为之齐衰。’狄仪行齐衰。今之齐衰,狄仪之问也。”由《檀弓上》此一记载,可知即使同为孔门弟子,对于同一服丧对象的丧服也有不同的主张,而且由此可知孔门弟子子夏在周季丧服制度的推行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再如,关于“三年之丧”的丧期究竟是多长时间这一问题,《仪礼·丧服》经、传均只说“三年”,未言其他,所谓“三年”,按平常理解,似应为三十六月。而《礼记·三年问》则对此提出了新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 尽,思慕未忘,然而以是断之者,岂不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注:按,《荀子·礼论》与《公羊传·闵公二年》也有将“三年之丧”缩短为“二十五月”的主张。由于《荀子·礼论》与《礼记·三年问》的内容基本相同,因而或认为《礼记》抄录《荀子》,而沈文倬先生则认为当是荀子抄录《礼记》,其说可从。参见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与〈仪礼〉书本的撰作》,《文史》第十六辑。)可见《三年问》主张将三年之丧的实际丧期缩短为“二十五月”。《三年问》何以要提出这一新主张呢?这可能是《三年问》的作者对当时存在的以为“三年”丧期过长的意见与呼声所作出的让步、妥协和调和。
(三)《仪礼·丧服》经、传的内容有歧异时,《礼记》或背经从传、或传违于二者之间。
《仪礼·丧服》传文的内容有时与经文不尽相同。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传文补加了经文所没有的一些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礼记》多是违经从传,有时也依违于经、传之间。如《丧服经》齐衰杖期章有“出妻之子为母”的明文规定,也就是子为出母之丧服与父在为母相同,都是齐衰杖期之服。此外,《丧服经》中再无其他关于为出母之服的规定。对于《丧服经》的这条规定,《丧服传》却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出妻之子为母期,则为外祖父母无服。传曰:绝族无施服,亲者属。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显然,“出妻之子为父后者”以下云云并非经文之义,而是《传》文新增的思想内容。
关于为出母之服的问题,《礼记》是怎样主张的呢?《礼记·檀弓上》载:“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孔疏云:“时伯鱼母出。父在为出母,亦应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犹哭,则祥后禫前,祥外无哭,于时伯鱼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据此可知孔子之子孔鲤(字伯鱼)所丧者为出母。而由孔子之批评伯鱼“期而犹哭”,可知他当是主张为出母服“期”之服,与《丧服经》的规定一致。而《礼记·檀弓上》又载:“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按子思名伋,伯鱼之子,孔子之孙;子上名白,子思之子。据子思所谓“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可知子思主张为出母无服,与《丧服经》的规定相反,也与其祖孔子的前述主张不同。此外,《丧服小记》还有云:“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这段《礼记》之文说明了出母无服的之原因。显然,其主张与前引《丧服传》文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上述《仪礼·丧服》经、传与《礼记》诸篇关于为出母之服的诸种不同意见,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丧服经》规定为出母之服与父在为母一样,同为齐衰杖期,可是有人则不同意这一规定,主张为出母无服。《礼记·檀弓上》所述孔子与子思对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观点,即体现了人们对为出母是否有服的意见分歧。而《丧服传》与《丧服小记》关于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亦即不为父后者为出母有服)的主张,则是对《檀弓上》所记述的两种不同观点的折衷和弥缝。
再如,关于妇人用杖与否的问题。《丧服传》、《礼记》所述似亦与《丧服经》有所不同。《丧服经》斩衰章于章首“斩衰裳,苴絰杖,绞带、冠绳缨、菅屦者”之下所列妇人之服丧者中,有“妻为夫”“妾为君”、“女子子在室为父”、“子嫁反在父之室”(为父)等。这些女子斩衰服是否与男子斩衰一样用杖?经未明言,但于“女子子在室为父”等妇人服下补充章首云:“布总,箭笄,髽,衰,三年。”清儒曹元弼认为:
此别言女服之异于男子者也。笄、总异于冠缨,衰不殊,裳异于衰裳。所异只此,则其余絰杖带屦皆同可知。杖是丧礼之大者。妇人果或不杖,经必别著之矣。齐衰期以杖、不杖分轻重,三年之丧无有杖者。不杖乃未成人者之不备礼也。(注:曹元弼《礼经校释》卷十二,《续四库全书》本(据清光绪十八年刻后印本影印)。)
曹氏之说甚是。据经文,妇人之斩衰不同于男子者确应只在首服,在是否用杖问题上,应承章首理解为与男子同样用杖。可是《丧服传》却说:“杖者何也?爵也。无爵而杖者何也?担主也。非主而杖者何也?辅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也?不能病也。妇人何以不杖也?亦不能病也。”明言妇人若非命妇,或非嫡妇为丧祭之主者,均不得用杖。显然,传意与经意有所不同。《礼记·丧大记》则云:“士之丧,二日而殡。三日之朝,主人杖,妇人皆杖。”与经意相合。而《礼记·丧服小记》却又云:“妇人不为主而杖者,姑在为夫杖。”虽然这是强调即使上有姑(婆母)在,也不为姑之尊所厌而为夫不杖。但由“妇人不为主而杖者”一语,则意味着妇人有因不为丧主而不用杖者。如此,则与经意相违。《丧服小记》又有云:“女子子在室,为父母,其主丧者不杖,则子一人杖。”郑注曰:“无男昆弟,使同姓为摄主不杖,则子一人杖,谓长女也。”这是指父母死无男儿,而使族人代主丧事,代主丧者不杖,故由在室女子中年长者一人用杖,其余女子则不杖。这意味着若有昆弟为丧主,女子子未嫁者则一律不杖。显然,这也与经意不合。
由此可见,在妇人斩衰用杖问题上,《礼记》依违于经、传之间,有时从经而主张“妇人皆杖”,有时又从传而认为用杖是有条件的。
三、对形成《礼记》与《仪礼·丧服》经、传所载丧服制度大同小异现象的推论
为什么《礼记》论礼诸篇与《仪礼·丧服》经、传所载丧服制度会出现主体内容相同或相近,但同中有异、大同小异的现象呢?
有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礼记》论礼诸篇与《仪礼·丧服》经、传所载服制内容相同或相近情况,是由于《丧服传》抄录、引用了《礼记》的有关内容。(注:沈文倬《汉简〈服传〉考》(下),《文史》第二十五辑。)而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不一定是《丧服传》抄录、引用《礼记》的结果,而当是由于《丧服传》与《礼记》论礼诸篇来自同一师承。这就牵涉到《仪礼·丧服》经传与《礼记》论礼诸篇的性质及其作者等问题。下面我们从《仪礼·丧服》经、传与《礼记》论礼诸篇三者的性质及撰作时代入手推究了造成三者有关丧服制度方面的内容存在同、异的原因。
关于《仪礼·丧服》经、传的性质及其撰作时代,笔者已有专文作过较详细的考察和论述(注:参见笔者的博士论文《〈仪礼·丧服〉研究》,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00年3月打印本。),兹仅撮述要点如下:孔子当年“修起《礼》、《乐》”时,将宗周以来流传下来的丧服礼俗遗制加以整理修订,编排为《仪礼·丧服》经,并参以己意,传授给其弟子。后来,子夏对孔子的讲授内容加以增补损益,再传授给他的弟子们。后经“师师相传”,著于竹帛,编定为《丧服传》。也就是说,今本《仪礼·丧服》经、传的著作权虽然还不能完全归于孔子与子夏,但将其主要的编撰、传授之功归于孔子、子夏二人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关于《礼记》一书的性质和撰作时代,传统的说法以为是孔子门徒所共撰。如唐儒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即认为:“《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世通儒,各有损益。”孔颖达《礼记正义》也认为:“《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缺,无复能明。……至孔子没后,七十子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虽然后世学者因《礼记》中夹杂汉儒的著述而对陆、孔二氏之说多所非议,但学界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礼记》是《仪礼》残存十七篇及已佚若干篇的传记,即皮锡瑞所谓‘弟子所释谓之传,亦谓之记’(《经学历史》二)。非常明显,它是依据《仪礼》书本来解经所未明、补经所未备的。……七十子后学者所撰之‘记’,在当时单篇传抄,未曾汇辑成书。因此,流传到西汉初年,渗入了若干篇秦汉间人的著作。”(注: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下),《文史》第十六辑。)
综上所述,可知《礼记》论礼诸篇中有关丧服制度的内容当主要是孔子后学所记述下来的当年孔子所传授的有关《丧服经》的内容与孔子及其后学所作出的阐释性的内容。由于《礼记》论礼诸篇的作者与《丧服传》的作者子夏同属孔子的七十子后学,因而就不难理解《丧服传》在解经时偶有与经义不合之处,而多与《礼记》一致。其原因就在于《丧服传》与《礼记》论礼诸篇的有关内容基本上同源于孔子当年的讲学,而《丧服经》却是孔子及其弟子依据宗周丧服礼俗遗制而整理出的仪节单子,孔子的讲学内容与这些宗周丧服遗制偶有不同之处是正常的。由于《丧服传》与《礼记》论礼诸篇同源于当年孔子的讲学内容,因而二者之间多有相合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