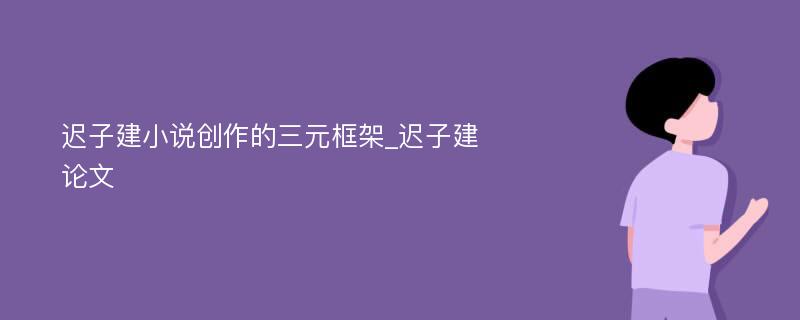
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三元构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构架论文,小说论文,迟子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识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她以其独特的地域性艺术视角,展现笔下人物特殊的生存形式和生命状态,反映他们不同的人生世界。
具体地说,迟子建的独特性就在于,她将故土人生表现的特殊方式作为其艺术特征的生长点,并以此为根基构筑她小说的艺术世界。在创作中,迟子建往往以地方的习俗风物、人物情感和生活故事作为她叙事的三元构架,在其交叉、融合和变化中,形成她独特的叙事方式,“把生活中本然的、真正的美显示出来。”[①]其中有人物自身的逻辑,也有作家对生命的体悟。因此,她才不同于其他作家,包括不同于本地写作同类题材的作家。迟子建这几年引人瞩目,其原因也在这里。虽然她不以深刻见长,却凭自己艺术表现的独特性取胜。可以这样说,自有迟子建,人们才真正认识了大兴安岭、黑龙江和北极村,才了解了那里的历史、生活,人们的命运、喜怒哀乐、奇闻轶事。而这一切,正是在迟子建三元构架的叙事中,散射出不同的艺术光彩,令人刮目。
在以往的创作中,叙写习俗风物,多是作为环境背景,体现人事的外部风貌,或者作为一种文化意识融入人物的生活中,从而给故事带来乡土气息,别有一番风味。而在迟子建的许多作品中,则对此进一步深化,把习俗风物看作是人物生命的一部分,是他们生活中的血肉经脉,深深进入人物的灵魂乃至生命基因里,成为人物和人生不可分割、与之同生同灭的同构物,因此它们同人物的生活、情感交融,难解难分。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将其分开,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便于分析、讨论迟子建创作的内部机制和规律。从迟子建的创作中我们不难看出,她的成功之作往往是具有这种三元构架的作品,而其中的习俗风物描写正凸现了她艺术创造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从她最初的创作中就已明显地表现出来。《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极村童话》、《北国一片苍茫》不但使读者领略了大兴安岭、北极村的自然风光、奇异然而却有中华民族传统特性的习俗,更主要的还在于看到了由此而构成的当地人的特殊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中体现出的人生命运,他们生命的挣扎和抗争,丰富的心灵世界。其后,她许多成熟的作品,更强化了这种叙事,《秧歌》、《原始风景》、《东窗》、《香坊》、《大树》等作品,则把这种描写推向极致,简直就成了《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然而它们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使读者赏心悦目,它们更是一个民族、不同人物的生命现实。
对情感的表现,对人物心理的观照,迟子建将这些看作是人物丰富复杂的精神状态的展示,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它有时成为作家描写人物的核心。也许是迟子建对人生的感受太强烈,对她熟悉的人物内心理解得更充分,才在她的作品中有那么丰富深沉的人物情感表现。这种表现即使不是直接的心理刻画,读者也会从人物的行为举止、神情言谈中感觉出来,并受到熏染和激动。而这种情感中有时就融入了作家的情感,所以作家创作时常常“长歌当哭”[②],并以此“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一线慰藉”[③]。她自己就说《乞巧》、《苦婆》、《支客》就是她哭出来的[④]。至于《白雪的墓园》、《旧时代的磨坊》等佳作,情感的抒发,愈加细腻和饱满,透出作家女性的灵秀之气,并有了摄人心魄的力度,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有血有肉的人物的活的“魂”。迟子建以地域风情显示了人物情感的独特样式,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受。
从本质上说,“生活是生命的质量体验”[⑤]。在迟子建的作品中,生活故事即是人物生存和命运的演绎,它因人物而存在,是人物自身行为的结果,因此它便成为表现人物的载体和支架。但它也有自身的内容,这内容也便表现出一个个人物的内质。一个个人物的生活故事便构成一个生活整体。所以,在迟子建的眼中,生活故事既是内容,也是一种形式,是表现人物的内容和形式,成为她创作的一元构架。总体上说,迟子建并不热衷于说故事,作品中的故事有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不甚具体,只是由人物(往往是一个中心人物)将它们串连成一个整体。表现在创作中,情节被大大冲淡,它只是一个线索和框架,把故事支撑起来而已。所以,她的作品与其说是寻求故事的意义,不如说是寻求人物的意义。由此可见,生活故事同习俗风物、人物情感一样,本质上都是对人物的叙事,人物才是作品的中心。如长篇小说《树下》,构成故事的,大都是女主人公七斗的一生经历,分别写了她在惠集镇、斯洛古镇、白轮船上和农场里的人生经历,而每一处经历又是她自身行为和与他人关系、纠葛中形成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不幸、挣扎与抗争,以及她性格的悲剧,从而得到对人生和生命的体味与感悟。
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生活故事、习俗风物和人物情感这三元构架在迟子建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同时也由于它们的相互交叉和融合,才使叙事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支撑起作品的中心——人物,人物也才有了独特性,成为“这一个”。迟子建的叙事有风采,人物有特色,秘密也正在这里。在三元构架中,人物情感同地方习俗风物交融,就产生了人物情感样式的特殊性;生活故事同习俗风物交融,生活和人们的生存方式也才有地域性内涵和自身的特色;人物的具有特殊性的情感同具有地域性内涵与特色的生活相交融,也才会形成一个有地域特征的完整人生世界,人物才最终有了本质风貌。
二
但是这种奇特性,也因三元构架近于魔方式的变化而各呈异采。
文学是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变化便没有艺术,有变化才有艺术的活力。但这种变化必须以深厚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艺术的表现必须以复杂多变的生活素材为依据,只有这样,作家才能施展才华,创作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品。因为一个成熟、有艺术追求的作家,其创作总是循着他个人的经验和艺术特长的轨迹探寻自己的艺术之路和境界。从迟子建的创作看,她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她的作品除了内部细微的艺术变化外,还有总体结构上的一些规律性变化。这种变化的突出特点就是习俗风物、人物情感、生活故事这三元构架之间的多种变形,亦即各元构架向哪一元转换倾斜,也便形成不同的叙事格局,产生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伴随三元构架的结构变化,三元构架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改变,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便由此诞生。
概括起来,迟子建作品的三元构架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种:
1.向习俗风物倾斜的构架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是以习俗风物为叙事重心,着眼于习俗风物中的人事。生活故事和人物情感的叙事都退居次要位置:生活故事被习俗风物叙事所吸纳或溶解,成为习俗风物中的故事,或者习俗风物引发生活故事;人物情感则由习俗风物而引发和反照,或者作用于习俗风物,浸润弥散其间。由于这种融合变化,一个奇妙的现象便出现了:读者面前展开的,完全是充满习俗风物并以此为基本内容的人生世界。一切矛盾、冲突、人物的命运,都与之密切相关,并且围绕它而展开。作品以习俗风物和与之相关的人物为中心,一方面突现地域习俗风物特色,渲染加浓生活氛围;一方面从中展开人生世相,表现人物的生命意识和自在的人性,使其具有本质意蕴。中篇小说《秧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作品几乎就是以各种习俗来结构故事,描写人物的。小说从平民女子女萝的视角切入,在女萝的情感弥散中,以秧歌和名角“小梳妆”为中心展开叙事,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多角度多层次地极写秧歌和“小梳妆”之美,以及由此引起的热烈、火爆场面。秧歌和“小梳妆”几乎融为一体,完全成了美的精灵,人人崇拜,个个迷恋,并且由此影响许多人的一生,成为他们生活乃至生命中的一部分。女萝和“小梳妆”也因秧歌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演出了自己的人生悲剧。作者对人们过小年、大年、正月十五、二月二以及婚丧嫁娶等种种风俗的描写,使这些风俗成为人物生命的表现形式。内中,既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⑥],也有他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⑦]。从象征意义上说,全篇是对美的高扬和追求,也是美的悲剧和毁灭。而造成这种悲剧和毁灭的,除了人的自身因素以外,更多的还有旧时代社会的原因,这样就使作品有了更深的社会内涵。另一部中篇小说《原始风景》几乎就是大兴安岭、黑龙江、北极村的风景大观,故事退到景物背后,情感也依稀隐于其间,而景物,不管是木刻楞房屋、白夜、月光、大雪,还是渔汛、野菜、一条普通的狗,都带有边地雪域特殊的风貌,有着人物特殊的心灵感觉,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具体“内容”。
2.向人物情感倾斜的构架变化。
在这种作品中,作家以人物的思想情感作为叙事的中心,其浓烈程度远远超出了作家对生活故事和习俗风物的描写,并且以此向人物的心灵深处拓进,展示人物最丰富最深沉的情感世界,而这时的生活故事除其自身的意义以外,主要是作为人物情感的载体,对人物情感起支撑作用;习俗风物则融会其中,成为人物情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加之作家情感的渗入,靠“一股激情调动这些事件和人物”[⑧],便产生了人物情感的巨大冲击力,震撼人心。充溢在《白雪的墓园》中的情感,是一位农村少女由丧父和母亲的极度伤痛而引起的悲哀和忧戚。人物的一切行为、言语,乃至炉火、墓园、纸钱、供品都负载着人物的哀痛与深情。其中的一些细节,简直就成为女主人公心灵悲恸的爆发点:母亲眼中忽然出现的“红豆”,使她觉得是父亲的灵魂栖息在母亲的眼睛里;母亲问上坟回来的弟弟说:“招呼你爹回家过年了吗?”简直催人泪下;而女主人公在过年时祝福母亲长寿、弟弟依照惯例跪下磕头为母亲祈求万福,也远远超乎寻常意义,而别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深情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作家将这一切集中在过春节时展开,使情感在习俗表现中得以最充分的体现,赋予作品以更深的意义。佛斯特曾说:“小说的功能就在表现内心深处的内在生活。”[⑨]迟子建以再现生活和习俗为契机,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深厚情感,正开掘出他们心中的内在精神“本性”。虽然,作这种重度情感倾斜叙事的,在迟子建的作品中不大多,但这无疑是她最成功的创作之一。
3.向生活故事倾斜的构架变化。
这种叙事倾斜,是作家以生活故事为表现手段,塑造人物形象,写出人物生活和生命的历史,并以此揭示人物生命的内涵。而在这种叙事中,作家又同时穿插。融入了带有地域特色的习俗风情,使整个生活故事闪射出浓重的地域文化色彩,同时又深蕴着人的自然生存意义和民族人文精神。虽然,人物情感的表现,有时不甚强烈,却似一股流泉,贯穿于作品的始终,使读者处处感觉到它的存在,并为之所动,受到潜移默化的熏染。于是,在生活中,人物的饮食起居、音容笑貌、人际来往、成败得失,便有了特定的意义和他们生命形式的个别性。这时的生活故事,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人生再现,而是带有地域生存特征和人物本质意义的生命现实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与那种缺乏地域特色的生活故事相比,它显得更真实,也更生动。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故事呈现出新的形态:
一是习俗风物和人物情感在与生活故事的交叉融合中,展现人生的历史,发掘出人物内在的神韵和风采。如在《树下》女主人公七斗一生的大故事中,作家以路过的鄂伦春人狩猎马队和鄂伦春人的隆重婚礼交织着七斗对一个鄂伦春小伙子的恋情和希望的破灭;七斗在船头向铺天盖地而来的水鸟投食和她倾慕黑龙江岸边平阔碧野的描写,正透出她的生命与大自然的和谐相融,是她对从前人生不幸的荡涤,灵性的重铸。因此,她才能面对人世的龌龊和陷阱,分外冷静和从容,也经受住了后来的种种磨难和心灵的创伤,保持了人性的那一份纯真和美好。而她珍藏的那条系辫锻带,不正唤起她心中的春意吗?虽然其中不乏沉重和苦涩,却给七斗带来了欣悦和轻松,给生活注入了几分生机。
二是较全面地展现生活和人物命运的复杂性及普通人的种种生存相。有时,生活虽不一定具体完整,有些只是不同生活片断和琐屑现象,但却多方面显示了人生存的不易和命运多舛,他们在现实中的欢悦与烦恼,矛盾与和谐,得意与尴尬,执著与无奈……以此给人以诸多的思考和启示。在《东窗》里,在女主人公和李鸿达一家、季曼云等人的种种生活故事之中,不论是对人的生死、女人吵架、坟地结亲、发洪水的描写,还是闹洞房、过端午、烧“替身”、瞎子算命、拜黄鼠狼等片断的穿插,都是对人生世相的多种展示,揭示了人的自身悲剧:他们的自我封闭和近乎原始的生活方式,落后的生存意识,正是造成自己不幸和生活停滞的自身原因。
三
当然,这种三元构架的叙事方式,同迟子建故乡生活的本然特征有天然联系。但是如何艺术地再现它,使之在作品中变幻多姿,融汇自然,却要由作家的内在因素决定了。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曾说:“艺术家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它不是一味的客观描绘。”[⑩]因此,三元构架艺术表现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心灵“内质”。
构成这种心灵“内质”的,首先是作家对生活和人生的深切体验。迟子建所以能写出大兴安岭、黑龙江和北极村及其特殊的地域风貌和内在特性,全在于那里的自然和生活铸造了她。儿童、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在她心中打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烙印,“从他出生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他的经验与行为。”[(11)]那里的一草一木、风土人情都化作强烈的生命意识,溶入她的血液灵魂里。因此,她的创作从一开始,便有大兴安岭、黑龙江的民族地域特性的胎记。即使是《原野上的羊群》这篇反映哈尔滨城乡生活的作品,引发她创作激情的,也是那里近似于她故乡生活的图景,因此创作中描写乡村生活的那部分保留了三元构架的叙事方式。在迟子建三元构架的创作中,有的就是来自于她亲自的生活经历,其中有她自我意识的作用和参与。所以,她往往以女性的视角写出人物的经历和感觉。由于过年、黄昏、月光、白雪、炉火、狗留给她的印象太深刻,与她生命的联系太紧,才使她情有独钟,总“带着一种怀念的心情”[(12)],所以在她的创作中反复出现,同人物的情感、性格,乃至生命紧密相连,有时对人物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她对于生、死和人性的本能尤其敏感,无处不体现出生命的顽强和亲切,而人的命运有时又祸福难测,仿佛命中注定,不可思议,这正与大兴安岭山林的古老、封闭和神秘有内在联系,形成三元构架叙事的内涵基础。正因为迟子建对故乡的人生体验得很深刻,她笔下的人物才有了内在的神韵和特性,而这正是其他外地作家难以掌握和表现的。他们的人物身上总像缺少点什么,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当地人那种近于与生俱来的生命体悟。而这又是作家心灵“内质”的内核,是绝然不可缺少的。迟子建有这种内核恰是她的优势所在,是别人一时无法拥有的。
其次,作家的心灵“内质”中还包涵着她对生活和人物的艺术感觉因素。王蒙说:“感觉是作家对人生经验、情感经验、社会经验、生活经验等各种经验合起来之后浮动在一般理性层次、经验层次之上的一种情绪、灵气和悟性。”[(13)]它“有时候是一种本能”[(14)],近乎一种天性,是作家的心灵感应。迟子建三元构架创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具有这种艺术感觉。因为,在一定的生活和作家的人生经验决定着三元构架的交融、变化之时,对其“度”的把握,就全凭作家的灵气和悟性了。《北极村童话》、《秧歌》、《旧时代的磨坊》、《大树》等成功之作,莫不如此。即使像《原始风景》、《东窗》这样情节散淡、片断繁杂、细节比较琐屑的作品,在三元构架的创作中,除了作家的框架设计之外,具体细微之处大都凭感觉去串连和布局:以女主人公“我”的经历、见闻和感觉,去融合人物、事件和生活细节,以作家的灵气贯通全篇,使叙事散而不乱,杂而有序,行文自然,气韵流动。假如迟子建没有自己的艺术感觉,缺乏灵气和悟性,仅以常识和理性去创作,许多“不合理”的片断和细节就无法调度和保留,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作品,也绝难产生自由散淡的艺术效果。
而且,这种心灵“内质”在迟子建身上是如此“顽固”,以致在她的先锋叙事实验中,只要是表现与她家乡有关生活的作品,就有三元构架的创造。《怀想时节》、《向着白夜旅行》、《炉火依然》,都明显地打着地域风土人情的印记。《向着白夜旅行》中,作为生活中“多余人”象征的幽灵马孔多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道奇异的风景,多少增添了一些地域性的魅力和他曲折“追求”的内涵。这时的三元构架已经不仅仅是生活故事和风土人情本身了,它已经成为一种意义。可惜的是,有些作品的先锋叙事将读者带入了迷宫,常常迷失方向,多少影响了意义的实现。即使是作家将其作为一种有意的模糊,作为见仁见智的生命感悟,怕也是一种难解的胡涂。这时,三元构架的创作几乎要被一种把玩智商式的操作所淹没,反不如传统的叙事来得纯真和明快。当然,作为一种艺术探索不妨一试,但变为一种偏执就不一定是幸事了。本来可以简单说清楚的,为什么要把它的时空打乱,故意写得扑朔迷离(比如《怀想时节》)呢?诚然,作家的创作应富于变化,但各有一路,迟子建对先锋叙事应改造、回归到她的传统叙事中去。迟子建生在大兴安岭,自有她的天分和特长,舍本求末便会迷失自我。
同时,我们也发现,迟子建进入大城市后,由于远离故土,失去了其生长艺术生命的根,又逐渐被缺乏特色的生活所同化,其三元构架的创作也在退化,作品中多了市民生活的琐碎和平庸,三元构架的创作正在被池莉、刘震云式的“新写实”所取代。这不能不是个遗憾。有的作家可以写遍天下,迟子建却不能游走四方。长篇小说《晨钟响彻黄昏》别人可以写出,《秧歌》、《白雪的墓园》、《原始风景》,甚至《大树》,别人却很难写出,这就是迟子建的价值所在。自然,进入城市并非写不出特色,《飞天》虽然浮了一些,毕竟还有南国风情的融入,还有作家对生命的深切感悟,给读者一种心理熨贴。但要真正保持三元构架的艺术生命、作家的心灵“内质”,写出独特的城市、外地生活,作家还须在那里来一次凤凰“涅槃”。写哈尔滨就要成为一个“老哈尔滨”。有了那里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才会找到新的艺术感觉,否则新的三元构架艺术创造便无法实现。但在“涅槃”期间,作家起码仍可写大兴安岭、黑龙江和北极村,到那里去寻根。
我们期待着迟子建。
注释:
①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
②③④迟子建:《长歌当哭》,《北方文学》1986年第9期。
⑤韩东、林舟:《清醒的文学梦——韩东访谈录》,《花城》1995年第6期。
⑥《汪曾祺文集(文论卷)·谈风俗画》,江苏文艺出社1993年版。
⑦《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关于乡土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⑧ (12)迟子建:《人间至情》,《中篇小说选刊》1995年第3期。
⑨佛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⑩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11)本尼迪克:《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3) (14)王蒙、王干:《感觉与境界》,《光明日报》1989年5月16日。
标签:迟子建论文; 小说论文; 三元论文; 中国习俗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秧歌论文; 作家论文; 东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