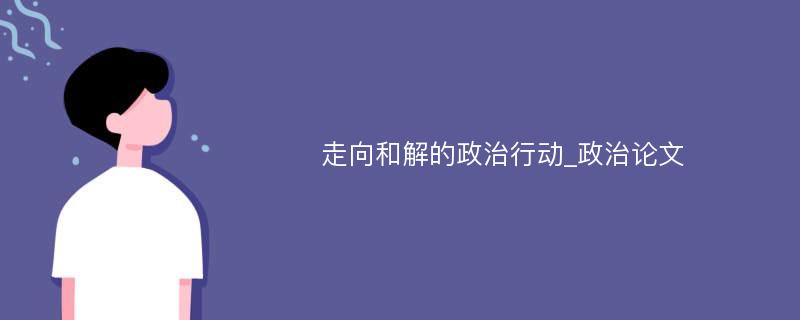
迈向和解的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政治是运动的政治
运动是现代政治的典型特征。这主要是西方化以及西方化的全球性扩张的结果。现代政治运动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它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治运动有一个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但保有基本主张同一性的意识形态。这与传统社会是不同的。在传统社会,政治观念不同于关于自然或宇宙的自然观念。也就是说,人们可能有很多种关于生活意义、宇宙本质、艺术特性的观念,但是,在政治方面,却只能有一种起根本支配地位的观念。也就是说,对于诸如这些问题: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合理的;权威的来源何在、人的政治性的义务是什么;美好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等等,基本上答案是一致的。谁应该拥有权力,谁应该下达命令或执行法律,谁又必须服从,答案是明确的、权威性的。传统的政治是非参与的政治,除了明确因为血缘关系天然地享有政治统治权的人,或者通过最严格的选拔(以中国古代为例,在汉代,是举贤良,隋唐后是科举)程序进入统治集团的人以外,一般人,至少在社会的常态,认为政治即统治①,而自己仅仅是被统治者,与统治甚至政治本身,是无关的。但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理想社会的想像、实现理想的渴望与改造社会的热诚,罗尔斯所谓的理性在自由的环境下运作,产生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②。这些政治运动,构成17世纪以后西方政治史的主要风景线。
第二是群体化与组织性。通过组织或宣传手段,或多或少公然地或公开地要求动用社会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越来越指向政治权力,或者至少使自己的意见或要求被当局或社会听到,是现代政治的明显特征。在西方,通过竞选的机制控制权力,政治组织谋求把自己的想法变成政策;而在政治不开放的地方,通过暴力性与会党性的组织取得政权,便成为另外一种选择。历史地看,在民族国家的层次,政治共同体越能对各种政治运动持宽容的态度,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就越有可能处于守法状态;相反,政府对各种政治运动越持压制态度,它们所积聚的破坏力就越大。在西方,政治运动虽然有可能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但是,它们的存在仍然被看成是神圣的权利。在这方面,纳粹与当代世界中各种各样宗教极端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
虽然现代政治由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构成,但是总的说来,公民权运动(民主运动或自由主义运动)、追求至善理想的运动以及追求某种宗教与文化的同一性的运动,构成现代政治的主要风景线。无论在民族国家层面的还是在国际政治层面,公民权运动的目标是建立欧美式的民主制度,它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权利的保护是国家的基础;而在所有的权利中,与古典的自由主义注重生命与财产不同,现代的自由主义更注重政治言论的自由,注重或强调在自由选举之上安排政治职位。自由主义无疑是欧美政治制度的观念基础③。但是,由于顽固要求按照西方甚至美国的方式建立民主制度,对西方以外的地区不断进行指责,这个运动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由于缺少欧美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对欧美方式的过度理想化,也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鼓励,公民权运动的核心是建立竞选式的政治游戏规则,在非自由主义的世界,变成了一种类似于秘密会党的运动,许多优秀人士走上了与政府为敌的道路,他们的牺牲精神与高昂的理想主义,加深了社会裂痕,增加了社会成本。
相比之下,另外两种运动,几乎是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回响。追求至善理想或至善的社会状态的运动,一方面,是历史上各种救世的社会理想的继续,因为在几乎所有的文明中,至善理想的思想都是很丰富的。另一方面,它也是对自由主义或者西方民主制度的决不缺乏真诚的超越。在现代世界,简言之,世俗的追求至善理想的政治运动,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政治中,都受到公民权运动的强烈挑战。这只要看一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争论就够了。
在西方世界凭借其物质的与思想的力量在全世界建立霸权的过程中,它对其他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严重的冲击。特别是在伊斯兰文明中,西方的霸权唤起了保持自己的文化同一性、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之纯正性的运动。这种运动的激进形式中,他们采取极端的形式,表达对宗教与生活方式的忠诚,要求西方的力量退回到自己的范围内。这种解决文明冲突的极端方式,有可能扩展到所有文化的内部,产生了极端的危险性。
当代政治意识形态皆不可以成为现代政治的观念基础
现代政治是由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构成的。政治运动既展开人类生存的诸多可能性(中立地说,无政府状态,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极权状态,和自由民主状态,都是人类的生存的可能性),又使人类的政治生活具有很大的风险性④。要在人类的政治经验中既包容又限制政治运动,既让它们展开人类的生存视野,又减轻它们对人类的损害,就应该建立一种底线的、共存的也是和解取向的政治。
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的自由主义,是现代世界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是,从现代史来看,它只是众多的政治运动中的一种,它并不能为现代世界提供充足的政治框架。自由主义的公民权运动为什么不能成为框架性的?很明显,它是西方文化在其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来的政治游戏规则,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起源。它的确在西方文化以外,产生了无数的仰慕者,但是,从经验的角度看,而不单单从维护某一特定的、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安排的角度看,毕竟还有,而且也应该允许有这样的可能性:在世界的某个地区有着广大的人口,他们可能根本无法接受自由主义对国家的理解。突出之点有两个。第一点,他们对国家持感恩的态度,或者说,持一种庇护者的国家形象;这种态度,奇怪的是,即使在西方民主制度的源头希腊与罗马,也是很通行的。换句话说,自由主义的视国家为“必要的恶”、为个人自由的天然敌人之说,离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几乎与离孔子一样遥远。那种主张严厉限制国家、且用权力限制权力的做法,在近代以前是很难理解的,也的确是与常识相距甚远的。很明显,说雅典或罗马的某一位高级官吏,特别是执政官,有可能渎职,或者说,用一种时代误置的词来说,有可能“侵犯”雅典或罗马公民的权利,这也许是希腊罗马人可以勉强理解的说法;但是,说存在一种抽象的国家,一种霍布斯式的“利维坦”,它是权利的天敌,这是雅典人无法理解的。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看来,“城邦”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公共福祉。共和国(res public),理想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国家,就是“大家的财产”(commonwealth)。的确,罗马人创造了权力相互检查的“共和制度”,但是,那出自一种非常不同的政治哲学:不是因为国家是恶,而是因为要处理不同的利益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的“公共利益”的特性。而这正是西塞罗政治观念的核心。第二点,重要的官职由竞选产生,由投票产生,这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支柱之一,但这种实践,同样受到思想家的检查,苏格拉底对拈阄产生高级官吏的批评,也受到西塞罗的强调。
为什么终极的至善论、目的论运动也不能成为框架性的?为什么追求宗教同一性的运动也不能成为框架性的?这两种运动或意识形态,与迫切要在全世界成为主导性的政治框架的公民权运动相比,本身就是特殊性的。在几十年前,在十九世纪,也许人们还有可能真心地相信有朝一日它们会成为主导性的观念。但在目前,它们无疑处于守势。这些观念只希望与别的观念在对话中相安无事地并存。
和解的政治,可以从不同的文明中吸取养料
能够为现代世界提供基本框架的根本政治学,或底线的政治,可能是既包容又限制现代政治运动的政治理论,可以恰当地称作“和”的政治或“和解的政治”。它既不同于解放的政治(反对压迫,争取平等)、承认的政治(要求受到平等的尊重,指向心理的、观念的或者态度的领域),也不同于传统治术的、统治的或控制的政治。
防范现代政治的高度的风险性,似乎应该对政治生活进行新理解。这种理解,是两个回复的过程:既回复到古代的,即文化轴心时期的单纯理想,又回到日常生活,顺着日常语言的指点,发现生活世界的规范性的因素。
“和”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理想。就像一种文化中的任何一个重要概念一样,它既作为日常用语挂在人们嘴边,又作为重要的术语进入哲学与宗教的思考之中。在人际的、日常生活的层次,“和”表示共存,共处,和是一种共在关系,而不是相互征服、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关系;也是和睦,即相安无事的关系。在中文中,和是最美好的词语之一。“和平”表示共同体之间的理想关系,积极的方面,是和睦、友善,否定的方面,也是共存、相安无事。“平和”是道德与个性方面的,指内心不冲突。“和气”、“和蔼可亲”,讲一个人对别人的态度,他纵然有不同的见解,纵然地位高,纵然从内心认为自己高明,但也表现出对别人的心平气和态度。“温和”是人文型自由主义者最欣赏的政治态度或姿势,用在日常生活上,往往指一个人和气,有较好的道德修养;用在政治生活上,指面对激烈的争吵或冲突时的自我克制。在中文中,表示“和”的含义的词还有很多。当然,这些词是现代汉语,有许多已经包含了外来语的含义。不过正是存在于现代汉语中的这些词汇,不仅对日常的生活理想有较强的指示,而且显示出把别的文化中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别的文化中对世界的经验方式融进自己的经验的努力。在宗教的与哲学的层次,“和”发展出这样一种观念: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参加宇宙的创造过程,进而把自己消融到这个过程之中。政治上的和的概念,与宗教与形而上学的观念不同,它应该从日常生活重新开始。
英文的Reconciliation,来自拉丁文。法文也有这个词。它的第一个意思是和解、和好,使争论的双方或多方,使处于分裂敌对与争吵状态中的社会,再处于和好的状态(to reestablish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它的第二意思是调停、调和,调解(to settle or resolve)。这往往涉及第三种力量或第三方,或者涉及只有旁观者才有的健全理智。与中文的意思相近, reconcile也指和谐、顺从与一致(to make compatible or consistent)。
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希腊哲学家就认为宇宙有种力量,一个是爱,一个是恨;苏格拉底对和解问题作出过思考。两个争吵、失和的兄弟要重归于好,按照苏格拉底的建议,应该化解敌意,表达善意。在苏格拉底看来,物质利益或财富是靠不住的,因此善意就显得更为重要:与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睦相比,也许利益的得失本来就是次要的,容易调节的。所以苏格拉底劝哈赖克拉泰斯努力和自己的哥哥和解,“对于一个体面的贤者,说服他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善意相待。”⑤ 这与利益冲突的大小决定善意的大小的现代看法是不同的。
西方古代的政治生活体现着和解的精神。在希腊,立法者的重要任务,就是对社会矛盾进行调和,发明更具包容性的制度,保障或体现各方的利益。也因为这种调和、调停精神,聘请中立而贤明的立法者(往往来自外邦)为本邦立法,成为希腊人的通常做法。古希腊的梭伦改革最为著名。梭伦虽然是雅典人,但改革以后,他就离开雅典,进行十年的游历活动。西塞罗对源自柏拉图的共和观念作出了重要诠释:他认为国家,或共和国,不是某一阶级的独占性的暴力工具,更不是某一阶级压迫其他阶级的机关,而是commonwealth,希腊文意义上的公共的财产,实现的是公共的利益,体现人的共同的福利⑥。罗马制度早期共和制度的发展,也的确体现了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把不同阶层纳入政治框架的过程。
和解的政治是对和平的、理性的、说理的也是平等的政治秩序的根本承诺
和解的政治的一条根本原则是:任何一种要求、建议,对共同体的公共生活的重组方案,或任何一种政治运动,价值主张,诉求,不管多么合理,都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提出;对于任何一种以理性的、和平的方式提出的主张,任何一种诉诸人的理性、以扩展人类的生活范围与经验眼界的运动,无论它看起来多么不合理甚至大逆不道,都应该受到和平的对待。同样,任何一种以和平的、说理的、扩展人类的善的领域与经验领域的运动,也是无所畏惧的。这是政治运动的根本原则,是对和平秩序的根本承诺,也是对平等秩序的根本承诺。
和解的政治拒绝清算的政治[7]。根据和解的政治观,政治是一个世俗的、向前看的、解决现实问题但留有余地的技术或过程。过去的错误或恶行的意义在于,可能缺少一种机制对本应避免的错误进行避免;可能人们对某一个目标看得太重,以至牺牲了其他重要的,特别是相反的目标,结果,社会处于失衡失态;可能,更一般而言,至善观或对人类基本问题的“最终解决”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陷阱。
当然,有时历史仿佛出现了死结。如果不清算,社会便无法回复到和解的状态,甚至无法再确立方向。明显做了恶行的人应该付出代价,而原来处于受迫害状态的人应该受到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补偿。否则,使人感到世间没有了正义。但是,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这种再平衡,这种对反常状态的纠正、“反平衡”,也就是过去受苦的人现在成为施于痛苦的人,无论是谁在受苦,其实都是共同体为自己的错误付出的代价。
在清算的时候,仍然可以区分,什么是一般政策的恶果,什么共同体的强大的政策取向所产生的恶果,什么又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一般来说,裹夹在强制性政策中的恶行,在这种政策被全盘否定的时候所受到的处罚,要轻于或理应轻于完全由个人选择产生的恶行。举例而言,由红卫兵执行政策时的抢劫,在文革以后被处罚,理应轻于单纯的抢劫。这是因为共同体用其宽大与厚实的肩膀,承担了他们的部分过错。而这种较轻的惩罚之所以较轻,也并不是因为罪恶本身较轻,而是因为犯罪者仍然处于一个共同体中,大家仍然要“一起共事”。
因此,(1)一般而言,和解的政治观拒绝清算的政治观;
(2)从实践上看,清算应仅以共同体的再定向以及共同体的和解与团结为目标;
(3)从理论上分析,清算的代价仍然是前一单元的代价的继续。
和解的政治必然要求在理论上突出共同体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给予共同体以优先性。
和解的政治不承认政治犯罪与良心犯罪。政治犯罪在当代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种情况加大了和解的迫切性。一方面,政治的犯罪比任何一种刑事的、局限于个体的犯罪所造成的灾难都更大。这甚至是现代社会的特殊现象。因为,只有在现代社会,政治才成为一种由观念推动的运动,而也只有在现代社会,因为绝对主导性的价值观念的消失,利益与表达的唤起,各种各样改造社会或提升人类的观念纷纷出现,它们的持有人因为对它们的承诺,迫不急待地要把它们变成政策,付诸实施。因此,现代社会是一个的高度风险的社会。自由主义越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这种风险越大,因为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框架中,国家已经对于政治观念严守中立,它严格说来只在于确定一种最一般的秩序。因此,在现代社会,呼吁动用社会或群体的思想的(鼓动、说服与怂恿)资源与物质资源来进行对社会的无所顾忌的重组,这样一种政治的犯罪,也是所有犯罪中最严重的一种犯罪,成了具有特征性的现象。为什么是最严厉的犯罪呢?因为在这种犯罪中,在这种观念先行的、所谓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中,生命、财产、名誉会毁灭于一旦。另一方面,这显然也是现代社会的现象,犯罪者不仅不认为这是一种犯罪,反而认为这是对人类做出的最大的善事。最简单的例子是恐怖袭击与宗教极端主义。这与从古到今在战场上同归于尽是完全不同的。只有在现代,同归于尽式的暴力才成为一种高度理性化的、深思熟虑的行为。这无疑大大地增强了现代社会的风险性。
因而,在政治犯罪,即通过掀起政治运动而造成严重的集体暴行的问题上,显示出现代社会的最严重的分裂状态。这种源于观念或世界观的分裂,这种源于本质上什么样的社会是最可欲、达成这种社会最合适的条件的观念的冲突,的确,要比单纯的物质利益(即所谓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冲突造成的分裂,严厉多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分裂,只能通过高一级的和解来弥合。而且,这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或以民族国家为一个单元的政治共同体是否“现代”的标尺之一。这种更高一级的和解是:没有政治犯罪,在由于推进政治运动产生的暴行的问题上,只能这样来处理:任何一种政治主张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罪恶,任何一种政治运动,在它因为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而受到规范之前,首先有存在的权利。政治运动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罪恶。但是,推进政治运动的个人,必须对由此而产生的现实的暴行承担最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或刑事的责任,也就是说,他的危害仅以他对具体的个人的损害程度来衡量。这就是政治运动的合法化与权利化。缓和政治运动对社会的冲击,将政治运动的暴力尽可能减小的方法,并不是取消政治运动,灌输与这些运动相反的“政治真理”;而是一方面使它们合法化,另一方面呼吁它们与它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各退一步,都承认最低的秩序。
这是和解的政治对人类本性的双重承诺:对经验的,永远处于开放性的生活境界的承诺,也是对人类生存本身的承诺。这也是人类追求现代性的成就:生活可能性的开拓总伴随着风险。
注释:
① 孔子的名言是“为政以德”,意思是统治者以“文明的”手段实现“德政”或“教化”。
② 〔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1章,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③ 参见应克复、金太军、胡传胜:《西方民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308页。
④ 〔英〕鲍曼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见他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同样的讨论,也见〔德〕乌德利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⑤ 参见〔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卷第3章。
⑥ Cicero,de republica,i,24—26.
⑦ 参见〔英〕安德鲁·瑞格比:《和平、暴力与正义:和平研究的核心概念》,载〔南京〕《学海》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