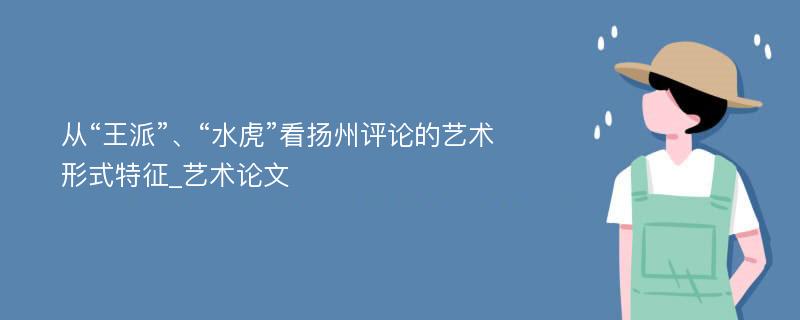
从“王派《水浒》”看扬州评话的艺术形态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话论文,扬州论文,水浒论文,形态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少堂承前启后说《水浒》,以毕生精力完善了评话艺术形态,成为我们认识扬州评话艺术规律的范本。扬州评话的艺术形态是由“全面表白”的口头文学叙事、书场音韵效果和说书人书台表演的形象塑造互动构成。认识这三大要素的互动整合是全面评价评话艺术的必由之路。研究王少堂说书艺术不能单凭书面整理本为据。以为“武、宋、石、卢”四个十回的整理本即王少堂说书艺术是一种错觉,书词录音也无法再现书台表演。老舍读完《武松》整理本慨叹:“可惜,没有少堂老人的眼神手势的配合,未免减色。”[1] 自古即体现了书词、音韵和书台造型互动特点的评话,由王少堂说《水浒》而发展到极致。
“王派《水浒》”是扬州评话中重视文学内容的口头艺术。这种文学,即使撇开所有的声音、造型,也不同于一般的书面文学。它是口头的,由表白产生。它遵循的美学原则是王少堂所说的“全面的表白”。老舍管这种手法叫“细巨不遗,搏兔亦用全力”[2]。王少堂常在书词中讲“我要各方面交代”。这种叙述方法与古典小说的详略虚实原则相左,更与现代小说讲究节制、力避枝冗的原则格格不入。扬州评话整理成书面读本,已或多或少地渗透了小说原则,对有声文本作了删削。这里对“全面表白”在书台上的主要呈现方式列举其要。
其一,诗、词、赋赞。作为口头的文学,这些文体不可少。书台上人物出场往往有赞词。北方评书的“赞儿”,若说两军交战,主将而外,即使出来八个偏将,也必得有八色不同赞词。书台效果强调“如在目前”,人物出场的赞词就相当于生活中人们初会的印象,而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可能通篇只见精神情绪,不言五官面目。评话也极少用散文叙述自然风景,武十回没有,宋十回只有“误入清风山”、薛永打探龙亭剑两节。书台上若用散文述景,听众会不耐烦。说书人必须以韵文诵景,才能抓住观众的神。诗、词、赋的形式则不可少。除了述景的功用外,这些文体还可以作为书情起落的标志、重要关头的强调。听众久听一种语调难免心理疲劳,一段或长或短的韵文演诵能起到恰到好处的提神作用。哪怕不懂词儿,光是音调的铿锵变化也能引起听众的兴趣。一旦成了书面记录,这种过分书面化的文体就会与口述语言构成风格矛盾,这样的文体就成了累赘。于是,整理本《武松》、《宋江》中的诗、词、赋赞几乎删除殆尽。
其二,人各有书。书台呈现要求“如见其人”,每一个上场人物都有动作。否则为说书家所忌,如评话艺人所鄙的“荒胚”、“幕表”、“捣鬼书”,人物仅存其名姓而无所事事。《武松·夜杀都监府》一节,厨房中有厨头、王二麻子、二癞子。厨头切火腿的刀功,与京油子对话;王二麻子炸鱼饼;二癞子烧火与王二麻子起矛盾。整理本中按长篇小说章法讲详略、繁简,这些人仅仅为了成武松刀下鬼而存在,其余无书。这种虚挨一刀的人物,搬上书台,有不如无。书台上的详略是书多书少,不能没有动作。
其三,同文再现。演述一件事的发生实况,后来再由某一人物重述一遍。有声文本毕竟不是书面文本,书台上只存在“异声再说”,不存在同文再现。书台上有它存在的必然:一、从知与不知的关系说。书台上的虚拟场面,一个人物把另一人物不在场时发生的事情说给他听是必要的。说书人全知,听书人已经预知,而书中某一人物不知,就有必要重说。乔郓哥作人命见证,向阳谷县衙重述命案始末。一无所知的老爷,必须知道前情。二、从悬念的延宕说。卖狗肉的赵大向施恩报信,说武松吃冤盗官司,故意把他与王小六的对话重复。心急如焚的施恩越着急,听众越是从中体味到戏剧性。如果赵大与施恩见面就摊底,则毫无趣味。
其四,知识介绍。曲艺形式,评话、大鼓、相声等常常担负知识介绍的任务。评话主要面向市民听众传播知识,正是说书人被称为“先生”的原因之一。知识介绍多被用作“热”书中的“冷”穿插,延宕或放松紧张气氛。《血溅鸳鸯楼》中插入戒指考证,杨贵妃“三美”介绍正属此类。从书面文学要求来看,只能算作横生枝节的芜杂成分。
其五,听书论场。金圣叹批《水浒》“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说书人受其启发讲究“字字好,句句好,段段好”[3]。艺人上台说一场书,要考虑今天的内容,哪里是重头戏,哪儿好穿插,如效果甚佳,就逐渐成为定型。段段好,却不一定十段放在一起都好。因为整理成书面文本的长篇大部比起书场内听书,接受的时间规定性发生了很大变化。每日听一段穿插,妙不可言,一气读十段穿插,乱叶遮花,反而有碍观瞻。
其六,叙述人现身。王筱堂在《艺海苦航录》中说,王少堂向后辈解释“全面的表白”时,强调“话要找尽,意要说透”,如何做到“尽”与“透”?书中往往由叙述人直接现身说法。现代小说讲究作者退出作品,评话总是说书人处处介入。因为评话是书台上下的交流关系,一些说书人“与听众接感情”的话在书场是必要的,在书面文学中又成了赘余之物。王少堂辈教听众不能如武松“好动不平之气”,历来受欢迎;但《创业史》中柳青以作者的声音直接介入,成为人们集中的疵议。
“全面的表白”真是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处处往细腻处讲,这正是“王派《水浒》”乃至扬州评话“说表细腻”的特征。
艺术形态学认为“口述本身是语言审美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书面语言距离原所标志的精神内容比有声语言要远得多。比起书面文学中的语言来,口头文学中的语言所具有的情感信息要无可比拟的多。”[4] 因为,音响能使语言形象不借中介地,有语调地体现和传达人的感情、体验和情绪,就像音乐所做的那样。没有进过书场的人,听广播录音能比整理文本更进一步了解扬州评话。上世纪30年代上海直播《武松》,[5]60年代初、动乱年代后,《武松》的录音打动了大江南北的几代人。广播形式拓展了书场空间,山陬僻乡与繁华闹市得以同时欣赏聆听,雅俗阶层能够共同咀嚼品评王少堂的说书艺术,而口头语言的声调、节奏与情韵才是广播书场生命力的基本保证。
1958年全国曲艺会演中,老舍观摩王少堂演出后说:“他的动作好像有锣鼓点控制着,口到手到神到。”[1] 这种与口一致的动作节奏也就是叙述的音乐节奏。王少堂也说父亲教他念词赋“强调有板眼,好听”。“板眼”当然是更明确地指节奏。把握节奏的原理,“说书要有阴阳高下,说起来自然就好听;有了紧、慢、起、落,说起来才有波浪。要快而不乱,慢而不断”[6] 304。
说书无论表、演都意在吸引观(听)众,抓住注意力,扬州人俗称“拿魂”。说书体现音乐性的基本功,行话叫“拿字”。其要求是咬得准,吐得清,送得足。咬得准,是分清唇、喉、舌、颚、齿的发音部位;吐得清,则要求在连绵说表中字字清楚,不至于出现“吃字”(疏漏某字的发音)的弊病;送得足,便是把关键性的字加以强调、重读,运用丹田之气或“脑后音”使得每一个字发音的声波震动频幅加大,加强对观众听觉器官的影响。要了解说书人声音情感节奏的互动呈现,且看《武松》中英雄入景阳镇一节:
走了五六家店面,只看见右边有一家五间簇崭新草房,檐下插一根簇崭新青竹竿,青竹竿上挂了一方簇崭新蓝布酒旗,蓝布酒旗上贴一方簇崭新梅红纸,梅红纸上写了五个大字:“三碗不过冈”。再朝店里一望,只见簇崭新锅灶,簇崭新案板,簇崭新桌凳,簇崭新柜台,簇崭新的人!——啊!旁的东西有新的,人哪里有新的?有!
内容注目日常中的英雄,叙述却不应流于平常,这就必须在语音语调上呈现波澜变化。说书人从武松边走边看并不经意的动作特征出发,缓诵第一个分句,由突然有所发现开始重读“只看见”,这是“起”。由第一个“簇崭新”重读,以下音调加紧,节奏变快。第二个“簇崭新”仍重读,但较前略低,而突出后面被修饰的中心词,接着“顶真”的名词则轻读,着重点放在新出现在人物眼前的事物上,连续出现三桩新物件,三次重复指称,音调由紧转“急”,而四个加着重号的修饰形容词“簇崭新”在急中显“促”。至此,叙述者再从中略显变化,放慢节奏,一字一顿地念出“三——碗——不——过——冈”,再“一望”,略略停顿,留下观察时间,也便于说书人换气。然后,由这一略慢的跌宕转到一段“快口”的高潮,运用一串排比句,“急促”转“繁密”,修饰词“簇崭新”每隔二字出现一次,五个偏正结构间不容顿,直至“人”字,戛然而止,为这一节书的“落”。若说“板眼”,这一节中九次出现的“簇崭新”一词便是鲜明的旋律特征与节奏标志。最末修饰语与中心词之间惟一出现了“的”字,便是收束的提示。
这一段表述人物眼中的环境。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每每让人不能忍受。听众对《武松》中的环境叙述,非但不感到腻烦,欣赏它还犹如美妙的音乐。每年新正,“簇崭新”的书词开端与听众新年新气象的情绪感受相沟通。可是书台上声音的接受优势被整理成书面文字时,则难以引起注意。以新文学的观点看,这样的文字近乎琐碎,必经艺术家台上演诵,方显其一字不易。
书台音乐效果,还通过非语言音响来传达。说书人开口之时的醒木声是,手、足敲击声是。此外,艺人还用辞典上找不到的地方性的拟声词来烘托、渲染气氛。王少堂口中的马、鼓、炮(其他艺术家的不同书目中也存在)声,无论是马由远而近,从近到远,逡巡往复,还是鼓点由缓至疾,轻重舒徐,都没有办法以书面语言表达。人物在特殊语境中哭、笑、躁的表现各个不同,但一成记录文字则千人一腔。
语音传播尽管比书面传播有了更浓郁的感染力,但没有与书词、声音并存的副语言特征,艺术家的表情、手势、眼神无法传达到听众面前,书场中书台上下的情感交流仍不能完全实现,书台上的空间造型被声音屏蔽,立体的人物形象终难直观显现。书面整理的话本与书台艺术隔着两层,广播书场也与书台艺术隔着一层,电视书场有说书人表演的视像,但仍然不能实现书场中的交流。“说书方面就是要有说工,要有做工”[6] 298。听广播,我们能够欣赏艺术家的“说工”,但是还缺少“做工”,在言表之外没有意表、神托,对人物的容貌、身形、动作,没有逼真的实物再现感。所以,仅凭录音也难作为研究“王派《水浒》”的全部依据。
说书是台上艺术,书台才是评话艺术生命的全部呈现。书台很简单,就像京、昆戏曲,倘无角色踏着锣鼓经登场,观众会对舞台视若无睹,同此一理,是说书人赋予书台以生命。小小的书台:一张半桌,一块桌围,一张木椅,一把茶壶,一只茶杯,一块止语,夏日多一把折扇,冬寒换一方手绢,醒木一拍就开口说书。醒木的响声是书词的开端,也是书台呈现生命的起始。伴随着书词,说书人王少堂的目光、手势可以将一个简单狭小的书台空间顷刻间变作无垠宇宙,它的空间地点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是:十字坡、二龙山的好汉出没,东京、大名府的热闹繁华,阳谷县街头武松跨马游街,江州、大名府法场宋江、卢俊义跪待毙命,九江府、阳谷县端坐大堂,潘金莲、阎惜娇深处内室,祝家庄兵马厮杀沙场,浔阳楼、快活林酒店或者紫石街茶坊。说书人总能把听众带入斯时斯境。这种极度的空间自由,是王少堂同时的戏剧艺术所不具备的。王少堂手执一扇,可以是武松、石秀的刀,也可以是卢俊义的枪,也可略略打开作蔡太师给蔡九知府的密信。戏曲演员按程式作整个舞台的活动,王少堂一般身不起座,只是以手膀代脚腿地表演,一切动作几乎都在端坐的书台上以手势配合说表完成。评话艺人在表演动作上较戏曲有更大限制,但表演的内容却有着无可比拟的自由。除了这种空间与行为的自由外,书台上的自由更体现在角色的更替上。书台上的表演,是不化装的独角戏。它不同于戏曲,生、旦、净、末、丑界线鲜明、各司其职。说书人可以不分角色区别,一人兼演各种角色,而又能做到“演到哪一个就像哪一个”[6] 297。王少堂自述《武松杀嫂》一段书中多重角色的变易与表演追求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自由扮演各种角色的过程中,追求让听(观)众对书中人物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受。并且,在表述的特定时间地点上人物之间的关系中完整地呈现诸如“杀嫂”、“醉打蒋门神”等场面。
书台上的表演(艺人称“演”)与叙述(称“表”)之间的关系,无分轻重主次。论表演与叙述互动,“王派《水浒》”在整个扬州评话中又恰好不趋极端处于中庸地位。以说《西游记》为长的戴善章,重说表,表演重面部表情、眼神,他偶尔动动右手,左手搭在茶壶上,好久也不动一下,天热,手背窝儿里能积下汗水来,同行戏称他搭的南货店老板的架子。他仅是脸这边掉掉,那边望望,右边指指,便能抓住观众。相反的例子是康国华重表演,“他演鲁肃、孔明两个人的声音笑容,传神会意……,他的手势上,演出这个下棋的动作,就等于这个桌上有个棋盘棋子”[6] 293。康国华的演能传神,虚神足,他的神意下面没有全面的表白、书说得不透彻。王少堂不像戴善章那样温文,也不像康国华、刘春山、朱德春那样火爆,他既重叙述,又重表演。
这种书台叙述与表演的完美结合,其实现途径是严格遵守书台艺术规程。书台上的评话,讲究说、做、念、打。书台艺术家们讲究程式,又明确意识到“书戏不同”的本门艺术特征。书台区别于舞台的特质是以说为本。书台上的说分“官白”与“私白”,演的是人物语言和心理。书台上的“念”,除了相似于戏曲的人物对白与独白外,还另有任务,就是完成、托现说书先生自身创作、叙述者的形象,最突出的方式便是各种诗、词、赋、赞的朗诵。书台上的“做”是“说”以外的最基本的功夫,于程式上不及戏曲讲究,但也有基本固定的形体、手势特征,其目的便是让观(听)众能够意会,把声音不能表达的书境传达给接受者,强化书词,突出人物。书台上的“打”,不能够与“做”有鲜明的界限,但它所表现的内容毕竟是独特的,不同于一般的人物行为动作。“王派《水浒》”的武打部分,基本上是短打书,有别于以演刀马长靠(同戏曲术语)为主的“三国”、“西汉”。短打特别注重人物的手、脚、身段、架势起落。而书台短打有别于舞台上的特征又在于,它不要求一气呵成地将格斗过程演完,有点像今天电影中的定格和慢镜头,将武打动作的一招一式进行解析。“何仙姑懒睡牙床”,是如何以静制动,败中取胜,假相欺敌;(《武松》)“红孩拜佛”,怎样双手合十,变做肩桩撞人。(《卢俊义》)台上的说书先生几乎都不会武功,他们无法以真功夫现身,但他们却能解得功夫说法。总之,书台上的说、做、念、打诸艺术因素,有着本身独立存在的艺术价值,必须从理性上揭示与肯定书台的独立存在,否则很难完整地认识“王派《水浒》”乃至整个扬州评话所呈现的形态特征。
王少堂与前贤后继在艺术实践和教学中,十分强调叙述与表演的诸种艺术因素的全面体现。而语言的节奏感和动作传神到位的分寸感以及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则是他们强调得最多的练艺要求。王少堂常说:“评话表演时,最主要的是五个字,少不了口、手、身、步、神。”[6] 301神是以目光来与书台下的观众进行交流,所凭借的媒介是无形的,是一种非叙述性的意会,能统摄辅助叙述与表演的口、手、身、步动作,与其共在,却无法与之分解开来进行单一剖析。艺人言“神”,常冠以“虚”,理由大部分即在此。眼神是物质材料以上的存在。“口”,便是有声的叙述了。撇开文字的符号意义外,它的物理形式便是声音。声波的组合构成音乐性的变化,正是评话艺术重要的形态特征之一。“手、身、步”三者都是以形体动作来辅助口头叙述,是“副语言特征”。它们构成书台造型,在观众面前直观呈现,让观众“如见其人”。王少堂说:“手、口、眼三者是连带的关系……,身步也是。”[6] 301眼神的意会性、声音的音乐性、形体的造型性,三者综合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与表白一起形成评话书台的完整形态。用一个典型例证说明,武松在景阳镇酒店吃酒,酒醉之后会账,取一两五钱有零的银子付与小老板,下面是小老板的动作与念白:
小老板伸手把账桌上一把戥子拿了过来,银子朝戥盘里一摆,右手两个指头拈住戥毫,左手就把戥花一理,一字平。银子称过了,低头望望银子,抬头望望武松的脸色:“爷驾!你老人家这个银子,是个一两——还欠一分呐……!”
王少堂演述场面上小老板/武松之间的欺诈/不知觉关系。小老板欺武松醉而不觉,可以避免冲突。书台场面的构成方式独特,其效果不同于舞台。演小老板时,说书人取直接与观(听)众对话的方式,仿佛武松置身于书台下的人群之中,书台上下的间隔几乎不存在,书场多大,书台上叙述者虚拟的场面就有多大。演述者进入对话中的任何一个角色,就把另外的角色交给观(听)众,而观(听)众虽不能演,起码也有个心理自居的作用。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鉴赏者,又是临时被虚拟的角色。此情此景,武松醉而观众醒,观众不是武松,但心理上与武松认同,他们仿佛置身其境,小老板欺诈武松便仿佛是欺台下观众。演述者的神色、音调、动作造型综合构成一个逼真的欺诈过程。观(听)众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欺诈,他们要从演述者的表演诸方面去领略这个欺诈,由心理上与之构成冲突,从意识上识破这个欺诈。
王少堂以一串动作、一副神色、一句台词,演小老板的欺诈过程与心理。他伸右手将戥盘取过,左手赶着戥花,右手提戥毫以示称银子的动作过程。书台上并无实物,说书人的表演是个象征,动作造型上十分讲究,动作中的拟实性有如在目前的效果。演述者右手食指搭在中指上,略微拱出,以示提戥盘的向上的方向与分量,左手赶戥花,作水平方向的移动,照应着“一字平”的表白。左手移动之初,与右手紧靠,指头的摆法与右手一式,只是中指不作拱势。左右手的指式构成一种富有对称美的构图,但在对称中更要注重变化,除中指的拱势外,左手在往左方移动前即须比右手低出一至二指的空间距离,以示戥毫比戥花秤杆高。在左手平移的过程中,演述者以神色配合,目光必须与手一致朝左移,目光的着落点即在左手指尖处,由此指示出银子的分量。左手动作与目光同时终止,应和着口头表白:“银子称过了”。
然后,是眼神的运用,在这个运用过程中托现小老板贪财与起欺诈之意的心理活动。秤杆上戥花既已明白标志着银子的重量,上述的眼光与表白便已交代小老板一目了然。他可以一口报出银子的分量,为何又要低头望望银子呢?这便是贪心的起始。演述者表演低头,不是无意一瞥,而是由左边向右下方作一以头部配合目光的动作,交代戥盘所在位置,并于表白“望望银子”时,放慢口头节奏,在望中表示出银子的吸引力,为下面一个眼神动作(居心昧财)作出铺垫。下面的眼神动作与念白,在记录上是上下文,但在表演上却是同时进行。念出“爷驾!你……”三个字,正是动作“抬头”之时,而下一个“望望”与前一“望望”又有眼神动作的区别。上一个“望望”,是目不转睛地盯视银子,下一个“望望”,在目不转睛地望“武松颜色”之前,先有一个回顾动作,头不动,目光疾落疾起,从武松身上回看银子,再疾回到武松脸上。这表现着银子的吸引力之强,他的昧财主意已定,又怕武松察觉,必须细察对面酒客的意态。这一回顾之间,口头念出“……老人家这个银子,是个……”。此后,便是一直盯住武松的脸,眼神不动,内心急剧盘算:如何实施昧银子的主意,会不会引起争执,终于决定昧财。
以下的念白,便是这一心理戏剧冲突的绝好表现。演述者必须借声音的节奏变化来体现人物内心活动的节奏。上面小老板的念白“是个”音轻而快,到“一两”便要念得重而响,但又不能戛然而止,因为念到这个地方,戏剧冲突仍是悬而未决。于是,演述者便利用这个词的后鼻韵作拖腔,以表现小老板内心决断的最后关头。报出“一两”这个数目的小老板此刻正一瞬不动地看清了武松的醉态。于是,他便大胆地实施其欺诈计划了。银子是一两五钱有零,清醒的听众早已知道。而对小老板装模作样,神情蹊跷的表演,观众必生疑惑。于是,他们便产生双重的心理期待。他们两难地发现,既期望小老板实报银数,又因其动作暗示而等待着骗局的出现。从现实生活利益,从武松立场的认同出发,他们恨小老板故弄玄虚;从纯粹戏剧审美出发,他们又盼望其欺骗的冲突爆发。此刻,小老板的念白中出现了戏剧性转折,在“一两……”的拖腔之后,他竟然报出了“还欠一分呐”的假数目来。这一动作呈现过程依赖于音调节奏的变化,拖腔标志矛盾悬而未决,到“欠一分”的突变之间,王少堂又加入一个衬字“还”,这一低缓的衬字把拖腔变作平调陈述,使意义的转折来得自然和谐。这一不着意的“还”字,起到关键性的掩饰作用,帮助小老板面无愧色地报出虚假数目。王少堂的表演并未到此结束,他在“欠一分”后面又有一个意味无穷的感叹词“呐”,这一个字的吐出,略带尾韵,既将后三字“欠一分”与前两字“一两”构成音调上的匀称、均衡,又把小老板的恬不知耻与自鸣得意的神态全盘托出。
由上述分析,我们得到了评话表演技巧的综合运用的鲜明印象,对其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听(观)众对这一戏剧性表演的领略,见出演述者口、手、眼密切配合,始终不脱离形体造型,导引观众意会的眼神,音乐性的叙述语调,确是“周身的书,满脸的书”。这一过程远不如“打虎”的动作性强,但是由此细微的动作管中窥豹,我们更可以见出整个扬州评话的艺术形态特征之一斑。
王少堂的表演手、口、眼相连,身步相连,构成造型,其效果在于呈示性。不同造型的连贯呈示,正是把人物与自然的面貌再现在观众面前。艺术家除注意造型动作的幅度外,更注重质感。他们要通过形体动作的造型演出个别的架势,来显示人物的精神、气质。动作造型的轻俏、柔美、凝重、端肃、粗犷、细腻无不形容毕肖于人物身份、个性与精神气质。这正是书台艺术家的魅力所在,也是各个艺术家功力不同的显示。王少堂“活武松”的美誉即是来源于此。
注释:
①表是叙述;演即是通常所说的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