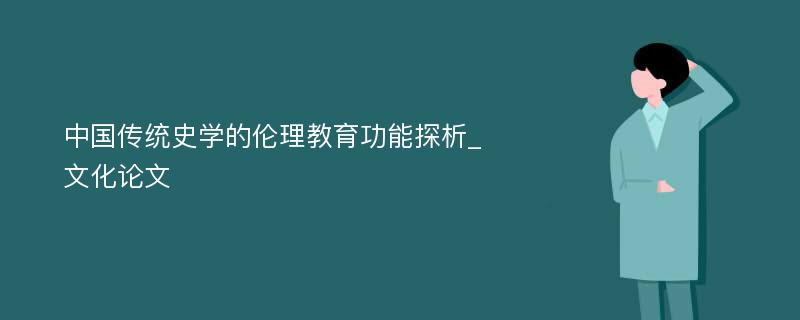
中国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试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传统论文,伦理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大抵涵摄了两个层面,即政治上的取鉴资治和伦理上的道德教训。文章集中对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进行了剖析,从文化学的角度审视了这种功能赖以存在的民族文化背景、历代君臣对史学教化功能的认识以及传统史学实现其道德垂训和收化功能的途径。作者指出,尽管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被神化,但它并未形成一种在道德上制约极权者的威摄力或约束力,而在向人民灌输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上,在强化君主专制制度上,在模铸中国人的奴性人格上却起到了行之有效的作用。
从文化功能的维度审视,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大抵涵摄了两个层面:一是政治上的取鉴资治,即古代史家所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二是伦理上的道德教训,通过对古人古事的褒贬惩劝,垂训将来,以有俾于教化。虽然在我们后人看来,传统史学在实际生活中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上述两大功能这一点似乎颇值怀疑,但至少从理论上说,传统中国的知识界精英们对于历史学的资治、垂训之功能,还是坚信不疑的。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考察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试图从文化学的角度审视一下这种功能赖以存在的民族文化背景、历代君臣对史学教化功能的认识以及传统史学实现其道德垂训和教化功能的途径,并在此基础上试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教化功能作一初步的评估。
1
在传统中国,历史学主要是作为王朝政治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门学术存在的。历代专制统治阶级都把历史学视为评断和审判前朝政治和过往人物、事件的法庭,如刘知己所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①;如荀悦所说:“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彰,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②。历史家们显然希望,通过他们的编史活动对历史上的圣君乱主、贤辅佞臣等各式人等的道德审判和定性,垂训将来,警示世人,以达到惩恶扬善、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目的。
古代历史家的上述价值取向,自有其赖以存在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的背景。应当说,重视名望声誉的习尚,是文明时代人类的通性。但如中国古人那般重视史书,看重生前身后名,却属世所罕见。在传统社会,帝王将相和知识界精英阶层对于青史留名的追求,其醉心、执着的热烈程度,完全可以比肩西方基督徒对千年福王国的无限向往。
在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看来,“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之朽。”③立德、建功、立言,死后流芳千古,名扬后代,是古人一生中梦寐系之、孜孜以求的不朽之业。历史家刘知己说得很清楚:“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历史)而已。”④对于中国人来说,生不能立德、建功、立言,死无以传名后世,就等于白过了一生,那是要抱恨终生,死也难以瞑目的。孔夫子一生周游列国,栖栖迟迟,晚年眼见其道不行,曾经喟然长叹:“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人物的孔夫子说的这席话,无疑道出了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人生取向。
史书在传统社会,是记载前代和当代人的伟业功绩并使之传输给后人、传之永久的主要信息通道,“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于莽卓,夷惠之于跖踽,高昌之与曾闵。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⑥因此,历代精英阶层对于生前身后名的热烈向往,就自然地外化为对“史书之一行”(争得史书中一行的记载)的追求,用宋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的话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册)。”⑦
正因史书记载中对一个人的褒贬,直接关系到其人留传给后世的名声之好坏,这样,历史以及记载历史的史官对于以生前身后名誉为取向的中国古人,也就具有了一种神秘莫名的神圣感和威慑力。唐朝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⑧中国传统社会的历代专制统治者,正是抓住了精英阶层的这种文化心态,有意识地利用和控制史学,并不断地加以神化之,把历史视为儒教伦理的道德裁判所,从精神上愚昧人民、制裁异端,以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
历史学被赋予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其历史几乎与传统史学一样渊源久长。早在中国传统史学萌生之初,古代王朝统治者就有意识地运用历史以辅助礼乐教化。历史著作既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使人弘扬善行,抑制邪恶之念,又可以警戒世人,培养光明的德行,处世行事消除昏乱暖昧之行。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古代王朝统治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史官制度。在当时,史官职责颇为神圣,他们继承国王的旨意,依据“周礼”原则记功司过,道名分,明礼义,辨是非,别善恶,名官撰录的著作,名之曰《春秋》。经孔子编订而留传至今的鲁国《春秋》,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著作。在《春秋》中,身处诸侯力征、礼崩乐坏、动荡离乱、战争频仍之世的鲁国史官,根据“周礼”审判一代君臣政事,一方面用以正名分、辨是非,在历史中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宗法封建等级制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历史的编纂,警示后人,惩恶扬善。
从文献记载看,《春秋》式的历史著作,在当时确已具有某种惩戒世人的特殊神秘功能。《左传·襄公二十年》:“卫宁惠子疾,如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宁惠子)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宁惠子因自己驱遂卫国君主的事载录于诸侯各国的史书之中而感到忧虑、恐惧和害怕,病重之时还念念不忘,请人帮助删掉史书中的有关记载。这一事实表明,史书在当时具有惩劝功能是确确实实的。但由此而认定历史在春秋时即已成为礼教的道德裁判所,却似乎为时过早。
史学得以成为庄严、神圣而具有神秘威慑力的道德法庭,是儒教徒不断加码的吹嘘神化和历代专制皇朝的钦定弘扬的结果。从历史看,史书教化功能的神秘化,是从战国时儒学代表人物孟柯开始的。这个被后儒尊为儒教“亚圣”的孟夫子,鼓吹恢复西周礼制,实行“井田”,以根治战国时期列强争霸,道德沦丧,礼制荡然分解的混乱局面。为推行其不合时宜的社会理想模式,孟柯有意神化历史,他说,春秋时,“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⑨孟子还吹捧孔子编订《春秋》,其功劳堪与大禹治水,周公定天下相媲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把《春秋》的著作权归到儒教圣人孔子名下,并吹嘘《春秋》之类史书行世以后,使乱臣贼子深感畏惧,这就开了神化历史学道德教化功能之端绪。
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经秦汉以后懦生尤其是《春秋》公羊家的大肆鼓吹张扬而神乎其神。公羊家认为,《春秋》是孔子“拨乱世、反之正”,申明“礼义”的杰作,是书评判春秋时代242年之中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⑩至此,历史学也就俨然成为神圣庄严的道德法庭了。
春秋公羊家把历史学神化成为伦理道德的审判台的那一套理论和操作程序,随着公羊学说被西汉皇朝钦定为学术正统而爬上并高居于史坛独尊的统治地位。此后,春秋史官以及秦汉公间家据礼义司功过、正名分辨是非的那套历史操作程序——所谓“春秋书法”,经懦教徒一代代阐释、重构和完善,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史学操作中具有规范化的模式。传统史学,终因两汉以后历代专制统治者和儒教徒的不断吹捧、渲染和神化,俨然成为专制皇朝的正统思想——儒教伦理的道德裁判所,在这里,奉极权帝皇之御旨而行法的执法官——历史家,兼而制控着历史上的死人和现实中的活人,他们严密监视和审视着芸芸众生,随时可以审判那些触犯儒教教规之徒,褒扬那些恪守儒教伦理的明君圣主、忠臣义士。
2
从历史上看,早在夏、商周时期,王朝统治者已设置有一套完善的史官制度,这套制度除了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段(例如两汉)曾经出现过某种程度上的断裂或空缺之外,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着,且越到后来越趋于规范化、程式化。以清皇朝时为例,在国史馆、实录馆等常设修史机构外,先后特开过明史馆、会典馆等临时性机构。在这些史馆中,每馆均置有监修、总裁、纂修、修撰、编修、检讨等职掌不同、分工细密的史官,负责编修历史,审判历朝人物,褒贬古今历史。历朝帝王或者通过任命宠臣权贵直接控制史馆,或者干脆亲自出马,御撰史册,从史书的体例、书法、列传的安排,乃至某些具体内容或遣词用字,都要经皇帝本人“圣裁”和“钦定”。因此,历代的史官,只不过是道德裁判所中具体操刀的执法官而已。
史官据以褒贬古今人物,评判是非善恶的指导思想,是儒教伦理中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两千年来,历代史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礼教伦理的基本思想去衡量、评估和审判历史上的善、恶、是、非、曲、直、忠、奸、邪、正,朝廷御用史官如此,浪迹江湖的历史家亦然。如清代史官所说:’盖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贬,史氏之是非则待于圣人之折衷。”(11)
在“三纲五常”这一总原则总前提之下,每个朝代,每个时期的历史家的具体操作程序又因当时的政治现实而互有差异。其中,汉代的公羊家和宋代的道学家曾经祖述《春秋》大义,先后重构了一套精密的“体例”和“书法”,用以指导史官们褒贬历史、记功司过的具体操作。历史家们以恪守“书法”为独一无二的天职,以讲究“体例”为独一无二之能事。用唐朝柳冕《评史官书》中的一段话说:“苟不以其道示人,则圣人不复修《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则后世不复师圣人矣。故夫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
所谓“书法”和“体例”,就其原生形态说,本是三代史官评判善恶功过,记载历史的一套规范。这一规范最初是依据“礼”的精神制定的,它具体而明确地规定了史官在历史操作中心须遵循的“书”(记载)或“不书”(不记载)或“如何书”(怎样记载和评判)的操作准则。
从《春秋》三传看,史官们决定史书记载内容的取舍,即决定某种史实是记录在案还是弃之不录,皆为奉国君之命而行事。《左传·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此事在《春秋》中未见记载。《左传》作者解释鲁国史官不载此事的原因说:“不书,非公命也。”杜预注曰:《传》曰君举必书,然则史之策书,皆君命也,今不书于《经》,亦因史之旧法,故《传》释之。”由此可见,依据先秦史官的传统法(“史之旧法”),史官记载和评判史事,均须奉国君之命,而不是由史官据己意自由裁定。又据《左传·隐公十一年》:“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然则不惟本国的历史要奉君命而记录,其他国家发生的历史事件,也要谨依各国诸侯之命以决定是否载入史册。
据唐代学者赵匡《春秋集传纂例》解释,古代史官记录历史、褒贬人物、是非古今的基本宗旨“大概有三,而区分有十”。所谓“大概有三”,即:
A、凡是国君即位、崩甍、卒葬、朝聘、盟会等应当记录在案的“常典”,就原原本本地予以记载,并由史官根据其事之邪正而予以褒贬之;
B、凡是祭祀、婚姻、赋税、军旅、巡狩等国家大事,也应当记录在案。但对这类事件的处理,则又可一分为二:即其事符合“礼”的,史官记载历史时往往略去不录;所谓“常事不书”,其事不合乎“礼”或所谓“合于变之正者”,才载录史册,并在记载该事时,通过遣词用字(如增损其文),以寄寓对是事的褒贬之意;
C、凡是庆瑞灾异,以及国君被杀、被劫持、出奔流窜、放逐叛逃、归国迎立等非常事变,史书也应记录下来,对于这类非常事件,名官往往据礼义精神予以褒贬,评断其事之是非善恶。
以上三项内容,是古代史官记载史事、褒贬历史的操作中必须遵循的三项基本原则。此外,还有十项更具体的操作凡例:“一曰悉书以志实,二曰略常以明礼,三曰省辞以从简,四曰变文以示义,五曰即辞以见意,六曰记是以著非,七曰示讳以存礼,八曰祥内以异外,九曰阙略因旧史,十曰损益以成辞。”(12)赵匡从《春秋》记事体例中归纳出来的上述原则,大抵涵括了先秦史官历史操作中的基本规范。
那么,古代史官在遵循上述规范进行历史操作时,又是如何记功司过、褒贬人物的呢?从《春秋》三传记载看,史官行使职权记功司过时,所运用的书法不同,对人物和事件的褒贬亦迥异。例如,同样是大夫被杀,因记载入史时使用的“书法”不同,史官对他所评判的对象的褒贬态度就大不相同。
例①《春秋·隐公四年》:“卫人杀州吁于濮。”——《公羊传》解释说:“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谷梁传》解释说:“称人以杀,杀有罪也。”
例②《春秋·僖公七年》:“郑杀其大夫申候。”——《公羊传》解释说:“称国以杀者,君杀大夫之辞也。”《谷梁传》解释说:“称国以杀大夫,杀无罪也。”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称人与称国仅有一字之差,其中却涵摄着史官对被杀大夫的褒和贬。例①说卫国人杀州吁,其意即卫国人都主张讨伐大夫州吁,文辞之中涵摄有州吁其人有罪该杀的信息。例②说郑国杀其大夫申候,则表示是郑国国君个人杀了申候,文辞之中涵摄着被杀者本人乃无罪被杀之意。
显然,古代史官在这里已经把历史著作当成了道德法庭,他们企图通过把那些“弑君、弑父”的乱臣贼子押上历史审判台,依据周礼的基本精神予以审判,正名定分、惩恶彰善,以遏制动荡混乱之世“君不君、臣不臣”、人伦纲纪沦丧的发展趋势。
古代史官把历史学当作道德法庭来使用的操作实践,被秦汉公羊家继承下来并予以重构和神化。公羊家编造了“圣人为汉制法”的神话,他们援阴阳五行说附会《春秋》,把天道与人事贯通为一体,使《春秋》成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经典的同时,又把史官评判是非、记功司过的“春秋笔法”吹得神乎其神,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铖。”从此以后,“春秋笔法”遂成历代史家相沿不废的编史操作程式。
到两宋时,欧阳修、朱熹等又据变化了的政治形势而予以更新完善,他们把“笔法”用作阐述“天理人伦”、维持三纲五常的工具。例如,朱熹著《通鉴纲目》,特编订凡例一卷论列书法,他祖述《春秋》,约辞严法,为后世史官执法制定了精密的程序,举凡统系、岁年、名号、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纂贼、废徙、祭祀、行幸、恩泽、朝会、封拜、征伐、废黜、罢免、人事、灾祥等等,都有具体而详细的规定。在朱熹看来,“岁周于上而大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13)只有恪守“笔法”条例,辨名分,定纲常,历史这座懦教伦理的道德裁判所,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明大道,定人道、昭鉴戒。《通鉴纲目》的“笔法”,经南宋至于明清历代帝皇的御批钦定,遂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史官衡量是非曲直,评断历史功过、评估人物善恶短长的操作模式。
在传统史学这个儒教伦理的道德裁判所中,“笔法”以外,还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编次规范的史体。其中,以“纪传体”较完美地体现专制等级秩序、体现儒教伦理的基本精神而受到历朝历代专制统治者的青睐。“纪传体”,形式在反映君臣名分纲纪方面,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纪传体”史书以帝王为中心,纪、表、志、传四体一用:“本纪”以明正统,“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14),“列传”以表臣属,外戚、宦官、名臣、忠臣、孝友、烈女、佞幸、酷吏、循吏、奸臣、贰臣、叛逆、四夷,与“本纪”相映成趣,正如众星拱月,“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界限分明,区分严格,完美地体现了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内华夏、外四夷的宗法专制正统观念。
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在传统史学这一举世无二的道德裁判所中,历史家恪守懦教伦理,“笔法”、“体例”相与为用,操斧持铖,记功司过,褒贬百代,“诛奸嫂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15),通过对死人的褒贬来整顿现实社会中活人的伦理纲常。有效地维护了宗法专制社会的君臣人伦纲纪,巩固了等级森严的极权专制统治秩序。
3
如果说,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因借助于野蛮恐怖的手段来剿灭一切真正的或捏造的异端,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基督教会的利益,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裁判所——史学,则是以更具欺骗性、蒙蔽性的“文明”方式,强化了懦教伦理纲常、巩固了建立在“家天下”皇权专制基础之上的皇朝统治秩序。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当初抬高和神化史书道德教化的功能时,也多少存有用道德来约束专制权力、惩处暴君乱主的幻想,希望专制君主由畏惧历史而生扬善抑恶之心。《国语·周语上》记载说:“天下听政,使公卿列士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传统社会的知识精英们显然以为,借助于历史学记功司过、褒贬惩劝的特殊功能,可以规劝专制君主昭明大德,可以匡正极权帝皇幽昏之行,至少也可以使专制者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限制,而不致于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因此,传统史家在谈到史书的惩劝对象时,往往也都是着眼于为人君者与为人臣者之两极的。例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的惩劝功能时,就认为,“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纂弑之诛,死罪之名。”(16)刘知己在谈到史书的惩劝功能时,也认为,“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17)
但是,传统历史家显然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予以制约,没有相应的权力与君权相制衡,而仅仅凭藉虚幻的道德,凭藉史学这一道德法庭,是决不能对专制极权者形成制控、决不能约束和制止专制帝皇或有权有势者的任意妄为的。何况,传统史家所据以从精神上的约束专制统治者的伦理道德,本身就是以维护等级尊卑纲纪,维护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为主要取向的。
更为可悲的是,传统历史家所拥有的这一点点微弱的可怜的制约权,也是由历代专制皇朝所严密控制着的。历史的记载、史家的褒贬、史书的刊行,都统统由皇家操纵。例如,当汉魏时期专制君主感到记载他们言行的“起居注”的公开不利于专制统治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采取行政手段,“密为记注”(18),不许公开刊布。唐朝以后,专制帝皇的手段更为高明,他们觉得不公布“起居注”,只不过使不利于他们的历史记载无闻于当时,最终还将流传后世,于是改而对本朝起居注、日历、实录的记载实行严厉的控制,或者不许记载起居注的史官在帝王之侧,或者规定史官记载以后,先要送皇帝过目,使起居注制度形同虚设。清朝时,皇帝对史官撰写的实录更是一改再改。光绪时定制,日讲官每日进讲实录一卷,遇有不如意处,在讲筵中间便行修改、删削。由此不难看出,历史这一道德法庭并没有在精神上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专制帝王形成有效制约,历朝的起居注、实录和国史,多是谀信媚主之作,“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19),一味歌功颂德,褒谀阿时,哪里能够匡救其恶?
事实上,当那些仗义直言的史官以道德法庭的审判官的姿态出现,对暴君乱主行“斧铖之诛”的时候,作为精神上的受审对象的皇帝往往反过来从肉体上对执法官(历史家)进行野蛮的摧残和凌虐。从历史上看,那些有意无意间触忤龙颜——或违背当权者的意旨或对极权阶级褒贬不当或载录了专制统治者的隐私的历史家,大多身罹祸难,轻者免官下狱,重者本人惨遭屠戮不算,还要诛连九族。例如,齐国太史因载录“崔杼弑其君”,而罹难者兄弟三人,司马迁因触犯武帝,而惨遭宫刑班固因私撰国史下狱,崔浩因披露“国恶”而满门抄斩,庄廷印明史、戴名世记录抗清历史而合族被斩,……无怪乎刘知己深有感慨地长叹:“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沈约)《宋书》多妄,肃武(梁武帝)知而勿尤;伯起(魏收)《魏书》不平,齐宣览而无谴。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已,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0)这对于历史上以道德法庭审判官自居,以记功司过,彰善瘅恶为己任的传统史学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嘲讽!
但是,由此而得出传统史学的道德教化功能为子虚乌有,则未免冤枉了传统史学。客观地看,史学社会功能的被神化,虽然没能形成为一种以道德上制约极权者的威慑力或约束力(Sanction),但在向人民灌输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愚忠愚孝上,在强化君主专制制度上,在模铸中国人的奴性人格上,传统史学却无疑是中国历代专制帝皇行之有效的全能武器、忠实可靠的奴才帮凶。
中国传统社会的历代专制统治者,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对于生前身后名执着追求的人生取向,借助于历史这个道德法庭大造舆论,敦励风俗愚弄人民。一方面,专制统治者利用历史推行礼教,大肆表彰那些“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的“孝子”谥之以“孝义”、“孝行”、“孝友”、“孝感”等美名,树立典型,宣扬孝道,并以“孝”为原点,由“孝父”推衍出“忠君”,宣扬君父居在三极,忠教的百行之先”(21)为那些忠于所事、各为其主,“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的忠臣死节之士树碑立传,赠之以“忠烈”、“忠义”、“忠臣”等荣耀,赞扬那些孝子烈女死节忠臣为“至性所激,感天地、动神明,名留天壤,行卓古今”(22),正是这种彪炳丹青之列的巨大诱惑,使“全孝”“尽忠”终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盛行不衰的一种社会性价值取向,从而成功地扼制犯上作乱的异己力量于未萌之前。
另一方面,专制皇朝统治者又借助于史学这个道德裁判所的特殊功能,从精神上严厉惩处欺父欺君、犯上作乱的所谓“叛臣逆子”、“僭伪奸臣”、“流贼乱寇”,打击异己,镇慑异端。身为道德裁判所审判官的传统史家,承当朝帝皇的御旨把那些凌驾、弑君、反叛、纂杀的乱臣贼子,把那些所谓进退无据、奴颜降附的奸佞贰臣,统统押上历史审判台,接受“铖铖之诛”。他们试图通过“隐殛其冥漠不灵之魄”,警告世人不得“惟知嗜利偷生,罔顾大义”(23)更不可怀非分之念,因为“宝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24),帝皇是真命天子,神意所授。生活在专制政治超强制控、儒教伦理毒害熏陶和宗法家族社会组织网络三位一体的传统社会中,而又生性特别好名重誉的中国人,再经史学这个道德裁判所中“华褒之荣”和“斧钺之诛”两方面褒贬惩劝式的一番整治,原有的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也就丧失殆尽了。这样,外于混沌无序状态的个体的自我和人格,就如一堆烂泥,任凭专制统治者拿捏,去塑造一个个为专制统治者“有用”的器具玩物,去模铸对一朝一姓矢志效忠的奴性人格:臣忠君,子孝父,妻事夫,忠君警上,从一而终,严格恪守上下尊卑的宗法专制等级秩序,老老实实地做着礼教纲常的驯服工具,死心塌地地做着专制皇朝的愚忠奴才,——这就是为当今学者们赞叹不已的中国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之功能。
注释:
①刘知己:《史通·直书篇》。
②荀悦:《申鉴》卷二。
③《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④刘知己:《史通·史官建置篇》。
⑤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⑥刘知己:《史通·史官建置》。
⑦文天祥:《过零丁洋》,载《文山先生全集》。
⑧《新唐书·朱敬则传》
⑨孟柯:《孟子·滕文公下》。
⑩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1)《四库全书总目》卷88。
(12)赵匡:《春秋集传纂例》。
(13)朱熹:《通鉴纲目·序》。
(14)刘知己:《史通·本纪》。
(15)韩愈:《答崔立之书》。
(16)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7)刘知己:《史通·直笔篇》。
(18)《周书·柳虬传》
(19)李建泰:《名山藏序》。
(20)刘知己:《史通·曲笔篇》。
(21)《晋书·忠义传》,卷89。
(22)缍明史·忠义传》。
(23)《清高宗实录》第1332卷。
(24)《晋书·桓温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