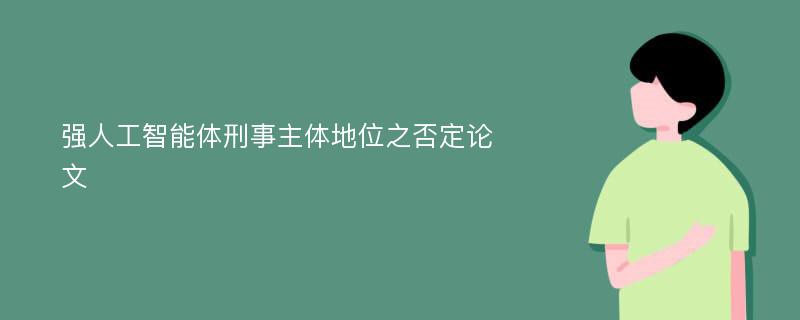
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之否定*
张成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的否定应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次展开。从实然层面来看,强人工智能体缺乏成为犯罪主体所应当具备的认识因素和辨认因素,无法产生规范意识且不具有意志自由,也无法实施犯罪行为,因而其不具备成为刑事主体的实然条件。承认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将会给传统刑法理论带来解构的危险,相关强人工智能体刑法立法也缺乏必要性,刑事司法活动更是无法展开。因而,从应然层面来看,强人工智能体不应被拟制为刑事主体。此外,强人工智能体和单位主体不具有可类比性,借鉴单位犯罪的刑法立法实践也行不通。
关键词: 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实然分析;应然探讨
一、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新发展、新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争议。人工智能体的刑事主体地位问题是当前刑法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围绕这一课题学界存在“人工智能刑事主体肯定说”(简称肯定说)和“人工智能刑事主体否定说”(简称否定说)两种相对立的观点。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阶段的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有弱人工智能技术和强人工智能技术之分,与之相适应人工智能体也有弱人工智能体和强人工智能体之别。因而,人工智能体的刑事主体地位也应就弱人工智能体和强人工智能体分别进行探讨。其中,就弱人工智能体的刑事主体地位而言,当前学界一致持否定态度。因此,双方争议的焦点实际上主要是围绕处于更高发展阶段的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的有无而展开。
对此,新一轮人工智能研究热潮已然在学界扩散开来,但是这种研究热潮极易使人们的判断偏离理性。特别是从肯定说学者的论述来看,强人工智能体时代似乎已经到来,而强人工智能体“入刑进典”也已势在必行。对于肯定说学者们的主张,笔者在担忧之余也存有一些疑问。其一,从实然角度分析来看,强人工智能体是否真的具备了成为刑事主体的条件?其二,从应然角度分析来看,我们是否就应当要将其拟制为刑事主体呢?对此,笔者将从实然和应然两个维度进行简要分析。
活动中进行了LEED认证授牌仪式,玫琳凯大厦获得LEED既有建筑运营和维护V4金级认证,是上海第一家获得该认证的物业公司。玫琳凯公司还与江宁街道签署了“共建绿色社区”的框架协议,共同开展环保科普类讲座。并结合玫琳凯“玫好家园志愿者”项目,推广垃圾分类,协助江宁街道推进社区垃圾分类绿色账户和两网融合等环保公益活动。
二、实然分析:强人工智能体无法成为刑事主体
强人工智能体的刑事主体地位首先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也即从实然层面来分析其是否具备成为刑事主体的条件。对此,在持肯定说的学者看来,“强人工智能体能够超越研发者设计和编制程序而形成的自主独立程序形成独立意识和意志,并可以在自主意识和意志支配下实施行为,从而能够成为独立刑事主体”(1) 参见刘宪权,林雨佳.人工智能时代技术风险的刑法应对[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5):54.持类似观点的论文还有:江溯.自动驾驶汽车对法律的挑战[J].中国法律评论,2018,(2);孙道萃.人工智能对传统刑法的挑战[N].检察日报,2017-10-22(003);卢勤忠,何鑫.强人工智能时代刑事责任与刑罚理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等. 。而在否定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的学者们看来,“强人工智能体不具备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自然无法具备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2) 王肃之.人工智能体刑法地位的教义学反思[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7.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叶良芳,马路瑶.风险社会视阀下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应对[J].浙江学刊,2018,(6):67-68. ,而且其在“刑罚适用效果方面存在困难”(3) 赵秉志,詹奇玮.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关于人工智能的刑法学思考[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98. ,此外赋予其刑事主体地位也还会“导致刑事责任体系崩塌”(4) 庄永廉等.人工智能与刑事法治的未来[J].人民检察,2018,(1).黄京平教授发言部分. 。而“意志自由是认定刑事主体地位的关键要素,其包括认识要素与意志要素”(5) 时方.人工智能刑事主体地位之否定[J].法律科学,2018,(6):67. 。所以尽管从争议内容来看,论辩双方就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的争议,早已从构成要件版块延伸到刑事责任和刑罚论等领域。但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的实然判断还是应当以分析其是否具备意志自由为前提。从这一点来看,强人工智能体并不具有意志自由,自然也就无法成为刑事主体。
(一)超越编程外无法产生意志自由
就强人工智能体意志自由的来源,有学者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机器人会产生独立的意识和意志”(6) 刘宪权,房慧颖.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正当性与适当性[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09. 。对此,无论是从其产生前提来看,还是从论述逻辑来分析,主张强人工智能体在超越研发者设计和编程内容之外形成自主独立程序,便具备独立意志自由的说法都有待商榷。
首先,从产生前提来看,论断的前提先验不可证。诚然,为保有理论的活力,理论研究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刑法学作为一门面向社会实践的社会科学门类,其也无法超脱于特定时期社会现实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因而,对强人工智能体犯罪主体地位的探讨,不能将超脱于现实实践基础之外,对未来的推定和假设作为论断前提。遗憾的是,当前肯定说学者探讨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并非立足于客观现实,而恰恰是将对未来的推定和假设作为论述前提。如肯定说学者首先假设“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行为人似乎不再局限于自然人和单位”(7) 刘宪权,林雨佳.人工智能时代刑事责任主体的重新解构[J].人民检察,2018,(3):9. ,尔后便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直接推定强人工智能体具有刑事主体地位,并进一步展开强人工智能体成为刑事主体后的刑事责任和刑罚体系方面的探讨。无论后续探讨在逻辑方面多么缜密,也都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事实,也即这一论断的前提是学者基于自身经验的推断,先验不可证。
其次,从论述逻辑来看,论断结论的得出存在逻辑倒置。按照前述学者的主张,人工智能体在超越研发者设计和编程内容之外实施相关行为时便具有自由意志。但是从二者的逻辑关系来看,具备独立的意志自由才应当是强人工智能体能够超出编程和设计实施相关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肯定说论者所主张的充分条件。在笔者看来,人工智能体超出编程外实施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原因不在于其具备了独立的意志自由,更大可能性在于编程自身的漏洞和缺陷,而这一点却囿于人类的认知局限而未能合理解释。可见,二者间存在逻辑倒置。
(二)编程时录入法条不等于法规范意识的习得
还有学者指出“设计者完全可以将人工智能所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在设计之初就以编程的形式植入人工智能之中,这与学生在学校学习法律法规以及法律工作者进行普法教育并无实质区别,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至少在‘记忆力’上要远强于自然人”(8) 陈叙言.人工智能刑事主体问题初探[J].社会科学,2019,(3):115. 。但是,对法规的记忆并不等于对法规内容的认知,更不能等同于法规范意识的习得。前述主张将规范意识等同于法规内容的认知,明显不合理。
首先,将编程过程中机械地录入法条内容等同于自然人的法律研习经历,不仅未能看到法律学习背后深层次的认知学习机理,同时也是对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不尊重。难道法律研习过程仅是单纯记忆法条吗?事实显然不是这样,记忆和熟知法条内容仅是法律学习的前提和基础。对法条内容的机械记忆不仅与法律研习的初衷相背离,更与决定实施或者不实施某一特定行为的自主法规范意识存在天壤之别。
首先,从内涵来看,二者就不同一。智慧指的是生物体所拥有的一种高级的综合能力,主要指的是对周围事物、社会、环境等进行的思考、分析、推理、决定等能力,其包含情感与理性、意向与认识、生理机能与心理机能等等众多因素。而智能则是智力和能力的总称,其包括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身体运动智能等等。二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智慧包含情感、分析、判断、决策、意志能力等非理性综合判断能力,而智能则主要指的是理性推断能力。在生命体之外,强人工智能体与自然人相比,其具备的仅是以理性推导能力为基础的智能,而非包含感性认知和非理性判断在内的人类智慧。
(三)生命体唯一区别说掩盖意志自由判断
有学者认为生命体是人工智能体和自然人的唯一区别,但是这一主张既模糊了二者的界限,同时也掩盖了对强人工智能体意志自由的判断。按照生命体唯一区别说的逻辑,由于“智能机器人和自然人的区别仅在于自然人具有生命体,而智能机器人是非生命体”(10) 刘宪权,林雨佳.人工智能时代技术风险的刑法应对[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5):54. ,因而强人工智能体除了不拥有生命体之外,自然便具备自然人的其他机能,这其中就包括成为刑事主体所必需的意志自由。但是,将强人工智能体和自然人的区别简化为是否具有生命体判断的做法,实质上混淆了智慧和智能这两个概念。
其次,法规范意识以行为主体具备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为前提,其无法通过编程时录入法条而获得。众所周知,法规范意识是刑事主体参与到刑事法治实践的重要前提。进一步需要指出的是,规范意识的习得必须以行为主体准确理解法条背后的社会意义为前提,而在编程时通过将法条内容录入人工智能程序之中无法使强人工智能体习得法规范意识。所以,寄希望于通过编程录入法条来使强人工智能体具备法规范意识的做法明显不可行。正如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无论多么强大都只表现于对规则理性的推理方面,而无法像人类一样运用超越规则之上的价值判断”(9) 李晟.略论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法律转型[J].法学评论,2018,(1):105. 。而这种基于价值判断基础上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缺失,正是强人工智能体欠缺意志自由的明证。
其次,强人工智能体通过深度学习习得的是智能而非智慧。原因在于,从获得方式来看,智慧的获得包括基因遗传与后天学习获得,其中基因遗传对智慧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而智能则主要是依靠后天学习获得。强人工智能体依靠研发人员的变成和设计获得的深度学习能力所获得的仅是一种后天理性推理和计算能力,也即智能。而以先天遗传为基础而成的智慧则是生物体所独具的一种能力,因而“人与机器人的最大区别表现在智慧与智能的巨大区别”(11) 黄欣荣.人工智能热潮的哲学反思[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9.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强人工智能体仅具有智能而无法具备人类作为生命体所专属的智慧。以“人机大战”为例,在机器人AlphaGo输给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的那场比赛后,研发团队后来发现AlphaGo输棋的原因是当时李世石下了一步棋谱里没有的棋,AlphaGo没有学习过就随机下了一步,结果才输了比赛。后来,团队在AlphaGo基础上升级了系统,并把人类有记录的3000副棋谱和可能的1.5亿副棋谱都通过编程的方式来训练和升级得到AlphaZero。后来再与柯洁对弈时,对升级之后的AlphaZero而言不过是按照之前训练过的棋谱进行情景再现,根本就不需要像人类棋手一样结合对弈局势,运用智慧来作出时时判断。究其实质,机器人战胜人类棋手不过是借助其在深度学习之后拥有的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而获得的智能“蛮”力,在事先知道人类棋手可能的落子结果后“作弊”取胜。
总之,班主任工作任重道远,班主任要具备反思意识和终身学习意识,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还要紧跟时代,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结合新课程发展的需求,进而提高班主任管理水平,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实现党的教育目标。
由此可见,强人工智能体与人类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拥有生命体,更在于智能与智慧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对此,生命体唯一区别说不仅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且还掩盖了强人工智能体自由意志判断问题。
“知道知道,什么单纯啊?一来就勾引上副院长,你瞧这速度!”另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轻蔑地说,“还不是为了毕业之后能留在我们医院,亏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1929年编纂委员会成立后,从事编纂事务的职员群体有了一个独立、统一、固定的组织。因此,编纂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群体的正式形成。尽管1935年以后“编纂委员会”这一名称不再使用且成员结构和数量都发生很大变动,但从事编纂事务的职员群体却继续以“编纂”或“编纂室”的名义独立存在着。据笔者统计,1929至1937年间,任职于编纂委员会或编纂室的成员共计有28人(见表2)。
(四)强人工智能体无法实施犯罪行为
从法律行为的要素来看,强人工智能体实施的动作仅是身体举动而非在特定意志因素支配下实施的法律行为,更谈不上是犯罪行为。无论是AlphaGo在对弈中的“落子”行为,还是2015年德国大众汽车机器人手臂的“杀人”行为,又或者是2016年美国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的“交通肇事”行为,并非是其在自由意志下实施的犯罪行为,而是在编程内或编程外作出的举动。
首先,从动作形成机制来看,人工智能体表现于外的动作是在既定编程程序设定下做出的固有举动。无论是强人工智能体还是弱人工智能体,研发者的编程程序设定以及原始数据的录入都是其作出相应举动的必要前提。人工智能体表现于外的所有“行为”都只是其按照既定程序设定作出的相应举动,而非其基于自身对外界的认知,在自我判断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实施相应的犯罪行为。换言之,人工智能体是按照编程指令而作出特定的举动。而在有的学者看来,那些未来可能发生“超出设计和编程程序范围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12) 刘宪权.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路径[J].现代法学,2019,(1):75. ,实质上仍是人工智能体基于既定编程程序而作出的举动,只是囿于人类的认知局限而未能合理解释而已。
其次,从犯罪行为的内容来看,人工智能体缺乏成立犯罪行为的主观要素。由于强人工智能体缺乏独立的意识和意志,其所实施的外部动作并非其基于自主意识“有选择地”实施,而是机械地“执行”既定编程程序。在强人工智能体根据编程设定的指令做出举动的时候,其对行为的性质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均处于未知状态,自然也就不是普通的犯罪行为。
在生态城市建设中,首要目标是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和旅游环境。相关部门要建设公共环境,有目的地策划各区的旅游景点,让大家能够在休闲时光里充分放松,缓解平时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工作压力,使大家保持愉悦的心情[1]。
立法活动通过其“产出”的法规范来对社会治理产生直接影响,通过预测和分析法规范出台后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也有助于我们反思立法的合理性。从当前肯定论者所提出的有关强人工智能体的刑法立法建议来看,其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存有疑问:
三、应然反思:人工智能体不应成为刑事主体
由于实然层面的教义学分析无法为强人工智能体成为刑事主体提供充分的论证。因而,要想赋予其刑事主体地位便只能运用刑法拟制技术,在刑法理论和刑法立法活动中将其拟制为新的刑事主体。而“刑法拟制作为立法者实现某种立法政策或价值的有效途径,是关切着立法者对某种立法政策或价值的考虑”(14) 苏彩霞.刑法拟制的功能评价与运用规则[J].法学家,2011,(6):29. 。如果说实然层面探讨的是强人工智能体可不可以成为刑事主体的问题,那么应然层面分析的则是强人工智能体应不应成为刑事主体,并且这种应然分析背后的价值选择也更有助于我们反思步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刑法的基本立场。从应然层面来看,将强人工智能体拟制为刑事主体后将会给刑法理论、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带来的一系列变动和困境。
解析:拉力的方向水平向右,作用点应画在物体的重心上,过作用点沿水平向右的方向画一条带箭头的线段,并用符号F表示,大小为20N。
(一)刑法理论面临解构危险
如前分析,根据当前的刑法理论,强人工智能体并不具备成为刑事主体的意志自由。因而,如欲想将其拟制为新的刑事主体,便只能修正刑法理论的相应内容。从表面来看,这种修正和创新貌似有助于推动刑法理论向前发展,但实际上这一“创新”给传统刑法理论带来的并不是积极的理论建构,而是消极的理论解构,使现有的刑法理论陷入困境。
首先,行为理论困境。行为是行为人踏入法律领域的唯一途径,犯罪行为是行为人成立犯罪的前提。如何将强人工智能体实施的外部举动解释为犯罪行为是承认其刑事主体地位之后,行为理论面临的首要困境。但是由于意志自由的缺失,强人工智能体表现于外的“行为”仅是一种客观举动,缺乏成为犯罪行为所必需的主观构成要素。因而无论是从社会行为论来看,还是从规范行为论的角度来分析,伴随承认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而来的强人工智能体的实行行为性问题,将会使当前的行为理论面临解构的危机。
2.刑罚适用条件不充分
再次,责任原则贯彻受阻。“随着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引入,责任观念从心理责任论向规范责任论演进”(15) 车浩.责任理论的中国蜕变——一个学术史视角的考察[J].政法论坛,2018,(3):66. ,以心理责任论为基础的规范责任论成为当前刑法责任理论基本立场。其中规范意识的保有和形塑是科以刑事主体规范责任的前提和目的,但是由于强人工智能体既无规范意识形成基础又无规范意识形塑客体,致使强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的认定被迫片面化为只注重行为客观方面的客观责任,这既与责任原则相违背也导致责任主义无法顺利贯彻。
2010年,王棣被提升为西王集团副董事长。同年8月18日,西王集团北京运营中心正式启用。在他看来,西王集团在北京建立运营中心,村办企业走向首都,完成向国内大公司,甚至是国际化公司的转型,最大的困难在人上。在北京需要重新建立团队,运营中心第一批员工几乎都是由他亲自招聘,那个阶段可以称得上是西王的“二次创业”。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均明确规定,“固定资产折旧按照各类固定资产原值和财务制度规定的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分类核算”。东线一期工程是在利用现有河道、湖泊及抽水设施的基础上,通过新建、扩建、改造输水、抽水设施等,采取逐级提水的方式向北方输水;中线一期工程是通过加高现有丹江口水库大坝增大蓄水量,开挖输水渠、建设涵管道等,采取自流方式向北输水。两者输水方式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东线工程固定资产采取分类折旧方法,折旧率泵站为2.6%,新建河道为2%,供电、通信设施和水情水质监测系统为5%;中线水源及干线工程固定资产则采取综合折旧方法,综合折旧率为2.14%。
最后,刑罚目的实现不能。当我们通过刑法立法将强人工智能体拟制为刑事主体之后,之前被遮盖住的更深层次问题便逐渐凸显出来,那便是刑罚的目的问题,也即刑罚和犯罪预防间的关系问题。一般认为,“犯罪预防是刑罚的目的,是刑罚正当化的根据,为刑罚发动提供了积极理由”(16) 郝英兵.刑事责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序言7. 。刑罚通过剥夺犯罪人部分权益,强化犯罪人和一般人的法规范意识以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法规范意识又是以包括感知、分析和自治能力在内的自主能力为前提”(17) 杜严勇.机器人伦理中的道德责任问题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7,(11):1608. 。但问题是,强人工智能体的感知、分析和自治能力并不因被拟制为刑事主体而客观获取,因而就算对其科以刑罚也并不能使其具备和强化法规范意识,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目的也便无法实现。
可见,刑法拟制技术的运用并不能顺利弥合强人工智能体不具备意志自由的客观现实和成为刑事主体必需的刑事认知能力主观要素间的鸿沟。而脱离这一客观现实强行赋予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带来的只能是新的刑法理论困境。
(二)刑法立法缺乏合理性和必要性
法者,国之重器。立法,特别是刑法立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则是刑法立法活动中必须考量的因素。根据持肯定说学者们的建议,在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立法也要作出的相应变动,这种变动主要体现在刑罚种类的变动和分则罪名的调整两个方面。其中就刑罚种类而言,肯定论者较为一致地主张应增设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三种刑罚措施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机器人犯罪(18) 卢勤忠,何鑫.强人工智能时代刑事责任与刑罚理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16. 。另外,强人工智能体犯罪的罪名设置则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其一,在罪名体系方面提出“科技犯罪”上位概念,形成“计算机犯罪—信息网络犯罪—人工智能犯罪”三位一体的科技犯罪规制模式(19) 陈伟,熊波.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治理逻辑与刑法转向[J].学术界,2018,(9):77. 。其二,在具体罪名设置方面需要修改的有:侵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类犯罪、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等(20) 李振林.人工智能刑事立法图景[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25. ;需要增设的新罪名有:“滥用人工智能罪、人工智能事故罪”(21) 王艳玲.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问题与应对思路[J].政治与法律,2019,(1):31. 等。但是,由于肯定说学者们的立法建议多是从罪名设置方面提出,客观而言,对相关立法建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都缺乏整体性考量。
1.立法必要性缺失
一般来说,立法的必要性包括立法前提的稳定性和立法对象认识的一致性。其中“立法的基本前提是事物的稳定性,对正处于过渡时期、转型时期的事物进行立法、试图通过人为法的外来稳定性来固化事物的内在稳定性,这无论对于立法还是对于事物都是一种伤害:人制定的法不可能长期地生存和发展;被强制立法之事物也难以取得理想效果”。(22) 于兆波.立法必要性可行性的理论基础与我国立法完善[J].法学杂志,2014,(11):56. 反观强人工智能体的现实立法条件,现阶段开展强人工智能体刑事立法恰恰缺乏这种必要性。
首先,作为立法规制对象的强人工智能体“犯罪行为”不稳定。众所周知,我们尚处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起步阶段的初期,现在所谓的人工智能应用更多的是专用型人工智能技术,通用型人工智能技术运用远未到来。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究竟会发展到什么水平,是否具备独立意志、又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动都尚未可知。当前肯定说学者们论述的人工智能体的“犯罪行为”都是基于个人经验、知识的设想,而缺乏稳定的认知。如此一来,动用对法规范稳定性要求极高的刑法来规制尚处于萌芽阶段且仍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的人工智能体的行为在合理性方面的欠缺也就不言自明。
其次,人们就强人工智能体“犯罪行为”的认识存在不一致。与学术研究的探讨性不同,确定性是立法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最终追求。在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的有无尚存争议,强人工智能体表现于外的到底属不属于犯罪行为都未能统一认识的当下,是否有必要直接通过刑法立法来设定与强人工智能体“犯罪行为”相关的罪名和刑罚种类也值得我们反思。从客观上讲,当前肯定论者们就强人工智能体所提出的立法建议天然的缺少充足的实践依据作依撑,自然也就缺乏刑法立法的必要性。
2.立法合理性存疑
综上,当前无论是持肯定说的学者,还是赞成否定说的学者,都是从实然角度围绕自由意志的有无来论证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具备与否。但是由于自由意志的先验性,使得着眼于教义学分析和逻辑演绎来探讨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的论辩双方都无法提出充足的论据来说服对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沦为一种文字游戏的危险。同样是自由意志不可证,但是我们却都赞成“自然人的自由意志偏偏是值得向往和保护的”(13) 张明楷.责任论的基本问题[J].比较法研究,2018,(3):7. ,那么强人工智能体的自由意志是否同样值得追求和向往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从应然层面反思强人工智能体应不应当成为刑事主体。
其一,从立法逻辑来看,无规制对象先立法,导致强人工智能体刑法立法活动背离立法规律。刑事立法滞后于刑事司法实践是所有成文法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为此一定的立法前瞻性便显得尤为必要且正当。这也是肯定论学者们提出前述立法设想的现实考量因素之一。但是法学作为一门面向社会现实的实践科学,立法更是以既存的社会实践为调整和作用对象,这是所有立法活动都必须遵循的立法规律,而超脱于社会实践的刑法立法则会造成一种“有刑法规范无规制对象”乱象出现。在尚处于弱人工智能初期的当下便提出有关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立法的具体立法设想,非但无助于强人工智能体刑事法治制度的建构,反而会降低刑法立法的实践导向。正如有学者指出,强人工智能体立法“理应回归到真实的犯罪治理上来,并且致力于在社会发展和刑法稳定之间、在立足现实与适度前瞻之间寻找恰当的尺度与界限”。(23) 王肃之.人工智能体刑法地位的教义学反思[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2019-03-12. 相反,缺乏犯罪治理实践和规制对象的强人工智能体刑法立法建议则只能是无源之水,按此建议制定出台的刑法规范也必将因缺乏适用对象而欠缺合理性。
其二,从立法的可预测的结果来看,将强人工智能体拟制为刑事主体将带来刑法立法的整体性变动。按照肯定说学者们的主张,我们应将人工智能体作为犯罪主体,在分则中增补相关罪名并设置相应的法定刑(24) 吴允锋.人工智能时代侵财犯罪刑法适用的困境与出路[J].法学,2018,(5):165. 。不可否认,增设新罪名、配置相应刑罚确实是刑法应对新型犯罪行为的必要手段。但是,与一般情形中新产生的犯罪行为不同的是,强人工智能体立法还涉及到一个基本前提——刑事主体地位的立法认可问题,而且通过刑法立法赋予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还将带来刑法典体系性的变动。这种体系性变动不仅仅包括分则条款中的具体罪名的新设,其同时还会在刑事主体、累犯、共犯、刑事责任、刑罚等方面引起刑法典总则内容的修改和变动。如此一来,这些变动对刑法而言不再是刑法典内容的部分修订,而是涉及刑法典全局内容的整体性变动。这些变动不仅是肯定说学者们所未能考量的,同时也远远超前于当前的刑法立法技术水平。
(三)刑事司法活动无法展开
通过刑事司法程序追究强人工智能体的刑事责任,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是肯定论者们选择以刑法方式来规制强人工智能犯罪的最终目的。但问题是,在现行的刑事司法环境下,我们无法通过刑事司法活动来有效规制强人工智能体实施的“犯罪行为”。尽管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承认强人工智能体的刑事主体地位,并通过刑法立法技术将其拟制为刑事主体,但是这还是无法改变强人工智能体不具备意思自由,缺乏意思形成机制和表达机制的客观事实。因此,强人工智能体也就缺乏顺利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能力和客观条件,导致相关刑事司法活动无法顺利展开。
1.刑事司法正义丧失保障
中国养猪业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在经营主体、经营方式、区域布局、生产工艺、疫病防控、产品安全、环境控制等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同时面临着由农户养猪向集约化和产业化转型的剧烈市场动荡期。作为我国农业主要产业部门和居民肉食品主要来源的养猪业,正在走向健康平稳发展的轨道。
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刑事司法正义的内在要求,但是由于强人工智能体的自主意思形成和表达机制的缺乏,使得其无法行使自己的刑事司法权利,从而也无法保障刑法司法正义的实现。
以刑事辩护权为例,其“作为基本人权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延伸和保障,辩护权成为每个人不可剥夺、不可扣减的基本权利,世界上许多国家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普遍确认了这一权利”(25) 艾超.辩护权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0.49.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也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并确立了辩护权的宪法地位。辩护权也因此成为保障刑事被告人基本人权的司法体现之一。从实现方式来看,辩护权分为自我辩护、他人辩护两种。但是由于强人工智能体属于非生命体,自我辩护已然不可行,另外由于其无法就案件事实、自身诉求等与人类正常沟通,因而借助第三方帮助的他人辩护在客观上无法实现。所以客观来看,强人工智能体作为刑事被告人所享有的刑事辩护权从行使途径层面就已经“被剥夺”。与辩护权相似,刑事司法中强人工智能体的上诉权、申诉权等保障刑事被告人人权、实现刑事正义的权利也都面临着相似困境,刑事正义也便失去了保障。
其次,共犯认定和未完成形态界定困难。共犯认定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界定是强人工智能体犯罪具体个案司法中必将回答的问题。虽然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可以通过立法技术拟制获得,但强人工智能体的“主观心态”却并不因拟制而应然地变得可知。如此一来,与强人工智能体成为刑事主体后将面临的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认定问题、共犯犯意重合范围界定问题,以及具体犯罪行为中止、未遂等犯罪形态的认定等问题都因强人工智能体主观心态的不可知而陷入困境。
刑罚本质上是一种恶,是以剥夺犯罪人所拥有的特定权益为前提。当我们试图创设一种适用于人工智能体的刑罚方式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体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只有确定了其拥有的权利那么对该种权利的限制甚至是剥夺才能够起到刑罚的效果(26) 陈叙言.人工智能刑事主体问题初探[J].社会科学,2019,(3):114. 。但是,由于强人工智能体无法享有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使得当前以剥夺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为主要内容的刑罚措施也就无法适用于犯罪的强人工智能体。
如此一来,就算承认强人工智能体的刑事主体地位,也无法通过刑事司法实现刑法规制其“犯罪”行为的目的。那么,通过刑法立法将强人工智能体拟制为新的刑事主体,并增设相应的罪名和刑罚手段来规制所谓的强人工智能体犯罪行为必要性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对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有无的探讨,不能仅仅停留于概念演绎和逻辑分析,分析承认人工智能刑事主体地位后带来的刑事司法困境,有助于从反面论证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的非必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应当承认其刑事主体地位。
反观肯定说学者们类比自然人刑罚种类而构思出来的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等在未来将要适用于强人工智能体的刑罚种类,这些刑罚手段最终毁损的是强人工智能体所有者的人工智能体实体,剥夺的是强人工智能体所有者的财产权,而不是强人工智能体自身的合法权益。因而,根据肯定说学者们的构思,适用前述新型刑罚将会导致一种强人工智能体犯罪、其所有者遭受刑罚惩罚、罪责不一致的怪象。如此一来,对强人工智能体科以刑罚的目的也只能无奈落空。
通过计算各指标的成本价值量及成本价值量可知,并不是所有已开通航线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主要原因,即表3优劣势.
(4)构造标志:区域内矿床分布在火山构造内或附近,并受断裂构造控制,断裂构造带既是成矿热液的运移通道,也是控矿和容矿场所,特别是构造复合地段,更是成矿的有利部位,因此,火山构造和断裂可视为本区金矿体的良好间接找矿标志。
四、余论:强人工智能体与单位犯罪间不具有可类比性
类比我国刑法理论中有关单位犯罪的相关理论,并借鉴单位犯罪立法实践,是很多肯定论学者试图证成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的重要论证策略。因此,在前文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就人工智能体不具有刑事主体展开分析之后,也有必要就强人工智能体与单位之间的可类比性问题进一步展开分析。在笔者看来,二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均不存在可类比性:
首先,单位具有独立的意思形成机构和决议执行机构,而强人工智能体没有。尽管刑法中的单位与民商法中的法人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但二者指代的都是自然人之外能够实施相应法律行为的集合主体,在大部分情形下二者都能够同等适用。单位虽是拟制的刑事主体,但我们在刑法立法中建构单位(法人)主体地位时,同时也为其设计了有相应的财产权利、设定有独立的意思形成机构和决议执行机构为其参加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制度支撑(27) 参见《民法总则》,第57条、59-61条;《公司法》,第36条、37条、98条、99条等。 。这主要是通过法律制度的设定,由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组成单位的意思形成机构和决议执行机构。这些自然人在成为单位成员后便与单位融为一体,并以单位的名义对外参加社会经济活动。正是这些法律制度的建构才使得原本不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单位,通过作为其成员的自然人具备了成为刑事主体所必要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此外,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法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并可以“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单位便也和自然人一样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利。这也为通过对单位判处罚金来惩治单位犯罪成为可能,刑罚的目的也因此得以实现。
用于补充维生素C——每天50~100mg。我一般一天吃一粒,有时候忘了吃也无所谓,如果口腔溃疡,我会吃两粒直到痊愈。
那么,我们再看看在那些主张强人工智能体具备刑事主体地位的学者又是如何肯定强人工智能体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呢?如前所述,学者们多是采取拟制的方式,认为强人工智能体“可以超出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自主判断并做出决策,显示出与人相似的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28) 卢勤忠,何鑫.强人工智能时代刑事责任与刑罚理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16.持类似观点的论文还有:刘宪权,房慧颖.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正当性与适当性[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王燕玲.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问题和应对思路[J].政治与法律,2019,(1);吴波,俞小海.人工智能时代刑事责任认定思路的挑战与更新[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政法论丛),2018,(5)等。 。法律拟制作为一种将虚拟事实拟作真实事实的技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突破,属于一种例外情形,因而在运用法律拟制制度之前,我们必须考虑适用的正当性基础和界限。“为尽可能地实现拟制规范与原规范间的衡平,刑法立法拟制一般都要求拟制事实与原事实间具有高度的类质性”(29) 李凤梅.刑法立法拟制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03. 。但是由于强人工智能体并未出现,当前肯定说学者们对强人工智能体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拥有采取的是一种先验逻辑假设,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因而,这种拟制“缺乏讨论的基础和前提”(30) 王肃之.人工智能体刑法地位的教义学反思[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5. ,其他部门法也并未构建相应的制度以便利其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之中。此外,与单位相比,人工智能体并不享有类似单位财产权一样可被剥夺的独立民事权利。
其次,将单位增列为刑事主体有充足的社会实践基础,而当前将强人工智能体拟制为刑事主体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实践。在单位(法人)列为刑事主体之前,单位早已实质性地参与到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各国对其也有充足的社会管理经验。就我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单位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之中,人们能够真切感受到其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并逐渐接受单位的存在。另一方面,在1987年,《海关法》首先规定了单位成立犯罪的情形,其后在12个单行刑法中也先后作出有关单位犯罪的规定。这些在先的立法实践都为1997年立法机关将单位新增为刑法主体积累了充分的立法实践基础和经验来源。
强人工智能体刑事立法面临的现状则正好与之相反。一方面,强人工智能体时代尚未到来,更不用说其真正有效地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之中。由于其缺乏客观存在实体,人们对强人工智能体的认知也都还处于想象和摸索阶段。另一方面,其他部门法对强人工智能也都还处于理论探讨阶段,更谈不上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构和出台,相关社会管理经验也处于空白状态。总之,与二十多年前将单位拟制为刑事主体相比,当前的强人工智能体刑事立法缺乏必要的社会实践基础和部门法立法基础。
最后,从社会效果来看,将单位拟制为刑事主体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而若将强人工智能体也拟制为刑事主体,其带来的后果则正好相反。正如有学者指出,1997年《刑法》一改1979年《刑法》从根本上否定单位犯罪的做法,“对单位犯罪不厌其烦地进行规定,主要是出于一种现实需要”(31) 周光权.新刑法单位犯罪立法评说[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2):34. 。而这一现实需要实际上也就是为了提高社会效率、社会经济发展,这也成为了立法机关在修订1997年《刑法》时增设单位为刑法主体的深层次经济动因。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技术,其极大推动了社会现代化脚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未来社会经济进步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而在民商事等前置法律规范尚未规定强人工智能体法律地位之前,便将强人工智能体拟制为刑事主体,让刑法成为规制人工智能领域社会实践的“急先锋”,这无疑会限制和束缚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人员的创新激情和研发热情,并可能会直接导致人工智能技术社会经济方面功能的发挥。此外,在民商法、行政法等前置部门法应对机制尚未建构的前提下,刑法学者便率先肯定其刑事主体地位,还会扰乱当前的社会经济活动秩序,阻碍经济的发展。这也与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人类中心主义基本立场相违背。
作为一名80后农村小学校长,我在工作中也有很多困惑和压力。但是,我没有气馁,巧释工作压力,带领学校不断前行。
由上可见,从强人工智能体的本体构造到社会实践基础再到社会经济效应等三个方面来看,强人工智能体与单位之间并不具有可比性。因而,那种主张类比借鉴单位犯罪的立法实践而承认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的主张缺乏合理性。
五、结语
刑法拟制确实是建构强人工智能体刑事主体地位的理想途径,但刑法拟制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创造”。面对风起云涌的新一轮人工智能热潮,“刑法学应遵从固有的‘沉稳’与‘谦抑’品格”(32) 时方.人工智能刑事主体地位之否定[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6):74. ,刑法学者也应冷静地看待。伴随人工智能技术而来的社会问题绝不仅仅局限于刑法领域,更是无法通过赋予其刑事主体地位、增设一些新罪名、增设几种新刑罚种类便能解决的。展望未来,强化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构建起包括刑法在内的多元社会治理体系才应当是未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可行出路。
A Research on the Criminal Subject of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wo Aspects
ZHANG Cheng-dong
(Criminal Justice School i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China )
Abstract :The negation of the criminal subject status of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be carried out at actual level and ought level.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cks the cognitive factors and identification factors that should be possessed by criminal subjects, neither produce normative consciousness and have no freedom of will, nor commit criminal acts. Therefore, it does not have the actual conditions for becoming a criminal subject.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riminal subject sta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bring the danger of deconstr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criminal law theory. The relevant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also lacks the necessity, and criminal judicial activities can’t be carried out.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ituation,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not be drafted as a criminal subject.In addition, there is no similarity between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ime and unit crime, and we can’t learn from the practice of unit criminal legislation.
Key words :str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iminal subject; actual analysis; ideal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 DF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69X(2019)05-0054-09
DOI. 10.19510/j.cnki.43-1431/d.20190910.001
*收稿日期 2019-06-03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9年9月10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刑法立法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与路径选择研究”(18AFX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成东,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盟刑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学。
(责任编校:肖姗姗)
标签:强人工智能体论文; 刑事主体论文; 实然分析论文; 应然探讨论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