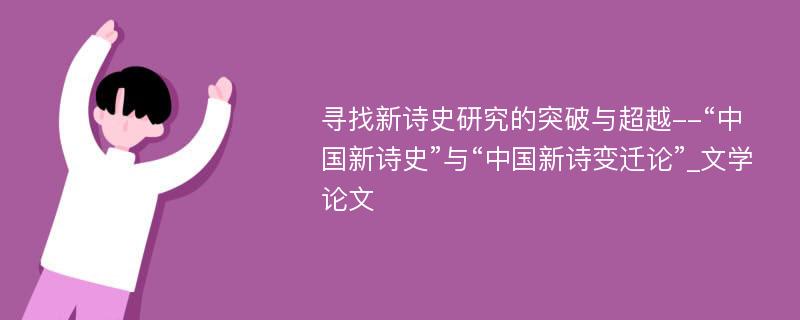
寻求新诗史研究的突破与超越——中国新诗史写作与《中国新诗流变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中国论文,诗史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来看,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30余年中,真正具有新诗史论意味的研究论著,似乎只有草川未雨(张秀中)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北平海音书局1929年版)和蒲风的《现代中国诗坛》(诗歌出版社1938年版)。尽管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代表诗人,张秀中也出版过几部诗集,因而这两部论著,仍具有“诗人言诗”的性质;而且,两部论著还留有结构不够严谨、谐调,阐论不够严密、精细等诸多缺憾,并不能算是成熟之作,更算不上整个新诗史上最优秀的新诗研究成果,但它们毕竟对新诗从诞生至成熟年代的历史发展,作了比较系统的回顾与评述,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体现了新诗研究最初的,试图超越一般的诗歌艺术鉴赏和诗歌现象的平面描述,进而对新诗的艺术发展走向作整体把握的努力,展示了穿越各自时代的宽广、深邃的审美视角。这两部论著主要是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上,而不是在学术水平上,成为后来的这一类新诗研究成果的先导。
新时期以来的新诗研究,也像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十分繁盛。这20余年间出现的新诗史论和新诗流派论的研究成果,已多得难以胜数。其中自然不乏佳篇佳构,其学术水平,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精细程度,恐怕早已超过那两部“先导”了。最近读到的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大约可以算是这“佳篇佳构”中的一部——一部兼有新诗史论和新诗流派论意义的新诗研究力作。
我一直认为,文学史论和文学流派论,可能要算是两种比较重要、比较经典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了。这两种方法分别从纵横两个维度梳理文学史的发展线索,覆盖重要的文学现象,能够比较真切也比较深切地再现文学史的“主旋律”。《中国新诗流变论》就是以新诗史论为“纵坐标轴”,以广义的新诗流派论(包括诗人群论和重要诗人专论)为“横坐标轴”,以将近50万字的篇幅,纵横交织地对30余年间新诗的艺术流变,作了全景式的理论描述,较好地融合了切实严谨的史实考察与深入精细的理论思考,透发出一种与“大部头”篇幅相应的厚重。在这样的“纵横坐标轴”所构成与规划的学术“象限”中,你从任何一个坐标点——任何一个诗人、诗人群、诗歌流派、诗歌现象、诗歌思潮与诗歌运动的研究“断面”,都能感受到一种整体的、历史的理论思考。
在本书的“纵坐标轴”——新诗史论的走向上,作者以史带论,阐发了一系列创见,但在具体的学术操作上,作者又是十分审慎的。如新诗史的分期问题。作者认为,1917-1949年新诗的艺术发展,可以分为4个时期。全书4章的标题以简赅的文字,勾勒了4个时期的主导诗潮和主要特征,即“新诗的草创:白话化运动”;“新诗的奠基:自由化运动”;“新诗的拓展:两大诗潮的并峙与交流”;“新诗的普及与深化:历史大汇合趋势”。这些概括无疑是新颖而精当的。然而,就每个新诗时期的起止时间,就每章所规范的诗歌文学的时代“框架”而言,大体上还是对应了现代文学史通行的分期,即“‘五四’时期的文学”;“20年代(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30年代(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抗战与40年代(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不过,在“对应”与关注主要是由时代历史发展所决定的现代文学史分期的同时,作者又表现出了对于新诗内部艺术发展矛盾运动规律的充分尊重,对于不完全服从历史的规范、有着较大艺术“惯性”的新诗文体个性的充分尊重。这样就尽可能在论著中保存了一个诗歌流派、一种诗歌思潮或一种诗歌运动发生、发展、全盛以至衰落的全貌,不使其轻易为“时期”所分割。所以,对于主要是由闻一多、徐志摩倡导“新格律诗”所引领的新诗艺术形式的“规范化运动”,以及主要是由“诗怪”李金发和后期创造社几位诗人所代表的新诗“象征主义运动”,作者就不是按照通行的做法,把它们纳入“20年代文学”时期,而是放置在主要是由30年代的诗歌思潮和诗歌现象构成的本书的第三章,与“普罗诗派”、中国诗歌会这样一些通常被认为是崛起于30年代的诗歌流派和诗人群对举。从本书第三章的目录编排中,我们可以约略窥见作者为这一“结构调整”所进行的“可行性论证”。那就是作者认为,这两个诗歌运动与30年代“并峙与交流”的两大诗歌潮流之一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有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而且,无论是“新月”诗派还是初期象征诗派,其主要诗人的创作和理论活动,其总体美学风格的发展流变及其作为流派、诗潮的艺术影响,也都迁延至30年代以后。因此,作者的这些“调整”,我认为是对新诗艺术发展的轨迹作了认真细致的历史考察之后进行的,是有一定的艺术史实和理论史实支持的创见,并非故作惊人之举。也许正是有鉴于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文学史分期的新的设想,即将现代文学史的“30年代”的起点,提前到1925年。这一设想是否可行,当然还可以也需要讨论,还需要在对整个现代文学思潮的流变,对其他文体的创作与理论批评活动做进一步考察的基础上进行充分论证。
在本书的“横坐标轴”——广义的流派论层面,作者对30余年间比较重要的诗歌流派、诗人群、诗歌思潮和诗歌运动,都作了比较精细、比较深入和相对全面的研究。这就使得史论的线索不但清晰可辨,而且显得丰富充实。作者不仅沿着史论的线索,从艺术流变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学术界谈论较多的那些诗歌流派、诗歌思潮和诗歌运动,阐发了新见,而且依据对新诗历史发展状况的再认识、再思考,提出了30年代的新诗坛上客观存在着“密云期”诗人群:40年代的新诗坛上客观存在着“延安诗派”的新说。作者在“密云期”诗人群代表诗人臧克家、田间、艾青的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了他们作为一个诗人群所共同作出的提高了现实主义诗歌整体艺术水平的贡献。对于“延安诗派”,作者指出,这是一个“以政治为纽带的诗歌团体”,因此,这里的“延安”,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了。这个诗歌流派,应是包括了此前一些研究者们所论及的“晋察冀诗派”在内的,“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及由此不断向四面推进的解放区的诗人,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与工农密切结合的新型的诗歌群体”。“密云期”诗人群与“延安诗派”的提法能否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可能还有待时日的检验,但作者在发掘、评价史料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深入研究,以及其中所透发的敢于阐发新见的探求精神,我认为是值得称许的。
“纵横坐标轴”的交错,构成了新诗成立之后的“奠基”、“拓展”、“普及与深化”三个诗歌时代。作者认为,郭沫若、戴望舒、艾青,是这三个时代的代表诗人(用如今流行的说法,或可称为首席诗人、形象诗人)。他们的诗歌文学活动集一个诗歌时代之大成,他们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和理论思考,对新诗进行了三次大的整合,促进了新诗艺术的自由与自觉,推动了新诗的双向竞争、互补与超越,以及诗与历史全方位的对话。诚然,这些论断都还只是一家之言,要读者接受或修正、补益这些结论,都还需要一些分析、思考的时间。但我相信不少本书的读者,都不能不为作者严谨、丰富、深入而富有激情的论述所折服。作为完整的学术活动,我想结论恐怕并不是惟一的节目,甚至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节目。
作为一部“全景式”的新诗研究论著,本书作者不但对1917-1949年的新诗作品和新诗批评、诗歌理论史料作了相对全面的、大规模的综合与集成,而且广泛阅读、参考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严格说来也属于“历史本文”的新诗研究论著,使得作者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重复劳动”,不仅是站在巨人,同时也站在了众人的肩上登高望远——其实,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基本要诀之一,只是作者用更清晰的形式,把这种方法、要诀明确化了,这就是用页下注的方式,一一注明那些在读者,尤其是本学科学术圈内的读者眼中似曾相识的看法、论述的具体出处。这种坦诚的学术品格是值得钦敬的。本书在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厚重的学术专著的同时,实际上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同样具有“全景”意味的,近15年间新诗研究的综述与引得。
不过,在作者提供给我们的,每个部分都显得严谨而妙曼的学术乐章中,我们仍然不难品鉴出其中的“华彩乐段”。那就是书中40年代诗歌的研究,显然要比其他部分的论述更加流光溢彩。例如,作者认为,40年代新诗的“散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时新诗普遍的“非诗化”倾向;“延安诗派”的诗作由于更多的非诗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从诗的范畴淡出,而更多地属于社会历史范畴;40年代诗歌表现出日益公众化、功利化趋向与坚守诗人的内心世界、经验世界的对立,以及诗歌日益意识形态化、非诗化与坚守、开拓诗歌自身生存空间的对立,而有成就的诗人的特点,正在于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平衡的张力;40年代诗歌有着比二三十年代诗歌更多的缺失和不足,但从总体上看,其成就并不让于此前新诗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诗歌的群体实力与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保证了诗歌质量一定程度的提高,等等,等等。这些美学评价和历史评价,我以为都是中肯的,精当的,也是比较独到的。这可能与作者曾在一段时间内,比较集中地研究过40年代诗歌,尤其是发掘、整理、编纂过40年代新诗批评、新诗理论史料不无联系。我们可以悬想当年作者在尘封的、发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发现所需史料时的惊喜、兴奋的心情;在翻阅史料的载体——旧报刊时,由当时的时代环境信息所产生的联想;还有这样的心情和这样的联想所激发的学术灵感和顿悟。而面对别人整理好的史料,恐怕是难有这番情景的。或许正是当年的一些灵感与顿悟经过长时间的孕育,才凝结为本书中的一部分文字珠玑。
当然,即便是“华彩乐段”,也还不可能字字珠玑。有些论断似乎还值得进一步推敲。例如,在本书的“结语”中,从“开放性、多元性、先锋性、民族性、创造性”等5个维度概括新诗的现代性特征,是否准确?尤其是“民族性”和“创造性”,是不是新诗现代性的特征?在我看来,至少很难说是显性特征。而且在不少时候,我们更习惯于将“现代性”与“民族性”对举。还有,作者在论述新诗对传统的承传与变异时不乏精深的见解,但有些说法似乎也还不够周全。比如,“中国新诗的最高审美追求”是否完全“由‘意境’转向了‘意象’”?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构思方式的不同,是否一定会造成前者“能使人在形而下的沉浸中获得美的欢愉与净化”,而后者“则更注重形而上的指向”这样大的审美的以至哲学的落差?这些,好像都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不过,指出这些并不意味着对这些论断的简单否定。相反,对于其中蕴含的作者的不倦探求、独抒己见的胆识和精神,我是充满敬意的。况且,这些论断即便稍有片面性,那也是一种“深刻的片面”。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深刻的片面”也许比“平庸的全面”更有意义。
总之,这是一本值得认真研读,难能可贵的新诗研究论著。在学术风气像世风一样不甚踏实,学术研究也开始日渐媒体化的今日,作者愿意耗费大量的时日、精力乃至心血,青灯黄卷,孜孜矻矻,完成了这样一部很难引发新闻效应、轰动效应的“大部头”学术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耗费不菲的人力、物力,出版这样一部很难畅销,很难被炒作,因而也很难带来很大经济效益的书,都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