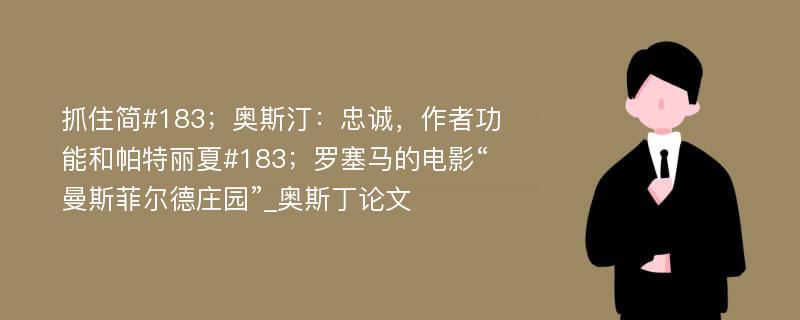
把握简#183;奥斯丁:忠实性、作者功能与帕特里夏#183;罗泽玛的影片《曼斯菲尔德庄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园论文,菲尔德论文,忠实论文,帕特论文,影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00年5 月《新标准》杂志登载了澳大利亚作家兼史学家基思·温德沙特尔题为《改写大英帝国历史》的文章,文章以讨论帕特里夏·罗泽玛1999年的影片《曼斯菲尔德庄园》开篇。温德沙特尔首先提到影片开头“原书中所没有的”一个场面(第1页),表现10岁的范妮乘马车从朴次茅斯到曼斯菲尔德,听到停泊在海岸边的船上有人唱歌。马车夫说:“这是贩运黑奴的船,小姐。”接下来温德沙特尔的评论有必要引得稍微长些:
这是一艘贩奴船,它是要告知观众,这场戏发生的时代,即1800年前后,英国仍然是一个从事奴隶买卖的国家。同时这也是一个预兆,暗示女主人公最终将会看到的恰是她这个新家的阴暗面。众多热爱简·奥斯丁的读者多半会对影片这样擅自改动小说感到不快,因为这样就把一个有争议的政治性话题强加在他们心爱的作者的一部原本是描写家庭事务的作品上了。而且,读者只要有些历史和地理知识,还会发现这个场面有些不伦不类。朴次茅斯是位于英吉利海峡的一个港口,而当时的贩奴船走的是“中央航路”,即从非洲几内亚海岸直接横跨大西洋前往美洲。跑到英格兰海岸的某个地方,就偏离航线几千里了。
片中之所以有这样一场戏,是因为文学评论家爱德华·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使许多读者相信,《曼斯菲尔德庄园》及其作者与加勒比群岛的奴隶制度和帝国主义问题有着很深的牵连,正是那里的甘蔗种植园给一些英国的大庄园,包括小说中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第1页)。
就是说,温德沙特尔指责罗泽玛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理由是,它既“不忠实”于历史的事实,又“不忠实”于文本的“真实”,即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描写家庭事务这一实质”。关于前一种“不忠实”,只要粗粗浏览一下彼得·弗赖尔论证确凿的著作《持久的耐力:英国黑人史》,就足以推翻这项指责。弗赖尔证明,在整个18世纪,经常不断有黑奴被一些贩奴船长、回国的种植园主、政府官员、陆海军军官带到英国(第67页)——正如罗泽玛影片中马车夫指给范妮看的那样,并且在一些贩奴港口——其中当然也包括朴次茅斯(第58—64,50—52页)——公开进行奴隶交易。不过,温德沙特尔的历史感遭到了触犯,因为他认为,蓄奴制和“帝国主义行为”都是早已过去的事,只有“后殖民时代的文学评论家和从事文化研究的学究们”才顽固地坚持认为这类问题对于当前大到历史、文化、文学的讨论,小到对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解读具有中心价值,从而扭曲了这部小说的“实质”意义(《改写》,第2—3页)①。
二
实际上,本文下面将要讨论的主要是第二种“不忠实”——“不忠实”于文本的“真实”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学者们对改编问题的研究明显地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随之使得“忠实性”成了一个人们熟知的概念,特别是涉及古典作品方面的一部重要的、广被引用的著作是布赖恩·麦克法兰的《从小说到电影:改编理论入门》。众所周知,麦克法兰的著作在质疑把忠实性作为评价影片改编的首要标准这一点上起了很大作用。他正确地指出,“忠实性评论依据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文本具有并且向(有理解力的)读者提供一个惟一的、准确的‘含义’,电影导演只能要么是遵守这一‘含义’,要么是在某种意义上违背和篡改这一‘含义’”(第8页),然而这个观念已经遭到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彻底否定。而且,只盯住忠实性一点,也会模糊了对改编研究中其他重要问题的注意,例如应该区分“……有些东西是可以从小说转移到电影中[转换],而有些东西则需要进行更为复杂的改编(真正意义上的改编)”(第10页)。不过,麦克法兰这个以转换与真正意义上的改编间的(有疑问的)区分作为基础的叙述学方法已被内尔莫尔(第9页)和惠兰(第9—11页)证明是狭隘形式主义,因为它贬低了文化和产业条件对改编过程的影响。诚然,尽管麦克法兰认为“忠实性评论……势必以小说占主导地位为前提来读解和评价影片”因而极力反对普遍搬用忠实性标准(第197页),但是他所提出的改编研究方法确实专注于叙事性的问题——因而归根结底也就是专注于原著文本——因为叙事性问题是可以从形式上加以分析的,这就损害了其他方面,即文化的和产业的条件,因为这些“是难于用常规的方法论加以分析的”(第22页)。
为了使讨论上升到更有实际效用的层次,希恩近来提出,对于某些忠实性评论来说,肯定是有发挥余地的,就是不要采取形式主义的角度,而是去分析“……[忠实性标准]是如何在具体的感受过程中起作用的”(希恩,《当服装……》,第15页)。换言之,对于一部改编作品是否“忠实”的这种反应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评论的现象,特别是被感受为“不忠实”的那些改编作品何以常常引起“无端的敌意”(希恩,《导论》,第3页)——例如上述温德沙特尔对历史的误读。希恩主张,忠实性评论应被视为“一种占有的表示”(《导论》,第3页)。 文学评论界通过表述其特有的改编方案,即对文本的阐释,主张他们对文学文本,特别是古典作品的文本的“所有权”。把自己确立为文本“真实含义”的“当然”捍卫者,于是就可以否定任何看起来“不忠实”于它的改编方案——忠实性评论因此同时也就是“失落的声明”(《导论》,第3页)。
三
温德沙特尔对罗泽玛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议论可以视为忠实性评论既是占有的表达又是失落的声明这种表述行为的绝好实例——他声称,这部影片“把一个政治性话题”,即蓄奴制,“强加在原本是描写家庭事务的作品上”,从而误读了原著。温德沙特尔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反对罗泽玛《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大合唱,说影片是对奥斯丁小说的歪曲和背叛。按这种观点,《曼斯菲尔德庄园》及其女主人公的“真实含义”就是托尼·坦纳(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序言,第7 —36页)和莱昂内尔·特里林等这样一些权威评论家所解释的——斯拉高的意见实际上是引用了坦纳为《曼斯菲尔德庄园》企鹅版所作的序言。从这个角度来看,《曼斯菲尔德庄园》确实是描写家庭事务的小说,其中缺少简·奥斯丁特有的冷嘲热讽,其中的范妮乃至那个庄园本身体现的,是处于一个崇尚运动、行为,盛行口是心非、装腔作势的社会中所坚持的静止、固有和恪守原则的价值观。所以罗泽玛的影片就要因“不忠实”于上述读解而受到指责了。有人说,影片“不忠实”地把蓄奴制说成伯特伦家财富的来源,突出了性爱关系,并把范妮变成一个言语尖刻、想法怪异、神情不屑的女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温德沙特尔引用的赛义德的话恰好使人想到他力图否定的——也是令人惋惜地被希恩在她关于忠实性评论的讨论中(《导论》)忽略了的一点,即对《曼斯菲尔德庄园》也可以有另外的读解。诚然,当涉及古典作品时,“改编过程……本已因围绕原作文本存在种种解释而增加了难度,这些解释都可能对影片制作中的重大处理提供启示”(惠兰,第7页),所以了解那些变化不定的评论反应可以说是研究改编问题者的一个“合理关注领域”(惠兰,第14页)。但是,温德沙特尔对赛义德的援引却是一种误导。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是要证明《曼斯菲尔德庄园》比表面看来“更着意于说明帝国主义扩张的根本原因”(第100页),而影片制作的着眼点似乎并不在此。实际上,正如导演本人承认的,影片得益最多的不是赛义德,而是玛格丽特·柯卡姆1983年在她的成名作《简·奥斯丁:女权主义与小说》中对这部小说的女权主义读解。
如大家所知,柯卡姆把简·奥斯丁的小说看做是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② 的《为女权辩护》(1792)一样的启蒙运动反浪漫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在谈到《曼斯菲尔德庄园》时,她坚持认为“……这本书远非20世纪众多评论那样,把它说成的是一部保守主义的清净无为的作品,而是体现了简·奥斯丁对当时社会与文学中的偏见最强烈、最激进的批评”(119页)。 她的论断是基于对小说中讽刺性暗喻和反论方式的仔细考察而得出的,有力地证明了,除其他各点以外,“简·奥斯丁采取了《辩护》一书中使用过的以殖民地的奴隶与国内的妇女,特别是已婚妇女相类比的手法”(第117页)。她指出,小说题名暗指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他曾在1772年裁定奴隶不可强制从英国送回加勒比海岛,引起了持久的争议,因为这一裁决被一些人解释为意味着英国实行解放奴隶政策,而与此同时在英国仍然存在贩奴活动和蓄奴制度(柯卡姆,第116—118页;弗赖尔,第120—126,第205页)。她还证明,奥斯丁熟知18世纪末人们普遍认知的反对贩奴的理由以及这些理由导致1807年通过废除(英国奴隶贸易)法案的经过,而且在酝酿《曼斯菲尔德庄园》故事情节过程中读过托马斯·克拉克森③ 的反蓄奴小册子《废除非洲奴隶贸易的兴起、进展与实现的历史》(1808)。小说时间始于1808——或1781,如果把玛丽亚·沃德与托马斯爵士结婚算作起点的话——而止于1809,使得这些暗指极度可信。
不必说,柯卡姆对《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这种读解被随后的评论引申和/或质疑。例如,在莫伊拉·弗格森的读解中,范妮对托马斯爵士所代表的种植园主价值观的态度是摇摆于“……两种对立意向——同谋和反抗——之间”(第73页),而柯卡姆强调的则是后者。与此同时,弗格森还进一步证明,《曼斯菲尔德庄园》可以读解为在当时关于蓄奴制的讨论中起调解作用——例如诺里斯太太的姓就使人想起当时蓄奴制最强硬的拥护者之一约翰·诺里斯④ (第70页),这个名字奥斯丁一定能在阅读克拉克森小册子时知道。另外,也像柯卡姆一样,弗格森从小说中发现了一个重要时刻,即对蓄奴制批评非常古怪地通过沉默,“死一般的沉默”(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第213页,着重记号是我加的)而强烈地表达出来,这就是在托马斯爵士从安提瓜回到国内不久,范妮对他就奴隶贸易的一次贸然质疑时所面对的沉默(柯卡姆,第118页;弗格森,第85页)。恰恰是针对议论纷纭的奥斯丁的沉默,朱利安·诺思(第40页)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20世纪90年代末,学术评论界已明显表现出“对保守的奥斯丁的不耐烦”,那么,现今的各种改编作品通过把她的节略、暗喻和间接议论变成明白的表述而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这种不耐烦呢⑤?她就李安的《理智与情感》(1995)以及像BBC在1995年拍摄的《傲慢与偏见》等当今对奥斯丁作品的改编得出结论说,它们“……利用了[奥斯丁]作品的颠覆性,但更是利用了它可以十分安全地包装起来这一事实”(第49页),从而也就模糊了这些小说更为激进的一面(第46页)。如果我们对罗泽玛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提出同样的问题,那么我们立刻就会涉及改编问题研究者的另一个“合理关注领域”(惠兰,第14页),即不同改编作品(例如同一作者的)之间的同步比较,以及寻求其作品在观众中获得不同程度成功的合理解释(惠兰,第15—17页)。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忠实性”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
李安的《理智与情感》明显是“不忠实”于原著文本的,尤其是对爱德华·费拉尔斯和布兰登上校的“浪漫化”,增加了两对新人结婚的终场庆典,或者还略去了玛丽安生病时威洛比夜访埃莉诺的情节。然而《理智与情感》的“不忠实”,却与《曼斯菲尔德庄园》不同,没有引起任何骚动,相反倒是赢得了广泛的赞许,而且获得了出乎意料的票房成功⑥。按照希恩的先例,我们在这里也不妨问一下,当评论家们承认《理智与情感》对奥斯丁原作的“不忠实”是无可指摘的时候,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把握方法呢?据说,李安的影片具有安德鲁·希格森称之为“遗产电影”(1993,1996,1997)的主要特征。所谓“遗产电影”就是一系列当今高档古装电影,大多改编自古典文学原著,其特别突出的视觉场景和怀旧情绪最终压过了叙事中往往表现出的嘲讽意味和社会批评(希格森,《再现》第119—120页)。这也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理智与情感》在评论界和观众中全面大获成功的原因吧。
与此相反,罗泽玛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则显然背离了“遗产”的美学;据说这种背离就是因为影片极力要直接表达出奥斯丁避而不谈的和间接说明的一些东西。奥斯丁作品的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克劳迪娅·约翰逊⑦ 在她对影片的评论和电影剧本出版时的序言中都指出,虽然罗泽玛启用了曾为李安拍摄《理智与情感》的同一位摄影师迈克尔·库尔特,但效果却惊人地不同:在无人居住的柯尔比厅拍摄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宅邸……色调主要为乳白和黄色,给人以冷峻的感觉,有时几乎没有什么陈设,而且破旧不堪,仿佛因支撑这所豪宅的那些罪孽而变得惨淡凄凉⑧,……(《发疯》,第16页;另见约翰逊为罗泽玛的电影剧本写的序言,第34页)。奥斯丁小说用暗喻或有时通过沉默来表现的蓄奴制在影片中就被直白地说了出来。它通过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衰败景象和前面提到的贩奴船的出现而被突出出来。此外,罗泽玛把故事时间设定在1806年,而不是小说里的1808或1809年,即发生在废除贩奴贸易之前,而且让埃德蒙提醒范妮说他们的日子就是靠贩奴的赢利所得而维持的。有那么短短的一瞬间,当全家人安逸地听玛丽·克劳福德演奏竖琴的时候,我们瞥见了一个黑奴的雕像。影片还表现了范妮从汤姆的速写里看到殖民者——包括托马斯爵士在内——粗暴地对待奴隶时的惊骇,以及范妮援引曼斯菲尔德的裁决和克拉克森的小册子反驳托马斯爵士的蓄奴观点,而托马斯爵士则干脆不理会她的话,而是赞美她肤色和身材保养得很好,并建议举行一次舞会把她推向“婚姻市场”⑨。所有这些无疑都突出强调了被柯卡姆认为是小说核心内容的对托马斯(专横)行为的有力批评。
在影片被指责“不忠实”于原作的另一方面——对性爱的表现,“奥斯丁影片中必不可少的”舞会场面也没有被拍摄成“摄政时期风格的大场面,而……像是近于私密的场景,表现范妮对自己身体快感的最初觉醒和几对主要人物之间性爱方面的连环关系”,即影片中把性爱表现为一种“令人痴迷的”体验的那一部分(约翰逊,《发疯》,第17页)⑩。在这里影片谨慎地表现了埃德蒙对范妮和玛丽两人的双重的吸引;玛丽亚对克劳福德的激情以及她如何拒绝她父亲提出的取消与拉什沃思的婚约的想法:范妮无意撞见玛丽亚与克劳福德两人在床上;范妮在朴次茅斯接受克劳福德的求婚,次日早晨又反悔(11);以及当然还有范妮与玛丽·克劳福德两人引人注目的“女性同性恋”场面(12)。约翰逊认为肯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许多观众在BBC 的《傲慢与偏见》里看到科林·弗思超出原著的暴露表演时曾经大为快乐,而现在却谴责罗泽玛的影片,说是奥斯丁作品中根本没有性爱描写,然而这个判断用于《曼斯菲尔德庄园》恰恰是极不恰当的,因为这部作品里有着许多受挫的、不正当的、反复无常的或变化多端的性爱(《发疯》,第17页)。
但是,对罗泽玛影片在性爱关系描写方面的责难并不仅仅像希恩所说的代表着关于如何把握——即从真正意义上并恰当地读解奥斯丁这本小说的歧见,而且,据我看来,这种指责还暴露了如何理解作者即简·奥斯丁本人的论争。
四
上述围绕罗泽玛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对“忠实性”问题的讨论,包含着一种类似约翰·威尔特希尔在《重塑简·奥斯丁》一书中(第5—7页)提出的对改编作品的见解,即把改编看做是对原作文本的读解,可以像评论一样说明阐释过程本身的性质。罗伯特·斯塔姆也主张“读解”应是一种说明性的转义,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巴赫金的互文对话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忠实性’的难题”,把改编不是看做试图复活“原作文本”,而应看做是“不断进行的对话过程中的又一轮”,其中“每一文本都构成不同文本面的交叉”。从这个角度来看,罗泽玛的影片,如我们已经表明的,是对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一种回应,它在互文的方式下接受着以前的各种回应——不管是对小说的评论或对这部小说,以及奥斯丁其他小说的电影改编——的折射。这样就反过来打破了关于“忠实性”以及把改编看做是原著文本与影片之间只能是一对一关系的僵硬的形式主义的观念(13)。
因此,我认为,首先罗泽玛的影片所读解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曼斯菲尔德庄园》,而且还包括《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作者——这个文化偶像兼文化作品的“简·奥斯丁”(14)。正如有人已多次指出过的,这部影片突出表现了原作者的在场(15)。这首先是通过把小说的充满讽刺意味的语调附加在范妮身上,例如当她对着镜头念那封给她姐姐苏珊的信时,她直接说出了叙述者对玛丽亚·伯特伦嫁给拉什沃思这件事的尖刻评论:“她已经做好一切重要的思想准备:为了全家人的憎恨,为了一场破灭的爱情的痛苦,为了她要嫁的那个人的轻蔑而准备好接受这宗婚事”(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第216页;罗泽玛的电影剧本,第70页)。除此之外,范妮还表达了奥斯丁本人对蓄奴制的看法,而片头字幕标明的原著不仅是《曼斯菲尔德庄园》,还有奥斯丁的“早期纪事”(少年时期习作)以及她的书信。其结果如前文已经提到的,范妮从一个弱不禁风的、羞涩内向的文学爱好者被改变成为一个精神焕发的年轻女人,她本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而她所写的东西则是摘自奥斯丁的书信和她早期滑稽放肆的文字片段,其中很多由她直接面对镜头朗读出来(16)。影片实际上是以突出范妮就是“奥斯丁”来作为开头和结尾的。在开头字幕衬底场景里是10岁的范妮向苏珊讲述《爱情与友谊》的片段,而在影片结尾是一系列场景简要地表现动作,同时以范妮的画外音交代出各个角色的命运,并反复用调侃的口吻说出:“我以为,事情本可不是这样……但结果就是这样了。”这句话与片中范妮先前面对镜头念出的奥斯丁本人在《英国历史》中评论圣女贞德的那句“他们本不该把她烧死的,但他们就是把她烧死了”(奥斯丁,《凯瑟琳》,第135页)形成相互呼应。随后是范妮与埃德蒙商量她的作品的出版事宜, 而这里提到的出版商恰恰就是出版奥斯丁本人作品《理智与情感》(1811)、《傲慢与偏见》(1813)和《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的出版商埃杰顿(17)。至于性爱关系方面,范妮对克劳福德先是接受后又拒绝,这与奥斯丁本人生活中关于比格—威瑟那段插曲(勒·费伊,第497页)非常相似,那些带有“女性同性恋”意味的场景可能是在1995年8至10 月间在《伦敦图书评论》通信栏展开的关于奥斯丁性爱关系的热烈讨论的背景下形成的(18)。那场讨论是由特里·卡斯尔对迪尔德丽·勒·费伊编的奥斯丁书信集1995年修订版的一篇评论而引起的,卡斯尔对那些书信从奥斯丁对女性近于同性恋的强烈好感和她与她姐姐卡桑德拉近于同性恋的极度亲昵关系的角度做了读解。
罗泽玛影片中对原作者的存在还提出另一些问题,正当后结构主义评论与审美理论强烈质疑关于作者在文本背后超验存在和作者是单一含义的终极来源的观念的时候,这些问题显得特别令人感兴趣。在这方面,约翰·考伊在《作者理论文集》中声称需要有一种“更新的”作者理论,“充分考虑作者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地位……并从概念上把握作者作为文本修辞的成分之一如何起作用,以及我们如何运用这一成分……进行读解并获得愉悦”(第1—2页)。现在,罗泽玛的影片清楚地——而且又是以互文的方式——表明了它在对奥斯丁作品所感受的历史中的姿态,采取了这样一种立场,没有把“简·奥斯丁”理解为斯文高雅、正派体面、热爱家庭、清静恬淡的同义语——一个“悲歌传统”的,终身未嫁的名门闺秀、一本正经的“奥斯丁”(约翰逊,《姐妹之间》,第4页),而是一个更具叛逆性的、十分激进的、女性主义的、鼓吹“反常规”或进步传统的社会评论家(第4页)。影片在范妮身上赋予了《曼斯菲尔德庄园》那种嘲讽的叙事语调和“少年时期习作”那种活泼的调侃,或者按考伊的说法,从概念上把握作者在其文本修辞上的存在及其所产生的功用,正是这种读解“简·奥斯丁”的方法的一部分和主要内容。这使我最终考虑到愉悦的问题并且在绕了一个圈子之后再次回到温德沙特尔以及其他极不喜欢罗泽玛影片的严厉批评家的评论。他们的反应意味着,请考伊先生原谅,恰恰不能说愉悦是一种人人皆有的体验,而且,罗泽玛的影片在重构《曼斯菲尔德庄园》和“简·奥斯丁”时为她的一些——但显然不是所有——读者和批评家提供愉悦的同时,无疑是在做着它自己的阐释行为。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恰恰是这部影片张扬了这一事实。与近年其他据奥斯丁作品改编的影片不同,罗泽玛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以自白的方式指明其互文性质,表明它是对当前有关奥斯丁和有关作者功能讨论的一次介入。最重要的是,它明白无误地承认,改编过程本身必然是基于一个读解和“不忠实的”把握行为之上的(19)。
注释:
① (温德沙特尔另著有《扼杀历史:文学批评家与社会理论家怎样抹煞我们的过去》(2000)。他是《新标准》杂志的经常供稿者,这份杂志则自称是“在当今搅动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战争中美国最先锋的持异议的声音”。
② 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英国女作家,以争取妇女在教育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而闻名。《论妇女教育》(1787)和《为女权辩护》是她最主要的著作。
③ 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1760—1846),废奴主义者,英国反奴隶贸易和反蓄奴制运动早期的重要政论家之一。——译者
④ 诺里斯(John Norris,1657—1711),英国基督教圣公会牧师和哲学家。——译者
⑤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尔的《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提出了一种见解,认为奥斯丁的小说在其“保守的”外表下面包含有一系列“隐蔽的”含义。塞尔斯认为,“她们的论据虽有不少破绽,但她们确是坚持把注意力集中于以前被忽视的问题和人物身上”(引自《简·奥斯丁》,第92页)。
⑥ 该片成本1550万美元,在美国收入4300万美元,全球收入12500万美元。该片还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爱玛·汤普森)和英国电影电视学院三项大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爱玛·汤普森)和最佳女配角(凯特·温斯莱特),以及其他重要奖项。而《曼斯菲尔德庄园》成本为1000万美元,在美票房收入470万美元(http://us.imdb.com)。未获重要奖项。
⑦ 见她的著作《女性、政治与小说》(1988)。
⑧ 演员的选配也隐含着挑战“传统的”奥斯丁的意图:如果说1996年的英国观众可以划分为“重演技”和“重原作”的两派,那么罗泽玛则通过选配演员而打破这种两分法的格局,他起用“重演技”的琼尼·米勒扮演埃德蒙·伯特伦,由澳大利亚女演员弗朗西丝·奥康纳扮演范妮,哈罗德·平特扮演托马斯爵士,林赛·邓肯扮演伯特伦太太和弗朗西丝·普赖斯两角,还有亚历山德罗·尼沃拉和恩伯思·达维兹分别扮演亨利·克劳福德和玛丽·克劳福德等等——用导演自己的话说,总之不是“通常预期”的“传统”改编组合。
⑨ 如果说片中有一处历史的失误的话,那么可能就在这个方面:影片背景设定为1806年,而克拉克森(1760—1846)著名的反蓄奴制小册子出版于1808年。不过,范妮并没有具体提到这本书,而克拉克森从1780年代中期(弗赖尔,第56页)就一直积极从事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这里,把小说中两个不同场景——范妮对蓄奴制的突然质问(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第213 页)和托马斯爵士建议在庄园举办舞会(奥斯丁,《曼斯菲尔德》,第260页)——合在一起, 同样像柯卡姆所说的,正是把奴隶的处境与妇女的地位做了一个并列的对比。
⑩ 作为对比,可参看1983年BBC拍摄的“经典”小型连续剧《曼斯菲尔德庄园》(导演:戴维·贾尔斯)中的舞会场面。该片是在罗泽玛影片之前惟一一次将奥斯丁这部小说搬上屏幕。
(11) 按照小说,范妮最后终于会接受克劳福德的求婚(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第451页)。
(12) 第一个这样的场面是,在排演《情人的誓言》时玛丽搂着范妮的脖子,故意让埃德蒙看到他不参加戏剧表演的结果是错过了多好的美事。后来,在牧师住所,她一面催促范妮说到埃德蒙,一面热心帮助范妮脱掉湿衣服。
(13) 而且,互文观念还对把原著文本看做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立自在的“原始文本”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如我已经表明的,按照柯卡姆等人的意见,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本身就可读解为是对妇女与奴隶以及其他重大问题争论的对话式暗示或回应。
(14) 威尔特希尔(第3页)用引号来表示“围绕‘简·奥斯丁’这个名字的一种现象,一种幻象”,他关于简·奥斯丁生平的那一章(第137 页)非常清楚地说明“简·奥斯丁”作为文本怎样继续被人们进行着结构和重构。
(15) 见坎特罗威茨以及其他众多的评论。另见特鲁斯特与格林菲尔德(第193页)。
(16) 影片采用的片段分别取自《弗雷德里克与埃尔弗里达》、《亨利与伊莱札》、《爱情与友谊》和《英国历史》(奥斯丁的《凯瑟琳》,第3—10、31—37、75—101、134—144页)。约翰逊还指出若干文字取自书信(罗泽玛,第6页)。
(17) 试比较最近两部“正统”奥斯丁改编影片:李安的《理智与情感》和BBC1995年的《傲慢与偏见》结尾的婚礼场面,却没有人指责“不忠实”,尽管事实上奥斯丁这两部小说的最后章节“……并没有写出婚礼场面,而只是概括地述说了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倒是对他们后来是否幸福表示了一些担心和预测”(诺思,49页)——这与罗泽玛影片结尾场面的精神倒是非常吻合的。
(18) 对这些场面也可从罗泽玛本人创作经历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她素来是一位关注女性同性恋问题的独立导演(《我听到美人鱼在歌唱》[1987],《当夜幕降临》[1996]。)罗泽玛“转向”奥斯丁也许是她本人导演特性形成过程的一部分。
(19) 感谢马蒂娜·安琴格和托马斯·利奇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中肯意见,而且总的说来对他们在第403 届萨尔茨堡讲习班上积极参与奥斯丁作品改编问题讨论的热情深表钦佩。那届讲习班的主题是:“从书面到银幕: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于2002年9月10—17日在萨尔茨堡附近极其迷人的利奥波德城堡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