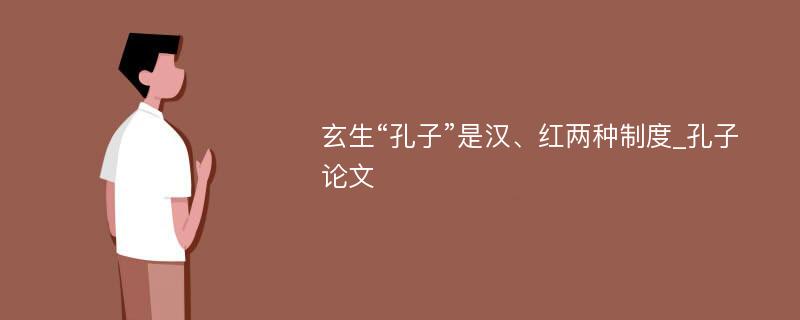
“玄圣”孔子“为汉赤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玄圣论文,汉赤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5;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8)04-0124-08
在历史上,孔子的形象是常常变化着的。梁启超先生曾形象地说过,随着历史的变化,孔子渐渐地变为董仲舒、何休,变为马融、郑玄,变为韩愈、欧阳修,变为程颐、朱熹,变为陆九渊、王守仁,变为顾炎武、戴震。顾颉刚先生也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各个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1] 而周予同先生则在其《谶纬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一文中指出:“两汉以来的孔子只是已死的孔子:他随着经济组织、政治现象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换穿着各色各样的奇怪的服装。”[2] 这些言论,都揭示了不同时代的“孔子”具有不同形貌的事实。历史的真相的确是如此,在汉代,统治者就曾借匿名谶纬家之手,在春秋公羊家说的基础上,把孔子塑造成了“为汉赤制”的“玄圣”。
“玄圣”说的产生,与流行于两汉时期的“尧后火德”说有密切的关系。所谓“尧后火德”说,是一个复合政治文化命题,它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汉家尧后”,意即汉朝天子是古圣王尧的后裔;另一层是“汉为火德”,意即汉朝在五行之运中属德为火。此说从宗法和天道两个方面,来论证汉朝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为了能使这个命题获得广泛认同并深入人心,汉朝统治者请出了在本朝建立前273年就已经逝世了的孔子来帮忙。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如果能通过圣人之口来证明“尧后火德”说的真实性,那么汉家天子树立和巩固自身政治权威的努力就会事半而功倍。
一、孔子为“王”说
《吕氏春秋·贵生》说:“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也。”按照“内圣外王”的理论,圣人在经世意义上被称为“圣王”,而圣王在道德的层面上则被称为“圣人”①。“圣”言其德,“王”言其功。孔子是历史上的最后一位圣人,他虽然不像尧、舜、文、武等先圣那样有过“王天下”的实际经历,但是也同样被认为是“王”。《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便是说孔子的事业与先圣尧、舜、文、武的王者之业一脉相承。根据《墨子·公孟》记载,孔门后学已有尊孔子为圣王的意思流露。该篇提到,公孟子对墨子说:“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孟子·尽心下》开列的圣统是“由尧舜至汤……由汤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
对孔子为“王”说强调得最充分的,莫过于春秋公羊家。他们声称,春秋时代王纲失坠,王令不行,天子名存实亡。这个“天下无王”② 的时代,需要非凡人物以“新王”的身份来重整政治秩序,恢复社会公正;而圣人孔子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是为担当“王天下”的历史使命而降临人世的。孔子是怎样担当这样的历史使命的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缘鲁以言王义”③,即借《春秋》经所记鲁国十二公的历史,阐明“内圣外王”之义。“王鲁”并不是以鲁为王,而是托“王”于鲁史十二公。皮锡瑞在其《春秋黜周王鲁解》中解释说:“隐公非受命王,而《春秋》始于隐,则以为受命王;哀公未尝致太平,而《春秋》终于哀,则以为实致太平。故《春秋》未尝称鲁为王,而据鲁史成文以推其义,则曰王鲁;犹之夫子未尝自称王,而据《春秋》立一王之法以推其义。”
对孔子为“王”的理论,春秋公羊家们还有另外一种表述,这就是“以《春秋》当新王”④。春秋公羊家们说,受命救世的孔子是一介布衣,他既无尺土之封,也无斧钺之伐,只好加“王心”于《春秋》,通过对历史的褒贬来行使天子的赏善罚恶之权,在天下无王的时代确立“新王”的秩序。《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说:“《春秋》上黜夏,下亲周,以《春秋》当新王。”“天子命五常,唯命是德庆,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以《春秋》当新王”,就是用《春秋》所创的义法——“王法”——来治理天下,就是把《春秋》看成是由“新天子”手定的、具有至高无上政治权威的大礼书、大刑书。后来的汉儒以经术缘饰吏事,以《春秋》决狱,均是此理论在现实政治的反映。蒋庆先生说:“以孔子为王,意味着世俗之王之上还有一神圣之王,此神圣之王与世俗之王相对立。世俗之王代表着实然的历史,而神圣之王则代表着应然的历史。”[3]
二、从“素王”到“黑帝后”
说孔子是“圣”,是没有人反对的,因为在道德的层面上孔子的确堪称楷模;说孔子是“王”,问题就来了,因为孔子并无“王天下”的实际经历。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为周密,春秋公羊家们在孔子为“王”说的基础上发明了孔子为“素王”⑤ 说。“素王”,意思是有道无爵者,即空王⑥。《孟子·离娄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汉赵岐注:“窃取之,以为素王也。”可见在《孟子》那里已隐约有孔子为“素王”之义。春秋公羊家阐发此义,于是产生了孔子为“素王”说。董仲舒在其贤良对策中说:“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4] 卢钦《公羊序》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春秋公羊学以孔子为“素王”的见解,获得了汉儒杂家的认同,也获得了与今文经学家立场相反的古文经学家所认同⑦。例如《说苑·贵德》载:“(孔子)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隶释·史臣祠孔庙奏铭》载:“……臣以为素王稽古,德亚皇代。”《论衡·定贤》载:“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论衡·超奇》载:孔子作《春秋》以见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淮南子·主术篇》载:“孔子……勇力不闻,技巧不知,专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风俗通·穷通》载:“(孔子)制《春秋》之义,著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载:“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徐干《中论·贵验》载:“于是(孔子)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仲尼为匹夫而称素王。”《孔子家语》载:“然凡所教诲,束脩以上,三千馀人,或者天将欲与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⑧ 这众多的引文说明,由春秋公羊家所着力阐发的孔子为“素王”之义,在汉代影响十分广泛。
谶纬吸纳了春秋公羊家的“素王”说。《孝经钩命诀》说:“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城之诛,故称明王之道’。”《春秋元命苞》说:“素王授当兴也。”《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在此基础上,谶纬家们还对此说做了奇异的发挥。本来,在春秋公羊家说中,孔子的形象不管被做了怎么样的改造。也还是现实中的人;而在谶纬中,他却被塑造成了似人非人、似神非神的怪异物。谶纬说这位“素王”头顶中央凹下,像“德泽所兴,藏元通流”(《礼含文嘉》),“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且“斗唇,舌里七重”,“虎掌”、“龟脊”,“辅喉姘齿”,“海口,若言含泽”,而胸口有“制作定世符运”的字样(分见《孝经钩命决》、《孝经援神契》和《春秋演孔图》)。谶纬还炮制了一个以“素王”孔子为中心、包括一批“素臣”在内的“春秋朝”。《论语摘辅象》载:“仲尼为素王,颜渊为司徒”,“子路为司空”(一说“子贡为司空”)。《论语比考》载:“左邱明为素臣。”在谶纬中,孔子与左丘明所以被描述为“王”与“臣”的关系,是因为经与传的关系是“主”与“辅”的关系。顾颉刚先生说:“到了汉朝,真是闹得不成样子了”,“他们把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浸入怪力乱神的酱缸里了”[1]。
孔子为何只能当“素王”而不能当实王或真王呢?谶纬家们的解释是:孔子属德为水,不合五德的运序。《孝经援神契》说:“丘为制法,主墨绿,不代苍黄。”孔颖达正义解释说,此“言孔子黑龙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苍也”。为了证明孔子的水德身份,谶纬从孔子出生开始编造神话。《论语撰考谶》载:“叔梁纥与徵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这是一个感生神话。按照这个神话,孔子是因其父母在尼丘山求子感应了“黑龙之精”而诞生的。关于孔子的感生神话,在谶纬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春秋演孔图》载:“孔子母徵在游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故曰玄圣。”既然孔子是黑帝后,因此谶纬就把他称为“玄圣”(玄也是黑)。谶纬把黑帝与孔子挂上钩,目的在暗示他五行属水。正因为是感生的,所以孔子长大后需通过“吹律”来定命。《春秋演孔图》载:“孔子曰:‘邱援律吹命,阴得羽之官。’”“羽”音在五行的相配图式中与水对应,《乐纬》亦说:“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宫,三言得火曰微,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因此《春秋汉含孽》和《易纬通卦验》都说孔子是“水精”。除了这个称呼外,孔子在谶纬中还有“玄丘”(《孝经援神契》)、“墨孔”(《春秋感精符》)等称,这些称呼,都与暗示他的水德属性有关。关于孔子为黑帝后之说,在汉代的很多文献中都能得着痕迹。例如《文选》班固《典引篇》“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李善注:“玄圣,孔子也。”《史晨碑》说:“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颜母毓灵。”“汁光之精”意思就是黑帝后,因为在谶纬中“汁光纪”是黑帝的别称⑨。
谶纬为何以孔子为黑帝后呢?顾颉刚先生认为,在谶纬中“孔子所以会成黑帝之子,并不是把他算作‘介于木(周)火(汉)之间’的闰统,乃是从三统说的黑统来的”[5]。顾先生的见解,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按照三统说,夏是黑统,殷是白统,周是赤统,三统轮流循环,周的赤统结束之后,继周而起者自当是黑统。然而,如果往深一层思考,便会发现把孔子为黑帝后看作是三统推衍的结果有几点不通:第一,“黑帝”、“水精”说出自谶纬家的炮制,而在谶纬盛行的时代(西汉后期及整个东汉),三统说的影响力已大大减弱,当时在政治历史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以相生为特征的新五德终始说,谶纬家们应当不会对三统说这么一种“过时”理论感兴趣;第二,孔子的祖上是宋人,宋为殷后,而殷在三统中是白统,按子孙与祖先同统的原则,孔子应为白统;第三,在三统说的理论框架下,孔子如为黑统,就应有资格继周而当实王或真王,而不应“有道无运”,因为赤统过后正轮到黑统当运。由此看来,把三统说看作是孔子为黑帝后说的理论根源是有问题的。我们莫如换个思路,从别的方面去找原因。从什么方面去找呢?从五德相生说中去找。见载于《汉书·律历志下》的《世经》说:“成汤《书经·汤誓》载:‘汤伐夏桀。’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商,后曰殷。”殷既然是水德,殷后孔子自是黑帝后。
三、“墨孔生,为赤制”
“素王”是空王,但空王也是王。孔子生而未逢其运,并不等于说生而没有意义。天赋使命决定了他作为圣人降世,绝不会庸庸碌碌度过自己的一生。周予同先生说:“孔子不是白白的降生吗?决不是的。他负了上天给他的很重大的使命。这使命,就是他应该替天下制法。”[2] 这层意思,在谶纬中被表述为:“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春秋演孔图》)
那么孔子靠什么来“显天心”而“制王命”呢?谶纬说,主要靠孔子自己撰著的《春秋》和《孝经》两部制法典籍。《孝经钩命决》载:“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又假借孔子之口说:“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与先王以托权,目至德要道,以题行。”《春秋演孔图》载:“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图》”。孔子欲制天下大法,为何不用具有系统理论框架的著作,而用一部被宋代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的历史书籍《春秋》,和一部简略得仅有一千八百馀字的道德读本《孝经》呢?对这个问题,谶纬用孔子自己的口气做了回答:“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春秋纬》)谶纬家声称,《春秋》不是一部简单的史书,它具备“三圣”的法度(《春秋说题辞》:“《春秋》经文备三圣之度。”),陈述天人的道理(《春秋握诚图》:“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改革当时的乱制(《春秋纬》:“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政。”),表示王道的完成(《春秋演孔图》:“丘作《春秋》,王道成。”),是一部货真价实的新制法典(《春秋纬》:“据周史,立新经。”)。又说,《春秋》反映的是孔子的“志”,《孝经》反映的是孔子的“行”。《孝经钩命决》载孔子语:“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这就是“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道理所在。通过《春秋》和《孝经》作媒介,谶纬家们在孔子与汉朝之间,建立了一种十分离奇的联系。
《孝经钩命决》说:“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匹夫徒步”四字,表明“素王”孔子只是个素王;可是“素王”能“制正法”,又说明“素王”终究是王。所谓“正法”,就是合乎五德之运的法则,因为在汉代,五德的运序被公认为王命的根据。在谶纬的感生安排中,周德为木,因此《春秋感精符》说“孔子按录书⑩,含观五常英人,知姬昌为苍帝精”。按照五行相生规律,木生火,故继“苍周”而起的王朝定是火德朝。孔子是“水精”、“黑帝后”,降世不合运序,无法顺理成章地继周而“王天下”,因此立黑制没有意义。但是,要是什么制都不立,他这个“素王”岂不真的成为百分之百的空王了么?要是这样的话,圣人降世还有什么意义?因此实际上孔子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无所作为,他只不过是改“为黑制”为“为赤制”而已。所谓“为赤制”,就是为刘氏的火德汉朝立制,这是汉代的谶纬家对春秋公羊家说加以移植改造而得出的结论。本来,在《春秋公羊传》中就有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之说,但《公羊传》并没有说这个“后圣”是运序为火的帝王,更没有说是刘氏。而谶纬家们引申发挥,把孔子作《春秋》、立“《春秋》制”之义转换成了“为赤制”之义,而把“赤制”说成为汉家之制。关于孔子“为赤制”的说法,在谶纬书中俯拾皆是。例如,《春秋汉含孽》说:“丘水精,治法为赤制。又黑龙生,为赤告,示象使知命。”《春秋感精符》说:“墨孔生,为赤制。”(11) 《尚书考灵曜》说:“孔子为赤制,故作《春秋》。”《春秋演孔图》说:“孔子论经,有乌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书上,化为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对“赤制”为汉家之制,谶纬也表述得十分清楚。《尚书考灵曜》说:“卯金出轸,握命孔符。”注曰:“卯金,刘字之别。轸,楚分野之星。符,图书。刘所握天命,孔子制图书。”《孝经援神契》说:“玄邱制命,帝卯行。”(“帝卯”是“帝卯金刀”的缺省,意思是“劉帝”)《春秋演孔图》说:“邱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李贤注:“《尚书考灵耀》说:‘孔子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汉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断十二公,象汉十二帝。”《孝经右契》还杜撰了一个神奇故事,说高祖的受命之符是由孔子代为收受的:
制作《孝经》,道备,使七十人弟子,向北展星而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衣绛单衣,向星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
在这个制作谶纬后的“告天”仪式中,孔子作为中介,使“炎汉”实现了继“苍周”而掌天下的受命(“衣绛”、“赤虹”都是火德的暗示)。
杨向奎先生分析:“素王之义,已近于教化之主,因为他仅能制礼作乐,并无其位。”[6] 此话颇得其理。《淮南子·主术训》说“孔子……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锄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主述训》把“王道”与“教道”并称,以《春秋》之道为王道,以“素王”之道为教道,正显示“素王”包含“教主”之义。而谶纬通过对孔子形象的更进一步改造,使孔子彻头彻尾地由不含运序的受命王变成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制法主。孔子成为制法主之后,其使命便由“以《春秋》行使天子赏善罚恶之权”变成了“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亦即“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春秋汉含孽》)。这种改造,是很合乎汉朝统治者的需要的。试想,孔子高高在上(12),在世俗的意义上与汉朝统治者不但没有任何冲突,反倒能“为汉制法”,助汉帝“受命”,这不是很理想的事吗!
四、“获麟”与“赤受命,苍失权”
讨论“玄圣”孔子“为汉赤制”,不能不提及“获麟”。
《春秋》在哀公十四年春记有“西狩获麟”事。所谓“西狩获麟”,是说周天子在狩猎时捕获了一头有角的怪兽。从常理来看,这应当是一件微末之事,不值得一提。然而在惜墨如金的《春秋》中,此事却被当成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来记载。《春秋》经为何要这么做?《公羊传》的作者解释说:
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
董仲舒也认为《春秋》记载“获麟”是为了宣示某种天意,大有深意。《春秋繁露·符瑞》说: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同百王之道。
上述说法,自是春秋公羊家的“非常疑义可怪之论”。而谶纬全盘接受了春秋公羊家说。《春秋元命包》说:“孔子曰:‘丘作《春秋》,始于元,终于麟,王道成。’”《春秋感精符》说:“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洛书摘六辟》说:“建纪者,岁也。成姬仓,有命在河,圣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征。”《春秋演孔图》说:“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不仅如此。谶纬在此基础上,还对“麟出”与“王者至”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春秋公羊家只是说“麟出”与“王者至”有关,并没有说“王者”是谁,更没有把此事与德运问题搭上钩。谶纬却说这个继周而起的“王者”属德为火,它就是刘汉王朝。《春秋汉含孽》说:“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赤受命,苍失权。”《春秋汉含孽》说:“周灭火起,薪采得麟。孔子曰:‘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述图录。”《易纬乾凿度》说:“孔子曰:丘按录谶论国定符,以《春秋》西狩,题刘表命,予亦握嬉,帝之十二,当兴平嗣。”
谶纬的说法让人感到很离奇古怪——一头被孔子断为“麟”的“瑞兽”(实为怪兽)被捕获,与“苍周灭”、“赤汉兴”有什么关系呢?谶纬有谶纬的逻辑。《诗含神雾》载:“麟,木之精。”(13) 《春秋演孔图》载:“苍之灭也,麟不荣也。麟,木精也。麒麟斗,日无光。”“木精”被人捕捉,因此是“苍失权”的征兆。那“苍失权”与“赤受命”或“火起”又有什么关系呢?《尚书中候日角》载:“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采薪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为了使“获麟”与“赤汉”受命的关系更为密切,谶纬对孔子闻获麟的故事做了有意的改编。《春秋公羊传》在传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时,记述了以下这个故事: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孔子所以如此伤心,据说是因为觉得人们有眼无珠,竟然把瑞兽“麟”当成“麇而角者”,而全不知“麟出”与“王事”有关。《春秋公羊传注疏》引《孔丛子·记问》把这个故事演绎成了如下的样子:
叔孙氏之车子曰鉏商,樵于野而获麟焉,众莫之识,以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麇而肉角,岂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将观焉。”遂往。谓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视之,果信。言偃问曰:‘飞者宗凤,走者宗麟,为难致也。敢问今见,其谁应之?”子曰:“天子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祥。今宗周将灭,天下无主,孰为来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犹麟之于兽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14)
《孔丛子》的所载亦应当是公羊家遗说(15)。按照上文的说法,麒出而死表示孔子有德无运,不能当位(是以孔子才会哀泣“予之于人,犹麟之于兽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故事固然有演绎成分,但是毕竟没有把“获麟”与“赤汉”之兴挂上钩。而谶纬版的故事却成了另外的样子。《孝经援神契》载: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夜梦三槐之间,沛丰之邦,有赤烟气起。乃呼颜渊、子夏往视之,驱车到楚西北范氏街,见刍儿捕麟,伤其前左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儿来,汝姓为谁?”儿曰:“吾姓为赤辅,名子乔,字受纪。”孔子曰:“汝岂有所见耶?”儿曰:“见一兽,巨如羔羊,头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为赤刘,陈项为辅。五星入井,从岁星。”儿发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趋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图广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刘当起,曰周亡赤气起,火耀兴,玄丘制命,帝卯金。(16)
比较一下两个故事的内容,不难看出谶纬编造者的良苦用心。前一版本说,孔子是得悉“有麋而角者”被弃于“五父之衢”之后往观麟这个人莫之识的动物的;而后一版本说,孔子因“夜梦”“沛丰之邦,有赤烟气起”,遂呼颜渊、子夏往视赤烟,不虞在半路遇上了麟(谶纬提到“孔子夜梦”,是暗示他遇麟系出于神谕;而沛丰是刘邦的家乡,此地“有赤烟气起”,明显是预示火运将兴)。前一版本说,获麟者是“叔孙氏之车子曰组商”:而后一版本说,获麟者是一位姓“赤辅”、名“子乔”、字“受纪”的“刍儿”(“赤辅”意思是“火德之辅”,“受纪”是“受命之纪”)。前一版本说,孔子见麟后的反映是泣而哀叹,因为他认为麟出而死意味着宗周亡而无主;而后一版本说,孔子见麟后的反应是欢呼“天下已有主也”,且明确说这位“天下主”是“赤刘”。后一版本说麟吐图卷,图卷文字称“赤刘当起”、“周亡赤气起,火燿兴,玄丘制命,帝卯金”等,前一版本都没有这些情节。
为了体现“获麟”的“划时代意义”,《春秋命历序》生造了一个从天地开辟到“获麟”的帝王谱:“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洛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蜚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还对各纪的历史情况进行了杜撰,比如“九头纪时,有臣,无官位尊卑之别。次后五龙纪,父子五人,分治五方:长为角龙,木仙也,号曰柔成;次为征龙,火仙也,号曰耀屏;三为商龙,金仙也,号曰刚瞻;四位羽龙,水仙也,号曰翔阴;父为宫龙,土仙也,号曰合离。其神后司于四时。”
谶纬关于“获麟”的说法在东汉有很大影响。今文经学家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所发挥的即是谶纬说:
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居其位,故麟为薪采者所执。西狩获麟者,从东方王于西也,东卯西金象也。言获者,兵戈文也。言汉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夫子知其将有六国争强,从横相灭之数,秦项驱除,积骨流血之虐,然后刘氏乃为帝。深闵民之离害甚久,故豫泣也。[7](哀十四年解诂)
何休牵强地把采薪与获麟与“木燃火”扯到了一块。在他笔下,“西狩”成了“从东方王于西”、“东卯西金”之象,“言获”是“兵戈文”,“西狩获麟”是“汉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之兆;而孔子预见未来的能力也十分离奇,不仅能知道后来战国的形势,而且知道“赢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汉业建”(《三字经》)的过程。何休还说:
人道浃,王道备,必止于麟者,欲见拨乱功成于麟,……故麟于周为异,《春秋》记以为瑞,明太平以瑞应为效也。绝笔于春,不书下三时者起,木绝火王,制造道备,当授汉也。[7] (哀十四年解诂)
这更是直接地把“麟出”与“木绝火王”挂上了钩。《解诂》在解释“麟出”一事时,还提到《春秋演孔图》所载的“端门受命”事:
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化为赤乌,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7] (哀十四年解诂)
端门前的血书实为一预言,大意是说孔子作法及身故之后,周朝将灭亡,然后秦始皇当政,他虽然焚书坑儒,但孔子为后圣赤刘所制之法不会断绝。端门受命的另一启示是上天宣布孔子具有为后世制法的使命,而《春秋演孔图》就是他为赤汉制法的标志。
谶纬的“获麟”理论在东汉碑铭中亦留有痕迹。例如孔庙《史晨碑》载:
孔子……获麟趣作,端门见征,血书著纪,黄玉愔应……钩《河》摘《洛》,却揆未然。
《韩敕碑》载:
皇戏统华胥,承天画卦。颜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宫,太一所授。前闿九头,以什言教;后制百王,获麟来吐。制不空制,承天之语。乾元以来,三九之载,八皇三代,至孔乃备。圣人不世,期五百载。三阳吐图,二阴出谶。
《韩敕后碑》载:
孔圣素王,受象乾坤。生于周冲,匡政天文。德参耀□,作应星神。稽易制孝,生出大人。证符洞虚,论要道根。赤书黄字,蜚于仓天。北落复下,大帝闿门。龙□□□,精历星官。雷动玄紫,声隐□震。《春秋》既成,效以获麟。(17)
“周灭火起,薪采得麟”(《春秋汉含孽》)、“知庶姓刘季当代周”(《尚书中候日角》)、“周亡赤气起”[7](哀十四年解诂)、“赤帝将代周居其位”[7] (哀十四年解诂)、“赤受命,苍失权”(《春秋汉含孽》)、“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尚书中候日角》)、“苍帝七百二十岁而授火”(《春秋保乾图》)、“卯金刀,名为刘,中国东南出荆州,赤帝后,次代周”(《春秋演孔图》)等等,这些言论都反映了在谶纬家眼中,火德“赤汉”是直接继木德“苍周”而王天下的。这种观点与刘歆伪撰的《世经》的说法相同。刘歆曾在“周木”(周武王)与“汉火”(汉高祖)之间,安排了一个闰统——“秦水”。谶纬也在“周木”与“汉火”之间也安排有闰统,不过这个闰统不是秦,而是为汉制法的孔子。像刘歆一样,谶纬是不承认秦在五德中的正统地位的,《易纬通卦验》说:“秦为赤躯,非命王,故帝表有七五命……以火代黑。”但谶纬比刘歆走得更远,它连秦的闰统地位也不承认。谶纬把同样不合乎运序的“黑帝”或“水精”孔子引入五德框架中,等于把居于闰统地位的“秦水”剔除出去了,因为在“周木”与“汉火”之间不可能并存两个“闰水”。谶纬在为古史平添一个虚拟的“孔子朝”或“春秋朝”的同时,也撤销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秦朝。说孔子未王而王,等于说赢秦王而未王。谶纬对闰统的置换,使“赤汉”继“苍周”而兴的媒介,由“伯”(即霸)变成了“圣”。这当然是汉朝统治者所求之不得的。试想,连圣人都甘居闰统而为“赤汉”制法,还有谁敢怀疑刘氏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呢?还有谁敢说赤汉不合乎五德的运序呢?
收稿日期:2008-05-26
注释:
① 在古代典籍中,“圣人”与“圣王”两词常相混用。例如《易经·颐·彖传》说:“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礼记·礼运》说:“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易经·说卦传》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这里的“圣人”等于圣王。而《史记·乐书》说:“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鲁仲连邹阳列传》载:“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多之口。”这里的“圣王”等于圣人。
② 许慎《说文解字》解“王”字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字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叁通之者,王也。”在古代,“王”字的含义,不外两说:从音训来说,是天下归往;从形训来说,是参通天地人。而春秋公羊家则从“内圣”和“外王”两个方面来理解天下归往与叁通天地人。他们眼中的“王”并不是现实中的统治者,而是理想中的统治者。
③ 《春秋繁露·奉本》。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庄公三十一年解诂说《春秋》“因鲁而见王义”,继承的是董说。
④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以《春秋》当新王”的理论其实在先秦儒家的议论中已见端倪。例如《孟子·滕文公》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来、墨翟之言盈天下。”又说:“《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并引孔子之言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说:“王者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连《庄子·齐物论》也承认:“《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从这些先秦学者们的议论看来,《春秋》作为一部经,是有其微言大义在的。不过“以《春秋》当新王”之义,是到了春秋公羊家那里才被发挥到极致的。
⑤ “素王”一词见于《庄子外篇·天道》:“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但此篇已被学者证明非庄生之作,而是秦汉间人的手笔。
⑥ 《史记·殷本纪》唐司马贞索隐说:“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索。故称素王。”此为别解。
⑦ 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论《春秋》素王不必说是孔子素王《春秋》为后王立法即云为汉制法亦无不可”条说:“据杜孔之说,则《春秋》素王,非独公羊家言之,左氏家之贾逵亦言之。”钱穆先生亦持此见解,参见《孔子与春秋》,《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7页。
⑧ 《孔子家语》当为三国王肃之伪作,然其材料大半采摘于先秦或秦汉典籍。
⑨ 《春秋文曜钩》说:“黑帝其名曰汁光纪。”《尚书帝命验》说:“黑帝汁光纪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昧,能权轻重,故谓玄矩,周曰玄堂。”“汁光纪”也作“叶光纪”、“协光纪”。
⑩ “录书”或称“图录”或“图箓”,即谶纬。
(11) 按,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注和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均把此语标点为“墨、孔生,为赤制”,误。墨子怎可能“为赤制”?“墨”实际是指“黑”,因为孔子的属德是水,为黑统。
(12) 罗梦册先生《孔子未王而王论》一书提出,以孔子为核心的虚拟的“朝廷”的出现,“严重地威胁着那个继秦而起的汉王朝的存在”。“由于孔子为王和春秋建代的结果,却使得现存的汉王朝大感威胁,而思有以救而安之”,于是汉代才出现了一个假手谶纬家进行的神化孔子的运动(见罗梦册《孔子未王而王论》,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2年版,第163、174页),这是与史实不相符的臆猜。
(13) 麟是土兽,却被称为“木精”,这很令人费解。旧说麟为土畜,因“性合人仁”,故为木精,很牵强。
(14) 这段文字本非谶文,孙瑴《古微书》误把它采入《论语摘衰圣》。周予同先生《谶纬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亦误把它作为谶文来讨论。
(15) 《孔丛子》七卷,原题孔子八世孙、楚孔鲋撰,鲋曾仕陈胜为博士。经后世学者考证,此书应为东汉末以至齐、梁时人的伪作,不过其内容有相当部分缀集的是先世遗文。罗根泽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册发表有《孔丛子探源》一文,对此问题进行过详细的缕析。
(16) 《孝经右契》亦载有此事,情节大致相同,不过刍儿的姓为“赤松”(一作“赤诵”),名为“时乔”。
(17) 史展、韩敕在桓灵时均担任过鲁相。因此,这些碑文也反映了东汉中叶至宋叶社会的流行思想。参考吕宗力《东汉碑刻与谶纬神学》,《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历史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