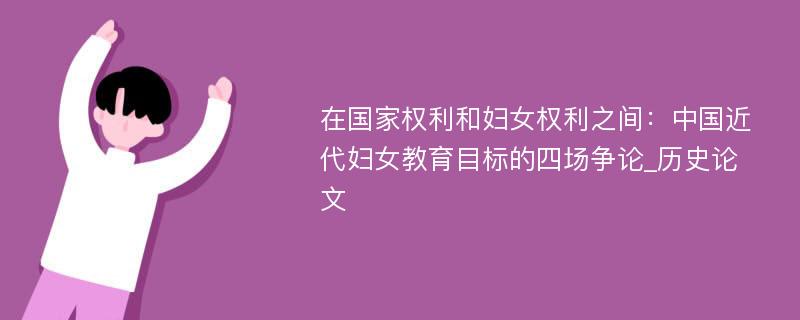
在国权与女权之间:近代中国关于女子教育宗旨的四次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权论文,女权论文,四次论文,宗旨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0)03-0075-06
教育宗旨作为抽象程度最高的教育目标,往往借助国家强制力予以颁布与实施,故而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诚如周予同所言:“教育宗旨植根于教育思潮,而教育思潮又植根于社会状况;换言之,教育宗旨实为一种意识形态之比较具体的表现。”[1]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当务之急,“兴女学”作为一种救国之策几无疑义地被精英知识阶层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中。因此,诸如“夫国势之积弱,既为女学不兴所致,则今日之兴女学,所以救国也”[2],“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本原也”[3],“今夫一女不学则一家之母无教,一家之母无教则一家之学失教,积人成家,积家成国……”[4]等言论在报刊上比比皆是。这种视女学为强国保种的手段的工具化思想,与20世纪初输入的视教育为妇女天赋人权的西方女权思想可谓南辕北辙,难以避免地发生碰撞,以致出现一种吊诡现象:在“兴女学”成为知识界共识的同时,女子教育宗旨却成为时人争论不休的话题。笔者在爬梳近代女子教育史演变轨迹时发现,自戊戌维新至抗战有关女子教育宗旨的大论争达四次之多,尽管论辩双方所倚重的话语随历史情境变化而有所不同,但贤妻良母作为底色却贯穿始终,进言之,它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不同政治派别对“国权”与“女权”谁之优先问题的考量。
一、20世纪前后“贤妻良母”与“反贤妻良母”短兵相接
贤妻良母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内涵。近代以前,“三从四德”是其最高标准。20世纪初,“贤妻良母”作为一种女学话语从日本传入,经精英男性将其与传统的贤良主义进行整合后,与女权、民权、革命等话语相提并论,形塑出具时代气息的贤妻良母观。诚如有论者所言:“中国近代贤妻良母观的确立,是中国固有的女性观、西方男女平权思想及日本贤妻良母一词合流的结果”[5],而“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中正式提出贤妻良母为女子教育目的者要以他(梁启超)为始。惟他之提倡女学,系为外侮所激,所以以强国保种为女学最后的目的。”[6]280这一说法缘自梁于1897年在《倡设女学堂启》中提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倡,千室良善,岂不然哉”的主张。他将相夫教子、宜家善种作为贤妻良母的新内涵、新标准提出,与传统的贤良主义划清界线,成为近代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同时也表达了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对性别伦理的新诉求。这一界定有着明显的局限:一是将女性角色划定在相夫教子的狭小范围内,未能动摇固有的社会性别等级制;二是过于强调女性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忽视女性应有权利。恰如舒新城所言:“此时所谓贤母良妻完全从男子底方便上着眼,并非以女子底天禀为本,故教育主旨重在服从。”[6]287这种将女性伦理融入国家观念,要求女性以尽贤母、良妻天职服务国家的男性本位思想,很快招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女界精英的质疑与抨击。
在众多论述中,《论女学宜先定教科宗旨》(1907)最集中地展现了论辩双方的交锋。支持者认为一切教科目的应专注于女子应尽之义务,视教育子女、管理家务为妇女的天职,反对妇女参与社会活动[7],故“考其华文功课,如《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皆有用之书也”[8]。这一主张几乎是传统贤良主义的翻版,遭到反对者的批驳。反对者提出女子教科目的应与男子相同,以养成“社会的人”,并呼吁女子不应满足于贤母、良妻,要做社会独立一分子。其中,对贤妻良母观予以最深刻、最坚决回击的人士当属陈以益。他在《男尊女卑与贤妻良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之贤母良妻,尤识字之婢女”,“实则,男子之高等奴隶耳”,“贤妻良母之教育,犹教婢女以识字耳,虽有若干之学问,尽为男子所用”;发出“呜呼!女子教育岂为男子而设耶”的慨叹,提出“苟欲去男尊女卑之谬说,则请取贤妻良母之主义并去之。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教育,即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权利,则平等平权庶非虚语,而女学与女权发达当有日矣”[9]。陈氏不仅将摈弃贤妻良母视为消除男尊女卑的先决条件,且将男女受同等教育视为女权的保证。
在反对的声浪中,女界精英反叛的力度尤其突出。前代的遗规,先圣的明训,女教的范本,成为她们否定与挞伐的对象。巾侠在《女德论》中对《周易》的“乾坤定位”思想予以批驳,指出“自天尊地卑之说出,而男女之别以起”,“积渐成俗,习非为是,男日以黠,女日以愚,剥权失势”,主张女子“与男子争衡”、“与男子权利平等”[10]。时就读于务本女塾的张昭汉对《女诫》发起猛烈批判,指出该著“以卑弱下人为宗旨,养成柔懦根性为目的,使群女子相率而为自暴自弃”,据此称班昭为女界罪人,“昭之罪不容逭矣,吾安敢随流俗人之后,昧昧焉施其崇拜哉!”[11]张文发表后,引起女界共鸣。常熟女子宋大年撰文与之呼应,指出拘守习俗拜读女教圣本的所谓“贤女”,实为“抱守《女诫》《女孝经》主义,甘为世俗之奴隶”[12]。陈撷芬在《独立篇》中针对“创一女学塾曰谋之男子,立一女学会曰谋之男子”状况,提出女子“非独立不可”[13]。这些批判性言论以毫不妥协的精神将矛头直指古圣先贤,是不甘做封建女教奴隶女子的“宣战书”,它预示着女界“群醒”时代的到来。
其实,女界“反贤妻良母”最直接地体现在办学实践中。1902年创办的广州公益女学、移风学校标举“国事重于家事,女子对国家的责任亦大于家庭”的办学宗旨,称女学为女子“自立之法”。直隶女子师范校长吕碧城针对女学只需学做“乳媪及保姆”之主张,指出兴办“乳媪学堂”是制造“奴隶之学堂”,“殊不知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具政治之思想,享公共之权利”,表示“我高尚独立之女国民”是不会甘心只做服役幼儿的乳媪保姆的[14],并以实际行动推行“欧美女子之教育”[15]。苏英义正言辞地表示:“如今我们的意思,是要撇脱贤母良妻的依赖性,靠自己一个人去做那惊天动地的事业,把身儿跳入政治接种,轰轰烈烈光复旧主权,建设新政府……”[16]
尽管贤妻良母与反贤妻良母在晚清知识界有过短兵相接式的对垒,后者有时还居上风,但前者几乎主宰整个女学实践。这与清廷于1907年颁布的《女学堂章程》关系极大,章程规定“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助家计”为教育宗旨,将女学纳入家庭教育范畴,使女校成为贤妻良母的养成所。民国初袁世凯执政后,保守之风盛行,1914年12月袁政府颁布《颁定教育要旨》,申明女子若“舍家政而谈国政,徒事纷扰,无补治安”,依旧鼓吹贤妻良母主义。时任教育总长的汤化龙放言,民国以来主张开放女禁、提倡男女同权等议论,不过是“一时风潮所驱”,“余对于女子教育之方针,则在使其将来足为贤妻良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17]。汤的观点看似“一家之言”,实极具代表性,否则不会出现“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后之女学固然以此主义(贤妻良母)为目的,社会上亦无何种反抗的思潮”[6]287的图景。
二、“超贤妻良母”: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贤妻良母”的试图超越
晚清至民初官方所秉持的贤妻良母观不仅使女学发展受到掣肘,女权思想也难以有效传播,1904年亚卢所展望的十年以后中国将有“女子世界之成立,选举、代议,一切平等”[18]的美好前景成为泡影。即便到新文化运动前期,“女子解放”、“人格独立”呼声此起彼伏之时,部分新刊物仍对贤妻良母津津乐道。1915年创刊的《妇女杂志》将欧美的强大归因于贤妻良母:“乃知欧美列强,纵横于世界,非徒船坚炮利,实由贤母良妻之淑,主持于内,为国民之后盾也”[19],声称“本杂志以提倡女学,辅助家政为宗旨,而教养儿童之法尤为注意……”[20]上海《中华妇女界》提出以培养贤妻良母与淑女为主旨。《新青年》杂志的“女子教育”栏亦指出:“……女子者,人类之母也。相夫教子,持家处世,其所贡献于国家者既多”,故“中国女子之急务,乃当洁身自爱,以期养成真道德、学问与经济之女,而作中华民国之贤母氏”[21]。上述刊物在当时颇负盛名,其主张反映了当时的舆论导向,使贤妻良母观在社会上产生强大的辐射力,为守旧势力提供取消女学的口实。1917年教育当局制定“取缔女学之规则”,1919年5月发布训令,将家事课列为最重要的科目[22]可为显证。怪不得周世钊对湖南女校发出如是感慨:“这些女学校性质虽各不同,但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向学生进行贤妻良母的教育。”[23]
然而,“五四”运动爆发后,贤妻良母观首当其冲地成为先进人士批判的靶子。陈独秀发刊的《新青年》杂志,极力攻击孔子之妇女观[24],坚决反对无独立人格的贤妻良母教育。胡适发表《美国的妇人》,从反面立论,提出“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他从亲眼目睹美国女记者精神风貌着眼,感慨道:如果把她“苍老的壮志,倔强的精神”,“补助我们的贤妻良母观念,定可以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生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并将“我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贤妻良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视为“‘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25]。该文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是对贤妻良母观的试图超越。尔后,留日学生冯飞所著的《女性论》出版,提出“培植其宿具之知能,使其必要知识充足,庶与男子立于对等生活之上不致败北”[26]。罗家伦亦指出[27]:
中国办女学的人到现在却开口还只是谈贤妻良母主义,更不愿意女子做独立的人,这种奴隶教育有什么用处呢?所以现在中国女子精神上最重要的解放就是打破贤妻良母的教育,而换一种“人”的教育。女子知道自己是人,才能自己去解放。
可见,在“五四”反传统大潮中,以陈、胡等人为代表的先进人士为弘扬女性独立人格,难以避免地对服务于“国权”的贤妻良母观展开批判。
与知识界形成微妙对照的是教育界人士的女子教育思想。1920年陆费逵发表《女子教育的急务》,将女子教育目的归纳为四项:一是健全女子的人格;二是养成贤母良妻;三是在男子能养的时代从事无害生理无妨碍家庭的职业;四是预备充足的实力于必要的时代代男子做国家社会一切的事[28]。最后一项是后来加上去的,言下之意是女性除担当贤妻良母外,还要做好准备以在男子缺席的情况下服务国家社会。同年3月,姜琦在浙江省立女子师范的讲演中提出:“男子有男子特殊的教育,女子也有女子特殊的教育”,认为“‘良妻贤母’四个字,并不是绝对没有价值,不过不能够当做女子教育的唯一目的,只能当做目的中之一部分”[29]。姜、陆的言论显然是教育界女学观的映射,他们试图将女权与国权融为一体,但由于二者存在着内在张力,现实中难以实现,因此可以说这种主张不过是一种调和论,顶多是一种无关痛痒的改良而已。
与男性精英相比,觉醒了的知识女性不仅仅在思想上反对贤妻良母观,还付诸实际行动。针对海外大学规定女生只占10%招收名额的歧视性规定,1921年5月30日,向警予、蔡畅等联络12名留法女生组成“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表《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致女界全体书》(下文简称《全体书》)进行抗议。《全体书》指出贤妻良母如幽灵般笼罩于各女子学校[30]:
女子秉历史的贤母良妻之沿革,以社会的贤母良妻之地位,受教育的贤母良妻之熏陶,其周围环境,无一非纳女子于贤母良妻之域者,故贤母良妻实为女子惟一归宿地;是以学校有所谓女子学校,教科书亦有所谓女子教科书,自小学以至高等大学,凡冠以女子二字者,无不含有女子之特质,即无不舍(含)有贤母良妻之特质。
这样,导致“女子中学女子师范毕业大多数不能考北大南高”,究其原因:“是真社会制度与教育之过,而非女子本身之过也”,要求“力辟贤母良妻之谬妄教育,否认苟简的女校教课,女子教科,与女校的陋劣教员。”[30]《全体书》将矛头直指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指出“女子实力不足”源于“社会制度与教育之过”,不仅击中了男权制的要害,也是对贤妻良母观的彻底清算。
应该说,在“五四”知识界掀起对传统性别伦理大批判的背景下,先进人士或以言论或以行动试图超越贤妻良母的羁绊,尽管未能彻底清除其流毒,但为男女平等教育的倡言与推行奠定舆论基础,使男女同校、大学开女禁、男女社交公开等成为社会共识,最终促成女子教育宗旨由“贤妻良母”到“男女平等教育”的嬗变。
三、“母性主义”:国民政府时期“贤妻良母”改头换面
“五四”后,男女平权不独为一种思想,在行动上亦已实现许多,使国民政府不敢等闲视之,但国民党迫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又不能不予以重新规范。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宣言》提出“女子教育,尤须确认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实为救国保民之要图,优生强种之基础。”[31]将“健全的母性”与“救国保民”相提并论,随之衍生“母性主义”教育观。与贤妻良母相比,母性主义外延更广。前者以家庭为中心,间接服务于民族国家;后者则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直接服务于国权,使女权隐而不显。4月26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确认“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5月,全国教育会议提出女子中等教育“应以培养女子特殊的社会职分,而适应其特殊的需要”[32]120,通过《中等女子教育应有特殊设施案》(下文简称《实施案》),称“此一要义,实为今后建设女子教育必不可易之方针”[32]120。经历次会议反复重申,国民政府最终确立“母性主义”教育宗旨。究其实,不过是对贤妻良母做一番改头换面装扮后的另样称谓而已。
为使教育宗旨落到实处,《设施案》规定“女子高初级中学,以特别设置为原则,各地方因经济力及教授人才之缺乏,不能分设者,得于中等学校中,分设男女两部。”[32]121这里的“特别设置”是指中学男女同学分开设立,实际上是以片面强调两性差异取代两性之共性,重弹男女教育不平等的老调。这种做法不仅与男女社交日益公开的时代潮流相背离,也与各地已然存在的男女同校相冲突,遭到部分省区代表的强烈反对。浙江代表刘大白、杨廉即日上书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此案通过,和男女教育机会均等的教育宗旨完全相反。如果大学院一定要采择施行,浙江大学区内已经开放女禁的各中等学校中千数女生便要被迫辍学,这简直是摧残女子教育,是浙江大学所不能做的。”[32]122迫于反对声音之强烈,大学院最终未采择施行,但“母性主义”在教育法规中保留下来,为贤妻良母日后死灰复燃埋下隐患。
四、“妇女回家论”:全面抗战前“贤妻良母”卷土重来
1933年,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为摆脱经济危机,大肆鼓吹妇女回到厨房、教堂、床铺的“三K主义”,这股逆流传入中国后,被统称为“妇女回家论”,并由此引发有关女子教育宗旨的一次最大论战。1931-1935年间,各党派各社会人士纷纷参与论战,国统区各大妇女刊物、主要报刊成为论争的战场,延续十余年。论战人士之广,两军对垒之尖锐,史无前例。
如前所述,国民政府推行的“母性主义”实为“妇女回家论”登场提供了温床,国民党右派借机提出男女天赋不等,理应接受不同教育。吴兆洪指出[33]:
把贤妻良母教育看作是一种不平等的教育,是一种浅薄而显著的误解。女子在家庭里工作,与男子在社会上工作,是各就其不同的天赋的体力脑力,对于人类社会作一个适当的贡献。……这是一种内外的分工。
志敏称贤妻良母教育是“女子生活的终极态度”和“女子教育唯一的目标”[34]。李赋京鼓吹“女子生育,就是社会的母性,养育孩子,就是为社会服务尽责任,其他的都是次要的。”[35]1935年,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附和道:“中国社会之单位,实为家庭。家庭之组织是否健全以及子女之教育是否良善,关系社会者至巨。在现在中国之经济阶段,男子因须外出谋食,在家之时甚少,故一切责任,均被于妇女之双肩。”[36]《妇女共鸣》杂志甚至开出“新贤良专号”,号召妇女做“新贤良”。上述种种论调均视女子教育服务社会为要旨,置妇女应有的受教育权于不顾。在这种舆论氛围下,4月25日,北平市市长袁良抛出《取缔男女同学案》,为树立“母性教育”样板,市党部专门开办女二中。袁在开学典礼上的训词中说:“你们来这里读书的目的,是要学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所以要你们学习家事和劳作。”[37]为此,校方不惜辞退厨役,让女生学“炊事”,将正常学业弃置一边。
“母性主义”也好,“妇女回家论”也罢,都是复古教育思潮的产物,因此遭到进步妇女界猛攻。杜君慧在《妇女园地》停刊后,协助沈兹九编辑《申报》副刊《妇女生活》,连续发表“妇女问题讲话”,帮助妇女认清女子复古教育的本质,她质问道:“妇女回家论、新贤良主义的教育以及家事专门化教育,不都是要强调妇女实行希特勒主义的企图?”[38]《妇女生活》发刊词中写道[39]:
卫道士先生们,有主张“妇女回家”,有的在高唱恢复“三从四德”……在这外患内忧的重重压迫之下,“我们怎样做人呢”,每个受到重压的女人都会这样疑问着,希望着解答,《妇女生活》便应运而生了。
黄心勉在《女子月刊》发刊词中大声疾呼[40]:
历史教育我们,时势昭示我们,我们除了家庭以外尚有许多应做的事业,不应再在家中仰赖男子过活了。我们应该服务于社会,尽忠于国家。我们应该为自身生活而努力,为人类文化而努力。
“中国越穷,男权对于女性的进攻越厉害;非到妇女达到自身能够获得生产和支配的权力后,这种夹攻的围阵是永久打不破的”,号召女子“抛弃被豢养的生活,投身各种生产事业,扫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参加复兴民族,建立国家的运动。”[40]为消解袁良提案在社会上的恶劣影响,1935年6月5日,上海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妇女协进会等4个妇女团体联合发表宣言,斥责袁案为“极端反潮流反时代”。北平二中的进步学生在女界支持下,一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面采取罢课、抗议等形式坚决抵制家事课,迫使校方减少课时,第二学期便停开了,更重要的是导致北平市党部苦心树立的“样板”失去示范价值,沦落为空洞的符号。总之,由于社会各界尤其是妇女界以群体力量与女子复古思潮相抗衡,并展开长久的拉锯战,使妇女避免了再次沦落为民族国家工具的命运。全面抗战爆发后,出于全面军事动员的需要,国民政府将之前兜售的“妇女回家论”暂时搁置,肇始于戊戌维新的女子教育宗旨之论争被迫退场。
纵观四次论争的大致脉络并深入现象背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论争实质上源于论辩双方在“国权”与“女权”谁之优先问题上的分歧。从历史合理性着眼,国权优先更容易因与终极目标救亡图存一致,而以精英男性的呼号和官方的认可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以致主宰了20世纪前期女子教育的发展态势。但先进人士尤其是知识女性并未因“国权”优先而放弃对于“女权”的诉求,恰恰相反,他们利用“兴女学”话语的合法性,据理力争,为女权不断拓展空间,推动女子教育思潮向前迈进。进言之,知识女性正是巧妙地凭借报刊这一舆论场所,发出自己的声音,赋权自我,完成其主体身份的建构[41]。此外,我们还发现,由于近代中国处新旧制度交替、新旧思想混杂的大变革时代,女子教育宗旨作为“意识形态之比较具体的表现”,无可逃脱地被烙上不同政治派别的印记,吸引了维新派、革命派、守旧派、国共两党等政治团体参与论争,亮出各自的女学观,合力营造出“众声喧哗”的舆论阵地,为女子教育思潮曲折演进发挥了或正或反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