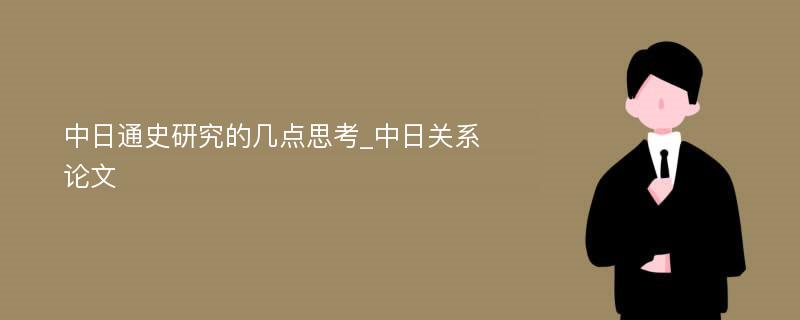
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时与中国领导人达成了中日两国就历史问题进行共同研究的共识,11月16日,李肇星外长和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实施框架”达成一致,12月26日,两国学者肩负着推动中日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的重任坐到一起,基于《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举行了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一次会议,标志着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工作的开始。
第一次会议确定将以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对中日近二千多年的交往史、近代不幸的历史以及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中日关系发展史进行共同研究,通过共同研究交流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交换不同意见;加深对历史过程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争取形成共识;在200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前发表专题研究共同报告和综合研究共同报告。
作为历史学者,与不同国家的学者就有关学术问题进行讨论、研究,甚至是争论,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中日之间的这一共同研究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反响则相当强烈。究其原因,首先是历史问题在中日两国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影响所决定的,同时也证明此次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确实具有相当特殊的背景。
历史问题为什么成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障碍
中国与日本之间有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友好交往的历史,人们常用“一衣带水”形容中日两国关系。当然,在那一时期也并非没有矛盾与冲突,但这并未成为影响今天国家关系的障碍。19世纪中期,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都遭受了来自西方列强的军事与政治压力,被迫打开国门,面临着成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也面临着同样的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任务。日本虽然率先摆脱了成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危险,但是却用西方列强的方式对待东亚的其他国家:将朝鲜强行变为其殖民地,并对中国进行了野蛮的侵略战争,从而使东亚的历史蒙上了阴影,中日之间最不幸的历史也由此发生了。当然,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现在,那一段不幸的历史也已经过去了60多年。尽管有一些战争遗留问题需要继续解决,但那些问题并不足以影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承认那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必须接受战后对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必须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因为只有这样做,战争加害国才能够得到战争被害国国民的理解与相信,才能够接受历史教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遗憾的是事态的发展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国内始终有人不肯承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历史问题的争论由此而发生。所以,历史问题主要是指历史认识问题。
一些日本人认为:历史认识问题在战后的日本已经解决,因为日本已经通过各种场合表示了对侵略战争的反省,是中国抓着日本的“历史辫子”不放而在打“历史牌”。这是需要首先澄清的问题。
日本投降后,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进行了正义的审判。由于是否接受对战争犯罪的审判是日本能否回到国际社会的基本条件,所以日本政府通过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和约》第11条表示“接受远东国际审判法庭及盟国在日本国内和外国的法庭上对战争犯罪的审判”。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也开始抬头,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日本军队的战争罪行,而且这种历史翻案活动愈演愈烈。
上一世纪60年代初期,作家林房雄的所谓“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曾经在日本社会掀起了相当强烈的历史翻案的浪潮。他连续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歌颂侵略战争的文章,认为从幕府末期到1945年战争结束历时百年,是日本抵抗西方势力入侵的“东亚百年战争”时期,“大东亚战争”则是其中的一环,必须把“大东亚战争”放到“东亚百年战争”的大环境中,才能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意义、作用。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命名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而在社会上广为发行,是战后日本第一部公开为侵略战争辩解和歌功颂德的著书。战后通过对战犯的国际审判,多数日本人已经认识到近代日本与中国和亚洲的关系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由于这一认识动摇了多年来支撑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框架,所以林房雄特地制造出所谓“东亚百年战争”的概念,有意将日本的对外侵略与近代日本抵抗西方列强侵入两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绝不相同的概念混在一起,这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确给许多对侵略战争并没有正确认识的日本人提供了思想武器,他们沿着这一理论模式开始否认中日近代历史的基本性质,一些日本的政治家也对这种错误的理论毫无警觉,这一点相当危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一部分急于把日本变成政治大国的政治家便把战后对日本的审判与处理视为成为政治大国的障碍,提出了对战后40年进行“政治总决算”的主张,对战后的民主与和平主义进行挑战,同时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所谓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认为:战后40年来把日本作为发动侵略战争国家的判断是错误的,要以“大东亚战争史观”取代把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的史观,要用“终战”的概念取代“战败”,要抛弃被东京审判束缚的日本近代史观,叙述历史的时候应强调“国家的光荣”,使日本人建立自豪感。(《月刊自由民主》,1985年第9号,东京)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日本一些政治家开始肆无忌惮地对历史问题进行翻案。如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1986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日韩合并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事实上,都是经两国商议好了的……韩国也是有责任的。”,并且说:“南京事件和原子弹轰炸哪个规模大?所以,必须要重新考虑东京审判的性质和意义”,“看一看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不能说只有日本进行了侵略战争。”(掘幸雄《战后の右翼势力》,劲草书房1993年10月版,第363、364页)
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1988年4月在一次公开的场合说,“战前白种人把亚洲作为殖民地,如果说谁是侵略者的话,那是白种人,只是日本坏的说法可以休矣”,(日中战争时)“日本没有侵略意图”,“日本是为保卫国家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在南京大屠杀碑前放置着中国人的白骨和日本军刀,宣传牺牲者是被日本人用日本军刀杀害的,这不是为了日中友好”。(吉田裕:《日本人の战争观》,岩波书店2000年版,第138、139页)
90年代后,更多的日本政治家卷入到对历史问题的翻案活动中,他们或者否认侵略事实,或者提出掩盖责任的谬论,这里包括担任过法务大臣的永野茂门、担任过环境厅长官的樱井新、担任过文部省大臣的岛村宜伸、担任过官房长官的江藤隆美等等。(《产经新闻》,2005年8月6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部分自民党的国会议员成立的“历史研究委员会”,他们彻底否定战后对日本的审判结论,编写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而且通过对日本历史教育的批判把历史问题的争论扩大到日本社会。于是,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为代表的历史修正主义抬头,坚决反对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追究,相反却提出:战后日本正式的历史观是一种“自虐史观”,即由美国占领军强加的历史观(东京审判史观)和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势力影响的历史观(共产国际史观)的混合物。他们认为这种历史观对日本来说是“黑暗史观”,接受这一史观的日本学者的反省就是在“自虐”。他们还认为这种史观并不是日本国民主体意志的自由表达,而是“内外的反日势力联合起来”策划的使“日本的国家精神解体”的阴谋,所以主张要在“东京审判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之外寻找第三条路,即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而且是描写“光明的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否认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有代表性的暴行问题为突破口,所以在日本全国上下掀起了将“慰安妇”的记述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的运动,同时也连篇累牍地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细菌战与毒气战,否认对劳工进行强制性迫害等文章。1996年末,“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针对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逐步改善的趋势而决定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到2001年,该编纂会编写了得到文部科学省审定的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在遭到了采用率极低的挫折后,该编纂会继续在2005年推出修订本,从而把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变成了亚洲社会关注的历史认识问题。
如何看待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是战后在日本社会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其中涉及到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也涉及到历史认识。其实,自民党从1967年将靖国神社的国有化问题提到国会后,连续6年遭到否决就已经表明了日本社会的基本态度。部分首相在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批评后采取谨慎态度,也证明这一问题与历史认识的关系。但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任首相以来,固执地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问题表现出明显的倒退。可以想见,日本政治家特别是政府首相一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历史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消极的政治结果。
可见,历史问题其实是战后在中日两国间,甚至是在东亚地区就一直存在的客观事实。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甚至得到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地伤害战争被害国人民的感情,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不健康环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历史认识问题并不像一些日本人所说的已经解决,并不是中国抓着日本的“历史辫子”不放而在打“历史牌”。
战后日本的反省与道歉
对于中国方面批评日本战后始终存在的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行的问题,有的日本学者感到有些委屈。他们认为:日本大多数国民承认战争是悲剧,不承认侵略战争历史的人在日本也只是少数,不是主流。他们认为战争历史已经过去了,战后日本受到了审判,走上了和平的道路,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向中国表示了道歉,为什么还不断批评日本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呢?而有的人则借此大做文章,声称中国对日本的不理解才是历史问题产生的原因,为此还举出2005年中国学生激烈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反日”游行,认为是中国对战后走和平道路的日本不理解与不了解。他们强调战后日本的和平外交路线,强调日本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总值中所占份额相当少,不拥有核武装,向国外派出很少执行维和任务的自卫队,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对中国的经济援助(ODA)等问题,一再强调不要把日本误解为好战的国家。
应当承认,战后,两国为解决历史问题确实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等政治文件就是两国政治家付出艰辛努力,对历史问题进行理智思考的结果。1993年新当选的首相细川护熙在回答记者关于当年的战争的性质的提问的时候明确表示:“我认为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同年11月,他在与韩国总统会见的时候,就日本对朝鲜进行的殖民统治表示了谢罪。而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就战后50周年发表谈话指出:“我国在不久前的一个时期,由于错误的政策而走上了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由于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给许多的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的人民以巨大的损害与痛苦。为了不再发生历史的错误,我们应谦虚地接受历史教训,从内心表示痛切的反省,向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牺牲的国内外的人民表达我们的哀悼。在迎来战败50周年的今天,我国要站在深刻反省的立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使日本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的一员而进行国际协调。”这一谈话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对战争历史的明确的表达。其后的历届首相尽管党派背景与之不同,但是在历史问题上,基本上都表示了赞同的意见。最新当选的安倍首相也表示了要遵守村山首相的谈话精神。我们在看到靖国神社问题的同时,也应看到中日之间还有联合声明、和平友好条约和联合宣言,相信多数日本人是爱好和平的,企图恢复军国主义的人极少。
在日本,不同的社会层面和不同的政治集团其实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其间甚至有根本的差别。战后坚持战争期间的“皇国史观”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保守势力始终存在,但是认真进行反省和谢罪的进步力量也一直在努力与之斗争。战后日本社会中对战争责任的反省有不同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亚细亚民族主义的立场、基督教的立场、市民主义的立场及女权主义的立场等。不同的立场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也有差别,有的涉及到政治层面,有的涉及到法律层面,也有的涉及到伦理道德的层面。
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主张从政治上彻底追究国家与以天皇为首的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并为此开展了十分活跃的左翼大众运动。因为日本共产党是战争中唯一的“手没有被污染”的政党,因此在战后追究战争责任的问题上有特殊的优越地位。
另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是社会上十分活跃的追究战争责任的力量。特别是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以陆军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及军队指导者进行了强烈批评,明确这些人对发动和扩大战争的直接责任。伴随这一批评,日本社会也曾涌动过一阵反省战争的思潮。
著名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男针对知识分子曾经提出了“悔恨的共同体”的概念,这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的概括。因为战争期间的多数知识分子为了保护自己而迎合了当权者的战争政策,或直接或侧面地支持战争,还有的对反战者进行告密。即使有人并不积极,但也缺乏斗争的勇气,没有明确地反对战争,更没能阻止战争。“悔恨”其实是知识分子对曾经允许错误战争横行而导致悲惨的失败结果的反省。
由于“战争中的记忆与悔恨是后来行动的动力”,所以知识分子的反省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和教师对侵略战争的性质认识更为深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导致侵略战争发生的以“皇国史观”为中心的日本历史教育的作用。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下,日本的历史教育在战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到70年代,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社会思潮又从反面促使日本的青年一代思考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与加害性。以至当时民意测验对中日战争性质的回答中,认为是侵略战争的占一半以上,而回答自卫战争的只有一成。特别是由于以家永三郎先生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就历史教科书中是否记述日本的侵略暴行的问题进行了长达32年的教科书诉讼,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确或比较正确地反映历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陆续出现,甚至一度占据了主流。
因此,客观地说,在“历史问题”上,日本给外界的印象是有人反省,有人否认;时而“道歉”,时而翻案,两种倾向同时存在。当然,不排除由于翻案倾向的存在和猖獗而有使人们忽略了反省与“道歉”的倾向的问题。正是看到了两种倾向,我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次会议的致辞中强调:珍视战后经历千辛万苦建立的新的和平友好关系,抵制破坏两国关系的言行,维护中日间基本政治文件的原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也应当成为两国学者的共同任务。
不过也还要指出,即使是“道歉”,情况也是复杂的。我们知道,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来北京的时候,在抵京当天出席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就因为在讲到那场战争的时候,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给中国“添了很大的麻烦”,而受到周恩来的严肃批评。虽然他后来表示了“道歉”,可是后来在众议院会议上回答共产党议员的质问时,他居然又说:“日本出兵中国大陆是事实,但是,我不能讲它是否就是侵略战争,这需要将来历史的评价”,又说,“我不能直截了当地回答是侵略战争,或不是侵略战争,这要让后来的史家评价,除此以外不能回答什么”。这种情况说明:仅仅用“道歉”一个词来表明历史认识,是很不可靠的。
更有甚者,有些强调战争历史已经过去了,强调战后日本受到了审判,走上了和平的道路的人,现在对“侵略”这个词已经三缄其口,甚至是千方百计地在回避了。他们所谓的道歉,难道不令人怀疑吗?
共同历史研究不是“政治框架以外的议论”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次会议后,日本的一些人立即出来大肆攻击,认为双方的学者都是政府选择出来的,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不能进行“纯学术”的研究,所以不可能有真正的结果。《产经新闻》在去年12月29日的一篇社论中提出:中方首席委员在第一次会议上批判日本国内的否定侵略的言行,要人们“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的发言“与共同研究的宗旨不吻合”,断言说:“对于政治主导的共同研究来说是荆棘遍布的,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不能说有了期待。”该报还质疑说:两国首脑的共识是让“有识者们进行政治框架以外的议论,填平认识的鸿沟”,即“把历史问题交给学术界,脱离政治,改变历史成为关系障碍的事态。中国当局是不是没有选好能够把握这一主张的人选?”
《产经新闻》所说的“政治框架以外的议论”与某些人所说的进行“纯学术”的研究是同一个意思,其实就是打着所谓的实证研究的旗号,让共同历史研究按照他们所设计的方式,背离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基本文件精神,或者在无关中日关系的问题上夸夸其谈,或者陷入对所谓具体问题的无休无止的争论,让本来是对两国关系将起重要作用的共同研究落入他们设计的以偏代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陷阱。
日本学术界一直流行一种所谓“无构造”的历史观。这种“无构造”的历史观不关心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不考虑历史环境与背景,单纯地强调微观的实证的研究。例如不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战争看作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行动,而是美化其中的一部分,如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另外就是则强调一些问题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如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及偷袭珍珠湾事件等,往往追究其中的一些细微末节,或者在一些本来是无法完全复原的历史现象、历史过程或数量等问题上纠缠不休。这种“无构造”的历史观影响很深,而一旦陷入这一争论,往往忽略了对根本问题的判断。事实上,历史认识的分歧发展到对中日两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绝不是什么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表述,认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就是要解决这些细微末节的问题,是对共同历史研究的肤浅的理解。因此,把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向是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在第一次会议的致辞中还强调应当把相互理解作为贯穿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过程始终的原则。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除了上述右翼与保守势力制造的政治原因之外,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产生差异。过去那场战争确实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他们亲身体验到的是战争接近结束时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特别是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悲惨后果。但是他们对日本军队在中国、朝鲜等地如何加害于当地人民既没有亲身感受,也缺乏这方面的教育。他们对这场战争在认识上和感情上很难达到中国人民那样的程度。一部分人虽然不直接否认历史,却“厌烦提历史”、“不愿多说前辈的错误”,十分缺乏对受害国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在长期轻视正确历史教育的环境下,日本年轻人的“无责任感”意识在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过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世纪转换,淡忘历史将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风潮。这种倾向如果没有变化,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或片面地夸大,肯定会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障碍。
谈到历史认识的差异,其实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国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涉及地域、利益、感情等诸多因素,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都可能存在差异。中日两国虽然地理距离不远,相互间有许多的影响,但历史发展过程的差异是客观存在,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文化障碍和交流的不充分也可能使这种差异演变为历史认识上的误解。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现象:对于本国人是司空见惯的问题,而对于外国人却仿佛是“天方夜谭”。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讨论历史认识相当困难。
然而,困难是一个问题,能不能通过相互理解而减少甚至消除差异是另一个问题。
通过战后数十年的交流实践可以看出,我们与大多数日本人民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不是在承认还是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问题上。应当承认,和平主义倾向在日本仍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目前还不存在军国主义复活的条件。我们可以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目标。在这样的政治判断下思考中日关系的历史,我们会在不同层面看到更多需要共同研究的问题。
比如:中日古代的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起了什么样的建设作用?而在田园诗般的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存在暗流?应当如何对古代和中世纪的两国关系加以概括?
再比如:中日两国人民是如何面对近代同样的民族解放任务?近代的民族主义这一双刃剑在两国是如何产生的?其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在哪里?这种差异又是如何产生并进而影响到当代两国关系的?
又比如:日本民众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带来的战争被害?而中国民众是如何看待日本的战争加害?两种认识是否存在可以沟通的地方?
还比如:战后的中日两国如何解决战争的负面的“遗产”?日本发展的经验对中国的影响,现代化进程中相互理解的障碍在哪里?等等。
上述问题虽然是中日两国共同经历的,但是位置不同,角度不同,认识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有误解。可能有人觉得这些问题不过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只要有学者们进行经院式的研讨就可以了。其实,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的差异乃至误解,正是诸多政治性的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原因。所以,我们这次进行的历史共同研究,需要自由讨论的环境,需要充分介绍自己的观点,了解对方的观点,以务实的心态思考分歧产生的原因,争取求同存异,缩小认识的鸿沟。从上述问题所涉及领域的宽度与深度上看,我们不可能要求双方的意见在短时间内完全一致,重要的是两国学者尽量将有关问题的各方面历史资料汇集起来,通过去伪存真、分析研究,向社会提供一个可资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当然,历史共同研究并不仅仅是罗列事实,因为有些问题的事实是相当清楚的,而如何评论和认识这些事实,需要学者们的理性、知识与智慧。通过共同研究达到学者间的相互理解,进而促进民间的相互理解。通过历史研究促使两国人民适当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对消除两国关系存在的障碍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就是历史共同研究的主要目的。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是在中日关系冲破重重障碍,开始新的面向未来的发展的前提下开始的,因此要求历史研究应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原则,发挥历史学的功能,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得更深、更远。历史学者需要关注社会大众的感情,但是又必须注意不能被褊狭的感情因素左右。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研究需要安静的环境。我注意到日本方面的个别媒体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对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唱反调,或者故意挑起事端,企图将共同研究引入纠缠具体问题的歧途;或者指责中国学者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是学者的基本职责,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也是一样。但必须看到:中日友好也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是符合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两国历史学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和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全面地审视和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中日两国利益的需要,也是整个亚洲利益的需要。
标签:中日关系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产经新闻论文; 战争论文; 史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