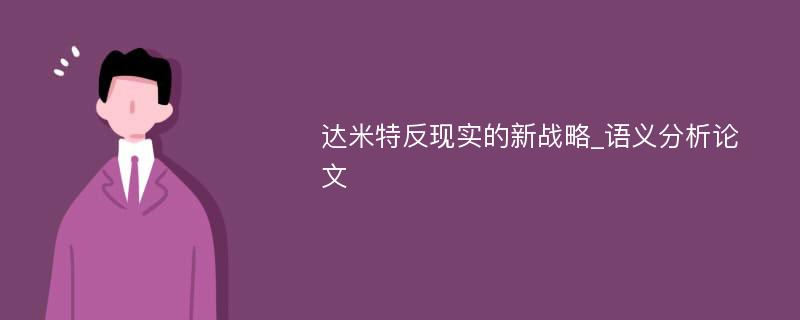
达米特反实在论新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在论论文,新策略论文,达米特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进行比较研究 致力“研究纲领
在西方哲学史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形而上学难题。几个世纪以来,尽管人们从未停止对这个难题的探讨,然而,他们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关于外部世界、数学对象、共相、科学规律或理论实体等是否存在,争论的双方始终各执一端,僵持不下。这一局面的形成,达米特认为,根本在于人们缺乏一个解决争论的总的策略。“哲学家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爱好站在这一边或那一边,而不是他们发现了解决争论的办法”。那么,这一解决争论的总的策略是什么呢?达米特认为就是进行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达米特之所以采取比较研究策略除了这一策略的可行性之外,关键还在于这一策略本身的优越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有助于减少盲目性,提高研究效率。鉴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这一问题的艰深性,做一些基础性的、针对性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而比较研究恰好可以满足这一要求。第二,有助于发现新问题。通过比较研究,容易显示出先前从未意识到或只是模糊意识到的东西。达米特提出做比较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促进一个“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产生,以便得出几个原则好让我们能够判断在什么情况下实在论是对的,在什么情况下它的对手是对的。
鉴于比较研究策略的可行性与优越性,达米特把它看作是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一个总的策略以及坚持反实在论哲学立场一个总的策略。在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过程中,达米特无时无刻不在运用这一策略。第一,比较二者的语义学基础。达米特认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实质在于语义学之争。实在论接受二值原则,认为陈述句具有独立于我们认识的真假值;反实在论则拒斥二值原则,认为对陈述句意义的说明离不开心灵和我们的知识,它主张一种诉诸直觉主义的语义模型。第二,比较二者的意义理论基础与逻辑基础,而意义理论与其核心概念——“真”密切相关。实在论所持的是一种以二值原则为基础的强的逻辑真概念,相应地,它也就接受以逻辑真概念为核心的真值条件意义理论。与此相反,反实在论对真概念作较弱的理解,它主张一种辩护主义的意义理论。在逻辑基础方面,实在论者接受经典逻辑,反实在论者则选取直觉主义逻辑。第三,比较不同题材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如物理世界的实在论与现象主义之争,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与构造主义之争等),以冀找到一些总体手段来指称任何一种争论题材。第四,比较不同版本的反实在论(尤其是具有还原论特征的传统反实在论与直觉主义)在反实在论方式上的差异。
比较研究策略是达米特反实在论哲学首要的、基本的策略,它贯穿于达米特整个反实在论过程之中,并构成了其他反实在论策略的基础。
二、语义上溯 转换论题
必须指出的是,“语义上溯”虽然是奎因哲学的一个专门术语,但并不是他个人独有的发明,而是自形式逻辑在弗雷格手里完成它的复兴之后,“这期间科学的哲学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作为深受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奎因等语言哲学大师影响的达米特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不论他是否专门谈论过:“语义上溯”一词,他其实一直都在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使用语义上溯这一策略。在探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达米特并不直接探讨有关对象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分歧,达米特选用的是“有争论的陈述类”(disputed class of statements)而不是“有争论的对象类”(disputed class of objects)。很明显,达米特在此是在运用语义上溯策略,即把所研究的问题上溯到语义学的层面。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一文中,达米特谈到了他之所以选用“有争论的陈述类”而不选用“有争论的对象类”说法的两个理由:首先,在有些事例中,例如,关于未来的实在论争论和关于过去的实在论争论似乎不存在有关的对象。倘若把事态算作对象,那就纯属诡辩了;其次,把一种实在论形态刻画为一个关于某种(推定)对象的论题是看错了方向。在这里,达米特所给出的两个理由实际上也是他运用语义上溯策略的理由。其中,第一个理由是较为浅层的,第二个理由却极具意味,它蕴含着达米特语义上溯策略的深层动机。对于这一深层动机,达米特给我们进行了一步步的展示。达米特是从数学哲学的角度加以说明的。他说,关于数学对象的新弗雷格派的柏拉图主义者,如赖特(Wright)和哈尔(Hale),仍然能够否认数学对象具有我们不能够认识的性质,而一个戴德金(Dedekind)主义者则相反,他主张数学对象是人类心灵的创造,同时却坚持认为,它们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具有了独立于我们认识它们的能力的性质。因此,在达米特看来,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不在于关于数学对象观点的分歧,而在于关于数学陈述意义说明模型的分歧。至此,达米特充分暴露了其语义上溯策略的深层理由和最终动机:语义上溯是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一个不可或缺的策略,语义理论是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关键。
三、自下而上 寻找基础
为了更好地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达米特在语义上溯策略基础上,又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策略。这一研究策略就是“从实在论与各色反实在论之间关于争论中的那类陈述的正确意义模型的分歧开始,而暂且抛开形而上学问题”这一策略,听起来似乎十分在理并且气势恢弘,然而达米特认为它会遇到许多困难。首先,我们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争论,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不断进行,争论的双方似乎都有道理,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方的论证在这场争论中的一些观察者中激起了反应,而另一方的论证也赢得了另一些人的赞同。但是,我们不知道确立争论双方是否正确的标准,因此,我们也不知道谁是这场争论的胜利者。其次,我们不能清楚地把握争论双方的内容。因为,这些形而上学的论证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图画、不同的隐喻。达米特认为,导致这一策略产生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正确理解意义理论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达米特从数学哲学的角度论证了这一点。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涉及到了数学对象的本体论地位与数学陈述说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问题是意义理论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数学中的体现。经过一系列详细的探讨,达米特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关于数学对象本体论立场的分歧并不影响关于数学陈述的意义说明。第二,关于数学陈述意义的说明对数学对象的本体论立场却具有根本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是说,意义理论是形而上学的基础,那种自上而下的研究策略颠倒了二者的关系,是必然行不通的。因此,达米特指出,必须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策略,寻找一个正当的(proper)意义理论,以此作为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这一特定形而上学问题的基础。
四、拒斥二值原则 诉诸直觉主义
达米特认为:“实在论学说的已一个共同特征是坚持二值原则——主张每一个命题都是确定地真或假的”。如数学实在论认为,若一个数学语句真,则它是由于获得某种事态为真,不管我们是不是知道这种事态,若这种事态不可获得,则该语句为假。与此相反,反实在论则拒斥二值原则。达米特说:“几乎所有反实在论版本,只要细加分析,均可表明隐含着对二值原则的拒斥。如数学中的直觉主义认为,数学语句是由数学家构造的证明而成为真或成为假。二值原则并不像实在论所说的那样包揽无遗。鉴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在语义学上的分歧,达米特主张把是否接受二值原则作为二者的分水岭。达米特的论证如下:
第一,语言意义的说明必须是语言理解的说明,亦即对意义知识的说明。意义由真值条件组成的论题之可接受当且仅当理解通过真值条件而构成的语句之可接受。第二,理解必定是公开可显示的。如果意义是由真值条件组成的,那么真值条件的知识必定可显示。要避免这种循环论证,我们将以一种更基本的方式显示对一语句的真值条件知识。这种显示是对特定能力的显示,亦即若一个语句真则可以知其真,若一语句假可以知其假的能力。达米特接着分析了这一显示的可能性。由于意义的知识必定是可显示的,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显示我们对该语句的二值真值条件的知识,因此,该语句的意义知识就不可能是二值真值条件的知识。这就表明二值的真值条件语义学不可能正确。
二值的真值条件语义学之不正确标志着实在论的困难与反实在论的初步胜利。为了进一步扩大反实在论的战果,达米特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策略——诉诸直觉主义。首先,达米特勾画出一种所谓“正当的”(proper)语义学模型。该模型就是对逻辑常项作直觉主义解释,并试图把这一解释从数学和逻辑推广到经验语句。这一推广的结果就是确立了一种新的证实主义形式——辩护主义。其次,在寻求语义学模型的同时,达米特进一步引入直觉主义逻辑作为其反实在论哲学的基础。通常,“直觉主义逻辑”指的是接受经典逻辑而不接受其中的排中律的逻辑。达米特认为它“尽管不是第一个非经典逻辑系统,却是迄今最有意思的一个”。
必须指出,达米特之诉诸直觉主义还出于一个实用的目的,那就是在与实在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中,比之传统的反实在论,直觉主义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传统的反实在论所共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还原论的方式来阐述关于争论类的陈述。然而,与传统的反实在论不同,直觉主义并不设定有任何描述(数学)证明的语言使其他的数学语言可还原为它。在达米特看来,这种拒斥实在论数学观的直觉主义办法是其他可行的反实在论形式的范例。因此,要反驳实在论观点就是应当遵循这个范例,依赖于一个关于争论陈述类的反实在论(非真值条件)意义理论,而不应该把它们还原为另一类陈述。一旦反实在论的论证脱掉还原论外衣,要打垮它们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总之,达米特在运用比较研究策略的基础上,结合语义上溯策略、自下而上策略和诉诸直觉主义等策略,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这一形而上学难题转换为语义学问题、意义理论问题和逻辑基础问题,从而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并坚持了反实在论立场。达米特的这一系列研究策略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它们不仅使我们深入地思考语言描述与客观实在的关系问题,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哲学问题的新视角、新方法,在学界激起了深刻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