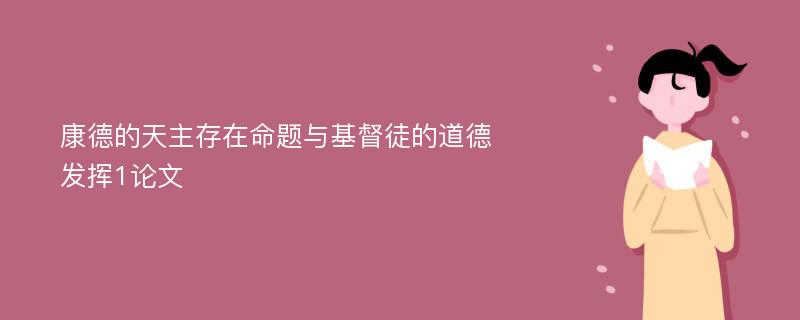
康德的天主存在命题与基督徒的道德发挥1
陈开华 神父
根据权威统计数字,目前,在中国社会中,有明确宗教信仰的信教公民人数近2亿,2中国共产党党员公民人数近0.9亿。3这两组数据显示,14亿4中国公民中,还有10亿人是无明确信仰的归属者。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并且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中共党员,以及那些已经拥有明确宗教信仰的信教公民,各自安身立命、成已成人,因此,他们并非福音的潜在皈依者。世界是一个让人“相遇”的空间,“对话”则延展了相遇的内涵;正是因着与他者“相遇”,才会产生进一步的“交谈”和“慕道”。在这个意义上,如何与那些无明确宗教信仰者“相遇”,就道德、信念、价值观等议题进行交谈,拓展彼此所据人性的深度,就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课题。
康德认为,理性实践意义上的“道德”意识,既能够解决哲学传统中仅仅从理性出发论证“天主存在”命题的困窘,同时,也能够为纯粹理性确立先验自由,以“拱顶石”般的确切观念支撑起其它——诸如灵魂不朽、天主存在观念的持存性和客观实在性。显然,厘清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意识”及其关涉到的三个观念,可以为基督徒在与他者相遇时,提供“交谈”的灵感,并且也可以为宗教信仰者充分发挥其宗教信仰“劝人向善”的参与社会功能提供足够高度的先导意向。
1.4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孕妇入院时及产后1个月的HAD 评分;②评价两组孕妇产后1个月的抑郁状况,具体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表(EPDS)[11]进行评分,评分≥9分为产后抑郁。③对孕妇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批判:传统上有关“天主存在”命题的不合理性
自启蒙运动以后,数学和自然科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于发现了更多的普遍定理而广为人知。这些定理,为人类揭晓了其学科对象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和必然性(necessity)知识。相反,“形上学”(Metaphysics) 却自笛卡尔 (René Descartes,1596-1650)开始就日渐式微:因着过于强调人的主性体,而导致“知识论”(Epistemology)取代了形上学,近代哲学遂因此失却“存有论”根基。近、现代哲学家中,康德(EmmanuelKant,1724-1804)、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等均从自己的立场,做了相应的补救措施,并据此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我们所关注的康德将他自己的批判哲学指向恢复形上学,意即,在哲学领域,寻找知识论后面的普遍性原则。
康德将形上学分为两部分:第一,研究人类感官经验所获得的知识的基本原则,此一知识的对象,乃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的对象,意即“感官经验的对象”;第二,研究超出感官经验的对象,意即处理好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以及天主存在这三个问题,这才是哲学最根本的慧命。因此,康德试图掀起一场“哥白尼式革命”,试图帮助人通过揭示人类自然经验的基础,处理时间和空间中的客观存有。感官经验的对象独立存在于人的理性之外,因此,这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对象,康德用“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来处理时空知识的问题。然而,自由、灵魂以及天主这三个问题却完全超出人类的感官经验之外,所有与之相关的知识,都发生在人的心灵里面,因此,只有通过“检验心灵的状态”,验证那些包含着这些先验对象的观念和原理的合理性,方才能够证明这些观念和原理后面的形上学原则。因此,在《纯粹理性批判》5当中,康德已经指出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以及天主存在这三个问题不能通过理性予以论证其合理性。
康德强调,传统上从思辨出发的“天主存在”命题的论证共有三种:(1)物理神学论证:从有关自然界的秩序经验出发,以感官经验为主,从因果原则逐一推导至最高的原因;(2)宇宙论论证:从感官世界中那些不限定的偶性经验出发,推导出那位“必然存有”;(3)存有学论证:以先验的方式,从纯粹观念推导出至高存有。这三个论证中,存有学(ontology)论证是基本论证,是其它两个论证的基础。因为“至高存有”(Sein,Being)乃是绝对必然存有,他是其它一切存有物(beings)的基础。同时,宇宙论论证又是物理神学论证的基础,意即在绝对存有的基础上,必然确定必然存有,因此,获得了经验世界和物理世界的论证基础。
康德从存有学论证开始批判了这三个论证的“无效性”。首先,存有学论证的问题在于,它混淆了观念。“天主”(Gott,God)与“存有”(sein)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性的内在联系,存有学论证视“天主”为一个先验观念,但是,“存有”却不是一个先验观念。在逻辑证论中,主词与述词之间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述词指涉主词的绝对立场,借此表达主词所指之物的有或无。因此,“天主存在”中的“存在”这个观念,就不是一个与真实直接有关的述词,其真实性取决于主词。那么,“存在”这个观念就不是单纯地从一个纯观念所能够必然推导而出,即便是涉及“天主是至高存有”这类观念。其次,康德亦指出“天主”只是理性方面的一个纯然观念,和其它纯然观念一样,只具备认知的主观约定作用,作为一个“预设”使知识论成为可能。至于“天主”本身是否存在,这是一个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问题(参阅KrVB618-670)。
相反,那必须通过实践理性来予以呈现。在《实践理性批判》当中,康德指出当我们为自己的行动拟定一条准则之际,那就必然连带预设了道德法则的有效性。实践理性,不证自明地表达了我们所相信的“意志自由”后面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于是,更高权威必然地指向其必然性条件:普遍性的道德法则或者绝对律令。普遍性道德法则的必然条件即是灵魂不朽和天主存在。6
二、论证:从道德的实践理性出发,“至善”观念作为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天主存在这三个命题之间相关性的内涵
康德进一步指出天主乃是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以及至善的根源、道德主体配享幸福的条件、理性存在者的道德性而存在。天主以“一位智慧的创造者”的身份成为人们分享幸福的惟一尺度。人们意欲使自己的意志与至善相适合,那就不得不将“仁慈”视作是最高的独立智慧。只有自己的善行建基于“仁慈”之上时,人们才能确保自己与创造者的意志的神性获得一致。那些将创造的目的设定在天主的荣耀之中的人们,即刻会发现一个事实:“再也没有比尘世中宝贵的东西更能荣耀上帝了,这说是:敬重他的诫命,遵循他的法则交付给我们的神圣义务,如果他的壮丽的部署还要使这样一种美好的秩序配上相适合的幸福而得以圆满的话。”(KpV A131)为人而言,天主首先是一个朝拜的对象,而非爱的对象。人们可以通过行善而获得爱,但是,却永远无法仅仅通过行善就获得敬重。敬重的条件比爱严苛得多,它要求道德主体遵循诫命、实践法则、履行义务,“以至于最大的行善也只有通过按照配享来施行,才给他们带来荣耀。”(Ibid)
康德有关“天主存在”的论证建基于其道德实践的理论基础上面。这个道德实践“要求”一个确定无疑的“公设”作为其论证内容的充分必然条件。意即没有这个预设,那么随后的一切论证将无法得以建立。这个不可质疑的预设即是道德法则。而“道德法则”的出发点固然是实践主体,但是,作为实践主体所追求的至善目标,却必然即是至善者的存有学预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至善”是理性于其理论应用中建立于道德法则的一个系统统一的目的性观念。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至善”变成了纯粹实践理性对象的无条件总体原则。而在《判断力批判》中,它又成为反思判断力在实践运用中创造性的终极目的观念。“论证的改变,主要决定于至善观念与道德法则之间关系的不同限定;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改变,则应当归因于康德对其形上学与道德哲学的坚持与奋斗。”7
微信的自定义菜单是微信与用户进行一对一交流的重要渠道。菜单功能是与本馆读者建立紧密联系的重要渠道,积极开发菜单功能能够增加用户黏度,不断壮大粉丝群体。如开发个人中心菜单,让学生在微信菜单下绑定读者证信息,能够在微信终端自助进行图书续借,查找本馆的馆藏资源,让用户随时随地了解馆藏信息,不用亲自来到图书馆,也能实现便捷自助服务。
(一)《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道德论证:至善是目的系统统一的观念
内服自拟的“宣肺通窍汤”,每日一剂,水煎服,早晚各一次,每次急火煎20分钟取汁200~300ml。基本方组成:荆芥、苍耳子、辛夷、藿香、柴胡、白芷、公丁香、黄芩、赤芍、升麻,葛根,石菖蒲、川芎、黄芪、路路通。
“至善”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是一个统一的、理想的观念。它是综合道德系统与幸福系统、道德目的论与物理目的论的一个基本观念。因此,作为一个纯粹观念,“至善”要着手处理的是康德三个问题中的第三个:“如果我做了我应当做的,我可以希望什么?”(KrVB833)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兼顾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乃是人类有关“幸福”的渴望的问题。康德说“一切希望都指向幸福。”(Ibid)幸福是所有偏好的满足,包括广度的多样性和深度的持久性(KrV B834)。因此,幸福并不能够因此而成为道德行为的动机。道德本身构成一个独立的系统,而幸福只是一个有条件的系统。
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如果一个命令是应当执行的,那么它必须是能够被执行的。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条件,符合所有道德法则的道德世界,在理论上,以观念的方式进行应当是可能的。并且,这个纯粹实践的观念,应当能够在感官世界产生影响,在人类历史当中有其客观真实性。因此,道德系统的先验性证明就自然地获致其答案。“我应当做什么”的答案即会是:“去做那使你配享幸福的事情吧!”(KrVB835)康德说,接下来的问题理所当然即是:“如果我现在如此行事,使我并非不配享幸福,我如何也可以希望由此能够享有幸福呢?”(KrVB837)于是,道德系统与幸福系统之间的关联,为康德而言,获得内在的统一性是可能的。理性自身的内在需求会必然性地回应这个关联,意即一个公正无私的理性必然会要求道德与幸福之间取得和谐一致(KrVB841)。即便在后期作品《实践理性批判》(KpVA199)和晚年作品《纯粹理性内的宗教》(KGSVI6)之中,康德依然坚持认为理性不允许道德与幸福最终互不相干。因此,每个人都会受到内在道德法则的推动,既为自身谋求幸福,同时“也是别人的持久幸福的创造者”(KrVB837)。这种以谋求幸福为目标的道德述求,康德称之为“自己酬报自己的道德性”。此一系统乃是“每个人做他应当做的”(KrVB838)存有必然性。
4根据第六次(最近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中国公民人口数据是13.73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引用日期2019年5月14日。
(二)《实践理性批判》:从促成至善的命令要求天主存在
在《实践理性批判》第二卷“纯粹理性实践的辩证论”中,康德再度依靠“天主存在”的“要求”处理形上学的问题。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公设”有两个:灵魂不朽与天主存在。
(1)作为纯粹实践理性之公设的“灵魂不朽”
在未来人才济济的形势面前,具备一定的自主探究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英语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一定会是一种优势。社会发展越来越迅速,互联网普及越来越广,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产出导向法指导下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教学模式的改变也将为学生大学英语的枯燥学习注入活力,提高学生学习的能动性,改掉他们长期以来的惰性。传统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化教学要求了,所以说新的教学模式可能会带来新的机遇新的发展,这也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应该向前迈出的一步。
在上述意义中,康德进一步呈现其人学思想与天主观。一方面,对于一个理性的,但却有限的存有而言,其道德完善的阶段性,在灵魂不朽与天主存在的两个先决条件中,找到了道德实践的内在依据:“惟有从道德完善性的低级阶段向较高阶段的无限进步才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善、无限者天主又为所有致力于道德实践的人,提供直观洞察,而非仅仅是理性认知的原则。康德说:“对于无限者而言,时间的条件是无,他把这个对我们来说无穷无尽的序列看作与道德法则的那种适合性的整体,而且他的诫命为了在他给每一个人规定的至善份额上与它的公正相符而毫不含糊地要求的神圣性,惟有在对理性存在者(存有)的存在的一种理智直观中才可以完全发现。”(KpVA123)于是,正是在从小善到大善、从比较恶的道德到比较善的道德的实际处境中,一个人始终不渝的坚守,获致道德实践上的“决心”。在这个决心的推动之下,他会坚持不懈、满怀希望地进步下去,并且“希望不论他的实存能够达到多久,甚至超出此生。”他会对可能自己曾经有过的“他的存在的某个可以预见的未来时刻”之类的想法分道扬镳,他也会不再在乎那些“与公正不相称的宽纵和赦免”。相反,他只在乎自己的持续存在与天主意志的契合与否。因为他知道,任何人的持续存在并非由他自己决定,恰好相反,取决于天主。只有超越时间的、无限性的天主才能“综观”持续存在、道德意义这类终极议题(参阅Kp-VA123-124)。
(2)作为纯粹实践理性之公设的“天主存在”
(三)《判断力批判》:天主存在的道德论证
从道德实践的原则出发,康德肯定了至善的首要性、道德性的必然完备性必然地指向“惟有在一种永恒中才能完全得以解决”,这也必然地触及灵魂不灭与天主存在的问题。这是理性实践所预设的道德性的最终归属。因此,从存在的先后顺序上来说,“天主存在”客观上是一个作为预设的根源性保障,同时,他也是幸福的最终嘉许者。在《实践理性批判》二章五节中,康德致力于论证幸福的最终指涉,“也就是说,导向一个与这种结果相符的原因的存在的预设,亦即把上帝的实存公设为必然属于至善的可能性。”(KpVA124)此一至善乃是人类意志的对象,与纯粹理性的道德立法必然结合。
“幸福”是每一个理性存有的状态,这种状态与他的整体愿望和意志直接攸关:他渴望幸福,他采取行动。因此,在期待与行动之间保持着一种和谐。道德法则是一条自由法则,为了获致幸福,理性实践者不能通过自己的意志而达成,他必然依赖自身之外的另外一个公设:“我们应当力求促进至善。”(KpVA125)惟其如此,至善作为一个公设,就统摄了一切的自然与不自然、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动机与环境,也因此为幸福与道德性的精确一致提供了基本保障。因此,“自然的至上原因,就其为至善而必须被预设而言,就是一个通过知性和意志而是自然的原因(因而是创造者)的存在者,意即上帝。”天主是“源始的至善”,是人类所期待的“派生的至善”(理想的、最好的世界)的基本保障,也是人类道德义务的基本条件。“既然至善惟有在上帝存在的条件下才是成立的,所以上帝存在的预设就与义务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就,假定上帝的存在,在道德上是必然的。”(Ibid)尽管这个道德上的公设所需,乃是纯然主观的,但是,惟有预设了这样“一个最高的理智”,那么,我们的道德义务才具备其合理性,这个世界才是可思议的;普遍性的道德法则与个人的道德实践信念之间才因此而产生与理性相符的内在关联。
对两个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验证。用X射线法测试大米标准品GBW(E)100377,将标准值代入回归方程(1)计算测量值为0.299mg/kg,实际12次检测均值为0.289mg/kg;用电化学法测试大米标准品GBW(E)100360,将标准值代入回归方程(2)计算测量值为1.901mg/kg,实际检测值为1.877mg/kg。
康德说,既便是基督信仰中的道德学说,也不过是建基于这样一个“至善”的观念上面。基督徒将至善界定为“天主之国”。建立在至善世界上面的道德法则是神圣的、不宽纵的,并且它要求道德的神圣性。尽管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和基督徒们都有共同的道德标准:素朴、明智、智慧和神圣,但是,基督徒却又有别于前三者。基督徒的道德更加纯粹,而不宽纵自己。这种道德意识,在剥夺了道德主体的此世自信的同时,又为他们建立起了一个更有力量、更有幸福内涵的希望之道:“即如果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所及地行为善良,我们就能够希望,非我们能力所及的东西,将在别的地方使我们受益,无论我们现在是否知道以何种方式。”因为,嘉奖他们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那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天主。基督徒期待幸福,他们就生活在幸福之中。就此而论,基督徒既有别于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也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道扬镳(KpVA128注一)。康德强调:“基督教的道德学说通过把理性存在者(存有)在其中尽心尽意地献身于道德法则的世界描绘为一个上帝之国而弥补了这一(至善的第二个不可或缺的成分的)欠缺,在上帝之国中,通过一位使派生的至善成为可能的神圣创造者,自然与道德达到了一种对二者中的每一个单独说来都不具有的和谐。”(Ibid)于是,理性存在者找到了履行自己义务的根据,他因此而满怀希望地活着。他活在永福的光照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吉尔松(ÉtienneGilson,1884-1978)建议基督徒要对康德的“天主存在”论证作出“真值”决定,他认为康德道德论证所具备的理性价值在于:“是某一形上学问题的一种哲学答案。”8
profitt=225884.3-8.31R&Dt+2.94R&Dt-1+7.42advertisementt-1.55advertisementt-1
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论”中,康德声称自由、灵魂和天主,这三个观念是纯粹理性不可避免的任务。而在《超验辨证论》中,这三个观念又成了形上学的探索目标。探讨这三个观念的目标是超验的,并没有任何人性自身的经验所能达致,因此,需要从纯粹理性的实践入手,重新开辟形上探讨的可能性。而形上探讨对这三个问题的处理,可以在知识论、道德哲学,以及先验神学的处境当中予以处理,意即: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以及我可以希望什么?这其中“我可以希望什么”,既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完善的人才配置机制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高效配置。目前社会需求对人才配置的机制的已经基本实现,但是仍然不健全,高校对于办学的自我约束机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也需要完善。大学生的就业市场化和教育的体制改革无法做到同步,这样仍然会造成两者之间的矛盾。继续医学教育学生在接受囿于计划体制下的专业培养课程后,又带着这样的制度和规则进入到另外一种具有明显差异性的体制中,这样会导致医学教育管理常见问题出现制度方面的因素。
一般无刷直流电动机结构简图如图1,主要由定转子、轴承、端盖、霍尔组件等构成,且空间较充裕。图2为某型双传感器微型无刷直流电动机结构简图,由图2可看出电机在结构上要复杂不少,也更为紧凑。图3为与其结构一致的实物图。由图可看出该电机小于1元硬币的直径(1元硬币直径为25 mm),长度小于48 mm,额定功率约为5.5 W,空载时转速可达将近20000 rpm,且为长时工作,能达到机载设备的各项要求。
康德进一步将此一“终极目的”与《实践理性批判》中所探讨的“幸福”做出了区别。幸福是人的道德目的中的一个维度,而非自然的目的,也不是创造的终极目的。人尽可能使自己幸福,意即实现一种圆满的生存状态,那是他最根本的目的。但是,幸福依然只会是人主观的目的,是有条件的目的。“幸福只能是有条件的目的,因而人惟有作为道德存在者(存有)才能是创造的终极目的;但是,就人的状态而言,幸福惟有作为按照那种协调一致的后果,才与那个作为人的存在目的的终极目的相结合。”(KUB436注一)在尘世生活中,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实践至善,抵达终极目标,意即幸福。幸福的客观条件即是“人与道德性亦即配享幸福的法则的一致。”(KUB450)
“终极目的”的问题在康德这里有着相当重要的人类学内涵,它和一个人之为人的本质、道德价值、幸福感休戚相关。“如果某个地方有理性必须先天地说明的终极目的成立,那么,这个终极目的就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服从道德法则的人(即每一个理性的尘世存在者)。”(KUB448)一个理性存有如果不能够在自由中原初地创造价值,世界上虽然有相对的目的,但是,康德敏锐地说,“这样的理性存在者的存在毕竟总是没有目的的。”(KU B449)但是,道德法则却不一样,它会为理性存在者设定并引导他趋附终极目的,让他在尘世中自由而可能地以追求至善为目的。但是,按照人的所有的理性能力,我们绝对不可能把通过道德法则为我们所提供的终极目的在“道德性”与“至善”之间取得一致,也不可能在针对道德而为的实践必然性与自然可能性之间取得一致。因此,理性要求我们必须设定一个道德世界、一个创造者作为我们的终极目的。这个设定取决于人的道德实践,于是,天主存在与理性实践之间必然地呈现为正比例关系,尽管它是主观意义上的道德性之所需。然而,它却是道德存在者的一个充足论证(参阅KUB450及注一)。就此而论,有的基督徒神学家从纯然神学的立场批评康德。他们认为康德的道德论证中,没有办法导引出融贯的天主教义,或者圣三神学。9显然,康德并没有计划为神学服务。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一种自然的神学却至少可以用做真正的神学的预料。”(KUB485)以道德证论为出发点的自然神学只能是将支持并规定理性实践的天主观念予以澄清,仅此而已。
三、价值:“天主存在”意义上的人类学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将有关天主的知识分作两类。第一类是既适合于天主,也适合于人类自身的“属性”:力量、知识、在场、善。这些观念被提升到最高的程度:全能、全知、全在、全善。第二类则惟独适合于天主:惟一神圣的、惟一永恒的、惟一智慧。这些观念不带有夸大的附加语,全部都具有道德属性。既然是“惟一性”,那其对象就不再受限于某一“属”(genera)或者“种”(species),所以,天主依次可以被表述为:神圣的立法者(和创造者)、仁慈的统治者(和维护者)、公正的审判者。“这三个属性包含着上帝借以成为宗教对象的一切,而与它们相适合,种种形而上学的完善性就自行添加进理性中。”(KpVA131注一)进一步,在《论神义论中一切哲学尝试的失败》中,康德指出天主的三种属性:神圣的,因为他是世界的立法者;仁善的,因为他是世界的统治者;正义的,因为他是世界的审判者。三个观念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三种特性中的一个绝不可以回溯到另一个,这三种特性循序构成了道德上的天主观念;其次,既不可能改变三种特性的顺序,也不损害以这一道德上的观念为基础的宗教。这三种特性的顺序,则由纯粹实践理性所决定。而理性实践首要的条件即是道德法则。有了天主作为立法者,那么,守法与义务之间才能取得一致性。10
早期的传统在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历经没落,反复调适,最终形成传统流失或者发明新的传统,这即是传统体育涵化必然经历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体育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时,由于各种传统均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所以这种神圣的对抗是双向的;而因为神圣与世俗具有同一性,是对现实的一种体悟,是世界上一切意识之源[17]。
明确了天主是人类道德实践的神圣立法者、仁慈的统治者,以及公正的审判者之后,康德最终给我们交待了他的哲学人类学。在种种目的的秩序中,每一个理性存有“就是目的本身”(KpVA132)。人不能被“某个人”,甚至天主也不能,“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而不同时是自身的目的”。人是实践道德法则的主体,因此人格中的人性必然地是神圣的,“是那种就自身而言神圣的,一般来说某种东西只是因为它并且与它相一致才能够被称为神圣的东西的主体。”由于视人的自由为最基本的“公设”,是理性大厦的“拱顶石”,是“灵魂不朽”、“天主存在”的先决条件,因此,康德强调“道德法则”建立在人的自由上面。道德法则的公设产生自“持存与道德法则的完整履践相适应这个实践上的必要条件”,因此,实际面对道德法则,自由的人必然会发挥其意志功能,以其“意志自律”在普遍法则与道德实践之间取得协调:“作为一种自由的意志,他的意志按照自己的普遍法则必然能够同时与它应当服从的东西协调一致。”(KpVA132)不过,康德也看到了自由公设的限度。他强调自由的实在性乃是通过道德法则,和一个具体的理知世界法则来阐明的;不过,对于这个理知世界的思辨理性,自由只能指出方向,却不能规定它的观念。于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一位无神论者是否能够过上完全有道德价值的生活?康德“假定”了两种对“天主存在与否”采取否定态度者的生活及其结局,来处理这个问题。
首先,无坚定信仰者,一钱不值。一个人由于认为论证“天主存在”命题证据薄弱,同时由于现实中所发生的那些“不合规则”的原因,而最终相信“不存在一个天主”,那么,他就会视道德义务为头脑中的产物。于是,道德义务就会对他失却约束力。由于被他视之为一钱不值,那他就会毫无敬畏地逾越这些义务。这样的人,即便他后来悔改自新,然而这种思想依然让他一钱不值。另一方面,如果他按照自己的意志真诚而无私地遵循道德义务,但是,常常因为怀疑是否存在一个天主,而立刻相信自己可以摆脱一切道德义务,那么,他心中的道德意向也就必然是坏的(参阅KUB451-452)。
在尘世中造就至善,乃是一个可以由道德法则所规定的意志方面的必然客体。不过,这其中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意向和道德法则得“完全适合”,方才能够成为至善的先决条件。这样就必然造就一种神圣性和完善性。这种完善性,又是道德实践方面的要求,同时,道德实践本身“惟有”向着“完全适合”的一种无限进展进发,方才具备纯粹理性实践的各项原则。如此,就必然涉及一个最基本的述求:预设同一理性存有的一种无限绵延的实存和位格性。意即,必然预设“灵魂不朽”作为先决条件。“灵魂不朽与道德法则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公设。”(KpVA122)这样一种预设,既补偿了思辨理性的无能,也为宗教的必要性增加了足够的论据。
其次,道德主义者,不能一辈子无动于衷。康德的另一个假定是说,一个诚实、善良的人坚持相信“不存在一个天主”,也不存在“来生”。那么,他就不会要求遵循道德法则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无论是现世还是来生。保持内心的自觉,他只想无私地促成善。然而,他的努力终究是受限的。尽管有可能在他心中偶尔会指望本性提供一种偶然的支持,但是却永远不能指望这种本性提供给他的,会是让他觉得有义务并且受敦促去实现的目的之间有一种规律的、持之以恒的规则。虽然他本人是一个正直的、和气的、善意的人,但是,他所身处的世界依然是欺诈、暴行、嫉妒四处横行,即便那些与他同样正直、善良的人,甚至那些相信天主是创造的终极目的人,总是遭受到无明的灾难,“被抛回到混沌的深渊”,因此,“这个善良的人”会有两种可能性的选择:要么因为看不到自己善良的结果,而放弃他一贯遵循的道德法则;要么持续地对自己内在道德上的召唤保持忠诚,不让自己内在的道德敬重感和高尚的、理想中的终极目的受到消弱。选择前者,让人自甘堕落。然而,如果选择了第二种,那么他不可能总是对道德上给他规定的终极目的无动于衷,他需要也极有可能会往前跨出一步:在实践方面,“至少为了对在道德上给他规定的终极目的的可能性形成一个观念,而假定一个道德上的世界创造者的存在,也就是说,假定上帝的存在。”他尽可以大胆作出这种假定,原因是这种假定与他自身的行为及理想不相矛盾(参阅KUB452-453)。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指出正是由于为了摆脱恐惧,人们产生了“神明”的观念。但是,理性会凭借“道德原则”对这些观念做出判断和裁决。“天主观念”的正确性,表现在它是内在性的、道德性的,它规定并补充了自然知识所丢失的东西,为一切事物存在的终极目的提供了基本保障。“天主”是一个具有种种属性,并有能力使整个自然从属于至善的神(KUB447)。“终极目的是这样一种目的,它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作为它的可能性的条件。”(KU B434)人在这个世界,乃是作为一种在因果性的目的论中,能够认识到自身的超感性能力(自由),和因果性法则的存有。他意识到自己是能够将自己预设为最高目的客体,意即至善的实践者。作为一个道德存有,他不需要问自己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他的存在本身即是最高目的,他能够尽己所能使整个自然都服从这个最高目的。“人就是创造的终极目的。”(KUB435)假设没有这个终极目的,人世间相互隶属的目的链条就无法完备地建立起来。相反,在这个世界上,惟有在人里面,我们才能发现道德目的的无条件性,因此,“惟有这种立法才使人有能力成为终极目的,整个自然都是在目的论上隶属于这个终极目的。”(KUB436)
四、结论:如何“发挥”功能,如何“把握”契机
2014年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宗教的本质是一种有神论世界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宗教“在劝人向善方面有很多智慧,有很多有益的阐述”。112019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在最近一个阶段内所要做的、与宗教相关的工作方向是:“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12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有明确的宗教信仰者或者宗教团体如何发挥自身的作用?如果不从纯粹的宗教教义出发,康德的宗教哲学能够为基督徒提供什么样的启发,在“劝人向善”方面发挥其道德优势呢?本文前言的“问题意识”中已经设问,在基督徒与他者“相遇”之际,康德的道德论证能够为相遇双方提供什么样的“交谈”灵感呢?
首先,追求至善和幸福是人的根本需要,这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因相遇而交谈的道德理性实践基础。本文研究显示,基于道德上的理性实践所需,康德依次论证了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天主存在三个命题的必要性。同时,康德也指出获得至善的前提条件是我们需要具备一个道德性情来帮助我们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中,都能够做出相应的道德行为,因此,“灵魂永恒”和“天主存在”就必然地成为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唯其如此,才能够保证一个理性存有获致生存论方面的意义。为康德而言,凭借其中的任何一个先决条件,即可解决道德实践方面的“二律背反”。意即,让人在实践道德之际,获得意志方面的自由。13为此,康德指出,“意志自由”乃是纯粹实践理性的第三个条件。因此,康德给我们的启发将会是,追求至善和获得幸福乃是生而为人的基本态度,然而,至善和幸福又是如此地遥不可及,因此我们在仰望星空之际,也不能忽略脚踏实地的在人间作光为盐。我们不能够将追求未来的幸福作为行善的动机,相反,应该坚定地以服从义务或者道德法庭作为行善的动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出于获得未来的幸福而行善,乃是出自他律的不自由行动,这种情况下的行为,并不具备任何的道德价值可言。人不是任何理由、任何人的手段,相反,他是目的,在智慧、正义、勇敢、节制的德行实践中,他以至善的名义趋赴至善之境。他深信即便是愉悦、财富、荣誉等都只是人——无论是自善,还是共善的努力——达致目的的手段。自觉自愿的实践理性,已经让他生活在幸福之中。在基督信仰中,“圣言成为血肉”的降生神学深刻地凸显了人的价值:天主子降生成人,正是为了让人分享天主的神性。因此,基督徒可以真诚地和相遇他者交谈:就在出于服从道德法庭而产生的善行这件事上,所有人已经获得了幸福。通往至善,并且在至善的光照之下行动,这本身即是一个崇高无比的道德行为。
其次,对于未知世界的敬畏感,既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幸福,也会在他们面对道德抉择,而不愿再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时,道德意义上的“天主”会及时援手。设定存在着一个道德上的世界创造者,会赋予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方面一个更大的勇气,他会更大程度地因此而获致理性上的澄明、意志上的自由。从民俗角度来说,中国人敬畏“举头三尺神明”;从道德立场而言,人会因为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而受到良心嘉奖,也会因为“明人做了暗事”而饱受良心煎熬。循此可鉴,承受精神上的嘉奖,是如此地吸引人心。因此,这些经验可以为基督徒提供一个普遍共识,至少可以在理性上发挥信仰范畴中“劝人向善”的心理认同功能。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它会为下一步,基督徒将自己“因信仰而更新”的宗教经验“分享给”他者提供人性论基础。基督徒的“更新”经验,为这个世界而言,是如此地难能可贵。是对这个有情世界最具真情的祝福。基督徒会展示出他们那出于神性关系中,以“爱”为出发点的道德义务。这义务要求他们毫无保留、毫无目的地走向他者。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Levinas,1906-1995)邀请我们珍惜与他者的关系,“面对面”的他者,乃是“神明显示”。他者对我并非无关紧要,这种显示能把意义带入存在之中。同时,只有通过他者,我们才能与天主相遇。“我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确定上帝,而不是采取相反的途径……当我应该对上帝说些什么时,我总是从人的关系出发。”14因此,将自己视作礼物,慷慨地走向他者的人一生行善,在光中行走。相反,因为圣爱盈溢,真光普照,他们在地若天、当下即道。他们善待自己,善与人同,爱国爱教,借此临现天国。人生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没有明确终极目的的漫长人生中,要尽其一生聆听良知、忠于允诺,并且持之以恒地“行善”,那无疑是在痴人说梦。因此,“天主存在”作为一个由“理性对话”到“理性实践”的生命课题而言,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保证。
最后,对于人性,我们需要一个整体意识。尽管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天主”是一个实践理性上的公设,但是,它却是人性因之而成全的基本保障。“天主”是存有之“最”,是这个世界奥秘的最终诠释。康德意义上的“天主”是神圣的立法者和创造者、是仁慈的统治者和维护者、是公正的审判者。因此,对于人生,尤其面对苦难,一个接受“天主”的人,他将会获得一个更为成全的理解;对于人性,他将会因之而获得更富有仁慈之心的接纳;对于自身,他会有一个更接近实相的自我接纳。“灵魂不朽”的观念会让他对自己的善行更有信心,不由自主地投身于心甘情愿为别人而活的献身性行动之中;“天主存在”的观念让他最终明白正直、和气、善意的道德意识本源性地来自人性,而人性的基础是作为“第一原理”(archē,principle)的天主。在从正面、反面考察了康德的宗教哲学之后,汉斯·昆(HansKüng,1928-)公允、正确地理解康德:如果我们想过一种真正的道德生活,必须预设天主,“这里存在着——在现代世俗化和解放过程中——康德的伟大思想:上帝应该被理解成人的道德自主可能性的条件。康德非常正确地不让矛盾、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侵蚀现实人存在的领域。”15因此,笔者认为,在“天主存在”观念的光照之下,对于自身命运、家庭生活、社会关系这些人性基本议题,任何一个理性存有将会因此而获致更为真实、整全的理解。他会与爱、公正、慈悲等德行一生相拥。他本然地活在真理的自由与实践道德的勇气之中。他是一个趋赴圆满幸福的存有。
综上所述,根据本文的研究,我们认为,一方面,相遇产生道德:基督徒在与他者相遇、在参与自身国度的繁荣进程中,既可以提供普遍人性经验的广度,也可以见证造物主至善至美的深度。他们是属天公民,也是在地赤子。受召于内在神性,他们见证美善灵境;发扬乎日用人伦,他们将爱心实践于兄弟姐妹。另一方面,交谈互惠彼此:理性固然有其限度,神学也必然自我设限,因此,尽管神学不能直接建基于自然神学上面,但是,康德以道德证论为出发点的自然神学却“能够使一种为了理性最高的实践应用,而充分地规定上帝观念的神学的需要变得明显。”(KUB485)准此,在理性哲学与宗教经验的“交谈”中,一个个获致整全至善观念光照的理性存有将会美丽地脱颖而出,在日趋成全的生命进程中,内圣外王、经世致用。
1本文曾经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云南天主教中国化研讨会”(2019年5月24日)口头发表。
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发布日期2019年4月3日。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s://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26514/1626514.htm,引用日期2019年5月14日。
3中共中央组织部:“2017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发布日期2018年6月30日。数据来原:共产党员网:http://news.12371.cn/2018/06/30/ARTI1530340432898663.shtml,引用日期2019年5月14日。
(10)绿色建筑评价软件实现了以绿色建筑新国标为基础的绿色建筑预评估功能,提供了技术路线指导、绿色建筑地图、具体条文解析、专业提资要求等模块,并附有大量的国内绿色建筑设计要点实例,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得力的软件工具。
尽管,每个人在理性上都会以“做其所应当”作为实践道德理性的目标,但是,在实际上,却并非总是得心应手,并非每个人的行为都能够合乎那普遍性的道德法则。因此,理性会发现无法在幸福追求与道德行为之间取得一致。不过,也只是在这一点上,理性发现了至善的可期待性。可欲,不可至的至高理性按照道德法则发布命令。至高理性本身即是至善,至善是其自身的原因(KrVB838)。康德将之称作“至善的理想”、“至高本源善的理想”。“我把这样一种理智的观念称为至善的理想;在这个观念中,与最高的永福相结合的道德上最完善的意志就是世间一切幸福的原因,只要这幸福与道德性(作为配享幸福)处于精确的比例之中。”(Ibid)因此,“上帝(天主)和来世是两个按照纯粹理性的原则与同一个纯粹理性让我们承担义务不可分割的预设。”(KrVB839)在“至善”这里,才能够合理地解释人之所欲的原因。它也是人之所欲的对象,是道德实践的“先验理由”,是作为道德动机的希望对象。“天主存在”以其作为“至善”的预设,为道德实践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道德法则本身对人没有什么约束性,然而,一旦明确了道德法则与天主之间的有关,那么我们的道德实践、理性实践就找到了足够稳定的基础。
5本文引述康德的三大批判文献中译本是《康德著作全集》(1-9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10年。根据国际惯例,第三卷中的《纯粹理性批判》简写作KrV,第五卷中的《实践理性批判》简写作KpV,第五卷中的《判断力批判》简写作KU。
6正是在否定了论证“天主存在”的传统命题的基础上,康德提出了自己在论证“天主存在”命题方面的“道德论证”模式。从1755年开始,康德在《一般自然史和天体理论,或按照牛顿原理对整个世界结构体之状态和机械来源的试验》和《形上认知之首要原理的新阐明》中首次处理“天主存在”命题的论证以降,至1781年发表《纯粹理性批判》期间,进行了多次有关“天主存在”命题的论证尝试:1763年,《证明天主存在的唯一可能证据》;1770年,《论可感与可理解世界的形成与原则》第四章“论可理解世界的形式原则”。不过,1755-1770年间,康德共提出了三种六个有关“天主存在”的论证,其中包括后验的物理神学论证、实体共融论证,以及先验论证等。所有的尝试都以“知识论的实在论”出发点,竟至于康德本人也不甚满意,因此,才会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重新处理这个问题。即便如此,从1781年的《纯粹理性批判》提出“道德证论”开始,康德又再四易其稿,才最终于1793年在《纯理性界内的宗教》中最终完整表述了自己的在“天主存在”命题上的论证体系。具体来说,康德先后在以下著作中,反复修正、完善自己有关“天主存在”的论证:《纯粹理性批判》的〈超越方法论〉第二部分“纯粹理性的法典”(1781)、〈何谓思想中定方位?〉(1786)、《实践理性批判》的〈纯实践理性的辩证〉(1788)、《判断力批判》的〈附录:目的论判断力的方法论〉(1790),以及《纯理性界内的宗教》第一版序言(1793)。因此,康德论证“天主存在”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1755年至1793年之间的间隔是35年,而1781年至1793年之间的间隔是12年。这种情况在康德的理论发展体系当中,是相当罕见的一个发展过程。在此漫长过程中,康德经历了从知识论过渡到先验形上学的理论发展过程。换言之,康德不但批评了前人针对“天主存在”所做的论证,自1781年开始,他也放弃了自己此前在同一议题上所作一切努力——物理神学论证、存有神学论证,以及实体共融论证,相反,他改弦更张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从道德形上学的立场来充分论证“天主存在”的命题。目前中文世界对于康德宗教哲学的研究专著有:赵广明:《康德的信仰:康德的自由、自然和上帝理念批判》(南京:江苏人民,2008);李艳辉:《康德的上帝观》(北京:师大,2010);张雪珠:《哲学家论上帝:亚里斯多德、多玛斯、康德、黑格尔论证上帝》(台北:唐山,2013);傅永军:《绝对视域中的康德宗教哲学》(北京:社科文献,2015);尚文华:《希望与绝对:康德宗教哲学研究的思想史意义》(南京:江苏人民,2017);贺方刚:《情感与理性:康德宗教哲学内在张力及调和》(北京:社科,2017)。
7张雪珠:《哲学家论上帝:亚里斯多德、多玛斯、康德、黑格尔论证上帝》,台北:唐山出版社,2013年,257页。
8吉尔松著,陈俊辉译:《神与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7年,109页。
2.6 施工安全与企业法人的关系企业法人是第一责任者。在我们走向依法治理国家的形势下,建筑安全也将走向依法治理的轨道,因此,企业法人对本企业的安全负有全盘责任。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安全管理原则,企业法人对员工的生命安全负全责,在经营决策上必须顾及安全,把安全摆到企业运作的非常重要的位置。
9参阅卡维里著,陈永财、蔡锦团译:《上帝论:全球导览》,香港:基道出版社,2007页,154页。
左达把钢筋扔掉,道:“干什么?我还要问你呢,我以为你是要债的,差点把你杀了。嗯,怎么是你?我约的可是张仲平,他人呢?”
10康德著,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10年,第8卷,260页。
我国最大的秸秆热电项目—辽宁阜新阜蒙县生物质热电工程一期(18MW)于2016年12月底实现并网发电,年发电量达3.2亿kWh。该项目是辽宁省重大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总建设目标是装机容量达到48MW。主要以玉米秸秆、花生壳等为燃料,秸秆灰渣作为有机化肥,实现了节能、减排与循环利用[23]。
11《把祖国的新疆建设得越来越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新疆考察纪实》,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4日,第1版。
12http://www.gov.cn/premier/2019-03/16/content_5374314.htm,引用日期:2019年5月14日。类似的阐述亦见:《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21日,第1版。
13沃德著,陈明瑶、陈晓坤译:《从康德出发》,黑龙江:黑龙江出版集团,2017年,194页。
14转引自傅佩荣:《一本书读懂西方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270页。
15汉斯·昆著,许国平译:《上帝存在吗?——近代以来上帝问题之回答》,香港:道风书社,2003年,199页。
标签:基督徒论文; 中国共产党党员论文; 中国先进生产力论文; 中国公民论文; 道德论文; 命题论文; 天主论文; 康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