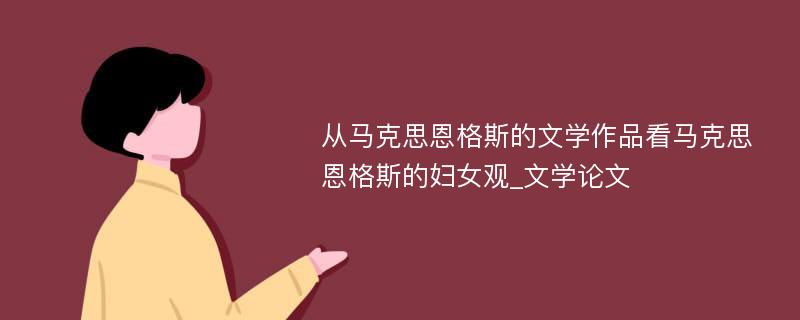
从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著看其女性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论著论文,看其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蕴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著中的女性观:各民族远古神话反映出,母系社会中女性居于被崇拜地位,由于异化劳动而产生的私有制,造就了人与人的对立关系和女性被压迫的社会悲剧;在男性中心文化统治的漫长社会中,文学作品反映了女性争取性爱自由、婚姻与爱情平等而进行的反抗,这是女性人格意识觉醒的第一举动,然而不是女性解放的最终出路;马克思恩格斯引导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女作家,将艺术视角引向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揭示了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女性彻底解放的制高点这一历史真理。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文艺论著 女性观
蕴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著中的女性观,体现着他们对人本质问题认识的全部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美学的宏观思想体系中,确立女性作为自然的人、社会的人、精神的人的价值和意义,从各个层面上揭示了女性是人类文化和人类解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为实现无产阶级与全人类解放的社会理想、为“实现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的审美理想而斗争。他们在关注全人类的同时,也必然地将目光投注于深受压迫的女性:一方面通过文学这面社会的“镜子”,审视女性的处境、遭际、命运和出路;另一方面,通过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审视,通过对女作家作品的关注,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形成了科学而又完整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女性才能获得彻底解放的论断,对于不断寻找自我,探索妇女解放的当代女性文学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女性达到角色面貌的新境界及其在世界中的最佳定位有着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
一
马克思在谈到古代民族的思想历程时写道:“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期”〔1〕。 各原始民族都曾通过神话这种原始思维方式,记述自己的古代社会图景。虽然各民族神话在发展时序和形态上,所反映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精神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对于人类社会早期女性地位的叙说,却有着很强的相似性。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女娲抟黄土创造人类,当天塌地陷、洪水猛兽肆虐的大灾大难之际,女娲炼五色石修补苍天,断鳌足支撑四极,杀死了猛兽,制服了淫水;在古埃及的神话中,奉天为母,抑地为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中,爱情与生命女神伊士塔尔为拯救植物神闯入七重地狱,从而使草木复苏,大地欣欣向荣;在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与他的母亲——“胸脯宽大的地母”盖娅结合,生下了六男六女十二位天神。他们各司其政,先知先觉的普罗米修斯用泥土塑造了人的躯体,智慧女神雅典娜把灵魂和呼吸注入了人的身体,使人获得了灵性,从而成为大地的主人。这些文明古国的神话向后人昭示了一个共同的信息:人类之初,女性与男性不仅是和谐平等的,而且处于被崇拜的地位。原始民族“女性崇拜”意识造就了创世造人、匡时济世的“女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神话中的女神的地位表明,在更早的时期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2〕。恩格斯晚年根据大量的人类学调查研究资料, 系统地考察了人类的演化过程,充分肯定了摩尔根、巴霍芬等人“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3〕母权制社会是男性崇拜女性、女性崇拜自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女性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亲的身份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4〕。
古希腊神话较之其它民族的神话,更具有完备的体系。它对原始片断的神话传说进行了集中和改造,以完整的神界故事折射出人类原始社会,生动地再现了人类从原始社会步入阶级社会的历史进程,汇集了父权制社会取代母权制社会的丰富的历史资料。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到古希腊神话故事中,探求女性社会地位沦落的“斯芬克斯之谜”。恩格斯晚年根据马克思遗言写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堪称女性研究专著。在这一论著中,恩格斯大量列举荷马史诗和悲剧作品,揭示了伴随奴隶制而出现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是以“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5〕从此, 女性由“女神”的祭坛上坠入了“女奴”的深渊。造成女性地位沦落的根源,恩格斯认为不是宗教观念的改变使然,不是性别差异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也“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而是“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6〕。 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表述了他的观点:“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7〕两性的对立是阶级对立的孪生物,女性被压迫是阶级压迫的特殊表现形式,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女性被压迫的阶级实质决定了父权制取代母权制,不可能是温良恭俭让的和平过渡,它经过了剧烈的抗争。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奥列斯特》,在一个古希腊贵族首领的家庭冲突中,浓缩了那个时代刀光剑影、血泪烟尘的社会特征,代表母权制地位的克丽达妮娅杀死了丈夫阿伽门农,代表父权制的奥列斯特为父复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孰是孰非?引起了维护母权制的依理逆司神与维护父权制的阿波罗神的激烈的辩论,最终女神雅典娜以审判长的资格投了奥列斯特一票。这一票标志着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维护母权制的依理逆司神“终于也同意担任新的职务,转而为新的秩序服务了。”〔8〕希腊早期神话中代表女性崇拜地位的雅典娜,在悲剧时代浑然不觉地演变为男权的保护神。恩格斯详细地叙述了《奥列斯特》的剧情,断言这部作品“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的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9〕并指出, 父权制取代母系制是“人类所经历的最激烈的革命之一。”〔10〕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将巴霍夫、摩尔根等人类学家对母系社会的确认与进化论和剩余价值论相提并论,是因为这一确认从人类学角度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客观历程,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十分有力地说明了女性对人类历史不可抹煞的重要推动作用。人类个体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与群体生存所需要的自身生殖,形成了人类的两种基本生产,“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11〕原始社会女性同男性在生活资料的生产上最初是平等的,由于女性所从事的采集性的生产劳动,由采集而形成的农业劳动,以及女性在共产主义制家庭中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愈来愈成为氏族成员生活的主要保障,使女性地位日益提升,特别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在群婚制社会中女性具有生殖的独占性,“谁是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却是知道的,……那末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12〕原始社会女性在人类的两种生产中都占据着优势,确立了女性受尊敬的崇高地位,各民族神话中表现出的女性崇拜意识,是女性崇高地位的真实反映。
巴霍芬、摩尔根等人确认母系社会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为马克思恩格斯探求人与人、包括两性之间对立关系形成的根源,进而探求铲除对立关系根源,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历史依据。早在1844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本质和私有制社会中人的本质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马克思提出劳动是人的本质,因为劳动是人的根本需求,人类的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创造而发展的过程。但在私有制社会,人类特有的创造性劳动,成为被迫性的劳动,劳动产品不为劳动者所有。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愈多,自身失去的也就愈多,人在劳动中体现的人的自由创造的本质被否定,劳动本身及劳动产品都成为劳动主体的对立物。这种异化劳动造成了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而“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它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13〕财产私有、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两性对立,均为异化劳动所造就的社会悲剧。随着私有制的高度集中和强化,女性社会地位日益恶化,女性被排斥在社会劳动之外,女性所承担的家务劳动也丧失了公共性质,它不再涉及社会,成为单纯的私人事务。成为家庭奴仆的女性,其生殖是为了替男性传宗接代,生产男性财产的继承人。甚至女性肉体也成了供男性消遣的“商品”,女性难以得到生命的快乐,正如马克思所说:“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出了人在对待自己本身方面所经历的那种无限的堕落”〔14〕,女性变成了“女奴”,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本质异化最惨痛的悲剧。
二
母系氏族社会女性辉煌的时代一经消失,人类社会变成了男性的社会,人类历史变成了男性的历史,人类语言文字为男性所垄断,变成了男性的话语和男权统治的工具。对这一人类文化现象,法国当代哲学家、文艺理论家雅克·德里达给予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人类社会很久以来是“菲勒斯中心”(男性中心),也是“逻各斯中心”(词语中心),他将两个词复合为“菲勒逻各斯中心”。人类社会长久地被男权所主宰,女性被厚重的文明帏幕遮蔽在人类文化舞台之后,只有在文学作品亘古不衰的爱情叙说中,还留着女性的身影。马克思恩格斯透过缠绵悱恻的爱情面纱,将男女性爱纳入了历史、社会、阶级等人类社会关系中进行审视,揭示女性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本质。他们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必然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15〕“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16〕“是纯粹人的关系”。〔17〕性爱关系作为人的自然本质而非动物的自然本质,必然地体现着人的各种社会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以性爱为标尺,判断“人的整个文明程度”,“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说来成为类的存在物,对自己说来成为人并且把自己理解为人”,“人的自然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18〕可以说,性爱是马克思恩格斯衡量男权统治文化情境中女性地位、女性价值的一个重要砝码。
围绕着对欧仁·苏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施里加等人进行了一场哲学与文学的论战,其中爱情是论争的一个重要问题。施里加在评论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时说,“意志加爱情是属于理论领域的”,“是同情欲相对立的”。他认为欧仁·苏塑造的理想人物鲁道夫是一位克服和战胜了情欲,改邪归正,继而用理性精神改造现实的英雄,妓女玛丽花经过鲁道夫理性的改造,从情欲中洗涮出来,成了“自己有罪这种意识的奴隶”,最终皈依了上帝。马克思恩格斯淋漓尽致地剥下了鲁道夫的伪装,指出他的理性和道德”是纯粹的虚伪”,他不过是“把自己邪恶的情欲发泄描述为对恶人情欲的愤怒”〔19〕。鲁道夫的私生女儿玛丽花连同她的母亲被抛弃而被迫卖淫是私有制的罪恶,其直接原因是鲁道夫玩弄女性的恶果,绝非出自于女性“情欲”的自由。鲁道夫所谓自我改造,依然以牺牲女性为代价,他对玛丽花的拯救只是统治压迫女性方式的变换,被他解救的玛丽花,从男性淫乐的“商品”和“做买卖的对象”,变成了禁欲主义的殉葬品,不仅丧失了人应有的社会价值,而且做为自然人的意义也丧失殆尽。施里加对小说的评论,“不是要揭露被掩盖的东西而是要掩盖已经被揭露的东西”〔20〕,同时,“把人身上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一概看作与人相左的东西,而把人身上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一概看作人的真正的所有。”〔21〕在施里加的眼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玛丽花是社会罪恶之源,制造罪孽的鲁道夫却是道德家和救世主。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的秘密》的分析批判,揭示了“文明条件下”产生“野蛮”的秘密是私有制,通过这一揭示说明一个事实,“菲勒逻各斯中心”是私有制的产物,作为“主奴关系的大卫道者”的鲁道夫,同时是“菲勒逻各斯中心”的化身。欧仁·苏寄托在这一形象身上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不但不可能使女性在爱情中获得自由、平等,而且在违背生活本质、曲解社会生活的艺术描写中,极大地扭曲了女性的尊严和人格。
对性爱自由的追求,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第一举动,因为“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上个人性爱的”,“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22〕处于男性统治下的婚姻对女性而言,更谈不上性爱的主体权和爱情幸福,女性的灵与肉不属于自己。特别是在中世纪基督教的统治下,性爱被贬斥为万恶之源,文艺作品也因驱散不尽的人间烟火而几经禁绝。基督教最主要的训诫是:这个世界因为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夏娃而遭到诅咒,“性爱是万恶之源,”这些训诫实际上是在说:“女性是万恶之源,”女性是祸水。所谓“拔本塞源”的禁欲主义教条就是对女性肉体和灵魂的严酷禁锢。恩格斯以热列的笔调赞扬中世纪市俗文学中所反映的“骑士之爱”,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甜蜜的通奸,称那些描写自然、健康肉欲,反映男女平等相爱的作品是“爱情诗的精华。”〔23〕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性爱关系,“是以所爱的互爱为前提的”〔24〕,女性从中享受到人性的欢乐和主体的权利。
中世纪市俗文学高举性爱的旗帜,冲决了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统治,引导了文学创作人性解放潮流。对此,恩格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性爱特别是在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25〕中世纪性爱文学所获得的这种历史意义,在于它体现了“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26〕在平等自由的爱情关系中体现了女性对自身生存价值的追求和对不合乎人性生存状态的精神反抗。
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从深层反映女性地位的个人生活领域,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家庭模式的沿袭和演变,深入思考社会发展规律,并从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作为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标志。这种历史主义的女性观同样渗透在他们的文艺思想中。恩格斯在论述巴尔扎克时指出,《人间喜剧》“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从摆布是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27〕建立在财产继承关系上的封建家庭和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资产阶级家庭,都是以男权统治为支柱的,“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28〕,“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们的经济统治的简单后果。”〔29〕
觉醒的女性,不仅要在性爱中实现自我,也势必摆脱束缚女性的家庭,追求人格的平等独立。当挪威作家易卜生把“社会问题”的艺术触角敏锐地深入到家庭时,产生了娜拉的离家出走。娜拉的家庭不乏爱情,但娜拉需要丈夫帮助她脱离困境时,她发现自己与丈夫并不处在同一地平线上,看似温暖的家庭里不允许娜拉的独立人格,她只是丈夫眼中“会唱歌的小鸟”、“快乐的小松鼠”。娜拉猛然醒悟,当丈夫不无真挚地表白:“你是我在世上最爱的人了!”“不管怎样地爱你,男子的名誉是不能牺牲的。”娜拉回答:“为了这个,不知有几百万的女子做了牺牲品!”丈夫向她提出女性最神圣的责任是对丈夫、对孩子的责任,她坚定地说,对自己的责任“是同样的责任”,“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娜拉空谷足音的呐喊,发自她觉醒了的女性人格意识、人格尊严。《玩偶之家》引起诸多社会评论家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保尔·恩斯特与海尔曼·巴尔的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中的女性”的论辩中,恩斯特不仅没有正确阐释易卜生作品所揭示的女性命运和社会实质,而且提出女性无需斗争,只要消极等待生产关系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男女平等。巴尔抓住了恩斯特的错误,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唯心主义,由此得出“女性问题不过是性别问题”,“女性不过是一块肉”。恩斯特把唯物主义“当作现成工具,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将挪威女性在文学上的反映纳入德国小市民的范畴,抹煞了挪威女性人格意识的觉醒和反抗的社会意义。巴尔则彻底否定了女性存在的社会价值,把女性还原为只有自然本能的“雌类人猿”。恩斯特与巴尔殊途同归,以不同的方式将走出去的“娜拉”纳入男权的刀斧之下。恩格斯指出,娜拉不仅具有女性的追求,而且是整个挪威民族性格和小资产阶级首创、独立的时代精神的写照。恩格斯对《玩偶之家》的评论,将女性从性爱表现中自然的人提升为社会的人,把家庭中女性的角色置于整个民族、阶级的进程中,思考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出路。有更多的评论家关心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是的,那个社会不会为娜拉提供更美妙的归宿,易卜生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不可能彻底解决女性的出路。但娜拉敢于挣脱没有人格的爱,走出不平等的家庭,矛头对准了丈夫这一男权文化的直接体现者。她放弃的不是一个家庭,而是对一段历史的告别,这是女性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娜拉唤醒了世界上一代女性。我国“五四”时期站在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前列的一大批女性,如冰心、丁玲、冯铿、张爱玲、庐隐、白薇、石评梅……,她们的人格和她们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无不萦绕着娜拉灵魂的悸动和精神追求。
三
马克思恩格斯的女性观的最终目标是女性解放,女性解放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有着统一的实质和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将女性的解放视为全人类解放不可分割的部分,视为衡量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重要尺度,“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30〕,“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31〕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深深地蕴含在他们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中。现实主义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思想的核心,集中体现了为他们社会理想所统摄的审美理想,解放全人类的社会理想,决定着他们审美的目光凝定于具有直面人生、揭示社会生活本质特征的现实主义,从而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的命运和前途的思考,自然而然地成为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内涵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对欧仁·苏和施里加的批判,表明了他们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滥觞。在《神圣家族》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设专章就女性解放问题与之论战。在欧仁·苏和施里加看来,女性卖淫,杀死婴儿,是由于“缺少一条惩办诱奸者并把忏悔和赎罪严厉惩治结合起来的法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鲁道夫未能了解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状况的非人性”〔32〕,因而不可能改造女性受压迫的处境,为女性提供解放的出路。他们大量引证了明确提出男女平等、女性解放口号的第一人——傅立叶的有关论述,说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道德和法律,是为私有制的“主奴关系”服务的,那种不触动私有制生产关系,企望借助道德、宗教的力量和法律的改良实现女性解放的愿望不过是“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对欧仁·苏、施里加等人所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主义”文学思想的批判,打破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对现实的歪曲和脱离现实的毫无意义的抽象”〔33〕,引导文学从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从“伪善”和“空想”转向现实,从主观唯心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在真实地反映人类社会关系中寻求人类和女性解放的正确途径。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使女性冲破家庭樊蓠、回归社会生产的历史气候,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34〕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将女性推向了社会,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这一进步并没有将女性从男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是将女性作为资本家榨取高额利润的廉价劳动力,使女性承受着更为直接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回归了社会生产,置身于不合理社会生存环境的女性跳出了爱情、婚姻的狭小天地,将实现自我价值、自我解放的追求投向社会,产生了与“人权平等”、阶级反抗具有同步性和同一价值的女性解放运动,激发了一批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女作家登上了几乎皆为男性的文学领地。她们是女性中最觉醒的部分,标明女性从自然的人到社会的人,进而成为精神的人——女性人格意识的形成,她们超越了长久以来文学中女性爱情、婚姻的宿命叙说,目光直逼社会底层,有意无意地感应并反映出社会的矛盾和时代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在为现实主义文学鸣锣开道的同时,努力张扬着女性文学创作。恩格斯热烈地称赞女作家乔治·桑同查·狄更斯一样,“无疑是时代的旗帜”,在其作品中描写了“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表现了“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35〕恩格斯还特别指出,乔治·桑是“妇女权利的勇敢的捍卫者。”〔36〕马克思将夏绿蒂·勃朗特和哈克尔夫人与狄更斯相提并论,称之为“现代英国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的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37〕
恩格斯晚年对德国女作家敏·考茨基和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小说的评论,完成了他和马克思终其一生的现实主义理论探索,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联系两位女作家的作品领会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概括,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他们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考,有着内在的统一性。
敏·考茨基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格里兰霍天的斯蒂凡》寄给马克思后,马克思把它推荐给自己的女儿,称赞这部作品是“现代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并写信给作者,告诉她:“我们全家是多么欣赏您的作品”〔38〕。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心和鼓励下,敏·考茨基参加到社会民主运动中,连续写出了一些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小说。恩格斯所评论的《旧人与新人》,描写了一个追求革命的女子爱莎,她从维也纳资产阶级“旧人”圈子逃入“新人”中去,与爱人一道在工人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这部小说在思想倾向和艺术表现上都存在着很大缺陷。但作者把自己的艺术视角投向工人阶级,在工人生活和斗争的背景下塑造女性形象,表现出女性冲破旧生活、旧观念参与社会斗争的新风貌,作者自觉不自觉的把女性命运同整个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爱莎的形象不同于以往小说寻找理想爱人的女性形象模式,这对于当时的作家,不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是难能可贵的。恩格斯对这部小说的评论,体现了革命导师对进一步觉醒的女性社会意识的热情肯定和积极扶持。
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同样显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超越。作者在精心描述主人公耐丽被资产阶级绅士诱奸、遗弃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时,目光投向工人的生活和命运。当然,哈克奈斯只是把女性不幸的遭遇同无产阶级受苦受难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而没有看到她和整个无产阶级是承担着反抗压迫,改造社会的力量。哈克奈斯将耐丽的归宿交给了慈善团体“救世军”。恩格斯对这部小说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肯定:“除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勇气”〔39〕。同时,进一步引导哈克奈斯向充分的现实主义发展,把艺术视角的焦距对准反映历史趋向和时代本质的“典型环境”,提醒她:“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40〕恩格斯将自己的评论寄给哈克奈斯时,同时寄出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对《城市姑娘》的评论,是经典的文艺理论专著,也不啻为启发女作家贴近时代大潮的主流,在人类解放斗争中争取女性彻底解放的进军宣言。
女性解放的本质是人的解放,是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完全的、自觉的实现。女性在重重的社会压迫下,最直接的压迫是男性压迫,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的目标是男女平等,在性爱方面、在家庭中、在社会地位上、在精神领域内,都应该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然而,争取男女平等不等于反过来欺压男性,女性的天敌并不是男性,造成女性社会地位沦丧的根源,是劳动异化所产生的私有制。因而,女性解放的途径是在以推翻私有制、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不断深入阐发,将女性的命运和女作家的视点引向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向世人昭示了一条真理: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娜拉”们、“爱莎”们、“耐丽”们才能寻求到自我实现的坦途。
在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中,女性不是被动的客体。没有女性,人类永远是一轮残月;没有女性力量的汇合,人类解放事业永远处于“偏瘫”。马克思恩格斯把女性作为伟大社会变革的酵素,在他们一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从未放弃过对女性命运、女性解放问题的关注。他们通过文学批评,启发和促进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在自然、社会、审美各层面上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这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必然要求。
女性地位的复归,永远不会回复到原始的自然平等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指明了人类彻底解放、女性与男性真正平等的最高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就是要铲除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的社会基础”,“消灭妇女被当做单纯生产工具看待的地位”〔41〕,“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成为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由、向社会的(即人的)复归”。〔42〕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解放的制高点,也是女性解放的制高点,没有全人类的解放,就不会有女性的解放,没有女性的解放,也不会有全人类的解放。我以为,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学论著所体现出的女性观。(收稿日期:1995年12月20日)
注释:
〔1〕〔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下同),第1卷,第6、269页。
〔2〕〔3〕〔4〕〔5〕〔6〕〔7〕〔8〕〔9〕〔10〕〔11〕〔12〕〔17〕〔22〕〔23〕〔24〕〔25〕〔27〕〔28〕〔29〕〔39〕〔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14、8、61、60、7、6、51、2、 36—37、230、72—73、66、73、229、463、70、78、461、462页。
〔13〕〔14〕〔15〕〔16〕〔18〕〔26〕〔42〕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第53、72、22、72、72、108、73页。
〔19〕〔20〕〔21〕〔32〕〔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261、69、232、249、23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
〔35〕〔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594、58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 月北京第一版,第二册40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 版, 第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