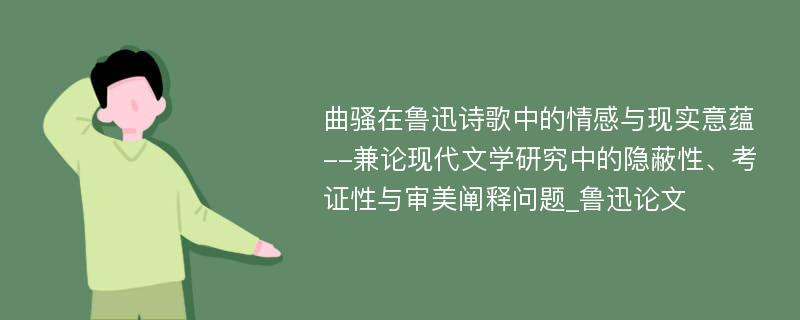
鲁迅诗作的屈骚情致与现实寄寓——兼论现代文学研究的索隐、考据及审美诠释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诗作论文,现代文学论文,现实论文,屈骚情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首小诗的繁复阐释史 在鲁迅的旧体诗中,《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是一首一向颇得推重的名作。据刘大杰讲,郁达夫曾称它为鲁迅七绝的压卷之作,而刘氏自己也认为它“意境高远,感情深厚,造句遣词,不同凡响”①。匡扶更将其放入中国诗史,称许其“音节和意境”的“响亮与高旷”,“即使放在中国旧诗发展最高峰的唐人七绝之中,也是毫无逊色”②。不过,对于它具体的诗意,几十年来却一直存在许多不同的说法。 较早出现的解说,一般都是将它与作者特定时期内心的苦闷相联系,而甚少言及诗的“本事”。比如金性尧1936年写的《鲁迅先生的旧诗》,论及该篇,便只是说“是有感而发的”,“似乎是一个老战士在落寞的沙场上,抚摸着他的创作而仍奋然前进的一幅写照”③。匡扶1952年撰《试谈鲁迅的旧诗》,也只肯定其“有所寄托”,至于对其“究系所指何事”,则明言“不敢妄加推测”。稍后,刘大杰、李拓之的文章,虽然较前具体了一点,但也只是将其与“一个战祸连年、哀鸿遍野、特务横行、文网严密的时代”及“说话写文的‘自由’”联系在一起④,认为“不是怀古,也不是纯客观的刺时”,而是“自我叙述”:“屈子的行吟尚可以写出离骚来,而自己所处的生活时代,连行吟都不可得”。⑤ 大约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有关的解释被更多的与具体的革命史联系在一起。1959年出版的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一书,论及此作,就明确将其联系于1932年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而将“眉黛猩红涴战袍”一句解释作:“国民党军队掳掠了无数妇女,卖到汉口各地作娼妓,有的破家丧亲的不幸妇女被迫作了女招待。国民党军官兵在‘战区’肆虐之余,仍不忘在各后方城市蹂躏妇女”,“那些践踏了洞庭湖滨广大土地的‘将军’们,在屠杀人民之余仍拥着浓妆艳抹的女人调笑,口红和眉黛染污了‘将军’的军衣”。⑥1962年,周振甫著《鲁迅诗歌注》对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以为“这诗应该怎样解释还没有把握”,“说口红染污军衣,可以,说眉黛染污军衣恐难成立”;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以“眉黛是指妇女”的基本看法,并据《鲁迅日记》“猩红”作“心红”的异文,另提出其“当指忠于革命的革命根据地的妇女。污战袍,她们的血沾染反动派的战袍。可能由于血染的意思不明显,所以改‘心红’为‘猩红’,指妇女猩红的血染上战袍”的看法⑦。此后绝大多数的解释,沿袭的均是这样的思路。 譬如1968年出版的武汉大学中文系鲁迅兵团《鲁迅旧诗注释》,认为“这诗是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而写的”⑧,1972年出版的杭州大学中文系《鲁迅诗歌浅析》,认为“眉黛句概括‘三光政策’的具体内容,无数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屠夫们的战袍。这里突出妇女,是举例而概其余”⑨。这期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77年出版的倪墨炎《鲁迅旧诗浅说》一书中的具体表述:“这首诗的前两句,是揭露和声讨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的;后两句,是揭露和声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眉黛“一般用来指妇女,这里泛指妇孺老幼”。虽然基本的思路并没有多少变化,但该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980、1987年多次再版,影响甚大。尤其是其中有关的“眉黛”“泛指妇孺”的说法,甚至被采入1993年版《汉语大词典》的有关词条,成为“眉黛”一词的基本义项之一。 除了这些笼统的说法,到七十年代末,这种与革命史有关的解说,还出现了一些更具体的说法。1977年鲁歌在《天津师院学报》第4期发表的《杨开慧同志的就义和鲁迅的几首诗》一文,直接将该诗的“眉黛猩红”与“杨开慧同志的不幸殒亡”牵扯到了一起⑩。文章发表后虽然旋即引起宋谋瑒的批评(11),但后者的解释同样着意于该诗的“本事”,不同只在于所联系不是杨开慧,而是所谓1932年7月鲁迅同陈赓的一次会见,认为“眉黛猩红”一句,实际是“借西汉末樊崇赤眉军起义的故事,暗指红军”。文章发表后,鲁歌因并不接受其批评,而再撰《再谈鲁迅的〈无题(“洞庭”)〉诗——与宋谋瑒商榷》,坚持己见。但吴奔星1979年写的《试谈鲁迅〈无题(洞庭木落……)〉一诗的艺术构思》,王维森1981年出版的《鲁迅诗歌赏析》(12),采用的却已是这种与陈赓会见有关的说法(13)。另,1980年曹礼吾《鲁迅旧体诗臆说》一文,认为“先生诗殆为第三次‘清湖’诸役而作,观眉黛语,必有女同志壮烈牺牲于其中”(14),虽未指明该“女同志”为谁,但同样为其后各种各样“索隐”的说法,提供了启示。 历史进入新时期后,随着文学研究思维的整体变化,有关的研究也开始不再像先前那样刻意附会革命史,而更着意于“回到鲁迅本身”。有关此诗的解说,也渐渐开始和鲁迅个人生活、交谊有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1980年,周振甫出版《鲁迅诗歌注》修订本,全盘推倒先前的说法,而采纳“有位同志”根据《鲁迅日记》中“为达夫”的线索及该诗与《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写作时间上的相近所提出的新说,认为后者的“主要意思”都“包含在这首《无题》中了”(15)。其后,徐重庆1981年在《浙江学刊》第3期发表《对鲁迅〈无题〉一诗的理解》,周艾文1983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鲁迅研究文丛》第4辑发表《谈鲁迅与郁达夫的友谊及赠诗》,又分别对这种说法作出了进一步的论说。此后,许多新出的研究著作,包括王达敏为孙郁主编的《走进鲁迅世界·诗歌卷》一书撰写的有关文字(16),倪墨炎2002年新出的《鲁迅旧诗探解》(17),也都改从此说。 此后,除了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情况,一般的解说大都没有越出上述诸说范围。 近二三十年,再次引起人们对这首诗的解说兴趣的,是1996年熊融发表的《鲁迅〈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诗新解》一文(18)。该文开头先是回顾历史,将历来有关该诗的解说分为“自述说”、“反围剿说”、“赞颂说”、“悼亡说”、“规劝说”五类,而后根据《鲁迅日记》及致增田涉、许寿裳等的信件,提出该诗作意在讽刺王云五旧宅在“一二·八”事变后沦为日军妓馆的“新解”。但文章发表后,迅即引起李思乐、刘泰隆等的反驳(19)。其中李思乐的文章,实际坚持的仍是“规劝说”,而刘泰隆的文章,则可算是“反围剿说”的又一种发挥,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则在指实:“诗中的‘眉黛猩红’就是指以叶紫的姐姐为代表的青年女子的鲜血”(20)。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几十年间有关此诗的解说,始终折射着文学思维和文学阐释的历史演变,而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一个看法的得出,又与该时期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此诗的难解,则主要在如何理解其第二句“眉黛猩红涴战袍”,尤其是其中的“眉黛”一词的具体含义。而所有前引说法,除了宋谋瑒以“眉黛猩红”为“借赤眉起义军暗指红军革命旗帜鲜明”外,其一致处均在以此诗必与某些或某个女性有关(21)。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二 红颜,抑或青山 2006年,鲁迅研究会第8届年会在广州召开时,我曾就这一问题写过一篇题为《眉黛解》的短文提交小组讨论,大意为:该诗中的“眉黛”一词,非关女性,而当指洞庭湖一带的山野,亦即古诗文中常用来与洞庭对举的九疑,并引唐李群玉《黄陵庙》诗“犹如含颦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为证(《全唐诗》卷569)。其后,文章并未发表,又读到张紫晨《鲁迅诗解》,才发现我这个“发现”,其实早为张先生指出。该书云: “洞庭木落楚天高”,以景入笔,“眉黛猩红涴战袍”,借景寓事,构成了秋景之下的一种血腥之气。“眉黛”一词首先是景,以景喻人。北宋黄庭坚在《托梦》诗中用“窗外远山是眉黛”描写过秋天景色。秦观词《生查子》也有“眉黛远山长,新柳开青眼”的句子。其用法都是以眉黛喻远山。鲁迅诗中“眉黛猩红”是说远山殷红,本为秋色。“眉黛猩红涴战袍”,是作者由远山殷红想到反革命的屠杀之甚,由屠杀之甚,又联系到战袍的涴染。诗句是说,楚天楚地落木萧萧,远山也是一片血红。这句诗概括了遭到血洗的南方革命根据地。(22) 显然,除了或许为它找到了更早的出典,并更加突出了“眉黛”一句与“洞庭”一句间的有机关系外,我所谓新解,其实并没有越出张先生所已揭示的内容。自愧学浅之余,问题也就撂在了一边。时隔数年,偶尔翻检《汉语大词典》,却发现在这部新出的权威辞书有关“眉黛”一词的释义中,竟也特别列有“泛指妇孺”这样一个义项,其唯一句例,正是鲁迅这句诗。于是,再翻检新出或再版的各种鲁迅诗歌注本,发现不但诸般旧说都有人采用(23),一些新出的索隐之说,甚且已被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张紫晨的书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能读到的人按说应该不少。奇怪的是,除了笔者,迄今似乎很少再有人注意到他这一说法的重要性。熊融先生的文章开头罗列的“五说”(24),大体概括了数十年来有关这首诗解说的几乎所有其他重要的观点,唯独漏掉的,竟然也是此说。 李思乐批评熊融“新解”的不审慎,曾反复引用闻一多《匡斋尺牍》里的一段话:“一首诗,全篇都明白,只剩一个字,只有一个字没有看懂,也许那一个字就是全篇中最要紧的一个字,诗的好坏,关键全在它。所以每读一首诗,必须把那里每个字的意义追问透彻,不许存在丝毫的疑惑。”(25)抓住的,应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解诗原则。遗憾的是,这个“最要紧的”“字”,却并非他反复论证的那个“涴”,而是更使诗意歧义丛生的“眉黛”。纵观目前除张紫晨外的各家说法,尽管具体的持论颇有异同,但在一点上大家几乎拥有一种共同的理解,即以“眉黛”为“妇女”。分歧只在,这“妇女”具体所指为谁。 的确,以“眉黛”为女性或与女性有关的事物,是古诗文中最常见的修辞。张向天注引《释名》“黛,代也;灭眉毛去之,以此代画其处”;周振甫释眉黛“画眉的黛石,指妇女”;李思乐引《楚辞·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泽只”;李义山《代赠》“总把春山扫眉黛,不知共得几多愁”;左思《妖女诗》“明朝弄梳台,眉黛类扫迹”等,均属显例。此外,若要继续证明它,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与之相似的用法。如《西京杂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孟浩然《美人分香》“髻鬟垂欲解,眉黛拂能轻”,杜牧《闺情》“袖红垂寂寞,眉黛敛依稀”,韦庄《荷叶杯》“一双愁黛远山眉,不忍更思惟”,晏几道《菩萨蛮》:“弹到断肠时,春山眉黛低”,欧阳修《桃源忆故人》“妒云恨雨腰支袅,眉黛不忺重扫”(26),《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杜撰《古今人物通考》为黛玉取字“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等等,几乎举不胜举。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常用来喻指女性的“眉黛”,同样可反转来喻指远山。这样的句例,在古今诗文中同样不算罕见。张紫晨说法的不被注意,除了下面要说到的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举证的简约和含蓄,恐怕也是一个原因。为此,且让我不避冗赘,在下面再多举出一些句例。 一个最早,也最耐寻味的句例,或许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唐李群玉的《黄陵庙》诗。该诗因在黄陵庙睹娥皇、女英造像而作:“小姑洲北浦云边,二女啼妆自俨然。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风回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鹃。犹似含颦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全诗所咏,在一种绵延千古的遗恨,但尾联“含颦”、“如黛”交互为文,于写实的描摹之外,更借文字的转喻,叠印出一种融合于山色里的深沉怅惘。“九疑如黛”,简单看是山色,联系“含颦”看,则也未必不在自然与人之间的形象、情感幻化、渗透。其后,唐诗中更显豁的以眉黛喻远山的句例,至少还有罗隐《江南曲》里的“江烟湿雨鲛绡软,漠漠远山眉黛浅”(《全唐诗》卷19)。而到宋代以后,类似的修辞,则变得更为常见。仅就张紫晨引证过的黄庭坚词看,除了那一句“窗中远山是眉黛”,同样的构思也见于更有名的《渔父词》:“新妇矶头眉黛愁,小姑堤畔眼波秋”(27)。《冷斋夜话》记谢师直评黄庭坚此句,谓“能于水容山光玉肌花貌无异见”(《增修诗话总龟》前卷九),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也称其“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均对这样的表现赞不绝口。可见以山色拟眉黛,已被视作是一种相当高明的修辞。 此外,随便翻检,宋及宋以后诗文中这类以眉黛拟远山的修辞,仍然不少。如张耒《自巴河至蕲口道中得二诗示仲达与秬同赋》“喜逢山色开眉黛,愁对江云起砲车”(《张右史文集》);王观《卜算子》“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僧慧洪《过永宁寺》“雪如镜底颔丝白,山学谁家眉黛新”;《赠潙山湘书记》“山学春愁眉黛,水如含笑花香”(《石门文字禅》);汪藻《次韵蔡天任十首之一》“江头山色旧所爱,倒影玉海空嶙峋。尔来处处作媚妩,似与世争眉黛新”(《浮溪集》);张孝祥《生查子》“远山眉黛横,媚柳开青眼”(《于湖居士文集》);范成大《次韵赵养民碧虚坐上》“已将山色染眉黛,更挽江波添酒罍”(《石湖居士文集》);虞集《题黄都事仲纲山居溪阁图二首之一》“连云一一列眉黛,细雨往往逢渔樵”(《道园学古录》);倪瓒《双调·水仙子》“东风花外小红楼,南浦山横眉黛愁”(《倪云林诗集附录》);黄宗羲《怀金陵旧游寄儿正谊·燕子矶》“诗法空江冷,远山眉黛愁”(《南雷集南雷诗历》);钱大昕《题袁蕙纕孝廉南湖草堂图》“湖光一轮镜面揩,四围远山眉黛佳”(《潜研堂文集诗集》);丰子恺《缘缘堂画笺》题诗“山如眉黛秀,水似眼波碧”;李乐薇《我的空中楼阁》“山如眉黛,小屋恰似眉梢的痣一点”等等。 先前那篇《眉黛解》写出后,我曾写信向王得后先生请教,先生回信自谦“不懂诗”,并云“向来‘诗无达诂’,能自圆其说就可成立”,但同时也肯定我的解释“比解为‘妇女’好;好在和‘洞庭’对上了。‘猩红’和‘木落’也对上了。而且比那些坐实的解释避免了穿凿和僵硬,也使全诗有一种‘浩茫’的气魄。”这“对上了”的说法,很让我感到鼓舞。的确,“洞庭”与“九疑”,原本就是旧诗中咏楚人楚事时极常用的典故。但凡对中国文化略有了解的人,只要看到洞庭、九疑、木落、湘妃、泽畔、《离骚》一类的意象,都不难发觉我们被引入的是一个怎样的文化意义网络。李思乐说这首诗“四句诗中有三句涉及屈原和《楚辞》”,明白了眉黛即远山,就不难明白,这首诗同王瑶所曾指认过的《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一样,其实“四句都与《楚辞》有关”(28)。明乎此,也就再无必要对所谓“眉黛猩红”做出种种比附“本事”的索解。 三 秋色与血的隐喻 虽然如此,但这也并不是说在这首诗中就完全没有现实的寄寓。承认“眉黛”为九疑,自然可想到,所谓“眉黛猩红”,所指首先应为山野间的秋色。中国的古诗文描写山野秋色,多喜用酡红。比较明显的如《西厢记》里的“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比较隐晦的如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之“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都是以醉颜喻红叶。鲁迅这里用“猩红”显然有点不同寻常,要讲通它,的确需要与后面的“涴战袍”联系在一起。因而,说这句诗中明写秋色,暗讽战事,显然不会错。或者,更深一层说,这种双关的描绘,喻示的或是在鲁迅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洞庭一带的秋色,业已染上了无数被杀者的鲜血。李思乐先生认为“战袍之前有一‘涴’,是说战袍是不应‘涴’的。可证‘战袍’决非写敌人的军大衣”,对诗意可能的反讽和曲折显然太少理解。另外,说“眉黛猩红涴战袍”是暗讽郁达夫情事,也还有另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这就是郁达夫曾不止一次地对史沫特莱、徐志摩等人说:“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而鲁迅在听闻他被左联开除后对冯雪峰的谈话里,也曾说到“郁达夫不能写什么斗争文章”。(29)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战乱频发,民不聊生,鲁迅做于这一时期的诗文,自不免时时流露对时局的激愤与忧思。说“眉黛猩红涴战袍”是讽刺当时有力者的滥杀无辜,显然并没有错。这一点,还可以与同期鲁迅另一些作品互为参证。 据《鲁迅日记》,该诗最早问世是在1932年的12月31日。当日,鲁迅为朋友写字五幅,其中即以此书赠郁达夫。虽然这未必就是做诗的日子,但我们大概也无法将它向前推得太远。此后不到一个月(1933年1月26日),他又为邬其山(内山完造)和画师望月玉成各书一笺。后者云:“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30)该诗的末句“只研朱墨作春山”,同样一向歧解纷出。比如李拓之认为:“以朱墨作春山,即‘血沃中原肥劲草’之意,朱墨即鲜血的代词”(31);但从启明、林辰到周振甫、倪墨炎,更多的人却认为它所表现的,是“希望和理想”,或“红色的革命根据地”(32);而张向天则释“春山”为“秀眉”,而以“只研朱墨作春山”为“当时的时尚”,即“当时上海的各香烟公司多以画‘大美人儿’为宣传,画家为了生活也放弃了正当有意义的创作而随波逐流地专画美人图。鲁迅于此对于当时的陋风做了讽刺”(33);近期,又有人将之比于陈寅恪的“著书唯剩颂红妆”,推测诗中所言不过是“在那样的时世,纵有再好的才情和创意,恐也唯有画画美女而已!”(34) 李拓之认为,诗中的“朱墨”,即朱色的墨,所以才有“朱墨即鲜血的代词”的说法;另有颜默、章华认为“朱墨”系对举“朱”“墨”两种不同颜色的颜料,其误已为倪墨炎辨明,这里不再申说。为何“作春山”而“只研朱墨”?如果说该诗前两句写千山晦暗、百卉凋残,后两句寄意画师,希望更多地表现“希望和理想”,则“春山”为何不“绿”而“朱”?也就是说,按常理,“春山”即便有“红花盛开”,也无从尽掩绿意。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矛盾,林辰的解说,实际也将一色换成了两色,认为前两句的“千林暗淡、百卉凋残的景象,正好和花叶繁茂、红绿相映的春山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而完全抛开了开头“只研朱墨”中的“只”的深刻含意;周振甫的解说,则索性直接以“革命根据地”的“红”置换了绘画设色中的“红”。 只有秋天的山野,才会“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所谓风生林暗、雾塞苍天、百卉凋残,所写都是秋意,但这未必即是自然的秋,相反,也可以是人间的秋。鲁迅同年作的《悼丁君》里说“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正是此意。本该带来春色的春风,带来的却是秋的肃杀;本该是“花叶繁茂、绿红相映”的春山,却只让人看到了一片鲜红,鲁迅说他作短文“好用反语”(35),这里其实何尝又不是如此?无论《赠画师》开头一句中的“白下”,是否即指南京及它所代表的政权,这里包含的某种极为现实的东西,却的确与现实的政治有关。但李拓之说“以朱墨作春山,即‘血沃中原肥劲草’之意”,究竟是否真有道理呢?同样令人疑惑的,还有1931年5月的《湘灵歌》:“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这首诗里的“今闻湘水胭脂痕”,绝大多数的注家都认为是暗讽国民党军的屠杀。 单一地看,这些诗中的红色的含义,似乎都不好仓促论定,但只要我们把它们看作一个系统,你就不难发现,从“今闻湘水胭脂痕”到“血沃中原肥劲草”,到“眉黛猩红涴战袍”,再到“只研朱墨作春山”,延展的几乎都是一种同样的感觉和隐喻方式。而其所指,也似乎都与遍洒山野间的被杀者的鲜血有关。我们再将视野扩展,从1903年《自题小像》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到1919年《药》里的“人血馒头”;从1926年《记念刘和珍君》的“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到1931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前驱者的血》;从1933年《为了忘却的记念》里“许多青年的血”,到1934年《三闲集·序言》“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等等(36),你就更能发现,在鲁迅的文学系统符号中,种种对“血”的谛视和思考,始终是他的创作中最令人震撼的内容之一。 四 索隐、考据及审美诠释 由一首小诗的解释,生出这么多纷繁的议论,这现象,本身就令人深思。旧体诗在新文学运动之后迅即被逐出现代文学的正统,有关旧诗的研究,也不再进入以新文学为主脉的各种文学史。但各类作家的旧诗写作,却一刻也不曾停歇。而作为其中一个特例的鲁迅旧体诗的研究,数十年来却一直有人予以特别的关注。尤其是在“文革”时期,围绕其中一些诗作的革命化解读,甚至出现过不止一次的热潮。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这个热潮兴起的时期,也正是“文革”对现代文化扭曲得最为厉害的时期,有关这些诗的阐释,常常就被有意无意地与某些特定的政治意图捆绑在一起。因而,不断产生出的,也就常是如说《湘灵歌》中的“胭脂痕”“是红旗”(37);说《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里的“萧艾密”是“在苏联的萧三”(38);说“只研朱墨作春山”是寄希望于“红色的革命根据地”;说“眉黛猩红”是悼念“杨开慧烈士”一类的奇谈。到新时期,这类说法中的一些过于牵强附会者,虽然渐渐被人遗忘,但其中有一些,也还一直保持着它的影响。新时期有关鲁迅旧诗的研究,同样著述不少,但要么刻意索隐,要么因循蹈袭,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许多重要的错失。 这一切,不但涉及一些具体的看法、结论,而且也涉及一些文学解读的基本原则和路径。即以我们前面论说的这首诗为例,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有关鲁迅旧诗的阐释,明显可以分出三个不同的阶段,不同阶段对同一作品的研究,无论是旨趣,还是方法,都有着重要的不同。1956年前的有关阐说,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阐释者政治文化立场的影响,但对“本事”考索,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批评者对这些诗作的褒扬,所持的主要还是一种艺术的或审美的立场。从五十年代末开始直到七十年代末达到高潮的第二个阶段,在解说的旨趣和内容不断革命化的同时,研究的方法也开始变成围绕革命史进行的种种形式的“索隐”。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有关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最初的尝试主要在尽力摆脱过去那种捕风捉影式的革命史比附,以回应“回到鲁迅本身”的共同追求,鲁迅的私人生活和日常交往遂成注释家更乐意挖掘的矿藏。到后期,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愈来愈历史化,一些夹杂着考据和推测的新的研究风气,又为它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动力。然而,无论这些论说看上去多么“实证”,当研究者一旦陷入对某些孤立的证据的一再发挥,这研究实际沦入的其实又是别一形式的索隐而已。当年胡适批评蔡元培的《红楼梦》研究,曾称其为“猜笨谜”,今天再看鲁迅诗作诠释中的许多成果,仍然不能不令人生出同样的感慨。 而这样做的一个最要不得的后果,便是对鲁迅诗作的屈骚情致和现实寄寓的漠视和扭曲。柳亚子说鲁迅的诗“远踪汉魏,托体风骚”。所谓“远踪汉魏”,说的自然是它的风骨。早在1941年,钟敬文(木犀)在题为《鲁迅氏的旧诗》的文章中谈及这些作品给他的印象,就说:“读过鲁迅诗作的人,都不免有这种感觉,就是他的诗是强烈的、深刻的,它所遗留在我们脑里的印象很不容易消灭。这好像诵读尼采一类作家的著作,即使是那些和他的思想体系无缘的,也要被他的思想艺术的力量所震撼。我们的心灵仿佛不容易抵抗它的逼迫。”这种强烈的、深刻的东西,便是它的风骨。至于“风骚”,则自然与来自屈原和《楚辞》的传统联系在一起。早在新时期之初,王瑶在为英译本《鲁迅诗选》所作序言《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中就指出,鲁迅诗中有许多词句来自《楚辞》。“《楚辞》中所歌咏的洞庭潇湘的风光不仅孕有古代的神话传说,可以丰富诗的想象和意境,而且湘赣一带当时是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激烈进行的地区,革命斗争十分尖锐,而这正是作者极为关心而又难于直接抒写的内容,因此运用《楚辞》所引起的想象和构思,可以含蓄而深刻地写出他的感受,易于引起读者的联想和共鸣”,“著名的《湘灵歌》、《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就是这样”。(39) 这段话,至少说出了鲁迅诗风与《楚辞》之间联系的两个方面。其一,是鲁迅诗作对《楚辞》意象、意境的直接继承与借用。早就有人注意到,在鲁迅的旧诗中,《楚辞》意象的存在是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现象。有人统计:“他的六十八首旧体诗中有二十多首(约有三分之一)或引用楚辞中的词语,或借用楚辞的形式,或点化楚辞的意境,都直接间接地受到楚辞的影响。”(40)这当然还只是一个相当粗略的统计。因为如前所论,这种影响很可能也存在于一些寻常不易看出的地方。王瑶分析“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可怜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一诗,认为全诗“四句都与《楚辞》有关”(41),我在前面也已证明,“洞庭木落楚天高”一首同样如此。其二,是鲁迅诗作得自《楚辞》的那一种借香草美人的象征、隐喻曲折表达作者的现实感怀的艺术方式。这一点,在我们上面提及《湘灵歌》《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赠画师》《赠丁君》等作时,都已有所表明。但更重要,也为王瑶这番话所未曾直接点明的是,鲁迅诗作与《楚辞》的这种关系,其实还表现在一种更具生存论意味的人生之思,表现在作者随时随地都能从具体的生活现实超拔而出,从对生活现象的观察、批判进入更为浩茫的人生之思的精神能力。即此而言,鲁迅的所有作品,不光是他的旧体诗,就连那些意趣相对幽邃邈远的小说、散文,如《在酒楼上》《伤逝》《铸剑》《采薇》,以及《野草》《朝花夕拾》里的许多篇什,其最耐人寻味的往往也都是这样的东西。即以《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一诗而言,其诗意的表层即便确如论者所言,与某时某地的具体史实有关,但其最终的艺境——兴寄怀抱、韵味风神,也绝非能为一时一地一事所限定。王得后先生说,将“眉黛”理解为远山,使全诗“有一种‘浩茫’的气魄”。所用“浩茫”一词,显然也来自鲁迅,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这不但是鲁迅对自我精神的一种阐释,而且也是所有足以称之为伟大的文学所共有的精神品质。而这也就是我所谓屈骚情致的根本,同时也是鲁迅诗歌最能动人的地方之一。 这一切,其实本不难理解。然而,在历史的一定时期,为了突出鲁迅的革命性,许多论者所做的,却不但不是对这种影响和特征的揭明,反倒是对它各式各样的否认和限定。如果说吴奔星当年的文章,为突出鲁迅与屈原“同统治阶级之间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阶级关系”,认定“真正革命的作家是不会写《离骚》那样的作品的”,尚因时代的原因而易于理解的话;九十年代以后一些论者坚执:“鲁迅决不会以屈原来自喻和自况,也不会将自己的诗文比作《离骚》”(42),就不免让人生疑,他这样的信念依据的不知究竟是什么。 总之,要正确认识、了解鲁迅旧诗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意蕴,就必须同时正视他的作品所特有的屈骚情致和辛辣、深刻的现实批判意味。郁达夫之称《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为鲁迅七绝的压卷之作,刘大杰说它“意境高远,感情深厚,造句遣词,不同凡响”,所着眼的显然都是它兴寄怀抱的超越性。 再看曾经流行的几种解说,且不论像有的人坚持的悼念杨开慧一类的稀奇说法,就是像说“只研朱墨作春山”是寄希望于“红色的革命根据地”一类的推想,大概也只有在五六十年代,也就是郭小川写“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的那种语境中,才能得到人们的广泛的认同和理解。说“眉黛猩红”影射郁达夫情事,乍看上去很切近生活,细想却不免有轻薄朋友的意味——今人因了解郁、王的关系后来的变故,不免站在郁达夫立场上对王映霞滥施轻蔑,但在当初,无论鲁迅有怎样的先见之明,恐怕也不好这样轻侮谈及朋友的私人生活。至于说讽刺王云五,仔细想来,更有降低鲁迅的人格的嫌疑——退一大步说,即使鲁迅真的对王云五有很多的不满,大概也不至于拿他的旧宅之沦为日军妓馆作为话柄。因为在这件事上,要说耻辱,也是中国人的耻辱,而非王云五一人的耻辱。这就是说,如以“眉黛”为某一个(或一群)女性,不但会从根本上掩蔽鲁迅诗作的屈骚情致,也未必不同时降低了他的趣味与人格。而这也正是笔者反复言说,意图辨清这桩公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约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有关《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一诗诗意的理解,就一再误入歧途。除了认识本身的局限,某些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诱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在历史进入“新时期”之后,有关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近些年现代文学研究中以校勘、辑佚、补遗等工作为主的文献学方法也渐渐兴起,与之相应,针对有关史事的训诂考释工作,也开始摆脱一段时期意识形态制约下的穿凿附会而不断焕发出新意。然而,具体工作中的许多得失,却仍然与这样一个基本的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在本属史学的方法的考据与文学作品的审美诠释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以保证这种实证的努力不致因捕风捉影式的“索隐”沦为笑谈,这也是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包括鲁迅研究,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王吉鹏《注目伟大的存在时空——鲁迅杂文、诗歌研究史》第四章专列“考据学方法的引入——熊融、靳极苍的研究”一节,即以其《鲁迅〈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诗新解》和《重读鲁迅〈赠邬其山〉诗》为依据,称许作者为新时期鲁迅旧诗研究“引入了考据学方法”,不但获得了“新的成果”,而且在“方法论的范畴”上,也带来了“启示”(43)。或许,从方法论的层面,将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引入现代文学研究,确有其意义。不过,要提醒的是,我们就是使用这种方法,也不能脱离对整个艺术作品的美学理解。而包括鲁迅研究在内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也已一再表明,所谓“考据学方法”,一旦脱开对作品整体艺术性的认知,则很可能误入种种时代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索隐”歧途。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实证之风渐兴的今天,如何防止因因袭的“索隐癖”、“考据癖”而冲淡(甚而遮蔽)文学对象本身的审美属性,这或许也是我们在这场具体的是非之外,更需要深入思考的另一问题。 注释: ①④刘大杰:《鲁迅的旧诗》,《文艺杂志》1956年第11期。 ②匡扶:《试谈鲁迅的旧诗》,《艺术生活》1952年第8期。 ③金性尧:《鲁迅先生的旧诗》,《青年界》1936年第5期。 ⑤李拓之:《鲁迅的小诗》,《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6期。 ⑥(33)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2~113、116页。 ⑦周振甫:《鲁迅诗歌注》,浙江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5页。 ⑧武汉大学中文系鲁迅兵团:《鲁迅旧诗注释》1968年版,第87页。 ⑨见张恩和《鲁迅旧诗集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页。余如1976年出版的江西大学图书馆编《鲁迅诗歌选注》;1977出版的西北大学中文系《鲁迅诗歌选注》,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注《鲁迅诗歌注》;1978年衡阳师专中文科编《鲁迅诗歌浅析》;1979年彭定安编著《鲁迅诗选释》;1982年郑心伶著《鲁迅诗浅析》等,具体辞句虽略有差异,表达的意思也基本如此。 ⑩鲁歌:《杨开慧同志的就义和鲁迅的几首诗》,《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第4期。 (11)宋谋瑒:《鲁迅〈无题(“洞庭”)〉与会见陈赓一事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12)王维森:《鲁迅诗歌赏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吴奔星:《试谈鲁迅〈无题(洞庭木落……)〉一诗的艺术构思——兼谈鲁迅对〈离骚〉的评述》,《齐鲁学刊》1979年第5期。 (14)曹礼吾:《鲁迅旧体诗臆说》,《天津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 (15)周振甫:《鲁迅诗歌注》(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144页。 (16)孙郁主编《走进鲁迅世界·诗歌卷》,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122页。 (17)倪墨炎:《鲁迅旧诗探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177页。 (18)熊融:《鲁迅〈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诗新解》,《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1期。按:熊氏又于1997年第8期《学术月刊》发表《鲁迅〈无题〉诗新解》一文,除个别字句稍异外,内容和前作基本相同。 (19)李思乐:《关于〈鲁迅《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诗新解〉的通信》,《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3期。刘泰隆:《我对鲁迅〈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诗的管见》,《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9期。 (20)刘泰隆:《我对鲁迅〈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诗的管见》,《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9期。 (21)唯一的例外,大概是宋谋瑒的解释,只有他认为:“眉黛猩红”为“借赤眉起义军暗指红军革命旗帜鲜明。眉黛即眉。“涴战袍”是说他们正在苦战。此说的不妥,已为周振甫指出。见周振甫《鲁迅诗歌注》(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页。 (22)张紫晨:《鲁迅诗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221页。 (23)譬如吴传玖编著《鲁迅诗释读》(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4页),吴中杰编著《吴中杰评点鲁迅诗歌散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傅德岷、包晓玲主编《鲁迅诗文鉴赏》(长江出版社2007年版,第55~56页)采用的都是所谓“反围剿”说;1991年夏明钊著《鲁迅诗全笺》,2004年金鹰《橄榄小集》中的“鲁迅旧体诗选注”(中国人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采用的是和陈赓会见有关的说法;孙郁主编《走进鲁迅世界·诗歌卷》中王达敏撰写的有关文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122页)及2002年倪墨炎的新作《鲁迅旧诗探解》采用的均是规劝郁达夫说。 (24)(42)熊融:《鲁迅〈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诗新解》,《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1期。 (25)见李思乐《关于〈鲁迅《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诗新解〉的通信》,《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3期;《鲁迅〈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诗“涴”字义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6期。 (26)按:《渔父词》中这样的描写,当时已成名句。《冷斋夜话》记谢师直评黄庭坚《渔父词》“新妇矶头眉黛愁,小姑堤畔眼波秋”,“能于水容山光玉肌花貌无异见,是真解脱游戏耳。”(《增修诗话总龟》前卷九)同样的评述也见于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山谷诗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自谓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 (27)按:此作又被误作秦观词,但字句稍异。“远山眉黛横,媚柳开青眼”作“眉黛远山长,新柳开青眼”。见《续选草堂诗余》。依此,则全句又像是以远山比秀眉。但今人赵炯《淮海词注析》云“上片是春天傍晚的景色,写了远山、新柳、楼阁、晚霞和淡淡的春寒”,是仍以眉黛为喻远山。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页。 (28)(39)(41)王瑶:《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250、249页。 (29)刘小清:《郁达夫缘何被左联开除》,《作品与争鸣》2005年第1期。 (30)《鲁迅日记》1933年1月26日,《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31)李拓之:《鲁迅的小诗》,《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5期。其后颜默、章华以“朱墨”所画为“鲜血”与“焦土”,应该说是这种说法的另一种表述。见张恩和《鲁迅旧诗集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5页。 (32)参张恩和《鲁迅旧诗集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7页。 (34)赵敬立:《重建鲁迅旧体诗阐释的诗学体系》,《鲁迅研究学刊》2009年第12期。 (35)鲁迅《两地书·致许广平十二》:“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 (36)《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37)杜元明:《心朝北斗唱浩歌——读鲁迅歌颂毛主席和工农红军的诗》,《河北文艺》1977年第10期。转引自张恩和《鲁迅旧诗集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38)刘逸生:《读鲁迅诗的笺注有感》,《羊城晚报》1963年5月8日。阿梅:《鲁迅旧诗中的一个虚词》,《羊城晚报》1963年9月18日。转引自张恩和《鲁迅旧诗集解》,第317页。 (40)叶肇增:《鲁迅旧体诗与楚辞关系浅谈》,《温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 (43)转引自陈梦熊《〈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标签:鲁迅论文; 朱墨论文; 文学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日记论文; 诗歌论文; 湘灵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