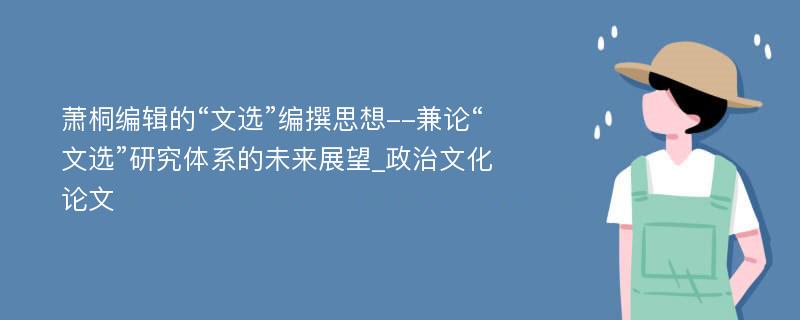
萧统主编《文选》的编纂理想——兼谈对未来“文选学”研究系统的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理想论文,未来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5-0107-06 有关《文选》编者及其编纂意图的研究,无疑是步入《文选》研究殿堂的首要课题,是《文选》研究系统的总开关,也是必须不断经受质疑检验、不断被启动骋怀想象的《文选》众妙之门与活水源泉。就编者问题而言,尽管不乏异议,当代研究主流还是认可萧统的主编权的。①就编撰问题而言,学界更多关注具体编纂时间、编纂过程等,自足于单纯的文学与文化审美意义认知,对萧统抱持崇高文化理念与编纂理想、重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高度关系的特殊编选用心,似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缺乏深具会心的具体、明晰论述。为了更好地认识《文选》的编选意旨与思想内容,本文拟对萧统主编《文选》的编纂意图问题略作探讨,并以此观照、反思当代“文选学”研究系统,提出对未来“文选学”研究方向的思考,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姬汉”用词与“比隆周、汉”:萧统主编《文选》以为一代国家文化大典 根据《梁书》等的记载与萧统在《文选·序》中的自述,萧统主编《文选》是受梁武帝重托、以太子身份实际主持朝政时期。②不过,对萧统自谦式叙述“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切不可断章取义。如此说法只是表明,萧统在主持朝政的同时,还情系主编《文选》,并将“监抚”的“暇日”与“余闲”全部贡献了。若曲解为萧统主编《文选》,仅是因“居多暇日”打发“余闲”,单纯为了满足其自我娱玩需求,就有悖情实了。因为他紧接着自述:“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历观”“泛览”云云,是说面对广大“文囿”,浩瀚“辞林”,其主编《文选》,是以高度系统化思维、研阅穷照与精心选择作为基础的。“心游目想,移晷忘倦”,是说他是以最深切的生命关怀,全身心地投入,因“心游目想”、专注忘我工作而无视时间流逝与身体疲倦。如此说来,萧统实际就是以自谦方式,描述了其全身心投入主编《文选》、耗费巨量精力及时间的真实情状,当然也渲染了其享受生命极值体验的无上精神之乐。可见,视忙若闲,以苦为乐,以高度专业内行的方式热爱文化,确是萧统得以主编《文选》成功的重要条件与动力因素。 但更大的也是更为内在的生命内驱力,还当是其抱持更高的文化理念与理想追求。必须指出,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P675)身为实际主持梁代朝政的太子,萧统不可能自外于“世情”与“时序”,其主编《文选》必然代表国家意志,彰显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定需要。而魏晋迄于梁代文化审美观念的臻于高度发达与成熟,南北朝后期华夏民族文化大融合所达到的新高度,与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成为南北朝后期愈加凸显的时代必然需求,③这三种时代因素的交互为用,更使萧统对历史文化发展抱持高度使命感与责任担当,而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高度有机结合作为其崇高文化理念,也使其将主编《文选》以为大一统文化王朝的一代国家文化大典,作为躬践文化理念与文化理想的重要方式。 《文选·序》中的“姬汉”用词显示,萧统主编《文选》,确是躬行梁王朝之国家意志,呼应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的时代必然要求。在《文选·序》中,萧统将其编选作品的上、下时限界定为“远自周室,迄于圣代”,并宣称:“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如此表述方式,高瞻远瞩,深具系统文化总结、继承的意味与气象,值得予以高度关注。 显然地,其以周代为起点,称述自周至于梁的所谓“七代”与“千祀”,并非不分轩轾,并列泛论,而是有着明确的思想关切。因为就中国王朝的起点而言,并非以周代为最早,《文选·序》开篇甚且论及“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文学创作也非始于周代。同时,若仅限于谈论文化王朝的起点,举一周代即可,没有必要连缀“姬、汉”为文。尤其是其谈论以周代起始的所谓“七代”时,直接跳过了秦代,而明确并列“姬、汉”,也不列出汉代以后的其它王朝,而仅笼统宣称“自姬、汉以来”,可知身为梁代实际主持朝政的太子,萧统目光高迈,其显然是专就典范意义上的文化王朝立言,故不屑齿及于秦代、三国、两晋、刘宋与南齐。如果认同昭明太子确是以周代为典范文化王朝的起点,推许大汉文化王朝可与周代比肩,再联系其界定《文选》选文的前后时限为“远自周室,迄于圣代”,则得出如此结论:其有表达梁代将可成为绍继甚且超迈“姬、汉”的第三大文化王朝的特定思想意涵,其主持编纂《文选》,必有为梁王朝大一统文化伟业服务的政治雄心。 实际上,萧统并称“姬、汉”,并非随意为文,或匠心独运,而是沿用了在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关于“姬、汉”的固定用词。而“姬、汉”用词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这一时代必然要求的外显。 就南朝而言,早在南齐时代,“周、汉”用词已成固定搭配,将周、汉视为两大文化王朝典范的认识,已经较为自觉而普遍了。如萧琛在永泰元年的奏议,就建言“宜远纂周、汉之盛范,近黜晋、宋之乖义”[2](P138)。祖冲之在更造新历的上书中,也以周汉为参照典范:“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闰,令却合周、汉,则将来永用,无复差动。”④南齐时代,南北分别由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故南齐王朝的以周汉为宗,就不仅是对文化王朝典范的推崇,很大程度上也折射了其以华夏文化正宗自居而与北朝竞逐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的精神价值指趋与思想追求意志。 梁代不仅接续了南齐的认知,其使用“周、汉”用词,也更为鲜明地体现了接续、超迈周汉大一统文化王朝的雄心壮志。在梁武帝的诏书中,多处可见“可依周、汉旧典”“在昔周、汉,取士方国”之类说解[3](P37-43)。受此影响,史家也将梁武帝封建所本,与周、汉联结:“自周、汉广树籓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将遵古制也。”[4](P437)邱迟在《与陈伯之书》中,也以梁王朝为接续周汉之正统必然会实现国家统一这样的情理相喻陈伯之,宣称:“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5](P1496) 以接续周、汉自任,也是北朝君臣的普遍性认知与追求。相关言论可谓俯拾皆是。北魏太祖拓跋焘时期的薛提在谈论皇位继承问题时,就举了“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汉”之例[6](P795)。北海王元详赞美孝文帝拓跋宏“德迈唐虞,功微周、汉,自南之风,于是乎始”[7](P559)。张彝赞美孝文帝“积德懋于夏殷,富仁盛于周汉”[8](P1429)。高闾《至德颂》以“夏殷世传,周汉纂烈”赞美孝文帝,其于太和十四年的上表,也举“尧汤逢历年之灾,周汉遭水旱之患”为例[9](P1197-1205)。宣武时期的元显奏书中追忆孝文皇帝:“乃命故中书监高闾,广旌儒林,推寻乐府,以黍裁寸,将均周、汉旧章。”[10](P645)故《北史·儒林上》评价孝文帝时代“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北魏宣武帝元恪诏有司敕勿六跋时宣称:“大魏之德,方隆周、汉,跨据中原,指清八表。”[11](P3257)孝明帝元诩的熙平二年八月诏宣称:“皇魏开基,道迈周汉,蝉连二都,德盛百祀。”[12](P226) 至于北周王朝立国,虽以周代为宗而偏重于周代,但其建构大一统文化王朝的雄心,比之于以接续周、汉自任的北魏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史·儒林传论》记载:“周文受命,雅重经典。于时西都板荡,戎马生郊。先生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于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再如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太子少傅萧圆肃所作《少傅箴》,就以周、秦正反对比大臣对国家安威的重要影响,宣称“姬周长久,实赖元良。嬴秦短祚,诚由少阳”[13](P755)。 北齐王朝则更重周汉并称。高洋天保七年十一月增加人口的诏命,就以周汉为参照楷模:“傍观旧史,逖听前言,周曰成、康,汉称文、景,编户之多,古今为最。”[14](P63)陈元康死后高洋的诏书也举周汉功臣为比,褒称元康如“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处盛汉,旷世同规,殊年共美”[15](P345)。 隋代实现了国家的大统一,延续这种普遍流行于南北朝时期的“周汉”固定用词,更是意指明确。如宣敏在隋文帝时代奉使抚慰巴、蜀归来,针对隋代封建国事上疏,就宣称“臣闻开盘石之宗,汉室于是惟永;建维城之固,周祚所以灵长”,故他期许隋代能够“继周、汉之宏图,改秦、魏之覆轨”[16](P861)。而薛道衡在炀帝时代所上《高祖文皇帝颂》,甚且推崇隋文帝的统一、化育之功是:“张四维而临万宇,侔三皇而并五帝,岂直锱铢周、汉,魏、晋而已。”[17](P1411) 由对普遍流行于南北朝迄于隋代的“姬、汉”固定用词的考察,不难发现,萧统《文选·序》中的所谓“姬、汉”用词,不仅渊源有自,尤有特殊用心:在自周代至梁朝的历代王朝中,萧统特别表彰周、汉两代大一统文化王朝,显然意在昭彰梁王朝欲绍继甚且超迈周、汉两代大一统文化王朝伟业的政治雄心。故其主编《文选》以为“比隆周、汉”大一统文化王朝的一代国家文化大典的内在心志,居然可知! 再具体考察萧统主编《文选》时所处的南北朝后期特定的政治文化发展现实:其时南、北对峙,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的梁王朝,正处于繁荣发展期,也有统一天下的宏志,甚至一度还取得南北对峙时的战略优势。梁武帝于天监元年四月即位,天监四年冬十月,即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兴兵北伐,直到太清元年“八月乙丑,王师北伐,以南豫州刺史萧渊明为大都督”。太清二年八月,“侯景之乱”爆发,太清三年五月,梁武帝死,可见建立大一统王朝实为梁武帝一生志业。而萧统作为太子,也曾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伐事业:“普通中,大军北讨,京师谷贵,太子因命菲衣减膳,改常馔为小食。”[18](P168)至于萧统主编《文选》,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得到梁武帝的亲自授意,这样的说法虽只是原情推论,并无文献依据。但即便没有梁武帝的亲自授命,“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并有“明于庶事”“天下皆称仁”的美誉,其被梁武委以执掌朝政重任,顺应时代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主编《文选》以为一代国家文化大典,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二、萧统重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高度的关系 在萧统本人关于《文选》编纂的论述中,确实不见直接论述梁代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高度关系的文字,但其主编《文选》时,重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高度的关系,当无疑义。由于学界更多关注萧统主编《文选》与文学、文化审美的关系,本文侧重论述萧统注重国家意识形态,并将其与文化审美高度有机结合的相关论述。 最为有力的证据,是萧统《文选·序》论述文体之源时,本儒家诗教,由《诗序》所谓“诗”之“六义”谈起,分论文体更以“赋”为第一,并将“述邑居”“戒畋游”列为“赋”之前两类;选“赋”也以“京都”“郊祀”“耕籍”“畋猎”为前四类。此种做法,明显不同于陆机《文赋》的先“诗”后“赋”,也与刘勰《文心雕龙》先“明诗”后“诠赋”异趣。如果萧统不是以太子身份实际主持朝政,并以肩负王朝政治文化使命自任,而是有类于陆机、刘勰等文士,其是否还会采用如此编选方式,确是值得予以思考的问题。故需要特别强调指出,在高度重视文学独立观念与审美功能的梁代文化氛围中,萧统在主编《文选》时,虽也注重各类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功能,但以“赋”为第一文体,并首重“赋”与帝王及王朝政治关联最为直接、深密的思想内容,确实体现了其借“赋”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功能来彰显国家文化总集的编纂理念。后世大型类书编纂每以“赋”为第一文体,正是师承、效仿萧统关于总集的编纂理念。⑤ 其二,在《文选·序》中,萧统追溯“文籍生焉”,关注的乃是其源自“伏羲氏之王天下”,追溯“文之时义远矣哉”,注重引述的乃是“《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萧统分明是在申明:“文”自其起源之初,就服务于国家政治文化意志,负有“化成天下”的政治文化功能。其如此论述“文”之起源,除了师承儒家教化成说,也当由于其身为实际执掌朝政的太子,而以国家文化发展方向的引领者自任,更加重视编纂作为总集的《文选》的教化作用。故萧统虽抱持“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的“文”之进化论观念,却不会否认“文”具有“化成天下”的政治文化功能,其所具有的特定政治角色,甚至还强化了重视“文”具有政治教化功用的思想观念。正因如此,在具体论述各文体的性质时,萧统也多强调政治教化功能。如其论“诗”重“正始之道”“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论“颂”重“游扬德业,褒赞成功”,论“箴兴于补阙”,论“戒出于弼匡”,论“诔”称“美终则诔发”,论“赞”称“图像则赞兴”等。由此以观身为太子实际执掌朝政的萧统,其指称各体文学作品“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耳之玩”,就不仅是指单纯的“娱”与“玩”,还包含在于更高的文化审美阅读活动中达成潜移默化、“教化天下”功用的政治意旨。⑥因为在《陶渊明集序》中,萧统就明确批判、否定无助于风雅之道、纯粹追求感官娱乐的行为:“齐讴赵舞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镳之荣,侈袂执圭之贵,乐则乐矣,忧则随之。何倚伏之难量,亦庆吊之相及!智者贤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贪士,竞此若泄尾闾。”[19](P18-19) 《南史》本传记载萧统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躬行潜移默化的“教化天下”之道的:“时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5](P1308-1310) 而其主张编选《文选》以精华作品为本,“略其芜秽,集其清英”,“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更当包含注重提供审美阅读精品、期望在高级文化审美阅读活动中达成潜移默化、“教化天下”的政治意旨。关于这一点,其《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注重为文与“君子之致”的关系:“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遵耳。”[19](P15) 《陶渊明集序》高度表彰陶渊明作品:“常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19](P19)都可作为最明晰化的注解。 其三,以国家文化发展方向的引领者自任,亲自主编《文选》,也表现了萧统本人的宏大文化追求理想。在中华民族早期文化发展中,就存在政治领袖与文化领袖合二而一的现象,儒家也往往将此作为孔子以前所谓“圣王”的标志。而自曹魏迄于梁代,以政治领袖而为文化领袖,更成为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梁代武帝与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父子四人,都以政治领袖而为文化领袖。萧统以太子身份主持朝政,其实更多发挥的是文化领袖作用。《梁书》本传称其“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18](P167)梁武帝诏令王筠所做的《哀册文》誉其:“总览时才,网罗英茂;学穷优洽,辞归繁富。或擅谈丛,或称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惭秀。望苑招贤,华池爱客;托乘同舟,连舆接席。摛文掞藻,飞纻泛醳;恩隆置醴,赏逾赐璧。徽风遐被,盛业日新。”[18](P170) 实际上,萧统心目中最希慕的兼政治领袖与文化领袖于一身者,就是与自己政治文化角色及爱好颇有相同之处的曹魏太子曹丕。如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萧统就自称“兴同漳川之赏”,以与曹丕《与吴质书》相提并论为荣。⑦而王筠《哀册文》中所谓“七子惭秀”,正以曹魏太子曹丕与建安七子的关系,比拟萧统以太子身份“总览时才”。“盛业日新”等语,也让人联想曹丕以太子身份撰述《典论》、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著名论断。而曹丕在代汉之后,还曾主导《皇览》编纂,“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丛,凡千余篇”[20](P88),开启了大型类书编纂传统。故指萧统效法曹丕,而将编纂《文选》视为“经国大业”,并亲为主导其事,自非无根臆断。 尽管《文选序》在界定选文标准时,将周公、孔子、老、庄、管、孟之文予以排除:“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但这主要是从编选总集的具体编辑方略出发,以接续孔子以来的“圣人”著述慧命自许,正是历代杰出文化人物梦寐系之、念兹在兹之事。司马迁、扬雄、刘勰如此,萧统也不例外。⑧尤需强调指出的是,早在南朝齐代,萧子显就喊出了“若无新变,难为代雄”的豪迈口号,⑨在梁代,这样的思想观念更是深入人心。故抱持“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这种文学进化论观念的萧统,当其思考如何接续“圣人”著述、超迈曹丕等的文化成就时,选择编纂荟萃“文”之精华成果的总集,无疑也表现了其欲成就前无古人、为一代之“雄”的国家文化编纂大典的雄心壮志。 在梁代文论派别中,萧统属于“折中”派的代表人物,每以文化均衡原理折中众家,再联系其以太子身份主持朝政的特定政治角色,则其集萃自周至梁“文”之精华,也表现了其从政治文化理想高度出发集“文”之大成的思想意识。⑩ 正由于萧统本人由文化追求理想高度等出发主编《文选》,日本空海和尚所著《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就剀切揭示:“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21](P163)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宁愿认为,虽然不排除其禀承梁武帝意旨的因素,但更多还是出于高度自觉的文化创造行为。而其主张以选择“文”之精华作品为本,注重在高级文化审美阅读与感悟中达成潜移默化、“教化天下”的政治功用,既是对孔子以编选《诗经》方式推广儒家“诗教”的教化方式的发扬光大,也表现了其高明的政治文化眼光。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萧统英年早逝,简文帝与梁元帝又都是梁代“新变”文论的代表人物,二人均痴迷于“宫体诗”创作,将“宫体诗”树立为代表梁代文学创造的一代之“雄”,故在萧统去世后的简文与梁元在位时期,《文选》作为一代总集的重要价值,实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虽然“宫体诗”创作及徐陵编纂《玉台新咏》专门选收“宫体诗”,也具有重要审美价值,但在南北朝后期的特定政治文化情势下,萧统所具有的政治文化眼光高度及其对国家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感,确实不是简文、梁元二帝所可望其项背的。尽管历史不可以假设,但联想曹魏政权正是由萧统所推崇的太子曹丕继位,并实际推动了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假如萧统没有早逝,而是由其继续实际主持朝政,或由其继承帝位,避免其父萧衍晚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各种昏荒举措,躬践其以《文选》作为“文”之总集的政治文化理念,并重视其它政治军事方略,真正做到“文”“武”并用、刚柔兼济,则梁代鼎盛文化怎样发展演变,乃至梁代历史怎样发展演变,确实是可予以骋怀想像的事情。尽管不能将梁亡完全归咎于文化方略偏误,但作为政治领袖与文化领袖,简文、梁元以个人偏嗜作为时代文化的主流方向,确实有其负面的政治影响作用,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与简文、梁元所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掌握东魏实际政权的高欢就喜爱《文选》,其身边诸学士多熟悉《文选》,而高欢正与萧统生活在同一时代。(11)魏收在谈论文体优劣时,对比号称“北地三才”的北齐魏收、温子升、邢邵三人,颇以擅长为赋自傲:“会须作赋,始成大学士。”[22](P492)明显受到萧统《文选》重赋思想的影响。尽管不排除个人趣味偏好因素,但被奉为北齐高祖的高欢以及“北地三才”对《文选》及居于《文选》各体之首的赋的重视,明显与大一统时代政治文化发展需求密切相关。 在隋代大一统时代,《文选》实际上已经被视为国家科举取士的重要参照读物。而作为萧氏后人,以《文选音》成为《文选》研究开山人物的萧该,正以重视“汉学”“尤精《汉书》”著称,其对《文选》的研究,也当寄寓对大一统文化发展的期待。《文选》及“文选学”对唐代精神建设与文化发展,也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支撑影响作用。后世每以汉、唐并称,唐人则具有浓厚的崇汉情结,但刘汉创业君臣普遍较为欠缺文化素质与追求境界,并不具备代表当时先进政治文明的水平,(12)李唐创业君臣则是南北文化成功融合的产儿。李唐王朝不仅建立在较高的文化基础上,其在创业之初就高度重视对前代精华文化遗产的选择继承与发扬光大,故以“宫体诗”为代表的浮靡文化被予以否定,而集萃唐前“文”之精华的《文选》,在初唐时期即被采纳为科举取士的第一权威读本,从而明确了其所具有的国家文化大典地位,“文选学”也兴盛繁荣于初唐时期,确实是时代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性选择。正因如此,初唐时期不仅涌现了曹宪及其弟子李善、许淹、公孙罗、魏模等“文选学”名家,李善《文选注》更成为代表唐代“文选学”研究高峰的著作。 正因萧统以太子身份亲自主编《文选》以为一代文化总集、大典,并且编选标准精当,在其后的封建时代,《文选》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建设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影响。盛唐文化高潮、宋代文化高峰与清代的乾嘉文化鼎盛,都与《文选》的整理研究与普及推广密不可分。 三、反思“文选学”研究系统与展望未来研究新景 论定重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高度的关系,自觉服务于建构比肩甚且超迈周汉的大一统文化王朝的伟大政治理想,主编《文选》以成就“比隆周、汉”的一代国家文化大典,是萧统主编《文选》的重要指导思想,将有助于更为全面、客观、准确地认识、发显萧统的特定编选思想与编选内容的价值,也带给我们反思当代“文选学”研究系统、展望未来研究新景的重要契机。 第一,《文选》之“文”的真正含义究竟为何?长期以来,学界较少关注《文选·序》开篇即将“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作为“文”之起点,并引述《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阐述“文”之“时义”的远大深广,较少关注《文选》实际是对“文”之发展的一种择取与总结,较少关注萧统注重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的关系,而是以当代被提纯化的“文学”概念与《文选》之“文”对接,从而仅将《文选》理解为一部当代意义上的“文学”总集,片面窄化理解《文选·序》“文”之进化论与审美意义的关系,单纯着眼于“沉思”与“翰藻”立说,讨论《文选》的诸多精义,也只局限于当代狭义形态的“文学”层面,刻意区分《文选》之所谓“实用文体”与“非实用文体”。姑不论先唐时期“文学”概念指涉远比今日宽广,如果正视由曹丕《典论·论文》所谓“四科八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所谓“十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到萧统《文选》的三十九体分类,则萧统之“文”绝非仅仅是“沉思翰藻”,而应该是遵从儒家诗教说“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文”,只不过这“文”更注重“文”的进化发展,强调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高度予以有机契合,从而使“文”在更高层次更好地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文选》也绝非今日意义上的所谓文学总集,而是一部包容更为广大的国家文化总集、文化大典。这样,研究《文选》就不仅要研究其属于当代所谓的“文学”之意义指涉,更要与古代之“文学”概念对接,全面拓展、系统研究《文选》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思想意义、审美精神与其它属于基础性、多样性的文化价值内涵,研究《文选》在后世被确认为一部国家文化大典,其被经典化、普及化的历程及其优劣得失。 第二,当代“文选学”研究的繁荣兴旺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但为了更好地发展,还必须追问当代“文选学”研究系统的建构是否合理。在“文选学”研究系统中,居于核心主导的方面究竟为何?可以肯定地说,“文选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乃在编选问题。因为其所选录的多数作品在当时皆为习见,仅分析作品显非“文选学”之要义。为何、如何选择这些作品,并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使这些作品构成一个自足的国家文化大典系统,这才是《文选》之所以是《文选》的关键。故研究萧统的立意,就显得特别重要。可惜学界过分专注在编者、编纂时间、编纂过程等方面的具体研究,以致《文选》的核心价值几乎湮没不彰。故笔者也在此向学界呼吁:超越今日之较为狭隘的“文学”观念,回归到古代“文学”观念的对接,不仅以深入研究《文选》这一部意欲“比隆周、汉”的一代文化大典为契机,积极思考重构“文选学”研究系统,推动“文选学”研究事业迈向新的高峰,也为实质推动中华民族21世纪文化复兴伟业的“文学”概念重构,以及核心精神价值与思想系统的重构,提供重要思想资源与智力支持。 注释: ①当代学界对有关《文选》实际编者的看法,大致存在三种观点:清水凯夫力持“以太子仆刘孝绰为中心”之论(《〈文选〉编辑的周围》,《六朝文学论文集》第31至45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力之认为乃昭明太子萧统独撰(《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顾农、俞绍初、曹道衡等则认为乃刘孝绰及众人在萧统的主持之下共同完成的(顾农《与清水凯夫先生论〈文选〉编者问题》,《齐鲁学刊》1993年第1期;俞绍初《〈文选〉成书过程拟测》,《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曹道衡《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 ②关于具体编纂时限,学界有以下众说:清水凯夫认为是“大通元年至大通二年”(《〈文选〉的编辑时期》,《六朝文学论文集》第43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曹道衡认为乃“大通二年至中大通元年”(《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俞绍初认为在“普通四年至大通三年”(《〈文选〉成书过程拟测》,《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力之认为“上限当为普通五年二月,下限为普通七年十月”(《〈文选〉成书时间考说》,《钦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傅刚认为“开始于普通三年以后至普通六年之间,完成则在大通元年末至中大通元年十一之间”(《〈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1期);穆克宏认为乃“普通三年至普通七年”(《〈文选〉编撰年代蠡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王立群亦持同说(《〈文选〉成书时间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③关于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一统体现了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预示着历史即将进入一个更加文明、更加繁荣昌盛的时代,即兆示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强大而又高度文明发展的大唐王朝的即将到来,拙著《汉魏六朝文史论衡·庾信与由南入北文士的“节操”问题》第246-250页有较为深入的探讨,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④参见《南齐书·祖冲之传》第904页的记载。另《南齐书·王融传》另818页记载王融上疏之“绵周、汉而不悛,历晋、宋其逾梗”类说解,虽不是推许“周、汉”,但其受到“周、汉”固定用词的影响,殆无疑义。 ⑤朱晓海所论也可作为本文观点的一个有力支撑,参见其论文《两汉六朝诗文中的李陵现象》第55-57页的相关论述,载《古典文献研究》第十四辑,凤凰出版社,2011年。 ⑥参见拙著《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第354-360页的相关论述。 ⑦参见拙著《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第98页的相关论述。 ⑧萧统乃弟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就提到从孔子、司马迁到萧绎本人的所谓“素王”谱系和当仁不让的“素王”情结:“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也可参看拙著《汉魏六朝文史论衡·“素王”造像、“素王”传人与〈孔子世家〉》第50-82页的相关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⑨参见《南齐书·祖冲之传》第906页。 ⑩参见周勋初《梁代文论述要》第195-221页的相关论述(《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64)及刘志伟《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第358-359页的相关论述。 (11)参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七所收隋代侯白《启颜录》的记载。 (12)参看拙著《汉魏六朝文史论衡·陆贾与汉初的道德重构及文化复兴》第13页的相关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