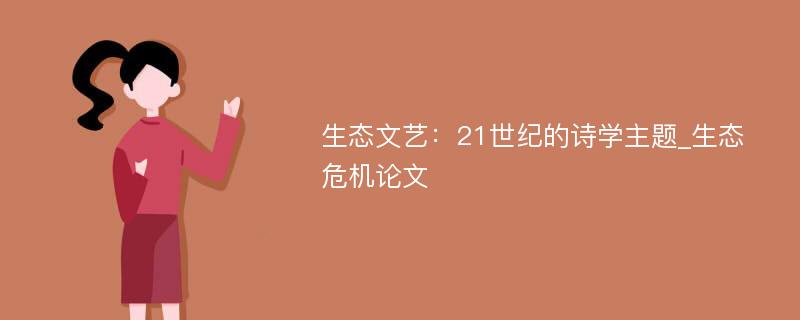
生态文艺:21世纪的诗学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文艺论文,生态论文,话题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1)02-0020-06
21世纪的文学艺术与文艺学向何处去?我觉得,关注生态,发展生态文艺,创建生态诗学,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这是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严峻形势对人们提出的要求,是文艺与诗学的必然走向,也是人类本身发展的需要。
一
我们的诗学不能离开人,不能离开人的生存。当我们走进21世纪的时候,发现人类的生态危机成为全世界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使当前的文艺与诗学不得不在生态危机的冲击下发生变化。
所谓生态,原指有机体与环境相适应的状态。随着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和人们认识的深入,生态话题逐渐转向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如今所说的“生态”,主要指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生存状态,人与生活环境共存的方式;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等层面。按照生态系统的观点,人在自主行为中必须保护环境与环境共存互补,实现生态平衡,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否则就会导致生态危机。
用生态学的观点看世界,就会发现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人在社会中与他人的矛盾、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矛盾日益突出而形成危机。一是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榨取与自身的盲目扩张,使地球不堪重负,生态失衡,出现自然生态的严重危机;二是全球化的掠夺、倾销、诱骗与威胁,使世界更加两极分化,加剧了社会生态的危机;其三,生存危机又带来文化危机,信仰失落,金钱至上,人性扭曲,失去了终极关怀的人们心理错乱,发生精神生态的危机。从自然生态到社会生态再到精神生态的失衡都已扩展为全球性的危机。有的西方学者曾预言人类走不过2100年,令人毛骨耸然。
这使人想起过去有一句宏伟的口号,叫做:移山填海,征服自然。工业技术的发达,的确能够“移山填海”,但是被“征服”的自然却使人类面临危机。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为什么要征服自己所依托的自然呢?太平洋东南部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为了建造巨型的神像以进行宗教仪式而征服自然,结果“耗尽了木材资源,以致危及自身的生存”[2]。又如前苏联为了灌溉农田而改造自然,向流入咸海的河流引水,结果使咸海干涸,周围的田地盐碱化。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3]事实上西方工业文明所谓征服自然的结果,已经破坏了生态平衡,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森林遭到毁灭性砍伐,野生动物被捕光杀绝,水土流失,空气污染,河流污染,海洋污染,物种退化,资源枯竭,土地沙漠化,二氧化碳大量增加使气温上升海平面升高,特别是有毒的化工产品和放射性物质直接危害生命造成病变。自然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又危及人类的生存。
于是人类不得不面对自然生态的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在西方空前繁荣的现代化景象背后发现了潜藏的生态危机。1972年,罗马俱乐部委托一批学者首次提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麦多斯等人在报告中警告说经济的无限增长将很快使地球上的资源耗尽。[4]沃尔德、久鲍根据58个国家的著名科学家提出的152项建议合著了《地球只有一个》的报告,再度向人们敲响警钟。[5]一些学者进而提出“自然不可改良”、“回到大自然”、“人类处在十字路口”和“生态革命”等口号。许多敏感的作家密切关注生态问题,如实地描述严酷的生态危机,在全世界迅速兴起生态文艺的浪潮。例如,加拿大的莫厄特就是最有代表性的生态文艺作家之一。他的生态纪实文学《鹿之民》、《与狼共度》、《被捕杀的困鲸》和《屠海》等作品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事实还告诉我们,与自然生态的破坏同时危害人类的是社会生态危机。因为自然生态的破坏正是由于社会化的掠夺而加剧。20世纪打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从未停止的局部战争乃至所谓白手套战争,给人类生态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跨国资本主义将世界缩小为一张网络以便随意炒作。西方金融资本控制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命脉,无形地榨取巨额剩余价值。占世界人口1/5的富国消耗着世界4/5的能源与财富。贪富差距的拉大,伴随着腐败与穷困的恶化。富国的财团一方面疯狂地搜刮穷国的自然资源,操纵走私与贩毒;一方面将带有严重污染的化工生产转移到穷国,加剧了第三世界生态危机,实质上导致了全球化危机。
更为严重的恐怕是还没有普遍意识到的精神生态危机。西方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并没有解决精神生态问题。金钱与权势的不平等使人性更加异化,摧毁了人们的精神家园,产生失落感、异己感、被抛感和孤独感。经济垄断和文化工业使亿万大众被异化为“单面人”,他们感到精神生态成了“荒原”。宣称“上帝死了”的一些西方学者又无所依托,有的试图向东方文化寻找精神寄托,然而东方并非乐土。在中国,经过“文革”的精神失衡之后,许多人又陷入了拜金崇洋的精神怪圈。仅仅用科学和法律还不足以解释腐败、吸毒和迷信“法轮功”的现象,那是另一种精神生态的危机。就像自然生态的破坏导致生物灭绝一样,精神生态的恶化也能毁灭生命。
生态危机警醒世人,生态文艺勃然而兴,“人与自然”成为21世纪全世界文学的重大主题。一批作家侧重于报告自然生态的危机,另一批作家致力于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有一些作家则以文学表现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危机。既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引起世界有识之士的关注,既然生态危机正在向我们袭来,也就逼得我们的文艺与诗学不得不关注自身的生态问题。幸而我们已经认识到文艺不是工具,而是一种“生命”,需要寻求新的生态。而生态文艺的发展与演变,必然成为诗学的研究对象。人类需要与自然和谐共存,需要寻求生态家园,需要可持续发展,对于21世纪来说,这些都是十分有意义的诗学话题。
二
生态文艺由来已久。盖因人们处在生态之中,感受到生存的自在或者危机,往往情不自禁地歌咏之,描画之,于是有了生态文艺。我们可以将那些描写人的生存状态,表现人与自然对话,展现精神生态的艺术及有关作品称为生态文艺。它们应该是诗学研究的对象。
例如,18世纪法国作家卢梭的散文《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抒写了处在大自然中的乐趣,其中写道:“我迈着平静的步伐,到树林中去寻觅一个荒野的角落,一个人迹不至因而没有任何奴役和统治印记的荒野的角落,一个我相信在我之前从未有人到过的幽静的角落;那儿不会有令人厌恶的第三者跑来横隔在大自然和我之间,那儿,大自然在我眼前展开一幅永远清新的华丽的图景。”使卢梭神往的是没有遭受任何奴役的“大自然的乐园”,他徜徉在那些充满奥秘的花草林木之间心醉神迷。由此表现了对自然生态的钟爱和对奴役者的厌弃。与之相反,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则直接描绘了被污染的环境。在他的小说《荒凉山庄》中有这样一段:“烟雾笼罩着泰晤士河的上游,在绿色小岛和草坪上空翻滚着,烟雾也笼罩了泰晤士河的下游,缭绕在桅杆之间,飘浮在又大又脏的城市靠近河岸的垃圾上……到处脏乎乎的。烟雾迷住了人的双眼,堵塞了格林威治靠人养活的一批老者的喉咙。”狄更斯对英国泰晤士河上烟雾的写实,揭露了工业污染破坏自然生态的状况,及时地表达了生态不容污染的呼声。19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草叶集》中一方面歌唱自然界的各种生物,例如说,“我相信这些带翅膀的生物有其目的性”;一方面斥责人们破坏生态的行为,他指出,大地给予人的是“物质的精华”,而“它从人那里得到的回赠,却是这些物质的垃圾”。此外还可以举出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等人描写自然与人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不一定是以生态为主题,但我觉得它们描写了生态处境,表现了生态意识或生态情趣,就属于广义的生态文学。而且,我们的诗学正需要研究这些早期的生态文学如何影响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生态文艺,需要研究国外的生态文艺如何影响我国当代的生态文艺。
中国的生态文艺可以说源远流长。古老的《周易》、《诗经》和乐府民歌用纯朴的语言歌咏了人与自然相依共存的情态。文人的创作从《庄子》、《楚辞》到魏晋六朝的山水诗与山水画,自然生态的意趣渐趋明朗;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等人之后,唐、宋、元、明、清,历代的生态作品丰富多彩,出现了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园诗,杜甫、杨万里等人的花鸟虫鱼诗,柳宗元、欧阳修等人的山水游记,《太平广记》和明清小说笔记中描述人与自然交往的故事,还有荆浩、郭熙、倪瓒、唐寅等人的山水画,黄筌、徐熙、赵昌、王冕等人的花鸟画,直至齐白石笔下的那些天真活泼的小生灵,以及流行于民间的戏曲、雕塑、装饰、园艺等等,多方面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趣。中国古代的生态文艺从基本意向看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是表示向往自然回归自然的情趣,如庄子所谓“与麋鹿共处”,山林皋壤“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其二是主张按时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保持生态平衡,如孟子所说:“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说:“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其三是表示对生态危机的忧虑,例如人们用“暴殄天物”(《尚书》)、“网张四面”和“竭泽而渔”(《吕氏春秋》)等话语批评破坏生态的行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杜甫的诗作,唐代诗人杜甫一方面以花鸟友于的情怀大量描写各种可爱的草木虫鱼,一方面对现实的生态危机表示深切忧虑。他明确写道:
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晓发公安》)
杜诗中提到的这“生态”二字,显然不等于现代生态学的概念,但是杜甫的诗确实可以代表中国作家对于自然生态的关切之情。例如,他的《观打鱼歌》与《又观打鱼》诗描写了一场生态悲剧:“苍江渔子清晨集,设网提纲万鱼急。”诗人替横遭网罟之祸的鱼儿提出控诉:“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干戈格斗尚未已,凤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6]诗人将这种破坏生态的罪行称之为“暴殄天物”。他还尖锐地指出:“前王作网罟,设法害生成。”(《早行》)[6]将批判矛头刺向制作网罟捕杀生物破坏生态的古代帝王。表现了相当超前的生态意识。研究古代作家的生态意识与当代生态文艺的关系,是21世纪诗学的又一任务。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周作人、朱自清等人描写自然生态的美文,鲁迅讲述未庄农民生存困境的小说,老舍讲述城市贫民生存困境的故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生态风情;当代文学中,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等报告文学,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与《金牧场》、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阿城的《三王》与《遍地风流》、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宋学武的《干草》、孔捷生的《大林莽》、李锐的《厚土》、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刘恒的《伏羲伏羲》、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等小说,都需要从生态文艺的角度重新评价。这更是21世纪诗学的重要课题。由以往的文艺观念看来,作品中的草木、虫鱼、飞禽走兽不过是人物活动的背景、道具,或者是拟人化的寄托物;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往往被视之为寓言或童话。因而在解读生态文艺现象之时,旧的诗学显得无能。于是21世纪呼唤我们建构新的诗学。
在我国文艺学界,生态文学的研究刚刚起步,一些学者发表了有关生态文艺或文艺生态的论文,提出了“走向生态领域的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中华文化生态”、“文艺的绿色之思”和“生态文明论”等观点,表现出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势头。但是其中某些论著还存在着简单化地套术语而不够深入的情况,特别是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学还没有能开始系统研究。而研究中国生态文学的传统和现状正需要建构新的诗学。
三
生态诗学是指在传统诗学的基础上吸收新兴的生态学理论,研究文艺生态与生态文艺现象的一种边缘性的文艺理论。随着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生态文艺和文艺生态成为21世纪文艺学的话题、热点和学科前沿课题之一,于是引起文艺学界对生态学的兴趣。
现在一般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命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人的生存状态和适应环境的方式,研究如何保护自然环境以利于持续发展的科学。关于生态的思想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它发端于1866年德国学者海克尔的《有机体的一般生态学》,原是一门探讨有机体与环境相适应状态的生物科学。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对生态危机的警觉和生态运动的兴起,促使生态学延伸到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等方面,发展为主要考察人类生存状态的跨学科的系统科学。继麦多斯等人提出《增长的极限》之后,罗马俱乐部又发表一系列研究报告,如《人类处在转折点上》、《第一次地球革命》等。在欧洲兴起了影响广泛的生态运动,或称“绿色运动”,还出现了一些以“绿色”命名的组织,如法国的“绿色人”、英国的“绿色人之友”、德国的“绿色行动与未来”等。他们兴办生态展览,出版书刊,举行“生态电影节”,积极呼吁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联合国也接连召开全球高层次的环境保护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生态学家们还提出可持续性发展的概念和建设生态圈的设想,甚至主张进行生态学革命。而生态学著作则呈现出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例如,美国学者P·奥德姆的《生态学》,德沃尔、塞申斯合著的《深层生态学:自然关注的生活》,C·富万的《生态系统和环境》,罗德里克·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法国学者让·多尔斯特的《在自然界死亡之前》;英国学者戈德史密斯的《工业社会的危机》;德国学者狄特富尔特的《人与自然》;巴西学者卢岑贝格的《自然不可改良》;日本学者岩佐茂的《环境的思想》等等。他们的许多观点对于理解生态文艺和建构21世纪诗学具有启示意义。
譬如,生态学的世界观及其对基督教神学理性的批判就颇有诗学价值。生态学家用“一种与现代分析科学的认识论模式完全不同的整体的思维方式”看世界,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用的、永无止境的复杂的网络”,人与自然可以平衡共存[7](P120)。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费雷认为,生态学是一种后现代科学,或称为一种后现代世界观。他说:
生态意识的基本价值观允许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正当的利益在一个动力平衡的系统中相互作用。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7](P121)
为什么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与这种“大花园”的理想相反呢?生态学家们认为导致生态危机的“征服自然”的思想源于《圣经》,因此他们对基督教神学和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理性进行质疑,“拒斥现代的、牛顿式的上帝。”[7](P141)另一个美国学者L·怀特也认为,上帝创世的思想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他指出:“第一,现代科学是自然神学的外推;第二,现代神学可以解释为西方唯意志论者实现基督教关于人胜过和合理统治自然界的教义。他主张创建“生态学化”的新的科学取代之[8]。再如巴西生态学家卢岑贝格写道:“现代工业社会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带着无休无止传教欲望的疯狂的宗教。”[9](P53)他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观……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古老的世界观。在被我们视为原始的所有文化中,关于这种世界观都有极为简洁、富有诗意和神话色彩的表达方式。”[9](P53)
生态学家理想化的这种“大花园”式的“富有诗意”的世界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我们要建构“生态学化”的诗学,正需要追溯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中国文化重生、贵和、富有诗意。重生,就是以生命为重,不仅注重人生,也珍惜自然界的生命。古老的《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就含有生命、生存和生态等意思,“生生之为易”。其二是贵和,以和为贵,不仅注重人伦和谐,也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例如,中国艺术的“艺”字,其原型为人与植物共生的形象。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庄子》说“与糜鹿共处”,都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乐。其三是诗意,和谐相处体现了富有诗意的文化。如《周易》所载:“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杜诗说:“山鸟山花吾友于。”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的诗意。古代诗学的经典之作《文心雕龙》反复强调“自然之道”,《二十四诗品》大量用自然意象,如“碧桃满树”,“流莺比邻”,来象征艺术境界。从文化沟通的意义说,现代生态学家的世界“大花园”的设想是否意味着重新寻找东方诗学的境界?
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文学艺术需要与人生与社会与自然建立有机的良性的关系,保持生态平衡,以利于健康发展;一旦破坏了生态平衡,就会造成生态危机,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也不利于文艺的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当今自然界遭到严重破坏,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面前,重温马克思的这段话,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自然观,或者环境决定论、生态终极论都令人怀疑。如何解决21世纪面临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矛盾,西方学者感到困惑而转向东方。追溯东方文化与诗学的精神,就是向自然复归,向人性复归,向民间复归,向生态复归,是一个走向世界的诗学课题。
例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潘光旦就提出“生物位育”,即生态问题。他引用《礼记·中庸》的话“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认为“位育”二字代表中国文化的生态观。郑玄注:“位,犹正也;育,生也长也。”潘光旦用古人语解释说:“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其中包含着可贵的生态思想。他在《民族的根本问题》一文中说:“生态学者讲位育,始终认定两个对象,一是生物的个体或团体,二是环境。所谓位育,就是两者之间的一种协调。[10]这所谓位育,指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就是如今讲的生态。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正视生态问题。古人所谓安身立命,当今所谓如何活着。活着,就要求生存,求发展。我们不能坐视全球化、西化、后工业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而需要努力争取适合人类发展的生态。因此,追溯和反思中国文化的崇尚自然的精神,发展生态文艺,创建生态诗学,这正是21世纪方兴未艾的话题。
收稿日期:2000-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