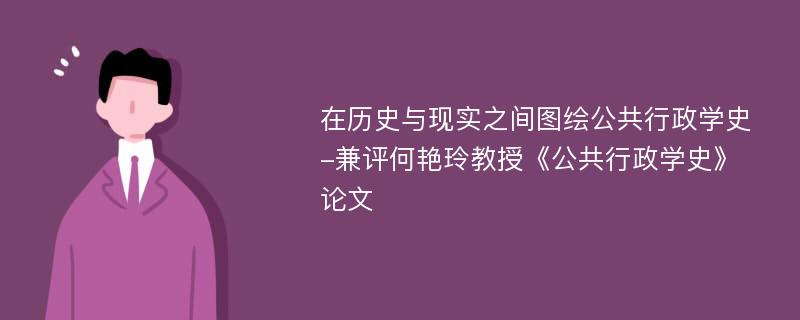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图绘公共行政学史
——兼评何艳玲教授《公共行政学史》
□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公共行政所拥有的独特思路和具体性思维方式从哪里来的问题显然要溯及公共行政自身历史。新著《公共行政学史》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采用将理论与行政实践联系的理论导向的叙事方式,对西方的公共行政历史脉络提出了新的解释视角。从公共行政学历史脉络的缘起、历史梳理的基本方式和结构等方面展开讨论,并以公共行政学史的历史脉络研究及其叙事方式为契机,提出关于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如何书写的重要问题。在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情况下,如何形成自己独立和更为专业化的研究和叙述,成为中国公共行政学者们有待反思与推进的重要议题。而前现代的行政思想史是否应当由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去AI写作,这是一个更需要思考和有待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 公共行政学;《公共行政学史》;学科;政治思想史
一、公共行政学的历史脉络:缘起与嬗变
中国改革开放后希望了解西学和向西方学习的热情数十年不辍不减,各门学科都展现了同样的景象。就公共行政学科而言,梳理公共行政学历史的著作在中国已有多种,丁煌、唐兴霖、谭功荣等学者都出版过他们的著作,而且也被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引为教材,影响很大。这是公共行政学科获取发展能量的重要所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通过学习了解了西方的理论、思维等,而西方却不甚了解我们在想什么和做什么,这也许成了我们与西方打交道时处于优势地位的一个法宝。西方国家由于处在发达地位,普遍存在着某种傲慢,从而把这种难堪的优势强加式地转让给了我们。当然,多年前我们就开始投入了大笔资金,并有了专门的“外译”项目,试图把中国人的研究、思考推介出去,但效果能否如期,尚不敢断言,因为处在世界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是某种无法抑制的傲慢。
西方研究者因为其傲慢而缺乏了解中国的愿望,这种说法可能会有很多学者反驳,认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其实非常充分。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关注也许仅限于与政治、军事相关的事务上,对于中国社会在思想和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们并无多大兴趣。并且,关于对中国政治和军事方面状况的了解,表面上看来,西方研究者似乎了解很充分,但这应该是个假象。因为,他们总是把大量对现象描述的东西塞进他们所拥有的思维方式中去进行整理、加工,从来也没有去关注中国人行动背后的思维方式,所以,不仅不能实现对中国的了解,反而生成诸多误解。比如,西方研究者肯定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感到困惑,其中,最无法理解的是在此过程中社会基本稳定是如何实现的。显然,西方国家是没有认识到中国政治以及整个社会治理的实质。因为,如果不打算了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状况,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中国社会治理的性质和功能的,按照西方国家所拥有的思维方式去整理那些由中国学者提供的或他们自己收集到的一些资料,即便描绘出了表象,也是不真实的。
也许有人会说,已经有许多中国学者到西方刊物上去发表文章,正在把中国的学术和理论推介给西方了。事实上,这同样是个假象,或者说,是个幻象。事实是中国人的作品如能得到西方刊物采用的话,往往是因为提供了关于中国的较为有价值的资料,而不是因为包含中国式的理论和思想。一些被西方刊物采用的文章,在提供资料方面是有价值的,至于按照西方的思维方式或在西方理论框架下所形成的结论,可能都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在笔者看来,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少做一些推介自我的工作。如果有一天西方国家想了解我们的时候,他们会产生出和我们今天向西方学习一样的热情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对任何一部介绍西方的作品都充满期待,认为是非常有益的工作。
以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新型材料和智能制造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加速孕育突破,引领全球制造业全面转型升级,并引发产业格局和生态的重构。汽车产业以其强大的基础性、关联性和带动性,历来是最新科技研发应用的前沿阵地。汽车,正加快从单纯的交通运输工具向具有情感的智能移动终端转变。当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和轻量化成为未来汽车发展的潮流趋势,汽车制造业将做出怎样的技术变革?
在此背景下,虽然已有多种西方行政学史的著作,但随着我们对西方的研究不断深入,视野不断拓展,视角的不断调整,西方行政学史推陈出新变得非常必要。所以,每一部新撰写的西方公共行政学史方面的著作的出版,都能戳中我们的兴奋点,都能够对于我们学习和了解西方国家公共行政学产生激励作用。也正是因为如此,何艳玲所著《公共行政学史》[1]这类作品的出版,亦能激荡起我们要为这个学科的发展作一份贡献的情怀。
与其他类似著作相比,《公共行政学史》一书补充了诸如“治理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等方面的内容,这显然是得益于国内公共管理学界近几年新的研究进展的。事实上,这些理论在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中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所以,在《公共行政学史》中,将这些新的理论系统地介绍给国内读者,也是非常必要的。而本书最后所专门列出的“结论”,则对公共行政学史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这一章对公共行政学的认识论传统进行了系统梳理,分别列出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传统”“解释主义的认识论传统”“批判理论的认识论传统”和“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传统”。通过这种梳理,作者试图赋予公共行政学一个统一的框架,从而改变人们关于这个学科是一种“知识拼盘”的印象,最为重要的是,能够从根本上终结这个学科时不时提出的“学科危机”之论。
在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后,我们更多地感受到公共行政的知识得益于相邻学科的救济。不过,我们也需要考虑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在这里是否存在着取舍的问题?如果说存在着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取舍的话,就会引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公共行政学在接受和汲取相邻学科的知识时,是以什么为依据的?当然,对这个问题的最为简便的回答是,公共行政实践是公共行政学接受和汲取相邻学科中知识的依据,即决定了知识取舍的情况。特别是关于方法方面的知识获取,更能证明实践的现实要求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如果说公共行政本身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路甚至具体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它在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吸收和借鉴中,想必也会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一来,持续的追问就会投向公共行政所拥有的独特思路和具体性思维方式从哪里来的问题。一旦希望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显然是要溯及公共行政自身的历史的。所以,对公共行政学历史的梳理不仅是服务于教学、学习和借鉴的目的,而且对于我们面向现实和未来的理论建构而言,也是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
一般说来,思想史面对的是三个维度或者说三个基本要素——理论、人物和时间,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显然是很费心思的事情。一般说来,简单的操作方式就是依时间顺序展开,但这样的话,会导致理论的碎片化。另一种方式是依时序而对人物进行安排,这同样呈现的是有历史而无逻辑的状况。所以,既要有历史又要有逻辑还要保持理论的完整性,就需要对三个维度都照顾到,特别是要根据理论去对人物和时间进行安排。《公共行政学史》所采取的正是这种方式。在以时间为依托的叙述中,作者充分地考虑了理论结构,从而使理论的逻辑和系统性都能得到较好的呈现。也就是说,治史的重心主要是去把握历史脉络,思想以及学科的历史亦如此。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只是20世纪的事情,短短百年却又无比繁杂,以至于把握其发展脉络比较困难。《公共行政学史》在此问题上显然是下了大功夫。一方面,清晰地界定了各个学派,认真梳理了每个学派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又考虑各个学派出场的时间先后,在时序中去进行历史建构,展现公共行政学史的历史脉络。总的说来,作者注重把公共行政学的各家理论与解决实践问题的需求联系起来,以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去为理论的嬗变更迭描绘出发展轨迹。应当说,这是中国学术语境中的通行做法,是中国学者的擅长之处。但是,如何做得不着痕迹,却是非常困难的,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治史者的学术功底。《公共行政学史》的篇章结构充分反映了这个学科的特殊性和专业教学的现状。一般说来,教材并不运用“导论”的形式。因为,考虑到教学的安排,都会在先开设了原理性的专业基础课的前提下再开设学科史方面的课程,所以,如果安排一章“导论”的话,内容会有重复。但是,从国内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实际来看,特别是对MPA的教学而言,在公共行政学科历史的课程中作一个全景式的专业基础概述又是必要的。而且,从公共行政学的历史来看,诸多基础性的概念使用不统一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需要通过设计出一个“导论”来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就本学科的研究者而言,在知识背景上也有着巨大差异,也需要通过一个“导论”而对他们的研究工作予以范式意义上的规约。这些方面,都决定了“导论”对基础性的概念、知识边界进行确认,对理论发展的状况、学科发展的脉络以及对学科构成复杂状况等给予一些交代,是非常必要的。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对公共行政学史的写作。就这一安排来看,作者显然是深刻地体会到了该学科的特殊性,对教学、研究等诸多方面作出了综合性的考虑,从而按照该学科的具体要求去设计自己的叙事逻辑。比如,作者在《公共行政学史》的第二章用了整整一章进行背景介绍,这不仅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感,也为公共行政理论切入到思想史中去做了良好的铺垫。
如今,设计已无处不在。设计已不仅仅局限于工业产品设计,而是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设计的基因已被植入人居环境、乡村振兴、旅游、体育、文化等诸多产业之中,设计让中国企业、中国品牌在发展的道路上策马扬鞭。
二、理论导向叙事:赋予公共行政学统一框架的尝试
当然,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科学史上较晚生成的学科,因而,与其他学科间的交叉互动也反映得较为典型。因为,公共行政学吸收了很多成熟学科的规范理论和体系化了的知识,使得公共行政学在学习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应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方面显得非常方便,省却了许多按照现代认识论模式独立建构的力气。所以,面对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一方面,人们主张这门学科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又随处可见来自于其他学科的思想、观点、知识和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如果对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观点、知识和方法都进行甄别、标识的话,就会发现,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并无属于自己的东西。从公共行政的研究者来看,在20世纪的统计中,几乎都有着其他学科背景;也正是他们,把各个学科的有益于公共行政建构的因素带了进来。这种情况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产生了积极效应,但这对公共行政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来说,却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困难:其一,如何把握包含在这个学科中的如此庞杂繁复的理论、知识、方法等。因为,这样做的话,需要首先去涉猎多学科的理论、知识等,在科学体系如此庞大的今天,样样精通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在需要的时候通过终端设备查访网络资源上的一些知识点,而这对于准确地理解一种理论则是远远不够的。其二,就公共行政学自身而言,在将各学科的理论、知识、方法等引入后,是如何实现它们的共处的。也就是说,既然公共行政学是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的,而且作为一门学科也得到了科学大家庭的承认,那么,这个学科就应当被认为是拥有了自己完整的知识体系的,否则,学者之间、学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就无法进行。进而,就会提出另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是由什么因素将知识整合成为体系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公共行政学知识体系中的知识都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其中肯定存在一个促动机制去使这个学科中的所有知识都动起来,那么,这个机制是什么?应当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学理推导中提出来的。对于管理类之外的其他学科而言,基本上都是可以通过学理分析而给出答案,而公共行政学则是无法做到的。然而,当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去阅读《公共行政学史》的时候,却发现作者如此轻松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即始终扣紧时代中的问题的具体性。这样一来,公共行政学所涉及到的理论、知识等无论是源于哪个学科的,都可以通过其所欲解决的现实问题来加以认识和理解,并显示和证明其价值。至于公共行政学的历史脉络,则是包含在时代的变迁和现实问题的嬗变之中的。把握了这个脉络,也就清晰地看到了那些来自于其他学科的理论的出场次序;也就看到了公共行政学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因为一种理论的引入而得到成长的,同时,新知识所带来的活力又是怎样促进了整个知识体系运转起来的;也就看到了分别来自于不同学科的理论如何在公共行政学这里得到洽接并被整合到了同一个逻辑线索之中。
由此也可以看出《公共行政学史》是以建构性的方式来书写学科发展史的,不再是作为局外人去观察和记述历史,也正是这一点,证明了著者不仅是公共行政学史的研究专家,也是公共行政学理论家。如果将此与分散在各章中的评论联系在一起的话,也确实看到了作者因为对这门学科的深耕而有了自己的理论建树。而在这种理论建树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构成了《公共行政学史》一书的创新基因,而且这个基因又得到中国文化和中国公共行政实践的滋养。总之,《公共行政学史》是一部由中国学者著述的透着中国气味的西方公共行政学史的著作,既有中国视角和中国气息,又有对西方公共行政学历史的客观记述。
对于范畴中心成员的确定,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见解,其中宗守云(2011)在对“副”对名词性成分的选择和量词范畴化的中心成员的研究中,得到中心成员的确定有着下四个特征标准:(1)中心成员类别的出现频率很高;(2)从语言发展上看,中心成员类别在历史上出现最早;(3)从性质上看,它们是最简单最和谐的相配,具有简单性、具体性和客观性特征,在认知上处于中心地位;(4)从交际上看,范畴中心所代表的事物都是稳固的,常用的事物,在思维上具有优先性特征。这四个特征皆是从具体语料出发,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结合人的认知方式概括得出。因此,范畴中心是一个范畴最本质的特征,有了这些特征才能开始去研究其扩展和非典型成员。
对于每一个专业来说,编纂学科发展史的著作都是基础性的工作,专业教育、知识传承都需要通过这类著作来实现。对于公共行政学而言,还不仅要服务于教育和知识传承,而且还要直接地对实践有所助益。因为,公共行政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包含在现实中,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在公共行政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特别是理论中的一些前瞻性的见解,恰恰切中了我们的现实问题。所以,《公共行政学史》的出版,不仅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提供了一本读物,也为实践工作者提供了遇到问题时可以查阅的手册。
书写的历史要形象地还原场景以及场景中的人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思想史就更加困难,但是《公共行政学史》在围绕着理论展开的过程中,作者把当时的思想交锋和讨论的状况逼真地描述了出来,从西蒙与达尔的讨论,及与沃尔多的论战,到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传统的冲突,该书都在着墨不多的情况下直观地呈现了思想是如何碰撞并相互缠绕的纹理。由于能够清晰地把握思想背后的思维线索和理论展开的逻辑,《公共行政学史》在介绍每一种理论的时候,都能用最少的文字而把理论的全貌呈现出来,既能直入理论的核心,又使理论丰满的质感得到展现,这也是作者学术功力的体现。或者说,作者是在对所有自己准备介绍的理论都做出了深入研究和认真思考后才下笔的。不仅在微观上给我们呈现出清晰的线条,而且在宏观上,也能够对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制度主义和技术主义两条线索作出清晰的描述,展现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是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展开的。如上所说,公共行政的理论较为繁杂,对其发展脉络的把握是较为困难的,但是《公共行政学史》在公共行政的渊源如何转化为公共行政框架上的制度主义,对如何在效率追求上走上了技术主义路线等,都能够化繁为简,娓娓道来,而且逻辑线条清晰,给人一种举重若轻之感。
《公共行政学史》的每一章都有对各种理论的精彩评论,我们不能不对这些观点作一点评价。阅读这些评论,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一种积极的引导,这种引导是建立在对各家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认真领悟的基础上的。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站在一个很高的学术和理论高点上,鸟瞰整个公共行政学史,将各种文献随手拈来,大大地增强了评论的信服力。比如,“如果没有西蒙,公共行政学就不知如何一步步地向前迈进,但如果没有沃尔多,公共行政学就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迈进”[1]82。从此也可以看出,作者的诸多评论性的论述是非常睿智的,而且也总是能够准确地切中各家理论的“命门”,让读者有着恍然大悟的感觉。
信息化技术与企业内控管理的融合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效率,让企业在内部管理时,构建完善的管理系统,通过能够随时调节的管理模式,让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能够打破传统管理模式的局限,通过先进技术,将企业发展的信息统计整合,结合传统会计计算和信息处理双方面的优势部分,实现企业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标准化、标准表单化、表单数据化,工作效率能够大大的提升,当前企业大多数缺乏这样的发展创新管理精神,导致很多企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
尼采说:“人类为着自存,给万物以价值。——他们创造了万物之意义,一个人类的意义。所以他们自称为‘人’,换言之,估价者”。“估价,然后有价值:没有估价,生存之核桃只是一个空壳”[2]。对于历史以及思想史来说,也同样如此。面对生成于西方的公共行政学史,我们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必然会赋予其价值。在认识世界时,人赋予世界以价值,这是因为我们要把世界纳入到我们的理解框架中去,并实现对世界的重塑。这也说明,一旦谈论价值的问题,离开了人就是不可思议的。只有人的世界,才有所谓价值的问题,人创造价值,人也赋予物以价值,或者说,价值无非是人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一个途径。人可以通过科学认识的方式去把握世界,人也可以通过价值规范去重塑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当人对世界的依赖性程度较高的时候,更多地需要依据科学认识的途径去把握世界,当人的认识成果取得了积极进展的时候,反而更加突出了通过价值的途径去把握世界的必要性。把握世界的科学认识方式给我们展示的是工具理性,而价值途径则提出了实践理性的要求。价值途径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不仅不排斥科学认识,反而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全部成就的基础上的,它所提出的实践理性要求,无疑是包含着工具理性的。
在公共行政生成之前,或者说,在前现代社会中,显然存在着行政管理,它不是现代性的公共行政,也不限于王朝机构内部的管理,而是面向整个社会的。这说明,古代的行政管理在职能实现方面与现代公共行政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其中所包含的经验和智慧也会对公共行政的实践有益。如果希望了解前现代社会中的行政管理经验和智慧,就需要对那个时期出现的行政管理思想进行专门性的研究。这样一来,就应像哲学学科一样,不是以自己的学科产生为时间上限,而是客观去看人类社会治理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既有的文献中去发现古代社会给我们留下了哪些行政管理的思想。虽然在实践上我们强烈反对不分场景、不分条件地把前人某个思想作为行政依据的做法,但对于学习和训练而言,了解前人的经验和智慧则是必要的。正如我们不能在上楼之后就拆除所有台阶一样,我们也不能在人类认识达到了今天这样一个高度的时候,就掏空这个知识框架赖以建立的基础。所以,历史研究不应因为某种傲慢而有意识地忽视前人的经验和智慧。
三、公共行政学史与哲学史叙事范式:反思与前瞻
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叙事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谈起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公共”一词限定了这个“行政”的时间范围,此前的“行政”是无法列入到“公共”范畴中的。但是,一门学科的产生与这个学科所包含的内容在历史叙事的作品中如何处理,仍然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提出的是一个“公共行政学史”的写作是否应当采取哲学史的叙事方式的问题。在行政学界,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人去关注,因为我们没有见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根据理查·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的说法,“哲学”这门学科是从康德开始出现的,准确地说,是由19世纪60年代的“新康德主义”提出了“哲学”这门学科。但是,哲学史的叙事一般都是从古希腊开始谈起。如果行政学史的写作按照哲学史的这种模式去处理历史的话,也许就需要到更早的时期中去做一些溯源的工作。从既有的几种版本来看,只有少数一两种是按照哲学史的叙事方式进行安排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行政学是实践取向的学科,与哲学的思想取向有着很大的不同。就此而言,行政学的历史叙事是不应像哲学那样把历史拉得很长的,而是应当关注能够直接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知识和理论。但是,我们也看到,几乎所有学科都有着追求知识完整性的倾向,而且,一般都是通过该学科的历史叙事文献去达成这种追求的。另一方面,对于一个专业而言,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前人思想遗产的态度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需要通过讨论而形成共识的问题。总的说来,对于理论建构而言,“凡是过去,皆为序曲”,但对于学科历史的研究来说,也许恰恰要把这个序曲演奏得尽可能完整,而不是截取某个片断演奏一下完事,更不能放弃对序曲的演奏。
显然,相对于人类漫长的认识史而言,20世纪的科学发展就像核聚变一样,瞬间爆发,闪耀着辉映天地的光彩。其实,科学的每一门新学科的出现,甚至每一项新的科学成就的出场,都是人类长期认识积累的成果。作为科学中的一个学科,公共行政学就是在科学爆发的20世纪成长起来的。显然,人类的社会治理文明有着远古的源头,却是在20世纪凝成了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并把社会治理引向了科学化、技术化的自觉状态。在公共行政科学化的维度中去看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20世纪之前甚至更早的行政管理思想也许并无可取之处。但是,如果说行政实践并不仅仅从属于科学和囿于科学的思维路径,而是包含着某些艺术特质的话,那么,学习和了解20世纪之前的行政管理思想,对于今天乃至未来仍然是有益的。特别是在民主政治的语境基本定型了的19世纪,在制度主义思路中所做的行政安排虽然没有突破政治的母体,但所包含的某些行政实践智慧,也许是需要我们去挖掘的。在宏观历史的视角中,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传承远比否定更有魅力,行政实践作为社会治理最主要的和最为古老的形态,必然包含着世代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可以发掘的宝藏。如果说今天的人们对此知之甚少的话,那么,是由于我们的研究不够。所以,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倘能成立,也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学史的叙事不能忽视公共行政实践得以产生的长期历史准备过程。
即使把行政放在一个平面上,如果我们区分出“行政”与“公共行政”两个概念,就会看到,在现代语境中,行政或者说行政管理(行政管理是一个中国式表述,在西文里就是“行政”一词)的概念多数情况下是指公共部门诸机构中的管理活动,在作为公共部门最为重要的机构——政府中,则与“公共行政”的概念所指基本重合。一般说来,公共行政特指“政治—行政二分”条件下政府中的行政,包含着行政管理的内容,但不限于行政管理。因为,行政管理主要是指一种活动状态,而“公共行政”一词则包含多方面的和综合性的内涵,特别是包含着对一种行政管理的定性要求。另一种情况是,就整个公共部门而言,除了政府之外,还有其他机构,这些机构中也有着行政管理的工作内容。在此意义上,行政管理就又不限于政府的活动,而是公共部门中的所有机构所共有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所有组织都有行政管理的事项。然而,公共行政是一种现代性的行政模式。在这一模式生成后,公共部门的所有机构中的行政管理,也都按照公共行政的要求而去界定职能和行为模式,基本上都是被限制在机构内部事务的处理上的。但是,如果我们跳出了现代语境,就会看到一个较为模糊的行政管理概念,这个概念所指的活动是与社会治理的概念大致重合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关于公共行政的视野是需要更为开阔的。
在公共行政学科历史的编纂过程中,我们也同样要赋予理论发展史以价值。也许人们会说公共行政学科的历史是属于西方的,但是,当我们去研究它的时候,当我们去写作关于它的著作时,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将其“出生地”痕迹抹去了。尽管我们指出那是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史,但在我们去谈论它的时候,是将其转化为了我们的所有物。或者说,我们对于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史的研究,写出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学史的著作,是从属于我们的价值需要的。虽然我们并不希望去重塑它,但学习和借鉴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其中也包含着我们对其作出价值重估的要求,并根据价值重估而增益于中国的公共行政理论建构。由此,《公共行政学史》中的每一段论述,不仅在评论中,而且在对公共行政理论的叙述中,都可看到那种隐含在文字背后的对中国当下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的内容。
公共行政的实践性决定了每一个理论的出场都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所以,对各种理论的介绍不仅要在思想史上去梳理前后承接的关系,也不仅要将其放在颉颃各方的比较中去揭示其性质,更要放在实践需求的语境中去考察其表现形式。但是,关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史,又是需要在理论发展脉络的描述中展开的,或者说,叙事中心是理论而不是实践。而理论往往是跟随着实践的脚步前行的,处在不断地丰富自我和完善自我的过程中。这样一来,如果更多地关注理论的结构的话,就会使时间线索变得模糊。特别是对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而言更是如此,理论导向的叙事方式会模糊公共行政学史的阶段性,或者说,使时间上的前后顺序变得不太清晰。所以,公共行政学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在编纂这个学科的历史时,是有着很大的技术协调难度的,但是《公共行政学史》却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公共行政学史》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理论导向叙事方式,而且也采用了按理论结构进行平面铺展的叙述。但是,作者更多地是通过对理论生成的原因、理论的特征以及功用价值进行追问的方式进行叙述的。由于给予了理论导向的叙述进而以这样一种方式,就在追问的过程中把理论与行政实践联系到了一起。在建立起了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后,理论就不再是苍白枯燥的教条,而是成了在我们面前鲜活生动的故事讲述者。更重要的是,实践的历史与理论的逻辑统一了起来,无论是一种理论的发展还是不同理论之间的更迭替代,都有了清晰的实践历史和理论逻辑。因而,公共行政学史的时间线索不仅没有模糊,反而是清晰可见的。作者通过这种叙述方式,还原了理论得以产生的现实场景,展现出了一幅幅移动着的鲜活画面。
关于历史研究,米尔斯评价道,“历史学家代表了人类的组织化了的记忆,作为书写下来的历史,是非常有弹性的。从这一代历史学家到下一代,它的变化往往很大,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后来更细致的发现使记录中引入了新的事实和资料,而且还由于人们的兴趣点和现在人们建立记录的框架发生了变化。这些事从无数可得的事实中做出选择的依据,同时也是对这些事实意义的主导解释。可历史学家不可能回避选取事实,虽然他会始终谨慎地解释,以否认这一点”[3]160。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历史就是现实,或者说,历史规定了现实。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一切研究工作的开展,都应建立在对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如果不知历史,也就无法理解当下的社会。当然,回顾历史和拥有历史的视角,也不能形成把当下的现实拉回到历史中去的要求,而是应当明确地意识到,“人们原来居处的社会并没有对可以创造的未来的社会设下严格绝对的限制。我们研究历史的目标是想发现一个替代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能运用理性与自由来构建历史。简言之,我们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在其中找出控制这些社会结构的手段。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逐渐地理解人类自由的限制及其涵义”[3]193。
总之,认识历史的目的是指向当下和未来的,是要思考我们的理论任务应当从哪里着手。对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而言,就如米尔斯所说的,需要通过历史来理解当下。同样,公共行政的实践如果被放在更长的历史过程中,就会看到其作为一门专门性实践形态的行政进化过程。当前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是从民主政治中分离出了公共行政,相应地,公共行政学也是在公共行政实践形态出现之后产生的。所以,历史源头在理论上可以追溯到威尔逊,而在实践上则是以“彭德尔顿法案”为标志的。这样一来,此前悠久的社会治理文明史就变成了没有行政实践和思想可言了,即使承认有关于行政的问题,也是将其推给了政治学,让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去代为书写。然而,从西方国家学者们的政治思想史的诸多作品看,政治思想史意识形态色彩较浓,意识形态支配了学者的学术研究,很少有为行政思想的发展留下应有的位置,以至于我们很难从政治思想史的作品中发现对行政思想的完整记述。
就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的研究来看,可能是由于这门学科的实践性很强,学者们基本上都是直接地从现实出发去进行历史取舍,所以,如果用一种不嫌偏激的表述来评价的话,那就是我们很难看到具有学术情怀的公共行政学者,即看不到客观求实的“公共行政学史”的著作。在此问题上,中国学者是应当学习西方学者的做法还是补其不足,则是一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其实,如果认真地审视20世纪初期“政治—行政二分”的表达式,是能够看到其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隐喻的,即政治与行政自此开始分化成两个专业领域,并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科学研究对象域。也就是说,不能把行政看作是由政治所孕育和从政治中脱胎而生的,而是应当把此前的社会治理看作是政治与行政的混沌状态,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种混沌状态被打破,分化而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进而,也实现了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学科分化。从这一角度看,政治学史或政治思想史对此前历史过程的叙述就不能代替行政学史的专门研究,当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时,公共行政学史也应有自己独立的更为专业化的研究和叙述。
选取2016年08月~2018年05月本院收治的后循环缺血患者92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46例。入选对象均知情同意,本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其中,研究组男24例、女22例,年龄43~62岁,平均(53.69±2.78)岁,病程5 h~2 w,平均(1.21±0.04)w;对照组男26例、女20例,年龄42~63岁,平均(53.49±2.90)岁,病程4 h~2 w,平均(1.17±0.06)w。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在这一问题上,《公共行政学史》的作者显然是有清醒认识的,而且也明显地处于纠结之中。因为,作者虽然把公共行政学产生之后的内容作为叙事主体,但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又努力把场景拉长,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弥补似乎已经成为定势的编写方式上的不足。总之,我们期待着未来《公共行政学史》著作者能再行开拓,写出代表公共行政学知识的更新的力作。
第四,协调平台建设。印度成立全印医疗旅游协会,为医疗旅游机构提供咨询沟通协调等服务;泰国卫生部、商务部和泰旅游理事会等也建立协同工作机制。
参考文献:
[1]何艳玲.公共行政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
[2]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55.
[3]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
Mapping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A Book Review of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y Prof. HE Yanling
ZHANG Kang-zhi
Abstract The question where does the unique way of thinking and concrete mode of thinking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me from should obviously trace back the hist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tself.In the course of answering this question,the new book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dopts a theory-oriented narrative mode linking theory with administrative practice,and puts forward a new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ical vein of west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from the origin of the historical vein of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basic mode and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outline,and will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question how to writ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vein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ts narrative mode.With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coming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iscipline,how to form its own independent and more professional research and nar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scholars in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 reflect and promote.However,whether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re-modern administrative thoughts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works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s is a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considered and discussed further.
Key words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discipline;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21(2019)04-0028-07
收稿日期: 2019-03-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重大项目(16JJD720015)
作者简介: 张康之(1957-),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王玲玲)
标签:公共行政学论文; 《公共行政学史》论文; 学科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