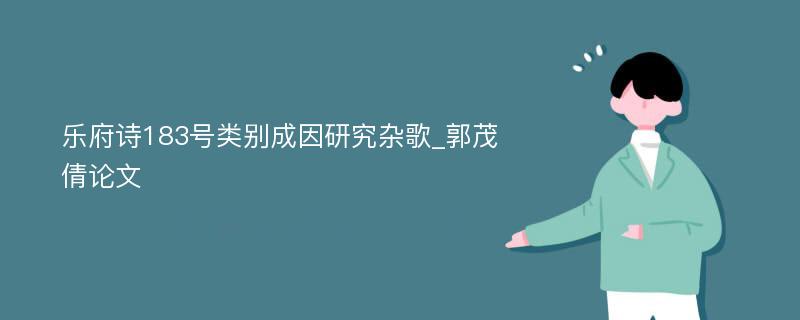
《乐府诗集#183;杂曲歌辞》类目成因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府论文,成因论文,诗集论文,类目论文,杂曲歌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0)05-0087-05
杂曲歌辞是《乐府诗集》中作品较多的一个门类,对其类目成因这个问题,前人虽常简言提及,但至今尚无学人做过专门探讨。如余冠英《乐府诗选·前言》:“《乐府诗集》的‘杂曲’相当于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乐府杂题’,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为无可归类,就自成了一类。”[1]6王运熙《汉代的俗乐和民歌》:“汉代的杂曲歌辞,风格跟相和歌辞相同,因其歌辞未被中央乐府机构采习或年代久远等原因,后世不详它们属于何调,故被列为杂曲。”[2]238杨生枝《乐府诗史》:“杂曲是一种声调失传的杂牌曲子,后世不详它们属于何调,故均被列为杂曲。”[3]103三者均就杂曲歌辞部分特征而言。任半塘《教坊记笺订》:“(杂曲)其内容之广,固如郭氏所云,然历代‘杂曲’之名,多因与大乐或大曲对立而后有,至唐,尤为显著,初不因其内容复杂之故。”[4]59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前言》:“‘杂曲歌辞’是以‘新声’和‘杂用’为辑录标准的。”[5]10二者从音乐方面概括杂曲歌辞特征。任半塘之大乐所指为朝廷雅乐,杂曲歌辞所用音乐确实与之相对;王昆吾也说出了杂曲歌辞的两个主要特征。但从《乐府诗集》具体收录来看,“俗乐”和“新声”并不仅限于杂曲,相和、清商及舞曲等类别中亦有不同程度的“杂用”。所以,仅从所用音乐方面入手也难以见出杂曲歌辞的类目成因。要真正弄清这一问题,必须结合郭茂倩《杂曲歌辞序》中的理论界定与整个《乐府诗集》的收录情况来谈。
一、所用音乐与雅相对
不论是所用音乐还是歌辞内容,杂曲歌辞无一不是与雅相对。郭茂倩《杂曲歌辞序》首先从音乐与社会政治状况变化的关系入手,证明新声杂曲的出现,是王政衰歇、雅音废弃的结果:
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6]884
那些随着王政衰歇与雅音废弃而出现的繁音新声,就是杂曲歌辞所用的音乐。这些新声去圣日远,变化繁复,故能感人至深。同时,它们还常杂有胡音陋乐,其辞哀淫靡曼,让人沉溺,流而忘反,故被视为亡国之音:
呜呼,新声之感人如此,是以为世所贵。虽沿情之作,或出一时,而声辞浅迫,少复近古。故萧齐之将亡也,有《伴侣》;高齐之将亡也,有《无愁》;陈之将亡也,有《玉树后庭花》;隋之将亡也,有《泛龙舟》。所谓烦手淫声,争新怨衰,此又新声之弊也。[6]884-885
可见,就音乐属性而言,杂曲歌辞所用是一种与朝廷雅乐相对的新声俗乐。这一点从《近代曲辞序》中可以得到证明:
两汉声诗著于史者,唯《郊祀》《安世》之歌而已。班固以巡狩福应之事,不序郊庙,故余皆弗论。由是汉之杂曲,所见者少,而相和、铙歌,或至不可晓解。[7]1107
《郊祀》、《安世》之歌因是朝廷礼仪所用雅乐,故班固著于《汉书·礼乐志》。而那些“汉之杂曲”,则因为“不序郊庙”,是不雅之乐,“故余皆弗论”。正因为史家非雅不录的态度,才使得汉代杂曲“所见者少”。
与雅相对是郭茂倩对杂曲音乐的定性,而他之所以要用“杂”字来指称这些与雅相对的俗乐歌辞,则是因为就所言事物性质而言,古人具有雅杂相对的观念。如魏征《隋书·音乐志》中叙北齐乐时,先叙四郊、宗庙、三朝等雅乐,次叙鼓吹二十曲,最后叙杂乐,其“杂乐”所指即是那些与雅乐相对的俗乐:
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后主)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陨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8]331
史家为何要将这些音乐统称为“杂乐”呢?从此段话的后一部分可以看出,这些杂乐都是“繁手淫声”,使人主“耽爱无已”,而且它们一般都是新声,往往“音韵窈窕,极于哀思”,是不合于雅正的郑卫之音。由此可见史家把与雅相对的俗乐视作了杂乐。在音乐性质方面,“杂”是一个与“雅”相对的概念,杂乐也就是俗乐。这一点,《隋书·音乐志》中所载开皇九年(589)牛弘请正雅乐的上表可以证明:
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其后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9]351
这里的“梁家雅曲”与“陈氏正乐”,所指为梁陈二朝雅乐,是牛弘表请修缉以备有隋雅乐的。“后魏洛阳之曲”与“后周所用者”,则因为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故牛弘认为“皆不可用”,“请悉停之”。正因为它们是新造俗曲,又“杂有边裔之声”,不是纯正的音乐,所以无益甚至有损于朝廷雅乐,应当废弃。于此可见古人认为“杂”有混合之意,使原有东西不纯正,所以它会成为一个与纯正的“雅”相对的概念①
二、所依乐调不明所起
杂曲歌辞除了音乐上与雅相对之外,还往往乐调不明所起。这一点《杂曲歌辞序》中所言甚明:
自秦、汉已来,数千百岁,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干戈之后,丧乱之余,亡失既多,声辞不具,故有名存义亡,不见所起,而有古辞可考者,则若《伤歌行》……《枣下何纂纂》之类是也。复有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拟述,可以概见其义者,则若《出自蓟北门》……《悲哉》之类是也。又如汉阮瑀之《驾出北郭门》,曹植之《惟汉》……《桂之树》等行,《盘石》……《虾鳝》等篇,傅玄之《云中白子高》……《车遥遥篇》,陆机之《置酒》,谢惠连之《晨风》,鲍照之《鸿雁》,如此之类,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其辞具在,故不复备论。[6]885
郭茂倩这里说明了杂曲歌辞的另外一个特征:乐调不明所起,往往声辞不具。其产生原因是“干戈之后,丧乱之余”,故而“亡失既多”。那些“名存义亡,不见所起,而有古辞可考者”与“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拟述,可以概见其义者”,其乐调自然已不明所起。至于那些“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其辞具在者”,从其所举之例来看,郭茂倩是就这些曲调的命名特征来谈的。这些曲调的命名,或源自名篇名句,或源自首句诸字,多有以篇系题的特征②,还有一些则是据歌辞之意概括而来的诗题。也就是说,这些曲调的命名,均不是根据音乐得来,而是根据歌辞得来的。后人难以详知其所据究竟为何曲调,也就等于是“乐调不明所起”了。正因为杂曲歌辞具有这样一种“乐调不明所起”的特征,故而无法根据曲调来对其进行归类。
比较一下杂曲歌辞与近代曲辞,就会对杂曲歌辞乐调不明所起这一特征有个更直观的认识。郭茂倩明确说到:“近代曲者,亦杂曲也。”[7]1107可见二者有很大的相通之处。郭茂倩将二者分开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近代曲辞多数都有明确的创调本事,其乐调所起是很清楚的。杂曲乐调多不明所起,而近代曲辞则多有确切的乐调起源,为了进一步突出杂曲歌辞“乐调不明所起,往往声辞不具”这一特征,郭茂倩便将乐调起源清楚的隋唐杂曲另立一类③。
三、前人未作同类归录
认真考察一下《乐府诗集》所分十二类的具体收录即可看出,不论是所用音乐与雅相对还是所依乐调不明所起或者声辞不具,都不是杂曲歌辞独有的特征。相和与清商所用音乐亦均为俗乐,且其中亦有或声调不明所起,或不见其古辞的曲调。同时,《杂曲歌辞序》所提到的乐府曲调中,《伴侣》、《无愁》等属于清商,《惟汉》、《浮萍》等属于相和,而且《惟汉》、《浮萍》等曲调,郭茂倩将其与《驾出北郭门》、《盘石》、《驱车》、《种葛》等一起视作“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的杂曲作品。郭茂倩既然在序中将这些曲调作为例子来举,显然已将它们都看作了杂曲。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从序中所言来看,相和与清商也是杂曲。但在实际的歌辞收录上,郭茂倩却将相和与清商另外单独归类,而不是将它们也统统归入杂曲歌辞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理论界定与具体收录之间的矛盾呢?这还得从“杂”字一词的具体含义入手探讨。
在我国古代,“杂”字除了在观念上可以与雅相对,在编排上可以指声调不明所起的乐府曲调之外,同时还可以作为那些不成体系、被排除在诸多类别之外的其他作品的总称。比如谢朓集中有他与檀约、江奂、陶功曹、朱孝廉等人同时赋乐府题而作的乐府诗各一首,此五人之诗在谢集中总题为《同赋杂曲名》,曲名包括《阳春曲》、《渌水曲》、《采菱曲》、《秋竹曲》和《白雪曲》。又有谢朓与沈约、范云、王融、刘绘等人以鼓吹曲名《芳树》、《临高台》、《巫山高》、《有所思》等为题所赋的乐府诗数首,总题为《同沈右率诸公赋鼓吹曲名先成为次》[10]160。在《玉台新咏》中载有梁简文帝萧纲《和湘东王横吹曲三首》,为咏横吹曲《洛阳道》、《折杨柳》、《紫骝马》等曲调的歌诗,这说明齐梁时期文人之间同时以某一类乐府曲名为题赋诗成了一种风气。所以,谢集中的“杂曲”与“鼓吹曲”以及萧纲等人的“横吹曲”一样,都是时人对某一类乐曲的称呼。从时人有“同赋鼓吹曲名”、“同赋横吹曲名”等来看,许多乐类在当时已有特定的曲类名称,但与此同时,定然还有许多乐曲没有特定的乐属名称,所以会被总称为“杂曲”,故这里的“杂”就有“排除其他后所剩下的类别”这样的意思④。
将所有能自成体系的作品排除之后所剩作品总称为“杂”,在赵宋时人的著作中常可见到。如郑樵《通志·乐略》中“琴操五十七曲”除了九引、十二操外,尚还有“三十六杂曲名”,所指包括河间杂弄二十一章、蔡氏五弄、《双凤》、《杂鸾》等在内的三十六个琴曲曲名。郑樵称之为“三十六杂曲”,可见他(或者就是《琴操》作者蔡邕)把琴曲中除九引十二操之外的另外三十六个曲调总称作了杂曲。朱胜非《绀珠集》“诸集拾遗·琴歌操引”条下云:“古琴曲歌有五,如《鹿鸣》、《驺虞》之类;操有十二,《将归》、《拘幽》、《履霜》、《别鹄》之类;引有八,《列女》、《伯姬》、《霹雳》、《思归》、《走马》之类;又有杂曲二十一章,如《阳春弄》、《连珠弄》、《蠏行清》、《看客清》之类。”[11]539在琴曲中分出了古琴曲歌、操、引、杂曲等小类。这里的“杂曲”与郑樵《通志》中的一样,都是“杂琴曲”的意思,所指均为“排除其他后所剩下的曲调”,即指琴曲歌、操、引等类别之外的其他琴曲。
郭茂倩《杂曲歌辞序》中的理论界定与其杂曲歌辞这一类别的具体收录所出现的不一致,也是从“杂”字可以作为那些不成体系、被排除在某些类别之外的其他作品的总称这一角度出发的。一般来说,一个类别得以成立并区别于其他类别,往往需要有它自己的类特征和类标准,但杂曲歌辞中的作品不具有自己的类特征与类标准。《乐府诗集》所收十二类中,郊庙与燕射乃朝廷雅乐,且历代正史礼乐志或乐志对其发展衍变以及表演体制等均有确切记载,自然能够独自成类。鼓吹与横吹虽然所用音乐与歌辞也多非雅正,但其在历代发展衍变中体制渐尊,已近乎雅乐。同时,多数鼓吹与横吹曲在一些正史乐志以及《古今乐录》、《乐府解题》等典籍中已有记载,而这些典籍中没有记载的谢朓《齐随王鼓吹曲》十首与柳宗元《唐鼓吹铙歌》十二首,各自别集中已载,且均题作鼓吹,郭茂倩将其归入鼓吹曲中,其来有自。
至于相和歌辞,从郭茂倩在“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等各小类解题中所引《古今乐录》的记载来看,晋荀勖《荀氏录》、刘宋张永《元嘉正声技录》以及萧齐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等书中均已有对相和歌辞曲调类别、体制以及流传情况的确切记载,郭茂倩将其归为一类并以相和歌辞名之,完全根据这些乐类典籍而来。从相和歌辞的实际收录来看,郭茂倩也正是在这三种典籍记载的基础上,对各个曲调加以同题补录以及衍生曲调的补辑。由此看来,相和歌辞中各个曲调的归类,有案可稽。同样,清商曲辞中“吴声歌”、“神弦歌”、“西曲歌”、“江南弄”、“上云乐”、“梁雅歌”等的归类,郭茂倩也是根据《古今乐录》的记载,对各个曲调加以同题补录,并对隋唐时期具有吴声化特点的歌曲加以补辑。清商曲辞的归类,郭茂倩也所持有据。
舞曲中收有雅舞歌辞,同时还收有杂舞歌辞与散乐,显然也是雅杂相对的。舞曲歌辞的立类,是因为其中有些歌辞(雅舞)所依附的舞乐的创制、承传体系有其特殊性;而另一些作品(杂舞)则早在《宋书·乐志》和《南齐书·乐志》中已被称作了“舞歌”或“舞曲”,即沈约与萧子显均已发现了它们相对于其他乐府诗所具有的独特性,郭茂倩便在二书所收作品的基础上,加以时代的延展及同题作品的补辑,总名之为舞曲歌辞。琴曲的立类,自有它所用乐器单一的原因,同时恐怕也与琴曲之用多为作者自娱,而其他类别的乐府则以娱人为多有关。上文已经提到,近代曲辞产生时代较近,多数都有明确的创调本事,能够详尽言之,且其所用音乐与隋前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也具有自己独立的体系性。
杂歌谣辞本身都是未曾入乐的徒歌,但它们与入乐的乐府之间有着“源”与“流”的关系,将它们单独列出,很容易让人看清乐府诗的历史衍变。唐代兴盛的新乐府多乃其作者“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准备状态下的歌词,而且作家创作时大都将其明确标明为“乐府体”;它的产生和音乐没有直接关系,入乐歌唱是后来流传过程中的事,因此它与唐前的乐府有很大不同,发生了新变。郭茂倩将杂歌谣辞与新乐府辞置于最后,是因为二者相对于入乐乐府来说,一为源头,一为流亚。
从上面对《乐府诗集》主要类别立目原因的大致考察可以看出,在前人记载的基础上,郭茂倩对那些具有相同特征、能够自成体系的乐府诗,往往都单独归类;而对排除了这些单独归类的作品之后剩下的那些不成体系的作品,就将它们都归入了杂曲歌辞。如果比较一下《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与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乐府杂题》对具体曲目类别归属的不同,就更可以看出杂曲歌辞是在前人记载的基础上排除了那些能够自成体系的作品之后所剩下的作品。《乐府古题要解·乐府杂题》所录46个声调不明所起的曲目中,有《日重光》、《月重轮》、《上留田行》、《相逢狭路间行》等22曲,《乐府诗集》未归入杂曲歌辞,其原因就是因为《荀氏录》、《元嘉正声技录》、《大明三年宴乐技录》以及《古今乐录》、《乐府解题》等书中已有其类别归属的记载,郭茂倩借鉴了前人的分类,而不是仅因它们乐调不明所起便将其归入杂曲歌辞。所以,余冠英所谓“《乐府诗集》的‘杂曲’相当于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乐府杂题’,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为无可归类,就自成了一类”的说法,看似准确,其实并没有了解杂曲歌辞类目的真正成因。
四、小结
古人往往把雅乐之外那些非正统、非正宗的音乐都看作杂乐,同时对那些不明乐调所起、难以具体归类的乐府诗总称为“杂曲”。另外,对那些不成体系、尚未有人对其作为一个具体类别进行归录的作品,古人往往以“杂”称之。杂曲歌辞中的作品,所用音乐都是与雅乐相对的“杂乐”,且多数都“声调不明所起”。正基于此,郭茂倩要用“杂”字来为这一类作品命名。但是,《乐府诗集》所录杂曲歌辞却并不是所有那些与杂乐相配的歌辞。也就是说,虽然雅乐之外的大多数音乐都被郭茂倩视作了杂乐,但他并没有将这些杂乐的歌辞都当做杂曲歌辞,杂曲歌辞并不仅仅是“杂乐的配乐歌辞”。因为相和、清商、近代曲辞等类别中的作品都有其共同的特征,能够自成体系,而且前代典籍中一般也有其类别归属的记载,故而郭茂倩有案可稽,可以将它们各自成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杂曲歌辞并不是一个单纯因为音乐标准而立的乐府诗门类,它同时还参照前人著述,兼顾了作品自身的非体系性。概而论之,杂曲歌辞就是郭茂倩在对那些有着相同之处而又能自成体系的曲调排除之后所剩下的那一部分俗乐歌辞。
注释:
①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雅”的“杂”并没有像“俗”、“郑”等词一样被古人直接与“雅”并提,也就是说没有与“雅俗”、“雅郑”等同义的“雅杂”一词。但不能否定认古人有“雅”、“杂”相对的概念。“杂”字最初并不与“雅”相对,这种最终的相对意义,是从其他意义引申出来的。“杂”有混合之意,使原有东西不纯正,古人常将雅俗或雅郑相渗的东西称之为“杂”,所以“杂”会成为纯正之“雅”的相对的概念。如郭茂倩《舞曲歌辞序》:“自汉以后,乐舞浸盛。故有雅舞,有杂舞。”这里的“浸”即“渐渐”是个表示逐步进行的副词。乐舞渐盛后就分雅杂,主要还是因为这种盛是一种互渗之后的盛,故才有分开的必要。至于古人说“雅俗”或“雅郑”而不说“雅杂”,应当还有一个语言习惯问题。
②最初的以篇系题应当是歌辞编纂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诗人在作诗时直接来以篇系题。因为古时一个乐曲的曲调往往会有不少文人为其作辞,如果统统仅以曲调名名篇,有时会让人不明所指,所以,在编纂乐歌集子时才会先说曲调名,再用首句中几个关键字加上一个“篇”字共同命题,以具体说明某个题名所指为何篇。这一点类似于后世词作的命名方式,曲调名就相当于词牌名,乐府诗的篇名则相当于词作的篇名。
③当然,乐调起源清楚只是郭茂倩将隋唐杂曲称作近代曲的原因之一,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隋唐时期的社会背景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重新归于统一,整个社会主要的音乐系统都已不同于以前了。近代曲辞与杂曲歌辞之间所用音乐性质的不同也是郭茂倩将二者分开的主要原因之一。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认为近代曲辞“乃依据宋时犹有流传的唱本编成,其中所载,均为曲子辞”,孙尚勇《郭茂倩〈乐府诗集〉的编辑背景与刊刻校理》(吴相洲主编《乐府学》第5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认为杂曲歌辞主要对应于诗乐结合模式的“声依永”,近代曲辞则主要对应于“永依声”,可参看。
④鄢化志《中国古代杂体诗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引施蛰存语认为,《白居易集》中有“格诗”、“半格”、“杂体”等名目,这里的“杂体”相当于“其他体”。由此可见“杂”字具有“排除其他后所剩下的类别”之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