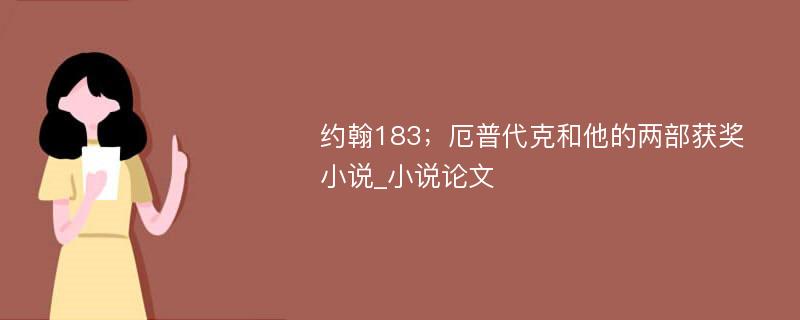
约翰#183;厄普代克和他的两部获奖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两部论文,小说论文,厄普代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当一部分评论者颇为赞叹约翰·厄普代克的非凡文学禀赋,称他为“天才”(prodigy)。 有一个事实可以印证此言不算妄赞:厄普代克在32岁时入选为美国国家艺术文学院院士,成为获取该殊荣的最年轻美国作家。大器早成,的确不枉“天才”之名,但厄普代克本人似乎更乐意为人了解他天才之外的一面。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的文学历程比作骑双轮车,唯有不停地蹬,才不致于从车上掉下来。〔1 〕照这番感受看,有位评论者将他比喻为“文学蜘蛛”的话倒更显得有会心默契之意。〔2〕不管是蹬车还是织网, 厄普代克显示出了一个优秀作家的成熟品质:勤奋、执着、不懈。他在自己40余年的文学生涯中殚精竭虑,笔耕不辍,至今为止已出版了16部长篇小说、10个短篇小说故事集、5 卷文章和评论、6部诗集、1个剧本和一本回忆录,〔3 〕成为当今文坛最高产、在诸多文学品种写作上造诣最为突出的作家之一。他所获得的众多文学奖项和荣誉确立了他作为本世纪重要作家的地位。
一
厄普代克1932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他生长于一个三代同堂之家,养家的是厄普代克的父亲,他在一家中学当了30年的数学教员。在厄普代克1964出版的小说《马人》(The Centaur)中, 主人公乔治·考德威尔身上就有这位父亲的影子。另外,这部小说中的部分故事素材也取自于这段早年的大家庭生活。
对厄普代克具有文学启蒙影响的是他的母亲。她喜欢阅读,而且自己也时常写作。在母亲的熏陶下,厄普代克的文学兴趣得到了鼓舞和培养。少年时的厄普代克曾梦想有朝一日当个职业漫画家,能在《纽约人》杂志里发表作品。在迷恋绘画的同时,他也开始尝试写一些诗歌和文章,但却屡遭退稿。对于这些最初的文学习作,厄普代克敝帚自珍地保留了下来。
1950年厄普代克入哈佛大学攻读文学,4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 哈佛对他日后的文学生涯有着重要影响。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在哈佛学到了许多。在当时的哈佛,曾经有一批诸如T.S.艾略特、罗伯特·弗罗斯特、狄兰·托马斯和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那样的文学名流亲临讲坛,这对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的确是弥足珍贵的经验。厄普代克曾在为《哈佛学报》(The Havard Gazette)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回忆过那段美妙的时光:
文学成为时髦,流行音乐听帕蒂·佩奇和佩里·科莫,电影看多丽斯·戴和约翰·韦恩,青年文化是那种发生在夏令营的事——如果要说什么地方的话。〔4〕
就在他从哈佛毕业的这一年,厄普代克在《纽约人》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一个题为“来自费城的朋友”的短篇故事。
1954年至1955年,厄普代克靠一笔奖学金在英国牛津大学拉斯金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在此期间,《纽约人》的资深编辑、著名作家E.B.怀特曾会过他一面,邀请他入盟《纽约人》的作家班子。厄普代克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携家返回美国,在纽约定居下来。从1955年至1957年,他主要为《纽约人》撰写专栏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写得机智优雅,显示了精湛圆熟的文字功夫。然而,他逐渐对纽约的社会和文学圈子感到失望,开始担心自己的文学事业就此顿滞不前,于是他辞去了杂志的工作,离开纽约,迁往马萨诸塞州一个僻静的小镇,在那里潜心从事创作,长达17年之久。对于当时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厄普代克来说,离开热闹的纽约文学界是个显得得失难测的举措,但他本人似乎相信这是明智之举,而他后来的发展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厄普代克在创作上最为致力也是最能代表他的文学成就的是他的长篇小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贫民院集市》(The Poorhouse Fair)出版于1959年,是个不俗的开端,得到了小说家兼评论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和其他一些评论家的好评。 厄普代克将小说中的故事时间背景前推到本世纪末,描写了一个州立贫民院里的老人与贫民院的管理者康纳之间的冲突。康纳在小说中被刻画成一种“未来人”,他认为现代的人类生活混乱无序,犹如“被困在一间封闭屋子里的疯子”。他相信代表理性的科学会给人类生活带来完美的新秩序。贫民院中的一位老人曾对康纳说过这样的话:
要是由你和象你这样的人来安排天上的星星,你们会把星星照着几何图形分布出来,或者把它们排出一个令人深思的句子。
康纳这一人物体现的是一种约束自由个性的机构化统治力量,小说开头讲到贫民院中的一位老人抱怨康纳在他们每个人的椅子上贴了姓名标签,这使人想起给监狱里的囚徒每人规定一个囚号的做法。而贫民院也确实象座监狱,老人们的生活在秩序的管治下变得死气沉沉。但他们也有反抗,那就是他们每年举办一次的集市。康纳从他那高高的办公室的窗子向下看到的集市是这样一幅场景:“一群群的人看上去象嗡嗡营营、没头没脑的虫子,彼此碰碰撞撞,胡乱而匆忙地在草地上过来过去。”集市热闹而混乱,有一种狂欢的气氛,但正是在这种气氛中老人们体验到了无拘无束的生命自由。狂欢唤发了他们抵抗衰老的生命本能。这部小说是对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的讽刺,指出建立在非人性的理念基础之上的完善秩序难免使人类付出牺牲人性自由的代价。厄普代克因这部小说获得了国家艺术院的罗森瑟尔奖。
真正使厄普代克文名鹊起的是他出版于1960年的第二部小说《兔子,跑》(Rabbit,Run), 这是他后来发展为“兔子系列”中的第一部。小说主人公哈里·安格斯特洛姆绰号为兔子,在中学时曾是位风头十足的蓝球明星。到了26岁时,已有了老婆孩子的兔子感到自己的生活黯然乏味,家庭日渐成为使他厌倦的责任,推销厨具的工作毫无成就感可言,冗烦单调的日常琐务在消耗他的精力,教会也给不了他精神安慰。总之, 他觉得身边周围的一切都在“挤压”他(小说中多次以“crowded”一词来描写他的感受)、窒息他的内心冲动和愿望。 当这种压抑令他不堪忍受时,他便开始了“跑”。然而,他并非一跑了之,而是跑了又回来,回来后又跑,如此反复数次。“跑”是这部小说中的核心隐喻,它体现的是兔子无法自己的内心冲突。这种冲突的实际内涵,笼而统之地讲,是个人精神需求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兔子的“跑”在小说中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行为。一方面,他逃离家庭,实际上是逃离社会要求于个人的正当责任;另一方面,他的“跑”也意味着精神方面的活跃性,含有一种探索的积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跑”也可以看作是要摆脱世俗社会里束缚个性及精神自由的种种规范和建制,包括婚姻、家庭的压力、机构化的宗教、问题百结的经济生活、中产阶级社会的道德价值和时尚文化的影响等。当然,兔子本人对其“跑”的深层心理动机不会具有如此的自觉意识。小说中的他不擅表达,多凭直觉来感受事物。对于来自内心深处的某种神秘召唤,他只能以含混不明的直觉性语言来表达:“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某个地方有某种东西要我找到它。”评论者格莱纳(Donald J.Greiner )通过对小说全部采用现在时叙述的分析,指出了兔子这一人物“感而不思”的特征。〔5 〕但正是这一特征才使兔子保持了兔子跳脱的活跃,而没有陷入“跑,还是不跑”的哈姆雷特式的行动麻痹症。
兔子的“跑”既令人同情又使人憎恶。从小说标题中的“跑”所含的祈使语气看,厄普代克的态度是偏于同情甚至鼓励的,但他又以同情的笔调表现了兔子不负责任的跑给家庭带来的痛苦。有些评论者因此而批评厄普代克在这一人物塑造上缺乏一致的情感和道德视角。〔6 〕这种批评实际上是要求作者对其笔下人物的行为作出公开的道德评判。厄普代克显然不想肩负说教家的责任,他认为文学中需要有“某种必要的模糊”,并且声称“我不希望我的小说比生活更清晰”。〔7 〕他不但不愿消除这种“必要的模糊”,而且还力图在作品中表达模糊。事实上,他的作品多带有一种“是的,但是”这样的调子。〔8 〕厄普代克的真正意图在于表现人物在冲突中的两难困境以及展现困境的复杂性。他在塑造兔子这一人物上的思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做一个人意味着要处于一种紧张情形,处于一种辩证的情形。一个完全适应环境的人根本就算不上是人——不过是穿上了衣服的动物罢了。〔9〕
兔子的困境反映了美国小镇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矛盾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兔子的“跑”实际上并非厄普代克所提倡的走出困境的办法,否则他就不会将兔子置于“跑—归—跑—归—跑”这样的钟摆模式中。如果把“跑”看作是力图摆脱困境的一种努力,那么这种努力实际上却是失败的:兔子屡屡跑开,但却没有方向和归宿。厄普代克的“模糊”里是否含有这样一种意味:所谓走出困境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终归徒劳的幻念,因为在困境中无论怎样选择都将导致代价的付出(这里具有悖论意味的是,在困境的前提下,这种代价的大小往往难以估算),从而消解了选择的功利意义?如此,兔子的“跑”便蒙上了一层存在主义的色彩。而事实上,厄普代克也确实受到过存在主义,尤其是基尔凯郭尔思想的影响。〔10〕若将这部小说置于其写作及出版的时间背景中看,兔子不安分的“跑”对于艾森豪威尔当政的50年代的平和保守社会则是颇具刺激性的,这也是小说在当时造成震动的一方面原因。
另一方面的原因与小说中的大胆性描写有关。美国《时代》周刊当时曾指责书中的性描写“过于露骨”,“趣味低俗”。这种责词似乎更象是书刊检查官的评语而非文学批评的反应。文学中对性的处理的确是个敏感问题,且争议由来已久,其复杂性已不适于在此文中进行深入探讨。笔者在此姑且提出几点有关的个人意见。文学既无法回避性,也就没必要讳莫如深。作品中关于性的描写程度并不能绝对地充当判断该作品是否为低级的色情文学的依据。从历史的态度看,读者对作品中的性描写程度的反应也受制于时代及观念的变化,因而文学批评的眼光在此问题上有必要含一些超脱的宽容。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性描写是否伤害了作品。就《兔子,跑》这部小说而言,厄普代克在其中的性描写是表现小说主题的重要内容。性,除了满足感官愉悦的需求外,还具有缓解紧张、消释焦虑的功能,兔子对性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属于后者的情况。对他来说,婚姻以外的性是一种安慰,或多或少地补偿了他的失败感。在他不擅思考而敏于直觉的头脑中,他的隐约混沌的精神追求——“它”(it),只有转诉于感官时才显得较为清晰。性体验中的某种流润感在他心理上唤起的是一种挣脱束缚的自由感。然而,性最终并不能将他引渡到精神之慰的境界,相反,它加深了他内心的负罪感、堕落感和失败感。性,强化了兔子的困境。厄普代克通过性描写展现了非情爱的性的空虚和无谓耗费,从而暗示性之于精神追求是一种荒唐的途径。这部小说使大多数评论者将厄普代克看作一位能够以开放态度处理性描写的严肃文学作家。在他后来出版的《夫妇》(Couples,1968 )和《兔子阔了》(Rabbit Is Rich,1981)中,性描写更是狂放无忌,但这些描写依然是他对美国中产阶级婚姻及性道德所作的细微观察。
《兔子,跑》的结尾是开放式的, 在此之后, 厄普代克几乎每隔10 年推出一部“兔子小说”, 它们分别是《兔子回来》(RabbitRedux,1971)、《兔子阔了》和《兔子安息》(Rabbit at Rest , 1990)。厄普代克在“兔子系列”中将主人公兔子的个人及其家庭生活置于包罗万象的社会辐射之下,以极为细腻写实的笔调描绘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图景,展示了灵与肉、个人与社会以及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婚姻、家庭、性道德、宗教、种族意识、时间、死亡、吸毒、科技发展、能源消耗等诸多问题。“兔子系列”的丰富容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自50年代以来的40年历史变迁。厄普代克本人曾说过:“在我的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说中有着比历史书更多的历史。”〔11〕厄普代克当然意不在贬低历史书,而是说明其作品更贴近生活本身,是对历史更为感性的表达。厄普代克的其它主要长篇小说有《农场的故事》(of the Farm, 1965)、《一个月的星期天》(A Month of Sundays,1975)、《政变》(The Coup, 1978)、《伊斯特威克的女巫们》(The Witches of Eastwick,1984 )和《巴西》(Brazil , 1994)。
大多数评论者肯定厄普代克是一位艺术上风格卓越的小说家,但其中有部分评论者同时又认为厄普代克的作品缺乏深刻的主题,思想内涵肤浅。一位评论者曾作过这样的评述:
他〔厄普代克〕常常以一种表面的东西令人目眩,使人想起七月四日的国庆焰花——有火花但没有热力,有光亮但不能照明;一种珍奇的娱乐,但本身并非珍奇之物。〔12〕
诚然,厄普代克的小说并非部部深刻之作,但他的一些最好的作品不但在风格上引人注目,而且在主题方面也显示了对人生及现实社会中重大问题的热切关注。下文将对他的两部获奖小说《马人》(国家图书奖)和《兔子阔了》(美国图书奖、普利策奖)所表现的主题作一番较为具体的评述。
二
《马人》首先是一部很有情感力度的作品,它最显在的主题是关于一位父亲对儿子的爱。厄普代克在小说中将这份父爱写得沉蕴而且富有悲剧的深度。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乔治·考德威尔,是小镇上的一名中学生物教员。过了中年之后,他身心疲惫,觉得自己在生活中碌碌无为。教书对他来说已不能成为精神寄托,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在他的学生身上不留痕迹,徒然消耗着他的生命。靠着微薄的薪水他要维持一个三代之家,靠他供养的有他的岳夫、妻子和正在上中学的儿子彼得,一家人的生活过得颇为窘迫。更糟的是,他因偶然撞见一位女同事头发零乱、衣衫不整地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的情形而面临失去工作的危险。比起《兔子,跑》中的兔子,考德威尔的失败感更为强烈,他把自己看作是行走的废物。他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和责任也比兔子要沉重得多,但他却没有象兔子那样逃避责任。从一个方面看,考德威尔与兔子形成了一种对比。事实上,厄普代克在构思《马人》时的确是想把这部小说写成《兔子,跑》的对照篇,也就是说他想通过这两部小说来体现对待生活的两种不同态度和方式。在1990年的一期《纽约时代书评》中厄普代克作过这样的解释:
一种是兔子的逃避方式——本能的、不假思索的、恐惧的……另一种是以马的方式对待生活,上套拉车,直到倒下为止。于是便有了《马人》。〔13〕
“兔子”之于安格斯特洛姆是一种隐喻,而在这部小说中,“马”的意象则实实在在地与主人公的现实形象合而为一了;考德威尔在小说中同时也是半马半人的客戎(Chiron)。
客戎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形象,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马,他博学多智, 是希腊年轻英雄们的导师。 据神话所载, 客戎在一群马人(Centaur)的一次混战中被一枝毒箭射中,箭伤使他痛苦难忍, 生不如死。但由于是神,他无法死去,于是他请求主神宙斯允许他以自己的死亡换取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解放。宙斯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将他变为一颗星星。厄普代克在《马人》这部小说里运用了客戎的神话故事,并将它融于现实生活的叙述之中。在小说第一章中,主人公是以考德威尔和客戎混为一体的重合形象出现的。一开始的情形是考德威尔在他的生物课上被学生的一枝用钢钎制成的箭射中脚踝。这段场景虽然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的,但情节本身实质上是客戎故事的重演。考德威尔所受的箭伤是一个暗喻,他所感受到的痛苦实际是他在生活中的痛苦。小说中对他的痛苦感受的描写暗示了这一点:
他希望私下独自体验他的痛苦,测出它的力度,估算它的持续时间,审视它的结构。〔14〕
伴随痛苦而来的是死亡冲动意识。象受伤的客戎一样,考德威尔也想摆脱痛苦的折磨,因而死亡的念头常常缠绕着他。当他给学生讲解宇宙的形成时,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带着一长串零的数字,随后对学生说“它们让我想起死亡”(第34页)。痛苦和死亡意识的心理暗示作用使考德威尔怀疑自己得了癌症。他的这种疑病症与其说是恐惧所致,不如说是他的死亡希求心理的折射。当他在X 光检查后得知自己并无绝症时,他待死的心理不仅没有释然反而更添了一层痛苦。痛苦在于他无法在想象的自然死亡中得到解脱,而只有继续活着履行他的责任,忍受他那失败生活的痛苦。
小说的结尾一句是“客戎接受了死亡”(第222页)。 这句话容易给人留下考德威尔最终自杀的印象。从表面看,这种推断似乎符合逻辑:既然客戎是自愿受死,考德威尔(同时也是客戎)的结局自然也应如此。然而,若是这样理解便取消了厄普代克在其刻意经营的模糊中所要表现的内涵深度。客戎求死的确是从根本上为了解除自身不堪忍受的痛苦,但客戎神话的意义却在于客戎的死换取了普罗米修斯的解放。考德威尔是客戎的意义也在于此。考德威尔若是自杀便意味着放弃责任,他的死不会有益于儿子彼得将来的发展。而小说告诉我们的是,彼得成年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儿时的艺术梦想,他终于从小镇到了曼哈顿,当上了二流的抽象派画家。小说结尾描写的这段情形发生于1947年,当时彼得才13岁,正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深以儿子为自豪的考德威尔不可能就此自杀而撇下彼得不管。从客戎神话意义上理解,考德威尔所接受的是一种象征性的死亡,它所意味的是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在第一章里描写的生物课情景中,考德威尔对学生说:
虽然每个细胞都具有潜在的永恒生命,但由于个体细胞自愿在一个有序的细胞群组织里担当某个专门功能,它于是进入了一个有损害性的环境,过度的劳损最终使它衰竭而死。它的死是一种牺牲,是为了整体的利益。(第37页)
这番话也可以说是考德威尔的生活写照。自我牺牲对于他来说意味着放弃解脱痛苦的愿望,继续象老马拉车那样承受生活的重负,“直至倒下为止”。彼得在回忆中说:“他(考德威尔)的上半身隐没不见,我最熟悉的是他的腿”(第201页)。小说将近结尾时写道, 客戎独自在大雪中走向抛锚的别克车。这里的描写象小说第一章一样,仍然是神话与现实交融在一起,人物是神话中的,但大雪和别克车却是现实中的景和物。这种叙述里既有事实描述又有隐喻。事实是考德威尔试图重新发动别克车,以便返回家中(很难将这一举动与自杀联系起来);隐喻在于别克车。这辆1936年的旧别克在小说中屡出故障,使考德威尔父子在回家的路上困顿了三天,它所象征的是考德威尔失败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走向别克车便意味着他接受自己的命运。自我牺牲使考德威尔成为悲剧性的英雄,
在他身上不无基督形象的影子(Chiron 与Christ在词形上的接近是否有这一暗示意味?)。
基督教思想背景下的人生观是小说故事层面下所要表现的深层主题。厄普代克在小说卷首引了一段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话:“天之于人是不可感知的创造,地之于人是可感知的创造,人便是天与地分界之间的造物。”从象征意义上说,客戎半人半马的双重属性代表了人性中的两极。人既是世俗的,受时空制约,但又想往和追求无限和永恒的境界,人类对神的崇拜即是这种向往和追求的体现。人创造了神话,试图使“可感知的”与“不可感知的”得以接壤。厄普代克通过将神话与现实的融合,表现了世俗生活背后的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人类堕落前”(prelapsarian)的天真无染的世界,是一个处处回响着隐喻的世界。然而,这一世界正在失落。有评论者指出,这部小说是一曲缅怀奥林匹斯众神时代的抒情挽歌。〔15〕奥林匹斯神庙在小说中成了小镇奥林杰,宙斯成了考德威尔所在中学的校长齐默曼。神性衰落与堕落有关。在小说中,“堕落”是通过三代考德威尔的职业变化来暗示的:从牧师(考德威尔的父亲)、教师(考德威尔)到艺术家(彼得),用彼得的话来说,是一种“经典性的堕落”(第201页)。 随着上帝受到怀疑,神学被理性的科学取代,而科学并不能最终使人的灵与肉归于统一。人失去了上帝,又无法在理性中找到生存的安慰,于是便求助于自由的想象力去重建精神家园。艺术象征着对永恒的关怀。少年时代的彼得是荷兰画家弗美尔(Vermeer)的崇拜者, 他一直梦想在美术馆亲眼一睹画家的原作,因为最令他神往的是画布上颜料的裂隙中凝固的时光。然而,成年后的艺术家彼得并没有在自己的抽象画艺术中得到精神超越的满足。在曼哈顿的一个小阁楼里,彼得面对躺在身边半睡半醒的黑人情人自言自语道:“我父亲献出自己的一生难道就是为了这一切吗?”(第201页)。彼得的问题在于他以艺术否定世俗世界, 他在艺术家的精神优越感中失落了他的少年时代。他的生活出现了断裂,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他无法找到生活的意义,怅惘和失落使他转向记忆去寻找慰藉,在追忆的过程中,他开始认识到父亲为他所作的自我牺牲。小说中发生的故事主要是通过彼得的回忆来展现的。作为艺术家,彼得试图在记忆中凝固1947年冬天他和父亲共同经历的3天时光。 在回忆中,他产生了负疚感,同时也发现了爱,而追忆于是便成了他的“赎罪”过程,从这里他开始找到了他个人生活的意义。在他追忆的眼光中,故乡奥林杰显出了奥林匹斯永恒的神性光芒。
成年彼得的处境是小说主题与其表现形式的逻辑联系所在,彼得在其艺术事业上的不尽成功使他必须痛苦地面对这一问题:父亲考德威尔为他所作的自我牺牲是否值得?寻求这一问题答案的途径是讲述父亲的故事。如何讲述是彼得的问题,而从根本上讲是小说家厄普代克的任务。厄普代克的手法是将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的混合叙述。有评论者认为这是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过时模仿,并无新意可言。〔16〕另有一种意见认为,客戎神话的运用在这部小说中虽然适于象征及叙事结构的目的,但却无助于凸现现实层面上的故事的意义。〔17〕在这两种意见中,第一种否认文学传统的可借鉴性,无视厄普代克的作品个性,近于苛责;第二种虽然认可厄普代克的技巧,但却失于忽略了彼得在小说中充当叙述者的同时作为故事人物的意义。正如客戎神话中不能缺少普罗米修斯,考德威尔的自我牺牲也有赖于受惠者彼得的存在。考德威尔的自我牺牲的意义是通过彼得的“精神净化的”(cathartic )叙述实现的。彼得的艺术家身份使他有自然的理由借助艺术表现的方式来进行他的叙述。因此,小说中神话与现实交融的叙述既喻示了考德威尔的复杂性格层面,也体现了彼得的复杂心理反应。〔18〕评论者罗伯特·戴特维勒(Robert Detweiler)颇具洞见地指出,厄普代克采用神话与现实的融合叙述,目的并不在于写一个寓言性的故事(allegory),而在于借助艺术家彼得的眼光以超现实主义和立体主义绘画的表现方式,通过变形和同时呈现人物及其行为的多面来扩大对现实的表述可能。 〔19〕正是在这种充满想象力和情感的叙述中, 自我牺牲和爱的主题得以凸现和强化。考德威尔变成了他在世俗生活中不可能成为的英雄。
多数评论者认为彼得是故事的主要叙述者,但仅此而止尚不足以说明全书的视角问题,因为全书9章中只有在第2、4、8三章中彼得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也许还可以算上以第一人称意识流叙述的第6章)。 有评论者进一步指出:“彼得与小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抒情诗人与他的诗的关系,诗中的每一个细节在最终意义上都来自诗人情感中的创造中心。”〔20〕持此论者认为小说在整体上借用了传统的“田园挽歌”(pastoral elegy)的形式,从而得以包容与之相谐的不同叙述样式:田园抒情诗、颂歌、忏悔、讣告、梦境、神话、铭文等。这种观点解释了小说中多种叙述视角混合的现象。厄普代克在1964年接受“国家图书奖”的讲话中说道:“这本书和它的主人公一样,也是马人。”〔21〕厄普代克的话里掩抑不住他的得意之情,他几乎是在提醒我们注意两点:其一是怪异的马人形象中所蕴含的非凡主题,其二是主题与表现形式所达到的珠联璧和的完美统一。读完这部小说后我们能说不是这样吗?
三
在《马人》出版的17年后,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中的第三部《兔子阔了》问世,再次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誉。比起前两部“兔子”小说,《兔子阔了》是一部更确切意义上的反映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小说,因为此时的兔子阔了,成了富裕中产阶级中的真正一员。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情感、道德意识随着他变阔的事实而实实在在地中产阶级化了。小说的标题既表明了兔子个人生活的变化,也暗示性地意味着这一变化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经济现实的必然关系。小说的主题便是在这种交织的关系中演绎出来的。
小说中的时间是1979年,正赶上世界石油危机的发生。车轮子上的美国在这场危机中受创严重,国内经济受到全面影响,物价上涨,美元贬值。然而,已过不惑之年的兔子却时来运转。首先,他继承了岳夫遗留下来的产业——斯普林杰车行,当上了车行的老板;其次,他因获权经销经济省油的日本丰田车而在这场能源危机中成了幸运的受惠者。钱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银行账户,他终于阔了起来。阔了之后的兔子过起了典型的富裕中产阶级的生活:他加入了“飞鹰俱乐部”,在那里打高尔夫球,和俱乐部的朋友们谈赚钱,谈如何逃税,谈性,谈报纸上的故事。他订阅《消费者报告》,视其为指导生活的《圣经》。钱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生活是甜蜜的,老人们曾这么说过,而当他年轻时他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说。”〔22〕他甚至开始对他和詹妮斯的婚姻感到满意,他“喜欢有一个能如此经常出现在俱乐部的妻子”(第35页)。此时的兔子已失去了昔日的“跑”的冲动。有了钱后,“他想要的东西少了。他原先一向认为是一种外向运动的自由却原来是这样一种内部的抽缩”(第89页)。如果说在《兔子,跑》中兔子对“它”的追求具有宗教性追求意味的话,那么“上帝”对现在的兔子来说“已经萎缩成一粒掉到汽车座位下的葡萄干那样大小”(第365页)。
美国对财富有着非同一般的迷恋情结,这种情结孕育出了“美国梦”。兔子的发财也许算得上是小有实现的“美国梦”(虽然他的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在不断增加,他在实际生活中的奢侈不过是由吃花生来换成吃腰果,保龄球为高尔夫球取代,飞往加勒比海海岛度假,以及在自己的车行里以“一地君王”自居的虚荣消费)。然而,他在70年代末品尝到的“美国梦”已经是一颗走了味的酸果。他“朦朦胧胧地认识到一个事实,变富即是遭受剥夺,变富即是变穷”(第351页)。 兔子的这一感悟颇有几分舍表入里的洞明,不失为对70年代末美国经济生活变化的一种深刻评判。但就兔子本人而言,他的思维并非具有自觉的理性批判意识,即使有所感悟,也只是发乎“朦胧”之中,这“朦胧”便是横隔于他的直觉与理性思维之间的一团混沌。正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他不明白它(钱)是怎么向他流来的, 也不明白它是怎么漏走的”(第129页)。显然,他所关心的是如何保护他既得的财富, 使它不致于莫名其妙地漏走。
对于兔子的财富的威胁主要来自他的儿子奈尔逊,在小说中奈尔逊被刻画成一个败家子。他大学没毕业突然跑回家,其原因是他使大学里的女友普露怀了孕。为躲开自己惹下的麻烦,他一拔腿溜回家,而且还带回另一个女友,以遮掩真相。奈尔逊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使人想起了年轻时的兔子,但无论怎样看,奈尔逊比兔子糟糕得多。当年的兔子为自己逃避责任的行为尚有良心不安的愧疚,而奈尔逊则无动于衷。他最终与普露结婚也只是由于情势所迫。在对待普露的行为上,他表现出了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冷漠甚至残忍。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奈尔逊竟然故意对已有7个月身孕的普露使绊子,致使她摔下楼梯, 受伤而住进了医院。后来,在普露临产之际,他又一次撇下她,逃之夭夭。在厄普代克笔下,奈尔逊属于美国70年代“唯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 )中的年轻人。他没有信仰,把宗教称作“玩艺儿”。他极端自私,放浪形骸,却认为所有的人都跟他过不去。他撞坏了兔子的车后满不在乎,并且对兔子说“钱是狗屎”(第157页)。 令兔子最难以容忍的是奈尔逊想插手于他的车行生意。在兔子眼里,奈尔逊是个十足的“祸患”(第169页)。由于他的返回,兔子不得不为汽车修理、 婚礼和普露的住院治疗大破其财。
兔子与奈尔逊的冲突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兔子眼中的奈尔逊代表着堕落和毫无希望的年轻一代,他们没有理想,无所事事,在毒品中寻求刺激和快乐。令兔子不安的是象奈尔逊这样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多,用他心里的话说:
世界一天天在走向完蛋,可这些浑头浑脑,不知好歹的后生却没完没了地冒出来,就象好戏才开场似的。(第81页)
在兔子的不安中也不无几分困惑;面对奈尔逊这样的年轻人,他不禁自问“他在这个年纪时也这样吗”(第35页)?兔子在这一自问中更多的是良好的自我感觉,并不会真正反省、检讨自己的过去。如果说他的困惑是真切的,那么这困惑实在是源于他对自己过去的忘却。年轻时的兔子也曾撇下妻子,逃离家庭,和妓女露丝厮混,在她怀孕后又抛下了她。因而,兔子对奈尔逊的道德上的指责由于缺乏自省而显得五十步笑百步。
奈尔逊的所作所为的确令人憎恶,但在他和兔子的冲突中,他的某些反应不无另一角度下的某种情理。他鄙夷兔子的守财奴行为,反感兔子将汽车看成一种神奇之物。他对兔子剥夺自己在车行的工作机会愤愤不平,因为兔子自己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兔子的解释之一是,奈尔逊若得到工作便意味着抢走车行里其他工人的饭碗,使他们失去养家的保证。然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理由对于奈尔逊并不十分公平,因为奈尔逊也将面临同样的处境。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奈尔逊对兔子的某些看法使我们认识到,兔子已失去了昔日的反叛个性,成了现存体制的维护者。〔23〕奈尔逊曾经对普露这样说起兔子:
老爹不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一副差劲的样子了。过去的他有一点让你钦佩,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心里有一种荒唐而模糊的信心,是他当蓝球明星那会儿或是从小到大受人宠之类的经历留下来的,凭着那种信心他有时能对别人说‘去你妈的吧’。可那股子劲头现在没了。(第29页)
小说的叙述在奈尔逊的婚礼之后有一部分转入了奈尔逊的视角,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厄普代克邀引我们从这一角度看兔子的用意。
通过状写兔子与奈尔逊的冲突,厄普代克向我们展现了两代人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并且对两种价值观都作出了不同程度上的批判。但我们从小说中不难感觉到,厄普代克在兔子身上明显地寄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有评论者认为,从人物塑造的角度看,奈尔逊的形象在小说中是个失败,“他显得在更大程度上是根据厄普代克对兔子的忠诚设计出来的,而非根据兔子的基因或心愿。”〔24〕这话不无道理,但厄普代克本无意将这部小说写成一部关于兔子和小兔子的小说,他的笔仍使我们的眼光聚焦在兔子身上。比起奈尔逊来,兔子的价值观中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时间变迁因素,他毕竟是从过去“跑”到了现在。
兔子在开始享受“甜蜜”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衰老。47岁的他已全然失去年轻时蓝球明星的矫健体态,变得大腹便便,并且已显出谢顶之势。小说开头第一句“油快没了”既是指石油危机也是对兔子日渐衰竭的精力和体力的一种暗喻。将近半百之岁的兔子已无法回避这一暗喻所预示的现实:他正在走向生命的尽头。在小说中,他的思绪常常为死亡之念缠绕。他居住的小镇布鲁厄在他的感觉中已是一座“幽灵之镇”:
死去的人,老天呀,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多。他们朝上面看着你,恳请你加入到他们中间去,并对你保证说他们那儿并不坏,他们那儿很平静。……报纸上的讣告栏每天都在向你显示新的收获,这收获不停地在丰富,永远也没个完。过去的教师、顾客、象他自己一样的当地有脸面的人物,他们的脸稍稍一闪便暗了下去。(第7页)
不难看出,兔子对死亡的想象带有自我安慰的色彩,但正是这种自我安慰暴露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心理。这一恐惧使他对于死亡产生了一种提前的体验:“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死去之前就已消失于我们身后”(第43页)。从这个角度想,我们在兔子对奈尔逊大肆浪费的痛恨中可以看到更深一层的心理作用。也就是说,奈尔逊的耗费行为以暗示性的方式刺激着兔子的死亡联想。相应地讲,兔子的吝啬行为于是也就具有抵抗死亡意识的心理象征意义。
如果说财富对于兔子意味着抗拒死亡恐惧的力量,那么在小说中它是通过与性的结合体现出来的。性能力在一定意义上是生命力的某种指标。年轻时候的兔子对性有着强烈的兴趣,那时候,性给他带来的是一种类似于他在蓝球场上体验到的快感,是旺盛的生命力的挥洒。他的“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利比多作用下的行为。而现在,“生命已过了一多半”的兔子却“越来越只情愿去想想它,而让年轻人去玩这种勾当了。……他试图想象能使他亢奋起来的情形,但他几乎想象不出什么来了”(第129页)。 虽然兔子在小说中将他性兴趣的衰减归罪于金钱带来的满足,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形却恰恰相反。在与詹妮斯的一次做爱中,他感到了一回少有的坚挺,以致于自鸣得意起来:“谁说他快没油了?”(第50页)在这段情形的描写中,厄普代克暗示了与兔子性欲高涨起来有关的两个因素:一是兔子做爱前正在读《消费者报告》,二是当他性欲赳昂之时他头脑中突然浮现出一辆精巧的丰田车。作为财富的相关意象,《消费者报告》和丰田车以微妙的方式刺激了兔子的性能力。
在另一个场景中,厄普代克以仿讽的手法描写了兔子与詹妮斯在克鲁格金币的刺激下如火如荼的交欢。正如在某些电影和小说中那些令人眼熟的庸俗浪漫场景中常常出现的香槟酒那样,金币在这里充当了调情的道具。兔子躺在床上,将两枚金币分别搁在自己的双眼上,随后又将它们拿开,这时小说这样写道:“他象死人复生,两眼炯炯有神”(第201页)。金币在这里显示出一种魔力, 给“快没油”的兔子“充了电”。在这一场景中,财富和性最直接地被结合在一起。如果说财富激发的性力给兔子带来些安慰的话,厄普代克的最终启示则在于揭示这种安慰的虚妄。性,在厄普代克笔下象一头双面怪兽,他让兔子先是看到了代表生命力的一面,之后又让他看到了另一面,在这一面上兔子看到的是空洞和死亡。在加勒比海海岛度假期间,兔子和他的俱乐部朋友们玩了一场“换妻”游戏。他在与朋友的妻子西尔玛的变态苟合中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洞感:“没有感觉:一个虚空,一个纯粹的黑匣子,一个完完全全空无的盒子”(第391页)。显然, 这里的“虚空”以及象征棺材的“黑匣子”都是死亡的意象。至此,厄普代克将财富、性和死亡的关系以戏剧性的方式演绎了出来,让我们从中透视到中产阶级生活本质中的空虚和人生危机感。
兔子阔了,但精神上却变得贫困了。一个深刻而辩证的矛盾。厄普代克笔下的兔子的确“快没油了”,但厄普代克却仍显得马力十足。
注释:
〔1〕Tom Verde,Twentieth- Century Writers( 1950 —1990)(Facts on File,Inc.,1996),p.161.
〔2 〕参见Jane Barnes 所撰题为“John Updike:A LiterarySpider”一文,刊于Virg inia Quarterly Review 57,no.1(Winter,1981)。
〔3〕据Tom Verde,第147页。
〔4〕Tom Verde,pp.150—151.
〔5〕Donald J.Greiner,John Updike's Novels( Athens,Ohio:Ohio University Press,1984),p.49.
〔6〕参见Donald J.Greiner,第51页上的讨论。
〔7〕转引自Donald J.Greiner,第48页。
〔8〕Harold Bloom, ed,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Vol.7 (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8),p.4005.
〔9〕转引自Dilvo I.Ristoff, U pdike's America: Thepresenc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H istory in John U pd ike'sRabbit Triology (New York:Peter Lang,1988),p.4。
〔10〕见Judie Newman,Macmillan Modern Novelists;
JohnU pd i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1988),p.80.
〔11〕转引自Greiner,第50页。
〔12〕引自Philip Corwin,"Oh,What the Hex" , 见HaroldBloom,第4010页。
〔13〕转引自Tom Verde,第154页。
〔14〕John U pdike,The Centaur (Fawcett Publications,Inc.,1962),p.9.后面出自该作品的引文均据此版本, 并注页码于文内。
〔15〕参见James M.Mellard,"The Novel as Lyric
Elegy:The Mode of U pdike's The Centaur"。见Harold Bloom 所编ModernCritical Views:John U pdike ( New York: Chealsea HousePublishers,1987),第101页。
〔16〕参见John W. Aldridge 所撰“The Private Vice ofJohn Updike”一文。见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Vol.7第4009页。
〔17〕参见Tony Tanner所撰“A Compromised Environment”一文。见Modern Critical Viows:John U pdike第51页。
〔18〕参见Donald J.Greiner,第104页。
〔19〕Robert Detweiler, John
Updike ( Boston:TwaynePublishers,1984),p.64.
〔20〕James M.Mellard,p.97.
〔21〕转引自Greiner,第105页。
〔22〕John U pdike,Rabbit Is Rich, (New York:FawcettCrest,1981),p.4.
〔23〕Dilvo I.Ristoff,p.126.
〔24〕Eliot Fremont-Smith语,转引自Greiner,第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