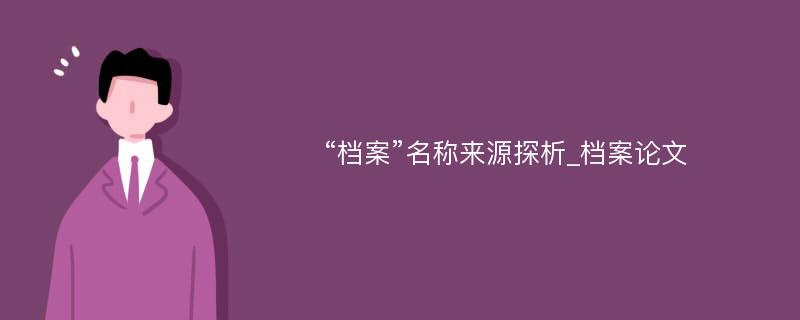
“档案”名义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义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档案”一词是怎么来的?这是自档案学产生以来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数十年来经多方研究,包括史学界的研究而至今未得圆满解决的一个难题。它不仅是一个词的来源问题,而且涉及到“档案”的本义及档案工作的范围和任务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对此问题的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近年来,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有关“档案”词源的论文,其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坚持满族人“档子”说,认为“档案”是“满汉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似有将其观点理论化的趋势。而另一派作者不安于清朝才有“档案”一词的现状,溯源而上,追溯到元代、宋代,直至周代的《周礼》。学术界为此时而掀起轩然大波,时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笔者在此对“档案”一词来源的探讨作点评论,并抛砖引玉,谈点自己的发现和思考,敬请行家指教。
一、关于满人“档子”说的纰漏
现在的辞书,凡是有关“档子”、“档案”的解释,都是以《柳边纪略》为依据的。档案史方面的著作也多从其说。《柳边纪略》是康熙年间的文人杨宾去东北地区看望被流放的父亲,综述所见所闻写成的一部书。其中说:
“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书于纸者,亦呼曰牌子、档子矣。犹之中土文字,汉以前载在竹简,故曰简,以韦编贯,故曰编。今之人既书于纸为卷为部,而犹呼之为编为简也。”〔1〕
杨宾的话非臆测之词,既有实际观察根据,又有文献可依。杨宾在山海关的南衙、北衙见过这些“记档”、“销档”的“档案”。至于文献记载,在此之前,汪琬的《钝翁类稿》已经问世,杨宾在他的书中曾引用过。我们可以在《钝翁类稿》中看到有关“档子”的记载:
“本朝用薄板五六寸,作满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数片,辄用牛皮贯之,谓之档子。”〔2〕
汪琬是清顺治年间进士,任过户部主事等官,“琬力学,於书无所不窥,而尤邃於六经。”〔3〕所以他的话是可信的。
本世纪三十年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学者们在清理内阁大库档案时也收集到这种称作“档子”的木牌。方苏生在《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叙录》中说:
“满文木牌为文献馆最近所发现,其字体圈点尚不完备,削木片为之。长者盈尺,短者数寸,宽狭均为寸许。一端作直角,有孔,四五片为组,贯以麻索。制甚粗,不加涂饰,与后来引见用之绿头签异。自其人名地名观之,知为崇德元年物。案杨宾《柳边纪略》云:‘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书于纸者,亦呼曰牌子、档子矣。’今此项木牌,内容均似军前捷报,正文而外,多别注‘前锋’,或‘固山达尔汉额附固山达赖’等满文,似记载报告者名,当即‘往来传递’之牌子,而贯以麻索,亦可称为档子。又案顺治二年有令‘各衙门奏事俱缮本章,不许复用木签’(见王先谦《东华录》。则前乎此奏事亦得用木签,惜其遗制无存,而此木牌二十余枚,发见于今日,乃弥足珍也。”〔4〕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这些用皮条贯起来的木牌为什么称作“档子”呢?“挂壁若档”是像档的意思,但这个“档”是什么?
史学界和档案界学者是这样解释的:
(一)徐中舒先生认为“档子”是汉语“榜子”的转音
徐先生是史学界知名学者,曾整理过内阁大库的档案。他认为:
“官署案卷,清初称为档子,内阁有满汉档子房。(下引《柳边纪略》,同前,此略)边外用木简书字,由来已久,这当因为边外得纸不易,所以这种旧俗一直流传到清初。《东华录》顺治二年内有一段记载:‘令各衙门奏事俱缮本章,不许复用木签,从御史高去奢请也。’这是清人初入关时事。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推知入关以前的奏事,明明是许用木签的,奏事用木,所以档子从木。汉语称木签为牌子、榜子,档子疑是从汉语榜子的转音,后来与案连缀并称为档案。《柳边纪略》说贯皮条挂壁若档,又为后起的解释了。”〔5 〕徐中舒先生认为“清初奏事用木,所以档子从木”,这个分析是不合适的。“档”在《康熙字典》中释为“横木框档”,所以从木,是指一种装具从木,而非指木制的牌子从木。至于读音,认为汉人称木牌为“榜子”,满人将“榜子”转读为“档子”,这是一种猜测,它显然与杨宾原书的意思不相符,徐先生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所以徐说难以服人。
(二)近人李荣忠同志认为“挂壁若档”是满人的联想。《档案学研究》杂志在1994年第3 期发表了李荣忠同志关于“档案”词源的探讨性文章,对“档子”作了大胆的论证,为了让读者较全面的了解作者的观点,在此要多摘录一些。
“‘档’、‘档子’、‘挡子’原为汉语词。‘档’,带格的架子或橱,起支撑固定作用的木条或细棍。‘档子’,方言量词,用于事件或成组的曲艺杂技等。‘挡子’,遮挡用的东西。在清之前,前面两个词都没有档案之义。后一个词至今也无档案之义。在满汉民族交往中,满语吸收了这三个词,并进行了加工。”
“在词义方面,满语将汉语词‘档’、‘档子’、‘挡子’合为一个词‘档子’(dangse)。满族的房屋窗子是用几条木板遮挡的,这种窗挡子汉语是‘挡子’而不是‘档子’,但满语则为‘档子’。”
作者以这个演变为基础,进一步推断说:
“其实,满人将数片木牌用皮条穿起来挂在墙壁上,在他们的眼中这些木牌就像‘档子’。这个‘档子’在汉语里应改为‘挡子’。挂在壁上的数片木牌象不象遮挡物挡子呢?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满人吸收汉语词‘档’、‘挡’不分,挡子就是档子,前面提到的窗挡子就是一例。正是这个原因,只有满人才会产生出‘挂壁若档’的联想,汉人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这种联想的。”〔6〕
李文的大意是,满人有“窗档子”的习惯读音,所以才视那些挂在墙上的木牌“若档”。而汉人有“窗挡子”的读音,所以不会联想出“若档”的。李文进一步论证满族之“档”与汉族之‘案’的联缀,得出“档案”一词是满汉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的结论。
我们且不说汉人看到墙上挂的木牌是如何联想的,这在下文再议,只就满族人称窗户上的木条为“窗档”,汉人则称“窗挡”这个微妙的差别来说,它是不存在的。汉人也称“窗档”,而不是“窗挡”,仅举一个例子即可证明。《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载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自在州向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呈报王时恩状告王时太诬陷兄弟五人殴死亲母亲的原词和审判书》,其中问得案情说:
“至万历十七年六月十七日,王氏偶得痢疾,又兼心疼,昼夜疼痛难忍。当有王官母舅王彦海看守三日,不在状舅母赵氏看守六日。延至本月二十六日,王彦海偶回伊家,比王时恩等兄弟五人因母病久无事,各去看守成熟谷禾,止赵氏同王时恩不在状妻张氏看守。至本日半夜,赵氏、张氏各因看久睡熟,王氏委一时犯疼难忍,密用绵线带在窗档上自缢身死。彼时王时恩、王时成、王时惠、王时良、王时立五人,各不合不行在傍侍奉看守;后闻缢死,即至伊家,夹亲解落,买棺盛殓殡葬讫,并无别情。”〔7〕
此件档案是被告康计民的一段供词,称王氏“用绵线带在窗档上自缢身死”,此证汉人称“窗档”而非“窗挡”。李荣忠同志将“窗档”为满族人独有称谓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由此可知,李文的进一步推论就难以成立了。
上述只有满人才称“档子”,只有清朝才称“档案”的观点在史学界和档案学界是有很久很深影响的。坚守这种观点,并且将其论证为“满汉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可能会限制人们的思路,缩小人们的视野。如果进一步说:“凡是明代和明代以前的官府文件和私家著作里出现‘档案’一词,其形成年代和内容真伪都是值得怀疑的,都是需要认真考订的。”这未免有点保守和固执了。如果真的发现明代或明代以前的官府文件和私家著作里出现了“档案”或近似“档案”的词汇,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吗?如果材料是可靠的,就不怕持不同观点的同志去怀疑、去考订。研究和探索正在进行,过早的下结论是不必要的。
二、关于“档案”溯源者受挫的教训
中国档案工作有悠久的历史,“档案”一词怎么到了清代才出现呢?它的来源应该更早些,这是许多档案工作者、档案学研究者的共同心声。早在1984年,郭树银、杨继波同志就在《“档案”一词考略》一文中指出:“‘档’、‘档子’、‘档案’等词来自汉语,……在明代或更早一点就在汉语中流行。”并且说:“现存明代档案很少,我们目前还未找到原始记载,又未看到史籍提及。故目前未敢妄下断语,确切时间还望读者诸君查考。〔8〕于是, 在明和明以前各代寻找“档案”词源的研究者潜心考索,时有发现,其勇气令人感动。但由于种种原因,却连连受挫,其教训也是应该总结的。
(一)元曲有“档案”说的败北
1986年7月, 张仲强同志在《档案工作》杂志上发表了《“档案”一词不始于清》一文,提出“档案”一词的出现最晚亦始于元。根据是元曲《赵元好酒遇上皇》中有“便肖曹律令不曾习,有档案分令史支持”一句。据此推论说:“‘档案’一词出现于元杂剧,说明其作为专用名词不仅广泛使用于其时之公务活动,而且由于使用频率之高度化而下移于民间,成为大众所熟知的词汇了。”这个发现令人鼓舞。但好景不长,和宝荣先生从版本考订上否定了这个发现。元刻本原是“有当案分令史支持”是“当案”而不是“档案”,“当案”是“当职”之意,没有“档案”的意思。民国时期王季烈校本误“当案”为“档案”〔9 〕。如此,这个令人振奋的发现被否定了。笔者有点遗虑,就此去信请教过中山大学著名元曲专家王季思先生,他也认为“当案”为是。此后,元曲“档案”说遂寝。
(二)《周礼注疏》“副当”说的兴起及其纰漏
1994年底,《档案学研究》第4 期发表了侯传学同志的《档案名义考析》一文,提出《周礼注疏》中有“写副当以授六官”一句,认为此句中之“当”字是文书的总称,经过一定过渡,变为后来“档案”之“档”。
此说甚为惊人。人所共知,《说文解字》中没有“档”字,侯传学同志却抓住《周礼注疏》中的“当”字,一下子将“档案”一词的起源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周代,起码可以追溯到《周礼注疏》的作者郑玄所处的东汉时代,着实令人高兴。此说得到查启森等同志的支持,新编教材《中国档案事业史》亦采其说,并有所发展。说:
“‘当’即指档案,我国古代文书档案之称谓,有称不从档之‘当’,《周礼注疏》郑玄注‘贰之者,写副当以授六官’,此处‘副当’即指档案副本。故守当官、勾当官是典守档案之人员。”〔10〕
但是此说甚险。1996年,《档案学研究》第2期发表了王荣声、 王玉声同志合写的文章:《“当”非“当子”、“档子”辨》,指出:“释‘当’为文书总称是作者对原文的误读所致。《周礼注疏》中凡提到写副本的时候,有时用‘写副’(如上文),有时用‘副写’……所谓‘写副当以授六官’即‘副写当以授六官’,‘副写藏之’即‘写副藏之’。‘当’在这里是副词,非名词,‘副当’不能连读,应与下文连读作‘当以授六官’”“‘当’作为副词用,犹‘将’也。”“‘当’在古代汉语中使用虽然复杂,但从以上所举各例及笔者所见史籍中,看不出‘当’可释作我国古代文书通称的任何迹象。”
虽然王荣声、王玉声同志的文章还有可商榷之处,但“副当”之“当”不是“档案”之“档”的前身是很明显的。至于说宋代的“勾当官”、“守当官”的官称表明是典守档案的官员,此说更是不妥。“勾当”、“守当”是干办、主管某一方面事务的意思,宋有“勾当御药院”、“勾当诸司粮料院”等官,他们与档案没什么关系。宋代档案工作的官员有专称,曰“架阁官”,下文还要谈此问题。
以上两种对前代史料的探索和提出问题的勇气是可嘉的。但都立足不稳,经不起推敲。究其原因,皆在“逐名求源”,对与“档案”近似的名称,如“当”、“勾当”、“守当”、“当案”等特别敏感,而没有从“名源于义”这一根本性问题上考虑。并且,在档案史研究中,还有一种流传甚久、甚广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书和档案是不分的,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是不分的,因此文书之名也可能演变成档案之名,如果古人称文书为“当”,那么就会演变成档案之“档”。此观点使“档案”探源带上一种盲目性,失败是不足为怪的。
三、宋代“架阁文字”即为“档案”
“档案”一词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古人为什么置“中”、“簿”、“文书”“案牍”等词不用,而改用“档案”或用一个“档”字与其它字组合成含有“档案”之义的词?究其原因是档案工作的特殊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使人们对“档案”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将文件生命过程中的“档案”阶段明显地与文件阶段区别开来,才可能产生“档案”或与“档案”涵义相近的词汇。
据笔者对历史的考察,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分工中的专业工作,始于文化已相当发达的宋代,宋代出现的“架阁文字”就是“档案”同义词。
宋代建立了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机器,文件数量急骤增加,人称“公人世界”、“公文世界”。由于长年积累,管理不善,往往出现案牍丢失,或急于查找而“累月检之不获”的现象,一些待审的案件也长期拖而不决。这种状况使统治者认识到档案工作的重要性,逐渐设置档案工作的专门机构,从中央机关到地方官府建立了规模不等的“架阁库”,还在景德二年(1005年)建立了具有中央档案馆性质的金耀门文书库。南宋时期又设立了六部架阁库和三省枢密院架阁库,六部架阁库已有库房110间,规模相当可观。 并且从北宋徽宗时期就开始设置档案工作的专职官员——“管勾六曹架阁文字”,南宋时改称“主管吏部架阁文字”、“主管户部架阁文字”、“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统称之为架阁官。这些官员的工作对象就是“架阁文字”,也就是档案。
“架阁”一词,在宋以前还未发现,宋人自己也说得明白:“六部架阁,古无之,元丰有六曹架阁库。”“架阁”是人们对木制档案装具的总称,“架”为书架、册架,是分为数层的横木框,上放木板,可保存书籍或文件。“阁”是什么?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说:“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此处“几”为几案,“阁”便是柜子。汉代的柜子很矮,这与人们席地而坐有关。唐宋时期,家俱增高,出现了真正的桌椅,柜子也变成立柜、版柜了。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阁者,板格以庋膳羞者,正是今之立馈。今吴人谓之厨者,原起于此,以其贮食物也,故谓之厨。”宋太宗曾在至道元年六月下令各州县的簿书“于长吏厅侧置库,作版柜,藏贮封锁”。宋人洪迈在《夷坚丙志》之《杨抽马》中写道:“四川制置司求三十年案牍不得,以告杨,杨曰,在某室某柜第几沓中。如言而获。”这些都说明“阁”就是立柜、版柜,里面有数层木格,可以存放文件、簿册等。故可将架阁里面存放的文字材料称作“架阁文字”或“架阁文书”。
宋人对事物的观察已很仔细,就文书而言,分为“现行文书”、“无行文书”、“应架阁文书”、“架阁文书”、“重害文书”、“非重害文书”、“长留文书”、“非长留文书”八种。这“架阁文书”是保存在柜架上以备查考的文书,与正在运行中的文书有明显的区别,对其保管、移交、鉴定,销毁、借阅等工作均有一定制度,在南宋法典《庆元条法事类》中有二十三条相当完备的条文,虽然列在“文书”门下,但专列一目,称作“架阁”。这也是宋代档案工作成熟的一个标志。
“架阁文字”与今天所说的“档案文件”是何等相似。今人所编的《辞海》解释“档”的涵义是“存放公文案卷的橱架,因亦即指案卷”。宋人所说的“架阁文字”完全可以说是“档案”的同义词。
宋代有架阁库,金、元代有架阁库,明代亦普遍设立架阁库,但是,宋人所说的“架阁文字”在金、元、明甚少见到,这个概念什么时间变成“档”或“档册”,进而与“案卷”联缀为“档案”,是古人留下的一个谜。此谜的解开并不是没有希望的,笔者近期查到明初出现的“文档”二字,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
四、明初“文档”考
笔者为研究“档案”一词的起源,查阅了一些元明文献,从辽宁省档案馆与辽宁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编的《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一书所载的《明实录》稿本中,发现明初已出现了“文档”的概念,现将《明实录》稿本中的一段记载抄录于下,以飨读者。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
据刑部近来因户部文档不明,着本部办理拿问该属官吏等情具奏,帝降旨:匡正迟违,非隐匿粮饷则勿问。钦此。”
此条史料甚为珍贵,在分析其内容之前,我们首先要考察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明实录》稿本是否可靠。此事牵涉的问题甚多,不免要多说几句。
《明实录》中的《太祖实录》曾三次修纂,这是史学界熟知的,据《明史·艺文志》载:
“《明太祖实录》二五七卷,建文元年董伦等修。永乐元年解缙等重修。九年胡广等复修。起元至正辛卯,迄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首尾四十八年。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
为什么要重修、复修?这里不去细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明成祖为了自己的地位而去修改历史记录。为了不让后人看到原本,二修时焚初修本,至三修时又毁二修本。所以今人见不到前两种本子。
不仅原本见不到,每次所修的底稿本也是难以见到的。按照修实录的惯例,每朝实录纂修完成后,誊录正副二本。其底稿则于择日进呈正本之前,史官会同司礼监官于太液池旁椒园焚毁,以示禁密。《野获编补遗》说:“实录成时,史臣俱会同焚稿于芭蕉园,人间并无底稿。”如此说来,今人更难见到《明实录》的底稿本了。
那么,辽宁省档案馆的《明实录》稿本是怎么来的呢?怎见得它是真的稿本呢?我们还是先听听编者的说明:
“这份档案,是九三胜利后,从伪满的皇宫中得到的。据说是罗振玉所藏。人们知道,民国年间,内阁大库发生八千麻袋档案被盗事件,罗氏把这些被盗的档案买出一部分,本件或即当时所购回者亦未可知。
世传明代实录,修撰时禁例很严,廷臣非参加修纂者,不得寓目。因此传抄的本子极少。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明实录,习见的有江苏国学图书馆的影印传抄本。罗氏所藏的这份实录,是洪武二十五年的一部分,系手写稿,字体苍劲,字里行间时有改动处。我们曾和江苏本对照,内容尚无大异,惟在字句上不同之处颇多。如丁卯日条内,江苏本为‘西平侯沐英卒。’兹本则为‘西平侯穆英病故。’江苏本‘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命英复姓,曰:不可使其乏嗣也。’兹本则为‘洪武元年,帝登基,旨穆英归原姓原族,不可无后。钦此。’总之,意同词异。从语言上看,兹本质朴纯厚,无斧凿痕。这个本子可能是初稿。”
说辽宁档案馆所藏《明实录》为初稿本的理由是:(1 )字里行间时有改动;(2)语言质朴,无雕琢痕迹;(3)摘录降旨文书等更接近原貌;(4)字体苍劲,为起草者手写,显得自然流畅。
那么,在焚稿制度甚严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将底稿的数十页保留下来呢?笔者认为这与初稿形成的年代及历史背景有关。我们将稿本与北京图书馆藏影印本加以对比,可以断定辽宁馆藏稿本是建文帝时所修《太祖实录》的稿本,在某些用词上与成祖时所修实录即流行于世的传抄本有明显的不同。比如稿本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壬寅日,“晋王朱刚、燕王朱禔、楚王朱珍、襄王朱博谨见。”成祖重修本皆改“燕王朱禔”为“今上”,由此一点也证明辽宁馆藏稿本必是建文帝首修《太祖实录》时的稿本。明朝统治者第一次修实录,制度必然不健全,加之建文帝统治只有四年,又发生明成祖推翻建文帝的“靖难之役”,战争整整打了四年,建文帝被打败,连皇帝都下落不明,何暇顾及实录的稿本。这可能是《太祖实录》的部分初稿保留下来的历史原因。
在确定了《明实录》稿本的真实可靠性之后,我们就可以分析“文档不明”的涵义了。
据史料分析,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刑部状告户部“文档不明”,要将下属官吏逮问之事估计是因户部对后湖黄册库档案的管理不善引发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是大造黄册之年,按照规定,全国各地所造黄册都要送到户部,然后转送到南京后湖集中保管。“(洪武)二十四年令各处布政使司及直隶府、州、县并各土司衙门所造黄册,俱送户部转送后湖收架。”后湖黄册库初次接收黄册,在统计和保管方面可能会发生混乱现象,造成赋税征收迟违的后果。后湖黄册库此时已造库房30间,每间库内置册架四座,每座分三层,上放木板,以置黄册。黄册又称文册,所谓“文档不明”之“文档”,就是“文册档”,是放在册架上的文册,据统计已达5300余册,“文档不明”可能是编号混乱;也可能是排架混乱;也可能是文册漏落钱谷数额,因史料不足,我们还不能说得很清楚。但既然说“文档不明”,显然是档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文书工作中的问题。不然不会冒出“文档”二字,此事因影响到赋税钱谷的征收,被刑部得知,刑部上奏皇帝,要拿有关官吏问罪。皇帝认为这是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改正就是了,只要不是故意隐匿户口,逃税漏税,就不必拿问。《太祖实录》的作者将此事记载其中,足见不是一桩小事。
初稿有“文档”二字,修成的实录或重修的实录却改动了。查北图影印本《明实录》,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刑部奏:近因户部案牍不清,令本部理之,其属官吏当逮问。上命:稽错者,令其厘正钱谷,非隐匿者勿问。”
改“文档不明”为“案牍不清”,将本已明朗的档案工作又隐入文书工作之中,为“档案”一词的溯源研究增加了困难。但是,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书稿档案维护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是值得庆幸,值得感谢的。
与“文档”一词相佐证的,还有“官档”一词,同样出现在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明代档案中,其中一条是:
“依议。又无袭次事:爱锡送马,病瘦革职;其袭次已尽,应销去官档。”
这是吏部奏报文书的摘要和钦批文字,不详年月,收录在《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第三部分第二十三节《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奏报拟办各事文稿摘要及钦批文件》中,这一节共收录55条文稿摘要,不少条文已残缺不全,也可能有些条文是清朝档案的残件混入其中,加以鉴别是对的,但不能一概全说成是清朝档案。笔者认为,“官档”是“袭官档”的简称。在上书收录的《义勇左卫、遵化、宁山等卫千户百户世袭清册》就是这种“袭官档”。册中所列袭官者一辈又一辈的姓名,相互之间的血缘关系,袭官时间等。凡后代因犯罪或无承袭之人,便写明“住支”,即停止支付薪俸,这便是“销去官档”。
明代的“文档”、“官档”等称谓含有明显的分类档册的意思,与以后清代的“上谕档”、“随手档”、“花名档”等等众多名称极为相似。
总之,明代“文档”、“官档”称谓的出现,为“档案”一词起源研究上推一个朝代提供了切实可靠的证据,是值得档案学界高度重视的。
五、再议《柳边纪略》
当我们考察了“架阁文字”中“若档”之义和明代出现的“文档”、“官档”之后,再来看《柳边纪略》中那段令人费解的话,似乎变得容易理解了。“外边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对于作者杨宾来说,什么是牌,什么是档,他脑子里的概念是很清楚的,不过随手写来而已。可以看出:“若牌故也”与“若档故也”,皆是从“义”上而言,而非从“名”上而言,为什么写满文字的木牌象“档”呢?行文之间已说得很明白:
(1)“存贮年久”。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这不仅从木牌的内容和时间看得出来,而且从发黄发灰的颜色也可看得清楚,它们不是刚形成的文书,而是年代久远的旧文书。由于还有查考的价值而没有被毁掉,以至于保留至今。这些木牌子与写在纸上的旧文书不是一样可以称为档案吗?
(2)“积累多”。这是从数量上说的。 数量浩繁是档案的一大特征。边外少纸,遇事,包括臣下向皇帝奏事,都用木签、木牌。经过长期积累,必然成千上万,不可胜记。这与关内官府堆积如山的档案,是一样的文化财富。我们且不可片面地想像边外的木牌很少,甚至只有挂在墙上像窗户上的几片木条一样零落稀疏,如果那样想,未免太简单化了。
(3)“贯皮条挂壁”。零散的木牌需要有整理的方法, 首先按内容分类,然后将一组一组的木牌用皮条或麻索串连起来。为了便于翻检,将其整齐地挂在墙上,一排一排的编号悬挂,甚是整齐,甚为方便。这与关内的纸质档案立卷编号排列在柜架上不是一个道理吗?
以上三点,完全可以概括杨宾这段文字的意思,十分明白,并不艰涩隐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杨宾将“档案”的涵义说得够清楚的了。以往学者之所以觉得难以理解,是因为不了解关内明王朝早已使用“文档”、“官档”这些概念,误认为“档”、“档子”、“档案”等是满人创造的生僻词,因此才挖空心思去研究它的“名”的来源,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义”在哪里,所以造成对《柳边纪略》的误解。
“名源于义”是各个名词形成的基本规律,“档案”一词也必然是这样。研究“档案”一词的起源是研究“档案”的本义及档案工作的专业性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若按此思路探索下去,一定可以有更多的发现。以笔者之见,明初的“文档”一词必是元朝人用语的沿袭,我们在元人和明人的著作与官府档案中,一定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说明“档案”一词的来源。我们期待着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新发现和新探索的出现。
注释:
(1)杨宾:《柳边纪略》,卷三。
(2)汪琬:《钝翁类稿》陕西提督李思忠墓志铭注。
(3)《汪钝翁本传》,见《钝翁文集》,卷首。
(4)方苏生:《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1935年。
(5)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 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
(6)李荣忠:《满汉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 载《档案学研究》,1994年,第3期。
(7)《明代辽东档案汇编》,970页,辽沈书社,1985年6月版。
(8)郭树银、杨继波:《“档案”一词考略》, 载《图书情报知识》,1984年,第4期。
(9)和宝荣:《“档案”一词始于元说质疑》, 载《档案工作》1986年,11期。
(10)《中国档案事业史》,2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32。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
(13)《明代辽东档案汇编》,1211页。
(14)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卷1。
(15)《明代辽东档案汇编》,1210页。
(16)万历《明会典》,卷42,《南京户部》。
(17)《明实录》,卷21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3172页。
(18)《明代辽东档案汇编》,1206页。
标签:档案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公文论文; 明朝论文; 周礼注疏论文; 明实录论文; 杨宾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