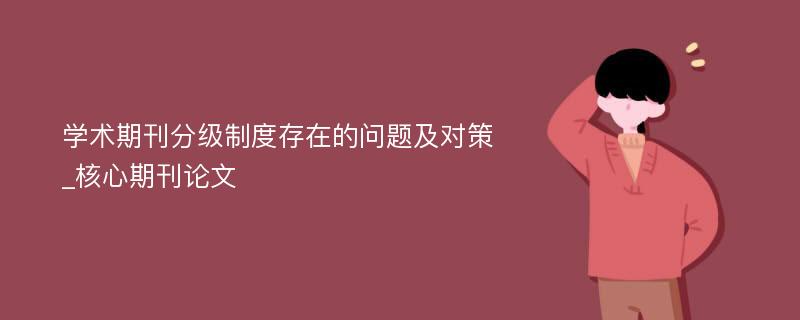
学术期刊分级制带来的问题与破解方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略论文,学术期刊论文,分级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3)07—0229—08
学术期刊作为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在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推动学术发展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有关期刊评价指标体系对学术期刊的分级,致使期刊出现了层级分化,它一方面对规范学术期刊正确办刊方向、促进优秀期刊的脱颖而出,具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期刊分级也犹如双刃剑,它对那些未被纳入核心类的期刊则产生了抑制作用,甚至还部分地制约了一般学术期刊的良性发展,致使其办刊面临的困难更大,挑战更多。要想真正地使学术期刊,尤其是一般期刊突破分级制带来的限制,一方面亟须改进和完善有关学术期刊的评价体制,另一方面需要使学术期刊真正地回归学术的根本点上,把学术期刊打造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
期刊作为刊发学术论文的重要平台,本来肩负着繁荣学术的重任,按理说不应该有一般期刊和特别期刊之分。但是,随着中国学术期刊和国际期刊的接轨,一些科研单位、大学图书馆或者学术评价中心,逐步地建立自己的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据此指标体系把期刊划分成为核心类来源期刊和一般期刊这样两个泾渭分明的期刊层级。
随着国内学术期刊和国际学术期刊发展的接轨,国外对学术期刊的评价方法也逐渐地被国内学术期刊评估中心引进,我国通过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期刊的评刊体系,逐渐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期刊评价机制。当前,它主要体现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来源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来源期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这三大评价指标体系。
客观地说,尽管中文核心期刊的评价指标体系和CSSCI来源期刊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全一致,两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对其作出优与劣的结论。但需要肯定的是,在中国学术期刊和国际学术期刊接轨的趋势下,中国能够不失时机地推出自己的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体系,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对学术期刊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使学术期刊反映和传播学术研究前沿成果的功能得以强化。虽然这两大评价指标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中文核心期刊评估滞后时间太长、评估周期太长,不能及时有效地反映学术期刊的最新发展面貌;南京大学的CSSCI来源期刊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者的局限,但又过分地凸显了“引文”这个数据,且这个“引文”数据又不是所有学术期刊的“引文”,而必须是刊发在已经成为CSSCI来源期刊上的“引文”,这就使得“来源期刊”和“非来源期刊”不是在同一平台上竞争。况且,“来源期刊”也会依恃其所获得的“特殊权力”,在与其他期刊关乎“你上我下”的竞争时,难以完全做到以学术为准绳。尽管如此,这些评价体系在我们探索的道路上毕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即便是需要调整,也已经具有了可以“涂改”和“修正”的“草图”。
尽管期刊评价机构曾再三地申明高校和科研机构不要把这个体系当作唯一评价论文的标准,但客观地说,各个高校在科研奖励、职称评定等排名时,却都将这些数据纳入到了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中。与此相对应,教育主管部门在测评高校的科研实力时,又依据这样的指标体系,尤其是根据CSSCI来源期刊的指标体系,对其所刊发的论文进行数量的统计,进而对期刊的档次[1]和大学的科研实力进行有效的排名。至于诸多的课题,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省社科项目,在课题中期检查和课题结题时,也都有刊发在CSSCI来源期刊上的论文的具体要求。这就使得学术期刊在国家体制的认同上已经出现了分化,并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中,逐渐地固化了其既有的层级,使那些进入了这些评价指标体系的学术期刊可以获得诸多的特权。
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标准中,由于其把期刊是否属于“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当作门槛,致使一般期刊无缘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这又进一步加大了一般期刊与核心期刊之间的距离。近几年,国家为了促进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开始把经费投向举步维艰的学术期刊,这本是一件推动学术发展、具有远见卓识的好举措,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的要求,它又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等名号作为前提条件,致使一般期刊连申请的资格也没有。那些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一般每年资助40万元,连续资助3年,如此下来,便是120万元。这样一笔“巨款”,对于一般期刊来说,可以说是十来年的办刊经费之和。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和一般学术期刊的竞争中,便如同“吃得膘肥体壮的马”和“饿得皮瘦毛长的马”之间的竞争。试想,那些没有“夜草”可吃的“一般之马”,不仅要赶上那些吃上“夜草”的“核心之马”,而且还要赶上之后再“反超”这些吃着“夜草”的“核心之马”,其困难自然是可想而知。
两极分化后的学术期刊,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其运行的基本情况将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按照正常情形来说,核心期刊因为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拥有了体制内的认同和推崇,也就自然获得更多优秀学者的认同;而这些学者,由于其本身在学术界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其所刊发的论文更容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就更可以作为权威性话语来加以引用。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转载类的期刊,自然也就容易关注这些处于学术前沿的学者所刊发的论文,从而使得其被转载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性。至于那些还没有累积起学术声誉的青年学者,则需要一个发现与培育的艰难过程,自然也需要被学界逐渐接纳和认同的漫长过程。如此一来,一般期刊要想摆脱业已形成的惯性作用而被学者认同,便陷入难以突破的悖论之中:期刊的档次越低,所获得的优质稿源就越少,就越难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越难和那些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核心期刊抗衡,自然也就越难进入“特权”期刊的行列。
一般情况下,在一场实力悬殊的不平等平台上的竞争,一般期刊要战胜核心期刊,其困难是巨大的。但是,背离这种一般情况也会偶尔发生,即某一核心期刊或者由于自身的期刊定位偏离了学术的轨道,并且在稿件质量的管理上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因为期刊没有遵循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要求,在提高学术质量上下功夫;或者是因为期刊追求暂时的经济效益,滥发多发稿件,致使办刊质量出现了大幅度下滑;或者是受关系稿的困扰,加上没有必要的制度作为“防洪墙”,而期刊的内部运行机制又无法及时进行纠错。否则的话,既有的这个“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基本法则是很难改变的,换句话说,这都是期刊自己打败了自己。如一些核心期刊,曾经具有相当美誉度,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法则,期刊把创收当作了目的,导致了发稿只注重数量的增加,而忽视了稿件质量的把关,论文越发越短,字号也大都成了小五号,排版密密麻麻的,进而使期刊办刊水准大幅下降,从而在新一轮评估中,被挤出了核心期刊的行列。但是,从全国几大核心期刊的评估结果来看,“败走滑铁卢”的核心期刊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期刊还是稳居核心期刊的行列。自然,那些能够晋升到核心期刊行列的“新科状元”也是少数。这种情形说明,期刊发展所遵循的基本规则还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期刊由分级而来的层级固化现象正在形成,期刊的“战国时代”正在远去,这既对一些核心期刊做大做强提供了历史机遇,更为一般期刊的发展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
总的来看,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对学者论文刊发学术期刊的特别推崇的动因还是来自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评价高校的标准体系。如在申请硕士点、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或者国家重点一级学科等方面的指标要求上,都特别突出了一些重要期刊的比重。如此一来,自然就使得那些一般期刊在这样的“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不仅难以和核心期刊相抗衡,使期刊分级成为难以规避的现象。
如果说过去在学术论文的测评上存在着某些模糊之处的话,那么,引入可以操作和掌控的量化标准,便可以从总体上测量出论文的实际社会影响力。一般说来,一篇论文能够产生社会影响力,自然会为学术界的同仁所关注,甚至其话题带有学术前沿性,这在转载和引用上都会有所体现。如某高校在对其学术研究的数据分析时,就清晰地显示了,那些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其所刊发的论文在转引和转载上都有较高的数据。“对中文数据库作者的发文总量、被引总频次和H指数进行分析,同属于发文总量前20、被引总频次前20和H指数排名前20的学者有11位学者”[2]。经调研,这11位学者和其在高校学术研究中的实际学术地位还是基本对称的。与此同时,在中国知网刊发的期刊论文中,不少论文的转载率和转引量是零。如果说高转载率和高转引量并不意味着高水平论文的话,那么,零转载率和转引量更不意味着论文的水平之高。客观的情形是,作者更关注的是如何使自己“生产”出来的学术论文顺利地刊发出来,进而满足体制对自己的评价指标。至于其转载和转引等指数,则不为学者所特别关注,尤其是转引,更没有引起学者的关注。个别学者甚至对自己过去发表的论文都早已遗忘了。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学者没有真正地把学术研究纳入到一个有机的传承链条中,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的学者没有意识到转载和转引之于学术论文的价值和意义。
期刊分级使得期刊评价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且这个相对客观的标准也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其对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扭转当下的学术功利化的不良倾向发挥了积极作用。期刊分级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期刊分级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期刊分级尽管存在着不够完美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定期刊分级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期刊分级有利于期刊循着尊重学术的轨迹发展,这对扭转当下的期刊注重刊发“短平快”的应景之文有显著的功效。在中国大学或者科研院所中,甚至是一些中小学等事业单位中,职称评定几乎是人们晋级最重要的途径,而职称评审体系又往往把发表的论文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这就导致了事业单位的大部分人,不管是从事领导工作,还是从事业务工作,不管是从事一般服务性的工作,还是从事教学工作,都将论文写作放在了首位,以至于出现了人人都在忙于写论文、然后再找人托人发论文的盛景。应该承认,大家都在搞科研,都在写论文,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但问题是,一些人写论文,不是因为自己在长期的科研过程中有了新的发现来写论文,而是因为职称需要才硬性地去写。在此情形下所写出来的论文,不是无病呻吟,就是东拼西凑。更有甚者,还有一些人请人AI写作,“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及其团队的研究统计发现,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约为1.8亿元;到2009年,其规模已膨胀5.5倍,论文买卖的销售额近10亿元。”[3](P.13)由此说来,正是职称晋升等需要,使得论文买卖泛滥成灾,这对从事写论文的作者而言,自然是一种极大的折磨,对社会资源而言,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与此同时,在职称的晋升中,其所看重的往往是论文的篇数和论文所刊发的期刊级别,因而大家为了能够完成指标,把论文的字数控制在五到七千字之间,页码控制在三四个页码之间,字号大都是小五号,这固然使期刊能够最大限度地刊发更多的学术论文,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刊发论文的机会。然而,不管期刊怎样竭尽全力地去刊发论文,就其供需关系来说,相对于如此浩浩荡荡的亟须刊发论文和晋级的“科研工作者”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这种被放大了的供需关系又为一些期刊收取“版面费”提供了机缘,进而使行情水涨船高,学术研究不再是以对学术研究本身为目的,而是演化为一种为完成工作目标和晋级的手段,使学术研究被极大地异化了。
其次,目前的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在客观上对期刊刊发论文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规范和制约作用。我们不管是否承认核心期刊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它客观上已经对期刊刊发论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一些把进入核心期刊为鹄的的学术期刊为了能够进入核心期刊的行列,开始在评价指标上和核心期刊的评估指标进行了必要的接轨。这样的对接,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促使许多期刊为了能够对接核心期刊的评价指标体系,从追求刊发论文的数量逐步转变为注重论文的质量。期刊的生命线是稿件质量而不是数量,期刊所发论文多少,与期刊的品牌建设没有必然的关联,它不是衡量期刊是否为名刊的标准,更不是衡量一个期刊主办方的科研水平的标准。因此,一些期刊从服务和服从品牌建设这个大局出发,其刊发的论文从注重“职称功能”向注重“社会功能”转变,通过刊发高质量的论文,达到提升学术期刊影响力的目的。在此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期刊是人文社会科学版的《上海大学学报》,该刊每期的载文量仅仅有12篇,一年下来六期只有72篇,一期杂志的页码在150个左右,每篇论文的页码都在十几个页码之上,其排版则与此追求相对应,每页共有37行,这和一般期刊的42—44行相比较,要稍少几行。如此策略,既是从载文量方面加以考量,也是从学术研究质量方面来考量——与其刊载一些“无关痛痒”的论文,还不如刊载一些能够代表学术前沿、具有真正学术份量的论文。当然,过分地凸显这一指标评价体系,并且一味地围绕着这一评价指标体系运转,而忽视期刊所承载的学术目的,也自然是不可取的。
再次,期刊分级对学者的学术论文生产具有潜在的规范制约作用。学者由于身在高校或者科研院所等体制中,其学术生产必然受制于体制的制约。一般说来,著名学者根本不需要那些一般期刊为其提供刊发论文的服务,缘于他们身在体制中,其所需要的是国家级的核心期刊,这些期刊在圈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试想,他们殚思竭虑写出的论文,如果刊发在一般学报,将来职称晋升作用不大,甚至连年终的考核都不计算(这在很多高校教师那里,称之为“工分”,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员”在生产队“磨洋工”来“挣工分”有相似之处)。由于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把核心期刊纳入到大学的学术排名和职称晋升、考核任期等指标上来,那就自然地如同高考作为学生的指挥棒一样,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的论文发表起着杠杆作用。这使得那些身在体制中的科研工作者,为了能够完成体制所设定的目标,把刊发论文的期刊层级当作极其重要的一个指标。学者们在投稿时便会先把稿件的质量分出一个三六九等来,然后把自己认为最好的稿件投给自己心仪已久的核心期刊,如果无法被采纳,再退而求其次。这就导致了优秀学者在撰写学术论文时,为了能够实现其社会效益和体制效能的最大化,把核心类的期刊当作了论文刊发的载体。如此一来,就使得核心期刊,具有了做大做强的机缘,这对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权威的核心期刊、对更有效地引导论文生产,其积极作用还是不可小觑的。
期刊分级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清除这种消极作用所带来的弊端,则可能会给核心期刊的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不管是具有学术创新性的论文,还是那些老生常谈的平庸之作,最后都被量化为几个冷冰冰的转载和转引的“数据”。我们在此不能说这些“数据”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但是,这样高涨的“数据”并不一定使学术期刊在国家学术创新体系中获得同步提升。纵观近几年中国学术期刊刊发的论文数量,我国早就成了学术论文“生产大国”,但是,我们却不是学术论文“生产强国”。在此,我们且不说自然科学类的论文在世界学术创新中的地位,单就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论文而言,真正对世界学术创新产生积极作用的论文到底有多少呢?哪些论文在业内产生了具有世界性的学术影响呢?在此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还会发现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现象,那就是在西方诸多的学术领域中,一些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著作或者学术论文,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能够穿越历史的时空,能够跨越空间的限制,直到今天,依然还能够一版再版,能够为后人再三诵读,依然具有非凡的学术影响力。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依然是我们几代学者学术阐释的对象和学术创新的根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因为隶属于主流意识形态范畴,具有特殊性的话,那么,像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所建构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像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样的学术专著,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学术著述,直到今天还被人们再三提及的历史专著,[4]我们实在是少之又少。我们所刊发的论文,不能说很多是职称论文、学位论文,但有很大一部分论文,并没有什么学术含金量,没有什么学术创新力,致使一些期刊上所刊发出来的论文,不要说是过几百年,上百年,几十年,甚至是几年就已经过时了,就成了历史的古董。更有甚者,有些论文从刊发之日起,就没有几个读者去阅读,就已经失却了生命力。如此情形说明:我们的学术期刊,不管是那些核心类的期刊,还是那些非核心类的一般期刊,其所刊发的学术论文真正地能够获得世界同行认同和推崇的,实在是太少了;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其所刊发的学术论文,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和实践的检验,成为累积起中国学术大厦的栋梁之材的,也实在是太少了。由此说来,期刊分级在具有一些积极的作用的同时,也有不容我们忽视的消极作用。
首先,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标志着学术期刊自由竞争的战国时代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以垄断和霸权为代表的期刊格局的形成。这意味着那些在期刊分级中成为核心的来源期刊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如此一来,期刊就分为一般期刊和核心期刊。核心期刊依据着自身被期刊评价机制所赋予的特别的权力,相对于一般期刊占据了更多的资源,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受到了学者更多的推崇。这使得学术生产和消费出现了一边倒的态势:优秀学者的优秀稿件受此影响,大都流入到了这些核心期刊中;而那些一般期刊则相反,其所流入的稿件,大多为一般学者的普通稿件,因而出现了两极分化,使得本来处于同一平台之上的期刊竞争,已经不再是处于一个基点上。
其次,那些被排斥在评价指标体系外的一般期刊,由于在“鲤鱼”自由“跳龙门”时,错过了最佳时机,致使其发展受到了核心期刊的挤压,也妨碍了学术研究成果更为顺畅地刊发——因为很多学者把学术成果刊发在那些核心期刊上。由于核心期刊的数量是有限的,其可以刊发的论文数量也是有限的,这使得核心期刊的刊发周期加长;相反,那些一般期刊倒是可以敞开大门,期待着刊发这些具有学术创新性的成果,但由于刊发在一般期刊上,作者就无法完成体制所设定的工作目标。这样一来,作者宁愿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滞后刊发,也不会轻易地刊发在一般期刊上,从而使得其时效性大打折扣,使学术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大大下降。这势必造成一般期刊被核心期刊挤压的态势。此种情形恰如生长于参天大树下的幼苗,所有的阳光都被大树垄断了,所有的养分都被大树吸收了,幼苗能够“苟延残喘”已实属不易,更不用奢谈成长为未来的参天大树了。
再次,那些被纳入到了核心行列的期刊,则会凭借其所拥有的“特殊权力”,在客观上对一般期刊的发展排斥乃至遮蔽,进而使得垄断成为可能。垄断既会妨碍了核心期刊的发展,也挤压了一般期刊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健康的市场要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提供平等的条件和机会。为此,很多主管部门对那些带有垄断性的企业,提出反垄断的诉讼,为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平等的平台。同样,在学术期刊中,那些拥有了“特殊权力”的核心期刊,恰如那些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一样,对弱小者不仅没有平等对待,反而利用自身所具有的优势,通过不正当竞争获得更高的指标。如此循环往复,那些处在这个“权力”圈子之外的一般期刊,便很难获得进入这个“特权俱乐部”的“门票”——因为能否进入这个俱乐部的“门票”,不在一般期刊手中,而在那些核心期刊手中。这种情形在个别核心期刊那里,甚至发展到了对与自己处于同级竞争行列的期刊,不管其是否存在着恶意引用的情形,都一律采取打压的措施。如此竞争,就不再是高擎学术的大纛,而是为“引用”而引用,为“数据”而数据了;个别一般学术期刊,又为了能够晋级核心期刊之列,采取不管需要与否,推荐给作者,期冀作者加以引用,这种混乱局面的出现,既是缘于评价指标体系这一“指挥棒”的导引作用,也缘于学术期刊唯“数据”是举的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如此情形,如果不从评价机制上加以调整,学术评价中的乱象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
如果国家的学术评价体制不发生改变,期刊要追求所谓的独立学术品格仍将存在难以突破的瓶颈。毕竟,学术期刊大都是体制下的产物,它或者搭乘体制的快车道,举体制之力,一切为了进入核心期刊这个“俱乐部”服务,甚至为此不惜投入巨资,有的连学术期刊的名字都改了,把那些限定在学报之前的普通的院校名字,更换为一个更“玄乎”一点的名字。显然,这样的一些现象,尽管问题出在高校或者科研院所那里,但根子还是出在国家体制上。如果学术期刊的分级没有把这样一些核心问题纳入到更富有效能的评价指标体系中,那所谓的核心期刊也罢,非核心期刊也罢,都将会沦为“为稻粱谋”,这和促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繁荣,相去自然甚远。
期刊良好的学术声誉是一个漫长的累积过程,这与“立竿见影”不同,其具有一个相当长的滞后期。也就是说,从“立杆”到“见影”,一般滞后三到五年乃至七年的时间间隔。不管怎样,作为一个以学术为其立足之本的学术期刊,在已经出现了“分化”和“固化”期刊层级的情况下,应当努力地去找寻到一般期刊的发展之路,进而通过艰难的跋涉,完成期刊从一般期刊到优秀期刊的提升的重要使命。
目前,学术期刊都把刊发具有学术前沿性的学术论文当作破解期刊困境的方式,尤其是通过刊发那些已经累积了学术盛名的学界名流的稿件,从而达到提高期刊社会影响力的目的,而期刊的提携和发现学术新人的功能则被弱化了。从学术创新的历史来看,那些具有深远影响的论文,并不一定是在作者累积了学术盛名之后才写出来的论文,而往往是在其学术发展的成长期所闪现的思想火花的集结。像那些在科学史上已经留下了深深足迹的学界巨擘,他们的学术创新能力往往是在其未成名之前的学术研究成果,如出生于1873年的梁启超,在30岁之前已经赢得了一世的盛名,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在28岁便已经完成了《江村经济》书稿,从而登上了社会学的顶峰,对此,费孝通的指导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译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5]像他们这样一些著名的学者,很多是在青年时期便已经把其创造的能力提升到了他们一生的最高值,至于在随后的时光里,他们所谓的学术创新往往都是在完善和发展这种学说,难以呈现出青年时学术创新的迅猛态势。因此,作为一般学术期刊,要破解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所带来的困窘,一要倚重学界那些已经累积起了盛名的名人,二要致力于发掘和培育学术新人,由此使学术期刊依托这些学者,支撑起期刊发展的广阔天空。
期刊把刊发名人的学术论文当作期刊提升的关键,其所看重的是名人作为权威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一般学者的话语权。对于话语权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进行充分的阐释。过去,我们常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或者是说,在学术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其实,这样的一些命题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它们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我们在承认这些命题时,不要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与人的话语权不平等混淆起来。平等的人所具有的话语权的权重是自从有了社会以来就没有绝对平等的。一般说来,一个著名的学者,经过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历练,累积起了巨大的学术背景,再加上他们本身参与了历史的进程,所以他们话语的权重就比一般人话语的权重要重得多。况且,他们所说出的“话语”是奠定在以前话语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其话语有前面的话语作为铺垫和累积,并且还获得了以前的话语支撑,因此,其话语本身就不再是简单的自我的内容之和,而是与前面的话语累积起来,形成了一个话语的倍增。因此,一个人的“话语”越是具有前面雄厚的话语基础作为铺垫,其“话语权”就会越重,就越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越容易被接受者所推崇和接纳。
从接受的角度来看,接受者在接受之前就对权威话语已经形成的较高信任度。接受者由于有以前的经验作为前视阈,以至于接受者在接受的过程中即便没有经过咀嚼也可能囫囵吞枣地接受,或者是先接受了再进行理解——显然,这样的一种接受,其实际结果往往是先假设了对方权威话语的真理性和先验的正确性,然后再以此来矫正自我的认识,修正自我的认识,以至于对方的话语本身是错误的,我们也不会去怀疑其错误,而是先验地认为自己的认知是错误的,而权威话语是不会有错误的。像那些发生在历史上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像那些所谓的“一句顶一万句”,其实质就是对权威话语的接受已经在思维上形成了一种定势。因此,我们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时,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前提,即平等的是“话语”,但不是“话语”的“权重”。话语的权重不会平等——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如果我们认为人人的话语权都是平等的话,又哪来的权威话语?
权威话语之所以能够产生出如此巨大的效能,关键点在于权威本身在这个社会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那些占据着核心权力或者是重要权力的人,其话语本身,就不再仅仅是自我话语的表达,而是自我话语和权力话语的结合体,甚至有些话语本身就是代表着权力体系发出的话语,这样的话,其话语就不再仅仅是代表着个体的话语,而是代表着政党、政府具有主导型、政策性和前瞻性的话语,这些话语又往往会通过一定的权力体系贯彻落实到每一层级中,制约和规范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如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3期撰写的《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一文,在中国知网的下载量达到了9432次,转引量达到了738篇次;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10期撰写的《新时期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一文,在中国知网的下载量达到了2481次,转引量达到了84篇次;1989年,江泽民同志在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时撰写的《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一文,刊登在同年的第3期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其在中国知网的下载量达到了345次,转引量达到了6篇次。[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江泽民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便高瞻远瞩,诚如有学者就其《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一文指出的那样:“文中的许多数据和资料是一般研究人员很难得到的,并且江所具有的战略眼光,也是许多学术论文难以企及的。”“江泽民论文的发表使朝野上下关于中国能源战略的大讨论再次升温。……鉴于江的特殊身份,这篇论文引发的波澜显然不仅局限于学术界,它在当今中国所处的能源局势中传达着非同寻常的意义。”[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江泽民同志的学术论文,正是凭借着其自身所具有的战略眼光,使得其论文超越了一般学术论文的价值,进而在转引量上达到了一般学术论文无法望其项背的高度。这恰是
权威话语与权威相结合的特点,使其在话语的传播中获得了先验的真理性优势,具有了在论证上的无可质疑性。权威话语之所以在一些学者的论述中再三被“引用”,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作者想借助这样的权威话语,使得自己的论证带有某种必然性和真理性,为自我的论证找到合法性存在根据,从而达到了自我分析论证与权威话语捆绑在一起的效能,这对“挣得”自我的合法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特点,使得人们在学术论文的撰写中,经常地把一些权威话语当作自己的挡箭牌,进而为自己的论证增加了一些话语的权重。而与此相反的是,那些不是权威的话语,或者是一般学者的话语,由于其缺少这样的一种历史累积,致使其话语的权重无法获得彰显,而对此论断的引用就难以起到“以一当十”、“以一敌百”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还会出现削弱其论证力量的反作用。因为,当读者在阅读接受的过程中,看到作者引用这样一些没有“名气”的“非权威话语”,会感到其学术传承的链条不是最前沿的,而是一些处在边缘上的自我言说。这样的自我言说,使读者认为作者所进行的研究,没有能够很好地和学术前沿进行接轨,而那些所谓的学术前沿,则往往是处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领军式人物所达到的高度为其最高值的,而那些处在研究起步阶段的学术无名之辈,则难以引起阅读者的高度重视,尽管这样的一些无名之辈的见解并不见得就没有什么真理性——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过的那样,其学术论文具有真理性和先验性,与其学术研究中的话语具有一定的权重,是两码事。也许,随着时光的流逝,以及学者的自我学术盛名的累积,其会逐渐地从边缘走向中心,但是,在其走向中心之前,其话语的权重,是难以承载起如此之重的学术含量的。因此,这样的一些话语便无法具有那种权威话语的力度。
学术期刊的发展倚重学界的名人,并不意味着就要排斥和打压学术新人。实际上,今日的许多学界名人在昨日也是学界新人,甚至在某一阶段还是默默无闻的平常之辈。一般说来,发现和培养千里马,远比骑在千里马上自由奔驰要艰涩得多。但是,一个时代的学术要想获得发展,如果没有必要的代际传承是不行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发现和培养学术新人,既是学术传承和学术提升的需要,也是期刊近期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需要。从近期来看,学术期刊对学术新人的扶持,对新人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远期来看,学术期刊对学术新人的提携,又为期刊的自身健康发展提供了可以依托的新生力量。毕竟,学术的代际传承规律告诉我们,今日的学界新人,也许就是明日的学界贤达——假设学术期刊在这些学界新人需要提携的时候,对他们置之刊后,那么,等到他们“功成名就”时,再请他们为期刊“增光添彩”,那自然是很难的。由此说来,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学术期刊,一定要处理好刊发学界名人名稿和提携学术新人新作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期刊能够发现和提携学术新人,就意味着赢得了未来期刊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的来说,我们的一些学术评价中心把国外的先进评刊方法引进过来,并逐渐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期刊评价体制,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是有效果的。从宏观的方面来审视期刊的有关评价指标体系,在当下的中国,不管是北京大学的中文核心期刊还是南京大学的CSSCI期刊,都大体上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的总体态势。当然,如果说这些数据也存在着不科学不公正的话,那也仅是一个如何完善的问题,在当下的情况下,是绝难去推翻这样一个已经进入了体制的指标体系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办期刊,正是戴着体制的枷锁跳舞,我们所能做的是,如何最大地规避枷锁的束缚,通过更加有效的方式,将期刊的枷锁转化为期刊的动能,从而使期刊从边缘走向中心,让期刊从一般期刊跃升到核心期刊的行列中,进而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尽绵薄之力。
